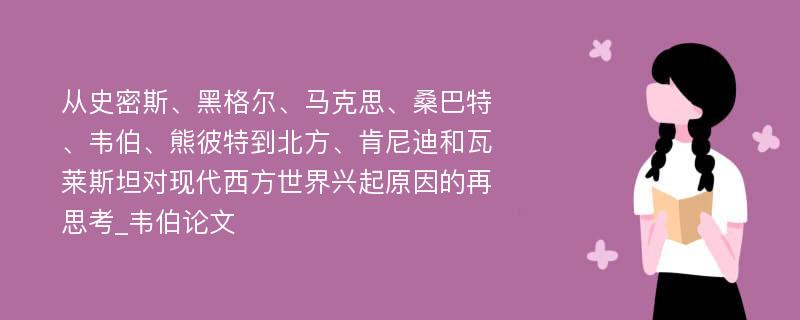
近代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再思考(上)——从斯密、黑格尔、马克思、桑巴特、韦伯、熊彼特到诺思、肯尼迪和华勒斯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黑格尔论文,肯尼迪论文,韦伯论文,马克思论文,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7)01-0082-07
近代世界历史上的“欧洲奇迹”,或者说西方世界在近代的兴起,已是一个世人皆知的历史史实。然而,对西方世界近代兴起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原因,学术界至今仍然众说纷纭、歧见迭出。综观西方学术诸家对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解说,可以发现,在这个问题上,诸多歧见中常有相通之处,而类似的见解中又有各种各样的差异。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希望打破学科之间的藩篱,为这个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提供一个综合的理论图景,并期望从人类近现代思想史上诸家对近代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理论反思中,解读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性法则,从而对准确把握中国现今的发展模式、体制格局以及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道路,产生一定的助益。
一、西方古典学者对近代西方世界兴起的理论反思:分工、市场深化与经济增长
在最近的两篇文章中①,笔者依照对经济增长的斯密动力机制(the Smithian Dynamics)的理论解释——并从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理论的视角来理解斯密动力——指出,近代西方世界的经济起飞,只不过是市场自发扩展秩序不断冲破欧洲各地的各种各样的布罗代尔钟罩,在一个国家疆域内以至在整个西方世界不断扩展开来的一个外在表现和历史结果。由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理论与著作是在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和大英帝国崛起之前形成及出版的,以至于我们似乎可以不甚恰当地把斯密的市场经济扩展秩序理论的出现,比喻为西方世界兴起之黎明前的报晓晨鸡。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样说低估了斯密市场经济秩序理论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历史的、理论的和现实的意义。其实恰恰相反,笔者最近的一些研究实际上旨在说明,人类社会绝大多数国家的近现代经济增长,尤其是西欧诸国在近代的兴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斯密社会经济理论的一个现实展示。从近代思想史发展的脉络来看,亚当·斯密的经济社会理论不仅影响了英国和欧洲各国的经济学家与政府政策的决策者,也影响了包括像康德和黑格尔这样的思辨哲学家。譬如,受斯密、萨伊(John B·Say)、李嘉图(David Ricardo)等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影响,黑格尔曾在《法哲学原理》中对劳动分工与机械化的关系做了一些思辨哲学的论述。黑格尔指出,“劳动的普遍和客观方面在于其抽象化过程,抽象化引致手段和需要的细致化,从而也引致生产的专业化,并产生了劳动分工。通过劳动分工.个人的工作变得简单了,以至于他自己的技能在抽象劳动中提高了,他的产量也增加了。同时,技能和手段的抽象化,使得人类为满足他们需要的互相依赖和互惠往来成为一种完全的必然性。加之,生产的抽象化使得劳动越来越机械化,以至于使人本身能够站在旁边,让一台机器来代替他工作。”[1](§198)基于他对当时西欧诸国的市场扩展、分工深化、技术进步、税收和国家财富的不断增加、海外市场不断拓展以及不断寻找新的殖民地这种社会内部诸因素关联动态的现实观察,黑格尔非常明确地指出:“通过冒险而追求利润,产业也同时提高了自身而超越其上。它不再固定在一定的土地上,也不受限于贪图享受和满足欲望的市民生活圈子之中,起而代之的是流动性、危险和破坏等因素。此外,通过这种强大的沟通媒介,产业本身也带来了与遥远国家的交易,以及制定契约的法律关系;同时,贸易又是最强大的文化沟通手段(Bilungsmittel)和渠道,商业通过它获得了世界的意义。[1](§247)这样一来,黑格尔就把企业家对利润的追求、市场交易、市民生活、商业贸易这些经济活动,以及西方诸国的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过程,诠释成了他那“绝对精神”在历史发展中的“世界的意义”。当时的欧洲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动态发展的情形?黑格尔认为,其原因是“当市民社会的活动不再受限时,它内部就蕴生了自身的人口和产业的扩张。一方面,通过人们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人们之间的合作关系(Zusanmmenhang)的普遍化,以及伴随着满足人们需要的手段被发明出来以及满足其方式的普遍化,财富的积累增长了,——因为这种双重的普遍性可以产生最大的利润;另一方面,特殊劳动的细分(Vereinzelung)和限制也加强了,与之相伴,束缚于这种劳动的阶级的依赖性和需求也愈益增长。”[1](§243)这里,黑格尔显然从其思辨哲学的视角,对18世纪之后西方世界内部经济动态发展的内在机制,做了一些他自己的解释,并提出了一些个人的理论猜测。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作为一位思辨哲学家,黑格尔不但对近代西方兴起的动态情形做了上述描述,而且对人们利己心的发挥与其外在制度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做了一定的分析。譬如,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曾指出:“利己的目的,就在它的受普遍性制约的现实中建立起在一切方面互相依赖的制度。个人的生活和福利以及他的权利的定在(Dasein),都同众人的生活、福利和权利交织在一起,它们只能建立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之上,同时,也只有在这种联系中才是现实的和可靠的。这种制度首先可以被看成是外在的国家,即必需的和理智的国家。”[1](§183)
从历史上来看,黑格尔处于比斯密稍晚的西方诸国工业革命刚刚萌发的初期。如果说此时黑格尔尚未能够自觉地解释西方世界兴起的历史原因的话,那么,处于近代科技和工业革命勃兴以及西方诸国经济起飞大潮中的马克思则在许多地方有意识地这样做了。可能正是因为马克思生活在工业和科技革命大潮中,致使他在许多地方讨论了技术革命,尤其是大工业生产方式在西方世界兴起以及西方诸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结果,后人常常把马克思的经济社会动态发展理论的核心简单地归结为“生产力(技术水平及其能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理论程式,甚至把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归结为技术决定论。其实,这是对马克思经济社会理论的一种莫大的误解②。
马克思究竟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早在1847年,生活在西方工业革命和经济起飞年代的马克思便观察到了这样一个现象:“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时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2](P256)那么,资产阶级运用什么样的符咒在短短的时间里呼唤出了如此巨大的经济增长以及大工业和科技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并未作回答。但在此之前,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提出过分工和自由竞争是大工业机械化生产与科技革命的主要动力源泉的思想,并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明确提出了“自由贸易扩大了生产力”的断语[2](p66)。马克思的这些判断,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见解,以及当代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派甚至哈耶克的市场自发—扩展秩序理论,在精神上应该说均是殊途同归的。那么,进一步的问题则是,什么力量推动市场分工、自由竞争以及机器的采用,从而导致近代大工业生产的产生?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我们还没有发现现成的答案。直到1867年,马克思才在《资本论》第1卷中好像有意无意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马克思说:“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为只是在这个不断更新的运动中才有价值增殖。因此,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作为这一运动的有意识的承担者……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是谋求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3](P175-177)。在另一些地方,马克思又指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就是增殖自身”[3](P260)。在这一市场经济扩展的内在动机的支配和推动下,市场的分工和协作就出现了:“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协调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3](P367-368)。另外,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在《资本论》第1卷第12章《分工和工场手工业》中,马克思非常明确地指出:“在工场内部的分工中预先的、有计划起作用的规则,在社会内部的分工中只是在事后作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自然必然性在起作用,这种自然必然性可以在市场价格的晴雨表中觉察出来,并克服着商品生产者的无规则的任意行动”[3](P394)。现在看来,马克思的这一见解,与其之前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市场运行原理,以及其后哈耶克在“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对市场价格机制的理论解释,在精神上是相通和一致的。
沿着工场分工和社会分工发展的思路,马克思达到了他对近代市场经济兴起的动力机制的如下理解:“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狂热地追求着价值的增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的基础”[3](P649)。
至此,我们可以大致把握马克思本人对近代西方世界兴起的内在动力机制的理解了:资本主义企业家对利润的无限制、无餍足的追求,推动着企业家去不断地进行企业内部和市场的分工,并不断发现新的生产方法,发明和使用新的技术及机器,并不断拓展国内市场和进行国际贸易。正如马克思所言:“一旦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基础(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奠定下来,在积累过程中就一定会出现一个时刻,那时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成为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杠杆”[3](P628)。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本人不但洞悉出资本主义企业家对利润贪无餍足的追求是现代西方市场经济动态发展的一个强有力的杠杆,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把西方世界的兴起归结为制度因素。可能正是辨识出了这一点,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的日文版的“绪言”中曾指出:“马克思之所以有别于同时代或前代的经济学家,正是因为他认为经济发展的特定过程是经济制度本身所产生的这一看法。……正是因为这一点,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才又都回到他这里来,尽管他们可能发现他有许多可待批评商榷之处”[4](P2)。
二、从桑巴特、韦伯到熊彼特:企业家精神与西方世界的兴起
受马克思的影响,作为一位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的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桑巴特 (Wemer Sombart,1863-1941)曾对近代西方兴起的原因做了许多探讨③,并对许多历史问题具有其独到见解。譬如,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桑巴特曾明确指出:“不管从哪方面说,有一点是公认的:奢侈促进了当时将要形成的经济形式,即资本主义的发展。”[5](P150)在其后的论述中,桑巴特又进一步强调说:“奢侈从许多方面推动过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比如,贵族的财产主要以债务的形式转移到资产阶级手中,在这一过程中,奢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在这种联系中,我们惟一感兴趣的是奢侈创造市场的功能。”[5](P154-155)接着,桑巴特从奢侈与贸易(包括批发业和零售业)、贸易与农业、奢侈与工业等方面的史实做了分析,并得出结论说:“于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奢侈,它本身是非法情爱的一个嫡出的孩子,是它生出了资本主义”[5](P215)。除了这类较为独到的见解外,桑巴特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在于,他较早地从企业家精神来探讨现代市场经济的扩展或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譬如,在《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桑巴特提出了“企业家精神”这一概念,认为这是“一种勇武的精神”,“一种不安静和不疲倦的精神”。这种精神“打破了那些建立在安逸自足的、自保均衡的、静止的、封建手工业的满足需要的经济的限制,并将人们驱入营利经济的漩涡中”[6](P212-215)。桑巴特还指出,如果说“企业家精神”在于“征服与营利”,那么,“市民精神”则在于“秩序与保存”,而后者的现实表现则在于“勤勉、节制、节约、节俭和守约”。根据以上两点,桑巴特说:“我们把那种由企业的精神和市民的精神所组成的一个统一的整体心态称作为资本主义精神。”[6](P215)桑巴特还认为,这种精神创造出了近代资本主义,因而可以认为,“资本主义是由欧洲精神的深处生发出来的”。之后,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见解:“在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所有近代文化中的最基本要素之一,就是建立在天职(the calling)理念基础之上的理性行为,而这种理性行为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这是本书所力图申明的观点”[7](P68)。尽管桑巴特与韦伯同样强调企业家的资本主义精神在西方世界近代兴起中的重要作用,但在这种精神的宗教起源上却与韦伯有着重大的理论分歧。正如我们在下面将要讨论的那样,韦伯强调新教伦理——尤其是加尔文主义和英国清教教义——在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形成中的原生作用;但桑巴特却认为清教教义一直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观的对立物。桑巴特甚至“考证”说:“清教教义的鼓吹者们完全反对所有发财致富的行为”;“清教教义极度谴责自由竞争”;“清教教义几乎不鼓励人们从事有长远打算的具有冒险性的事业”;“在加尔文教控制的地区,教会是明确敌视资本主义的……”在否定了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联系之后,桑巴特试图把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家精神与犹太教教义联系起来。桑巴特认为,资本主义精神主要有下列因素培养而成:犹太教的理性主义观点与条文主义,以及犹太教宗教领袖的商业精神,等等。桑巴特还认为,没有现代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永远也不可能建立起来,但远在16世纪之前,在欧洲就蕴成了资本主义企业家精神,其中,犹太教的教义和信仰最早在这种精神形成中发挥了作用。
我们再来讨论马科斯·韦伯的观点。与马克思相比,同样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企业家的功能和作用来探察近代工业革命与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但韦伯主要不是从资本家无限追求利润和企业扩张的增值冲动来看待问题,而是从正面强调企业家精神对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促动作用。上文已指出,韦伯与桑巴特的看法有很大差异。譬如,韦伯是从西方基督教文化精神——尤其是新教伦理——来省察其资本主义精神动力源的。至于哪种观点更接近于历史事实,我们今天已经很难判断。但是,通过介绍桑巴特的观点后,我们至少对韦伯的一些著名观点不再盲信了。从桑巴特与韦伯的一些尖锐对立的观点中,至少可以确知一点,资本主义精神——或言企业家精神——确实在近现代西方世界兴起中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至于这种作用到底是从斯密眼中所见的那种人类喜欢交易和交换的禀好转化生成而来,还是从桑巴特和韦伯所见的那种宗教教义精神中衍生出来,则可以另当别论了。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名著中,韦伯曾指出,“如果你问他们(指那些充满资本主义精神的企业家——引者注)自己永无止境的活动的意义何在,他们为什么不能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永不感到餍足,并从而对任何纯粹世俗的人生观如此无动于衷,他们可能回答(如果他们知道答案的话)道:‘为了要供养我的孩子和后代子孙。’但是这样的动机并非他们所独有,对于传统人士来说也是如此。更精确地说,或者更简单说来,做生意和不停地工作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了。实际上,这是唯一可能的动机。但同时从个人的幸福观来看,这种生活是非理性的:人为了他的生意而存在,而不是为了人的存在而经营生意”[7](P70)。从这一点出发,韦伯发现,西方世界的兴起,并不是如后来的弗兰克在《重新定位: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一书中所认为的那样,是由于“源源不断用于工业投资的新货币引起的”,“而是由于这种新的精神,即资本主义精神已经开始发生作用了”[7](P68)。由此,韦伯深刻指出:“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在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数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7](P68-69)韦伯还举例说,不管在世界的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所需要的资本和货币,来用作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换句话说,不是有了充足的货币和资本,才会生发出资本主义活动,而是一旦创造财富的资本主义企业家精神具备了,他们会创造货币和资本④。
那么,什么是这种作为近现代市场经济扩展的永动机的“资本主义精神”?根据桑巴特在《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对“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解⑤,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确实等同于通过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企业来追逐利润,并不断产生新的利润”[7](P17)。在对导致近代西方世界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的资本主义精神有了这样的理解后,韦伯提出,尽管由私人企业家经营,利用资本来赢利和不断购买生产资料来生产和出售产品这种“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capitalistic enterprises)在传统社会中就存在,但是,只有当这种在资本主义精神的不断重复发挥和对世界日益增强的征服中,才导致了近代西方世界的兴起。韦伯还认为,尽管企业的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与企业家精神并非互相依存,但二者确实一般处于“某种互相适应的关系”。韦伯接着指出,“这一点已经为历史史实所证明:一方面上述心态在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中找到了它最为合适的表达;另一方面,企业又从资本主义精神那里汲取了最适合的动力”[7](P64)。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一再指出,在西方国家,人们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工商业界的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大都是新教徒[7](P47)。由此,韦伯得出结论说,新教徒的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导致资本积累:“人屈从于自己的财产,就像一个顺从的管家,或像一部获利的机器,这种天职观念在他的心目中占据一个很重的地位。假如这种禁欲主义的生活态度经得住考验,那么财产越多,为了上帝的荣耀而保住这笔财产,并竭尽全力而增加的这种责任感就越重。这种生活的根源,如同资本主义精神的许多方面一样……是在禁欲主义的新教伦理中找到了其坚实基础的。这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已是显而易见的了”[7](P170)。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韦伯一再强调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基督新教伦理——即禁欲主义的节俭和为上帝积累财富的天职责任感——的内在关系,但韦伯绝非是一个宗教文化决定论者。相反,他曾明确指出,“我们根本不打算坚持这样一种愚蠢的教条主义观点,即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仅仅是宗教改革的某些影响的结果,或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制(economic system)是宗教改革的创造物。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商业组织的某些重要形式在宗教改革前就已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这种观点的有力驳斥。相反,我们只是希望弄清宗教力量是否影响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以及其在全世界量的传播。”[7](P91)
基于他对西方世界兴起初期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这种相互关系及其二者对经济发展影响的这种清醒认识,韦伯还探讨了资本主义精神与种种经济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我们的个人主义的政治的、法律的和经济的制度(institutions),具有为我们的经济秩序所独有的组织形式和一般结构。……在我们的制度下,资本主义精神是可以纯粹被理解为一种适应性的结果。资本主义体制迫切需要人们投身于赚钱的事业。这种对物质财富的态度则完全适应这一体制,并且与为生存而进行经济斗争中的条件密切相关。”[7](P72)
沿着这一思路,韦伯将西方近现代市场经济秩序与西方近代法律制度的形成和衍化过程联系了起来,他发现“近代理性资本主义不仅需要生产的技术手段,而且需要可靠的法律制度以及依照正式规则办事的行政机构。没有后一条件,冒险性的和投机性的贸易资本主义以及各种各样的由政治决定的资本主义可能存在,但绝不可能有由个人创办的、具有固定资本以及稳定核算的理性企业”[7](P25)。接着,韦伯还指出,在近代历史上,这样的法律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只有在西欧社会中才处于一种相对来说合法的和形式上完善的状态。此外,从发生学上来追问,为什么只有在近代西欧诸社会中才产生了这样的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法律制度和行政体制?或者说,这种独特的法律制度和司法精神是从何而来?沿着这一思路,韦伯认识到,尽管资本主义企业家对其利益的追求反过来有助于一个受过理性的法律训练的法律界阶层在司法和行政中占据支配地位,并为之铺平了道路,但是,资本主义利益本身绝非独自促成了这一点,甚至也没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因为这些利益自身并没有创造出那种法律”[7](P25)。为此,韦伯接着问到:“为什么资本主义利益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作出同样的事情呢?为什么印度和中国的科学、艺术、政治与经济的发展没有导致它们走向西方所独有的这条理性化道路呢?”[7](P25)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促成并导致了近代西方社会产生出这种独特的理性化的法律和行政制度呢?韦伯在这部著作中好像对此悬而未答⑥。
在桑巴特和韦伯之后,经济学家熊彼特也特别强调企业家在西方近现代市场经济兴起中的作用,但与前两人不同的是,熊彼特较多地从经济学分析的视角观察和论述问题。在熊彼特看来,“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与方法,它不仅从来不是、而且永远不可能是静止不变的”。借用生物学上的一个术语,熊彼特把近代市场经济的“不断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地破坏旧的和不断创造新的结构”这种过程,称为“产业突变”。熊彼特指出,“这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事实,应该特别予以注意”。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熊彼特认为,“创新”(innovation)、“新的组合”、“经济发展”,这些都是近现代市场经济秩序的本质特征[8](P82-83)。根据英国古典经济学家萨伊 (John B.Say)的“企业家的职能是把生产要素带到一起将并之组合起来”[9](P76)的见解,熊彼特在许多地方一再指出,所谓“资本”,就是企业家为了实现“新组合”且以“把各项生产要素转向新用途”、“把生产引向新方向”的一种“杠杆”和“控制手段”,因此,资本的主要社会功能则在于为企业家“创新”提供必要的条件和手段[9](P116)。
那么,什么是“创新”呢?在熊彼特看来,“创新”不是一个技术概念,而是一个经济概念。它是指在经济中引入某种新的东西,与技术发明(invention)不是一回事。一种发明,只有当它被应用于经济活动时才会成为“创新”。熊彼特还具体解释到,“创新”是指“企业家对生产要素所作的新的组合”[9](P66),它具体包括以下五种情况:(1)引入一种新的产品,或改进某种产品的质量;(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一个新的市场;(4)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应来源;(5)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例如,建立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熊彼特不仅从“创新”理论视角来解释商业周期的变动,而且以这个概念来解释市场经济增长的动力、过程和目的。在熊彼特看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是通过经济周期来实现的,即从旧的均衡到新的均衡,并经历经济高涨到经济收缩的各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经济总量虽然有起有落,但长期趋势却是不断扩张的,产品的结构也是不断变化而趋于多样化的。从旧的均衡到新的均衡,正是经济增长的实际过程,而在这整个过程中,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创新者”,即有远见、有组织才能和敢于冒风险的企业家。熊彼特认为,他的整个经济发展的理论所要说明的,“根本不是具体的变迁因素,而是这些因素起作用的方法,即变迁机制”;“‘企业家’只不过是这一变迁机制的承担者”[9](P61)。
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这部名著的第12章,熊彼特还对这个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他指出,近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是企业家精神,而企业家的功能则是:“通过利用一种新的发明,或者更一般地利用一种未经试验的技术可能性,来生产新商品,或用新方法生产老商品;通过新开辟原料供应新来源或产品的新销路;以及通过改组工业结构等手段来改良或彻底改变生产模式。”[8](P210)熊彼特举例说,近代早期的铁路建设、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电力生产、蒸汽机、钢铁冶炼和汽车,以及在殖民地进行风险投资,这些都是企业家创新的典型的例子。还值得注意的是,在熊彼特的整个理论体系中,他一方面特别注重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近现代西方世界经济发展中至高无上的作用;另一方面,又特别注重历史分析法,极力倡导“变动”、“发展”和“动态”的观点。与斯密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的理论解释相契合,熊彼特认为,“创新”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内在因素”,而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只不过是来自于市场经济体系“内部自身创造性”的一种动态变化,并进而强调了社会经济制度的“内在因素”与“增长动态机制”的作用。
[收稿日期]2006-10-28
注释:
①韦森:《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研究西方世界兴起和晚清帝国相对停滞之历史原因的一个可能的新视角》(《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韦森:《从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理论看经济增长的“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东岳论丛》,2006年第4期)。
②譬如,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诺思和托马斯(North & Thomas,1973,中译本,第37页)就明确指出:“目前最广泛接受的一种解释仍沿袭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技术变革是打破平衡、派生出其他的力量。当代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都坚持这一观点,加入他们行列的还有在其他方面自认为是彻底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流行的观点是把周期性的经济增长归因于新发明和新制度的积累性作用,这些新发明和新制度使更多的畜力、水力和风力得到利用,使投入组合更加有效。”在《经济史的结构语变迁》中,诺思(North,1981,p.147)则更明确地指出:“马克思对技术的重视使马克思主义者误入了歧途,因为产业革命的技术不是出现在结构变迁之前,而是在其之后。”
③许多学者均注意到桑巴特在思想上曾在多方面受马克思的影响。在其晚年,桑巴特曾以明白无误的词句告诉读者,其代表作《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所有一切好的东西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的精神”(Sombart,1922,p.XIX)。然而,尽管桑巴特受过马克思思想的多方面影响,但他在许多问题上——特别是在作为一种经济体制的资本主义的性质及起源上——与马克思有很大的不同。
④在另一个地方,韦伯(Weber,1983,p.126-127)曾明确指出,正如桑巴特所指出的那样,不能把贵金属的流入视为近代资本主义产生的最初原因。韦伯承认,在某种既定条件下,贵金属供应的增加可以引起价格革命,正如1530年以后欧洲所发生的那样。但反过来看,印度的例子则证明,单凭贵金属的流入,并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因为,从历史上看,在罗马统治时期,巨额的贵金属曾流入印度,以交换其土特产品。但这种贵金属的流入只在很小的范围内促进了印度的商品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发展,而大量的贵金属则被藏在王公的钱窖中,没有转化为流通的货币。韦伯还发现,即使近代以来欧洲自身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譬如,美洲的金银矿发现以后,大量的贵金属首先流入的国家是西班牙,但在欧洲近代历史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同贵金属的流入是不相称的。结果是,贵金属流过了西班牙,却很少触动它的传统的经济生活方式,倒使其他国家如荷兰和英国富庶起来。根据这些史实,韦伯(Weber,1983,p.127)得出结论说,“可见,人口增长和贵金属输入均不是产生欧洲的资本主义的主要原因”。
⑤韦伯的思想曾受桑巴特影响,直接可以从在韦伯的许多著述中大量引用和提到桑巴特的著作这一点上看出来。并且,在《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Weber,1958,p.198)还曾明确指出:“尽管下列研究在其最重要的观点上追溯到了很早的著作,但通常来说,我不必指出他们在其发展中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桑巴特那些阐释直截了当的重要著作,可能尤其是这一篇,——尽管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即使那些一再明确地不赞同桑巴特的见解的人,以及那些反对他大部分观点的人,只应在全面研究他的著作之后再采取这样的态度。”这里应该指出,尽管与韦伯与桑巴特一样特别强调“企业家精神”或企业家的“资本主义精神”,但在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中这种“资本主义”的来源及本质等问题上,两人却有很大分歧。他们的理论分歧甚至达到了在他们共同主编的《社会学与社会政治学文献》杂志上经常互相指责的地步。譬如,韦伯曾指责桑巴特的《资本主义精华》充满着“不实之词”,而且将其描述为“一本关于该论题最糟糕的书”。在提及桑巴特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中其他那些记述性的引文时,韦伯曾说桑巴特不时“严重歪曲了”他的原意,挑起了“针对他(韦伯本人)的辩论”、“坚持不能自圆其说的论点” (参见西格曼为桑巴特的《奢侈与资本主义》撰写的“英译本导言”,中译本,第235页)。而桑巴特反过来则多次反驳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的观点。对此,下面我们还要具体讨论。
⑥在另一个地方,韦伯(Weber,1983,p.150)指出,与中国的旧制相比,“差别恰恰出在近代资本主义能够发展起来的合理国家(rational stale)上。这种合理国家的基础是专业官员(expert officialdom)和理性的法律。……近代西方国家中的理性法律,是训练有素的官员做决策的基础”。韦伯还指出,虽然近代欧洲国家中的法律的内容不是源于罗马法,但是是从罗马法中衍生出来的。由此,韦伯(Weber,1958,p.151)认为,“罗马法的复兴已经被认为是农民阶级衰落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尽管如此,韦伯还是强调说,“罗马法并非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基础”,——譬如,韦伯举例到,资本主义的故乡英国就并没有接受罗马法。
标签:韦伯论文; 企业家精神论文;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经济利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亚当·斯密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