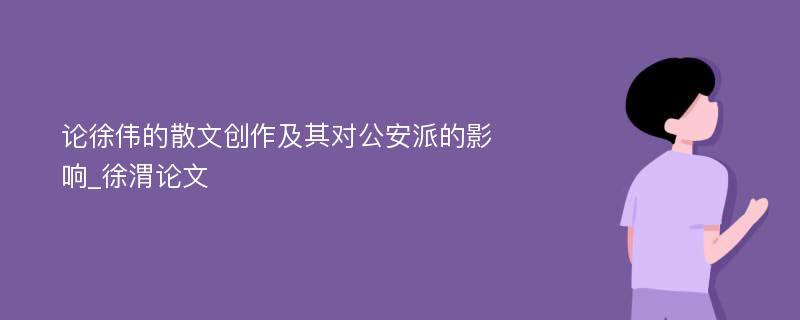
论徐渭的散文创作及其对公安派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其对论文,散文论文,公安论文,论徐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活在晚明的狂生徐渭,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艺术通才。他曾颇为自负地声称:“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注:见陶望龄《徐文长传》,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徐记室渭》。),如果再加上他自己未予置评而又深受后辈揄扬的戏曲创作,那么,他的创作几乎涵盖了传统文人创作的各个方面。由于徐渭在创作上的巨大成就,更因为他作为明代后期文学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的特殊身份,徐渭的创作正越来越多地受到当代研究者们的关注和重新解读。但是,纵观近年来的徐渭研究,不难发现,与对徐渭的哲学思想、文学思想、戏曲创作等方面的研究相比,有关徐渭的散文创作的研究还是相对薄弱的,或许这与徐渭文集中充斥着大量的应酬文字,令人很难有耐心卒读的状况有关。但是,晚明文学解放运动的巨擘袁宏道并未因此而减低对徐渭的敬佩,他认为徐渭的诗文“一扫近代秽芜之习”(注:见袁宏道《徐文长传》。),称赞他的文章在明朝数得上第一(注:见陶望龄《徐文长传》,虞淳熙《徐文长集序》。)。袁宏道对徐渭的赞誉不会是没有道理的,这对我们也是不无启发的:假如不对徐渭的散文作一番探讨,那么,我们对崛起于晚明的文学解放运动的发展脉络及其性质的理解,就有可能带有某些方面的片面性。
一
徐渭在晚明是以狂傲不羁著称的。胡宗宪总制东南,声势煊赫,“文武将吏庭见,惧诛责,无敢仰者”,徐渭却敢于以屡试不第的秀才的身份“长揖就坐,纵谭天下事,旁若无人”;胡宗宪后来因党严嵩而被捕,死于狱中,徐渭“冤愤不已,而力不能报,往往形之诗篇”,他还多次自杀,甚至发出“乃渭则自死,孰与人死之”的悲怆呼号;此后徐渭又因猜妒而杀继室张氏,被关入狱中长达七年,在亲友特别是同为王门子弟的同乡张元忭的营救下得到释放。徐渭心怀感激之情与张元忭接近,可当张及其友人欲以礼法来拘束他的时候,他愤然说道:“吾杀人当死,颈一茹刃耳,今乃碎磔吾肉!”并绝然辞去;回乡之后,徐渭更加憎恶官场中的富贵之人,“自郡守丞以下求与见者,皆不得也。尝有诣者伺便排户半入,渭遽手拒扉,口应曰:‘某不在’”,即使是“人多以是怪恨之”也不改故态(注:见袁宏道《徐文长传》,陶望龄《徐文长传》,张汝霖《刻徐文长佚书序》,徐渭《自为墓志铭》。)。凡此种种不近人情的举动,正表现了徐渭对自我真实的执著。明末的章重就准确地把握了徐渭这一心态所反映出来的人格特征,他在为张岱所校辑的《徐文长逸稿》而写的《梦遇》一文中便如此地感叹:“先生志不媚世,存吾真而已!”
徐渭独立不羁的人格规定了他的创作方向,可以说,徐渭的散文就是他执著于自我真实这一人格精神的自然流露。
徐渭生活的时代,正是后七子把持明代正宗文坛、应者云从的时期(注: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陈征士弼》:“自嘉靖末,迄今八十余年,七子之风声,浸淫海内。”)。对于后七子的食古不化,以为只要“格调”高古就足以将诗文创作引上正途的理论和实践,徐渭采取的是不屑一顾、“斥而奴之”的激烈态度:“今世为文章,动言宗汉西京,负董、贾、刘、扬者满天下;至于词,非屈、宋、唐、景,则掩卷而不顾。及扣其所极致,其于文也,求如贾生之通达国体,一疏万言,无一字不写其胸膈者,果满天下矣乎?或未必然也。于词也,求如宋玉之辨,其风于兰台,以感悟其主,使异代之人听之,犹足以兴,亦果满天下矣乎?亦或未必然也。”(《胡大参集序》)他甚至还挖苦七子的“不出于己之所自得,而徒窃于人之所尝言”的创作,将之比喻为“鸟学人言”(《叶子肃诗序》)。徐渭不仅从反面针锋相对地批驳后七子的主张,在《赠成翁序》中,他还提出了自己的正面理论主张,那就是写“真我”,以真去伪。他说:“今天下事鲜不伪者,而文为甚。夫真者,伪之反也。故五味必淡,食斯真矣;五音必希,听斯真矣;五色不华,视斯真矣。凡人能真此三者,推而至于他,将未有不真者。”
所谓“真”,就是不隐讳自己的观点。试看徐渭《赠礼师序》一文中对韩愈的评价:“论道则稍疵,及攻佛,又攻其粗者也。”众所周知,在韩愈的一生中,倡导道统和排斥佛学异端是二而一的,后人对他祟儒排佛大都持肯定态度,欧阳修等人修撰的《新唐书·韩愈传》所说“自晋讫隋,老佛显行,圣道不断如带。诸儒倚天下正义,助为怪神。愈独喟然引圣,争四海之惑,虽蒙讪笑,合而复奋。始若未之信,卒大显于时”,真德秀认为韩愈的《原道》、《论佛骨表》等文是“圣学之渊源,治道之根柢”,有“扶正道,辟异端”之功(注:真德秀《〈大学衍义〉序》、《文章正宗》。),就是较有代表性的意见。当然,对韩愈的倡儒排佛不以为然的也大有人在,比如苏轼和朱熹(注:苏轼《韩愈论》:“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朱熹《读唐志》:“若夫所原之道,则亦徒能言其大体,而未见其有探讨服行之效,使其言之为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不过,苏轼是站在思想活泼的文学家立场上不满韩愈对圣人之道盲目的“张而大之”的作法,朱熹是以理学家的身份指责韩愈割裂道与文,甚至重文轻道,他们都没有触及韩愈崇儒辟佛本身的理论漏洞。徐渭则不然,由于他对儒学佛学都有一番钻研,所以他认为韩愈所称道的“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为之盛”只不过是“吾儒之粗”,而韩愈攻击佛教徒“祝发而髡之”、“绝父子蔑君臣”也只是皮相之谈;他还进一步论证了“佛氏论心”的“精微之旨”反而能补足儒学本身的缺弊。与宋明理学家既要吸收佛教精华却又羞羞答答地不肯对此加以承认的态度相比,徐渭确实是大胆而又直率的。更可贵的是,他并没有因为对韩愈的尊重,并没有因为自己不止一次表示“昌黎之文,余夙诵好之”,就掩饰自己对韩愈的不同看法。徐渭对胡宗宪的态度也很能说明问题。胡宗宪对徐渭有知遇之恩,贵为总戎的胡宗宪对八次应举不得一第的穷秀才徐渭言听计从,尊礼有加,这不能不使徐渭感恩戴德,因此徐谓在《奉答少保公书》、《少保公五十寿篇》等文中对胡宗宪的不乏过情之誉的吹嘘,也就不足为怪了。但这绝非徐渭对胡宗宪的评价的全部。嘉靖三十三年,胡宗宪出按浙江,次年他与赵文华部署明军进击盘踞在陶宅的倭寇,因指挥失当,大败而归(注:《明史·胡宗宪传》,《明通鉴》卷61。)。徐渭专门为此为了《陶宅战归序》一文,在记叙了主持军事行动的大吏不听从了解情况的会稽县尉吴君和王山人的积极建议,不明了倭寇虚实的情况下贸然进兵,以至明军一败再败之后,感叹道:“嗟夫,世独忧无善言耳,然或有言而不能用,或能用而不察言之是非。大抵能言者多在下,不能察而用者多在上,在上者冒虚位,在下者无实权,此事之所以日敝也。”再联想到徐渭在《拟上府书》、《拟上督府书》、《治气治心》等文中对用兵之法的建言,对“用兵之妙,机而已矣”,“夫物有化也,兵亦有化也,取胜不难,知化难也。故曰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也”的论述,也就不难窥见徐渭对胡宗宪不善用兵的不满了。不仅如此,就算胡宗宪下狱瘐死的消息使徐渭痛心疾首之时,他也没有听凭痛失知音的感怆压倒一切。在为胡宗宪写的仅百字的《祭少保公文》中,徐渭竟然两次提到“公之律已也则当思己之过”。仅此数端,亦可见徐渭对胡宗宪盖棺论定的另一面了,他并没有因个人恩怨就丧失了“真我”。再如《瑞麦赋》,也是一篇颇有意思的作品。嵊县吴县令“治有恩惠,时麦秀有多至三歧者”,于是该县县学子弟不远百里跑到山阴请徐渭写赋歌颂,这大概是由于徐渭曾代胡宗宪写过《进白鹿表》,使得嘉靖皇帝“大嘉悦”,从而名闻天下的缘故。可徐渭却在赋中“不知忌讳”地大唱反调:“岂若今日,戎马蹂躏而甫旋,艨冲瞬息而靡定,东南当春夏之杀伤,西北苦秋冬之奔命。万室不保,一麦何支?四方如此,一县何为?”,尽管徐渭是以写“祥瑞”而时来运转的,可在他的内心深入,对“祥瑞”之说是大不以为然的,无怪乎他一有机会便吐露心声,大放厥词了。
徐渭散文的另一显著特点是真情毕露,这与他倡导“真我”是互为表里的。徐渭在二十七八岁时拜王守仁弟子季本为师,季本对他淳淳善诱,共同商讨学问,这使徐渭大得教益,乃至感叹自己“前此空过二十年,悔无及矣”(注:徐渭:《畸谱》。)。季本去世后,徐渭怀着敬佩哀痛之情作了《师长沙公行状》,历数老师种种美德:为人耿直敢言,不孜孜于个人的名利地位;担任地方官时一以安民为本,处理民事案件耐心细致,发现错案勇于改过;学问反复钻研,与同志讨论探求,对时论绝不随声附和。最后,在写到季本“以故疾革之日,犹进门人讲《易》学于榻,疾且革,诸子泣请遗训,亦唯曰‘读书’而已。问家事,笑不答。时偶就侧牖寝,至是先生遽起栉发,家人止之,必强栉,已乃起走,就正室,易榻而瞑。”此刻,徐渭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了,他不得不“拭泪而为之状”,这种在传统的传状类作品中极为罕见的对作者本人的情感状况的直接描写,正反映出徐渭写作时的丰富细腻的情感特征。徐渭在创作中感情还是深沉执著的。嘉靖年间因为弹劾奸相严嵩而轰动天下的沈炼,是徐渭的同乡和忘年交。沈炼遭到严党迫害诬陷被害之后,徐渭写了《知清丰沈公祠碑》、《赠光禄少卿沈公传》、《会祭沈锦衣文》等文章,对沈炼因慷慨直言而罹祸“扼腕流涕”,悲愤难已。然而徐渭并没有像一般文人那样把写悼念沈炼的文章当成责任的完成,或者是情感的句号。恰恰相反,沈炼的身影,在此后的徐渭心灵世界中是一个巨大的挥之不去的存在,对畏友始终不渝敬佩伤感之情,也一直沉甸甸地压在徐渭的心头,以至他在写其他文章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联想起沈炼来。如《周愍妇集序》,是徐渭为一位女子所写。这位周姓女子“贤且孝”,却被恶婆婆无理迫害至死,对于这种在封建社会中是常见的家庭伦理悲剧,徐渭的心情是哀伤莫名的。他由此而想到了历来争论不体的人性善恶,也想到了所谓天命。他愤恨地责问苍溟:“吾越人常谈沈锦衣之死,而将并夷其伯子也,适有天幸以免,遂谓天真能与善人,而诋非司马氏论伯夷语。然天能活伯子,何不能不死锦衣也?岂伯子为善人,而锦衣为不善人耶?”这道无人能解答的难题下,奔涌着徐渭的难以压抑的情感巨流。
说起徐渭散文中的“真我”与真情,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徐渭散文中的应酬之作或代他人所作的数量占了其文集总量的一半以上,这也是人们拒绝更多地研穷徐渭散文的原因之一。徐渭本人对此也不是没有觉察,他在《抄代集小序》、《幕抄小序》、《抄小序自序》等文中感叹“渭于文不幸若马耕耳”,对这类“谀且不工”的文字爽然若失。但他还是怀着敝帚自珍之情,把其中的部分文章收进了自己的文集。徐渭此举并不是毫无道理的,因为在这批文章中仍然留下了徐渭“真我”与真情的痕迹。如《慈溪县学训导祝公行状》、《张太仆墓志铭》、《邑侯徐公生祠记》等文,都是受请代作之文。对于这些勤于公事不畏强暴的循吏、“数却生贫者贽”的穷教官,徐渭没有因为是受请代作就以局外者的身份漠然地讲述他们的生平事迹的,当他们被调离任时,“送者万人,自邑门而达于江,遮不得行者百里,有渡江守数日而返者。返而复往者,涕湿襟者,哭失声者,举酒悲、悲而不得饮者,亭驿皆是”;而当他们的死讯传来时,徐渭所代作的当事人“遽位而哭”,“索铭于予,予涕不能字”,谁人能分辨得出,作文的到底是徐渭,还是向徐渭请托之人?也正因为徐渭在替他人写文时的全情投入,有时究竟是他自己的文章还是代他人所作的文章不大容易分得清。像《吕尚书行状》,中华书局1982年版的《徐谓集》未标明为代作,且不论徐渭以秀才的身份替贵为尚书者作状的可能性有多大,就看《行状》中称吕尚书曾带着“先子”一起征讨云南,时在嘉靖四十二年;而徐渭之父虽然是在贵州考中举人,做过云南巨津州知州(注:徐渭:《嫡母苗宜人墓志铭》。),但他死于徐渭不足一岁时,即正德十六年(注:徐渭:《畸谱》。),因此《行状》中的“先子”绝不可能是徐渭的父亲,这足以证明《吕尚书行状》只可能是徐渭代他人所作的。因此,徐渭状中“噫!此吾所以状之日为恸移晷,三掷笔而未成也”的痛心,只能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家之块垒了。徐渭的应酬代作文字亦贯穿着真挚,这与徐渭对应酬文字的认识是分不开的。徐渭曾为右布政使胡某写过《胡公文集序》,胡某虽然“平生所作,而应俗者固十居六七”,但他能做到“随事与人而各赋之,直不伤时,而婉不失己”,这对徐渭启发甚大。或者可以说,所谓“直工伤时,婉不失已”云云,正是徐渭的夫子自道,正是他写“应俗”文字时的指导思想。因此徐渭在写此类文章时能够大致保持其真挚的一贯风格,也就是固有之义了。
二
全面评价徐渭的散文,不能不涉及到他的思想。徐渭在嘉靖四十四年因杀妻而下狱时写了《自为墓志铭》,文中简述了自己思想上历程:“少知慕古文词,及长益力。既而有慕于道,往从长沙公究王氏宗,谓道类禅,又却叩于禅,久之人稍许之。然文与道,终两无得也。”细味徐渭的这段自白,不难发现其思想的蒹收并蓄的特征。徐渭的成年之后所接受的是王守仁的心学,这种带有“狂禅”色彩、张扬个体精神的绝对自由的学说,使徐渭的疏狂个性得以进一步发展。因此,徐渭对拘谨偏执的程朱之学是颇不以为然的。他在《奉师季先生书》中就说过:“先儒如文公者,著释速成,兼欲尽窥诸子百氏之奥,是以冰解理顺之妙固多,而生吞活剥之弊亦有,此正后儒之所宜深戒者,不宜驳先儒而复蹈其弊,乃复为后人弄文墨之地也。”在《评朱子论东坡文》中,他更是指责朱熹“件件要中鹄,把定执板,只是要人说他是个圣人,并无一些破绽,所以做别人着人人不中他意,世间事事不称他心,无过中必求有过,谷里拣米,米里拣虫”,简直是张汤、赵禹一流的吹毛求疵的苛刻之吏。不过,徐渭之师季本在王门的子弟中思想是偏于保守的,他有感于王门后学如王畿等人对“自然”的过分强调及由此而引发的化解传统道德规范的可能有的可怕结果,著《龙惕书》,提出了“自然者,顺理之名也。理非惕若,何以能顺?舍惕若而言顺,则随气所动耳,故惕若者,自然之主宰也”,认为应以伦理自觉来节制人的自然本能。徐渭在为季本所作的《墓志铭》中特意提到此事,并说季本与王门的其他弟子邹守益、聂豹、钱德洪、王畿再三争辩暂时没有结论,“先生亦自信其说不为动,久之诸先生者亦多是之”,这与黄宗羲《明儒学案》中他人不从季本主张,而“先生终自信其说,不为所动”的记载有着明显的不同,两相比较,徐渭的倾向性不言自喻。也正为如此,在徐渭的文集中,对“圣人”、“吾孔子”、“吾孟子”的亲热称呼不绝于篇,这种对儒学从总体上的认同,是徐渭少有出世之想的根本原因。当然,对权威的尊崇服从,往往又是与对精神自由的追求背道而驰的。为了寻求调和两者间矛盾的方法,使之不仅相反而且相成,徐渭又钻研过老庄之道和禅学(注:徐渭《论中七》:“聃也,御寇也,周也,中国之释也,其于昙也,犹契也,印也,不约而同也,与吾儒并立而为二,止此矣,他无所谓道也。”徐渭《答钱刑部公书》:“门下是出世人,作出世事,仆虽不得其门,曩时亦尝留意于此宗,作一看经僧过来。虽不认得真月,莫亦认得人手指月处。”),认为老庄之道“与释与儒而为三,而本非三也,二之三,嫡之庶,统之闰也”(注:徐渭:《论中七》。),从而进一步主张“学道者苟能舍其藏,不键其户,道在是矣”(注:徐渭:《虚室生白斋扁记》。),这些都充分表现了徐渭对传统学术思想的通达和超脱态度。徐渭还写过一篇《又跋于后》,是看了《朱太仆十七帖》后借题发挥的文字,文中写道:“昨过人家圃榭中,见珍花异果,绣地参天,而野藤刺蔓,交戛其间,顾问主人曰:‘何得滥放此辈?’主人曰:‘然,然去此亦不成圃也。’”不妨说,徐渭在这里是以其特有的隽永含蓄的方式表达了对自己思想上的广闻博采、兼收并蓄的自豪与自信的。
徐渭的《自为墓志铭》关于其思想历程的自述,与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依据王畿的记载而叙述王守仁“学凡三变”的经历的那段著名的文字十分相似。不过,王守仁从“始泛滥于词章”到最终皈依了“圣人之道”,而徐渭则是从“少知慕古文词”到颓然地承认“然文与道终两无得也”,这恰恰证明了:徐渭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文学家,而不是王守仁式的道德家。其实,他的“两无得”一语,“道无得”是实情,而“文无得”则是自谦之词。因为他在另一场合曾明确表示:“夫语道,渭则未敢;至于文,盖尝一究心焉”(注:徐渭:《聚禅师传》。)。事实也正是这样,比如同是学习儒家的圣经之一的《大学》,季本和徐渭对一对师生的基本立足点就大不一样。作为理学家的老师季本在投到王守仁门下后,“获闻致良知之语,悉悔其旧学,一意于圣经”,通过反复阅读《大学》,“沉思者半年,而始悟其一以贯之之妙,移视他书,无不一览而通者”(注:徐渭:《师长沙公行状》。),把《大学》视为学道历程中举一反三的捷径;而作为弟子的徐渭却别具法眼,从中悟出的是作文之法:“《大学》首篇,人人熟之者也,而文之体要尽是矣。通其故,千万篇一也,首尻与脊也,然而一开一阖者,则又且无定立也,随其所宜而适也”(注:徐渭:《论中五》。),徐渭的这一表现,不能不说是部分地背离了师门教诲的一种文学家的独特眼光。
徐渭在学术思想上的杂取旁收,再与其强烈的文学家的自觉意识的奇妙结合,使他对文学规律的把握的深刻与准确,迥出于同时代的后七子、唐宋派之上。
古代散文发展到徐渭生活的时代,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两千多年来古人在散文创作中积累的经验、运用的手法,成了明人心目中仰之弥高、不可企及的法式。在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上,前后七子和唐宋派都陷入了迷途不可自拔。七子们的“学不的古,苦心无益”(注:李梦阳:《与周子书》。)固然贻笑大方;唐宋派主张为文“未尝无法,而未尝有法,法寓于无法之中”(注:唐顺之:《董中峰侍郎文集序》。),“所谓法者,神明之变化也”(注:唐顺之:《文编序》。)的见解不乏高明之处,但毕竟是一种抽象的原则,更何况唐宋派的领袖唐顺之从嫌弃王慎中模仿曾巩而写的文章有“头巾气”(注:李开先:《荆川唐都御史传》。),到自己也推崇在唐宋八家中道学味最浓的曾巩(注:唐顺之:《与王遵岩参政》:“三代以下之文,莫如南丰。”),把传统的“文道合一,以道统文”的思想推到了极致,不再承认文学的独立地位,这就更谈不上在文学创作的范畴中正确的把握继承与创新的了。徐渭并不拒绝借鉴古人,他认为古人的经验是“人出一思也,人创一事也,又人累千百人也,年累千万年也”的积聚下来的,如果不尊重和利用古人积累的经验,一切只依赖于自己的摸索、自己的体验,那就会“苦悖且不暇”,是“非愚则病惑者”,因此他提倡“贵因”;但是,如果样样以古人为依归,“忘其彼之古者,即我之今也,摹古而反其所以为古者,则惑之甚也”。因此,“贵因”必须有自己的思考,有自己的抉择,这就是“贵不博”(注:徐渭:《论中三》、《论中四》。)。在古文大家中,徐渭最佩服的是庄子、韩愈和苏轼(注:徐渭:《赠礼师序》:“昌黎之文,余夙诵好之。”《评朱子论东坡文》:“东坡千古一人而已。”徐渭虽然没有直接评价庄子,但在他的《一吾说》、《一登龙门引》、《赠王翁七十序》等文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对庄子的刻意模仿的痕迹。)。这三个人在文笔上的共同特点,是纵横恣肆和对“行云流水”之美的自觉追求。徐渭选择了他们,也在思考着他们,在对前人的学习中形成自己的创作个性。他提倡“兼并昌黎、大苏,亦用其髓,弃其皮耳。师心横从,不傍门户,故了无痕迹可指”(注:徐渭:《书田生诗文后》。),认为“不学而天成者尚矣”,但这种天才毕竟是凤毛麟角,更多的人是“始于学,终于天成”,而对他“天成”的解释是“非成于天也,出乎己而不由于人也”(注:徐渭:《跋张东海草书千文卷后》。),即在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这比七子把古人的创作经验当作“物之自则”(注:李梦阳:《答周子书》:“方圆之于规矩,古人用之,非自作之,实天生之也。今人法式古人,非法式古人也,实物之自则也。”),只懂得亦步亦趋,自然清醒得多了。
徐渭的散文主“真”、主“情”,具有强烈的个性特征。袁宏道曾说其“文有卓识,气沉而法严,不以模拟损才,不以议论伤格,韩、曾之流亚也”,翻阅徐渭之文,就会发觉袁宏道实在信言不谬。徐渭的议论文有真知灼见,往往得出出人意表的结论,如他的《军中但闻将军令论》,劈头就是一句“古之善为将者,使士卒畏己而不畏敌;而古之善将将者,使士卒畏将而不畏己”,然后论证不畏敌才可以取胜,畏将则能够遵从军法的道理,接着又举周亚夫军细柳士卒不闻天子之诏、冒顿指令手下以鸣镝射杀其父头曼单于等事例说明军中将领权威的必要,最后得出“将能而君不御者胜”的结论,令人折服;又如《友琴生说》,记友琴生善鼓琴,他的琴声不仅吸引朋友,连老鼠也被吸引到出穴偷听,简直可以与伯牙鼓琴使马仰秣的传说相媲美。而当友琴生要求徐渭对“声之感人”的道理进一步说明的时候,他却话峰一转:“生诚思之,当目未有桐时,蚕不弦时,匠不斫时,人具耳或无听也,是为声不成时。而使友琴生居其间,则琴且无实也,而安有名?名且无矣,又安得与之友?”这一番话使友琴生恍然大悟:“乃知与琴友而未尝友,不友而未尝不友也”,懂得了不应空求虚名而要去追求与他人的超越物质和感官层面上的心灵沟通,“大音希声”、“由人籁进而聆听天籁”这种深邃的思想,就被徐渭以相当轻松的方式阐述清楚了。而这种假想的与友琴生的对答的写法,又分明是受到了赋体的主客问答方式的启发的。
徐渭不少记叙文也写得不坏,其特点是流畅简洁并间以议论来增强文章的神气。比如《赠吴宣府序》,记自己在青年时代与后来任宣府巡抚的吴某惩戒悍卒的往事。嘉靖三十四年,明廷对倭寇用兵,明军中的悍卒乘机搔扰会稽的百姓,在集市上饮酒不付账,强闯民宅胡作非为,根本不把维持治安的地方官放在眼里。正在喧哗的时候,“余方与君罢讲稽山,下逢之,直前视,彼四人者嗔曰:‘酸何知,敢视我,直年攫乃巾碎之耳!’余谓君曰:‘市人足恃也,盍佚诸?’君曰:‘不约易散,未可也。’君归呼族人于家,余归呼族人于寓,得七八辈,余曰:‘可矣’。君曰:‘不约莫任其害,未可也。’约族人曰:‘侪等击,击其下,莫击其上。’约市人曰:‘侪等莫击,第喊而声援。’遂击。四人者靡不仆,几烂,击者逞褫其绛锦与靴,四人者裸而号,乞命,君曰:‘悉还之。’稽首悔谢如崩角。”文章是徐渭在事发二十二年之后写的,但依旧如此绘声绘色,生灵跳脱。这类大快人心的故事在越地广为流传,这大概就是日后袁宏道在《徐文长传》中根据传闻记载徐渭“尝饮一酒楼,有数健儿亦饮其下,不肯留钱。文长密以数字驰公,公立命缚健儿至麾下,皆斩之,一军股栗”之所本。再如《钮太学墓志铭》写得出很风趣,纽鼎岩在国子监中屡试不第,便回到了任按察佥事的父亲的官邸里跟着他读书。“而翁性刚毅,遇人若事,斤规而任方,与龊龊者不相能,中谤挫,道不行。鼎岩时时婉颜色以进,曰:‘鲁国一儒,大圣人也,贵中,尤贵时。愿大人少刓其方,无召龊龊者忌。’翁诧曰:‘孺子耶,汝来就爷教,顾教爷耶?’鼎岩跪请笞,翁为一笑而罢。”对两父子之间的相互劝勉的情状,简直的描摹如画,令人读了忍俊不禁。《寿徐安宁公序》则又是另一种写法。徐渭是通过徐学诗才了解其父徐安宁的生平的。嘉靖二十九年,任刑部郎中的徐学诗上疏弹劾严嵩,“言切直英特,慷慨嘘欷,读之者夏栗而冬汗。当是时,天子为动色,而海内直节忧时之士,因其言,莫不想慕,愿见其人者”,徐安宁也因此受到牵累而被罢职。徐渭后来了解徐安宁为官时也以耿直著称,不禁感叹:“陈咸之在汉以直闻,而其父之教之也以谄。至于今千载,人言其子不能无少于其父,是家难全德,而誉罔流也。刑部君仕居中,以直忤宰相于朝;安宁公仕居外,以直忤巡使者于郡,虽非其相约以必为也,而其守道抱贞而轻富贵,若出一辙。将使千载之下闻之曰:‘某邑里徐氏父子,世直臣也。’其于家之德不为全,而誉不为久乎?”这番引古论今的突兀议论,不仅没有偏离文章的主旨,反而更加强了徐氏父子品德的感染力度,从而使徐氏父子的形象更加鲜明突出。徐渭凡此种种生动流畅的文字,比起七子们的诘屈聱牙来,不知高明多少倍!
三
在对徐渭的散文创作进行了一番巡礼之后,接着就该来谈谈他对公安三袁,特别是袁宏道的影响了。袁宏道是凭着诗文与徐渭结缘的,在《徐文长传》中,袁宏道形象地描写了他在发现了徐渭作品时,与友人陶望龄在一起“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的惊喜若狂的神情。此事发生在万历二十五年袁宏道游历杭州时,该文则作于两年后,了解这一时限,对于弄清徐渭给袁宏道的影响具有重大的意义。
对于袁宏道的“性灵说”的思想渊源,当代学者大多把自己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袁宏道与李贽的关系上。无可否认,袁宏道在万历十八年至二十一年之间,曾数度拜访李贽,宾主相谈甚欢。袁宏道对李贽的《藏书》、《焚书》极为倾倒(注:袁宏道《得李宏甫先生书》:“迹岂《焚书》白,病因老苦侵。”《别龙湖师》:“死去君何恨,《藏书》大得名。”),据袁中道在《中郎先生行状》的形容“先生既见龙湖,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完全可以说,袁宏道此后数年中提出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见从己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等公安理论的核心主张,是与接受李贽思想上的影响有关的(注:见袁宏道《序小修诗》(万历二十四年)、《张幼于》(万历二十五年)、《雪涛阁集序》(万历二十八年)。)。此后,袁宏道多次与李贽通信,在与他人的通信中也常提起李贽,表现出他对李贽的尊重和感激之情。不过,袁宏道给李贽的最后一封信是在万历二十八年,此后李贽的名字在他的笔下出现得越来越少了。至万历三十年,李贽下狱自杀。而出人意外的,是袁宏道从没有在诗文中提及此事,甚至以后绝不再提起李贽的名字,这使不少人感到大惑不解。任访秋先生在《袁中郎研究》中推测袁宏道是因为自己和李贽的关系一向很密切,怕随便议论会惹事生非,这种推断恐怕是难以成立的。事实上,李贽被捕前住在因上疏言事而被革职为民的前御史马经纶家中,马经纶陪着李贽入狱,后来又为李贽料理后事,并没有有惹来什么麻烦(注:《明史·马经纶传》、袁中道《李温陵传》。),袁中道《龙湖遗墨小序》也说:“当龙湖被逮后,稍稍禁锢其书,不数年盛传于世,若揭日月而行”,这些事实都说明了,明廷对李贽事件的处理是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的。以袁宏道那种目空千古的个性,竟然担心承认他与李贽的亲密关系会惹起祸端,反倒是不可思议的。
引起袁宏道与李贽疏远的根本原因,是两人思想上的分歧。我们过去是太看重袁、李之同,而忽略了两人之异了。他们在人生观上的根本分歧,在于袁宏道偏于人世,而李贽偏于出世,关于这一点,在韩经太先生的新著《理学文化与文学思潮》中有着相当精彩的论述。李贽的《焚书》中有一篇《心经提纲》,其中说道:“《心经》者,佛说心之径要也。心本无有,自颠倒也,安得自在?独不观于自在菩萨乎?彼其智慧行深,即到自在彼岸矣。其时也,自然观见色、受、想、行、识五蕴皆空,本无生死可得,故能出离生死苦海,而度脱一切苦厄焉,此一经之总要也。”李贽在这里表述得十分清楚,他认为人生即“空”,他追求的是彼岸世界之真。袁宏道在初次接触李贽时,刚好是会试下第,在苦闷中与长兄袁宗道一起钻研禅宗的时候,因此,他与李贽探讨的主要的禅宗之学,这在他的《张幼于》一文中讲得很清楚:“仆自知诗文一字不通,唯禅宗一事,不敢多让,当今勍敌,唯李宏甫先生一人。其他精练衲子,久参禅伯,败于中郎之手者,往往而是。”袁宏道在谈禅论道中吸取了李贽的“心无挂碍”即解脱世俗束缚的思想,提出激进的文学主张,但是,在他内心深处却始终保持着对世俗生活的浓厚兴趣,即以人们反复引用以证明袁宏道玩也不恭的人生“五快活”之说,他反对的也还是“无复生人半刻之乐”,欣慕“一生受用”,其中洋溢的世俗之趣,何尝有半点人生即“空”的影子呢(注:袁宏道:《龚惟长先生》。)?承认李、袁二人在人生观上的差异,也就不难发觉他们在文学主张上的距离了。有人认为,袁宏道提倡的诗文之“趣”,是李贽“童心说”的另一种说法,这也是对袁宏道的一种误解。袁宏道作于万历二十五年的《叙陈正甫会心集》一文较为集中的了他对“趣”的看法。表面看来,他说的“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面无端容,目无定睛,口喃喃而欲语,足跳跃而不定,人生之至乐,真无逾于此时者。孟子所谓不失赤子,老子所谓能婴儿,盖指此也”,与李贽在《童心说》中的“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的论断如出一辙。但仔细分析,则可发现两者的不同。李贽的“童心”,在现实世界中是一种不可能的假设,是与现实生活对立的先天存在,是对彼岸世界的执著;而袁宏道的“童趣”强调的是趣味的自然,不刻意强求,这与他后来在《寿存斋张公七十序》中所言“故叫跳反掷者,稚子之韵也;嬉笑怒骂者,醉人之韵也。醉者无心,稚子亦无心,无心故理无所托,而自然之韵出矣”是同一个意思。他在这里所说的“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有哪一点是脱离了现实人生的?再者,袁宏道在万历十七年专心“华、梵诸典”,与袁宗道一起探讨性命之学,“亡食亡寝,如醉如痴”,但所得不多。“一日见张子韶论格物处,忽然大豁”(注:袁中道:《中郎先生行状》。),张子韶即宋代理学家张九成,他是杨时的弟子,思想上虽受禅学影响很深,但仍是以儒学家伦理纲常本位的,主张“天理”不可违,“君子慎其独”,认为释老之学都比上不儒学高明(注:参见候外庐等《宋明理学史》第二编第九章。)。袁宏道从张九成起步接受禅学,这注定了他的基本立足点是现世的,袁宏道的诗文创作中执著于表现个人的清高闲适的同时,又不乏对世道人心的关心这一矛盾现象,也就不难解释了。这样,他与李贽在人生观上的分歧日见,也是必然的了。袁宏道给李贽的最后一封信中说:“世人学道日进,而仆日退,近益学作下下根行。孔子曰:‘下学而上达。’枣柏曰:‘其知弥高,其行弥下。’始知古德教人修行持戒,即是向上事”,信中固然不乏自嘲意味,但更多的是对自己所选择的人生道路正确性的深信不疑。在某种意义上,这封信甚至不妨可以视为袁宏道宣告从此在总体思想上与李贽分道扬镳的绝交书。从此之后,李贽的影响开始淡出了袁宏道的生活。
其实,袁中道早在《中郎先生行状》中就指出了袁宏道思想上的这一变化:“戊戌,……逾年,先生之学复稍稍变,觉龙湖等所见,尚欠稳实。以为悟、修犹两毂也,向者所见,偏重悟理,而尽废修持,遣弃伦物,偭背绳墨,纵放习气,亦是膏肓之病。夫智尊则法天,礼卑而象地,有足无眼,与有眼无足者等。遂一矫而主修,自律甚严,自检甚密,以澹守之,以静凝之。”戊戌的次年是万历二十七年,恰好是袁宏道写《徐文长传》的同一年,这绝非是时间上的巧合。按通行的说法,袁宏道在接触了李贽之后,文学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此后的十年中即万历十八年至万历二十七年是公安派形成并发展的阶段。不过,袁宏道是万历三十八年下世的,袁宗道更是活到了天启四年。公安派在万历二十七年之后的流变也是这一流派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不加注意就谈不上把握了它的全貌。而说起公安派在后半阶段的发展状况,就不能不提到徐渭的影响。
袁宏道对徐渭的陷于痴迷的激赏,事实上也是他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发生了又一次重大变化的标志。徐渭在思想上的经历与袁宏道是有几分近似的,他从学文到学道,再浸淫于禅学,最后还是回到了现实人生。徐渭在《拟上督府书》中曾称“生平颇阅兵法,粗识大意,而究心时事,则其愚性之使然,亦遂忘其才之不逮”,信虽然是在徐渭进了胡宗宪幕下之后才之写的,但对时事和实务的关注,却贯穿了徐渭的终生,他的诗文创作就是其人生祈向的记录。从这点上说,袁宏道在看到了徐渭诗文之后的狂喜,就不仅仅是对他的文笔的欣赏了,其中不能不包括了遇到了人生追求的知音时的心灵振颤。徐渭对袁宏道的影响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此岸世界的执著。袁宏道在万历二十七年之后的创作与以前的相比,忧虑国计民生的作品明显增多了,如《答沈伯函》、《竹枝词》、《荆州后苦雪引》等揭露了万历矿税之祸;《显灵宫集诸公》、《冯琢庵师》、《答王继津大司马》、《与黄平倩》、《寿邹南皋先生六十序》等抒发了对国事日非而大贤不出的焦虑;《程母义行述》、《郑母节行始末》、《明司城陈君墓石志铭》、《题出世大孝册》等倡言化理道德。与在任吴县县令时的埋怨“抱牍之苦”相比,袁宏道在再任京官时从政的热情显然高了许多。他曾上《摘发巨奸疏》,严惩长期把持吏部事务的胥吏;他又上书尚书孙丕扬,直陈对吏部应该如何选取人才的意见;他甚至对公安派中的同志黄辉说出“每日一见邱报,必令人愤发裂眦,时事如此,将何底止?因念山中殊乐,不见此光景也。然世有陶唐,方有巢、许,万一世界扰扰,山中人岂得高枕?此亦静退者之忧也”的话来(注:袁宏道:《与黄平倩》。)。黄辉是以“好佛,茹斋持诵若老僧”出了名的(注:朱国桢:《涌幢小品·己丑馆选》。),并因此而受到了言官的弹劾而去职,变成不折不扣的“居士”。袁宏道竟然和他讨论起国事纷扰、个人出处的问题来,可见其用世的热忱确实今非昔比。也正是在这种精神状态下,袁宏道在《行素园存稿序》中提出“物之传者必以质,文之不传,非曰不工,质不至也。树之不实,非无花叶也;人之不泽,非无肤发也,文章亦尔”的观点,把内容视为诗文创作的第一要义,部分纠正了自己在前期创作中只重个人的情趣,而多少与客观的社会现实绝缘的倾向。如果认为袁宏道的创作思想和实践的这种改变是一个倒退或自我否定,那就会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强调作家对作品的主观情感投入,不应当成为否认文学与现实之间血脉相连的关系和理由。
此外,徐渭倡导的“彼之古者即我之今”,彻底否定复古主义;强调“本色”、“自然”,解决雅俗之间的矛盾;以“师以横从,不傍门户”的方式在作品中实现真实的自我等思想也在公安派的理论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其于公安派理论的建立和发展的重要性,至少是不逊于李贽的。前人对这些都有较为详尽的分析,在本文中就没有必要展开讨论了。要之,徐渭对公安派主张和创作的发展演变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他在思想上给予公安派的启迪,是一个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
本文1998年12月收到。
标签:徐渭论文; 袁宏道论文; 胡宗宪论文; 散文论文; 自为墓志铭论文; 大学论文; 公安派论文; 花论文; 季本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