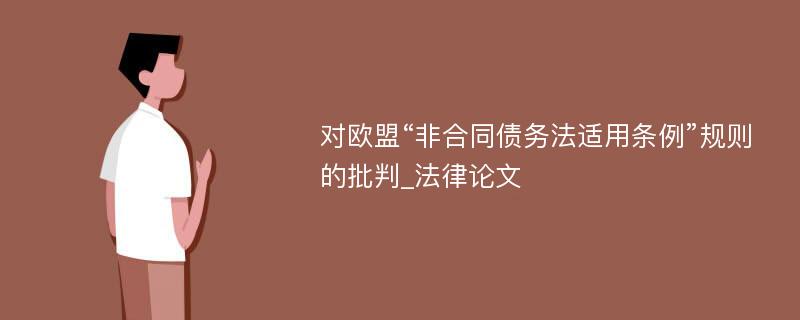
欧盟《非合同之债的法律适用条例》之规则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盟论文,条例论文,规则论文,合同论文,法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9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33(2009)12-0161-07
尽管欧共体各成员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相继进行了国际私法的法典编纂,但在非合同之债准据法领域的冲突规则并不一致。这与欧共体实现共同市场内部货物、资本、服务和人员自由流通的目标甚不相称。
《罗马条例Ⅱ》是欧洲国际私法统一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总结其规定,一方面,一般性规则给予“损害发生地法”和“共同惯常居所地法”以优先地位,增加了法律适用的可预见性。另一方面,例外条款软化了一般性规则的僵化性。此外,当某一问题需要由特别规则调整时,该一般规则将让位于特别规则。这些特别规则主要适用于产品责任、不正当竞争责任及限制自由竞争行为责任、环境损害责任、侵犯知识产权责任。另外,《罗马条例Ⅱ》还在非合同之债的准据法领域赋予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不可忽视的地位。所以,从立法技术上说,《罗马条例Ⅱ》的主要法律适用规则顺应了当今国际私法的发展趋势,增加了非合同之债法律适用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使欧共体在创制统一的国际私法规则方面向前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但是,任何一种制度都不可能做到天衣无缝,《罗马条例Ⅱ》的规则无疑不是完美的,但是否已经尽量好还令人怀疑。
一、对当事人事前选择准据法的限制与审查过于松散
关于当事人是否能够自由选择适用法律,《罗马条例Ⅱ》第14条规定:“1.双方当事人可以同意将非合同之债适用于他们选择的法律,通过:(1)造成损害的事件发生后订立的协议;或者(2)如果所有当事人都在从事商业行为,造成损害的事件发生前双方自由谈判达成的协议。选择必须是明示的或根据案件情况以合理的确定性表明的,不能影响第三人的权利和义务。2.如果造成损害的事件发生时,与案件情形有关的所有因素都位于非当事人选择法律所在国家以外的另一个国家,双方当事人的选择不能影响该国家法律中不能通过协议加以减损的法律条款的适用(“强制性条款”)①。3.如果造成损害的事件发生时,与案件情形有关的所有因素都位于一个或多个成员国家时,当事人选择非成员国的准据法将不影响共同体不能通过协议加以减损的法律条款的适用,如果在成员国法院执行是适当的。”
本条赋予了当事人自由选择适用法律的权利,但同时规定了必要的限制。第1款允许当事人自由选择适用于非合同之债的法律,与现代国际私法所追求的在更大范围内鼓励人们的自由意愿的目标是一致的。但自由选择须服从于下列限制:
(1)选择的时间:选择须在纠纷产生后进行,这样可避免事前选择对弱方当事人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当双方当事人都在实施商业活动时,选择可以在纠纷产生前进行。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处于平等的地位,他们有能力通过自由谈判作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
(2)选择的确定性:选择须是明示的,或根据案件情况以合理的确定性表明的,后一种情况留给法院一定的裁量权,有可能导致不一致的判决。
(3)选择的后果:选择不能影响第三人的权利和义务。
(4)第三国强制性规则限制:第3款规定同样是对自由意志的限制。当损害发生时,当所有除法律选择以外的案件因素都位于同一个国家,而该国家并不是双方当事人所选法律的所属国时,选择依然有效,但该国家不能通过协议加以减损的强制性规则必须被适用。实际上,本款涉及的纯粹是某一成员国的国内案件,之所以属于本条例的调整范围,唯一的原因是当事人选择了外国的法律。本款所指的强制性规则与本条例第13条②规范的“优先的强制性规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反映一个国家的国内公共秩序的,不能通过协议加以减损的规则,某个成员国旨在保护弱者的国内法律规则属于此类。而后者是指某成员国不能通过冲突法加以规避的法律。此外,它与第26条③所规范的法院地的公共秩序也须区别对待。
(5)共同体强制性规则限制:第4款是对第3款限制的扩展,适用于当所有的除法律选择以外的因素的都位于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内时的情形。该款规定的目的是防止当事人通过选择第三国家的法律逃避共同体法律中的强制性规则的适用④。
可见,《罗马条例Ⅱ》第14条规定了侵权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适用于其因侵权或不法行为引起的权利义务的法律。而且对侵权行为发生前与侵权行为发生后的法律选择作了区别。它允许所有当事人在侵权行为发生后进行法律选择,但在侵权行为发生前,只允许从事商业活动的当事人通过“自由协商(freely negotiated)”选择法律⑤。很明显,侵权行为发生后的法律选择并没有多少争议可言,因为侵权发生后,双方当事人在知晓本身的权利与义务方面处于相同的地位,他们可以根据事态情形,权衡法律选择的利弊。所以,这些协议实际上不太需要法律体制的审查,这样对于促进司法经济,节省司法成本也有好处。而在侵权行为发生前,双方当事人并不知晓谁将是责任方,谁将是受害方,以及损害的性质与程度,所以法律选择应当被禁止,如果没有被禁止,就需规定较高的审查标准。
遗憾的是,《罗马条例Ⅱ》第14条唯一规定的审查限制是双方当事人须“自由协商”并“从事商业活动”。这并不充分,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即使“商业活动”这个术语被欧盟予以明确定义或统一解释,它仍然包含一些由特许、许可或保险合同引起的单方关系。比如,一个特许合同是非常明确的商业行为,但被特许方通常处于讨价的弱势地位,这也正是很多国家颁布消费者保护类型的法律保护被许可方的原因。允许当事人在这些情况下事前选择适用法律,第14条并没有达到第31条声明所要求的“对选择施加特定的条件去保护弱方当事人”的期许。光凭第14条第2、3款的强制性规则条款,以及第26条规定的公共秩序条款来保护弱方当事人是根本不够的,因为这些条款距离可操作的地步还有一定差距。
二、《罗马条例Ⅱ》一般性规则中存在的瑕疵
关于侵权与不法行为的一般性规则,《罗马条例Ⅱ》第4条规定:“(1)除非本条例另有规定,适用于侵权或不法行为引起的非合同之债的法律,应当为损害发生地国家的法律,而不管引起损害的事件发生地国家,以及事件所引起的间接后果所在地国家在哪儿。(2)然而,当损害发生时,责任承担人与损害蒙受人在同一个国家拥有惯常居所地时,该国家的法律应当被适用。(3)当案件的所有情况清晰地表明,侵权或不法行为明显地与另一个国家,而非第1款或第2款所指定的国家,有更密切的联系时,该另一个国家的法律应当被适用。明显地与另一个国家联系更密切可以以与争议中的侵权或不法行为有密切联系的双方当事人已经存在的关系为基础,比如合同。它不适用于第5条至第9条规定的五类特殊侵权行为引起的非合同之债。”
该条第1款规定了确定准据法的基本规则——直接损害发生地或可能发生地国家的法律。《罗马条例Ⅱ》以直接损害发生地作为确定准据法的基本规则,有利于增强法律的确定性。该条第2款规定属于基本规则的例外——共同惯常居所地国家的法律,当双方当事人在损害发生时于同一个国家拥有惯常居所地时,这个国家的法律应当被适用。该规则反映了双方当事人的合理期望。该条第3款规定也属于基本规则的例外——最密切联系地国家的法律。它的目的是赋予僵硬的法律条款一定的弹性,使法院能够在具体的案件中适用反映案件“重力中心地”的法律。因为这样做有可能导致法律的不确定性,所以必须被例外适用。在决定非合同之债是否与另一个国家有明显的更密切联系时,允许法院考虑已经存在的约束双方当事人的关系。
(一)阿尔卑斯山脉雪崩案对直接损害地法规则的拷问
《罗马条例Ⅱ》第4条的一般性规则,是传统的侵权行为地法规则(lex loci delicti commissi)的重申,它与《美国第一次冲突法重述》(简称《第一次重述》)的相应规则⑥可归为同类。为了尽可能地避免措辞含糊,《第一次重述》规定了数个详细的限制性次规则。譬如,将人身损害案件中的损害发生地定义为有害性效果在身体上发生的地方,将中毒案件中的损害发生地定义为有毒性物质发生效力的地方。《第一次重述》中的规则虽然清晰明了,但却从未达到确定性的目的,该事实对于法典编纂的后来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深刻的教训。《罗马条例Ⅱ》的起草者注意到侵权行为地法原则是所有成员国解决非合同之债适用法律的基本方法⑦(尽管一些成员国家在一般规则外规定了一些例外条款),也注意到很多国家在“侵权行为地”的定义上存在分歧:有的成员国选择了行为地⑧,有的成员国选择了损害发生地⑨,有的成员国允许受害人或法院在二者之间进行选择⑩,而有的成员国在某些案件中适用行为地法,而在其他案件中适用损害发生地法(11),更有甚者,对此问题根本没有作出任何明确的回答(12)。《罗马条例Ⅱ》的起草者毫不含糊地选择损害发生地法来消除这些分歧,因为该方法有利于平衡受害人与责任人二者之间的利益,也反映了现代民事责任的承担方法(13)。
但是,损害发生地法规则在一些案件中并不能发挥较好的作用。我们假设一个案例:位于瑞士阿尔卑斯山的一家瑞士采矿公司实施爆破工作,结果造成法国阿尔卑斯山发生雪崩,一批在此旅游的英国游客因此受伤。瑞士为引起损害的事件发生地,法国为损害发生地,英国为事件引起的间接后果发生地。我们假设行为地国家对侵权行为人的行为标准与对受害人的保护标准高于损害发生地国家的规定。比如,瑞士法律对在特定地区或时段进行爆破行为的采矿经营者规定了本身过错制度。而法国为保护采矿工业,采用了一般过错标准。根据《罗马条例Ⅱ》第4条第1款的规定,应该适用直接损害发生地国家的法律,即法国法,而不管侵权行为发生地国家(瑞士)和间接结果发生地国家(英国)在哪儿。相反,如果这是环境侵权案件,《罗马条例Ⅱ》第7条允许受害人选择瑞士法律。起草者没有将此选择权扩展于其他侵权案件,理由是该解决方法“超出了受害人的合理期望”。而在环境侵权案件中,给予受害人选择法律的权利不是因为这样做对受害者有利,而是出于尊重行为地国家政策的目的,因为它是唯一一个不适用其法律就会有所损失的国家。在这样的案件中,瑞士的本身过错制度是为了阻止人们从事像爆破这样的本身危险性行为。因为被告是在瑞士境内行为的,瑞士在主张行为的法律后果方面具有充分的理由,即使在跨越边境发生损害的这类案件中。如果因为发生了国外损害而排除它的适用,该政策的阻止效力将大大受挫。而且,从公平与当事人期望的角度讲,对侵权行为人适用其行为地国家的法律是无任何不公平可言的。如果侵权人违反了该国家的标准,应当承担违反的法律后果,而不允许其启用其他国家的较低标准而逃避责任。相反,适用法国法律是没什么理由的,它的一般过错规则是为了保护在法国境内采矿的被告,而非在别国经营的外国经营者。
总之,在跨国侵权案件中,允许受害人或法院在行为地国家与损害发生地国家的法律之间进行选择是充满智慧的。《罗马条例Ⅱ》的起草者没有采纳与环境侵权案件中相似的规则是令人遗憾的。
(二)共同惯常居所地规则的不当适用范围
《罗马条例Ⅱ》第4条第2款首次明确提出损害发生地法的例外。它规定当损害发生时,责任承担人与损害蒙受人在同一个国家拥有惯常居所地时,该国家的法律应当被适用。关于产品责任的第5条、排他性地影响了特定竞争者利益的不公平竞争责任的第6条对此例外条款作了重申。值得注意的是,该例外条款并不适用于一般不公平竞争责任案件(第6条)、环境侵权责任案件(第7条)以及知识产权侵权责任案件(第8条)。我们可以推断,该例外条款隐含地承认涉及后者的案件包含了超越诉讼当事人个人利益的广泛社会利益。
在采用共同惯常居所地规则(The Common Habitual-Residence Rule)时,《罗马条例Ⅱ》吸取了近期国际私法典以及国际公约的经验(14),即当侵权行为人与受害人与同一个国家相关联(通过国籍、住所、惯常居所),该国对于决定二者的权利义务有最充分诉求时,即使侵权行为完全发生在另一个国家,该国家的法律应当被适用。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判决的50个涉及共同惯常居所地法律的案件中,大多数案件涉及“Babcock”型案件,即共同惯常居所地法律比行为地或损害地法律更有利于救济受害人(15)。这些案件呈现了典型的“虚假冲突(false conflict)”(16)特征,因为只有共同惯常居所地国家在适用其法律方面拥有利益。在其他涉及“converse-Babcock”型的案件中,共同惯常居所地法律相对于行为地和损害地法律,更加禁止或限制对受害人的救济。这些案件并不像“贝克”案那样具有明显的假性冲突特征,因为事故发生地国家在对其境内伤者进行赔偿以及促进当地医疗费用的取得方面具有适用其法律的明显利益。然而,在“Babcock”型案件或“converse-Babcock”类型案件中适用共同惯常居所地法律都是合理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不依赖于共同惯常居所地国家法律内容的共同惯常居所地规则是可以经久运用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案件所涉及的全是损失分配规则的冲突,而非行为调整规则的冲突(17)。而《罗马条例Ⅱ》的共同惯常居所地规则的范围不仅包括损失分配问题,而且包括行为调整问题。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作为一般看法,即使侵权人与受害人都不在某国居住,或者双方当事人共同在另一个国家居住,该国在实施行为调整规则上也是有利益的。
我们假设一个案例:某奥地利乘客在法国遭遇一起交通事故,该事故的发生是因违反法国交通规则的行为所导致,乘客所受损害也是由该行为引起。在此案件中,法国不可能拒绝对乘客提供保护,即使双方当事人共同在奥地利居住,法国也拥有将其法律适用于该案件中有关行为调整方面的权力。这些方面并不局限于公共法律规则或有关速度限制或红绿灯指示的交通规则,它们也扩展至因违反交通规则而应施加的民事责任方面的规则。因为《罗马条例Ⅱ》的共同惯常居所地规则是用封闭性语言规范的,所以它要求将奥地利法律适用于案件的所有方面。如果该规则不从属于任何逃避条款,问题将更加糟糕。《罗马条例Ⅱ》的该规则虽然从属于两个例外:第4条第3款规定的“最密切联系”规则与第17条规定的“安全与行为规则”,但使这两个例外规则发挥作用却并不容易。
从另一个不同角度来看,《罗马条例Ⅱ》的共同惯常居所地规则的适用范围是狭窄的。因为它仅仅适用于双方当事人在同一个国家居住的情形,而不适用于双方当事人不在同一个国家居住,但遵守相同法律的情形。更好的做法应当是对后一种情况与前一情况作相同处理。
我们假设一个案例:一个法国猎手在肯尼亚狩猎时,伤害了某与其没有任何事前关系的比利时猎手,而法国法律与比利时法律规定了相同的损害赔偿数量,而且该数量比肯尼亚法律规定得高。这是一个典型的虚假冲突,在此法律冲突中,肯尼亚在适用其损害赔偿法律上没有任何利益,因此适用肯尼亚法律没有任何理由。任何一个合理人都会认为要么应该适用法国法律,要么应该适用比利时法律。而《罗马条例Ⅱ》第4条第1款要求适用肯尼亚法律。而且不幸的是,《罗马条例Ⅱ》关于侵权行为地法的所有例外规则都无法解决该问题。
(三)一揽子适用最密切联系逃避规则的缺陷
《罗马条例Ⅱ》第4条第3款规定了一个在近代欧洲法典与国际公约中常见的例外条款,它既可以背离第1款的侵权行为地法律规则,也可以逃避共同惯常居所地法律规则,那就是“最密切联系逃避规则”。第3款还列举了一个具体情况,“明显地与另一个国家联系更密切”可以建立在双方当事人的先前关系的基础上,比如与争议中的侵权或不法行为有密切联系的合同。《罗马条例Ⅱ》的最初草案将该逃避条款的范围限定在一般规则管辖的案件中,即特殊规则管辖的案件并不能适用该例外条款。但《罗马条例Ⅱ》最后文本将其范围扩展到了产品责任(第5条第2款)、排他性地影响了某个具体竞争者利益的不公平竞争责任(第6条第2款)以及法律选择协议(第14条第2款)中。尽管在范围与措辞上存在瑕疵,但作者仍然庆幸《罗马条例Ⅱ》的最后文本包括了该逃避条款。实际上,逃避条款在任何法定制度中都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在法律制度的世界里很难存在完美,越来越多的立法者开始承认法律规范的易错性。逃避条款几乎已经成为近代所有法典的普遍特征。正如亚里士多德在许多世纪前所承认的那样,任何“事前规则(pre-formulated rule)”,不管多么仔细与明智地被起草,基于其一般性或特别性(18),很可能产生与起草目的相反的结果。这是“法律制定不同于法律适用的自然结果。”(19)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是该逃避条款能在多大程度上弥补《罗马条例Ⅱ》一般规则的不足。
逃避条款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它不允许逐个主题的分析与评估。只有整个侵权与不法行为明显地与另一个国家联系更密切时才能启动它的适用。法院不能分开审查可能由同一个事实引起的不同债务,比如当案件涉及多个侵权行为人或受害人时。相反,逃避条款的表述迫使法院将侵权行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如果发现作为一个整体的侵权行为与另一个国家有更密切的联系,法院有权以该国家的法律整体地取代其他适用法。所以,该逃避条款是一个“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命题,这也是其最严重的缺陷。
逃避条款的该缺陷使得它只能在显而易见的案件中发挥作用。比如,在阿尔卑斯山脉雪崩案例中,使法院相信“侵权或不法行为”整体(而非过错本身或危险限制)“明显地”与瑞士具有更密切的联系将是困难的。即使受害人的住所地(英国)允许无限危险,法院也不能避免法国法律的适用,因为与英国的联系可能称不上明显地比法国更密切。
在影响受害人赔偿方面,也同样存在以上提到的问题。我们仍以阿尔卑斯山脉雪崩案为例,假设雪崩导致了某个英国游客的死亡,该案件的一个问题是谁有权对其不正当死亡要求赔偿。假如根据法国法律,该权利授予受害人的配偶与子女,而根据英国法,只有受害人的配偶有权利要求赔偿,而子女无此权利。依据第4条第1款,适用法律应当是损害发生地国家(法国)的法律,而不管事件的间接结果发生在哪个国家(英国)。《罗马条例Ⅱ》第15条反复强调,在这样的案件中,法国法律将实质性地适用于所有可能由侵权诉讼引起的问题,包括有权要求损害赔偿的个人,以及要求损害赔偿或救济的权利是否能够转让的问题等。然而,英国仍然是最密切地被涉及的,最有理由主张适用其法律的国家。旨在指定不当死亡案件受益人的规则反映了特定社会中,某人的死亡如何影响他的遗留者以及哪个遗留者最有可能需要赔偿的主张。该主张与价值判断属于一个受害人所生活的社会,而非损害发生于其领域的社会。在《罗马条例Ⅱ》的术语里,英国是明显地与不当死亡受益人有更密切联系的国家,即使它与其他问题可能不是联系最密切。然而,逃避条款不允许聚焦于具体问题,也不允许法院弥补规则的不足。
在共同惯常居所地规则范围内运用“最密切联系”逃避条款时,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假设两个奥地利人在法国发生交通事故,一个人可能主张,关于行为与安全的问题,法国比奥地利具有明显的更密切的联系,所以管辖法律应该是法国法。而该主张的问题是它与逃避条款的全盘性措辞是违背的,它不允许逐个主题分析,而是要求整个侵权与不法行为与另一个国家联系更密切。该措辞使得被奥地利法律管辖的整个侵权行为与法国联系更密切的主张很难说得通。只要稍微修改逃避条款就可以软化共同惯常居所地规则,在以上的案件或其他例外性案件以及规则负面地影响了第三人的案件中产生更多理性的结果。我们假设下列两个案例来说明该问题。第一个案例为,在葡萄牙发生一起单车交通事故致使车内的西班牙乘客受伤,而该交通事故的部分原因是道路状况有瑕疵。该西班牙乘客提起诉讼要求葡萄牙当地机构承担道路维护责任,而后葡萄牙当地机构控诉该汽车的西班牙司机对其在事故中的过错承担比较责任。而车内的司机与乘客是夫妻,而西班牙(而非葡萄牙)法律禁止夫妻间诉讼。(“西班牙乘客葡萄牙受伤案”)在这样的案件中,原告可以主张当地机构的诉求并不在共同惯常居所地规则的范围之内。但是,如果主张失败,避免适用西班牙法律的唯一方法将是延展最密切联系逃避条款的措辞。在第二个假设案例中,当地机构并没有卷入其中,汽车在葡萄牙被租赁,葡萄牙(而非西班牙)法律禁止夫妻间诉讼。受伤乘客启用西班牙法律起诉汽车的保险人与司机,而保险人启用葡萄牙法律拒绝赔付。同样,如果保险的赔付义务属于共同惯常居所地规则的范围,避免适用西班牙法律的唯一方法便是突破适用最密切联系逃避条款的障碍。
总之,最后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一个良好的逃避条款甚至能够改善较差的规则制度,也能够在法律的确定性与灵活性这两个永恒竞争目标间保持适当均衡。然而,逃避条款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内置灵活性才能达此效果。起草者钟情于不能吞噬(swallow)一般规则的严谨的逃避条款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一个过于严谨以至于鲜能利用的逃避条款,或在“要么全有要么全无”意义上的逃避条款,适用效果大打折扣。
(四)事前关系例外规则的意图模糊
《罗马条例Ⅱ》第4条第3款后一句话:明显地与另一个国家联系更密切可以以与争议中的侵权或不法行为有密切联系的双方当事人已经存在的关系为基础,比如合同。该例外条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起草者似是而非的意图:此种情况下,(1)是适用管辖事前关系(Pre-existing Relationship)的法律;(2)还是适用事前关系主要集中地国家的法律(20)。根据《罗马条例Ⅱ》的解释性报告,起草者倾向于第一个意图(21)。但《罗马条例Ⅱ》第4条第3款并没有像某些欧洲法典那样对此明确规定,这就导致了其他可能性的存在,也就是事前关系集中地国家法律的适用。的确,在某些案件中,两种情况可能会引出同一部法律。比如事前关系集中在A国的家庭关系,由该国的法律管辖。根据以上分析,法院将适用相同的法律于相关的侵权或不法行为之债。然而,如果事前关系是合同关系,那么合同关系集中地国家也是管辖其法律所属国家的一定性是无法保证的。比如该合同可能包含了适用B国法律的法律选择条款(22),即使该国家与该关系具有轻微而非充分的联系。在此种情况下,哪个国家将是更密切联系例外规则的候选国呢?B国不是,因为它没有足够密切的实际联系。A国具有实际联系,但适用A国法律将与该例外条款所追求的适用相同法律于侵权与合同关系的目的相违背。对侵权或不法行为之债适用与合同关系相同的法律虽然简便实用,但模糊的规定将导致相反的结果。
三、安全与行为规则的偏袒性适用
《罗马条例Ⅱ》第17条规定:在评定责任承担人的行为时,在目前适当的情况下(in so far as is appropriate),作为一个事实,应当考虑造成责任的事件发生当时与当地现行有效的安全与行为规则。根据条例第34条声明,它是指所有与安全与行为有关的规则。实际上,该独立条款的存在表明《罗马条例Ⅱ》勉强承认了行为调整规则与损失分配规则之间的区别。然而,该条款究竟是真实的法律选择规则,还仅仅是决定被告的过错(culpability)程度时指导分析相关事实的旁证,《罗马条例Ⅱ》并没有明确规定。虽然该条款的措辞明确揭示出后者的可能性,但是,对该问题进行分析是有价值的。如果该条款可以被当作法律选择规则而运用从而导致某国法律的适用,那么第17条就为《罗马条例Ⅱ》的所有法律适用规则提供了一个灵活性例外,特别是(1)在跨国侵权引起的法律冲突中,第4条第1款规定的损害发生地法规则;(2)在国内侵权引起的法律冲突中,第4条第2款规定的共同惯常居所地规则。然而不幸的是,将第17条转化为真正的法律选择条款具有以下几方面的障碍:第一,尽管使用了命令式的词语“必须”,但“考虑”一词又将此条款拉回到完全任意性的位置。第二,根据该条款,法院只需要简单地考虑安全与行为规则,而不必适用它。虽然条例本身并没有排除这些规则的适用,但解释性报告指出:考虑外国法律与适用外国法律并不是一回事,法院只适用冲突规则指定的法律,但它必须将其他法律作为一个事实点予以考虑。比如,为了计算损害赔偿数目而估算过错的严重程度或责任者的善意或恶意时(23)。此项解释,特别是“只”这个字,似乎将行为国家的安全与行为规则的适用予以排除。第三,这些规则将在“估算侵权行为人的行为时”被作为“事实”予以考虑。这个措辞与欧盟委员会的《罗马条例Ⅱ议案》相比,是相当狭窄的。议案规定这些规则应该在确定责任时被考虑。《罗马条例Ⅱ》的限制性表达将第17条减损至仅仅在如何估算侵权行为人的过错(culpability)时发挥证据性指导作用。
而且,《罗马条例Ⅱ》的起草者似乎想将该规定限制在更为狭窄的范围内,他们将其描述为侵权行为人的专用保护工具,受害人不能使用。《罗马条例Ⅱ》的第34条声明指出,为了保持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合理平衡,第17条是有必要的。《罗马条例Ⅱ议案》第一次审议时,委员会拒绝了欧洲议会提出的诽谤与不公平竞争责任不能适用第17条的建议,认为“没有任何原因能够剥夺该条款为这两类责任中的侵权行为人提供的保护。”(24)另外,解释性报告描述了这样一个属于第17条适用范围内的情形:侵权行为人遵守了行为所在国家的较低环境标准,而没有遵守损害所在地国家的较高标准,根据第17条,法院必须注意到侵权行为人已经遵守了其营业所在地国家的现行规则的事实(25)。作者认为,此种情形下,最关键的问题是,一个合理人是否应当预见到在某个国家实施的行为可能会在另一个国家产生损害,而非为侵权行为人过多地考虑。比如,在A国边境附近经营化工厂的人应当预见到风力有可能将工厂的排放物带入B国境内。在此情形下,不应该允许经营者适用A国的更低标准而获庇护,因为它与第7条追求的“污染者支付原则”是相冲突的。同样,在阿尔卑斯山脉雪崩案例中,于瑞士—法国边境的阿尔卑斯山从事爆破业务的瑞士经营者应当预见到它的操作将引起雪崩,某些雪崩将穿越法国边境。如果法国比瑞士实施较高的行为标准,经营者为什么被允许寻求瑞士法律的庇护呢?如果在这种情形下运用第17条保护侵权行为人,那么,在相反的情况下,即瑞士法律比法国法律施加了更高的爆破行为标准时,不运用相同的条款就很难说公正了。不管是基于国家利益还是单纯地为了诉讼当事人之间的公正,此案例都应当适用瑞士法律。经营者违反瑞士法律标准的事实隐含了瑞士国家监察边境行为的政策,虽然在本案中,行为结果发生在法国。相反这并不能体现隐含于法国较低标准下的政策,因为该规则是旨在保护和鼓励法国境内行为的。换句话说,这正是在美国冲突法中典型的“虚性冲突”,在这个法律冲突中,只有瑞士在适用它的法律上具有利益,或者至少应当考虑瑞士法律。如果起草者的意图是对侵权行为人有利时运用该条款,对受害人有利时却不运用该条款的话,很难说第17条是恰当的法律适用条款。
四、产品责任法律适用规则的缺陷
《罗马条例Ⅱ》第5条规定:“在不影响第4条第2款规定的情况下,适用于因产品造成的损害而引起的非合同之债的法律应当为:1.(1)损害发生时,损害蒙受人的惯常居所地国家的法律,如果该产品在该国家销售;如果不能,或者(2)产品取得地国家的法律,如果产品在该国家销售;如果不能,或者(3)损害发生地国家的法律,如果产品在该国家销售。然而,如果责任承担人不能合理地预见该产品或同类型产品会在第1、2、3款规定的准据法所属国家销售时,准据法应当是责任承担人的惯常居所地国家的法律。2.当案件的所有情况清晰地表明,侵权或不法行为明显地与另一个国家,而非第1款所指定的国家,有更密切的联系时,该另一个国家的法律应当被适用。明显地与另一个国家联系更密切可特别以与争议中的侵权或不法行为有密切联系的双方当事人已经存在的关系为基础,比如合同。”
《罗马条例Ⅱ》第5条规定了适用于由产品造成损害而引起的非合同之债的法律。第1款规定依次适用三个国家的法律:(1)受害人惯常居所地国家;(2)产品取得地国家(26);(3)损害发生地国家。每个国家法律的适用都必须依赖于产品是否在该国销售的事实。
我们假设某德国原告于埃及获得某产品,却在印度被其伤害,如果产品在德国销售,应当适用德国法律,如果产品不在德国而是在埃及销售,应当适用埃及法律,如果产品不在埃及而是在印度销售,则应当适用印度法。显然,虽然被告被允许反驳或证明,但证明产品在某个特定国家销售的责任是施加在原告身上的。而且,第1款的最后一句话明确给予被告抗辩权——如果被告证明了他不能够合理预见到争议产品或其同类产品在该国家销售,就可以不适用以上三个法律中的任何一个。按照字面意思讲,即使原告已经证明了(被告也没有反驳)产品实际上在某个特定的国家销售,被告依然可以通过证明他不能够合理预见到这种销售而进行抗辩。作者认为该条款对于被告是过于慷慨的。幸运的是,基于当代的销售模式,在大多数案件中,该抗辩并不能成功。但是,一旦抗辩成功,适用法律将是被告惯常居所地国家(27)的法律,而非第1款依次规定的三部法律。所以,如果产品是由日本被告制造的,日本法律将管辖该案件,当然是在日本法律比埃及或印度法律更有利于被告的情况下,因为若非如此,被告根本就不会启用该条抗辩理由。
《罗马条例Ⅱ》第5条不影响第4条第2款共同惯常居所地规则的适用,也就是说,如果原告与被告在同一个国家拥有惯常居所地,该国家的法律将排除其他法律而得以适用,即使产品并未在该国销售。所以,在以上的假设案例中,如果产品被德国被告制造,德国法律将被适用,即使产品并未在德国销售。而所有的第1款(包括惯常居所地法律的交叉适用)全部从属于一个例外条款,就是第2款规定的“明显地与另一个国家联系更密切”,该例外条款赋予法院这样的权利:或者背离第1款规定的顺序,适用其中的某一国法律;或者适用某一第1款并没有列入的法律,比如通过证明产品制造商所在地国家明显地比第1款中规定的国家与案件具有更为密切的联系,而适用前者的法律。
虽然《罗马条例Ⅱ》第5条措辞表达略显复杂,实际操作却比较简单,主要依赖于“产品在某一个国家销售”的基本条件是否容易满足。在如今这个市场全球化的时代,大多数案件并不需要过多的调查就可证明该条件。所以,第 5条将导致以下法律的适用:(1)少数案件适用原被告共同惯常居所地国家的法律;(2)大多数其他案件适用受害人惯常居所地国家的法律;少数案件适用产品获得地国家的法律;更少数案件适用损害发生地国家的法律。如果这些假设是正确的,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些结果是否容易被接受。虽然从抽象上讲,可能有很好的理由批评受害人居所地法律的适用,但在大多数案件中,该国家可能拥有至少一个或更多的额外联系。虽然这些额外联系的存在使受害人惯常居所地法律的适用更加立得住脚,但在缺乏该额外联系的案件中,第5条本身也应当是无可辩驳的。
另外,第5条没有区分受害人惯常居所地法律对受害人是否有利的情况提出了诸多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第5条是否对发达国家的居民有利,而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居民不利。在以上的案例中,被于埃及获得的日本产品在印度损害的德国原告将从德国法律中获得福利。然而,如果被于德国获得的德国产品在奥地利损害的印度原告,只能局限于印度法律的救济。如果产品责任法的目标仅仅是保证受害人损害赔偿的数量,对德国原告适用德国法,对印度原告适用印度法可能是立得住脚的。然而,产品责任法也旨在追求其他目标(28),比如阻止不安全产品的生产与传播。所以,反对在印度原告的案件中适用印度法具有很好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期望法院启用第5条的最密切联系例外条款来避免这个结果。公平地讲,由于产品责任冲突本身所固有的复杂性,完美的解决模式是不易被提出的。
虽然,《罗马条例Ⅱ》在法律适用规则上存在以上提到的各种不足,但须明确的一点是,并不能仅仅因为这些瑕疵,就全面否定它的的价值。毕竟,它在统一欧洲国际私法方面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另外,任何一种制度都无法全面保证适用结果的纯粹正义,对《罗马条例Ⅱ》我们也不能如此苛求。
收稿日期:2009-06-04
注释:
①欧盟国际私法中的强制性规则,大体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为普通强制性规则,包括国内强制性规则和保护性规则。此类规则不能被双方当事人协议减损或排除适用。另一类为国际强制性规则,也就是本章4.3.10所分析的内容,它包括法院地强制性规则、第三国强制性规则和形式有效的强制性规则,它们不能被冲突规范加以规避。我们应该将这两种强制性规则加以区分。
②详见本章4.3.10的分析。
③《罗马条例Ⅱ》第26条是关于公共秩序的条款。它规定:只有本条例所指定的国家的法律条款的适用明显地与法院地的公共秩序相抵触时,这种适用才可以被拒绝。
④Proposal for ROME Ⅱ,p.22,23.
⑤没有在事后选择的规定中,明确“自由协商”,并不意味事后选择并不需要自由协商,当然,事后选择也须在双方没有争议的情况下达成。显然,起草者是为了保证对事前法律选择协议的更高程度审查。
⑥American Law Institute,Restatement of Conflict of Laws § 377 Note (1933).
⑦ROME Ⅱ,recital (15).
⑧Austrian PIL ACT of 15 June 1978 § 48(1); Polish PIL ACT of 1965 art.33(1).
⑨Dutch PIL ACT,art.3(2); English PIL ACT of 1995 § 11 (subject to exceptions).
⑩EGBGB art 40(1); Italian PIL ACT of May 31,1995,art 62(1).
(11)Portuguese CIV.CODE,art.45(1) and(2); Swiss PIL ACT,art.133(2).
(12)Spanish CIV.CODE art.9; Greek CIV.CODE,art.26.
(13)ROME Ⅱ,recital (16).
(14)《路易斯安那州国际私法》、《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比利时国际私法法》以及《海牙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
(15)Symeon C.symenoids:Rome Ⅱ and Tort Conflicts,A Missed Opportunity,56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2008).
(16)这是美国教授柯里的“政府利益分析法”中出现的术语。柯里的政府利益分析法将法律冲突看成是政府利益的冲突。如果经过对有关政府利益的分析,只有一州(国)的政府对适用其法律和政策有利益,这时的冲突就是虚假冲突。
(17)根据1963年纽约法院的措辞,“行为调整规则”是那些管辖防止伤害发生的行为,具有预防效力的规则,“损失分配规则”是那些侵权行为发生后的禁止、转让或责任限制规则。
(18)Aristotle,NICOMACHEAN ETHICS,V.x 7.
(19)Peter Hay,Flexibility Versus Predictability and Uniformity in Choice of Law,226 RECUEIL DES COURS 281,291(1991-Ⅰ).
(20)如果事前关系仅仅是社会关系(比如邻居),而非法律关系,要求适用于侵权的法律与管辖该社会关系的法律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该社会关系可能不被任何法律管辖。但是,要求将关系集中地国家的法律适用于侵权问题,就不能说是没有意义。
(21)W.L.M.Explanatory Report for ROME Ⅱ,p.13.
(22)根据《1980罗马公约》、《罗马条例Ⅰ议案》的规定,当选择法律时,只有所有与案件情形有关的其他因素与另一个国家有联系时,B国的法律才不能被全部适用。即使这样,不被适用的程度也被限定在“影响了另一个国家不能被合同予以减损的法律的适用。
(23)W.L.M.Reese,Explanatory Report for ROME Ⅱ,art.13.
(24)Commission modified legislative proposal.COD/2003/0168 (Feb.21,2006).
(25)W.L.M.Explanatory Report for ROME Ⅱ.art.7.
(26)但是,第5条并没有对以下情形作出区分,产品是由受害人取得,还是由第三人(比如,购买者或运输者)取得,区分的重要性请参见:Symeonids,the Choices-of-Law Revolution 268-70,351-52.
(27)根据《罗马条例Ⅱ》第23条第1款的规定,如果被告是法人,它的主要营业地被看做是惯常居所地。
(28)ROME Ⅱ,recital(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