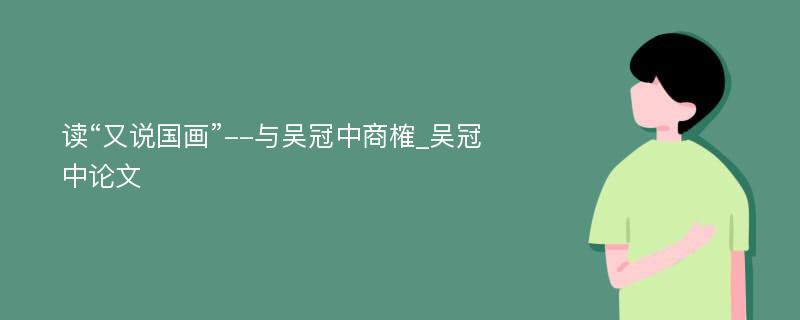
读“也说‘国画’——与吴冠中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画论文,也说论文,冠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记得我在拙稿《张大千“不做文人画家”、谢稚柳“不入一笔明清”的思考——兼论张大千、谢稚柳的绘画艺术》一文中曾就吴先生的“笔墨等于零”说了一段话,现附录于此,聊作一管之见,尚乞童教授不吝赐教。拙见是:
纵观20世纪山水画和花鸟画,在极具成就的画家中没有出现百花竞秀的局面,原因很明显,那就是过度的“营养缺乏”,个个“石涛”、家家“吴齐”。一如徐建融根据谢稚柳的“传统观”所阐述的:“……至明清的文人画(包括正统派和野逸派)则萎靡成了‘池沼的一角’、‘萎靡地拖延了五六百年’,尽管有石涛、八大等成就辉映千古,但从整体上看,却是‘如花流水谢,春事都修’。”
在“山重水复疑无路”困境中萌生了吴冠中的“笔墨等于零”的出台。其实,吴先生的这一提法理应是无可厚非的,绘画艺术的最终目的是表现——表现自然万象和自然万象对画家的启发、感受,以及画家对自然万象的认识、理解,这是形而上的。笔墨只是一个载体,是微观的技法,技法是形而下的,它不是形而上的艺术理念。高明的艺术家不会为技法所役。所谓天人合一,是一种境界。就像传统不仅仅是笔墨一样,传统最核心的问题是生活。过分地纠缠和在意“笔墨”,抑或是潘天寿、朱屺瞻等在大写意花鸟画领域举步维艰、自始至终没能摆脱对单一的传统文人大写意花鸟画形式(构图、笔墨)的“勾金填彩”,在前人开采过的“矿井”里其乐无穷,以致在追求先贤“剩余价值”的同时置他们本身的资源宝库而不顾。要言之,潘、朱诸贤,成功在于对微观笔墨的过分考究,失败也是对微观笔墨的过分考究。
我之所以要引用自己这段话,是因为童教授举出的与吴先生商榷的具体而又有力的理由是:“何况明、清五百四十余年,一批卓有建树的画家,民国至解放后数十年,更有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傅抱石、李可染等,作品面目一新。”
既然童教授承认“确实,明代以来,‘仿’逐渐形成一种风气,清代更盛”,那么要“驳议”吴先生“‘国画’的特有制作法是抄袭,美其名曰临摹,曰仿。陈陈相因、千人一面的绘画形式却延续于几千年文化的民族中”的观点的支撑点就不应该是“何况明、清五百四十余年,一批卓有建树的画家,民国至解放后数十年,更有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傅抱石、李可染等,作品面目一新”。更何况童教授也说了“这种‘守成’的心态应该批判(古人也早批评过,如说:‘临摹工多,本资难化;笔墨悟后,格制难成’)”。
至于因“但所谓‘制作法’如果是指‘创作’法,则‘仿作’因寓有个人的‘性’、‘能’,也非‘千人一面’,还是具有欣赏的价值;而‘临摹’原是保留前人经典、佳作(古人谓‘移画’或‘传移摹写’)以及学习的一种手段,怎么可以一起说成为‘国画’的特有制作法是抄袭呢?”显现“具有欣赏的价值”、“保留前人经典、佳作”而“面目一新”的是“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傅抱石、李可染等”。窃以为,童先生所列举的诸贤,其之所以“闪光”,究其本质,原本是明代徐青藤、清代朱若极、朱耷这三颗“恒星”的光芒折射所致。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如果我们稍作回忆,“文革”后“文艺复兴”的中国画画坛,山水画,莫不特别张扬“笔墨当随时代”,然究其“内涵”却无出石涛的藩篱。尽管我们不否认石涛是“叛逆四王”的锐意革新者,但,作为石涛身后250余年的画家仅以石涛为“传统的典范”而其笔墨“创新”的标志却又以类石涛的意蕴为荣光,那么,众口一词且重复不已的“笔墨当随时代”岂不成了一句名副其实的自我嘲弄?这是否可说是对延续千余年的中国画传统本质内容的一叶障目?
此外,再加上一部分学者、画家对董其昌的“以径之奇怪论,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决不如画”以及后来黄宾虹“研发”的“七墨法”的过度“推崇”,“笔墨”就理所当然的成了中国画的代名词或曰第一要素,浸淫笔墨、玩弄笔墨的新奇竟成了山水画家们苦思冥想且企望不择手段以求达到“创新”的目的,自然物象、山川丘壑从此便“沦落”为服从并服务于笔墨抒写的小前提。而这一本末倒置、远离生活的“创作理念”及至到今天,也依旧非常盛行。结果如何呢?石涛之后且以其为“精神”、“血脉”的山水画家能为人称道的又有几人?不刻薄地去“点将”,好像也只有黄宾虹、傅抱石、李可染、陆俨少数人而已。形象地比喻,如果说石涛是一颗巨大的“恒星”,那么黄、傅、李、陆也就是围绕着这颗“恒星”运转的“石涛系行星”。除此而外,我们似乎并没有遨游中国绘画更广袤幽深的大千世界。
山水画领域是这样,花鸟画领域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吴昌硕、齐白石之后,接步者虽阵容庞大,可惜的是,翼图在大写意花鸟画领域再有所作为者,客气一点说是“寥若晨星”,刻薄一点说是“每况愈下”。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真正领会吴湖帆先生秘而不宣的感叹:石涛的画“后学者风靡从之,坠入魔道,不可问矣。”傅抱石先生的“吴昌硕风靡画坛,中国画荒谬绝伦!”从而对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吴昌硕、齐白石是中国大写意花鸟画殿堂里的最后一缕香火”以及后来的“中国画穷途末路论”和“废纸论”产生某种程度上的认同。
如果说,“五四”以后深锁“国画”的有那么一堵究竟“是聪明人、傻子”还是“奴才”筑就的无形的“墙”,那么因此而持不同见解者,极力为这堵“墙”加固的“钢筋混凝土”便是明清以后(“中国人的艺术智慧,造就了写‘心目界之所有’的中国画,成为世界上独特卓异的一个绘画高峰,我们后代子孙必须自尊、自信、自强、自立,必须坚持主体性,延续其精华,并且使之更宽、更高、更大”)的“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傅抱石、李可染等”。
其实,这是一种浅薄、狭隘的“捍卫‘国画’”的“神圣职责”。
既然如此肯定“‘中国画’有没有‘墙’?这要看如何看待。从发展的眼光看,没有墙。汉人、唐人何曾立墙?宋人元人何曾立墙?”那么为何要树立“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傅抱石、李可染等”这堵“中国画应有的标准”的“墙”?这堵“墙”的“根深蒂固”岂不是“忽略”了明以前的中国绘画艺术和二十世纪一批勇于和善于“吸收外国绘画的长处”并有所成就的艺术家?这是不是可以说是童教授“芥蒂太深,以致概念不伦,莫知所云”?
因为我们在童教授“捍卫‘国画’”的“砝码”里,并没有看到明以前的画家,同时也“回避”了20世纪一批勇于和善于“吸收外国绘画的长处”并有所成就的艺术家。尽管童教授罗列了《易睽卦·象传》、《周易·系辞》里的一些“法理”,可是,《易睽卦·象传》、《周易·系辞》里的一些“法理”不知早“国画”这一名词诞生多少年,尽管“‘国画’一词诞生何年何月,我无研究”。
谈到“正宗”与“异种”,可能不仅仅是吴先生所说的“传教士传来了西洋画,中国人看那洋画,毕竟是异种,于是乎我们传统了几千年的画法为‘国画’,以示‘正宗’”。吴先生这一说法很宽厚,因为在某些人的“心目中”,“正宗”的“国画”不是“传统了几千年”,而只是传统了几百年亦即明以后的“文人画”而已。研究表明,恣肆、野逸是“文人画”,然“文人画”并非就是恣肆、野逸,“文人画”是传统的中国绘画,但传统的中国绘画并非仅是“文人画”。这是一个不可以混淆的概念!以研究“文人画”这一中国传统绘画表现形式中的一个小小支流就自诩为是在研究中国传统绘画,只能说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童教授说得很好,这一“症结是在画的‘标准’上”。明以前画家绘画的“标准”是生活,明以后画家绘画的“标准”是笔墨。唯笔墨技法论,从而也就衍生了“‘中国画’的表现方法,最基本同时也是最高的标准,是‘笔墨’”。
所谓“唐画山水,至宋始备”,原来这“始备”的核心问题是生活的蒙养。
董源创为江南山水画派,他的笔墨线条是基于江南之山土多于石,而他的水墨韵致则是源于江南多雨这一雨水充沛环境特征;范宽的北方刚劲雄强的山水画,则是北方石多土少、山石峥嵘以及空旷少雨这一地理形貌所形成。山水画的理法“至宋始备”,根本问题是古人的创作是“师造化”,通过对自然万象的仔细观察、写生来揭示自然的规律和发现自然的美,最后提炼出既符合自然规律,也合乎画家自身性格特征和审美要求的笔墨技法来实现状物寄情的目的,这正是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所说的“景者,制度时因,搜妙创真”,以及五代荆浩在其《笔法记》中明确表示的那样:“画者,画也,度物象而取其真。”
宋元山水画家之所以成为中国山水画史上一座照耀千古的丰碑,诚如张大千先生所言:“画家当以天地为师,不可拘泥一格,所谓造化在手耶!”明清山水画风神气象不及宋元,究其实质是为宋元的笔墨技法所牵制,忽视“制度时因,搜妙创真”和“度物象而取其真”。所谓“近师某某,远师宋元诸家”云云,成了衡量一个画家成就高下的标准,似乎只要笔墨“拟某某”或“远师”了宋元某某、某某的传统,就成了“学有渊源”、“根正苗红”、“集古今之大成”的传统大画家,唯独不注重笔墨源于真山真水这一最核心的传统。尽管他们的口中还时常念叨“师古人之心,不蹈古人之迹”,可究竟有多少人去真正践行宋元人“造化在手”、“度物象而取其真”、“制度时因,搜妙创真”这一“以天地为师”的创作理念?纵观明以降的山水画家,有谁能像宋元画家那样以真山真水为师创立一种既能体现某一地域山貌又有个性色彩且具美学价值的表现技法或曰皴法?这大概就是吴先生所指出的“‘国画’特有的制作法是抄袭,美其名曰临摹,曰仿。陈陈相因、千人一面的绘画形式却延续于几千年文化的民族中,是骄傲,是悲哀!”吧?
童教授说“吴先生的‘西中结合’,也是一堵墙。我的看法,还是各自为‘家’,各自治好自己的‘家’,固基扩充,兴旺发达,既不硬去挤进人家的墙门,也不去推倒他家的围墙。吴先生望‘中国画’之墙而欲推倒之,没有必要。”我以为是对吴先生观点的曲解。
“西中结合”,不是一堵墙,而是一个不妨为之实践(实则已经有不少人早就实践了)的途径。1957年5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中国画院成立大会上的致辞中就说过这样一句话:“希望北京中国画院今后能团结中国的画家,继承中国绘画的优秀传统,吸收外国绘画的长处,努力创作,加强研究,不断提高,培养后代,让百花齐放、众美争妍,为创造社会主义中国的新美术而斗争。”在这篇致辞中,周总理也曾就“中国画”这一说法妥不妥提出了可以开展讨论的建议。
再言之,“西中结合”的最终使命不是“硬去挤进人家的墙门”和“推倒他家的围墙”。如果说西中文化的结合就是要“硬去挤进人家的墙门”和“推倒他家的围墙”,那么,我们今天的改革开发岂不是大错特错?“吸收外国绘画的长处”又作何等的解释呢?无视他人的长处的“各自为‘家’,各自治好自己的‘家’”,实际上是一种妄自尊大的狭隘民族保守意识。“国画”之墙不是非倒不可,而是已经倒了不少年了。徐悲鸿、张大千、刘海粟、王季千、林风眠、及至现在的吴冠中、黄永玉、陈佩秋、刘国松等人的“西中结合”的成功实践,已经使得自明以后“陈陈相因,千人一面的绘画形式”的萎靡、酸腐、小气的画风相形见绌。固执地坚持“各自为‘家’,各自治好自己的‘家’”,是不是要我们义无反顾地废弃现代通讯技术,再回归到“飞鸽传书”的时代?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有关“国画”问题的讨论几乎没有中断过,正反两方的意见可谓水火不相容。但是,双方都是立身于各自“筑就”的一堵“墙”内向对方实施“火力”,但“炮声”消停之余,谁又能保证双方不在揣摩着对方的“火力”配置?
我在《徐悲鸿画马艺术谈及〈神骏图〉考》(《中国文物报》2005年8月31日)中就“笔墨”问题说了如下一段话:
一般说来,一个画家的笔墨特征,是构建在其习惯造型的基础上的,因为笔墨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是依附于结构的笔墨语言,也可说是形象元素符号,尤其像徐悲鸿这样风格特性十分明显的画家。
概言之,要想区别他人的笔墨,就得建立起非我莫属的造型特征,继而在这个基础上揣摩出又是非我莫属的笔墨语言。
徐悲鸿首先是一位油画家,因而他始终强调“绘画为造型艺术之主干”(《中国美术学院筹备志感》),在欧洲求学的几年里,严格而又残酷的物象造型、结构训练使得他对传统中国画的认识有了前瞻性的突破和令人深省的反思,对陈陈相因的传统笔墨训练,他用几近“矫枉过正”的呐喊,予以摧枯拉朽般的痛斥:“中国三百年来之绘画,承《芥子园画谱》之弊,放弃人天赋之观察能力,惟致意临抚摩(模)仿,视自然之美如无睹,其流毒之深,至于浑不似之四王山水之外,不得知有画。堕落若此!吾国固多名山大川,及极丰繁博富之花鸟草虫,但吾国犹有数千年可征信之历史,伟大之人物,种种民族生活状态,可供挥写,顾在最近以前,罕用以人画者。一种腐败衰颓之滥调,令人欲呕,世苟有观风者,以吾国近三百年之画视之,当深知此民族之不振矣。”(同上)
所以他大声疾呼“故欲振中国之艺术,必须重倡吾国美术之古典主义,如尊宋人尚繁密平等,画材不专山水。欲救目前之弊,必采欧洲之写实主义,如荷兰人体物之精,法国库尔贝、米勒、勒班习,德国莱柏尔等构境之雅。美术品贵精贵工,贵满贵足,写实之功成于是。”(《徐悲鸿用无线电演说美术》)
徐悲鸿赖以改良中国画的基础就是欧洲的写实主义,他为之身体力行,顽强地践行着这一在他看来“美术品……必须有谨严之Style,如画如雕”(《世界美术之起源及其真谛》)的良方。
我想,徐悲鸿先生的“绘画为造型艺术之主干”,其与吴冠中先生“笔墨等于零”的要义并不相悖;而“故欲振中国之艺术,必须重倡吾国美术之古典主义,如尊宋人尚繁密平等,画材不专山水。欲救目前之弊,必采欧洲之写实主义,如荷兰人体物之精,法国库尔贝、米勒、勒班习,德国莱柏尔等构境之雅。美术品贵精贵工,贵满贵足,写实之功成于是。”当是开吴冠中先生“西中结合”之先河。
在我看来,吴先生“西中结合”的艺术观念是历史的必然,吴先生“西中结合”的艺术实践是时代的必然。
杰出的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认为,艺术家和科学家一样,一生都在追求真理,所不同的是,科学家面对的是大自然,艺术家面对的是整个人类。在李先生看来,吴先生的艺术是超越时间、空间和跨越文化的,是无国界的。所谓“艺冠中外”,舍“西中结合”何以为之?
英国牛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荣誉院士、著名美术史家和艺术批评家苏立民(Michael Sullivan)教授认为,吴冠中先生成功地将东西方艺术融会贯通,他抽象的画法极具影响力。并就现当代艺术形成的挑战及画家如何有选择性地加以探讨,认为关键是要真实、真诚,对生活、大自然和艺术充满激情并具备表达这些感情的技巧。我想,这大概就是奥地利著名表现主义画家席勒关于艺术创作所主张的三个冲动,即:面对描写对象内心的感性冲动、找到表达自己感性冲动的形式冲动,以及消除感性冲动中自然要求和形式冲动中理性要求的游戏冲动。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文艺理论家王文章先生就非常肯定吴先生“笔墨等于零”、“风筝不断线”这一富有哲理性的艺术思想,并提醒人们:要完整、全面地理解吴冠中先生真正的思想含意,关键在于要弄清楚究竟是什么样的笔墨等于零。
由此,我有如是想,即:童教授之所以认为“吴先生的‘西中结合’,也是一堵墙”,是因为童教授并没有“完整、全面地理解吴冠中先生真正的思想含意”,也没有“弄清楚究竟是什么样的笔墨等于零”。究其实质,在童教授的心目中“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傅抱石、李可染等”这堵“墙”实在是太高、太厚了。如果说童教授的“不得不辩”是“一针见血”,那么这一“一针见血”恰是凸显了其自身对“国画”的狭见。当下指着稍有“偏离”“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傅抱石、李可染等”“传统”的画说“这不是国画,那不是国画”的人确实是大有人在,而这与“于油画、版画有何损害?”无涉。
套用童教授的一句话,那就是:童先生是一位教授。创作或观念上的“狭见”,可以促成其本人的艺术个性。但唯我独是、发为普遍性的“思想”,以一己的是非为是非,难免翻为谬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