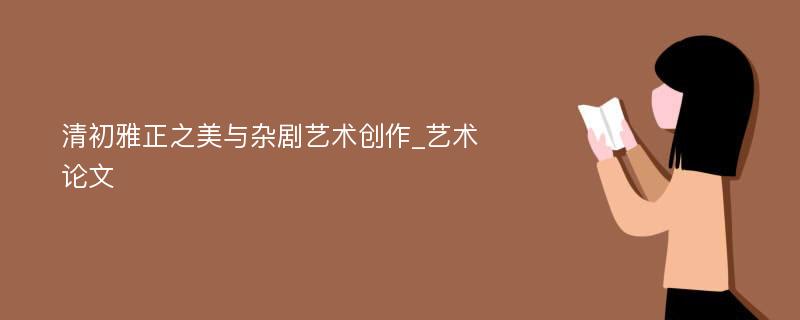
雅正之美与清初杂剧的艺术构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杂剧论文,清初论文,之美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初杂剧既有对前代杂剧的总体继承,更体现了因袭明杂剧同时的进一步发展。尤其在审美品格方面,基本上沿着明杂剧的运行轨迹并且趋向了更为雅正的发展方向。郑振铎说:“尝观清代三百年间之剧本,无不力求超蜕凡蹊,屏绝俚鄙。故失之雅,失之弱,容或有之。若失之鄙野,则可免讥矣。”[1]即是对这一审美走向的准确把握。有关清初杂剧雅正审美品格之艺术构成,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理解。
一、抒情原则的基本确立与叙事观念的淡化
中国戏曲在本质上属于叙事文学,但这种叙事往往通过抒情而实现。元杂剧虽然体现出了比较典型的叙事文学特征,仍以写情为主,戏曲作家始终相信“惟情至,可以造立世界”[2]。在文本形态中,也以轻事重情为特征,许多不合理的行为,不合逻辑的性格发展,以及那些与创作观念相违的情节,一旦与主观的情感联系起来,便获得了充分的存在依据。吴梅所谓“元剧之胜,正在荒唐”[3],正是对这一艺术特色的高度概括。而且也恰恰是这种情在笔先,“把某种情感的抒发、某种意境的凝结作为最高宗旨,并以情感结节为建造结构的基本出发点”[4]的叙述方略,为中国戏曲赢得了民族特色。
“情”不仅成为依然统摄戏曲作品的灵魂,也成为戏曲创作的首要目的,为杂剧后来回归“诗言志”的雅文学传统埋下了伏笔。尤其是那些专门表达书生愤世的作品,通过对历史性题材的重新诠释,借以表达自己的情感或价值取向,为元以后杂剧对主体之情的高扬提供了借鉴,最终确立了杂剧“以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的抒情原则。清初杂剧作家亦往往从个人情志需要的角度选择杂剧题材,并将之归附于有关雅正的审美追求。他们多重视选择那些富有情感内涵的故事,建构历史与现实、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同构对应关系,借以表达作者之身世怀抱。如吴伟业,身处舆图换稿的非常时期,个人的思想感情经历了巨大的磨折,内心的块垒无以释放,便选择处于历史变乱时期的沈炯作为审视对象,以其在国破家亡之际观念情感上的忧思徘徊为切入点,展示其怀才不遇无所适从的尴尬处境。杂剧作品《通天台》处处以情取胜,主人公那隐微复杂的情感犹如一条红线贯穿整个作品,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也成为作品独具魅力之所在。也就是说,作品的关注视点并不在其情节的曲折与否,而只重视写人——那个隐藏在剧中人身后的作者自己以及他的意志与情愫。难怪清初另一位杂剧作家尤侗在《读离骚自序》中再三提醒读者:“后之君子读其文因之有感,或者垂涕想见其为人。”正因为如此,杂剧作者的声音常常打断文本情节的运行规则或超越人物形象的性格逻辑而凸显出来。
杂剧文体本身也为抒情原则的确立给予了技术层面的保证。如本为主角制的杂剧角色系统已不再限定末本或旦本,上场人物全凭主人公抒发内在情感的方便,开始忽略排场的动静、冷热以及文场与武场的搭配等等,许多作品为了突出主要人物的情感世界,甚至将其他脚色驱赶净尽,往往只有一两个脚色当场。如吴伟业《通天台》第一折,只有沈炯和一个书童出场,郑瑜《鹦鹉洲》只有祢衡与一只鹦鹉,而廖燕的《醉画图》通篇仅一个人物,并且作者公开宣称为这个脚色就是他自己。又如关目本是排场结构关系的表达,文人为了刻意情感结构的营造,不惜损伤排场结构,当然也无暇顾及关目的起伏、转折、照应等等,完全以“情”为出发点,以叙事服从抒情。往往是,杂剧作品担当了个体情感的苦闷发泄,完整而有一定长度的发泄终止了,一部剧作也就宣告结束。此外,体制的短小也为抒情的集中提供了便利。一本四折的体制不再是唯一,而一本一折、一本多折等则获得了普及,作家往往因抒情的需要而设计体制的长度,避免了元杂剧为适应一本四折的体制而强行作戏的尴尬。南北曲的自由运用更为抒情的强度以及个性化提供了保证,尤其是南曲的引入,不但改变了北曲“调长而节促”的单一音乐结构,而且加强了杂剧整体上悠扬婉转的抒情效果,表达情感也更加细腻、婉约。
杂剧抒情原则的确立,固然说明了随着人类自我意识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主体情感体验和表达的重要性,以及在不同时空中的个体生命所达成的精神共识。然而,对因叙事的发达而成熟起来的戏曲而言,叙事的短缺毕竟是一个致命的短处。与同时期的传奇相比,清初杂剧作品无法容纳曲折复杂摇曳多姿的情节,当然也难以细腻全面地刻画人物的性格构成,构成叙事的许多因素都围绕着情感运动这一核心,总体上体现着逐渐淡出的态势。如王夫之的《龙舟会》,是清初杂剧中叙事比较完整的作品之一,线索清晰,人物性格的刻画也相当出色,但是整个作品并不仅仅以情节的整一性追求作为创作目的,而是倾力于一种悲愤情绪的抒发,这种情绪仿佛作品的精神浮标,若隐若显地浮游于情节运行的过程中,规定着情节的发展,并且通过叙事策略的帮助逐渐凝聚起来,在作品的结尾喷薄而出。也就是说,情感总是依托于具体的情境,缘事而发,叙事则同时为抒情提供环境,使其获得集中有效地阐发,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向。因此,清初杂剧虽仍有叙事的大量存在,但它在许多时候沦为抒情的一种手段,重要的已经不是“事”的内容——这些“事”读者多已耳熟能详,而是由“事”引出的“情”,“事”只是引发作家创作兴奋点的触媒,“情”才是作家创作所要追求的结果。
时间和空间是构成叙事的重要因素。陆九渊曾说:“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6]清初杂剧作家恰是凭借这样的观念建构杂剧,从而关注叙事技巧之于时空的关系的。一般而言,空间是由人物带出的,比较单纯、充裕,主要为主体抒情的需要而提供,往往一个场面即可以达成创作的旨归。时间则变化较多,但基本上是按照情感的自然变化而顺延,依从抒情的实际需要而运动。如沈炯在通天台下的时间表达是非常自由的,第二折的梦境描写,表面上是一种回溯,实际却是指向未来的,显示出抒情主体介入的痕迹。正是这种回溯式的时间变态中,作者表达了蛰伏于思想深处的有关出与入的矛盾心态。有时时间的流转是大跨度、高速度的,这又与情节的疏密程度相关,也就是说,情节越密,时间速度越慢,反之,情节越疏,时间速度越快。往往三五句话,就简要介绍了故事的来龙去脉,囊括的时间域则不仅是三天五天、三年五年,甚至是上下千年、几世几劫。杨义说:“叙事时间速度,在本质上是人对世界和历史的感觉的折射,是一种‘主观时间’的展示。”[7]与文本疏密之间所形成的叙事节奏,正是作家情感节奏的反映,所以,化主观时间为心灵时间是清初杂剧在叙事上的一个重要特色。
对时间和空间的主体控制,使看似松散的结构带来了自由多维的向度,为情感的自由开合留下了充裕的空间。如郑瑜的《鹦鹉洲》表达了孤独的文士精神探索的过程,整个作品没有具体的情节,只有一条祢衡去岳阳楼会吕洞宾的路,只有一个在时空中自由遨游的祢衡形象,鹦鹉的形象与其说是“随意飞扬”的动物的精灵,毋宁说是祢衡精神的投影。通过祢衡与鹦鹉的对话,作者将汉末历史陈述一遍,发表了他对历史的种种认识与感想。认识与感想发表了,祢衡与鹦鹉也到了岳阳楼,作品也在一种孤寂冷峻的氛围中接近了尾声。作为戏曲文本所应有的叙事也在这种孤寂冷峻的情绪中被彻底消解。
二、题材的历史性追求与文士趣味的凸显
在中国古代,始终有通俗艺术形式借鉴历史普及历史知识的传统,而历史生活的可叙述性又使历史题材在叙事材料上弥补了想象与虚构的不足,因此,历史剧发达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特色。清初,因时代文化风尚的濡染,戏曲创作也不可避免地强调崇古,表现出对古代题材的格外青睐,历史或历史传说中的人物大规模地进入创作视野,借古写心几乎成为杂剧作家不约而同的艺术追求。然而,由于传奇与杂剧之间的文体差异,传奇偏重叙事,杂剧偏重抒情,其有关题材的历史性追求也迥然有别。也就是说,尽管在“纵发欲言”和“笔墨之巧”方面杂剧仍存在优势,题材选择和历史性叙事所要达到的却主要是随心所欲抒发主体情感的目的,而这样的情感主要是文人禀赋的具有雅文化特征的情感。
对题材的历史性追求首先要面对题材熟烂的问题,但杂剧作家显然没有陷入因缺少题材创新而带来的尴尬,他们力求在旧瓶中造出新酒,通过对带有人类普遍经验的情感的摹写,抒发个性化的情怀,寻求知音式的理解。一句话,就是通过情感的灌入,达到一种陌生化的艺术效果,从而升华自我乃至读者的情感。在清初杂剧中,多是前代文人反复吟咏或叙说过的题材,如王昭君的故事、屈原的故事、陶渊明的故事、李白的故事等等,题材的创新意识对中国古代的杂剧作家而言永远不是它的本身,他们头脑中所要追求的新奇除了情节的奇幻,更多地落实在具有感性的现实指向的“人情物理”上。如王昭君故事,仅戏曲领域已出现过多部制作,如马致远的《汉宫秋》、陈与郊的《昭君出塞》、无名氏的《和戎记》、薛旦的《昭君梦》,另有关汉卿的《元帝哭昭君》、张时起的《昭君出塞》、吴昌龄《月夜走昭君》等,皆不传。其中,马致远的《汉宫秋》杂剧更是一座难以企及的高峰,寻求超越几不可能。尤侗的《吊琵琶》杂剧,题材本身已难有出新之可能,立意方面也并没有实质性突破,但仅仅是加入蔡文姬的吊祭,就如平地高峰,使《吊琵琶》突兀而起,具有了独立的审美内涵,成为清初杂剧的佼佼者。作品通过蔡文姬的吊祭,表达一种惺惺相惜的情怀,借两代佳人的悲剧命运,寄寓了作者才高命薄的怨愤,为题材的出新别开一片洞天,在当时即就有“名家杂剧已为压卷”[7]之誉。香港学者曾影靖指出:“作者以蔡文姬哀吊昭君冢作结,亦是出人意表之笔。因二者同是伤心苦命人,借清笳之拍,以极哀艳之思,调促音长,余音袅袅,缠绵欲绝,使人唏嘘再三。”[8]实际上,正是一种抒情的需求使文人泄露出生命的偶然感悟,往往超越了日常生活的局限性,洞察到生命的本质及悲剧意义,并赢得了古今才人的声气相应。
因此,在具体的题材选择中,对人的关注仍然是作者构思的起点。杂剧作者往往选择与自己身世境遇容易契合的题材本事,通过个人视角的确立,建构起自身与人物之间的同构对应关系,通过个性化的理解方式和情感渗透传达一种全新的美学信息。这就是艺术形象的自喻特性。吴伟业身处易代之际,面临着出与处的矛盾,便关注沈炯类处于动乱之际的历史人物,通过杂剧创作表达自己的思考;尤侗一生以才子自居,却始终才高而不见用于时,落拓不遇的感伤,也引导他观照屈原、陶渊明、李白一类大才子的身世经历,等等。这种人物形象的自喻特点几乎构成了清初杂剧塑造人物的首要手段,为作者充分表达他们之于命途多舛际遇的伤感、贤愚颠倒现实的愤慨,寄托他们尘世的理想与恢弘的人生愿望提供了素材与审美的张力。
人物塑造的自喻特征,不仅仅喻示着古人的为我所用,更重要的是促成了作家代古人立言,充分展示个性化的价值追求。这样,人的活动、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以及人的性格与命运等构成了清初杂剧最富于魅力的景观,从而也为其抒情原则的确立提供了生动的依凭。后来的吴梅曾总结说:“自来帝王卿相,神仙鬼怪,皆不可随意而为之,古今富贵寿考,如郭令公者,能有几人?惟填词家能以一身兼之。我欲为帝王,则垂衣端冕,俨然纶綍之音。我欲为神仙,则霞佩云裙,如带朝真之驾。推之万事万物,莫不称心所愿,屠门大嚼,聊且快意。士大夫伏处蘧庐,送穷无术,惟此一种文字,足泄其抑塞磊落不平之气,借彼笔底之烟霞,吐我胸中之云梦,不亦荒唐可乐乎?”[9]这一论述揭示了作家倾心古代题材的心理取向,也恰当地点出了杂剧作为一种审美艺术创造“称心而出,如题而止”[10]的创作特点。在这种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的创作过程中,一种历史为我所化用的崭新的历史观念逐渐形成。他们突破旧有的历史观念,化物理时间为心灵时间,任意地表现自己的情怀,发泄内心的苦闷,从而使感性与理性、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现实与历史达到了本质上的和谐,杂剧遂成为一种真正自由的审美艺术创造。当被封建专制异化了的情感在历史故事中展现时,作家已不是借古喻今,而是借古写心,主体的思想意志将历史故事、历史人物强化为一种个体的情感或情绪诉出,“我”不仅超越了历史,“我”亦能动于历史,历史心灵化成为杂剧崭新的审美追求。
应该说,对题材的历史性追求也是一种文人趣味的表现,这与明清以来作家基于性情之天然所进行的人文追求是一脉相承的,也是审美观念发展到近代时美学的一种新的表现形态。汤显祖在论及戏曲创作时强调“意趣神色”,李贽则直接涉及了题材的历史性追求,指出:“天下文章当以趣为第一。既是趣了,何必实有是事,并实有其人?”[11]清初的黄周星更是将之落实为感动人心的新异奇特的人事,以及这种人事带给人情感的冲荡”,指出:
制曲之诀,虽尽于“雅俗共赏”四字,仍可以一字括之,曰:趣。古云:“诗有别趣”,曲为诗之流派,且被之弦歌,自当专以趣胜……趣非独于诗酒花月中见之,凡属有情,如圣贤、豪杰之人,无非趣人;忠孝廉节之事,无非趣事。[13]
只要能够表达“趣”,无论今人古人。如此,向古人寻觅灵感并将之作为载体,便是时代赋予作家的优先权力了。
为了达成这样的创作旨归,清初杂剧作家对历史的阐释是能动的,也是艺术的,带有强烈的主观性与个性化色彩。无论是表达返璞归真的抑或是雍容典雅的趣味追求,多通过对古人古事的欣赏表现出来,并达成一种对逐渐失落的古典艺术或人文精神的追索,其与一般得之于自然之境的趣味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古人特有的精神气韵,他们对生活与人生的理解与把握,给现实中的人提供了典范与借鉴;同时,崇古本身便是一种风雅趣味的体现。正是在对古人古事的摹写过程中,文人与历史的关系拉近了,与现实的疏离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消解。
文人趣味还体现在对自我表达的关注,对世态人情的批判,以及对具有普遍性的人类情感的体悟诸方面。如张韬的《续四声猿》之一《王节使重续木兰诗》杂剧,有关王播发迹前所遭受到的种种待遇,作品并没有像以往的创作那样从头到尾一一加以交代、敷衍,只是截取他发迹后旧地重游的一个片断,以世态人情的视角将现实与历史加以对比,揭示了世态炎凉的现实,也交代出那一段尴尬的历史对他心灵的伤害,一个“重”字既写出令人百感交集的今昔对比——不仅是今昔的对比,还是贫富的对比、哀荣的对比、尊卑的对比,也表达了作者与王播一样的磊落不平之气。这样的感慨不仅具有历史的苍凉感,也带着个人的伤痛感,具有人类的普遍性。而如此处理题材,必然导致对结构的忽略,即作者只是根据情感的发展组织题材,当胸中之块垒得缓解后主题即已确立,结构始终处于开放的状态,适应着情感的要求。所以,杂剧的结尾往往余韵悠长,情味绵绵。
文人趣味凸显的直接后果,便是杂剧作家案头意识的强化以及场上意识的淡化。他们往往对登场与否并不在意,仅仅关注当下的情感自娱或抒情言志。比如尤侗的几部杂剧作品都有登场搬演的记录,但在谈及这类问题时,尤侗仍旧表现出抒情第一的原则,云:“不欲使潦倒乐工斟酌,吾辈只藏箧中,与二三知己,浮白歌呼,可消垒块。”[14]可见登场与否,并不是他从事创作的直接目的。另一位作家廖燕也在《诉琵琶》杂剧中声称:“文人唱曲,岂效优人伎俩,把手拍桌子应腔就是了。”既将杂剧创作当成了兴之所至的趣味追求,也反映出对抒情言志的情有独钟。而实际上,他们的创作也确实担负了这样的人生使命。
三、以曲为文与音乐结构对曲词的规定性
在中国古代的戏曲作品中,构成文本主体的曲词具有主导性的话语地位。李渔说:“言者,心之声也,欲代此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15]在“曲本位”观念的支配下,戏曲创作始终关注曲词而忽视宾白,对戏曲曲词的经营向为文士从事创作的重点,这也是曲体风格往往决定了文体特色的直接原因。
文词的典雅是审美观外化的一种表现。清初人追求博学,崇尚雅正,在创作中则往往体现出逞才的心理倾向,通过对典雅工丽语言风格的经营,促成了以诗词为剧的创作现实。许多作品的曲文继承了传统诗词情景交融的创作技巧,注重神韵的塑造与传达,为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丰富完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艺术经验。如吴伟业的《通天台》杂剧,曲词典丽,迂曲优美,意境深邃,随处可见古典诗词的常用意象,如果不是衬字和宾白的插入,俨然一篇情景交融的诗词作品。曾影靖指出:“梅村杂剧,文学成就极高,曲辞佳处,往往使人一唱三叹。”[16]当是切中肯綮之言。
情景交融的意境美向是诗词作家的审美追求,力求追求雅正之美的杂剧作家显然也没有忽略这一点。王国维曾云:“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17]在这一点上,清初杂剧作家有过之,他们始终注意将曲词的运用依托于特定的场景与情绪,倾尽才力营造意境,其对元杂剧曲词艺术的发扬光大是独具特色的。意境的构成作为作家审美追求的一个平台,不仅依靠清丽疏朗的曲词,还仰仗着复杂多维的情感构成,雅的审美趣味亦因之获得充分的展开与最大程度的呈现。
曲词的运用规则往往出自杂剧作家对话语策略的选择,其终极目的则是为了抒发那些饱含了个体人生经验的普泛性的人类情感。但曲词毕竟不同于诗词,其在戏曲结构中首先要求与音乐结构的有机统一,通过一种形式美传达出“曲情”,达到塑造艺术形象的目的。谭帆、陆炜指出:“‘曲’在古典戏剧艺术中乃是一种音乐和文学的综合体,它是古典戏剧艺术用以表现生活的最为基本而又最为重要的手段。”[18]南曲的高度发展所导致的北杂剧音乐结构的重建,促使本来结构单纯的音乐结构呈现为开放性的特点,与之对应的曲词也呈现出新的变化,适应了雅正的审美与文化追求。
首先,由于曲牌联缀规律的变化。原来相对稳定的套数规则被打破,独用的曲牌可以连用,连用的曲牌有时又单独出现,曲牌的联接次序发生了相当的变化,曲词愈加贴近个体情感的细微变化,抒情性获得了加强。如陆世廉《西台记》第一出所用之商调,在杂剧创作中应属于特例,作者为表达天崩地坼的凄苦冷寂的情绪也还贴切,但作者完全打破了惯例,首曲没有用规定的【集贤宾】,次曲也没有选广为认可的【逍遥乐】,反而将一般不用的【高阳台】连用了六次,显然是对商调曲牌联缀规律的破坏。如果说,作者对【集贤宾】、【逍遥乐】两个引导曲段的弃置不用是为了表现突兀而来的家国败亡之感,那么,【高阳台】的连用则主要是各个人物表达了自己于国变之际的忠贞态度,从关目的角度看是为了转入平缓的叙述,使情节发生转变。对于曲词的要求,则在于通过音乐结构的重复提高其抒情性,促使其进一步与叙事剥离,强化了清初杂剧对雅正之美的追求。
其次,宫调的联套方式也出现了新的变化。每一作品不再限定四套曲牌,宫调与情节的对应关系更加自由,也就是说,宫调一般只对应情感的内在发展逻辑,不必刻意去照应情节的起承转合,这导致曲词成为自足的审美载体,与叙事的要求愈加疏远。如南山逸史的《中郎女》,第一出写曹操为修国史而决心赎回流浪匈奴的蔡琰,用表现“感叹伤悲”的南吕宫,第二出写蔡文姬在匈奴苟活与思家的心情,用表现“陶写冷笑”的越调,第三出写如期返回的蔡文姬与董祀完婚,用表现“清新绵远”的仙吕,第四出表现蔡文姬的修史以及有关的历史评价用南北合套,且不说宫调与曲词所描写的情绪是否能够对应,仅元杂剧约定俗成的第一折用仙吕、第四折用双调的格式已不符,第二折用越调尚属正常,而第三折用仙吕宫在元杂剧中亦绝无仅有,但第四折通过北曲的激越雄健表达蔡文姬的英雄情怀,通过南曲的婉约柔弱表达男性的昏庸无能,体现出曲词在与音乐的配合中所要求的“以调合情”,还算比较贴切。
此外,南曲进入杂剧,并与北曲组合,南北曲自由运用,不但宫调可以借用,韵脚也可以重押,也导致曲词应变能力的增强。如徐石麒的《浮西施》,一反五湖同载之说,写范蠡在功成名就之后欲沉西施于江,西施不服,二人争辩,所选用的曲子便是一南一北,范蠡唱北曲,西施唱南曲,借助南曲的婉约表达西施的柔弱无辜,北曲的强健表达范蠡的自信与自私,对突出人物形象的主要特征非常贴切。总之,音乐结构的变迁使本来与诗词亲缘关系密切的曲词结构显得更为自由灵动,但并非是曲词俗化,而是使曲词雅化,向传统的诗词靠拢,促使曲词本身呈现出对抒情强烈的亲和倾向。实际上,这也逐渐消磨了杂剧文体对叙事的呼应,推动了杂剧趋向雅化的过程。
综上而论,审美品格在艺术上的诸种呈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杂剧这种曾借助了市井文化的繁荣而兴起的艺术样式逐渐完成了由俗至雅的转型,进入了自觉接受传统文化观念规约的发展过程。客观上,这确实提升了其在中国文化结构中的地位,但同时也促成了杂剧对其所禀赋的质朴鲜活的俗文化传统的背弃。殆到晚清时期,杂剧已彻底异化,成为一种“拟剧体”,此为后话,暂不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