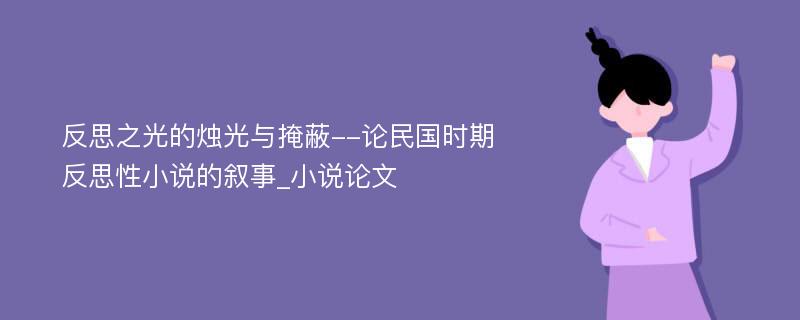
反思之光的烛照与遮蔽——试论反思小说对民国时代的叙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光论文,民国论文,试论论文,说对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当代小说一直未中断对民国时代的叙述,并在文化语境的制约下,形成了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产生了互不相同而又密切相关的主题,从革命主题、英雄话语、反思主潮到颠覆经典、大众视点、个体存在,构成了与中国当代文学相呼应、相印证的另一系统。本文仅就反思小说对民国时代的叙述加以概括论述。
一、批判“文革”的时代主潮
新时期文学的最初涌动是以对“文革”的反拨姿态出现的,这种反拨的出现来自两方面的规约,一方面来自意识形态,一方面是作家的内心需求,这和人们关于“文革”的心理阴影紧密联系在一起。就前者而言,伴随着“凡是”观念的瓦解,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出和党对诸多重大历史性问题所作的决议先后公诸于世,中国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威面临着挑战,作家要让作品重归主流,就必须在新的政治参数下重写历史,重新确定历史的延续性和合理性。于是他们纷纷反思“文革”,并开始怀念革命战争年代,从而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回声”。就后者而言,与人们的情感流向相应,当时文学人物画廊中最引人注目的形象是“受冤屈的英雄”,从现实题材的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到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曙光》,都包含一个“英雄历劫”的神话内核,一个被误解、遭放逐的主体通过考验被再度认可的故事。这一点就像雷蒙·阿朗所指出的那样,“知识分子又是与民族共同体息息相关;他们以一种特殊的尖锐形式体认国家的命运”(注:雷蒙·阿朗:《知识分子的鸦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第275页。)。
不过,这一时期纯正的民国叙事小说还比较少,只有《黄河东流去》、《漩流》、《功与罪》、《旋风》、《最后一个冬天》等为数不多的几篇。但作者的创作目的并不在于书写民国时代人们的生存状况及其精神内涵,而是通过拾取散落乡村的充满爱、真生命的文化智慧来重建和恢复十年浩劫中被破坏的价值理想,通过再现民国时代的复杂社会状况来恢复被文革小说“纯粹”掉的感性艺术世界。李準在谈《黄河东流去》的创作目的时说:“我要使人们看到这勤劳勇敢、吃苦耐劳和团结互爱精神的分量。”(注:李準:《我想告诉读者一点什么?——<黄河东流去>代后记》,《人
民日报》1984年9月10日。)
另有一些小说,虽然在这个阶段发表,但与反思主潮关系不大,如汪曾祺的《受戒》、《异秉》等,或“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或只是旧稿的修改,它们对民国时代的书写,由于对风土人情的注重、宽容精神的灌注等,实际已置换了原生的民国时代风貌,而且有了风俗文化小说的意味,其对文坛的影响与价值将在几年后得到彰显与发现。季红真就曾认为寻根文学最早的潮讯是汪曾祺的风俗短篇。(注:参见季红真:《历史的命题与时代抉择中的艺术嬗变——论“寻根文学”的发生意义》,《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1期。)。
当然,大多数作家创作时都无法回避现实,他们回眸革命历史时,总是企望用历史阐述并界定着现实,一般的做法是直接用历史阐述现实,在历史与现实的并置、对比中,通过肯定历史,来界定今天。如在《冬天里的春天》这类作品中,革命历史依然被视为遥远的过去,只有在与现实的对比中才能获得存在的价值。而它们对民国时期的认识则完全来自于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所积累下来文学话语的库存,根本没有认识到他们参照的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重大的位移,也没有认识到这种坐标其实只是文学叙述的结果。于是他们依据现实主旋律来重新观照和书写民国历史,并在此前提下专注于批判“文革”。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既阻碍了反思小说对民国时代精神的探寻,也阻碍了其对“文革”反思的深入。
这种状况被戴锦华概括为:中国共产党的“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权威结论这一历史定位,“无疑以充分的异质性,将‘文革’时代定位为中国社会‘正常肌体’上似可彻底剔除的‘癌变’,从而维护了政权、体制在话语层面的完整与延续,避免了反思质疑‘文革’所可能引发的政治危机;但完成一次深刻的社会转型所必需的意识形态合法化论证过程,却必然以清算‘文革’肇始”(注: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其实,正是其时“文革”的历史定位制约着作家对“文革”的反思程度,使反思小说往往越过了对民国时期充满复杂性与差异性历史的重新审视与考察;而正是由于这种越过,使对“文革”的反思最终是肤表化和简单化的。因“文革”的发生来自于国家制度、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国际形势、现代化追求等多种因素的合力作用,并不局限于“文革”十年。但如果对“文革”深究下去,有可能越过“文革”历史的疆界,触及现当代中国历史的某种延续性和同质性,或者最终显露出这一历史复杂的成因与繁复的过程。但这种可能并未成为现实,因当时的人们只是对极左思潮所导致的社会政治畸形深怀不满,而这种不满也是以十七年为参照系的,没认识到“文革”和人类固有的乌托邦冲动及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联系(注:参见许志英、丁帆主编《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正如孟悦所说:“新时期前期文学的主导倾向之一便是建构某种足以使人从废墟中站起,足以使人跨出恐怖和毁灭所缠绕的世界的拯救的乌托邦。”(注:孟悦:《叙事与历史》,《文艺争鸣》1990年第6期。)而现有的可供选择的价值理想无疑是由十七年小说所提供的,那种为理想而不惜生命、为他人而忍受苦难的奉献精神,与“文革”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鲜明对比。所以《冬天里的春天》、《黄河东流去》等都是作者历经磨难后的重构,他们在反思“文革”原因的同时尽力挖掘民族生存之根。李国文曾就《冬天里的春天》说:“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坚忍不拔,为什么有顽强的生命力,正是体现在这亿万勤劳的默默无闻的农民身上”(注:李国文:《我的歌——谈<冬天里的春天>的写作》,《文艺报》1982年第1期。)。对“文革”浩劫的批判和对人民、党的赞美同步进行,并行不悖。但“文革”是空穴来风吗?作家开始了自己的反思之旅。这使作家的反思之光有所烛照的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遮蔽;在对“文革”停留于简单否定的同时,向民国时代的革命历程寻求民族战胜劫难的精神力量。
二、反思之光的烛照与遮蔽
于是反思小说一方面毫无保留地赞美农民的质朴沉默及民国时期的军民鱼水之情,另方面又不无轻率地将“文革”发生的原因归结为个别人的破坏捣乱,从而使反思的理性之光仅仅烛照到一些“身份暧昧”的人物,至于这些人物所赖以生存的土壤、气候则被完全遮蔽。
其一,通过对比研读我们发现,反思小说为解答“文革”发生的根源而塑造的经历复杂、“身份暧昧”的人物形象却无心插柳地突破了以往的民国叙事,触及到了某种历史现象,但同时也使“文革”发生的真正原因处于遮蔽状态。
最早以“身份暧昧”者形象为主人公的是《内奸》,小说截取长达40年的全部变故中的几个横切面,并集中讲述了两个不同年代的两件密切关联的大事——抗战时期田玉堂、田有信巧妙地躲过日伪的耳目护送“表妹”就医和“文革”时期田玉堂对此事无法自我证明而深陷冤狱、田有信为了自己的官职而落井下石。田玉堂是交际场中的活跃人物,同时与共产党、国民党、日伪军来往密切,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服务于抗日战争。田有信作为传统文化的产物,是个随机应变的常胜者。民国时期他为生路而投靠田玉堂,“文革”中他又为仕途而出卖田玉堂,“文革”结束后仍稳当“父母官”。这是一部纵横交错的历史,田有信是中国这块土地上,不管风吹浪打,成长起来的一个“怪物”。无奈小说的目的乃在于反思,认为“文革”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田有信这类假共产党人的存在。这种叙事目的阻碍了小说对这一形象的深层挖掘,同时限于篇幅的短小与横切面的截取,田有信的行为动机、内心隐秘及其产生的文化根基未能得到充分展示,这在后来的王玮宇身上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弥补。
王玮宇是《冬天里的春天》中的人物形象。他是渔霸的儿子,出生在“高门楼”,因不满哥哥为他安排的婚姻而出走,投奔了游击队。艰苦的战斗生活使他动摇,想拿游击队作为与哥哥讲和的条件,因被芦花发现而落空,最后他杀人灭口打死芦花,并继续留在游击队;解放后他如鱼得水地搞土改,“文革”中春风得意地搞运动,“文革”后仍能适应形势发展。这是王纬宇的人生经历,很可以填补“问题人物”的形象空白。但由于小说以于而龙的行踪、思绪为主线来叙述故事,从而使王玮宇失去了自我呈现、自我辩解的可能,并带有着强烈的于而龙色彩。这样,王玮宇显得像一个有预谋地投靠游击队、混进革命队伍伺机破坏的奸细,而不大像一个因地主家庭内部的兄弟阋墙而向革命寻找个人出路的复杂角色。细心体察和善于思考的读者,也许能发现小说的叙述视点对王玮宇的形象所造成的扭曲与变异。但作者由此完成了自己的主题:王玮宇一贯狡诈狠毒,“文革”之所以发生,是因这样的人隐藏在党内。而“造就了这场文化革命的原因——历史本身从故事中一次次滑脱”(注:孟悦:《叙事与历史》,《文艺争鸣》1990年第6期。)。“文革”发生的真正原因依旧安然存在。
尽管如此,我们仍能透过于而龙视角所给小说世界覆盖上的厚密纱幕而窥视到王玮宇人物形象的真意所在:革命者并非一色的赤贫,革命队伍并非铁板一块。当然我们不是因革命队伍、革命目的的不纯而窃喜,没有这样的必要;我们只是设身处地地“悬想其事,遥体人情”,中国特有的“穷当兵富读书”正是对参军目的形象贴切的概括,出于各自不同的情况而选择走革命道路似乎更符合民国时期的社会状况。
或许作者始料未及,正是王玮宇这个人物突破了以往民国叙事中所形成的两阵对垒、界限分明的模式,模糊了两个阵营的边界,也在十七年小说所开始的、“文革”小说所强化的阶级分野之间画上了一条鲜明的连接线。或许是作者自我保护的策略性考虑,把王玮宇设置成一个混进党的奸细,但这条连接线毕竟客观存在着,它无声地昭示着一种新的写作方向。
其二,通过对比研读我们发现,反思小说为讴歌民族生存之根而塑造的正面人物形象承袭了十七年小说的民国叙事话语,但其描绘的普通生活场景却在某种程度上建构起了“文革”小说业已塌陷的感性艺术世界,恢复了民国时代的复杂含混。
在自认为找到了“文革”发生的原因后,作家们便放心大胆地在革命战争年代寻找民族的生存之根,并尽情讴歌。《剪辑错了的故事》认为民族复兴的根源在于“党的光荣传统”,《黄河东流去》认为农民的互帮互助、吃苦耐劳品质是民族的生存之根,小说用了绝大部分篇幅描写黄泛区下层民众为生存而吃苦耐劳:梁晴背盐、王跑赶脚、申奶奶教小孩如何要饭,这种令人辛酸的“美德”,其实只是生存环境恶劣的结果。《冬天里的春天》借助于而龙的思绪,将四十年的历史变迁和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融合交叉在一起,构成前后呼应和鲜明对比。其间不变的是: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十年内乱期间,民众都舍出性命来维护党,为革命的胜利默默地献出自己的一切,革命胜利后,又默默地过着依然困苦的日子。这种奉献精神正是作者所寻找的民族顽强生存的根源所在。李书磊曾说:“李国文用心理跳跃手法写成的《月食》把人民的麻木和容忍当成美德来歌颂。同样手法的《冬天里的春天》则把当代具有丰富文化意义的政治斗争概括为忠奸之争。”(注:李书磊《观念的进步与艺术的成熟》,《文学的文化含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页。)这种批评可谓一针见血,但考虑到作者情感的真诚、愿望的良好,更考虑到当时的言说语境:那时候,百废待兴,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理解了作者;而且作者的这种价值建构依赖于对民国历史的描述,芦花、小石头、李大波等这些人的身份、爱情、苦难与死亡都无一例外笼罩在革命的旗帜下,在他们身上我们会依稀看到娟子、朱老忠、小萝卜头的影子。他们与十七年小说描绘的民国时代的人们在生活状况与精神状态上毫无二致。
这样,反思小说的阅读效果便产生了令人回味的错位:为批判而塑造的“身份暧昧者”令人难以忘怀,并触及到了中国问题的根源,尽管由于思维惯性及作者的情绪化评价,未能深入挖掘,仅停留于个人品质层面;为讴歌而设计的正面人物形象因其承袭性叠印在一起,显得面目模糊,这是作者始料不及的。
但是正面人物的模糊重叠,并不意味着其生活环境的雷同化,实际上,反思小说很注意时代氛围和地域色彩的描绘。不论是《晚霞消失的时候》“宴会”一场中谈笑风生的人事交往,《剪辑错了的故事》中一棵枣树给困苦百姓带来的遐想与期望,还是《冬天里的春天》中对30年代石湖地区婚丧嫁娶风俗的描绘,都特意突出了乡土中国的小农经济关系下的人情世态,使人物获得了较为丰蕴的时代、文化等精神质素,并生活在一个特定的感性世界。
在《漩流》中,第五章写重庆千厮门河坝的早晨,浓雾未收,四川独特的河市中只有专卖洗脸水的摊铺敞开了铺门,形形色色的脸盆分为搪瓷盆、铜盆、木盆、瓦盆四大类,洗脸毛巾也相应地分为四个等级。洗一个脸,顾客的社会地位就分成了四等;街上,卖梆梆糕的白发老头敲着竹梆,叫卖着桂花糕……这些细致真切的细节,弥漫于全书各个章节的字里行间,一方面刻画了30年代天府之国的历史风貌,一方面为主人公朱佳富提供了充分感性的生活世界。《黄河东流去》中的“水上婚礼”集中反映中原大地农村风俗人情:窝棚作洞房,芦席、花格土布被子、包袱、铁锅、碗筷;唢呐吹出欢快的《上轿调》,看热闹的姑娘、小孩……这一切都构成了一幅感性生活画面,从而展示了中原大地农村的真实面貌。
这种对时代氛围和地域色彩的关注与刻画,使小说获得了坚实的感性支撑,而避免了空洞的理性说教。民国时代的历史画面由此显得五光十色,并鲜明独特起来。
其三,对“文革”时代的反思理所当然地带来了对“样板”模式的改造与超越,反思小说偏离了其纯粹英雄话语,并将立体人物性格和复杂社会状况勾连在一起,从而一定程度上再现了民国时代的精神风貌。
《剪辑错了的故事》中的甘书记,在革命战争时期为革命出生入死,处处为群众利益着想,在和平建设时期为了自己的政绩,不顾百姓的实际生活,甘愿违背自然规律“大放卫星”。《冬天里的春天》中的于而龙在战争年代,他和贫苦百姓同甘苦,共命运;解放后他更关注自己的仕途。可见,作者肯定的是革命者的过去(这与十七年小说的民国叙事话语毫无二致),批评的是革命者的现在(作者认为正是这种可怕的变化造成了“文革”的不可避免)。但革命者的蜕变无疑与社会结构性质的变化密不可分。
《旋风》则将士客籍之间的宗族械斗这一历史存在与革命斗争糅合在一起,既折射出社会生活的矛盾错综性,又写透了人物的特定历史处境和内在复杂生动。小说中的凤妹子,集时代、社会、宗族、阶级对她的影响于一身,她对赵泉生说的那句:“你是共产党,我就放了你;你是东塔人,我就杀了你”,是其宗族观念和帮会偏见的表现,而人物身上的这种时代、历史印记也为读者揭示了民国社会的复杂状况。《瀑布》也逼真地描写了民国时期的种种典型社会场景,新式军阀汤继舜、新式赃官王光宗出场和出巡的“威仪”和排场为读者充分展示了时代特色:绿呢大轿和双肩缀着金黄丝带的将军服,中式唢呐和西式的喇叭,清道、肃敬等传统“威仪”和下轿接见百姓的“新式”作风交错杂糅。
而《黄河东流去》以编年史的手法为我们展示了民国时代黄泛区农民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以至我们似乎听到他们的心跳,闻到他们身上的泥土气息。徐秋斋,一个在农村土生土长的教书先生,路见不平,常出谋相助,如闹盐行、为王跑索驴价;但他又过于世故、怯懦狡黠,对待蓝五和雪梅还有远近之别,在是否提醒梁晴上也顾虑重重;集智谋与狭隘于一体,是中国传统智慧同古老的农村生态环境凝聚而成的鲜活人物。与徐秋斋的“有所不为”相反,《漩流》中的朱佳富视目的高于一切,为使公司摆脱困境,用尽权谋机变:三次设计敲诈金四、小恩小惠网罗私人羽翼、借整顿船规打击异己、分化工人、平息罢工等,使涪陵轮船公司在短期内得到小小的复苏与发展。这个在内外交困的夹缝中残喘的资本家,在精神上是西方现代竞争意识与中国传统权谋文化的混血儿。
这种历史烙印和生存画面使人物获得了自己的具体性和生命力,一度被“文革”小说割舍掉的历史丰富性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恢复。
三、时空交错的叙述方式对客观化历史的冲击
民国历史作为小说反思“文革”的基点,需作为一个实体存在以构成与“文革”时代的对比,但几十年的时间跨度,使顺时序叙述显得笨拙而无效。主题表达的需要,促使作者去寻求更合适的叙述方式;电影蒙太奇手法和意识流小说的引进,也为当时叙述方式的更新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当然,“明晰的、单一的故事线被冲破,代之以复杂的、交错的抒情线,最根本的是由于作家们对社会现实的审美感受的结构发生了变化”(注:黄子平:《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26页。)。饱经忧患的人们对用连贯有序的故事线和恩怨相报的伦理圈子能否表现现实表示怀疑。于是他们放弃已往遵循的规则、理念,而开始依顺、尊重自己的情绪、感受,为了容纳“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这样巨大的时空容量,反思小说最终选取了时空交错的叙述方式,其中的复线条结构,放射线结构,以及无数的跳跃、切入、自由联想、时空变换,都对客观化叙述效果构成有力冲击。
《剪辑错了的故事》选取七个生活场景,并借助老寿的心理活动把它们组接在一起,有意略去情节之间的连贯性,打破正常的时间空间顺序,跳跃式地在现实、历史和梦幻之间巧妙地交织与相互间隔,从而使历史与现实并置,加大了两者的对比幅度:一方面是现实中左的虚假浮夸风给党和人民带来的政治、经济危害,另一方面是历史中党为革命出生入死、军民团结一心。而越过这种对比,我们看到一种历史的呼应,不变的内容便是日益贫困的民众生活。
作者明确突现自己的小说为“剪辑错了的故事”,暗示出顺时序叙述方式的深入人心,是正常叙述的代名词,是大家公认的“正确”剪辑;意味着作者对叙述方式创新的一种策略性定位,也是对顺时序叙述地位的一种承认与首肯。但限于短篇小说的篇幅和文体特征,《剪辑错了的故事》没有展开描述人物的历史联系,这一点由后来的《冬天里的春天》来补充完成了。
《冬天里的春天》以于而龙的行踪、回忆和联想为线索组织情节,使各种时间里的往事随着他飘忽不定的思绪穿插进来:30年代石湖地区生活状况与风俗、抗日战争中石湖支队和日本军队艰苦卓绝的战斗、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劳动热情、“文革”中种种颠倒与荒谬等波澜壮阔的历史生活画面都交错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从而把历史与现实交织起来,使二者发生联系,形成对比,并由此生发出许多富有启示意义的见解,“历史是一个任人装扮的女孩子啊!”“历史不惮其烦地重复,常常出现许多惊人的雷同之笔。”“错误是积累而成的,存在着许多历史渊源,决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在对自身经历的回顾中,于而龙意识到了历史的延续性、言说性。也许他的本意只是对自己与王纬宇40年交往的感慨,但无意中却对“历史在曲折中前进”的历史观进行了消解。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对历史新解的阐发与小说对时间的理解紧密相连,如果把作品中的时间还原后重新排列,我们就会发现小说依然保持着思维发展的连贯性,保持着故事情节的完整性和人物面貌的清晰度。即“意识流要流成情节,拼贴画的画幅之间又要有故事的联系”(注:张贤亮:《心灵和肉体的变化——关于短篇<灵与肉>的通讯》,《鸭绿江》1981年4月号)。李书磊也认为这种创新不过是人为的时间错置,它从本质上没有摆脱古典艺术的“线性圆形”的时间观念(注:参见李书磊:《文学的文化含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但它毕竟放弃了对事件进程的顺时叙述,并开始有意打碎有序的自然时间生活,把不同时间的历史事件并置在一起,产生出顺时序叙述所根本无法产生的叙述效果。
《内奸》虽未采用时空交错的叙述方式,但在讲述了1942年的“护送”事件后,经过几句概括的交待,便直接跳跃到此事在23年后给主人公带来的厄运,从而使不同时空的画面并置在一起。当年田玉堂凭借自己的善于交游,好吹好炫,随机应变而完成“护送”任务,现在田玉堂既不吹,又不炫,老老实实交待作证反而连遭毒打,被视为“内奸”;当年的护送之旅危险而巧妙,现在的审问过程残忍而武断。这一切既相互矛盾冲突,又缠绕纠结为一团,历史如此地矛盾荒诞,又是如此地顺理成章;到底哪个是历史的真实面目?
此外小说还有意突现叙述者的声音。如提醒读者注意历史的连贯与对比:“小戈这颗糖果不是好吃的,要以满嘴牙齿为代价。……但那是后话,我们还是往下说吧。”这种提示使我们看到了新潮小说“许多年后”语式的前身。也许作者只是借用中国白话小说、说唱文学的传统,让叙述者显形在文本中,但这种方式确实让读者感觉到叙述者的支配力量,显示出小说的讲述性。这种讲述性对客观化的历史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当然仍有许多小说采用传统叙述,《旋风》、《瀑布》等以中心人物的生活为主线,依照时间顺序展开故事情节,《黄河东流去》、《漩流》等则采纳了多头发展、事随人走的顺时序叙述;“文革”时代并未直接呈现在作品中,但反思“文革”的现实基点,使作者注意突破“文革”小说的民国叙事,变彻底政治化、简单化的纯粹英雄而为社会的、宗族的、性别的感性存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民国时代的复杂含混,当然这也是一种以意识形态观念为指归的复杂,这相比较于后来的新历史小说就能看得更清楚,对民国时代的个体化理解仍未出现。
不论是《内奸》的“讲述”他人故事,《剪辑错了的故事》的“剪辑”历史画面,还是《冬天里的春天》的回顾自我经历,叙述者表达的依然是相信历史、相信未来,对现实的怀疑是局部暂时的。其中对民国历史的叙述依然袭用了十七年小说的模式与见解,坚定的信仰、无畏的战斗、革命的魅力仍是民国人们的精神状态,“文革”的磨难成了人们信仰坚定与否的试金石,“文革”只是党内小部分人暂时得势的结果,在这个曲折之后,历史依然勇往直前。从此,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作家的反思仍然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另一方面也能体会到十七年小说所描述的民国历史对人们、对作家的影响之深,在作家几乎成了无需怀疑的历史真实。尽管《黄河东流去》、《冬天里的春天》没有突破十七年小说对民国叙事的经典模式与价值寻求,它们在历史与现实的对比中,肯定历史,否定现实。但这种局部否定毕竟撕开了怀疑的裂口,为后来刷新民国叙事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因怀疑既然已经出现,那也就无法控制、规定它所怀疑的对象;即对“文革”的深究,可能越过“文革”,而波及更远的历史,引起对民国历史的重新审视与书写。这简直是一定的,《灵旗》、《红高粱》的出现就是明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