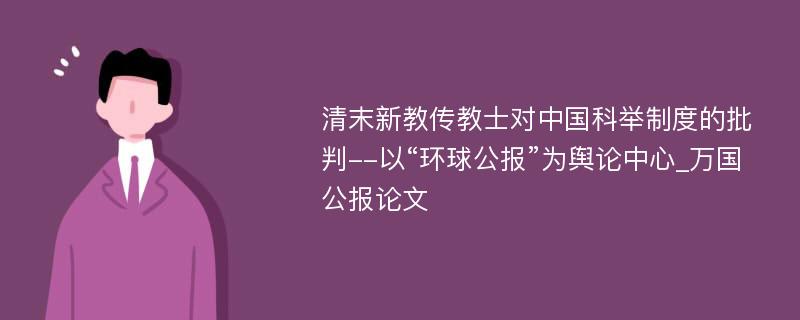
晚清来华新教传教士对中国科举制度的批判——以《万国公报》为舆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万国论文,新教论文,晚清论文,传教士论文,科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通过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但是,由于科举制度本身带有不可避免的弊端,自它正式实行之始,就不断有人提出批评意见和改革方案。特别是有清一代,不少有识之士多次对科举制度发表言辞激烈的批评意见。晚清来华新教传教士也纷纷加入进来,并以《万国公报》为主要舆论阵地,发表了许多尖锐的批评意见。
一、内容既单一又一成不变
清代科举考试,在内容上主要是考儒家的四书五经,连中国传统学问中的其他文史知识都不受重视,更甭说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由此造成文人和官吏知识贫乏、单一,思想僵化。因此,自19世纪70年代起,科举考试内容成为新教士批判的重点。
西教士对科举制度的批判首先是把它视为西方文化和新式教育在中国传播的障碍。1875年10月,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自办的《万国公报》上发表《中西关系论略》之文,把“大学问”分为“神理之学”、“人生当然之理”、“物理之学”三个部分或层次。他认为作为异教徒的中国士人对“神理之学”自然是漠然不知,对“格致之学”也只是“存其名”,而不知其实,所谓“诚正修齐治平之事”(即“人生当然之理”)也只是“伪知者”而已,若问这些人“何为诚正?何为修齐?何为治平?则茫乎莫解,与未学者等,谓之为士,其信然耶?”总之,中国士人没有真才实学,而造成的总根源正是科举制度。林乐知并不否认开科取士的本意很好,但是由于在考试内容(仅限于儒学)、形式(八股文、策论)上的致命错误,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他说:“中国开科取士立意甚良,而唯以文章试帖为专长,其策论则空衍了事也,无殊拘士之手足而不能运动,锢士之心思而不能灵活,蔽士之耳目而无何所见闻矣。”(注:《万国公报》,第358期,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第1583-1585页。)同年,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在《教化议》中同样指出人类的学问包含各种不同的学科和层次,每一学科各有其用,不能偏废。他说:“士有士之学,农有农之学,工有工之学,贾有贾之学,皆有至理存焉,非积学之士不能窥其堂奥。各学皆有其用,不容偏废。”但是,科举制度恰恰引导士人只重形而上的儒学,轻视形而下的艺学,并造成重科举、轻学校的社会风气,使学校教育废弛,“士人舍科目则无以为学,欲学他学,而苦无学之地,即能造其堂奥,亦徒劳而已”(注:《万国公报》,第554期,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第6630-6631页。)。1881年6月,丁立端发表《中国考试利弊论》,指出中国科举制度的两大弊端之一就是使人弃实学、崇“虚”、“伪”之学(注:“古之考以道德者,今则考以词章矣,古之考以功能者,今则考以诗赋矣,致使文人学士,皆舍真修而崇伪术,弃实学而务虚名,举毕生之聪明才力尽用之于诗词文章,无怪文章愈工人心愈刻也。”(《万国公报》,第643期,第8174-8175页。))。
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在山东登州积极创办教会学校,进行基督教、儒学、西学等综合教育。耐人寻味的是,他一方面鼓励自己的学生参加科举考试(注:1875年文会馆学生邹立文参加乡试,名列前茅,后来,郭中印考取为最后一届秀才,仲伟义则考取为附生。),另一方面却又严厉批评科举考试和传统教育。1881年,他在《振兴学校论》中,历数科举制度的弊端,其中一条就是“拘定学经书”,即把学问仅仅局限在儒家《四书》之内,而且以程朱理学为唯一准绳,由此引导士人只问儒学,不仅对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史书、诸子百家不闻不问,更不要说西方近代各种科学知识了。考试内容的片面、狭窄直接导致了学校教育内容的片面和狭窄(注:《万国公报》,第555期,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第6647-6649页。),主要表现为“唯知学古训”,排斥最新的知识(注:《万国公报》,第655期,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第8379-8381页。)。1889年,英国传教士韦廉臣在《治国要务》中也认为:中国士人“谬于一偏之见,而不能达观,拾五经之糟粕,拘八股为文章,而于天文、地理、算学、化学、重学诸大概置诸不论不议之列”,都是科举制度所直接造成的(注:《万国公报》,第654期,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第8361-8365页。)。
19世纪70至80年代,西教士对中国科举制度侧重于批判,并兼而提出改革意见,90年代后,随着维新运动的高涨,改科举、兴学堂的教育改革成为重要议题,西教士对中国教育问题关注的方式,转而侧重于提出改革科举制度和中国教育的建议,但仍然发表了一些批判科举制度的意见。其中,以林乐知最为典型。林乐知指出中国的教化曾经“先于天下”,“超于亚洲”,但千余年来毫无进步,其祸根就在于科举制度。他说中国教化的根基全在于“士”,朝廷治国也总是依靠“士”,“唯国家之所重者,专在于士,而以考试得官者目为正途出身”,但是,士人读的是四书五经,作的是五言八股,除此之外,一无所能。古往今来,社会已发生了很大变迁,知识亦随之而变,而士人所读之书皆为2000多年前的古书,他由此讽刺道,这样教化出来的士人,其品行、学术、识见岂不仍就是商周秦汉之人!(注:《万国公报》,复刊第84期,第15727-15728页。)中国教化怎不落后呢?
英国传教士麦嘉温在上海英文报纸《北华捷报》上发表文章着重批评中国文人的知识贫乏,“用西方的观点看,获得以上学位(即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等——引者注)所需要的知识是贫乏而有限的。在我们英国学生的眼里简直少得可笑。”因为他们所有的知识仅仅是来自于“对儒家经典深刻而又透彻的理解”,但是那些书籍“常常是晦涩难懂的,让人觉得提不起多少兴趣,它们从不触及人的生活,而只是谈论一些抽象的道德和哲学问题。这里面没有有关现实思想的课程,也没有对自然的研究来获得创造性的课程”,因此,他认为整个学习过程枯燥乏味,是对学生身心两方面的令人恐怖的折磨(注:[英]麦嘉温著、朱涛等译:《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时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46-49、62、83-87页。)。
美国传教士、外交官何天爵也曾经批评说中国的一切教育都是围绕着科举考试进行,从而使儒家经典成了唯一的教育内容。这些内容又怎样呢?首先它们都是从儒家经典中断章取义地摘抄而来;其次,都是“写于早在基督诞生的几百年前”,在今天,既难以理解,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注:[美]何天爵著、鞠方安译:《真正的中国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l75-189页。)。
二、“病国病民莫八股为甚”
明清科举考试文体采用八股文,文章必须采用固定的排偶文体,再加上只能依据朱熹的《四书集注》“代圣贤立言”,丝毫不能发挥自己的思想,从而造成士人们的思想僵化。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曾痛心疾首地指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坑儒”(注: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拟题》。)!晚清来华西教士同样对八股文体进行了批判。
花之安指出中国民众无真才、国家缺乏人才的祸根就在于科举制度“不得其法”。因为整个社会“唯科目则为正途,人皆趋于八股,不暇及于他学”。但是,每个人都各有所能、各有所长,“皆可为世用”,“不能学八股者,非不能学格致,不能学格致者,非不能学历算”,而科举中式的人毕竟只是少数。他由此批评道:“今屈天下之人才尽出于八股,使有才者不得伸,非病民而何?”进而指出八股文只是求得功名的工具或阶梯,根本不能经国治天下,“名卿巨公以经济之才治天下,非以八股之才治天下,明矣”,因此科举考试使中国士人“所学非所行,所用非所学”(注:《万国公报》,复刊第554期,第6630-6631页。)。韦廉臣则集中批判八股取士严重阻碍了中国科技的产生和发展。他指出西方知识分子百余年来用心探索自然,科学技术得以飞速发展。中西方人的智慧不相上下,科举制度却使中国士人都埋没于无用的八股文之中:“中人乃以有用之心思埋没于无用之八股,稍有志者但知从事于诗古文,矜才使气,空言无补。”(注:《万国公报》,复刊第555期,第6647-6649页。)
狄考文批评八股文,不仅不可能代圣贤立言,反而束缚士人思想。他说:“是为搭[答]题文法所限也,既不足益士子之大智,更不能阐圣道之渊源”。而且,仅以一篇文章定优劣,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这样选出来的人才仅为一偏之才,“要宜知人之能文,乃学问之偏端,非学问之全体。夫能文者,不必尽为博学,即博学者,亦不必尽能文也,……能文,特一偏之长也”(注:《万国公报》,复刊第385期,第2348-2349页。)。林乐知也直言八股取士不能使国家遴选到真才之士:“若夫朝廷得人而官之,固欲其能经国家、利社稷、定民人者也,乃取士之制,只凭制义试律,土饭尘羹,既空疏而无用,即条对经史、时务诸策,浮辞剿说,亦摭拾而无根”,总之,“所举非所用,所用非所举”(注:《万国公报》,复刊第654期,第8379-8381页。)。
科举制度使士人们终身耗费在陈旧的儒学和空疏的八股文之中,但最终能得第者只是少数,大半人必成落第者。林乐知感叹这样的人“进既不能奋于功名之路,退更不能免乎贫窭之嗟。”全家人由此将无以为生(注:《万国公报》,复刊第704期,第9262页。)!花之安则指出落第者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会铤而走险,沦为危害一方的游民、荡民,由此滋生社会动乱。他说:“中国游民甲于天下,其故在于教民不得其法,有志之人不甘为农工,舍八股无以为学,舍科目无以上进,不以正途取,必以偏途取,人皆趋于偏,是养乱之阶也”(注:《万国公报》,第555期,第6648页。)。
近代中国不断遭遇到数千年未有的强敌,西教士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然坚持实行八股取士制度已不合时势,因为空疏无用的八股文章,显然无助于拒强敌。在19世纪70年代,花之安较早地表明了这种观点。他指出今日中国四面强敌环伺,“今东则有日本,北则有俄罗斯,南之缅甸属于英,安南属于法国,四周皆强国。昔日为中国之屏藩,今则他人据而有之”,“大敌当前,岂赋一诗可能退,挥之八股可能服耶!”(注:《万国公报》,第556期,第6665页。)自80年代起,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更为险恶,林乐知故而重复了花之安的观点。他说:“万一疆场有警,讵一篇诗赋数行文字,即能成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功?”(注:《万国公报》,第704期,第9262页。)必须指出花之安、林乐知等西教士多次强调八股文章无助于中国拒强敌,并不是要劝导中国人抗击列强入侵,只不过是以此证明八股文章的空疏无用。花之安曾痛快淋漓地指出:“病国病民,莫八股为甚!”(注:《万国公报》,第555期,第6647页。)
晚清来华西教士对八股文的批判,上承清初士人顾炎武的观点,下联早期维新思想家、维新派等人的思想,但是言辞之激烈、尖锐程度,则远远超过后者。
三、关于“学而优则仕”
“学而优则仕”一直是中国古时读书人的共同追求,并随着科举制度的产生而强化。但是,“学而优则仕”的读书观本身带有非常明显的缺陷和消极影响,在日益多元化的近代社会中,其消极影响越发严重。西教士对“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教育观也进行了批判。
何天爵生动地刻画了弥漫在整个社会的读书做官论情形:“在中国,读书求学的一切动机和最高期望,就是要步入仕途。当每一名孩子由懵懂无知到渐谙人事而进入学堂时,他首先被灌输和想到的,便是读书做官,而所有父母在为孩子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时,他们念兹在兹的,也不过如此。”继而揭露它的毒害作用,因为许多人为此不光耗尽了青春年华,而且直到白发苍苍却仍是考场上的失意者,一代又一代中国读书人就是这样“在希望与失望、成功与痛苦之间苦苦挣扎,皓首穷经,孜孜以求。”(注:[美]何天爵著、鞠方安译:《真正的中国佬》,第186-187页。)
狄考文根据西方现代教育思想指出人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获取各种知识和理论。他说:“学问之足重者,其首益在能知,即上而天文,下而地理,远而物性,近而人身,及古今天下所有之事理尽列于学问中,凡学之者不独知其当然,又能知其所以然。”(注:《万国公报》,第654期,第8361-8365页。)并指出国家富强之本在于学校培养出为国所用的英才。当今世界,英才必须具有某方面的真才实学,“或专化学,或专格物,或专天文,或专算法,或专创造机器,以利农工,或专制作货物,以利商贾,此其所以蒸蒸日进之故也”。他直言以选官为目的科举制度使学校教育偏离了传授知识、培养真才的正轨,完全成为科举考试的预备场所,读书人则除了功名利禄,别无所求,何来真才?“今之势徒令人役志于功名,取其才而听其无用”(注:《万国公报》,第655期,第8379-8381页。)。林乐知更尖锐地指出选出来的士人根本就没有为官之才。因为他们只读从前的古书,作的是无用的八股文章,既不学习最新的知识,又不观察今日民情国事,为官之才从何而来?“考试得官之后,使之治今日之民,其能不仍如古之寂寞哉!”(注:《万国公报》,复刊第84期,第15727-15728页。)丁立端指出:“穷经将以致用,今之读书者率皆朝咏夕吟援作求荣之具,寻章摘句藉为士禄之阶,至问以意何以诚?心何以正?身何以修?则曰吾不暇计此。再问以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道何以不可离?可离则非道,彼则曰此圣贤工夫,吾不能用也。……所以逐日读书讲书,而书中之精意奥旨置若罔闻矣,虽读如不读也。”(注:《万国公报》,第643期,第8174-8175页。)狄考文劝导现在的年轻学者不宜再抱有传统的读书做官思想。他甚至认为一些人即使有为官之才,也不一定有为官之德,有才无德者万万不能为官(注:《万国公报》,第654期,第8361-8365页。)。特别是那些为了实现读书做官梦想,不惜采取夹带、请人代考、行贿、作弊等舞弊手段达到目的的人,一旦做官之后,又怎么能奢望他有为官之德呢?
这些西教士非常清楚根深蒂固的“学而优则仕”思想是中国建立新式学校教育制度的巨大障碍,因此,1898年,以在华新教传教士为主体组成的中国基督教教育会和广学会在拟定中国教育改革方案时,明确提出必须改变考试制度中的官本位制和应试者的官本位意识,“中国科场立法至为周密,然其藉考试以拔取人才者,乃只以网罗官吏之用,……士为四民之首,关系于国计民生者,岂有崖矣”,并计划通过报刊传媒大力宣传新的教育观,使年青的学子们明白除了入仕之途外,“尚有无限之事,足以有益于国,有益于己,而不必专恃为官”(注:《万国公报》,复刊第115期,第17866-17867页。)。
中国士人在晚清时期仍为传统教育观念所左右,因而唯有来华西教士率先起来彻底否定“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读书观,并且通过现代传媒宣传新的教育观,使年轻学子树立起通过新式学校教育获取新式知识的新式成才观。应该说,西教士们在《万国公报》进行这样的宣传是非常必要和有意义的,无疑具有开风气的积极作用。
四、泥古不化和排斥西学的根源
晚清时期中国传统士大夫死守孔孟之道、程朱理学,强烈排拒西学,泥古不化。故此,西教士纷纷发表文章,对其进行批判,并把守旧的根源归结为科举制度,为中国的借法自强运动大造舆论。
19世纪70年代,林乐知用对比的方法明确指出善变与守旧的不同正是导致西方富强与中国贫弱的直接原因。他说:“外国视古昔如孩提,视今时如成人,中国以古初为无加,以今时为不及。故西国有盛无衰,中国每颓而不振,西国万事争先,不甘落后,中国墨守成规不知善变,此弱与贫所由来也。不知泥古转以病今,今之时势何如?当审时度势而为之超乎古之上,合乎今之时,此识时务者为俊杰也。”(注:《万国公报》,第356期,第1528页。)他用进化的历史观指出古今时势不同,批评恪守“先王之道”的传统士大夫是食古不化:“以率由旧章为不违先王之道,而不知先王之道宜于古未必宜于今,今之时势非先王之时势矣”(注:《万国公报》,第358期,第1583页。)。为了说明中国如果继续固守旧法将无法实现强国富民的道理,他用换位思考的方法,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倘使将欧洲与中国人易地而居,不将中国兴而欧洲弱乎?即使欧洲人仍居欧洲,中国人仍居中国,而以中国治国之法治欧洲,欧洲能必其不弱乎?以欧洲治国之法治中国,中国未有不兴者也?”(注:《万国公报》,第392期,第2541页。)结果当然是不言自明的。
19世纪80年代,狄考文批评了中国“唯知学古训”的思想。他指出:“学问之道宜愈久而愈广,适如江河之流,必愈下而愈阔也,是以今不古若之说,人固不可发于口,而尤不可存于心”。他认为学问之道是永无止境,且愈求愈多,愈求愈新,“只因学问之道无尽,古人所未知者,今人务求知之,今人所未知者,尤斯于后人知之,于是进益之途愈引愈长,实为当然之下也。”并以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来证明这一道理,批评中国正统士大夫“唯知重古薄今,不思前进”(注:《万国公报》,第654期,第8362-8364页。)。狄考文提出今胜于古的思想,是从学理的角度对中国自古以来言必称三代、学必尊孔孟的泥古思想的有力批判,因而对中国思想的解放和新式教育的兴起具有一定启蒙作用。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于日本之后,寓华西人发表一系列文章总结中国失败的原因。林乐知认为这是“中国正坐不变之病”的明证(注:《万国公报》,复刊第82期,第15624页。),再次批判今日中国人“仍泥两千余年以上之说,而执其尽美之旧学,以与又尽善之新法为仇”(注:《万国公报》,复刊第85期,第15803页。)。19世纪90年代初,李提摩太在主笔的天津《时报》上,直斥阻碍借法自强运动的守旧势力“狃于见闻,蹈故安常,任情纷议”,是“不知为国家一深长思也”(注:李提摩太:《西法有益于民论》、《论中国易于富强》,见《皇朝经世文三编》卷三十四。),他说:“处今之势,岂犹可安常蹈故,而不知变计也!”(注:李提摩太:《西法有益于民论》、《论中国易于富强》,见《皇朝经世文三编》卷二十五。)随后,他又在《万国公报》发表文章,批判禁锢人们思想的汉宋之学。他说:“今天下号为读书好古之士,不外汉宋两途。专考据之学者,宗汉儒;务心性之学者,宗宋儒。一似极天下之能事,无出乎汉宋两朝之外者,何其迂谬固蔽,无用至于此极哉!”“动曰:西洋之法,我中国不当学也,无论其识之隘而不广也,明知西法之有益于生灵,而故为骄矜闪避,视吾民之颠连困苦,而莫之动,则其心之不仁,为何如乎?”(注:《万国公报》,复刊第117期,第18007-18009页。)20世纪初年,林乐知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天地不变,则孔子之道亦不变”的教条主义哲学。他说:“华人之推尊孔子者,往往[言]过其实,或云孔子为万代之师表,自有孔子则不但前无圣人,即后世亦永不能”,这种思想“实为中国守旧者之口实,亦即为中国教化阻滞之大原因”(注:林乐知:《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第十集上卷,第十章《教道》,第52页。)。
早在19世纪70年代,林乐知不仅批判中国传统士大夫食古不化,而且把守旧思想的根源直接归结为科举制度,他说:“中国士人何食古不化若斯哉!终年伏案功深,寻章摘句,以为束身于名教中也,而实为八股文章束缚其身耳,天下所望于士者安在?”(注:《万国公报》,第358期,第1583-1585页。)稍后,慕维廉也多次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以诗文弋取科名未免拘墟”(注:《万国公报》,第505期,第5417页。),“凡童蒙入塾读书,不特以四书五经而编简富有,惜泥乎古法,而不精究夫天地之功用也,士人考试每以诗文博取功名,未能黜华崇实,自号斯文,足为士林式,然于礼宾司义廉耻,仁义道德置若罔闻也。”(注:《万国公报》,第514期,第5671页。)韦廉臣则批评以科举制度为核心的传统教育迫使士人从小闭门读圣贤书,不问世事人情,从而造成见闻不广、思想守旧。他说:“弟子自束发授[受]书而后,或则杜门,或则闭户,世事不知,人情不解。盖恐其分心于外务也,而不知其锢弟子之聪明,蔽弟子之见闻者,莫甚于此。”(注:《万国公报》,复刊第10期,第10761页。)
西教士还批评说由于科举制度和传统教育的片面、狭窄,从而强化了中国士人的夷夏之防观。这种观念表现在西学观上,存有畛域之见。19世纪70年代,林乐知从两个方面对此进行批判:第一,天文、算学、格致等是天下“公学”而非“西学”,即科学无国界,而且科学是“当今切用之学,非异端左道之学”,只要有用,都可以学,何言“用夷变夏”;第二,采纳中国人提出的“西学中源”说,“天算溯始于羲和。格致导源于《大学》,特后世置而不问,而西人得其余绪转能以精心求之,遂以成其技器之精,获其富强之效。今华人反以‘西学’目之,抑何悖欤?”(注:《万国公报》,第325期,第689-690页。)80年代,狄考文重申了这一观点:“自来国分中西,人分中西,唯学问之道可通天下,我得之,则属乎我,尔得之,则属乎尔,初无中西之分焉。”“无论何法,合用则用之而已,胡问其由何方而出、自何国而来哉!”(注:《万国公报》,第654期,第8361-8365页。)应该说林乐知等人提出的知识没有国界的思想,比中国学人和思想家提出的“西学中源”说、“中体西用”说,更科学、更先进。但是,由于它曲高和寡,在当时还很难引起中国人的响应与共鸣。
五、余论
晚清来华新教传教士以《万国公报》为主要阵地,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年,围绕着考试的内容、文体、目的、后果等对科举制度进行了系统地批判。尽管中国的学者、思想家、官吏早就对科举制度进行过批判,但是,作为来自异域的西教士,他们批判的深度、系统性以及言辞的激烈程度,不仅远远超过中国一般的开明官吏和学者,而且从总体上还超过了同时期或稍后的早期维新思想家和维新派。中国一般的开明官吏和学者虽然也曾指出过科举制度中的弊端和缺陷,并提出改革建议,但是,他们毕竟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因此不可能发表言辞激烈的批评意见;同时期的早期维新思想家虽然也多次批判科举制度下的学校培养不出“奇才异能”之士、通过空疏的时文所选之人是“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长”,但没有西教士那样从以上四个方面进行系统、深入地批判;维新派领袖一面多次参加过科考,但因思想激进而招致顽固派的不满,屡试不中,一面又不断发表文章或上书皇帝揭露科举制度的弊端,但是,他们基本上也没有提出如同西教士那样系统的批判意见。西教士之所以能提出言辞激烈而又系统、深刻的意见,首先,是由于他们心目中有西方现代教育理论和制度这一衡量和批判的武器;其次,因为他们是来自异域的旁观者,与科举制度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晚清西教士系统地批判科举制度,主要是为了在中国推行西方文化教育,并且建立以之为主要内容的新式学校教育制度,也就是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以西国之新教育广中国之旧教育。很显然,他们发现科举制度是在中国推行西方文化科学知识教育、建立现代学校教育制度上的障碍,所以,他们不仅连续发表文章进行猛烈地批判,而且纷纷提出改良主张和建议(注:关于新教士对科举制度改革的建议,笔者将另有专文发表。)。值得玩味的是,西教士不厌其烦地提出对科举制度的批评意见和改革建议,但是,除了韦廉臣外,很少有人明确提出废除八股文及整个科举制度的观点,在这方面西教士不仅不如早期维新思想家和维新派的观点明确,而且不及洋务派的殿军张之洞。实际上,只有在废除科举制度之后,新式学校教育制度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并得到健康、顺利地发展,这个任务却只能由中国开明的官吏和思想家完成,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在华西教士们对科举制度的废除所起到的促进作用。当科举制度正式废除时,林乐知等人非常赞成;但是,当他们发现新学堂仍以“备朝廷之任”为人才培养观,毕业生仍授予相应“出身”,与科举制度藕断丝连,林乐知当即尖锐地指出:“学堂之目的犹科举之目的,舍是则何必立学堂,舍是则何用入学堂哉!”(注:《万国公报》,复刊第200期,第23654页。)
目前,有的学者津津乐道西人把科举制度介绍到西方,及由此对西方考试制度发生的重要影响。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西人对科举制度的态度非常复杂,不能无视他们对其所进行的批评,否则,就不是全面而科学地分析问题的态度。
标签:万国公报论文; 乐知论文; 科举制度论文; 传教士论文; 晚清论文; 国学论文; 基督教论文; 狄考文论文; 八股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