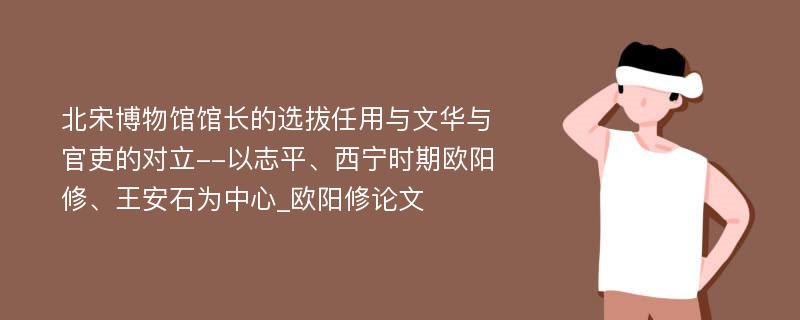
北宋馆职、词臣选任及文华与吏材之对立——以治平、熙宁之际欧阳修、王安石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治平论文,北宋论文,对立论文,王安石论文,欧阳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进士高科荐试馆职,由馆职拔擢两制词臣,有宋两朝,名臣贤相多出此途。馆阁实为宋代文官政治的基础,因此朝廷搜求人材必关注馆职选任,馆职试除以诗赋、策论为取舍标准,词臣序迁则须加试四六制诰。换言之,馆职、词臣考察均侧重文章词笔,但道德与吏能亦不可偏废,有时甚至占据首位。北宋政坛固然颇多集文人学者与官员于一身的综合型人材,如欧阳修、王安石即是,但在文辞、经术与政事的关系上,他们的认识却有很大差异。从根本上讲,他们分别代表了文章家与政治家两种立场。治平、熙宁之际,欧、王作为前后任相继的词臣与执政者,其政见分歧日益加深,馆阁选人制度也成为争论的重要议题。馆职、词臣是宋代作家队伍的主体,因此馆阁改革又不可避免地波及到文章诗赋的写作。贯穿这场论争的主题是文华与吏材的关系,这实际上也是北宋文坛文道关系问题的深化与具体化。
欧、王分歧焦点之一:文章与政事
欧阳修是由馆职出身的最成功的儒臣代表,他由大臣荐举入学士院召试馆职,由最低等的校勘(副馆职)依次升迁集贤校理、同修起居注,知制诰,翰林学士,又由翰苑入二府——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成就了文章词学之士最荣显的仕宦功名。王安石亦曾供职文馆,但与欧阳修乃至宋代绝大多数进士高第出身的词臣及宰辅不同,他却屡辞馆职之命,而后特命直集贤院,直除知制诰,迁翰林学士,打破了由馆职到词臣的试除序迁常规。
欧、王两人由词臣到执政的时间正好于英宗、神宗之际前后相接,他们都以文章学术为天下宗师,但在有关馆职、词臣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上观点却尖锐对立,直接影响到当时及以后的政治决策与文化走向。
首先,怎样看待馆职儒臣与胥吏材臣的地位及作用?治平三年十一月,欧阳修应诏举荐馆职时论及进用贤才问题。他认为富弼、韩琦执政十数年间用人虽多,“然皆是钱谷刑名强干之吏,此所谓用才也。如臣所言进贤路狭,谓馆职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8,以下简称《长编》)。他明确将馆职与吏区别为两种人材,进而具体比较两者的长短与朝廷用人之失:“若夫知钱谷,晓刑狱,熟民事,精吏干,勤劳夙夜,以办集为功者,谓之材能之士;明于仁义礼乐,通于古今治乱,其文章论议,与之谋虑天下之事,可以决疑定策,论道经邦者,谓之儒学之臣。”材吏与儒臣各有所职,朝廷要善于区别使用,让材吏负责中央及地方各级的具体事务,让儒臣供职馆阁,“而又于儒学之中择其尤者,置之廊庙而付以大政,使总治群材众职,进退而赏罚之”。在他看来,儒臣的作用显然大于材臣,“是以前世英主明君,未有不以崇儒向学为先,而名臣贤辅出于儒学者,十常八九也”。但近年馆阁取士的路子太窄,进士高科召试与大臣荐举两路几乎都被堵死,造成“先材能而后儒学,贵吏事而贱文章”的政策偏差,致使馆职零落,人材短缺(注:以上参见欧阳修《上英宗进馆阁取士札子》。)。这非常清楚地表明欧阳修推重儒学文章,重视从馆职中培养选拔高级文官的思想。
治平四年王安石针对十人同时试除馆职一事,于《论馆职札子二》提出了与欧阳修等人针锋相对的观点(注:王安石《论馆职札子二》之一云“十人”,之二云“九人”。按《长编》卷208治平三年记韩琦、曾公亮、欧阳修、赵概等荐馆职二十人,后以人多故先召试十人。)。他怀疑大臣荐举馆职的作法是否可靠,建议设置“三馆祗候”,给予一年考察期限,使其处理一二十件实际事务,然后录用那些“可以备任使之才”者。显然,他看重的是馆职是否具备处理政务的实际能力而不是馆职赖以立身的文章词学。正是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也一贯反对以诗赋取士,鄙薄那些由进士出身的“文吏”徒然能吟诗作赋,但“所学非所用,政事不免决于胥吏”(《长编》卷221)。
王安石执政以后,更坚决地贯彻了他重吏能而薄文华的主张,并公开批评了欧阳修的用人倾向。《长编》卷211载:熙宁三年,神宗有意重新起用欧阳修,反复征询王安石的意见。“(安石)曰‘修好有文华人。’安石盖指苏轼辈,而上已默谕”。“它日上论文章,以为华辞无用,不如吏材有益。安石曰:‘华辞诚无用,有吏材则能治人,人受其利。若从事于放辞而不知道,适足以乱俗害理。如欧阳修文章于今诚为卓越,然不知经,不识义理,非《周礼》、毁《系辞》,中间学士为其所误几至大坏”。王安石所谓“学士”,应当包括欧阳修参政时所荐用之馆职(注:馆职亦可称学士,参见洪迈《容斋四笔》卷1“三馆秘阁”条。),从中的确可见欧公好用“有文华人”的倾向。如《举章望之曾巩王回等充馆职状》(嘉祐年)言章“学问通博,文辞敏丽”;曾“所为文章,流布远迩”;王“学行纯固,论议精明,尤通史传姓氏二书,可备顾问”。《举苏轼应制科状》(嘉祐五年)称苏轼“学问通博,资识明敏,文采烂然,论议蜂出”。《举刘攽吕惠卿充馆职札子》(嘉祐六年)称刘“辞学优赡,履行修谨,记问该博”;吕“材识明敏,文艺优通,好古饬躬”。《举梅尧臣充直讲状》(嘉祐元年)既称梅“辞学优赡,经术通明,长于歌诗,得风雅之正”。嘉祐三年《与韩忠献王》又荐梅为馆职,以为“国子监直讲梅尧臣以文行知名”。此外欧阳修曾荐王安石任谏官,也标举其“德行文学为众所推”(《荐王安石吕公著札子》)。
总之,欧阳修论荐馆职均强调其文章辞学及学问经术,王安石则一反其旧,唯重吏材。熙宁时期除授馆职曾一度以审阅章奏代替试策论,以考察“实用之材”而变革“虚文旧俗”(《长编》卷211)。熙宁四年冯京荐举刘攽、曾巩、苏轼直舍人院,此三人皆为欧阳修所曾荐举以辞学著称充任馆职者,是词臣的最佳人选(直舍人院权行知制诰之职),但未能得到神宗的首肯(《长编》卷220)。由于王安石与神宗对文辞与吏材的偏执认识,文章之士正在失去原来的荣宠地位。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欧阳修并非不重政事。《能改斋漫录》卷13“记事”条载,张舜民初游京师,对欧阳修多谈吏事表示不解,说:“学者之见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为欲闻者。今先生多教吏事,所未谕也。”欧阳修这样表达其文学与政事观:“大抵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这个体会得自于贬谪夷陵时因阅读公案多枉直乖错,刺激他从此更留心政务并以此勉励士子。这一思想曾影响到苏氏父子。“其后子瞻亦以吏能自任,或问之,则答曰:‘我于欧公及陈公弼处学来。’”但欧阳修(包括苏轼)重视政事吏能,并没有象王安石那样片面地将文吏等同于胥吏,以吏材取代文章并因此而贬抑诗赋文辞。
欧、王分歧焦点之二:华辞与吏文
科举文化为宋廷造就了大量文官,也造就了一个文牍社会。最能体现文官特色的,应是馆职及由此出身的词臣。馆职、词臣都是“文字之职”,专掌诰命的知制诰与翰林学士尤“以文章为职业”(注:《长编》卷103记仁宗语。)。诏敕诰令之类概属吏文范畴,虽系实用文章,但草创润色,同样存在文字表达的工拙繁简等属于“文华”的问题。在欧阳修、王安石的政治活动中,对词臣文章也都给予了很大的关注,这与他们的文学思想相辅相成,同样值得重视。
庆历三年九月,李淑任翰林学士,知谏院欧阳修认为李淑奸邪阴险,不宜任词臣。他说:“才行者人臣之本,文章者乃其外饰尔,况今文章之士为学士者,得一两人足矣。假如全无文士,朝廷诏敕之词,直书王言以示天下,尤足以敦复古朴之美,不必雕刻之华。自古有文无行之人,多为明主所弃”(《论李淑奸邪札子》)。欧阳修强调翰林学士应才行为本文章为辅,符合北宋前期选用两制词臣的基本原则。因为,翰林学士虽然“以文章为职业”,但毕竟不同于纯粹的文士,而实为天子机要秘书,号称“天子私人”,直接对皇帝负责,因此尤须品行端方,性格谨重。
另一方面,翰林学士在宋代经常出任权知贡举,主文衡士,并参与宫廷游宴与馆阁唱和,以其地位与声望领袖一时文风。因此范仲淹在天圣三年《奏上时务书》中即建议“敦谕词臣,兴复古道”,“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可见词臣又担负复古崇雅的使命,这已涉及当代的文章之道。欧阳修赞同词臣文章“敦复古仆之美,不必雕刻之华”,正与范仲淹十八年前的呼吁遥为桴鼓。宋代诏诰率以四六为之,自然难免雕刻之习。欧阳修虽能四六,却颇为不屑。康定元年,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副使,辟修为掌书记,他推辞说:“今世所谓四六者,非修所好,兼此末事,有不待修而能者。”(《长编》卷127)其庆历三年所作《谢知制诰表》曰:“伏念臣虽以儒术进身,本无辞艺可取,徒值向者时文之弊,偶能独守好古之勤,志欲去于雕华,文反成于鄙朴。”嘉祐六年秋所作《内制集序》认为,当今学士所作文章虽多,但“制诏取便于宣读,常拘以世俗所谓四六之文,其类多如此。然则果可谓之文章者欤”?自己的文章亦未能免俗:“予在翰林六年,……其屑屑应用,拘牵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欧阳修于仁宗天圣初年步入文坛,正面临景德以来文坛科场的浮华之风,他自庆历三年至嘉祐五年任两制词臣凡九年期间,一方面要勉力于“王言之体”的写作,一方面又极为不满这种四六“时文”的卑弱,致力于倡导新文风。
王安石在其早期的《上人书》中表达了他“以适用为本”的文章观:“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这一文章观在其后来对吏文的改革中发展得更为偏激,即去除文华,务求实用。
王安石改革文章的显著成果是简化最通用的制辞与考功文字。熙宁四年安石提出:“制辞太繁,如磨勘转常参官之类,何须作诰称誉其美,非王言之体,兼令在官者以从事华辞费日力。”神宗也认为此类制辞多名实不符,王安石建议将一篇考察官员政绩的诰辞固定为17字的格式,即:“朕录尔劳,序进厥位,往率职事,服朕命,钦哉!”其他制辞仿照撰定,这样的文字其实依样画葫芦即可,“甚省得词臣心力,却使专思虑于实事”《长编》卷220)。熙宁五年商议省略空洞无物的“考功文字”即考核评语,王安石认为:“天下无道,辞有枝叶,从事虚华乃至此,此诚衰世之俗也。”(《长编》,卷235)熙宁九年王安石与神宗论“道”时又说:“陛下该极道术文章,然未尝以文辞奖人,诚知华辞无补于治故也。风俗虽未丕变,然事于华辞者亦已衰矣,此于治道风俗不为小补。”(《长编》卷275)同是论词臣文章,欧阳修批评四六文的雕刻拘束与卑弱不振之弊,是从文体本身寻找根源;王安石以为华辞不仅无益而且妨害治道风俗,是衰世的产物,则是从政教“实用”的角度将文辞问题彻底功利化了。由此一端,即可见欧、王论文重文与重道的不同宗旨。
革除华辞的有效措施是以义理统一文辞。熙宁三年时王安石就批评欧阳修虽文章卓越但“不知经,不识义理”。熙宁八年,神宗与安石谈论欧阳修新修《五代史》,“王安石曰:‘臣方读数册,其文辞多不合义理。’上曰:‘贵以义,则修止于如此:每卷后论说皆称呜呼,是事事皆可嗟叹也。”对欧阳修的指责,多半因其所作史论多感慨叹恨之词,寓褒贬惩劝之意,情文胜于义理,议论出于己意。实则所谓“义理”,不过是以王安石新定经说为标尺。王安石推行经术的实质是“经世务”,“变风俗,立法度”(注:《宋史》卷327《王安石传》。),带有强烈的实用精神和干世色彩,但以此衡量道德文章就不免武断。如果说王安石对欧阳修用人的批评体现了重吏材而轻文章的倾向,那么他对欧阳修文章的非议则明显可以看出重义理而轻文辞的倾向,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也可以说,政治问题与文章问题不可分割。由此可以联想到,嘉祐五年,王安石任直集贤院时,受宋敏求委托编选《唐百家诗选》,竟会感叹:“废日力于此,良可悔也”(《唐百家诗选序》)。宋代馆阁有浓厚的谈诗论文气氛,编选唐诗既属正常馆务,亦可供馆职诗人追摹讨论。但王安石以此为徒然耗费日力,正反映了政治家排斥文华无益之事,以诗赋文辞与吏事经义相对立的偏激态度,而这一态度不可避免地越出了吏文范围,侵入到史学与文学领域,对欧阳修的批评是最显著的例子。
文华与吏材之争的历史渊源及现实背景
文辞、儒学、吏能之因依对立关系具有极深的历史渊源,汉魏晋唐宋以来,因应着时代的政治功利和文化策略,它们与时嬗变并转化成不同的文化型态,也使作为传统文化承传者的士经历了从经师、文儒到学士的三次文化转型。
汉代尊崇儒学,士以儒学为业,经学是官方主流文化,朝廷虽以“文学”和吏道两途取人,但儒学与政事,士与吏之间并未出现偏重偏轻的现象。正如马端临所说:“今按西都公卿士大夫,或出于文学,或出于吏道,亦由上之人并开二塗以取人,未尝自为抑扬偏有轻重。……后世儒与吏判为二途”(注:《文献通考》卷35《选举考》。)。唐宋人普遍认为,分裂肇始于魏晋时期,首先表现为文、儒分化。《资治通鉴》卷193《唐纪》载王珪曰:“汉世尚儒术,宰相多用经术士,故风俗淳厚。近世重文轻儒,参加法律,此治化之所以衰也。”“近世”即指魏晋以后。司马光在嘉祐七年所上《论财利疏》中也表达对类似看法:“自魏晋以降,人主始贵通才而贱守节,人臣始尚浮华而薄儒术”。元祐元年司马光重新进入政坛后上疏论科场制度时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自魏晋以降,始贵文章而贱经术,以词人为英俊,以儒生为鄙朴。下至隋唐,虽设明经、进士两科,进士日隆而明经日替矣。”(《长编》卷371)可见,自唐代进士词科大兴,儒学受到文学更猛烈的冲击,两者的分裂愈益显明。唐代进士得人远较明经为多,故文辞明显重于经术。胡应麟《诗薮》外编卷3称:“玄宗开元中,宰相至十数人,皆文学士也。……古今词人之达,莫盛此时。”与此同时,文辞与吏能的矛盾也从唐代开始凸显出来。即如胡应麟所举“文学士”出身的开元名相,实亦可分为重吏能如姚崇、宋璟与重文学如张说、张九龄两派。当开元中期文学派占据主导地位后,遂造就了一个新的文士阶层,葛晓音称之为“文儒型的士人”。盛唐文儒的主要特征是兼通儒学和文学;其次,他们普遍反对吏能,大都志存高远,不屑吏事。当然,由于时代、门第及科第不同,唐代文儒的文化型态也不平衡。一般而言,开元以前进士科出身的新进文士较重文辞,而天宝以后旧山东士族则更崇奉儒学;开元后期张九龄罢相与李林甫执政,可以看作是吏能派排斥文儒派斗争的胜利,中唐时期的牛李党争在某种程度上则是新进词学与传统儒学矛盾的延续(注:参见葛晓音《盛唐“文儒”形成和复古思潮的滥觞》,《文学遗产》1998年第6期。);初盛唐文人往往将儒学与游侠、纵横家思想相糅,喜空谈王霸大略、帝王之术,中唐以后的士人则更注重参与政治实践。简言之,唐代以文章词学占主导地位,文学与经学、吏能的对立斗争依然存在并时常激化。
文士及辞学特别是进士高科的地位到宋代有了空前提高。宋仁宗庆历八年、嘉祐二年分别赐张方平与欧阳修“文儒”称号,《渑水燕谈录》卷6专记“文儒”事迹,但这与唐代“文儒”已有很大不同。我以为,宋代文士或可称为学士型。首先,在群体组成方式上,学士型的文人大部分由进士高科入馆阁为学士,其尤者则升为两制词臣;其次,从群体素质上说,学士型文人大都是集官员、学者、文士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他们更追求文章、儒学与吏干的统一;第三,宋代学士与唐代文馆学士相比,社会地位更高,真正成为国家的“知识精英”。当然,宋代学士型态的构成也并不绝对均衡。陈植锷认为,从宋初三朝至仁宗朝,宋代官员大致经历了从吏材型到文章型再到综合型的发展过程(注: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第一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这大体不错。但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在文学、经术与政事综合平衡的前提下,文辞与吏能的矛盾仍然较为突出并且在神宗朝趋于尖锐化,最重要的变化是转向重吏事而轻文辞,并在南宋以后成为占据支配地位的倾向。借用戴复古的诗句说:“致身虽自文章达,经世尤高政事科。”(《湖南见真帅(德秀)》)
在馆职与词臣的选任标准上可以明显看出这一转变。宋初三朝重视文辞与德行兼备。最典型的是前南唐词臣张洎,执政欲荐为翰林学士,太宗认为“洎文学资任不下(毕)士安,第德行不及耳”(《长编》卷32)。后洎虽以“文彩清丽,巧于逢迎”而入翰林,但太宗仍表示“缙绅当以德行为先,苟空恃文学,亦无所取”(《长编》卷34)。真宗曾召翰林学士梁颢询问当世台阁人物,颢曰:“晁迥笃于词学,盛玄敏于吏事。”真宗不答,却问道:“文行兼著如赵安仁者有几?”梁颢卒后遂任赵安仁为翰林学士。前引仁宗朝欧阳修反对李淑入翰林,仍然体现了文行并重的观念。不过从真宗、仁宗开始,文章词学之士益受崇重,文辞渐渐偏重于德行、吏事。以帝王为首,形成了词臣为学者宗师,学士以词命为职的观念。欧阳修回忆当年钱惟演的名言说:“昔钱思公尝以为朝廷之官虽宰相之重,皆可杂以他才处之,惟翰林学士,非文章不可。”(《内制集序》)真宗朝著名馆职词臣如杨亿、钱惟演、刘筠、晏殊等都以文章词学名家,杨亿更为“一代之文豪”(注:《渑水燕谈录》卷10“歌咏”。)。仁宗明确提出“馆职当用文学之士名实相称者居之”(注:《麟台故事》卷3《选任》。),嘉祐时期以欧阳修为代表的馆阁文人群如苏舜钦、尹洙、刘攽、宋祁、宋庠、范镇等实与景德时期杨刘钱晏馆阁文学集团声气相承,均以文章进用,以词笔或史学见长。
但对馆职学士的优宠逐渐造成“误恩”滥赏及华而不实的现象,导致士风颓堕文风流宕,因此自仁宗即位以来,矫正士风文风、严格馆职选拔标准的呼声越来越高。《麟台故事》卷3《选任》称仁宗朝“时大臣所荐多浮薄之人,盖欲以立私恩尔”。天圣四年谏官陈升之上言:“此来馆阁选任益轻,非所以聚天下贤才,长育成就之意也。”(《长编》卷104)《石林燕语》卷7记天圣、宝元间范讽(时为龙图阁学士)与石曼卿(时任馆阁校勘)“皆喜旷达,酣饮自肆,不复守礼法,谓之山东逸党,一时多慕效之”。开封府判官庞籍劾奏,以为“苟不惩治,则败乱风俗,如西晋之季”,遂贬谪之。文风往往与士风相表里。《长编》卷106曰:“自景德后,文字以雕靡相尚,一时学者向之。”于是天圣六年九月,七年五月,明道二年十月,朝廷有意识地借任用词臣、进士加试策论等措施,倡导复古,纠正以诗赋取士的偏颇,扭转文坛“荟萃小说,磔裂前言,竞为浮夸靡曼之文”的流弊,这与太宗、真宗朝热衷于编纂大型诗文及小说总集的趋尚明显异趣。进士入馆考试经过反复争论,也终于在治平四年决定以策、论代替诗赋,进一步削弱了文华的影响。
其次,政府机构中文官数量过多而素质下降,无法有效处理愈益困顿繁冗的政务吏事,也导致对文辞之士的激烈批评。蔡襄《国论要目》指出:“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三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文士也”。文士已遍布行政、文化、军事、经济等所有重要部门,但文臣毕竟有本身能力的局限。司马光《论财利疏》亦极论朝廷在用人方面的失误及造成的积弊,主张“随才用人而久任之”;“先朝以数路用人:文辞之士置之馆阁,晓钱谷者为三司判官,晓刑狱者为开封府推、判官,三者职业不同,趣舍各异,莫相涉也。……近岁三司使、副使、判官,大率用文辞之士为之,以为进用之资塗,不复问其习与不习于钱谷也。彼文辞之土,习钱谷者固有之矣,然不能专也。”司马光区分文士与材吏“职业”的不同,较之欧阳修所论儒臣重于材臣的观点更为客观务实,更能切中滥用文辞之士的时弊。
总之,馆职词臣及一般文吏的选拔任用与士风、文风及吏治问题密不可分,治平以来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愈益尖锐而成为当世之急务。于是在王安石执政之后,即采取了一系列变革馆阁排斥文华革新吏文的激烈措施,并且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成效。如神宗称王安石:“吏文有条序,皆由卿造始”(《长编》卷263)。熙宁七年,知河中府、集贤校理鞠真卿以在郡无政绩,一岁中燕饮九十余次而落职,王安石对神宗说:“旧俗大抵如此,陛下躬服勤俭,此俗已顿革,在京两制非复往时,但务过从而已。”神宗亦曰:“馆阁亦一变矣。”(《长编》卷250)从行政的角度说,这些改革对于消除积弊,推动变法,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自有其积极意义。但矫枉过正,物极必反,吏治改革的成果以文学性丧失为代价,以政事取代文辞,对文学繁荣、学术发展及馆阁建设都造成明显的损害。
断层:文馆寂寥,词臣无文
北宋文坛呈现突出的趋群性与集团化倾向。王安石水照师指出,北宋文学群体以天圣时钱惟演的洛阳幕府僚佐集团、嘉祐时欧阳修汴京礼部举子集团,元祐时苏轼汴京“学士”集团三大文人集团层次最高,它们具有系统性、文学性与自觉性的特点(注:王水照师:《北宋的文学结盟与尚“统”的社会思潮》,收入《王水照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除此之外我们注意到,这些文人集团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特点,即多以词臣及馆职学士为主体,而且上述三大文学群体的盟主均曾任翰林学士。宋代翰学与馆职之间往往有道义师友之交,“盖祖宗时内外制官无不自三馆出,馆中之人往往前日僚友之旧,道义之交,不专以势利高下为心”(注:《南宋馆阁录》卷6“大宴学士院具食”条引《麟台故事》。)。盟主对尚未进入馆阁或翰苑的成员也多会以馆职词臣相期许,如钱惟演曾对幕府文士谢绛、尹洙、欧阳修等说:“君辈台阁禁从之选也,当用意史学,以所闻见拟之。”(注:《邵氏闻见录》卷8。)而词臣盟主的凋零进退,使得这些集团呈现出较明显的阶段性,各个集团的前后相续,则组成特色各异而又有连续性的文学长链。
当我们循此思路观察北宋这条由馆职、词臣为主构成的文学长链时,可以发现在嘉祐欧阳修文学集团与元祐苏轼文学集团之间,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馆职、词臣文学群体,即熙宁、元丰时期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作家群。尽管对这一集团的评价褒贬各异(注:如沈松勤在《北宋文人与竞争》(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中认为此派大部分成员同时以文学为立身立业,并不乏文坛作手,他们对繁荣北宋文学具有不可磨灭的推进之功。但在《论王安石与新党作家群》(《杭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一文中又认为王安石将文学纳入经术之中,侵蚀了文学性,从而在北宋文学史上产生严重的负面效应。),但不可否认的是,王安石在馆职、词臣选拔任用上采取的偏重吏材排斥文华的态度,赋予这一群体过于浓厚的政治色彩,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熙、丰之际的文学断层。
首先从政治人事之递接看。欧、王于嘉祐元年订交,欧阳修曾以李白、韩愈比拟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赠王介甫》)王安石则自谦说:“欲传道义心虽壮,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奉酬永叔见赠》)王将“道义”与“文章”、“孟子(轲)”与“韩公(愈)”对举,青年王安石弘扬道学的志趣隐然可见。治平以后,欧、王的分歧已不可调和,欧阳修于至和元年至嘉祐五年为翰学,六年拜参政,神宗即位不久后即坚请致仕,逐渐淡出政坛。王安石于治平四年入翰苑,熙宁二年拜参政,次年为相。两人在政坛上基本先后交替,但欧阳修执政时所开拓的文学革新局面却未能由王安石继续发扬光大,他更多的精力放在论争和变法中,馆阁改革成为其政治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馆职、词臣的选用也纳入了他重政事轻文辞的轨道。
其次,从馆职、词臣之代谢看。神宗即位以来,两制严重缺人,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是王安石为变法的需要,排斥异己力量,致使旧日文臣过早退出政坛或移居州郡。熙宁四年,六月杨绘言:“今旧臣告归或屏于外者,悉未老,范镇年六十三,吕诲五十八,欧阳修六十五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被劾引疾,司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闲散。陛下可不思其故耶?”(《长编》卷224)其中范镇、欧阳修、司马光皆曾为翰林学士,王陶则曾为知制诰。其二是受王安石否定文华思想影响,进士、馆职考试均罢诗赋而专试策论、经义。治平四年御史吴申建议馆职召试“兼用两制荐举,仍罢诗赋,试策论三道,问经史时务”。王安石《乞改科条制札子》主张“宜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熙宁四年进士科遂罢诗赋试策论,但这样一来“所试事业即与制举无异”(《长编》卷253),故经过争论又于熙宁七年五月罢去制科。既取消诗赋,又统一经义,势必使思想趋于僵化。不仅于政事无补益,而且很快导致馆阁冷清、学士无学、词臣无文的尴尬局面。
《长编》卷253载,熙宁七年,馆阁校勘吕升卿与国子监直讲沈季长同为崇政殿说书却不学无术,经筵间“多舍经而谈财谷利害,营缮等事”,却不能从容解说经义。“上问从谁受此义。对曰:‘受之王安石。’上笑曰:‘然则且尔。’”这的确不给经学大师王安石面子。又如熙宁中两制阙人设直舍人院权知,但此辈人许多文字功底较差,文学素养尤低。《能改斋漫录》卷12“记事”条载,熙宁五年九月御史张商英上疏列举词臣无文现象:
盖自近世,文馆寂寥。向者所谓有文者,欧阳修已老,刘敞已死,王珪、王安石已登两府。后来所谓有文者,皆五房检正,三舍直讲,崇文检书,间有十许人。今日这所谓词臣者,曰陈绎,曰王益柔,曰许将是己。臣尝评之,陈绎之文,如款段老骥,筋力虽劳,而不成步骤;王益柔之文,如村女织机杼,虽成幅而不成锦绣;许将之文,如稚子吹埙,终日喧呼而不合律吕。此三人皆,皆陛下所用出词令,行诏诰,以告四方而扬于外庭者也。今其文如此,恐不足以发帝猷,炳王度云。
按欧阳修至和元年任翰林学士,卒于熙宁五年;刘敞曾任知制诰,卒于熙宁元年;王珪嘉祐元年拜翰林学士,熙宁三年拜参知政事;王安石则于治平四年入翰林,熙宁二年拜参政。陈绎治平中为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神宗朝入直舍人院,修起居注,知制诰,拜翰林学士。许将曾任集贤校理,后迁直舍人院及进知制诰均为神宗特命,不试而除,但神宗很快对其文字能力表示了不满(注:《长编》卷238载神宗谓安石曰:直舍人院许将“文字颇不佳”。)。王益柔本以博学著称,杜衍、丁度曾以学术政事荐举益柔,范仲淹荐试馆职,因其不善词赋,特许试策论,熙宁初直舍人院,知制诰兼直学士院。陈绎、许将、王益柔皆由馆职出身,但与精通诗赋的“有文者”欧阳修、王珪及王安石相比,其文笔词采显然难当“文学之极任”的称誉。
熙宁时期词臣“无文”的现象其实也是王安石简化和统一制辞文字的必然结果。熙宁十年六月,知制诰孙洙批评自熙宁四年统一公文定式以来,词臣因循苟简,所作制诰千人一辞,“群臣虽前后迁官各异而同是一辞;典诰者虽列著名氏各殊,而共用一制;一门之内,除官者各数人,文武虽别,则并为一体。至于致仕、赠官、荐举、叙复、宗室赐名、宗妇封邑,斋文疏语之类,虽名体散殊,而格以一律,岁岁遵用”(《长编》卷283)。朝廷虽然采纳了孙洙改易吏文格式的建议,但取消制科辞赋带来的消极影响却一直延续到元祐中,“制科词赋既罢,而士之所习者皆三经。所谓三经者,又非圣人之意,惟用安石之说以增广之,各有套括,于是士皆不知故典,亦不能应制诰、骈俪选”(注: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甲集“制科词赋三经宏博”条。)。可见文章辞赋的取舍对保持一个高素质的文官队伍决非无关紧要的细微末节。
如果说王安石鄙薄文华的结果直接造成词臣学士无学无文,使朝廷难觅长于制诏词令的“大手笔”,那么他偏重吏材的结果则是使馆阁充斥着大量钱谷俗吏,馆职的文学职能消失殆尽。《容斋四笔》卷16“馆职名存”条云;“政和以后,增修撰直阁贴职为九等,于是材能治办之吏,贵游乳臭之子,车载斗量,其名益轻。”馆职成为酬赏材吏亲信、安插权贵子弟的手段,士子竞趋,益呈浮滥:“熙宁执政,务欲速援亲党,假此以为进人之阶,浮躁狂妄者争趋之,故有朝除校理而夕拜词掖,夕为直院而朝作辅臣。馆阁涵养之风,遂至委地,士人廉耻之节,靡有孑遗。既无素养之才,悉皆苟合之士”(注:胡宗愈:《请令带职人赴三馆供职事》。)。这样元丰官制后罢馆职也就是势所必然的结果了,其后元祐间复置馆职,绍圣初再罢之,反复不定。南渡以后,馆阁虽存,但已有根本更革。因此可以说,熙、丰之间馆职的整改撤并在宋代馆阁制度史上造成一个明显的断层,同时在文学人才的培养、文学气氛的营造等方面间接地造成文学发展的断层。苏轼曾尖锐地批评王安石“欲以其学问同天下”,造成文坛“惟荒脊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的萧条景象,虽有些夸张色彩,但决非意气相激之语(注:参见苏轼《答张文潜县丞书》。)。固然,如论者所说,王氏新党中不乏文坛作手,不少人且撰有专集,但其整体水平与文学色彩都无法与其前后的馆职词臣文人群体相比拟。事实上,整个熙、丰期间,神宗“未尝以文辞奖人”,宫廷、馆阁唱和活动甚少,馆职多忙于行政事务性工作。至于崇宁、政和中两度沮诗赋、崇经义的政令(注:《容斋四笔》卷14“陈简斋葆真诗”条:“自崇宁以来,时相不许士大夫读史作诗,何清源至于修入令式,本意但欲崇尚经学,痛沮诗赋耳,于是庠序之间以诗为讳。”《石林燕语》卷9:“政和末,李彦章为御史,言士大夫多作诗,有害经术,自陶渊明至李、杜,皆遭诋斥,诏送敕局立法。”),虽有党争的因素,但也不难看出安石执政时贬抑文华留下的后遗症。
熙、丰变法至元祐更化、绍圣绍述时期,馆职屡罢,诗赋屡禁,不同的政治势力与文学群体都在扩大或弥补着这个断层。幸赖以苏轼为首的元祐名士组成的馆阁学士集团以其整体性全面性的文学成就,足以与以欧阳修为首的嘉祐馆阁文人群体相颉颃。苏轼《居士集序》称赞欧阳修“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石林燕语》卷5云:“元祐初,用治平故事,命大臣荐士试馆职,多一时名士。”苏轼及王安石无疑是“嘉祐多士”的中坚,而“元祐名士”则显然以“苏门四学士”和“苏门六君子”为代表。嘉祐与元祐时期是北宋文学的两个高峰,与馆阁制度的完善及馆职学士的文学素质有直接的联系。元祐远承嘉祐,上接治平,中间恰是熙、丰时期罢馆职所形成的断裂。亦幸赖这一断层的制造者——王安石本人以其个人的文学天才和出色的诗文创作使斯文不坠(如果不考虑其初仕、执政及隐退期间创作成就差异的话),“此道不寂寞”(注:欧阳修《与刘原父书》称王安石新诗。),以致当我们的目光集中在现行文学史所提供的作家系谱(尤其是诗文革新运动)时,会因其成就的辉煌而完全忽略某些断层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