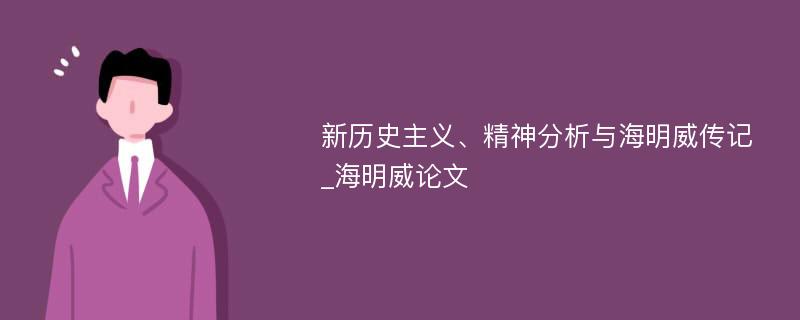
新历史主义、精神分析学说与海明威传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明威论文,历史主义论文,传记论文,说与论文,精神分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厄内斯特·海明威1961年举枪自戕后,便不断有他的传记问世。到1997年,已有二十多种不同版本的海明威传记出版。可是,多数学者认为写得最好的海明威传记早在近30年前就已问世,这就是著名海明威研究专家卡洛斯·贝克于1969年出版的《厄内斯特·海明威的一生》(注:Baker,Carlos.Ernest Hemingway:A Life Story,New York:CharlesScribner's Sons,1969,p.Ⅶ,16,125.)。这本传记文笔优美,资料翔实,在细节描写方面真切感人。作者是一位长于思考、精于分析、目光敏锐的学者。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海明威从小就具有写文章的天赋,他在写作方面的执著追求,以及他成为叙事文学一代宗师的心路历程。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位小说家嫉妒心强、报复心重,有时气量相当狭窄,而所有这些观点,贝克都以充分的事实为依据。因此,这本书被称为海明威研究方面的里程碑。多数海明威专家认为,要想研究海明威一生中的任何重大问题,这本书是必不可少的资料。
既然已经有了这个权威的版本,为什么还要不断出版新的海明威传记呢?用新历史主义的某些观点来阐释这一现象,或许可以使我们得到一些启发。
后结构主义的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提出了“历史知识的相对性问题”。在《知识考古学》里,他说:“我们所看到的某种历史,包括谁讲话、讲什么、怎么讲、以及什么是真、什么是伪等等,其实都已是经过具有约束性的话语规则的选择和排斥以后的产物。……一旦看穿了这种‘历史’的‘文本性’,并由此及彼地思考下去,我们就不难发现,包括我们平时用以考虑和把握世界的种种观念和分类原则,它们本身其实都是有待于被审视的话语的产物。 ”(注: Foucault,Michel.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Introduction,"Trans.A.M.Sherican-Smith,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2,p.X,7.)实际上,历史知识需要不断更新的论点,早在二百年前就有人提出过。歌德曾说:“世界历史要不断地重写, 这一点现在已不再有人怀疑了。 ”(注: Thomas,Brook.The New Historicism and Other Old- Fashioned Topics.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p32.)不过,福柯更加明确地指出了历史的相对性,突出了历史的文本性。在后结构主义者们看来,传统意义上的“历史”(history )再也不被当作一种客观的存在,
而是一种“历史叙述”,
或“历史修撰”(historiography)。从“历史”到“历史修撰”,最关键的一个变化就是“历史”的“文本性”被突出了,就是原先一个大写的、单数的“历史”(History)被小写的、复数的“历史”(histories)所取代。放在人们面前的“历史”,只是以“文本”形式存在的“历史”。(注:盛宁:《二十世纪美国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56、258、268、262、260页。)
近些年来在美国方兴未艾的新历史主义接过了福柯等人关于历史知识相对性的观点,更加强调历史的文本性,甚至把历史与文学等同起来。新历史主义的重要批评家怀特(Hayden White)希望把历来被认为是主司“真实”之再现的历史话语,与以想象和虚构为基本特征的文学话语之间的隔墙打通。他发现“进入20世纪以后,人们在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意识’,什么是‘历史知识’等问题上,似乎越来越不能做出充满自信的回答,从瓦雷里到海德格尔,到萨特、列维-斯特劳斯和福柯,这些欧陆的思想家似乎都越来越强调历史重构中的虚构特性。”(注:盛宁:《二十世纪美国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年, 第256、258、268、262、 260页。)于是,他把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联系起来考虑,试图找出它们的共同点。在1973年出版的《元历史》中,怀特就强调历史修撰离不开想象,历史叙述和历史文本中也不可避免地有虚构的成分。五年以后,在另一本著作《话语转喻论》中,他用最明确的语言,彻底拆除了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之间的隔墙,断然把历史和文学等量齐观。在这本书中,他讨论了史家与文学家重合、相似以及相互观照到什么程度,最后得出结论:“历史作为一种虚构形式,与小说作为历史真实的再现,可以说是半斤八两,大同小异。”(注:盛宁:《二十世纪美国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56、258、268、262、260页。)怀特的这个结论未免失之偏颇,不过他毕竟提醒我们,史学著作不同于历史事件。 对同样的史实,由于史家观察的角度不同,立场各异,完全可能做出不同的阐释,甚至不同的叙述。
有了“文本叙述”的概念作为认识和把握世界的中介,昔日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的那种天真无邪的透明度就再也不存在了。(注:盛宁:《二十世纪美国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56、258、268、262、260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通史或断代史才会以不同的文本形式出现,各种文本不但不尽相同,而且可能大相径庭。传记也是一种历史,是个人的历史,因而也是文本。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流行之前,一个名人出一本传记似乎就够了。而在“历史的文本性”这一概念流行之后,仅海明威的传记已出版二十多本。虽然“历史的文本性”及由此而推导出来的“传记的文本性”也许不是如此众多的海明威传记问世的惟一原因,但这种对历史的新认识很可能启发了不少传记作者,促使他们从新的角度,用新的观点去探讨这位伟大作家的一生。在谈到文学史的撰写时,袁行霈教授指出,“各家对这门学科的理解并不相同,因此《文学史》的写法也有很大差异。”(注:袁行霈:《关于文学史几个理论问题的思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5期,第58页。)传记作品也是这样。众多作家对传记主人公的理解相去甚远,因而写出的传记特色不同,风格迥异,各有自己的侧重点。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文本在形成过程中受到历史环境、认识条件和学术体制等各种作用力的约束。传记文本也同样如此。下面我们就以海明威的传记为例,考察影响传记作品的一些重要因素。
正如政治家的传记离不开传记人物的政治生涯和政绩一样,文学家的传记必然以传记主人公的创作生涯和文学上的成就为主,而且传记作品的侧重点也往往受批评热点的引导:如果在某段时间评论界对作家的某部作品特别重视,评价特别高,那么传记作者也往往对传记主人公这一时期的生活和创作大加泼墨;如果在另一段时间评论界的兴趣转到了该作家的另一部作品上,传记作者的兴趣也往往跟着转移,浓墨重彩地刻画产生这“另一部作品”的社会环境和作家的生活经历。例如,1952年,海明威的最后一部力作《老人与海》轰动全美,全文刊登这部作品的那期《生活》周刊销量达五百五十万册,为世所罕见,该书的单行本也高居全美畅销书榜首达二十六个星期之久。这本小说简洁、干练的硬汉子风格,含义丰富的隐喻和象征,以及它所崇尚的“一个人可以被消灭,但决不能被打败”的精神立即征服了全美乃至世界读者的心。1953年,《老人与海》获普利策奖;1954年,主要由于这本书显示出海明威“精通叙事艺术”,瑞典皇家文学院授予海明威诺贝尔文学奖。如果当时有人写海明威的传记,这本小说以及作家在古巴的生活经历无疑会占全书很大的篇幅。实际上,直到十五年后,在卡洛斯·贝克所著的《厄内斯特·海明威的一生》中,《老人与海》及与该书有关的事件仍占不小的比重。
可是到了七八十年代,海明威专家们的兴趣则越来越偏向于作家在巴黎的学艺时代,以及海明威这段时间的最重要作品《太阳照样升起》。研究这部作品的论文日渐增多,而《老人与海》则越来越受到冷落,似乎它的内涵已被穷尽。于是,随着海明威批评热点的转移,传记作家的兴趣也随之改变。迈克尔·雷诺兹正在写一部五卷本的海明威传记,其中的第二部就专门探讨海明威在巴黎的生活和创作。(注: Reynolds,Michael.Hemingway:The Paris Years,New York:Basil Blackwell,1989.)在这一卷里,雷诺兹详细分析了海明威最终成为文学大师的种种因素:在巴黎时海明威不但勤于练笔,刻苦钻研写作的技巧,力求“写出一句真实的句子”,而且努力培养自己的个性、人格和敬业精神。
肯尼思·林恩1987年出版的传记《海明威》(注:Lynn,Kenneth S.Hemingway,New York:Simon & Schuster,Inc.1987.)也明显地受到批评热点的影响。这本书风格明快、引人入胜,但在篇幅安排上似乎不够匀称,因为他让海明威在巴黎的九年生活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一。毫无疑问,这也是由于作者受到美国文学评论界的影响所致。
进入90年代,美国的评论家们对《太阳照样升起》更加青睐。近几年,在每年研究海明威的单部作品的论文总数中,研究这本小说的文章有时竟占一半左右。于是传记作家们偏重海明威这一时期的倾向也更明显。在1992年詹姆斯·H·梅洛撰写的海明威传记中, (注: Mellow,James R.Hemingway:A Life Without Consequence, 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Cornpany,1992.)大量的篇幅写的是1921 年至1929年间海明威在巴黎生活、工作、交友、学艺的内容。1992年还出版了一部海明威的第一位妻子海德莉·理查逊的传记。海德莉·理查逊一生并无多大建树,出版她的传记,不但因为她曾做过海明威的妻子,而且由于她是海明威在巴黎时的主要生活伴侣。海德莉活了八十七岁,但她与海明威共同生活的时间只有五年,而这五年的生活却占了全书篇幅的四分之三!因此,这本《海德莉·理查逊传》在很大程度上是海明威在巴黎生活的详细记录。由此可见,批评热点对文学家传记的作者起着明显的导向作用。
新历史主义认为,从“文本叙述”的角度看历史,就是要去除“历史”(文本)的神秘性,看到“历史”文本在形成的过程中是如何受到历史环境、认识条件和学术水平等各种作用力的约束的。(注:盛宁:《二十世纪美国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56、258、268、262、260页。)作为个人的历史,“传记”文本在形成过程中也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不仅包括批评界对传记人物关注的热点,而且包括传记作者的历史环境、认识条件和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状况,甚至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最新发现也可能对传记文学产生一定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可以说,传记实际上反映了一个时代的认识水平。
譬如,近几十年来,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心理学批评方法受到文学评论家的青睐,也影响了一些传记作家。在论文《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他童年的一个记忆》中,弗洛伊德研究了达·芬奇童年时期的家庭环境和经历与他的绘画作品之间的关系,发现“他的童年时期的偶然境遇对他产生的意义深远的和带扰乱性的影响”。(注: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美文选》,张唤民、陈伟奇译,裘小龙校,知识出版社,1987年,第97、97、84—85、139、15、48、96页。)根据弗洛伊德的调查,列奥纳多·达·芬奇是私生子,他的非法出生剥夺了他父亲对他的影响。大约在他五岁之前,“向他敞开的只有母亲对他的温情的诱惑。”(注: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美文选》,张唤民、陈伟奇译,裘小龙校,知识出版社,1987年,第97、97、84—85、139、15 、48、96页。)弗洛伊德认为,童年时期的这种家庭环境对达·芬奇的一生和事业都是“有决定性意义的。”(注: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美文选》,张唤民、陈伟奇译,裘小龙校,知识出版社,1987年,第97、97、84—85、139、15、48、96页。)由于从小只和温柔慈爱的母亲在一起,达·芬奇对母亲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性依恋,这种情感在他长大成人后被压抑下去,但并没有消失,而是进入“无意识”中。在受到外界刺激时,它仍会不自觉地表现出来。例如,蒙娜·丽莎脸上那使人着迷的微笑,《圣安妮和另外两个女人》中女性的表情都反映了成年的列奥纳多对他童年早期的母亲的记忆。在弗洛伊德看来,促使艺术家创作的动力是里比多,即被压抑的性本能,而达·芬奇的传记作家没能把他童年时期对母亲的性依恋和成年后的性压抑与他的艺术创作和成就联系起来,因此不可能深入了解达·芬奇的精神生活,也无法真正理解他的作品。这位心理学家对传记作者的忠告是:“如果传记研究真想让人理解它的主人公的精神生活,一定不要避而不谈人物的性行为和性个性。”(注: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美文选》,张唤民、陈伟奇译,裘小龙校,知识出版社,1987年,第97、97、84—85、139、15、48、96页。)
传记作家肯尼思·林恩认为,以前的海明威传记作者就犯了弗洛伊德所指出的错误,因此他就是按照这位心理学家的精神分析学说来研究和理解海明威的。在他撰写的海明威传记中,林恩特别强调海明威的母亲格蕾丝对这位大作家的影响。他把海明威童年时代的各种事件收集到一起,并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展示出格蕾丝的性别暗示、性角色的含混意识对幼年时期的海明威形成的心理包围,并对他日后的生活态度和文学创作产生的巨大影响。多数人认为,海明威不少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硬汉子,具有“重压下的堂堂气概”。生活中的海明威也是如此:他酷爱打猎、钓鱼、斗牛、拳击,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内战,在五十五岁时两天内经历两次飞机失事,靠着顽强的毅力和惊人的胆量死里逃生。因此,把海明威称作“硬铮铮的男子汉”似乎一点也不过分。可是林恩运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研究了海明威青少年时的家庭环境后得出结论:母亲的影响使海明威形成了既具男性特征,又有女性因素的心理和个性。这一论断不啻在海明威研究界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实际上,林恩不仅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而且得到荣格的神话及原型批评方法的启发。荣格在他的个性化(individuation )理论中,提出了几个特殊的原型:阴影(shadow),人格面具(persona)和阿尼玛(anima)。荣格称男性心理中的女性倾向为阿尼玛, 亦即男人在其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中都具有的一种女性形象。正如一则古老的德国谚语所说:“每个男人身上都有他自己的夏娃”——换言之,人的心理是双性的。(注:Jung,Carl G.The Archetypes and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Vol.9,part 1 of the Collected Works,Trans.R.F.C.Hull,2nd ed.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8,pp26—30.)或许正是基于这种对于人的双性心理的认识,林恩才不遗余力地挖掘海明威的心理和性格中的女性因素。试想,如果没有现代精神分析学说、心理学和荣格的神话和原型批评方法,林恩怎么可能写出这样的海明威传?由此可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对传记文学有明显的影响。新历史主义认为,从“文本叙述”的角度看历史,历史就是一个又一个不断更新着的认识层面,它将不断激发我们对世界作新的思考。(注:盛宁:《二十世纪美国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56、258、268、262、260页。 )正是因为有了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传记作家才能不断更新他们对传记主人公的认识层面,进行新的思考,写出富有新意的传记。
另一位海明威传记作家詹姆斯·R·梅洛在1992 年出版的《海明威:无足轻重的一生》中仿效弗洛伊德分析达·芬奇绘画作品时所用的精神分析学的方法,研究海明威的性倾向。弗洛伊德认为,母亲的影响使达·芬奇长大成人后成了性变态者。当列奥纳多还是个艺徒,住在师傅家里时,就因被指控进行同性恋活动而被拘留。在他成了老师后,也只收一些十分俊美的男孩或青年作学生,而且他选择他们只是因为他们漂亮,并非因为他们有绘画方面的才能。因此,弗洛伊德断言,达·芬奇“真正属于同性恋的类型。”也许是受到弗洛伊德这一研究的启发,梅洛在他写的海明威传记中也探讨了这位大作家同性恋的可能性。虽然梅洛对海明威没有像弗洛伊德对达·芬奇那样做出不容置辩的结论,但他常常有意识地把海明威作品中有同性恋倾向的人物和作者的生活联系在一起,以证明海明威模糊的性倾向。
新历史主义的重要理论家路易·芒特罗斯说:“我们的分析和我们的理解,必然是以我们自己特定的历史、社会和学术现状为出发点的,我们所重构的历史(histories), 都是我们这些作为历史的人的批评家所作的文本建构。”(注:盛宁:《二十世纪美国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56、258、268、262、260页。)作为重构个人历史的传记作家们为同一个人写的不同的传记,便是他们为传记主人公所作的文本建构。弗洛伊德指出:“传记作家们用非常特殊的方法观察他们的主人公,”(注: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美文选》,张唤民、陈伟奇译,裘小龙校,知识出版社,1987年,第97、97、84—85、139 、15、48、96页。)而不同的传记作家用来观察各自主人公的方法是各不相同的。因此,传记作家对人物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兴趣不同,写出的传记也不一样。例如,在较早的时候,传记文学的主人公往往是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其内容的侧重点是历史人物与重大历史事件的关系以及他们在这些事件中的作用。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是这类传记的典型例子。18世纪英国著名的词典编纂家约翰逊博士在写《诗人传》时,他所感兴趣的是一百年来英国重要诗人的成就和不足,因此,这部传记对于诗人、作家和评论家具有极高的价值,但普通民众对它就不一定感兴趣。然而约翰逊博士的忘年交,《约翰逊传》的作者鲍斯韦尔感兴趣的就不仅是传记主人公在诗歌和学术方面的成就,而且是约翰逊本人,尤其是他机智隽永、强劲有力的谈话,而这些充满魅力的谈吐往往是在他交友、旅游和平时的趣闻轶事中显露出来的。因此,鲍斯韦尔在他写的《约翰逊传》中,再现了这位大学者的许多趣闻轶事,使传记主人公的形象真切感人,栩栩如生,也使这部著作成为传记作品中成就最高的之一,不但赢得评论家极高的赞誉,也为广大平民百姓所喜爱。
由此可见,传记作者对人物研究的侧重点是决定传记内容的重要因素,写不同人物时是如此,写同一人物时也是如此。以不同版本的海明威传记为例,卡洛斯·贝克感兴趣的是作为硬汉子的海明威。因此,在贝克写的传记里,我们看到的海明威是硬铮铮的男子汉。而肯尼思·林恩则把他对海明威的研究重点放在精神分析和母亲格蕾丝对他的影响方面,写出了一位男女性格兼而有之的海明威。迈克尔·雷诺兹感兴趣的则首先是产生海明威这样的大作家的社会文化环境。在第一卷《青年海明威》(注:Reynolds,Michael.The Young Hemingway,New York:Basil Blackwell,1986.)中,雷诺兹详尽地研究了在海明威出生地伊利诺州橡树园市的各种记录,提供了丰富的社会—历史材料,证明对海明威青少年时期所处的文化环境影响最大的是西奥多·罗斯福提倡的价值观念,其核心是充实的生活、健壮的体魄和自立的精神;罗斯福倡导的生活经历则包括战场上当过英雄,猎场上是位勇士。显然,青年海明威正是那个特定文化环境的产物。同时,雷诺兹对海明威的内心世界也特别感兴趣。在他写的海明威系列传记的第三卷《海明威:回到美国》(注:Reynolds,Michael.Hemingway:The American Homecoming,NewYork:Basil Blackwell,1993.)中,我们可以透过雷诺兹的笔,窥探到海明威心中的不少秘密。
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历史和文学都是“作用力场”,是“不同意见和兴趣的交锋场所”,是“传统和反传统势力发生碰撞的地方”。(注:盛宁:《二十世纪美国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56、258、268、262、260页。)传记作为介于历史和文学之间的形式,也是不同意见和兴趣的交锋场所。贝克、林恩、以及雷诺兹写出的完全不同的海明威,就反映了这种交锋与碰撞。不过,对于作家来说,他的作品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成果,因此,这种交锋与碰撞也表现在对作家同一作品的不同阐释上。为说明这一点,让我们以海明威最早发表的作品《在我们的时代里》中的一个故事“印第安营地”为例。
“印第安营地”是《在我们的时代里》的开篇第一章,讲的是尼克随父亲和叔叔来到一个印第安人的营地,当医生的父亲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为一位印第安妇女施行剖腹产手术的故事。产妇痛得死去活来,乱抓乱咬,产妇的丈夫就在妻子撕心裂肺的尖叫声中用刀割断自己的咽喉自杀。多数批评家认为,这个故事主要是让少年的尼克第一次感受到了生命的诞生并亲眼目睹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恐惧、痛苦和死亡,明白生活中有许多可怕的事。但也有的批评家指出,在故事的最后,尼克仍对生活充满信心。卡洛斯·贝克则认为,这篇小说有自传的因素,其中的人物亨利·亚当斯医生、他的兄弟乔治,以及少年的尼克分别是实际生活中的海明威的父亲、叔叔和海明威自己。不过小说中令人惊心动魄的场面和情节则是海明威充分发挥想象力,进行艺术创作的结果。(注:Baker,Carlos.Ernest Hemingway:A Life Story,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69,p.Ⅶ,16,125.)可是另一位海明威传记作家杰弗里·梅尔斯却指出,海明威有丰富的人类学知识,研读过弗雷泽的人类学经典著作《金枝》,而且在写这篇小说时运用了这方面的知识,反映不同种族文化之间的冲突,并断言只有这样看,才能对产妇的丈夫自杀一事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梅尔斯的解释是:那位印第安丈夫不能忍受白人男医生违反神圣的禁令,进入女人生孩子的地方。由于白人违反了印第安人的戒律,玷污了他妻子的纯洁,他自己甘愿接受惩罚,把妻子的血和自己的致命伤联系在一起。(注:Meyers,Jeffrey."Hemingway's Primitivism and 'Indian Camp,'"Twenty- Century Literature,1988,34:211—222.)
同一本传记,译成不同的语言,读者得到的印象也不完全一样,因为译者与原作家对传记主人公的认识水平往往不尽相同。例如贝克把他写的传记取名为《厄内斯特·海明威的一生》,但是林基海先生在把这部传记译成中文时,却在书名中加上了“迷惘者”三个字,成了《迷惘者的一生——海明威传》。(注:《迷惘者的一生——海明威传》,林基海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显然,译者认为,海明威是“迷惘的一代”的代表。美国学者中也有一些人持这种看法。他们的根据主要是海明威用了格特鲁特·斯泰因的“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这句话作为《太阳照样升起》一书的题记,而且这本书描写了“迷惘的一代”人的生活,成为这方面的代表作品。但是,究竟海明威是不是“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呢?我们先来看看他自己怎么说。
《太阳照样升起》出版一个月后,海明威在1926年11月19日写给该书编辑麦克斯韦尔·帕金斯的信中说:“看到有人认为我并不把格特鲁特·斯泰因的话当真,使人感到耳目一新。我的本意是要嘲弄那句夸大其词的伟大的话(格特鲁特自以为是的预言家的角色)。没有人了解比自己晚一辈的人,因而也无从做出判断。”(注:Baker,Carlos.ed.Ernest Hemingway:Selected Letters.1917—1961.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81,p743、744、292.)显然, 海明威并没把斯泰因关于所谓“迷惘的一代”的话当真。他比斯泰因小二十五岁,正好比她晚一辈,因此,在他看来,斯泰因根本不了解他们那一代,更无权给他们下定义、贴标签。三十八年后,海明威在回忆录《流动的圣节》中甚至称斯泰因的这句话为“废话”。(注:Hemingway,Ernest. AMoveable Feast,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64,p31.)
海明威是这样看待“迷惘的一代”这一标签的,那么他的传记作者贝克又是怎么认为的呢?实际上,贝克也同意海明威自己的看法,认为根本就不存在所谓“迷惘的一代”,更不用说把海明威看作其代表人物了。贝克说过:“他(指海明威)根本就不同意格特鲁特·斯泰因所谓‘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的话,他自己就一点也不迷惘。”即使在《太阳照样升起》中,作者所赞赏的几个人物杰克·巴恩斯、比尔·戈登和年轻勇敢的斗牛士佩特罗·洛梅洛也是共和国的严肃公民,他们全都精神健全,有明确的生活目标。只有罗伯特·科恩、布莱特·阿瑟丽和迈克·坎泼贝尔才是精神软弱者,“而三个精神软弱者是无法构成迷惘的一代的。”(注:Baker,Carlos.Hemingway:The Writer As Artist,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4th Ed.1972,pp75—93.)基于这种认识,贝克绝不可能用“迷惘的一代”这类的词给他写的海明威传记命名。他给这本书取名为《厄内斯特·海明威的一生》,这是一个不带任何倾向性的书名。贝克显然想告诉读者:写作本书时,作者力求不带任何偏见,客观、公正地展现海明威的一生。可是这本书的中译者却想当然地在书名中加上了“迷惘者”这个标签,殊不知这样一来,译者在不知不觉中已犯了一个大错误,违背了原作者客观公正的初衷。因此,不管中译本在内容上是否忠实于原文,书名中的“迷惘者”三字已使中译本的读者在接触此书的第一刻与原书的读者得到完全不同的印象,这乃是由于译者和作者在认识水平上的不同所致。
标签:海明威论文; 文学论文; 新历史主义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小说论文; 精神分析论文; 读书论文; 弗洛伊德论文; 老人与海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