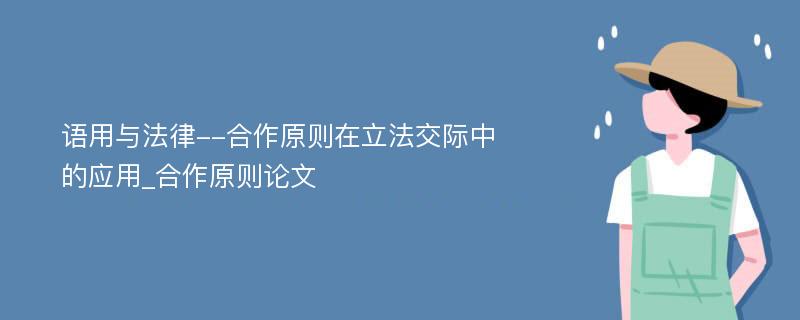
语用学和法学——合作原则在立法交际中的应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则在论文,法学论文,语用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绪论
当今,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无论是在语言学界还是在法学界,①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意识到语言与法律的密切关系,特别是语言对法律的重要性,以及法律语言研究的重要性。无论是语言学界,还是法学界,都有越来越多的人研究法律语言。国际两大法律语言学组织②的大会越来越频繁,吸引如会的人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国际上除了法律语言学的专门期刊“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eech,Language and the Law”之外,一些其他的刊物也开始关注法律的语言问题,出法律语言学的专号。③国内最近一些有影响的刊物连续出了法律语言学的专号④或者法律语言学的专栏。⑤由于学科背景不同,出发点不同,法学界更关注法律问题,所以他们总是把“法律”或法学放在前面,语言或者语言学放在后面。⑥而语言学界更关注语言问题,所以他们总是把“语言”或者语言学摆在前面,⑦而把法律或者法学摆在后面。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语言学和法学有机地、水乳交融般地结合起来,真正做到严格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体现跨学科研究的真谛。作者认为,就方法论来说,法学似乎是很贫穷的,差不多是叫花子,因此,要向语言学和其他学科学方法,借方法。⑧鉴于这一点,作者特专门撰写系列文章,介绍国外在这一方面做得较好的、较成功的学者及其作品。第一批先介绍美国的两位学者,他们都是法学专业出身,都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法律,都努力把语言学的一些重要的、有重大影响的且相当成熟的理论和方法用于法律(法学)问题的研究,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他们的研究非常有启发价值。本文主要针对国内读者,而且主要针对法学界,因为相对来说,从事法律语言学的人法学界要少一些。本文介绍辛克莱教授,⑨作品是:“法律和语言:语用学在法规解释中的作用”,⑩方法是把语用学的经典理论与立法和立法解释结合起来。
二、语用学与法学的结合:“法律和语言:语用学在法规解释中的作用”
“法学家历来对法律语言的历史和社会特征视而不见……不去研究法律语言实践的实际发展……”,(11)而辛克莱教授则力图克服法学的这个通病,把法律的语言实践置于社会和历史的视角下加以考察。作者借用语用学上非常成熟的基本理论——言语行为理论,(12)把立法作为交际,研究其社会事实和意义。这种把言语行为理论与法规解释的一些基本的普遍接受的本能感受结合的结果,便是一组相当连贯、很容易适用的原则,它们能帮助澄清法学(法律)当中一些常常令法学界非常棘手的问题和一些非常难以处理的解释过程,从而大大减少法规的不确定性和神秘性。
语用学上的言语行为理论之所以可以很好地应用于立法实践,主要是因为立法人(机构)在立法的时候,就是在与受所立法律管辖的人进行交际。立法是交际行为。立法人(机构)只要说话,其言语就是立法言语,每一个法律条款就是一个话语。而言语行为理论说到底是一种关于交际的理论。因此,我们就可以把言语行为理论用于立法。当然,立法人(机构)虽然要“说话”,要实施“言内行为”,但这种说话不是一般严格意义上的说话。现代的美国——其他国家亦然——立法人(机构)是通过书面语来实施交际行为。立法人(机构)通过法规来说话。那么这样的说话,在多大程度上受支配日常互动话语生成和解释的那些规则的制约呢?能不能把日常会话必需的解释规则用于国会呢?需不需要作一些修改呢?这些都是辛克莱在本文中要解决对问题。
扼要地说,语言学研究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句法、语义和语用。句法学研究语句的结构规律,语义学研究语句的意义,语用学研究语言的实际使用规律。这三者当中,语用学是法律或者法学研究最合适的参照方法,(13)而语用学的核心和奠基之石是言语行为理论。言语行为理论是英国(日常)语言哲学家奥斯丁(14)1955年在哈佛大学做威廉姆·詹姆士(15)系列讲座时提出来的。后来,他的学生厄姆逊(16)根据演讲的记录和录音整理,编辑出版了《如何以言行事》(17)一书。针对当时哲学上盛行的“语言的主要事情就是陈述事实”这一观点以及逻辑实证主义的意义真值论,奥斯丁通过对一种他称为“施为句”(18)的言语行为的考察和分析提出,许多话语不是陈述事实或者描述状态,因此没有真值条件,即是说无所谓真、无所谓假。成功实施这些话语行为需要满足一些条件,因此,研究或者确定这些话语的意义,就是研究成功实施这些行为的条件。随着研究的深入,奥斯丁发现,区分“述谓句”(19)和“施为句”很难,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因此认为所有的话语都是行为,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一个言语行为抽象成三个行为:(1)言内行为——发出的声音,用的词语;(2)言外行为——实际所做的事情;(3)以言取效行为——实施言语行为产生的效果,从而分别进行研究。言语行为理论是语言学上的一场革命,它彻底改变了人们对语言的看法,从而导致了语用学这门学科的产生。
在以言语行为理论为基础和核心的语用研究中,格莱斯的“合作原则”在各种语用原则中影响是最大的,相对来说也是最为成熟的。合作原则(20)是格莱斯(21)1967年在哈佛大学做威廉姆·詹姆斯系列讲座时提出来的,后来在“逻辑和会话”(22)一文中发表,作者认为:“我们的口头互动通常不是由一系列互不相连的话组成的,否则就不合理性。这种互动的典型特征——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合作的努力,每一个会话参与者——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意识到一个共同的目的,或者一组共同的目的,或者至少是一个互相接受的方向。”根据这一点,格莱斯提出会话的合作原则:“要按照需要做出你的会话贡献,在需要做出贡献的时候做出这种贡献,根据你所参加的会话的共同目的或者方向做出这种贡献。”(23)这一原则下面有四个准则,准则下面又有子准则:(1)量的准则:①提供所需要的信息(以符合当前互动的目的);②不要提供多于需要的信息。(2)质的准则:①不要说你认为是假的话;②不要说没有足够证据的话。(3)关系准则:(说话)要相关。(4)方式准则:①避免表达隐晦;②避免模棱两可;③要简洁(避免不必要的冗赘和啰嗦);(4)要有条不紊。(24)
格莱斯并不认为人们在会话中事实上都遵守这些准则,但认为遵守这些准则是合理的和理性的,我们不应该放弃。这里有两个意思:第一,格莱斯认为,人们会话只要有共同的目的,只要在乎这个目的,就要合作。这样,人的行为才是理性的、合理的。第二,在日常会话中,我们总是设定对方是合作的。合作原则的一个重要应用价值,或者说,格莱斯提出合作原则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会话含义的解释。人们在日常会话中常常说反话、讽刺话,常常字面是一个意思,实际上又是一个意思。传统的语义学和句法学始终无法解释这些问题。而有了合作原则,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我们在碰到这些问题时,首先设定说话人遵守了合作原则,然后根据语境等知识推导出含意。虽然会话合作原则受到很多人的批评,但它仍然是一种非常有力的解释性原则。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
哲学界和语用学界都知道,经典的言语行为理论和会话合作原则主要适用于口语,尤其是日常会话。而立法则是一种机构活动,一种文本语言行为。那么,合作原则和这些准则能否应用于立法言语呢?辛克莱首先将立法言语与日常会话进行对比,以便找出这种应用的基础。他认为,两者之间的相同之处是:(1)都使用语言,这是最大的相同点。在这一前提下,两者存在差异。人们开始会话时,总是认为对方能理解他的语言。虽然会变换语言,但是不会变得无法推进共享知识。但是立法人(机构)在这方面就有些限制,他们只能用他们的官方语言,因为他们只能用一种受到很大限制的书面语言,他们不能使用手势、表情等等手段。(2)第二个共同点是立法和会话都限于一个话题或者一个语域。但是立法在这一点上更严格,通常限于一个主题域,而日常会话却可能经常变换话题,因此立法更类似于一种理想的会话。立法和会话的最大区别是立法话语是单向的,任何立法话语的对象都不在场,不对立法会话形成制约。有人会说,立法言语的对象是法庭。然而,很少有立法是针对法庭的,任何立法都是针对立法所管辖的对象的。法庭只不过是让立法管辖的对象让人知道而已。立法话语的另外一个显著特征是与真值没有关联。与会话不同,立法话语是否为真,既不重要,甚至说也不相关。这是因为立法话语的根本目的不是推进或者完善立法者和其听众的共享知识,而是创造法律,立法的听众要在这个法律的范围内行事。但是,立法要有一致性。
虽然真值于立法不起作用,但是立法却具有强烈的目的性。目的之于立法,犹如真值之于会话。这是因为在立法中,任何话语,任何法律条款,只要与立法的目的相反或者不相关,都是不合适的。会话也是有目的的。因此立法和会话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25)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格莱斯的合作原则适合这种单向的书面的会话吗?根据立法话语和日常话语的相似点和不同点,辛克莱把会话合作原则下的准则应用于立法话语,并且做出了相应的修改和调整。
(一)方式准则
作者认为,在合作原则所有的准则中,最适合于立法的是第四个准则,即方式准则——“明白易懂”。这一准则跟其他准则有着根本的不同,因为它涉及的不是所说的话,而是说会话贡献应该如何作出。这一准则和其子准则可以直接应用于立法:立法应该避免模棱两可,避免晦涩,应该有条理,不应该冗赘。作者认为,相比较日常会话,这一准则更适合立法话语。因为立法话语是单向的,立法言语的听话人不能在现场当面对立法人(机构)说:“这个条款这样表达我不明白,你能重新表达一下吗?”另外,这里还涉及到用什么样的语言问题。大法官霍尔摩斯曾说:“如果要向世人发一个警告,这个警告要用世人能懂的语言来表达才是公正的。”(26)
在这几个子准则之外,阿尔伍德(27)建议再增加一个准则,即“充分性”准则,或者“最大限度地使用语言”准则。也就是说,立法使用的词语,其字面意义要最接近你想表达的意思。作者认为,阿尔伍德的这个准则是合理的立法交际的根本。立法的用语如果不能准确表达立法的意图,法规的理解就没有什么基础。
(二)量的准则
辛克莱认为,量的准则也能直接使用立法言语。立法言语与日常会话承载信息的方式不一样,立法言语并不告诉我们事情是什么样子,而是告诉我们如何行事。立法并不像会话那样向前推进就会增加共享知识,立法增加的是对行为的支配。作者建议对合作原则量的准则的第一个子准则作以下修改,以便更好地使用于立法话语:
“使法规的每一个条款涵盖你想涵盖的所有人和所有行为。”
格莱斯的量的准则有时被理解为“能说多少,就说多少”。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你想涵盖多少,就涵盖多少”。这一准则非常重要。如果法规要有意义,能够成功地指导人的行为,那么立法人就要遵守这一条规则。如果我们设定立法人的确遵守了这条准则,那么我们就能推出一些很可靠的含意。按照格莱斯的合作原则的量的准则的第一子准则(说点什么),我们同样也能设定:法规每一个确定的条款都说了点什么。因此,如果一个条款只是重复前一个条款,我们则认为这一新的条款是欺骗性的,就会在后一个条款中努力找出新的内容。如果后一个条款用不同的方式涉及了前一个条款的全部范围,我们也当这个条款是欺骗性的。立法人在第一个条款中没有说一个任意的、无根据的话语,但确是说了点什么。
这一含义的应用价值还体现在对《统一贸易法典》(Uniform Commercial Code)第9节第506条的解释上。
9-506.Debtor’s Right to Redeem Collateral(债务人赎回抵押品权利)
At any time before the secured party has disposed of collateral…the debtor or any other secured party may unless otherwise agreed in writing after default redeem the collateral by...
这里的问题是:“after default”是修饰“redeem the collateral”,还是修饰“otherwise agreed in writing”?如果是前者,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债权人在对方违约的情况下就重新获得抵押品。由于只有债权人拥有抵押品,债务人的赎回才有意义,所以赎回是在违约之后发生的——很少有例外。根据这一假设,立法人加上“after default”这个修饰语,等于没有说什么。如果取后一种解释,即“after default”修饰“otherwise agreed in writing”,那么这就意味着一个剥夺债权人赎回权的违约前的协议将是无效的。这样,这个条款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有目的的条款。因此,我们就很容易作出选择了:量的准则的第一个子准则规定:在这个语境里,“after default”修饰“otherwise agreed in writing”,因为另一种解释使得这个条款毫无意义。
这一准则的另外一个一般语用含义是:一个法律条款不适用于不在其特定范围之内的实体和行为,也不制约规定之外的这样的实体或者行为。一个典型的案例是“Iselin诉United States”案。Iselin女士对把她在大都市歌剧院出租的包厢的收入计入课税有异议。相关法规对涵盖内容非常细致,明显包括戏票的所有二手销售,但是——正如政府所承认的那样——法规没有规定对向被告所享受的那样一种特权进行课税。政府认为:“国会的意图明显是对所有的戏票销售进行课税,国会的这一总目的应该给予实施,以便使该法案能够涵盖立法目的内的所有案例。因此,这一法规在解释时应该扩大,使之涵盖这一案例。换言之,政府认为国会违反了量的准则的第一子准则,但是又不应该因此而败诉。最高法院认为,国会应该遵守适切条件:“政府要的不是对法规的解释,事实上是要法院把法规范围扩大,以便把因疏忽而漏掉的情况都包括进来。补漏超出了司法的功能。”法院认为立法人遵守了量的准则的第一条子准则,从而没有对法规作出包括规定之外的人或者行为这一解释。如果立法人对某一主体说了什么,那就认为它说了它想说的话。换言之,法规若沉默,它就没有制约作用。沉默必须解释为故意的。
辛克莱把格莱斯的量的准则的第二个子准则修改为:“使法规的每一个条款只涵盖你想涵盖的人和行为,不要超出这个范围之外。”
由这一准则可以产生一个一般语用含意:立法意图让所规定的控制适用于一个法律条款中规定的所有行为(即人加上行为)。如果意图的涵盖面变窄了,那就等于没有说应该说的话。这个准则适用的最佳例子是“Camininetti诉United States”案。国会在“曼法案”(28)中规定,该法案适用于“所有故意在州际贸易中……为了卖淫和淫逸的目的,或者任何其他不道德的目的,而运输妇女或者女孩的人”。然而国会会员曼的委员会自己的报告却说,该法案只是涵盖商业犯罪,而不涉及“泛泛的不道德行为”。换言之,该委员会的报告等于说,该法案涵盖范围超出了国会的意图,立法机构违反了量的准则的第二个子准则,但是又认为实施制约的应该是意图而不是法规。最高法院坚持认为,国会讲话总是贴切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在这个案子里,国会遵守了量的准则的第二个子准则,因此按照法规的条款应用了该法规,维持了对那些周末带着情愿的女人从Sacramento到Reno消遣的年轻男人的有罪判决。
(三)质的准则
格莱斯的质的准则是以“真值”和“证据”为标准的,而“真值”并不适合立法,因此,作者把质的准则修改为:“不要订立一个被证明不能促进立法目的的条款。”
这种修改有两个麻烦:一是怎么体现(反映、表达)日常说话人对其话语的“假”的了解:是应该用“已经被证明”这个说法来表达实际的感知状态,还是说“能够被证明”这个更有用且更有力的形式?作者倾向于用第二个,因为立法人在确定法规是否能够促进它所意欲的目的之前已经对提出的法律条款作了充分的研究;第二个困难是用“不能促进”还是“有害于”。用后者更接近格莱斯的“假”这个概念,作者倾向使用第二个,主要出于政治的考虑:世间一切都应该是自由的,除非出于某种重要的目的我们才非限制它不可。这些考虑自然导致我们对格莱斯的质的准则的第二个子准则作如下修改:“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能够促进立法的目的,则不要订立一个法条。”
作者认为这是一个政治性的且颇有争议的修改。因为,这个规则本质上是说,在对受制约者实施进一步制约之前,首先要满足举证的责任。这一点等于格莱斯的合作原则中的要求会话参与者能够为一个断言提供理由这个社会规定。但是作者认为这一准则并不重要,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当遇到一个法律条款有两种解释时,那么根据质的准则的第一个子准则,哪一个有利于促进立法的目的就适用哪一种解释。辛克莱以法官Learned Hand对“Lehigh Valley
Coal Co.诉Yensavage”一案的判决为例来说明这一点。Yensavage在Lehigh Valley公司的煤矿工作时受伤。州立法规定要向在不安全的地方工作的雇员提供赔偿,但是煤矿公司与Yensavage签订的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合同,该合同规定矿工为独立订约人(承包商)。现在的问题是对法规中“雇员”一词的解释。公司当然希望——尽管后面有保守的当局支持——应该对该词做出与立法目的相背的解释。法官Hand是这样说明的:(公司的观点)忽视了这种立法的目的——保护那些经济地位不利的人。诚然,法规用了“雇佣”这个词,但要根据立法的目的来理解它,因此在所有的相关条件都要求保护的地方,就应该给予保护……这种法规……不要理解为欧几里得的定律,而要设想到其后的各种日的。
(四)关联准则
作者认为,格莱斯的这一准则也能适用于立法言语,但是问题是:“与什么关联?”在(理想的)标准会话里,有话题和子话题。谈话时,我们凭直觉就能知道话题是什么。但是制定一个在一定的语境里找出话题的规则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对立法言语来说更难。立法人(机构)不能随心所欲地变化话题,他们在实际的立法(话语)中,遵守一个预先确定的计划。作者认为在两个意义上应对立法会话的题目加以说明。一是立法范围。规定商品销售的立法(例如《统一贸易法典》的第2条)是关于商品和销售的,其中就不能有关于医生执照的规定。所以关联准则要求每一条款只涉及法规范围内的事情(东西)。第二,说立法言语有一个话题是说立法有一个目的或者宗旨。立法人试图获得什么?对理想的会话来说,我们的目的是增进和完善会话参与者的共享知识。对立法话语来说,我们要用立法目的来代替日常会话的这一目的。另外,立法话语的关联准则主要指一个特定条款的意图和包含这个条款的整部法规的目的之间的关系。而在一个条款的内部同样存在这种关系:组成词语的意思必须符合该条款的目的,具体词语的解释必须依据立法的意图,否则我们就认为立法人(机构)违反了关联准则。我们认为立法人(机构)遵守了这一准则,这一点不仅非常合理,而且也符合实际。我们还是以上面Hand法官对涉及煤矿工人受伤的这个案子的判决解释为例。公司的立场紧扣法律辞典的解释,认为“雇员”有别于“独立订约人”。这一区别的根源在于涉及受伤害的第三方(人)的侵权责任和作用的法律。它跟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法规的“雇员”这个词的使用毫无关系。煤矿公司的观点认为立法人违背了关联准则,而Hand法官则反其道而行之,认为立法人遵守了关联准则。
作者在文章的第5节专门谈格莱斯理论在立法解释中的运用,限于篇幅我们不予介绍,读者看完本文,如觉得不过瘾,可以看原文。总之,作者认为,格莱斯的合作原则准则可以很好地应用于立法和立法解释,但是需要做出相应的修改。作者的这些修改很多是出于本能,但是从经验上来说是有效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认为立法人(机构)遵守了这些准则。
三、结论与批评
我们认为,辛克莱教授的这种尝试是非常有益的、有价值的。首先,它为立法和法规的解释提供了一条很好的途径。法律在应用中会产生争议,需要解释,那么我们根据什么来解释呢?有了格莱斯的合作原则和这些原则的准则——尤其是经辛克莱教授修改后的这些准则,我们就多了一种解释的依据和途径。第二,辛克莱教授的这种尝试非常富有启发意义。语言学的一些理论并非只适用于语言学而不能应用于其他学科、解决其他学科的问题。第三,辛克莱教授的尝试也是基本上成功的。作者本人在研究法庭审判话语时也曾经发现——或者深刻地感受到——格莱斯的合作原则及其准则基本适用于法庭审判话语。(29)法官在法庭上实际上一般都在自觉不自觉地遵守合作原则的这些准则,这样审判才会成功、才会公正。第四,这种研究既有借鉴和继承,又有创新和发展;既有理论,又有实例,这是作者非常赞成、非常提倡的一种研究范式或者风格。第五,作者把语言学理论应用于法学,旨在解决法学问题,但同时又对语言学作出了贡献,因为格莱斯的合作理论一般适用于日常会话,那么他对其他形式的言语交际适不适用?要不要做出修改或者调整?作者对这两个问题都做出回答,从而对合作原则和言语行为理论——乃至整个语言学学科——的研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辛克莱教授在论述关联准则时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与什么关联?”这也是作者一直对关联理论(30)进行批评的基础:关联理论始终没有说明与什么东西关联这个问题,而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不搞清楚与什么关联这个问题,谈什么关联?格莱斯的合作原则也没有说明与什么关联。辛克莱教授的解释是,在日常会话中,我们会本能地认为,关联就是与目前谈话的内容关联。但是,立法话语与日常话语不同,因此,我们得首先确定与什么关联,然后才能谈这个准则的使用。在辛克莱教授看来,立法话语的关联,就是与立法目的或者宗旨的关联。笔者非常赞同这一观点。实际上,不仅立法话语如此,日常会话也是如此,我们解释关联必须依据会话的目的和言语行为的目的。这样,关联理论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否则就是空中楼阁。笔者看到,在美国很多被上诉法院驳回或撤销的下级法院的裁决的理由(opinion)说明中,不少都是说下级法院没有按照立法的目的来处理有关争议。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目的原则(31)是更重要的原则和依据。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随后的“目的原则”系列研究论文中详细论述。
我们认为,关于“方式准则”有一条应该加上:话语明白易懂。由于日常会话不存在这个问题,或者说这个问题不大,所以格莱斯没有专门规定这么一个准则。而在立法交际中,这一点就非常重要。辛克莱教授曾经提到霍尔姆斯法官的话(这句话非常重要,很多睿智的大法官都说过类似的话,因为这些法官在法律实践的最前沿,所以他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语言的可懂性问题的重要性,而许多高高在上、坐在书房里或者在大学课堂上自我陶醉于只有自己能懂的那一套法言法语的法学家或者法哲学家,却根本不了解这一点或者不屑一顾)但是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辛克莱在对比日常会话和立法话语时说得非常清楚:立法话语是单向的,听话人不在场,听话人因此不能像日常会话那样,如果听不懂或者不清楚,可以当面问说话人、让说话人解释,从而达到交际的真正目的——理解和沟通。在缺乏日常话语这些条件的情况下,立法话语如果不考虑其言语行为的可懂性、明白性、清楚性,也不对其言语行为的可懂性、明白性和清楚性进行调查的话,那么立法人(机构)使用的话语很可能就是一种“霸权话语”、“欺负性的”话语、不公正的话语,本身就可能构成对受法规约束对象的侵权。顺便说一句的是,作者在美国布鲁克林法学院作富布赖特访问学者期间,(32)到位于布鲁克林的联邦法院、纽约州立法院旁听过不少刑事法庭的审判,且详细研究了几场刑事审判的录音转写语料,发现法官们都非常重视语言的规范性和易懂性,他们在庭审中的语言也很好懂。(33)这一点请我们国家的司法部门和一些提倡多半只为圈内人士才懂的“法言法语”的学者注意。
注释:
①尤其是法哲学界。
②The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Linguistic Law和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Forensic Linguistics。前者侧重法语国家和地区,后者侧重英语国家和地区。
③如《华盛顿大学法律季刊》(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Quarterly(1995,Volume 73,Number 3))。
④如复旦大学的汉语类核心期刊“修辞学习”,2006年第4期。
⑤如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外语研究》,2006年第2期。
⑥例如:本文要介绍的辛克莱教授的文章,题目就是“Law and Language:The Role of Pragmatics in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另外一篇,F.S.C.Northropt教授的“Law,Language and Morals”,(the Yale Law Journal Number6,Volume 71,1961-1962)。
⑦廖美珍:“语言学与法学”,载葛洪义主编:《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第4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⑧当然这不是说语言学就是方法论的百万富翁。语言学也是乞丐出身,很多方法都是从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学科借来的。
⑨辛克莱是美国印地安那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1974年获新西兰维多利亚威林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78年在密西根获得法学博士学位(M.B.W.Sinclair,Assistant Professor,Indiana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B.A.1968,B.A.(Hon.S)1970,Ph.D.1974,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Victoria,New Zealand; J.D.1978,Michigan.)。
⑩辛克莱:“法律与语言:语用学在法律解释中的作用”,载《匹兹堡大学法学评论》(1995)[Law and Language:the Role of Pragmatics in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1995,University of Pitsburgh Law Review]。
(11)彼德·古德思奇:《法律话语》,麦克米兰出版社1987年版(Peter Goodrich,Legal Discourse,1987,Macmillan Press)。
(12)英文为Speech act theory。
(13)同注7引文。
(14)J·L·奥斯汀(1911-1960)。
(15)威廉姆·詹姆士系列讲座。
(16)J·O·厄姆逊。
(17)《如何以言行事》,牛津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1962,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Performatives,即实施行为的语句,如:“我宣布大会开幕。”说这个话的同时就是实施“宣布”行为。
(19)Constative,即描述状态之类的语句,如:“她很漂亮”,和“他开的是一辆白色小汽车”。
(20)合作原则(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
(21)格莱斯(Herbert Paul Grice(1913—1988)),著名英国日常语言哲学家。
(22)《逻辑与会话》(Logic and Conversation)。
(23)格莱斯:“逻辑与会话”,载《话语论文集》(Grice,H.P.1999.Logic and Conversation,In Adam Jaworski and Nikolas Coupland(eds),The Discourse Reader,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
(24)同注23引文。
(25)狄克逊(R.Dickerson,the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Statutes 9-11,1975)认为,立法的目的是一个等级体,最具体的目的是采取一个行动,最宽泛的目的是促进全体公民的福祉。辛克莱把立法的目的等同于会话的总目的。
(26)McBoyle诉United States,283,U.S.25,27(1931)。
(27)Allwood,Negation and the Strength of Presuppositions,2 Logical Grammar Rep.3,1972.
(28)正式名称是the White Slave Traffic Act。
(29)但是有例外。参见廖美珍:《法庭问答及其互动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30)sperber,D.&D.Wilson,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2nd edition)[M].Oxford,Blackwell.1995。
(31)参见廖美珍:“目的原则和目的分析”,《修辞学习》,2005年第3期、第4期。
(32)2006年8月-2007年7月。
(33)提醒读者注意的是:英语不是我的母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