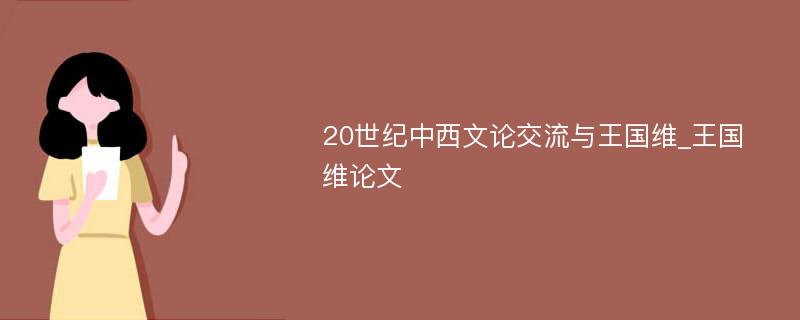
20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与王国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理论论文,中西论文,王国维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20世纪是文化大交流时代,也是中国文艺理论开始和西方接触和碰撞,并走向更宽广境界的时代。而王国维正是自觉到这种现代文艺美学意识的重要学者。他的学术思想体现了从“小文化”向“大文化”,从“受动时代”向“能动时代”的转折,为中国现代文艺美学的发展开拓了思路。
【关键词】 大文化 20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 学无中西 道通为一 世界文学
翻开20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王国维(1877~1927年)的名字会首先出现在我们眼前。这位生活在世纪之交的学术大师,在把传统文化精神香火带进现代文明殿堂的过程中,燃尽了自己的生命。无疑,王国维是一个标志性人物。要想真正理解和把握其在现代中国文艺美学上的价值和意义,就不能不跨出任何一种抱残守缺的文化观念,去拥抱一个开放的、完整的理论时代。
理论生命的完整意味正是从这里显示出来的。
一、从“小文化”到“大文化”
20世纪是人类文化进入一个大交流、大汇合的时代。这个时代到来的前提是,一方面是物质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精神文化上的欲望和追求。后者是一种对完整、对超越、对开放的欲望和追求,更是一种对残缺、对偏狭、对封闭的不满和对抗。在这个时代,某一地域型或某一民族性文化传统的怀疑者或叛逆者有可能不再是完全的文化意义上的孤独者和破坏者,而成为不同地域文化传统的沟通者和新文化形态的建设者。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情形不仅仅发生在经济文化上向外扩张和发展的西方发达国家,而且也发生在经济文化发展滞后的东方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讲,20世纪人类文化处于一种转型期,它正在从一种分散的、隔绝的、各自自成系统的小文化形态,向一种综合的、沟通的、互相紧密相连的大文化形态转化。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不能不重估和重建一系列文化价值标准,在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中寻找同源、同理的线索,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之间,拥有互相理解的桥梁,并创造一种更有包容性、也更有凝聚力的精神文明。
显然,只有到了20世纪,交流才成为一种自觉的历史意识。没有它,文明就不会诞生和发展,人类就不可能从野蛮状态中解脱出来。美国学者罗伯特·路威(Rebert H Lowle)在《文明与野蛮》《Are we civilized human cultureinperspective》一书中已提出这种观念。他以1877年绝种的塔斯曼尼亚人(Tasmanians)为例,提出并且回答交流之与文明进步这一问题:“他们没有草房子,只有简陋得可怜的障壁,他们不知陶器为何物,甚而至于他们的石器也不比(假定是)三万年以前的尼安得特人高明。为什么他们会落在别的民族后面整万年呢?是因为气候炎热影响人的智力吗?塔斯曼尼亚在赤道以南的距离和费城(Philadelphia)在赤道以北的距离不相上下;关键在当初的塔斯曼尼亚人一到了他们家里以后,立即和外面的世界断绝往来,他们自己和他们最近的乡邻澳洲人全都没有可以促进交通的船只。拿这个和历史上的任何复杂文化比一比,古代的埃及人和巴比伦人互相受影响,巴比伦人本身便是苏末尔人(Sumerians)和阿卡得人(Akkadians)的混合物。中国人老早和这些高等文明有接触,过后又从马来人、突厥人、蒙古人那里输入不少发明,希腊人的文化建筑在埃及人所立的基础之上,罗马人又尽量从希腊人那儿搬过来,我们的现代文明更是从四面八方东拼西凑起来的一件百衲衣。我们的文明的仓库丰满,塔斯曼尼亚文明的仓库空虚,不为别的,只因为我们前前后后接触过异族不计其数,而塔斯曼尼亚人接触过的简直等于零,因为任何民族的聪明才智究竟有限,所以与外界隔绝的民族之所以停滞不前只是因为十个脑袋比一个强。[①]
文明如此,文化也是如此。若干年前,我曾提出大文化和小文化的概念。所谓大文化,就是指一种开放的,由多种文化交流融合而成的文化形态,这是一种具有包容和转换能力的、在现代社会中富有活力的文化,唯有这种文化今天是有前途的,能够在新的文明阶段继续存在;而所谓小文化,是指一些自给自足的,在相对封闭状态中存在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在今天无论如何珍惜并试图加以保护,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消失或名存实亡。
不过,虽然考察这种交流过程已成为当今学界的热点课题,但是对这种交流本身的理解仍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完整。有一种看法认为,由于经济发达水平的差异,20世纪人类文化交流的主要流向是从西方到东方,即处于封闭和落后状态的东方文化在危机之中向西方文化求救,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而西方文化是“输出者”和“征服者”,主要是向东方国家和民族输出文化,由此也就产生了“西方文化侵略论”、“殖民主义文化论”等等立论和说法。如果不进行深层的文化探究,这种看法似乎很符合实际,很有说服力。但是从进一层分析就可以看出,这种说法除了把东方文化塑造成一种被虐待、甚至被强暴的形象之外,并不能给人们提供什么有益的东西。相反,一种对人类文化交流过程及其意义的怀疑开始出现,人们恐惧会在这种交流中失掉自己的传统文化,因而纠缠于对外来文化进行对抗和搏斗。
这种搏斗已经持续了几千年,这几千年也是人类根据不同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需要进行规模组合,从氏族部落到部落联盟,再到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以至于更大规模的跨民族、跨国家的国际联合体出现的历史过程。文化作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精神命脉,作为一种心灵图腾,曾经与某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政治体制、思想权威、甚至宗教仪式、神话传说连在一起,共同构成一种合乎人们想象,合情合理,合乎日常生活逻辑的意识形态。它不仅为个人思想行为规范提供依据,更为国家权力以及既定利益分配的“现实存在”提供难以动摇的思想基础。因此,文化的功利化、物质化和其神圣化、神秘化在人类历史上是同一过程,都不约而同地寻求着共同的平衡。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在不同范围内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文化圈,它们彼此竞争而又彼此隔绝,把必要的交流限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尽力维护自己生存状态的稳定性。
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对于文化交流意义的认识经历一个痛苦、矛盾的认识过程。因为交流本身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需要,即便是从最基本的生物进化过程来说,没有横向的联姻交媾,人类就无法从最原始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在这方面,人类也许是地球上最早觉醒的物种,所以最原始的氏族部落也禁止内部通婚。然而,由于人类生存和认识能力的局限,不可能创造一种宽容的文化观念和机制进行交流,而更重要的,在当时的文化群体意识中,血缘、肤色、民族、宗教等因素是难以逾越的界线,每一种文化都难以接受和容忍不同于自己属性的因素,以此来维护自己文化的尊严,所以,为了进行这种交流,人类一开始就不得不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战争和暴力曾是进行这种交流并有效地保存自己的有力杠杆,由此强悍的部落能获取弱者的妇女、财产和劳动力;而弱小的部落(主要是武力因素显示出来的)则因此会失去自己的生存地位和文化权利。因此,在崇尚暴力的时代,文化交流不可能是平等的,它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征服。这种征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交流,带来了历史发展新的机遇,但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痛苦的记忆。
这就在人类心理深处种下了一种恐惧感,以至于现在我们还时时处处感受到人们对文化交流所持的那种奇怪的双重态度:一方面非常推崇和向往,在很多场合赞美它,推动它;与此同时又心怀恐惧,在很多情形下限制它,拒绝它。这种情形也许会使我们联想到荣格(G.G.Jung,1875—1961)的“影子原型”(Shadowarchetype),当人们向往并进行文化交流的时候,总有一个阴影形影相随,它总是站在对立面,不断告诫人们:“小心呵,这是多么危险,最好立刻停止!”
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只要回顾一下历史上的种种痛苦记忆,很多人因此失去了自己的文化权利和精神家园,对此就不能不抱一种理解的态度;况且文化是人类灵魂安身立命的基础,任何一个人的自我意识都依赖于某种特定的文化传统而存在,一旦失去了这种基础,个人就不再有心理上的安全感,存在的自尊心就会受到挑战,如果他找不到一种新的精神家园的话,灵魂就永远得不到安宁与归宿。显然,征服具有剥夺性,它强迫人们放弃或接受某种文化体系或信仰,以摧毁人们原有的自我意识为前提,无论这种征服在言辞上有多么冠冕堂皇,都会对人性和人的存在造成伤害。
这种伤害不仅造就了人们、特别是处于受剥夺地位的弱小者,对文化交流的恐惧感,而且加深了人们对文化存在本身的误解,由于文化物质化和功利化的结果,人们已经习惯于把某种特定的文化和一些物质外壳联系起来,它们包括特定的政治权威、国家体制、民族和地域界限等等,而对于文化的内在化本质把握不足,这样,文化本身不仅成了处在种种物质包裹中的“壳中之物”,失去了自然和自由存在发展的性质和空间,而且极其脆弱,很容易在政治经济体制变动中被肢解、被摧毁。人们常常把文化和一些既定的现实存在混为一谈,以为一旦触动和改变了后者,就危害到了前者,因此也使得一些浅薄的既得利益者有机会发表危言耸听的言论,扩大人们的恐惧情绪。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所扮演的角色更是与众不同。这个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大国,过去对外界一直保持着精神上的自我完满、只出不进的姿态,中国人感到过物质上的贫乏和武力上的软弱,但是从未意识到精神文化上的贫弱,因而也从未想到去探索其它文化的秘密,自觉吸收外界精神文化财富,这种情况与西方有所不同。文艺复兴之后,中国文化逐渐被西方世界所了解,很多西方文化人象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不已,在西方世界掀起一次次“中国文化热”,从很多方面直接或间接吸取中国文化因素,并把它们溶入到自己的思想创造中,向世界贡献出许多跨文化、具有人类精神开创性的思想成果。
从某种意义上说,王国维(1877—1927年)和西方文化就是在这种时代文化氛围中相遇,并一同进入我们精神视野的。一些学者已经指出,王国维的出现对于中国文艺理论,乃至整个学术思想发展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不仅是中国传统文艺精神的真正继承者,而且是现代文艺理论,乃至现代学术意识的开拓者和创建者,至少在中国文艺理论发展中,他是一个标志性人物。他的批评创见和理论建设标志着中国现代美学和文艺理论的开端,体现了中国文艺美学从传统向现代、从中西隔绝向中西融合的历史转变。
这种评价无疑是有见地的,但是如何理解这种转变及其现代文艺美学精神,却并不能一言以蔽之,用某种含糊其辞的方式搪塞,因为这不仅直接影响着我们对王国维著作的阅读和评价,而且决定着我们对整个20世纪文艺美学历史的把握。假如中国现代文艺美学的特殊性就在于批判地继承传统,借鉴西方文艺理论来整理和重建中国文艺理论,那么中国20世纪文艺美学的现代性就显得过于简单和贫乏了,它至多不过是一次文化移植和嫁接过程而已,其中并没有多少世界性意义。如果王国维的意义就仅在于他是“以西洋的文学原理来批评中国旧文学的”“第一人”,在于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文艺美学上的天才说、古雅说、游戏说、痛苦说和境界说,那么他至多是一个成功的借鉴者或移植者,比起同时代的西方理论家来说,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换句话说,他对于整个20世纪世界文艺美学发展并没有什么独到的贡献。假如是这样,我们也就不得不把发生在中国20世纪的这场理论变革理解为一次地域性、而不是世界性的,它的意义也只能局限在中国文艺美学的发展变化之中。
这就牵扯到了文艺美学发展的尺度问题,尽管这是一个极其敏感、而又难以说清楚的问题,但是又是我们必须面对、不容回避的。文艺美学的现代性不等于用西方文艺理论观念来说明一切,更不是把中国民族的文艺美学思想归入到西方的体系之中,当然也决不是相反,用中国民族化的标准来批判、筛选和选择西方乃至整个外来文化。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依然无法摆脱“西方文化中心论”阴影的束缚,在文化心理上继续扮演一种“被征服”的角色,这种心态有时潜藏在人们心理深处,与另一种强烈的渴望征服他人文化的心理同时存在而互为表里,驱动着对外来文化反复无常的选择方式,时而表现出对中国传统的全面否定,对西方文化全盘接受的倾向,时而又陷入对传统文化无限自恋的情绪中不能自拔,对西方文化拒而绝之。在这里,我无意于深入分析这种心态的历史形成过程,只想指出它的存在对于学术研究视野和方式极其明显的限制,使其不能进入一种真正宽广清明的境界,与外部文化进行平等的对话。
二、关于从“受动时代”到“能动时代”
无疑,在王国维的思想意识中,渴望交流是和渴望理论生命的完整性是一致的。文化交流意识的觉醒,也正是中国现代文艺美学理论更新的开端。
其实,中国唐宋以降,思想理论上的贫困现象就日益突出,和西方同时代相比,恰巧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文化以春秋战国时代最为辉煌,思想巨子辈出,孔孟老庄诸子百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此后虽有两汉独尊儒术,但随后就有魏晋儒佛文化大交流,激活了中国精神文化创造力,为唐宋文学艺术创造高峰积聚了力量。但此后的岁月,精神文化创造力进入低谷,特别是数次被外来暴力征服的惨痛体验,中国文化人在专制暴政压迫下辗转反侧,失去了思想的独立性,精神疲软到了极点,除了用佛老哲学保身活命,用孔孟之道维护风化之外,真正卓越超群、划时代的思想文化创造几近空白。几百甚至上千年来,中国朝代频频更替,但时代文化精神却代代如此,中国人靠“吃”传统文化为生,却未能为其贡献新的精神,再也没有出现象孔孟老庄那样的大思想家,而差不多就在这段历史时期,西方出现了一代又一代大思想家。从文艺复兴启蒙时代,实证哲学、科学主义,到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不断进行新的创造,积聚新的思想力量,激励他们把社会推向新的阶段。
思想僵化和精神文化的贫困,必须导致社会发展的滞缓。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之所以落后于西方,固然表现在科技和生产力方面,但是其根源之一应该在先前的文化机制和精神状态中去寻找。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和丰富的思想创造,就不可能启动和承担快速的经济发展。
王国维最早深刻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他的时代,如何保存中国文化命脉,如何建造新的精神家园的问题已经提出,王国维之所以对此心领身受,更有一种沉重的文化责任感,是因为他不仅意识到了精神之于物质的这种历史关系,而且深感近代中国精神上贫困之遗害无穷,因为无精神之慰藉,鸦片缠足,腐败贪污等人心堕落,社会滑坡状况才成为必然,例如他在《文学与教育——〈教育杂感〉四则之四》一文中略述了近代西方思想界巨人辈出的现象后就如此感叹:
今之混混然输入于我中国者,非泰西物质的文明乎?政治家与教育家,坎然自知其不彼若,毅然法之,法之诚是也,然回顾我国民之精神界则奚若?试问我国之大文学家,有足以代表全国民之精神,如希腊之鄂谟尔,英之狭斯丕尔,德之格代者乎?吾人则不能答也,其所以不能答者,殆无其人欤?抑有之而吾人不能举其人以实与欤?二者必具一焉,有前之说,则我国之文学不如泰西;由后之说,则我国之重文学不如泰西,前说我所不知,至后说,则事实较然,无可违也。我国人对文学之趣味如此,则于何处得其精神之慰藉乎?求之于宗教欤?则我国无固有之宗教,印度之佛教亦久失其生气,求之于美术欤?美术之匮乏,亦未有如我中国者也,则夫蚩蚩之氓。除饮食男女之外,非鸦片赌博之归而奚归乎?故我国人之嗜鸦片也,有心理的必然性,与西人之细腰,中人之缠足有美学的必然性无以异。
有了这种意识,对于精神和理论创造的渴望自然非常强烈,王国维把它看作是国家民族永久利益之所在。因此,在学术研究中,他也时时在寻求一种理论上的突破。以《红楼梦评论》为例,王国维引古用今,中西参证,不只是在探索红楼梦的艺术价值,更是在探索一条理论之路,自始至终不忘对艺术之美和“美学上最终之目的”的阐述,这正是王国维评论红楼梦的与众不同之处。红楼梦作为一种感性的艺术现象早已存在,但是人们之所以对其精神与美学价值不能真正领会,就是由于缺乏对美对艺术及其本质的认识,丰富的艺术现象与其同时存在的贫困的文艺美学观念并不吻合,相反,两者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和间隙,因此造成了阅读和评论中审美的缺失和贫乏,王国维是“为破其惑”而作的,这个“惑”就是理论之惑、观念之惑,是中国近代在美学艺术理论上的贫困所致。
这就引起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问题,这就是现代文艺美学理论的觉醒,这也正是20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过程中最多期盼、也最步履艰难的追索。几乎每一个理论家批评家到了一定的阶段都会发问或者扪心自问:“我的理论和批评方法是何处而来?我们何时能有自己的理论?”
这也就是王国维非常强调哲学和美学作用的原因之一。他坚持要在大学设置哲学课程,并认为这是一个国家“最高之学术,是文明昌盛的基础”,“故无论古今东西,其国民之文化苟达一定之程度者,无不有一种之哲学。而所谓哲学家者,亦无不受国民之尊敬,而国民亦以是为轻重”。[②]他还认为,自19世纪以来,西方强国以教育为本,致使教育学很发达,而“夫哲学,教育学之母也”[③]所以,要搞好教育,自然也离不开宏深的哲学思想基础,所有这些都表现了他对思想理论创造的高度重视。一个民族没有它,就没有主心骨和文化素质,就谈不上开拓和创造未来。王国维的这种思想实际上构成了后来五四新文学精神的基本内核,这就是用新思想新观念启蒙人心,改造国民性。我们在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中不难听到它的回声。
单单就文艺美学观点来看,王国维很容易给人一种空灵的感觉,尤其和梁启超、鲁迅等人相比,而他最后自杀身死之结局,又加深了这种印象。对文艺美学和哲学,王国维不仅讲超脱讲游戏,而且是推崇无用的。他那篇著名论文《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开首就是“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学是也。”但是,只要稍微贴近一步就会发现,王国维远非脱尘隐逸之人,其深深的责任感和价值意识就在这“无用”之中。因为“无用”是有针对性的,是有具体内容的。它一方面针对世俗利益之追求,另一方面更是一反传统文学价值观,追求现代思想自由和艺术独立之价值,这一点,陈寅恪最为理解,他在为王国维身后写的铭文中字字见血,表达了20世纪中国文化人的任重道远和持久追求,这就是他于192年在“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文中所写:“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这一切都溶铸到了王国维的交流意识之中,和美国学者罗伯特·路威的思路相同,只不过时间更早些。王国维认为思想理论的贫困来自于交流的匮乏。基于这种思路,他对中国文艺美学理论的发展历史进行了新的反思:“外界之势力之影响于学术,岂不大哉。自周之衰,文王、周公势力之瓦解也,国民之智力成熟于内、政治之纷乱乘之于外,上无统一之制度,下迫于社会之要求,于是诸子九流各创其学说,于道德政治文学上,灿然放万丈之光焰,此为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自汉以后,天下太平,武帝复以孔子之说统一之,其时新遭秦火,儒家唯以抱残守缺为事,其为诸子之学者,亦但守其师说,无创作之思想,学界稍稍停滞矣,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敝之后,当此之时,学者之见,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担簦访道者,接武于葱岭之道,翻经译论者,云集于南北之都。自六朝至于唐室,而佛陀之教极千古之盛矣。此为吾国思想受动之时代,然当是时,吾国固有之思想与印度之思想互相并行而不相化合,至宋儒出而一调和之,此又受动之时代出而稍带能动之性质者也。自宋以后以至本朝,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是也。”[④]
这也许是首次把中外文化交流看成是文化进步的根本动力之一,王国维以此贯串历史,为近现代中西交流第三次从“受动”到“能动”时代的到来提供了历史依据。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发现,而且是一种对理论的创造,它是对以往只重纵向继承。内部生成思维方式的否定,转向了对横向交流、内外交融的肯定和重视。中国文艺美学第三次能动时代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时代,而这个时代的理论无不与文艺美学交流有关,这种理论意识无疑是新的文学时代最明显的标记。
很难说清楚王国维这种理论意识的来源。在那样一种封闭的社会环境中,没落的传统文人多半沉浸在怀旧意识之中,而王国维(而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过自己旧朝贵族文人的身份)竟然能有如此宽广的胸怀,提出如此超前的观念,不能不使我们重新思考传统与现代的历史联系,从个人文化身份来说,王国维虽然根植于华夏传统历史文化,但是一直认同于满清旧朝体制,证明他内心深处已经接受满汉合一的文化观念。在他看来,满清入关,推翻汉人统治,并不意味着否定华夏文化,而华夏文化命脉在历史演进中已经与满清存亡汇入一体,否则,他在当时的思想行为就显得不可理喻。这不仅表现了他当时和许多同时代文化人决然不同之处——后者依然以灭清扶汉为己任,同时决定了他华夏文化历史生成过程的看法,至少他已经超越了单一的汉文化观念,选择了多文化融合的观念,而这一点对近现代文人的文化观念影响极大,香港作家金庸生活在中国最现代化的都市中,但是在他初期创作中,汉人王朝的正统观念还很浓厚,直到后期才有所改变,而把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作为基调。他认为:“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⑤]
可见这种观念之根深蒂固,而从王国维到金庸——他前不久被聘为北京大学的名誉教授,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文化观念从单一向多元、从学界向民间转变的艰难而又漫长的过程。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在考察和论述文化交流过程,同时在重新理解和确定交流的理念,我们在建设和确立一种现代文艺美学的观念,而又不得不从检讨我们的文化心态开始。事实上,学术和理论之本在于人心,没有健康完整的心态,就不可能有健康和卓越超群的理论创见。尤其对于现代中国来说,文化语境非常特别,我们拥有几千年优秀文化传统,它已经并还在给我们以历史的文化自尊心和自信心,我们心理深处有根深蒂固的文化自豪感甚至优越感;与此同时,我们近几百年来多次被外来势力征服,长期在经济和科技方面落后于他人,体验了从高贵自大的顶峰向卑贱弱小深渊降落的痛苦过程,自尊心和自信心都曾降落到最低点。对这种心态,鲁迅曾有过深刻的分析和描述。《阿Q正传》中所表现的阿Q式“精神胜利法”,就是这一过程心理积淀的成果,这种阿Q心态不但表现在中国人一般日常生活中,也渗透到了思想方式和理论方法之中。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中,时常在自傲和自卑之间徘徊,这样不但会失去对西方文化完整的把握,而且也可能迷乱于传统文化的历史沼泽中,后者有时是骄傲的资本,有时是自卑的源泉,心理文化优势会在瞬间变成劣势。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20世纪中国中西文化及文艺美学理论深度交流的倡导者,王国维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被征服”心理。这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他在建立自己文艺美学理论的时候,从来没有仅仅把西方理论作为依据;第二,他在借重西方文艺美学理论的时候,时时都在寻求东西方共通的因素,试图解答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第三,他在精神文化追求中,从未把西方文艺美学思想当作“工具”或者“手段”,用来追求功利和世俗利益。
显然,王国维独特的价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传统文化修养的根底。也就是说,他之所以一开始就能抛开狭隘学术偏见,把中西文化交流看得那么重,认定这是中国第三次“能动时代”来临的关键,这是在于他比一般人更深刻地把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在这方面,他并非仅仅从静态眼光去看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范畴和观念,而是从它的生命发展过程去理解它,因此得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辉煌灿烂者,皆由于能够吸收各种域外文化,求通于各家学说。所谓“不通诸经,不能解一经”,正是古人留下来的至精之言。所不同的只是,过去的诸经,可言之于诸子九流,可言之于佛学东渐,可言之于各种少数民族文化,而到了20世纪,就不能不言之与西方文化的沟通。所以王国维如是说:
若夫西洋哲学之于中国哲学,其关系亦与诸子哲学之于儒教哲学等。今即不论西洋哲学自己之价值,而欲完全知此土之哲,势不可不研究彼土之哲学。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
——《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
此种洞见不仅打通了中西学术之关系,而且表达了一种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世界意识,是中国学术睁眼看世界,面对世界并溶入世界的开始。
王国维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文化态度,他迷恋于西方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思想,并非是出于舍弃中国文化,直取西方文化之意愿,而是敏锐感受到了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应合和相通之处,例如其《红楼梦评论》就是最明显的例子。这篇论文历来被学者认为是首次运用西方文艺理论方法研究和评论中国文学名著的典范作品,却是以引用老子“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和庄子“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之语开首的,继尔开始论述人的欲望作为生活的本质,不仅是人的思想行为的根本驱动力,而且也是造成人生痛苦的根源。观其全文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思想意识,特别是老庄思想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奠定了其基本思路,是王国维评论《红楼梦》理论方法的基本来源。它和叔本华的思想互相映照印证,决定了这篇论文的通达气势。所谓通达,是指它打通了东西方文艺美学思想,以中喻西,以西比中,中西合璧,互相引展,从而以世界性的美学眼光来考察《红楼梦》,揭示了其超越中西文艺观念界限的艺术意义。在这里,不仅东西方观念的隔阂被打破了,而且超越了以往对作品来源和意图进行追求的思路。作品本身并不是终极,而是一座艺术桥梁,它通向人类共同面临并寻求解脱的人生和艺术问题,通向人类心灵深处;评论家的任务就是通过这座桥梁把这两者之间鲜为人知的秘密揭示出来,告诉人们。正因为如此,王国维认为,《红楼梦》的精神价值就在于切中了人类共同为之烦恼的问题——欲望和解脱,而且是“非徒提出此问题,又解决之者也”,它的主题不仅最贴近艺术的根本任务——“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痛苦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⑥]而且实现了美学与伦理学价值的高度相合。
由是观之,过于强调或者仅仅看到王国维运用西方文艺理论方法评论中国文学名著这一方面并不全面,至少这种提法欠准确,而且容易引起误解。首先,王国维在这篇评论中不仅仅只运用了西方文艺理论方法,正如上面所说,他也同样运用了中国传统思想方法。而更重要的是,此文的思路并不是用西方理论解析中国文学现象,或者用中国作品印证西方文学理论,因此无论在理论或者论述之中都无中西思想谁高谁低问题。在这里失之毫厘的表述,都有可能形成差之千里的判断,我之所以强调这种细微之处的准确性,不仅直接牵扯到对王国维学术精神的评价,而且触及到了对中西交流观念的深度理解。长期以来,人们似乎已经接受了这种观点,20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就是“西学东渐”的过程,期间基本特点就是用西方理论来“指导”中国实践。因此,在理论批评界也形成了如此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无论潮流和言辞如何变化,西方理论观念一直处于“先进”的主导地位,而中国文化只能是分析、综合和重建的对象或“材料”。无疑,这里隐藏着一种微妙的文化心理上的不平等。“文化征服”的暗流一直潜伏于意识高涨的革命热情之下。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文化心理上的病变积累,它与后来发生的象“十年动乱”那样全面否定和仇恨文化的悲剧行为不能不说有关联。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也有选择,但只是对诸种西方理论中的一种进行选择。
当然,学界近年来对这种情形已有稍许觉醒。
文化是不能被消灭的,它只能被溶解,变成不显形迹的人类深层意识,而不可能被完全清除和摧毁。因为文化和人密不可分,文化的最终成果是人,是人的精神意识。只要人存在,文化就存在。这正是很多迷信暴力的征服者所难以想象的,也是很多柔弱文人之所以能在残酷专制条件下逆来顺受、泰然自若的原因。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的文化好象已经消失了,或者被其它强有力的文化毁灭了,但是这种消失和毁灭只是表面的、形迹方面的,而其内在的精神因素则继续存在于人类生活之中。难道西方古代的希腊文化、罗马文化真的已经毁灭,已经不存在了吗?难道中国人的文化血液中不再有殷商文化的积淀吗?当然,文化不能被消灭和清除,并不意味着某一种文化能永世长存,能一直保持固有的形态,文化会在历史发展中变化和转换,可以从一种形态转换到另一种形态,这也正是文化交流的意义。文化交流给这种变化和转换提供时机和必要的新因素,使某一种文化能够摆脱自身的贫困状态,获得新的生机。
20世纪之所以与前不同,并不仅在于文化交流的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而在于人类对此有了自觉意识和自觉要求,能够从自身发展的根本意义上理解它和把握它。在这个过程中,优秀的思想家和文化人——不论他身在何处,在何种文化氛围中——都意识到了自身文化的局限性和偏狭性,开始对于原来文化传统的中心地位和完美性产生怀疑,并积极向外面的文化学习。这种情形不但发生在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东方国家和民族,而且也发生在先进的西方国家。因此,这是个双向交流的时代,东方和西方都感到了自己文化的危机和匮乏,都意识到自己只是整个世界的一半,都需要用另一半来补充自己和完善自己。
由此说来,文化的“受动”和“能动”是互相联系的。在现代中国,没有“受动”,就没有文化思想内部的“能动”(由此观之,则近数年之思想界,岂将无能动之力而已乎,即谓之未尝受动,亦无不可也。——王国维语),这无疑道出了20世纪中国文艺美学交流的一个重要认识。(待续)
* 本文于1997年2月28日收到。
注释:
①《文明与野蛮》,中译本,吕叔湘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3—14页。
②《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第55页。
③《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第76页。
(46)《王国维文学美学论文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06页、9页。
⑤《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1994年。
标签:王国维论文; 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文艺理论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文艺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