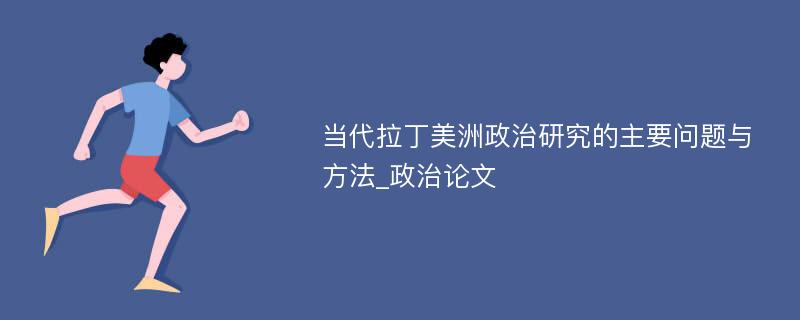
当代拉丁美洲政治研究的主要问题与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拉丁美洲论文,当代论文,政治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的30余年间,拉丁美洲的社会政治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①无论具体的运作和相关的主张与认识存在多大的差异,拉美国家目前无一不属于或自视为民主体制。这一演变是20世纪拉美政治变迁的延续,即20世纪30年代以后寡头政治秩序向大众政治社会转变的一个自然的、逻辑的后果。大众政治时代的到来,伴随着以现代化理论为代表的政治发展研究,而70年代末以来拉美国家政治体制的转型则引发了有关民主化进程的一系列分析和辩论。
拉丁美洲政治研究所关注的就是这一演变过程中的政治结构、制度、思想、政策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拉美政治研究对于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建设和知识积累具有重要的意义。拉丁美洲历来被视为一个具有分属不同“世界”特征的地区:宗教、语言、文化乃至政治思想的欧洲影响与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后裔的传统并存,使这一地区既可以属于“西方”也可以归入“非西方”;独立和发展进程启动较早,使这一地区有别于亚洲和非洲新兴国家,但对外依赖的现实又无法置身“边缘”地位之外;历史上资本主义发展与追求社会正义的交织以及专制独裁与民主政治的循环,又使这一地区成为各种经济、政治理念和模式的试验场;而20世纪末叶最独特之处则在于,整个地区在政治上已经属于民主体制,即公民在形式上已经享有自由、平等权利,但同时却仍面临着世界上几乎最为突出的贫困、不平等和社会排斥现象。拉丁美洲因此而为政治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证分析材料。
与此同时,拉美政治研究也为当今世界主要政治问题的分析提供了富有洞察力的思想和十分有价值的理论工具。事实上,所谓“发展中”世界的研究和理论发展最初主要就是基于对拉美国家状况的观察和分析。拉美研究得益于同时也激发了不同地区包括发达世界与发展中世界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催生并验证了许许多多的政治概念和理论,从而为政治研究范围的扩展和深入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已经耳熟能详的研究术语可以举出发展主义、依附论、官僚威权主义、民众主义、法团主义,等等。
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编著出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丁美洲政治》一书,全面介绍和分析了20世纪中叶以后拉美地区的政治动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②其主要章节包括:拉丁美洲概况及政治简史、拉丁美洲国家的政治体制、军队、拉丁美洲的政党和工会、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思潮、拉丁美洲民族民主运动、拉丁美洲的天主教会和战后拉美国家的对外关系等。差不多与此同时,1990年,美国学者戴维·W·登特编辑出版了《拉丁美洲政治学研究手册——从60年代到90年代的趋势》③。登特就美国和拉美学者的拉美政治研究历史和方法作了归纳,其中关于研究的主要问题,美国学者主要关注革命、国别和比较研究、军队与政变以及政党与选举;拉美学者关注的问题则是革命、政治人物、政党与选举、政府与法律机构。美国学者主要采用法团主义、庇护主义、民众主义以及结构主义等概念和理论工具,而拉美学者则主要运用依附论、官僚威权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
显然,中国学者、美国学者和拉美学者所关注问题和所使用方法的范围存在较大的交集,或者起码用不同的表述来指称所研究的同一种现象,例如最为突出的是对于革命问题的重视(中国学者将革命问题归在民族民主运动项下)。但是,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学者观察问题的视角和研究路径还是有很大差异,除了关注问题的重点有所不同外,这尤其体现在所使用的理论工具上。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两部书所涉及的问题和方法至今仍是拉美政治研究中的基本问题和方法,也是今天拉美政治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但是,其中一些问题目前已处于“蛰伏”状态,或是通过其他方式表现出来;同时不可否认的是,拉美政坛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可以说,拉美政治研究议程中既有常见常新的老问题,也有许多需要借助新的思路才能加以认识的新问题。因此,拉美政治研究议程有必要不断地进行调整和补充。
一 当代拉美政治研究的主要关注点
20世纪末叶拉美政坛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民主化的逐步展开和深化过程之中。60~70年代,军人干政和威权体制主导着拉美大陆;自1978年始,从安第斯、南锥体到中美洲和墨西哥,民主体制相继确立并延续至今,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变化。几乎与此同时,80年代初期以后,拉美国家陆续陷入经济危机并相继开始了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以新自由主义信条为指导的经济政策调整席卷了整个拉美大陆。政治民主化和经济改革意味着利益和权力关系以及社会整合模式的调整和变迁,并几乎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矛盾、冲突和动荡。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既关乎政治领域自身的演变规律,也涉及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变化之间的关系,并对传统或“经典”的理论和解释模式形成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在拉美政治研究领域,一方面,所谓“社会学传统” (即基于社会历史和阶级结构的解释模式)开始转向社会运动和文化分析。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政治”本身作为独立的推动力量(而不仅仅是社会、经济因素的产物)日益受到重视。由此产生的研究导向是在不否认结构条件和社会力量制约的条件下,将分析焦点集中在现实的政治行为体及其互动关系上,并且承认政治过程由于受制于人的选择而充满不确定性。政治学、政治经济学以及政策选择和实施模式分析的影响日隆,政治和国家制度开始回归或占据政治分析的中心地位。因此,可以看到政治研究议程开始关注体制(regime)研究,即二战后拉美国家出现的不同类型的政治体制及其稳定性的分析;民主过渡(transition)研究,即80~90年代拉美国家告别威权统治确立民主体制过程的分析;以及世纪之交关于拉美国家民主体制实际生存和运行状况的分析等。④
另一类变化涉及所谓的“学术共同体”。从事拉丁美洲研究的学者既来自拉美国家也来自拉美以外的世界其他国家,后者包括以拉美研究为主业的学者(Latin Americanist)和对拉美感兴趣但学业上另有专攻的学者。拉美研究状况受到这些学者群体自身演变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学者群体之间交流和对话的影响。例如,长期以来来自拉美内外的学者一直在关于欧美政治发展经验及其模式的普适性(universality)、可欲性(desirability)以及在拉丁美洲的可行性(feasibility)等问题上进行着持续的对话,并且就拉美的“西方”或“非西方”定位进行着激烈的辩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虽然很多学者仍摆脱不了自我“种族中心”倾向,但一些欧美学者却开始怀疑甚至否定欧美政治模式在拉美的有效性,而许多拉美学者在秉持强烈民族主义立场的同时,却积极主张拉美是“西方”世界的一部分。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中国学者介入国际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多,并且学习和引进了国外同行的大量研究成果,特别是研究方法。由此产生的一个后果是,中国学者基本上能够了解当下拉美政治研究议程中的主要问题,但由于环境和学者个人条件的不同对方法的应用有所取舍。这与国外同行的情况大同小异,即学术界对拉美政治研究“问题”的认定基本上有一个趋同的局面,政治议程涉及哪些方面并无太大分歧。但在观察视角和分析方法上却很难形成一致的意见,不同学者的研究结论自然有可能大相径庭。
从国内外学者的拉美政治研究的一般情况来看,当代拉美政治的动态主要是围绕着“民主化”进程展开的,即将政治民主化视为拉美政治研究的中心问题。而这一中心问题牵涉到一系列需要分别加以探讨的主题,例如按照民主化进程研究的学术轨迹相继出现的关于民主过渡、民主巩固和民主治理的分析。由于民主化进程始终充满变数和不确定性,民主政治可能向着制度化的方向发展,也可能逐步退化、衰微,最终重蹈历史上民主体制垮台的覆辙;因此出现了许多关于民主体制运作和绩效的实证分析,特别是运用新制度主义的方法考察选举、政党和政党制度、行政和立法机构及其相互关系、司法体系、监督机构、联邦制度等。而民主体制的前途不仅系于制度本身,它还与社会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结构)、经济因素、国际影响密不可分,因此有关拉美国家政治行为体的演变、各种经济和政治思潮、经济改革与发展状况以及与外部世界的互动等等,都成为拉美政治研究议程中的重要内容。⑤
在观察视角和研究方法方面,首先需要明确的一个问题是所谓当代拉美政治研究的时空框架。从时间上看,一般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历史时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但是,鉴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拉美国家政治生活的内容与此前时期相比已发生巨大变化,可以将战后时期分为不同的阶段。目前拉美政治研究主要涉及的是70年代末以来民主化进程中的有关问题,这可以视为当代拉美政治研究时间框架的一个大致范围。在地理区域上,按照惯例,拉丁美洲国家是指南美洲10国(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拉圭、秘鲁、乌拉圭、委内瑞拉)、中美洲6国(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马)、墨西哥以及多米尼加共和国、海地和古巴,共计20个国家。南美大陆上的圭亚那、苏里南和法属圭亚那,中美洲的伯利兹以及加勒比岛国一般通称“加勒比”地区,在社会学和地缘政治意义上有别于上述20个国家。因此,有关上述国家的完整表述应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鉴于加勒比国家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往往有必要专辟专题加以研究;同时,古巴作为西半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拉美国家中的一个特例。因此,所谓“拉丁美洲政治研究”需要根据所研究的问题划定地理范围;就民主化问题的研究而言,一般涉及除加勒比地区和古巴以外的拉丁美洲国家,其中许多研究通常会开宗明义具体指明所涵盖的国家。⑥
就拉美政治研究内容本身而言,它应包括关于拉丁美洲政治“实际动态”的描述,也应包括学术界对实际政治进程的“研究动态”。对于中国学者来说,除少数情况外,一般是根据国外文献进行学术研究(或根据媒体信息进行综述),实地考察(田野调查)和理论建构尚不具备充分条件。学术访问(包括所谓长期出访)也基本上是文献资料收集式的(在学术机构的访谈学者属于此列),而非就某一特定问题直接进行调查。因此,这里所谓的拉美政治研究主要涉及的就是如何界定和把握“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两个方面的内容。
拉美政治研究的主要问题
这里所谓的研究问题指的是纳入研究议程的拉美国家政治生活历史演变和现实发展中的政治现象。界定和选择问题要求审视和分析特定时间框架(例如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30余年)所涵盖的拉美政治发展历程,主要是通过“学术动态”即国内外学者的有关研究去认识拉美国家政治的“实际进程”。这既包括“概论”式的研究,即就某一时期政治生活中各种主要问题作一总体梳理和阐述,也包括“专论”式的分析,即就某一具体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细致的考察和探讨。这既是一个知识积累的过程,主要通过“拿来主义”方式掌握“实际”材料、概念和理论,也不妨碍在条件具备时提出新的方式、发掘新的材料或重新组织现有的资料并给出某种独特的历史描述和说明。这是对历史和学术史的双重把握。
按照政治研究的一般逻辑顺序,掌握政治生活的历史脉络无疑是必要的第一步骤。有鉴于此,拉美政治研究可以首先从政治发展的角度出发,探讨和明确不同拉美国家所处的政治发展阶段。当代拉美政治研究一般以20世纪50~60年代的现代化研究为逻辑起点,依历史顺序大致涉及民众主义、依附论、法团主义、官僚威权主义、民主化等主要议题。20世纪70年代以后,民主化进程成为分析焦点,其基本内容包括了拉美政治的动态过程及其演变的方向和条件。
如果将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历史阶段视为拉美政治发展的民主化时期,那么这一时期的政治生活演变则涵盖了政治研究所能够涉及的方方面面的问题,换言之,政治生活各个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民主化进程的影响而发生着变化。就民主化进程本身而言,需要分析的问题主要包括民主化进程的描述与解释,这至少涉及民主化进程的起点、民主过渡的类型、民主化的理论分析和解释模式、民主化进程的影响因素、民主体制的合法性与效率、民主政治面临的难题与困境等方面。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一方面必须借助传统或“经典”理论的帮助,另一方面又要考虑拉美国家的现实处境以及根据具体情况而归纳出来的分析模式,例如传统的民主政治概念和理论在拉美政治环境中的应用及其局限、治理和可治理性分析及其在拉美政治条件下的特点、特别是非正式规则和政治文化的独特影响,等等。
民主化进程的启动和展开,伴随着拉美国家政治结构和政治制度的变化。政治权力分配模式的变迁是民主化时期拉美政坛的突出特点之一,即从法团主义模式演变为一种可称为“新多元主义”的模式,以市场为中心的社会利益和集团整合模式取代了以国家为中心的、有选择的“包容”(inclusion)进程;而这种演变所赖以生成的社会经济状况——发展模式和政策的调整与改革、经济形势的波动、非正规部门的发展等等——则有力地催生了一种所谓的“新民众主义”政治现象,并引发了相关的探讨、评价乃至激烈的政治辩论。与此同时,拉美各国的“国家改革”也提上了政治生活的议程,这是拉丁美洲发展进程中国家地位和作用演变过程的延续。而各国的政党在民主化进程中也呈复苏和活跃之势,进而成为民主政治中的主要角色。上述变化是在拉美社会政治力量演变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即政治权力关系及其嬗变成为这一时期拉美政治生活的基础条件,这又涉及政治结构的两种分析路径,一种是传统的阶级分析,另一种为晚近的政治行为体分析,将拉美社会的传统政治角色(如土地权贵、军队、教会等)、新兴政治角色(如工会、商会、农民组织等)以及其他活跃在体制边缘或体制外的政治角色(如社会运动、非政府组织等)统统纳入了政治结构分析的总体框架。拉美国家政治制度分析则涉及宪法、立法、司法、行政、选举、政党、科层以及国家结构形式等内容,但拉美国家政治制度的核心和象征是其总统制安排,因而总统制的运作在威权时期和民主化进程展开以后的异同及其演变也就成为政治制度分析的主要内容。
20世纪的拉美政坛呈现出一种不同政治势力兴衰和政治体制模式周期性变化的格局,这种状况被形象地称为“钟摆效应”。20世纪末叶至21世纪初叶,不同政治倾向的社会力量及其政党的命运也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政治钟摆现象,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冷战终结和经济改革对右翼政治力量的抬升,以及世纪之交至今社会政治气氛左转和左翼政治力量的崛起。拉美左翼力量在多数国家赢得了选举的胜利,但左翼政府的执政理念和政策选择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因而也引发了有关左翼力量存在不同类型的辩论,同时选举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一种新型治理模式的确立,左翼力量仍面临着提高执政绩效的严峻考验。
与政治民主化几乎同步展开的经济改革进程也是一个充满政治抉择的过程,其间选举周期、社会经济差别、党派意识、利益集团以及民主政治发展等因素都与改革的目标模式和政策选择密切相关,因而经济政治分析也成为拉美政治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上述分析的目的是力图把握30年来拉美政治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基本问题,并为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奠定基础。
需要注意的是,“民主”“民主化”和“可治理性”等概念在这里只是作为分析工具用以解释和说明政治现象,并不必然地为这些现象提供合理性或正当性的证明。这一提示与下列事实相关:拉美政治研究中的概念和理论主要来自西欧和北美。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所使用的概念和理论也基本上自外部引进。这种状况决定了有关研究的现实处境,一方面,通过这些文献习得的概念和理论是研究拉美政治无法回避和绕过的必要途径,并且可以据此接触和认识拉美地区政治生活几乎所有方面的内容;另一方面,对于这些概念和理论与拉美政治现实的契合程度,又必须持谨慎态度,因为拉美的政治现象并非发达世界历史经验的简单和完整的摹本。在处理上述问题时,必须对经典理论和政治现实的关系给予一定的关注(例如可治理性研究涉及的非正式制度和政治文化问题),同时注意资料来源的局限,对于不同地区(如拉美学界)、语种(如西班牙语)、倾向(如左翼观点)研究和视角进行必要的综合,同时一些重要的政治问题(如拉美政治研究文献一般要涉及的宗教、种族、性别、环境、国际关系以及国别研究等)也应该纳入分析框架。对于中国学者而言,上述方面的探讨目前还处于研究的初级阶段,许多问题还有待于未来进一步的研究和合作研究加以解决。
三 拉美政治研究的主要方法
这里的方法是广义的、宽泛的概念,指的是研究目的和议程的确定、材料的选择以及概念和理论工具的运用。一般而言,拉美政治研究既有知识体系建设的学术考虑,但更重要的也往往关乎国际交往和发展借鉴等方面的实际目的,因此它主要是一种实证研究,即认识和理解实际存在的问题。材料的取舍应兼顾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学派和不同的政治倾向。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则必须根据所提出的问题加以确定。
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运用或发展所谓“中层”(mid-range)理论,旨在根据少数几个变项来研究和解释一定范围内的政治现象。与试图说明范围广泛的现象且分类系统包括绝大部分政治现象的“宏大”(grand)理论不同,“中层”理论围绕几个关键概念和变项搭建分析框架、构筑研究议程,并且将分析和研究置于某些成熟理论和具体案例资料的基础之上。在拉美政治研究中,所谓“民主过渡”、“民主巩固”和“民主质量”的分析,就属于这种聚焦于政治生活中某些重要维度或广泛政治进程中某些重要因素的中层理论研究。例如,安德森、皮勒、林茨、史密斯、梅因沃林等学者关于民主过渡和民主巩固的分析⑦,奥唐奈、多明格斯、菲利普、维亚尔达、福沃瑞克等学者关于民主质量以及民主治理的分析⑧,既触及拉美政治演变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又集中处理了与政治理论发展密切相关的一系列概念和分析模式,成为认识拉美国家的政治历史脉络、政治力量状况以及各种政治变项间互动的重要途径。
拉美政治研究领域的上述趋势明显受到美国学术界的影响。随着拉美国家选举民主体制的普遍确立,美国政治学界盛行的理性选择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理论越来越多地用来说明从威权体制向民主政治的转换以及民主体制的效率和合法性问题。理性选择分析假定政治行为体的行为旨在实现效用最大化、行为体偏好固定且有一定排序,同时将个体或单一行为体设定为分析的基本单位。因此,理性选择分析常用来解释那些涉及物质利益和权力、关乎个体或单一行为体且制度、规则、行为体身份明确条件下的政治行为。而新制度主义并不完全将焦点放在个体或单一行为体身上,它更关注制度对政治行为后果的影响。新制度主义分析虽然也以行为体的理性选择为前提,但其分析的焦点却在于制度规则与政治行为后果的关系,例如选举制度与政党体系之间的关系。拉美国家民主化进程启动以来,出现了许多以政治行为体为中心、以理性选择假定为分析工具或者以博弈模型乃至数学模型说明政治现象的研究,例如关于政治人物操纵公共支出谋取政治支持、政客的选举策略和立法行为及其与选民的物质利益交换、文人政客与军队的关系、威权体制退场与中央银行权限扩大、行政改革与党派利益、教会与国家的关系、民主过渡进程中的各派政治力量关系等问题的分析;同时也不乏沿新制度主义思路探讨制度安排与经济、政治后果关系的许多论述,例如关于行政与立法部门及其相互关系、行政部门的宪法或行政法令权力、不同类型的总统制安排及其运作、权力分立与可治理性、固定任期制的影响、选举制度设计等方面的阐释。⑨
然而,拉美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及其在民主过渡中表现出来的高度不确定性与理性选择理论关于制度、规则和行为体的明确性假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紧张关系。即使将分析焦点放在政治行为体身上,现实政治中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困境和选择也无法与理论推定的行为体偏好、约束条件、决策模式以及战略互动等分析完全吻合。与此同时,假如分析涉及社会政治力量间的权力关系及其演变,特别是长时段、大范围的政治进程,影响制度和制度变迁的条件和因素就会成为更为重要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结构主义、文化分析以及纳入更多变项的综合分析框架就可能成为更为合适的分析途径。例如,奥唐奈等人关于民主过渡进程不确定性的论述、林茨等人关于影响民主过渡和巩固各项因素(结构、制度、过程、行为体、机缘等)的综合分析、梅因沃林等人关于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全景式考察等⑩。由此可以看出,拉美政治研究仍无法摆脱“社会学传统”的影响,或者更准确地说,社会经济和结构分析在“纯”政治分析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仍保持着固有的旺盛生命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许多政治现象及其理论分析似乎在复兴过去历史时期的行为模式和理念,例如涉及拉美地区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依附与发展问题,涉及政治权力、社会整合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民众主义和新民众主义问题,以及超越50~60年代现代化理论而纳入更多因素的新现代化思路(除社会经济发展外还考察政治文化、种族关系、政治制度、政党体系、殖民遗产、国际关系等)(11)。
新旧世纪之交,拉美社会政治倾向和氛围明显向左偏移,左翼政党在许多国家上台执政。这一方面突显了左翼力量日益适应并能够通过选举政治影响政坛,掌握和运用国家和地方各级行政和立法机构推行自己的理念和政策;另一方面也将政治研究中的所谓主流(mainstream)立场与替代性(alternative)观点之间的张力以及替代性观点自身的矛盾更加明显地呈现于世。(12)历史上,基于“进步”(progressive)政治理论的替代性观点一般更表现出“宏大”理论而非“中层”理论的特征,即其分析框架以关于“政治”(the political)本身而非政治进程某一侧面的界定和认识作为前提,其中最主要的当属社会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些理论分析中,国家作为自律的实体或上层建筑是政治和政治权力的中心地带,政党、国家机构、社会运动、革命先锋队是社会改造中的关键角色,而社会改造则有赖于组建以特定纲领和意识形态指导行动的议会党派或革命政党。随着拉美大众政治及其形式的日益多样和迅猛演变,许多更为激进的新兴社会运动越来越以摒弃政党、国家、政治代表性和领导权力为主要特征,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和墨西哥的萨帕塔武装力量只是众多新式社会运动中影响较大的两个代表。这些运动在公共生活、民主参与、经济和文化发展等方面都不仅对现行秩序和体制构成了挑战,而且比传统的社会民主和马克思主义走得更远,政治、权力、社会和自我都在重新界定的过程之中,价值、文化和治理实践也都处于不断生成和更新的状态。针对这种“政治”的理论探讨被称为“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和“开放的马克思主义”(open Marxism),成为激进政治及其理论行列中更极端的一翼。
事实上,对于中国学者而言,虽然在研究议程和研究方法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但总体而言,拉美政治研究基本上还处于学习的阶段。因此,在有关研究中,既有必要避免“虚无主义”的态度,即对于一系列历史或理论定论(包括中国学者自己的学术积累)的全面否定或排斥;又要防止所谓的“中国式傲慢”,即对国外学者的新颖概念和观点充耳不闻、视而不见。(13)只有这样,中国学者的研究以及相关争论才能具有历史和理论的深度。
收稿日期:2009-07-06
注释:
①本文系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重点课题《当代拉丁美洲政治研究》一书序言部分改写而成。
②关达等编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丁美洲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中国学者的其他著述还包括徐世澄著:《拉丁美洲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徐世澄和袁东振著:《拉丁美洲国家政治制度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肖楠等编写: 《当代拉丁美洲政治思潮》,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等等。
③David W. Dent,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on Latin America:Trends From the 1960s to the 1990s,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90.
④参阅Karen Remmer,"Theoretical Decay and Theoretical Development:The Resurgence of Institutional Analysis",in World Politics,No.50,October 1997,pp.34-61; Gerardo Munck (ed.),Regimes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Theories and Method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1-37.
⑤中国学者的有关归纳见梅柯《拉美政治前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7月4日,2007年5月15日,2008年4月15日。
⑥多数民主化问题专题研究将范围明确限定在除加勒比地区以外的拉丁美洲20个国家(包括古巴)或19个国家(不包括古巴)。
⑦Lisa Anderson,Transitions to Democrac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 John Peeler,Building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Boulder,Lynne Rienner,1998; Juan Linz and Alfred Stepan,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Southern Europe,South America,and Post-communist Europe,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 Peter Smith,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Political Chang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Frances Hagopian and Scott Mainwaring,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in Latin America:Advances and Setback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⑧Guillermo O' Donnell,Jorge Vargas Cullell and Osvaldo M.Iazzetta (eds.),The Quality of Democracy:Theory and Applications,Notre Dame,Indiana,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2004; Jorge I.Domínguez and Michael Shifter (eds.),Constructing Democratic Governance,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3; George Philip,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Cambridge,Polity Press,2003; Howard J.Wiarda and Margaret MacLeish Mott (eds.),Politics and Social Change in Latin America:Still a Distinct Tradition? Westport,Connecticut and London,Praeger,2003; Joe Foweraker,Todd Landman and Neil Harvey,Governing Latin America,Cambridge,Polity Press,2003.
⑨参阅Evelyne Huber and Michelle Dion, "Revolution or Contribution? Rational Choice Approaches in the Study of Latin American Politics",in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44,No.3,Fall 2002,pp.1-28.
⑩Guillermo O' Donnell and Philippe Schmitter,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6; Juan Linz and Alfred Stepan,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Southern Europe,South America,and Post-communist Europe,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 Frances Hagopian and Scott Mainwaring,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in Latin America:Advances and Setback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11)中国学者的有关分析见曾昭耀:《政治体制的变革与发展》,载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28~408页。在该项研究中,拉美国家的政治发展被置于独立以来三次现代化浪潮的框架中进行分析,其核心问题是政治上的治与乱。
(12)参阅Benjamin Arditi,"Arguments About the Left Turns in Latin America:A Post-Liberal Politics?",in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Vol.43,No.3,2008,pp.59-81; Sara C.Motta,"Old Tools and New Movements in Latin America:Political Science as Gatekeeper or Intellectual Illuminator?",in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Vol.51,No.1,2009,pp.31-56.
(13)参阅达巍:《中国人看世界,别走极端》,载《环球时报》2009年8月18日;张胜军:《“中国式傲慢”害了中国学者》,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8年12月25日。
标签:政治论文; 拉美国家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美国政党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