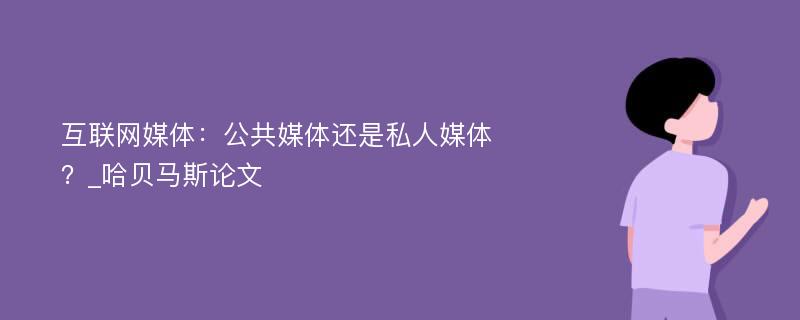
网络传媒:公共还是私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私人论文,网络传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网络传媒的发展,早期具有乌托邦色彩的匿名交往逐渐失去了吸引力,人们越来越感到,在网络匿名环境中,人们来去匆匆,一别永年,不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安慰。于是,在匿名交往的新鲜感过后,实名交往越来越成为网络应用的主流,很多人都主动选择脱去匿名性的伪装和保护,将自己的真实身份暴露于网络空间,并主要与那些和自己有现实联系的人进行交往。与匿名交往相比,实名交往的最大不同在于,它能将人们在现实世界中业已建立起来的各种社会联系带入网络空间,并将人们的线上活动和线下活动协调起来。这也就意味着,网络空间越来越不再是一块远离现实世界的飞地,而成了现实世界的延伸和补充,很多虚拟社区早已不那么“虚拟”——它们主要是由熟人组成的,其主要功能就在于满足人们分享个人经历、倾诉内心情感的需要。可见,网络空间也并不纯粹是公共性的,对于它的私人性质,我们也不能视而不见。
在研究网络传媒时,公共领域理论是人们经常援引的理论资源,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对于网络传媒来说,公共领域理论对“公共”和“私人”的划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效,当事人就是因为对这一问题认识不清,才在无意中惹下祸端。这就引出了一个亟待厘清的问题:日渐活跃的网络空间究竟是公共性的,还是私人性的?对于这一问题,如果不存在一个非此即彼的回答,那么,它又给公共领域理论带来了哪些冲击和挑战?
经典公共领域理论对“公共”和“私人”的严格界分一直饱受诟病。可以说,在西方两千多年的知识传统中,这种界分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正如理查德·桑内特所说,这种观念形象地体现在雅典的城邦规划中:“古代雅典人把他们从事政治活动的地点普纳克斯山与城邦的中心集市分离开来,这种分离体现了社会学思想中的一个经典假设,即经济活动会破坏人们从事政治活动的能力。其中的逻辑非常简单,用柏拉图的话说就是,经济运作靠的是需求和贪婪,而政治运作靠的是公平和正义。”①
不管是阿伦特还是哈贝马斯,都深受这一知识传统的影响,他们的公共领域理论都建基于对“公共”和“私人”的清晰界分之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区分构成了阿伦特整个政治哲学思想体系的一块基石。在她看来,在人类事务中,有一类是必须公开显现的,而另一类则必须隐藏起来,在理想的状况下,它们之间的界限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是完全重合的。她提出:“许多东西无法经受公共舞台上由他人持续在场而带来的无情而耀眼的光芒,因而,只有那些与公共领域相关、值得被看到或听见的东西才能进入公共领域,从而与它无关的东西就自动成了私人事务。”②有一种常见的误解认为,阿伦特贬低私人领域而抬高公共领域,其实不然,她坚持认为,私人领域中的活动不仅为人进入公共领域准备了条件,而且一些对于人类来说弥足珍贵的东西也只有在私人领域中才能得到完好保存,如爱和善,它们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就不仅会造成自身的变质,而且还会对公共领域形成破坏。阿伦特之所以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进行严格界分,并不是为了做出孰高孰低的价值判断,而是为了强调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界限,不管是私人事务向公共领域的入侵,还是公共事务向私人领域的撤退,都是十分危险的。终其一生,阿伦特的这一观念都未曾动摇。正是在这一观念的烛照下,她在《论革命》中清理了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出现不同走向和结局的内在逻辑。她提出,革命是一个典型的发生在公共领域中的政治事件,而在法国大革命中,贫困、同情、暴力、必然性观念等这些本来属于私人领域的东西却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正是这种“公私不分”,最终导致它由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走向了腥风血雨的恐怖统治。相反,美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除了得天独厚的社会条件,还在于它的开国者有着明确的“公私分明”意识。
由于哈贝马斯以现代民族国家而非古希腊城邦为分析模型,所以他对公共领域的理解与阿伦特稍有不同,但是,在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界限的强调上,他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那里,公共领域是处于国家和社会之间、公共权力和私人利益之间的一个独立交往空间,它既要严防国家权力的干涉和控制,又要警惕私人利益的侵入和腐蚀。他批判大众传媒的根本原因也在于,在私人利益和国家权力的双向夹击下,大众传媒已经失去了自己的自主性。一方面,大众传媒为私人利益的侵入敞开了大门;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机器越来越为各种私人利益集团所控制,大众传媒在国家权力面前的独立地位也变得岌岌可危了。由此可见,哈贝马斯实际上是想要在国家权力和私人利益之间为公共领域圈出一片纯净的天地:向上它要同国家权力保持距离,向下它要与私人利益划清界限。
很多学者都曾指出,对“公共”和“私人”的这种严格区分是不切实际的,一个人从私人领域跨入公共领域后,不可能完全把各种私人关切抛诸脑后,摇身一变而成为另外一个人。也就是说,从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的完美一跃,或许只是存在于理论家头脑中的一个高蹈姿态。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网络传媒出现以前,这种区分仍然是有合理性和解释力的,它不仅将公共讨论与日常闲聊和讨价还价区别开来,而且还提示人们不同的场所有不同的性质,要求人遵循不同的行事规则。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这种区分确定了大众传媒的基本定位,即社会“公器”——不管实际效果如何,严肃的大众传媒总是倾向于关注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话题,并试图超越狭隘的个人偏见,发出一种不偏不倚的声音。
可是,对于网络传媒来说,这种“公共”和“私人”的区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意义。首先,我们已经很难区分什么是“公众”、什么是“私人”。经典公共领域假定,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在鸿沟的一边,人们以私人身份进行各种社会交往;一旦跨越这条鸿沟,私人就变身为公众,并就各种“普遍问题”进行公共讨论。要跨越这一鸿沟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在阿伦特那里,只有那些摆脱了生存必然性束缚的男性公民才有条件进入公共领域;而对于哈贝马斯来说,公共领域是专为资产阶级白人男性准备的。很多人认为,这反映了哈贝马斯根深蒂固的阶级偏见和种族偏见,其实不然,他之所以把普通大众排除在外,是因为在他看来,只有那些通过阅读报纸、定期出版物等传播媒介而掌握了信息的人,才有能力参与公共领域中的讨论,而在当时社会中,普通大众并不具备这些获取信息的手段。这种排除不仅保证了公共讨论的质量,而且还有助于人们形成公私分明的意识。然而,在网络空间中,这种排除已经不再可能了,因为网络交往的参与主体已经大大扩容,甚至变得无所不包了。这一方面意味着话语权的平等化,即更多的人获得了发声的机会,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公众”和“私人”之间的界限已经消弭,当一个人在网络上发言时,我们已经很难断定他的身份到底是“公众”还是“私人”。
其次,我们已经很难区分哪些是公共空间、哪些是私人空间。在经典公共领域理论的视野中,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都是有显著标识的,比如,城邦大会、咖啡馆和沙龙与家庭之间的区别就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标识提醒人们,在不同场所人们的身份是不同的,需要遵循不同的行事规则。而在网络虚拟空间中,却不存在这样的标识。如前所述,网络空间里存在各种各样的虚拟社区,其中一些具有很强的公共性,而另一些则完全是由熟人组成的。人们在不同的虚拟社区间往来穿梭时,很难意识到公共和私人之间的边界究竟在哪里。而且,很多虚拟社区其实都兼具公共和私人的双重性质,比如微博,它既是人们沟通信息、交流感情的工具,同时又是一个公共讨论的平台,我们很难简单地说它是一个公共空间还是一个私人空间。
最后,我们也已很难区分哪些是“普遍问题”,哪些是“个人事务”。经典公共领域理论认为,公共领域是有排他性的,只有那些“值得被看见的东西”(阿伦特语)或“普遍问题”(哈贝马斯语)才能进入公共领域,而个人事务则必须被排除在外。然而,在网络空间中,我们已经很难分清哪些是普遍问题,哪些是个人事务。正如雷米·里埃菲尔所说:“所有的公共问题(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社会问题)既不是偶然出现的,也不是由事先组合好的公众承担的,它们只有当某些人深陷困境、并将此确认为真正的麻烦时才出现,他们逐渐行动起来将其变成普遍的利益问题,以呼唤公共权力来解决这些问题。”③在网络传媒时代,这种从个别事件中生发出普遍问题的模式更是屡见不鲜,比如,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就引发了人们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广泛关注,并最终致使施行了20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2011年,郭美美的几条微博就引发了中国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并给中国慈善事业带来致命打击。可以看到,很多网络事件一开始都是以“个人事务”的面目出现的,但到后来就慢慢演变成了一个“普遍问题”。
总之,在网络传媒的冲击下,经典公共领域理论的基石已经松动,我们既不能完全把网络空间视为私人性的,也不能完全把它看成公共性的。对此,目前人们还认识不清。比如,吴虹飞在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时说,自己的微博并不具有公共性,而只是表达私人情绪的地方,“我虽然有十几万粉丝但基本都是‘僵尸粉’,真正关注我微博的人就那几个。而我大部分的微博,还是在谈论音乐和生活,谈得也很私人化”④。在她看来,一个人的微博是否具有公共性,粉丝数量是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指标,但问题在于,粉丝数量到底超过了多少,我们就可以认定它具有了公共性?显然,这一问题并没有答案。再比如,2013年9月9日,中国“两高”出台司法解释规定,“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诽谤行为“情节严重”。其实,这背后的逻辑与吴虹飞的辩解是非常一致的,即一条微博是否具有公共性,完全是由它的影响范围决定的。这其中存在的问题依然是,这个标准为什么是500次,而不是501次或499次?可见,在考察网络传媒时,经典公共领域理论已经显得笨拙和错位,如果依然持守它对“公共”和“私人”所做的严格区分,就会漏洞百出,因此,我们需要寻找新的理论模型和阐释工具。
其实,西方很多学者都已经意识到,在面对网络传媒时,公共领域理论的适用性已经大打折扣,我们与其继续紧抱着这一概念不放,不如改弦易张,要么寻找一种替代性的阐释框架,要么对它进行必要的重构,以适应新的媒体条件。
比如,马克·波斯特分析说:“在哈贝马斯那里,公共领域是指处于平等关系的主体走进一个共享的空间,通过批判性争论和有效性宣称寻求共识的达成。我认为这种模型在电子政治时代已经被全面推翻了,因而,在考察作为政治空间的互联网时,我们应该放弃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⑤在他看来,公共领域是指咖啡馆、沙龙之类的供人们进行面对面交往的空间,在此空间中,人们不仅借助于语言,而且还通过表情、语气等媒介将自我全面呈现于他人。而网络传媒却并非这样一个空间,它虽然也能将人联系起来,但这种联系始终无法摆脱处理信息的机器这一中介的影响,在网络交往中,我们直接面对的是机器而不是人。在这种条件下,一个人的身份不再是借助于他人的镜像作用而形成的,而是完全由自己手中的键盘来控制,这种可以不断涂改自我身份的主体与公共领域理论所假定的理性主体是大相径庭的。因此,我们与其继续纠缠于网络传媒是否建构了一种公共领域,或网络空间是公共性的还是私人性的这类无解的问题,不如转而考察它对主体性建构所产生的影响。
还有人提出了其他的解决方案,比如,约翰·汤普森就不主张废弃公共领域这一概念,而主张对它进行重构。在他看来,经典公共领域理论是与面对面交往相联系的,这可以被看做一种“共在情景中的可见性”。随着大众传媒的兴起,这种“共在情景中的可见性”已经越来越少,因为人们已经很少就公共事务展开面对面的交往,也很少有机会直接见证公共事件的发生。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社会中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减少了,也不意味着公共领域已经衰亡了,我们应该看到,在面对面交往减少的同时,“媒介化准互动”正大量出现,这就意味着,大众传媒为公共事件带来了一种新的可见性,“我们必须把公共领域的古典模式放至一边,将其看做众多模式中的一种,并用一种崭新的眼光考察印刷媒介和其他媒介的兴起如何改变、重构了公共领域”⑥。
在我们看来,马克·波斯特主张废弃公共领域概念的观点,未免显得过于粗暴,因为显而易见的是,网络传媒的确为公共讨论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这也是它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潜能之一。研究网络传媒对主体性建构的影响固然重要,但这与研究它成长为公共领域的潜能并不矛盾。同样,约翰·汤普森用“可见性”取代“公共性”的方案也问题重重,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可见性”并不能涵盖“公共性”的全部内涵。不管是在阿伦特那里还是在哈贝马斯那里,公共领域都不仅仅是一个显现空间,而且还是一个讨论“值得被看见的东西”或“普遍问题”的空间。因此,可见性的提高并不一定意味着公共性的增强,“可见性”这一概念能够用来描述人们经历公共事件的方式的变化,但完全丧失了批判的潜能。
相比之下,我们更认同彼得·达尔格伦的主张。在他看来,公共领域理论是建立在传统的政治观念之上的,这种政治观念假定了一系列清晰的二元对立,如理性—感性、知识—愉悦、信息—娱乐等。在网络空间中,这些清晰的二元对立已经不复存在,因此,公共领域概念的适用性已经大打折扣,现在它只能说明部分问题了,我们需要用“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这一概念对它进行补充。
在面对网络传媒时,公共领域理论的一个主要缺陷是,它所依赖的协商民主观念大大限制了它的适用性。首先,协商民主观念在“真正的协商”与其他形式的交谈之间做出了过于严格的区分,忽视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非正式交谈对于民主政治的作用。达尔格伦指出,公共领域中的政治协商要求人们具备一定的对话能力,而这种能力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日常交往中得到培养和锻炼的,也就是说,日常生活中的交谈为人们进入公共领域进行理性协商提供了一个操练场。就此而言,“散漫的闲谈同样可以产生政治影响,在个人对话与政治对话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关联。对于民主政治的活力来说,轻松的、漫无目的的日常对话及其创造性同样不可或缺”⑦。由于协商民主观念切断了政治协商与日常交谈之间的关联,将公共领域与日常生活领域截然割裂开来,所以在考察网络交往时,它的弊端就显而易见了。如果按照理性协商的标准来衡量,大部分的网络对话都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公共交往,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公共交往形式,并对民主政治的运作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其次,协商民主观念还有一种理性主义偏向,忽视了其他一些同样有意义的政治交往方式。“协商”要求每个参与者都超越自己的特殊利益,自觉服从那些最好的观点。为了使人们能在相互竞争的观点中做出理性选择,它甚至要求人们尽量使用透明化的语言,而避免使用任何可能会对人的理性判断形成干扰的修辞技巧。达尔格伦认为,一方面,这一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在阐释抽象观念时,一定的修辞技巧是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这种要求也是不必要的,说理和修辞并不矛盾,恰当地运用一些修辞技巧还会使说理变得更加清晰和有力。因而,“协商民主的理性主义偏向忽视了许多对于民主来说至关重要的交往模式,比如,情感性的、诗性的、幽默的、反讽的,等等”⑧。对于网络交往来说,那种完全理性化的协商已经颇为少见,大量的论争都显得轻松随意,充满着嬉笑怒骂,它们不仅大量使用各种修辞技巧,而且还常常跨越娱乐和政治之间的边界,呈现出一种混杂性。显然,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否定网络交往的意义和价值,与严肃的理性协商相比,这种交往方式不仅同样能够促进政治知识的传播,而且很多时候还能更好地激发人们的参与兴趣。
最后,协商民主观念还假定参与者之间存在一种平等关系,而这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美好愿望。协商民主观念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参与者之间是完全平等的,他们都拥有自己的观点,并单纯依靠说服的力量赢得别人的赞同。事实上,这种平等关系只是一种假设,在协商过程中是不可能存在的,这是因为,人们的公共言说能力与他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是紧密相连的,而这些资本在不同人群中的分配是不平等的。从这一角度看,协商民主观念具有一种宗教性的博爱论色彩,它单纯地信仰平等的价值,坚持认为在政治讨论中每个参与者的意见都同等重要,却没有意识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在很多问题上都既没有时间和精力,也没有相关的知识去发展出自己的原创性意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各种社会精英的影响和引导。
因此,“在分析和理解互联网上的政治讨论时,尤其是当我们聚焦于那些新型的、议会以外的政治时,协商民主概念尽管还是有用的,但它已经只能部分地说明问题了。协商民主视角的理性偏向需要用我所说的公民文化来补充”。⑨虽然大部分网络交往都不符合协商民主的标准,也未能形成一个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但毫无疑问的是,它们组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交往空间,在此空间中,不同的观点彼此相遇和交锋,并由此形成了一种公民文化。如果说公共领域概念指向一个与民主相关的正式交往空间,那么公民文化则描述了人们参与公共领域的社会文化条件,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发达的公民文化,就不可能有广泛的政治参与。“尽管在参与社会交往与处理真正的政治问题和冲突之间仍然存在着鸿沟,但是,公民社会却可以被看做一个操练场,为公民的政治参与准备了条件⑩。正是在各种非正式的社会交往中,公民的政治参与技能得到了培养和锻炼,因此,我们与其继续纠缠于网络传媒是否建构了一个公共领域,不如考察它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公民文化的形成。
基于这种理解,我们就不宜再用公共领域的标准来要求网络空间了。因为一方面,网络空间是开放的,每个人都不得不考虑自己的言行可能会产生的公共后果,就此而言,它不是私人性的;但另一方面,网络空间又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要求人们时刻保持理性、完全超越个人偏见又显得过于严苛和不现实,就此来说,它又不纯粹是公共性的。那么,我们应该用什么标准来要求和规范人们在网络空间里的言行呢?在我看来,公民文化应该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标准。恐怕所有人都不会否认,不管是在网络空间还是在现实世界,人们都不能突破公民道德的底线,都应该遵纪守法,不伤害他人,而这正是我们所理解的公民文化标准。
①Richard Sennett.The Culture of the New Capitalism,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pp.136—137.
②Hannah Arendt.The Human Conditi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8.p.51.
③[法]雷米·里埃菲尔:《传媒是什么:新实践·新特质·新影响》,刘昶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5页。
④应琛:《摇滚阿飞那十天》,《新民周刊》第752期,2013年8月7日。
⑤Mark Poster:What's the Matter with the Internet,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1.p.182.
⑥John B.Thompson:"Shifting Boundaries of Public and Private Life",Theory,Culture & Society,2011,Vol.28(4).
⑦Peter Dahlgren."Doing Citizenship:The Cultural Origins of Civic in the Public Sphere",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2006,Vol.9(3).
⑧Peter Dahlgren."The Internet,Public Sphere,an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Dispersion and Deliberation.Political Communication,2005,22.
⑨Peter Dahlgren."The Internet,Public Sphere,an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Dispersion and Deliberation.Political Communication,2005,22.
⑩Peter Dahlgren."Doing Citizenship:The Cultural Origins of Civic in the Public Sphere",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2006,Vol.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