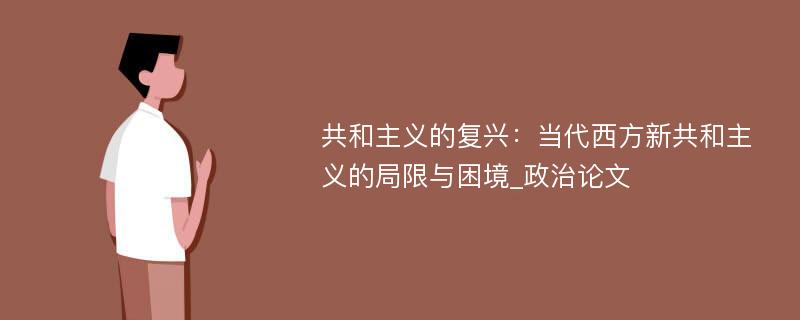
共和主义的复兴——当代西方新共和主义的局限与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和论文,主义论文,困境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D092
自20世纪50、60年代以来,“共和主义的复兴”逐渐成为西方学术界的一道独特景观。到了 90年代,这场学术运动非但没有像当初有些学者所预料的那样转瞬即逝,反而由政治思想史领域波及到法理学、政治哲学、公共政策等领域,其强劲的发展势头令人侧目。①
共和主义的当代复兴不但重新描绘了西方政治思想的图景,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西方政治遗产的认识;而且,新共和主义在自由、民主、公共善、公民美德、公民身份等议题上与自由主义的对话与互动推动了西方政治哲学的进一步繁荣。
但是,当代西方的新共和主义也面临着诸多的困境。美国学者保罗·韦茨曼(Paul Weithman)曾经指出,任何一种新共和主义理论如果想保留自由主义相对于古典共和主义的优越之处,同时又避免它打算取而代之的各种自由主义理论的缺陷,那么它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它必须是智识上令人满意的,即它必须对公民身份、自由和公共善这些概念提供智识上令人满意的解释;第二,它必须在政治上是充分的、在实践上是可行的,即它必须能够充当一种适用于多元民主社会的自足的公共哲学;第三,如果这种理论被称做“新共和主义的”,那么它必须在历史上是有依据的。②
按照这三个标准(历史依据的可靠性、理论上的融贯性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可欲性和可行性)来考察当代各种版本的新共和主义,我们会发现它们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问题。本文旨在通过审视新共和主义所面临的这些困境和难题,检讨其成败得失,从而探求新共和主义的出路。
一、历史想象中的古典共和主义
众所周知,当代共和主义的复兴发轫于政治思想史领域共和主义谱系的重新描绘,正是对古典共和主义这一几近湮灭的古老传统的新近挖掘激发了一些理论家的政治想象,从而引发并推动了共和主义的复兴。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新共和主义受到了最初的回应和反击。批评者们首先提出的问题是,西方历史上存在一个共和主义传统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传统?
针对新共和主义者描绘的政治与思想谱系,很多学者提出疑问:从希腊城邦、罗马共和国,到意大利的城市共和国、英格兰的混合政府,再到美利坚的复合与扩展的共和国、法兰西的雅各宾道德专政,这其中可能存在一以贯之的政治思想传统吗?在城邦理论家亚里士多德、罗马共和的辩护者西塞罗、佛罗伦萨外交家马基雅维利、英国革命的支持者哈林顿、日内瓦公民卢梭、美国宪法的设计者麦迪逊之间,他们的思想有多大的相似性和继承性呢?③
接下来的问题则是,就算存在一个共同的、单一的共和主义传统,那么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传统?尤其考虑到新共和主义者试图在当代以“共和”来重申民主的理想,就必然要面对如下的历史困境:古典“共和”的主要含义之一是混合政体,④ 而混合政体预设了对民众参与理想的修正,“共和国”的典范不是雅典而是罗马、斯巴达;古代共和国的实践及其公民身份的狭隘性与封闭性曾给古典共和主义带来精英主义、寡头政治的恶名;⑤ 古典共和主义中的两大分支,即混合政体论与公民德行论,要么(如前者)已经被自由主义所吸收,要么(如后者)并不比自由主义更具包容性、民主性——因为它以公民履践德行的能力为基础,而自由主义以所有人的人格平等为基础。所以,麦考米克指出:“与其说古代和现代政治理论与实践中的共和主义为普通平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便利,不如说它保障了精英的特权地位”,当代新共和主义者试图以共和主义来补充当代的民主,“只能使当代的自由主义民主变得越来越糟糕。”⑥
作为一种前现代的政治意识形态,古典共和主义存在着诸多缺陷,这些缺陷既来自于其理论,也来自于古代共和国的政治实践;既涉及共和主义理想的可欲性,也涉及其可行性。⑦ 当代新共和主义者要复兴这一传统,就不能不正视这些缺陷。
其次,在具体阐释问题上,针对共和学派对马基雅维利、哈林顿、杰斐逊、斯密、托克维尔等思想家的共和主义解读,批评者们从不同立场和角度提出了质疑。⑧ 我们以曾在古典共和主义传统的复现中起到先锋作用的、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对美国革命和立国的共和主义阐释为例。以弱化甚至消除洛克对美国革命的影响为宗旨的共和主义修正运动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其他各家各派的强劲反击。左翼的科兰尼克(Isaac Kramnick),右翼的狄金斯(John Diggins),施特劳斯学派的潘格尔(Thomas Pangle)和朱克特(Michael Zuckert),自由派的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一起加入了反对共和修正派的阵营,并且这场争论成为20世纪后半期美国史学界的一大热点。面对这些回应与批评,20世纪80年代以后,共和修正派不得不对自己作出“修正”,这场争论才算尘埃落定。如今,再也不会有人固守自由主义的“洛克神话”了,但恐怕同样也不会有人相信公民人文主义的“马基雅维利神话”。更普遍的观点是,18世纪晚期的美国政治思想采用了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政治话语(从清教思想、自然权利学说、普通法传统到苏格兰启蒙运动),古典共和主义只是其中之一。⑨
另外一个更具普遍性也更具争议性的问题,是历史上古典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问题。很多学者都对将古典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刻意对立起来的做法表示怀疑,认为这是一种虚幻的对立;尽管“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之间的对立激发了共和主义最近的复兴,但这种对立更多的是这一复兴的臆造,而不是可以弄清的历史事实”。⑩
一位批评者尖锐地指出:共和主义的复兴以过度的热情为特征,“人们会怀疑它的目标是说明在世界历史上不存在自由主义者,或者约翰·洛克是惟一的自由主义者”(11);而另一位批评者则指出,新共和主义者利用自由主义的幌子来指称那些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理论上看都截然不同的信仰体系,“自由主义这一术语变得如此含混,以至于它包括了整个西方传统——黑格尔和马克思也许是例外”。(12) 这样的共和主义谱系与自由主义谱系显然是无法让人信服的,以此为基础的对立自然也是站不住脚的。
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思想史上也许并不存在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二元对立,相反,它们存在着明显的继承关系。(13) 以共和主义/自由主义的对峙来重绘近代政治思想与其所打算纠正的“辉格式历史观”并无二致。倡导“历史语境主义”的剑桥学派摇身一变成为“借思想史来解决当代政治争论”的共和学派,个中缘由颇值得玩味。(14)
最后,共和学派与新共和主义者还要面临这样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那就是思想史的重新阐述与解决当代政治困境之间在何种意义上是相关的?
虽然大多数共和学派的思想史学家强调,他们无意将历史研究作为规范理论批判(更不用说政治批判)的手段;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政治思想史领域共和主义范式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为规范理论中的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述提供了历史依据,而且其政治意图一览无余。比如,桑德尔就曾宣称:“如果‘共和学派’在我们意识形态的起源上是正确的,那么或许有望复兴我们的公共生活,并重新激发一种共同体的归属感。因此,关于我们过去之意义的争论会对我们关于当前政治可能性的争论产生后果。”(15)
对此,赫佐格(Don Herzog)作出了评论。他指出,桑德尔的主张听起来至少是一个不合逻辑的推论,即他的“如果”从句与他的“那么”从句之间可能是什么关系?“即使美国始终是由哈茨所鼓吹的毫无疑义的洛克式国家,为什么就不会‘有望复兴我们的公共生活’?……我们可以不断地变换这个问题:‘为什么就不能第一次有望复兴我们的公共生活?那些同情共和主义的人既然通晓神奇铸造术的秘诀,何不直接将我们腐化的政体带回到它所如此不幸背离的基本原则?为什么我们就不能首创一个共和主义的政体呢?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赢得马基雅维利慷慨给予立法者的赞美呢’?”(16)
更致命的是,如果新共和主义者将当代政治困境的解决与古典共和主义的重述绑定在一起,那么一旦古典共和主义被证明并不是一种民主的、参与的政治思想传统时(就像麦考米克所指出的那样),上述回应和批判对新共和主义的政治谋划来说就可能是釜底抽薪式的。
所以,像佩迪特这样的规范理论学者一开始即声明,他所说的“无支配自由观”虽然是以共和主义传统为出发点的,但他所阐释的共和主义“与思想史上许多富有争议的主题并没有本质上的联系”。(17) 但是,既然他以共和主义之名为其无支配自由观张本,并在诸多问题上向古典共和主义思想家的论述寻求灵感,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说,历史解释问题仍然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
当然,新共和主义者可能会接受上述批评并承认:在逻辑上,共和主义的复兴并不以思想史中古典共和主义的描绘为前提;规范政治理论中新共和主义的重构并不会因为历史阐述问题而被取消。更何况,按照希尔斯在《论传统》中的说法,“要成为传统,并不意味着,那些感受到传统并接受传统的人是因为传统在过去真的存在过才接受它的”。(18) 历史的“迷思”往往会强化而不是损害某些观念的建构。对此,新共和主义者坦承:“当代共和主义的任务不是追根溯源:它与其说是被发现的,不如说是被制造的。”(19)
二、反自由主义与暧昧的政治方案
评论者们普遍注意到,新共和主义者对当代西方社会政治问题的所有诊断最后都指向了自由主义。然而,他们几乎又都重蹈了霍尔姆斯在《反自由主义剖析》中所揭示的“反自由主义者”的覆辙,即没有严格区分两类批评对象:自由主义理论与自由主义社会;忽视了根据自由主义的理想对自由主义社会进行批判性评价的可能。结果就导致,“他们审视自由主义理论不是为了找出其智识上的弱点;或揭示其陈旧,而是为了发现当代危机的根源。他们没有把自由主义视为有时不适应当前的问题,而是将它看做当前问题的惟一来源”。(20)
因此,我们首先应该追问的是:当代西方国家所面临的那些社会政治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是自由主义的理论造成的?这些问题到底是自由主义之病还是现代社会之病?如果是前者,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也许会有所纠正;如果是后者,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岂不是在打稻草人?
自17世纪以来,自由主义逐渐在西方政治意识形态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它之所以能够经历各种严重挑战而立于不败之地,表现出持久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与现代社会保持着某种“同构性”,尤其是它适应了西方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和多元主义这两个基本特征。毋庸讳言,随着现代社会的复杂演进,自由主义在政治参与、经济平等、价值建构等方面始终没有实现它们与维护个人权益的平衡。对于利益集团—官僚主导政治生活、资本宰制政治、社会价值观念混乱、消费至上主义盛行等问题,自由主义至今尚未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但也应该承认,这些现代性的难题不能归咎于自由主义理论本身,而自由主义应对这些问题的资源也远没有耗尽。自由主义所面对的难题也是所有现代/后现代政治意识形态都要面对的难题。(21)
接下来的问题则是,“就算自由主义是病,共和主义也未必是药”。从长远来看,作为一种前现代的政治意识形态,古典共和主义具有贵族政治、精英主义甚至种族主义、军国主义的成分,而且往往只适用于小规模的同质共同体;而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除非接受个人主义、普遍主义、平等主义和多元主义这些与自由主义相一致的理论预设,否则新共和主义是难以发挥作用的。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又如何对自己作出独特的界定而区别于自由主义呢?
不可否认,新共和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阿伦特、波考克、斯金纳、泰勒、桑德尔、佩迪特这些新共和主义者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诉求重点和理论进路,甚至不乏重大分歧:在自由观上,有积极自由和无支配自由的不同进路;在民主观上,有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两种可能的范式;在政治参与和公民美德问题上,有本质论、工具论等多种区分;在共同善或者公共利益的问题上,更是含糊其辞,莫衷一是。(22) 但是,不管这些观念和主张有何分歧,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它们要么是不可欲的,要么与自由主义并无实质性差异。(23)
比如,在自由问题上,与亚里士多德主义勾连在一起的积极自由无疑是新共和主义的一个稳固的立足点,但绝大多数当代政治理论家都承认,在现代多元主义社会中复兴亚里士多德主义是极其困难的。(24) 于是,斯金纳、佩迪特等新共和主义者便致力于阐述这样一种自由观:它既要超越消极自由,又不包含任何富有争议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关于人类真实目的或最高本性的假设;既要和政治参与这样的行动联系在一起,又不能主张人类只有在参与中才能获得最充分的发展。然而,人们普遍质疑:这样一种自由观在何种意义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不同于自由主义自由观?尤其是在佩迪特那里,无支配的自由理想也许比无干涉的自由理想更有吸引力;但问题在于,自由主义者从来没有仅仅满足于无干涉的理想,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会否定无支配的理想。(25)
让我们回到新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这个关键性问题上来。笔者曾经提出,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存在分歧并不意味着新共和主义就是“反自由主义的”,毋宁说它是“后自由主义的”。(26) 首先,同共和主义内部存在不同的流派一样,区分出当代政治理论中的三种自由主义是十分必要的:以罗尔斯、德沃金等人为代表的程序/中立自由主义(procedural/neutralist liberalism)、以哈耶克、诺奇克等人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以及利益集团多元主义(interestgroup pluralism)。不同的新共和主义者所指称、批判的“自由主义”事实上并不一致。
其次,我们不难发现,当代新共和主义者对个人主义、多元主义、普遍主义、平等主义等自由主义预设程度不等、方式不一地予以接受,在各项议题上也没有彻底抛弃自由主义,尤其是在政治建制方面,更没有超越自由主义民主的框架。
最后,有些新共和主义者自己也承认,共和主义不是对自由主义的替代,而是对其的完善或补充,它应当具有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特征。所以,他们将自己的共和主义称做“自由主义的共和主义”或者“共和主义的自由主义”。(27)
相反,坚持共和主义/自由主义这一令人绝望的二元对立必将导致大多数新共和主义者不愿正视自由主义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从而忽视了平等导向的社会自由主义、参与导向的公民自由主义与新共和主义结合的可能,并回避了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对工具性共和主义的接受、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中对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的综合等理论调和。
新共和主义在理论上的进退也导致其所提供的政治方案要么在实践上不可行(比如,阿伦特的“评议会制”以及其他一些理论家所设想的各种参与和审议机制),要么根本就语焉不详,因为“太多的时间被他们用来抨击自由主义,从而无暇顾及详细阐述和捍卫一种替代物”。(28) 试想,如果连自由、共同善、公民美德这些概念都不能达成一定的共识,提供一种融贯的说明,新共和主义还能为现代政治提出什么具体的、实质性的救治呢?
概括地像,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共和主义,无论是在历史层面还是在理论层面,都是异常复杂的。当新共和主义者把整个自由主义作为自己的批判对象,并试图通过反照来确立自己的影像时,不但可能会忽视自由主义在自由、美德、公共善、公民身份这些议题上作出自我调整的能力,而且还会遭遇共和主义自身的历史、理论与实践的困境。在所有这些困境中,最重要也许莫过于公民美德的难题。
既然共同善、公共利益和公民美德一直是所有共和主义者的轴心原则和不二法门,既然整个古典共和主义传统都认为,道德败坏是人性的普遍趋势,人们总是倾向于将个人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既然雅各宾派“美德与恐怖结盟”的道德专政已经向世人表明了在现代世界复活古代政治的危险;既然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多元主义社会中——“它几乎不可能由对公共善的一种共同理解而统一起来,有德性的公民几乎不情愿总是为了整个共同体的利益而放弃他们的偏私要求”,(29) 那么,如何识别并捍卫公共利益、如何激发并维系公民美德、如何保持积极的公民身份自然便成为新共和主义者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30)
曼斯菲尔德(Harvey C.Mansfield)指出,当代的共和主义者在试图用积极公民身份来替代利益动机(the profit motive)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当斯金纳否认(自马基雅维利以来的)古典共和主义者持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积极自由观,而声称道德败坏“仅仅是理性的一种失败”时,“这究竟意味着义务或德行是符合你的利益——如此一来仍然是利益动机,还是败坏脱离你未实现之本性中最好的那一部分呢——这仍然是一种积极自由观念”?(31) 也就是说,如果放弃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前提,新罗马共和主义的经验分析将不得不面临“集体理性”的问题。同样,桑德尔承认,一元论的公共利益假设导致了卢梭政治学的专制倾向,但他从未清晰阐明他所谓的“灵魂艺术”(soulcraft)到底如何区别于卢梭“强制自由”、“倒因为果”的重塑人性计划。
事实上,自由主义者从未否认公民美德是可欲的。只不过,他们首先考虑的是不要增加国家的权力这一“自由主义剃刀”;他们宁愿把培养“深厚”的公民美德这一任务交给公民个人或者自愿性团体(公民社会);在考虑公民美德的激发时,他们往往诉诸“开明的自利”。共和主义者尽管并不反对“开明的自利”,却认为这不足以激发公民德行,他们还需要借助国家(法律)的强制、宗教的驯服、习俗的熏陶、神话的鼓舞,有些共和主义思想家甚至还坚持政治参与是最高的善这一独断论。这一切都是自由主义者无法认可乃至唯恐避之不及的。
当然,在公民美德问题上的困境不应该被我们用来轻易地否定新共和主义的理论努力;相反,这是一个真正的现代性难题,当代任何一种严肃的政治理论都必须认真地对待它。我们也许应该铭记著名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关于政治理论之乌托邦品质的格言:“一种理想,不管它多么有吸引力,如果现实中的人并没有欲求生活在这种理想之下的动力,那么这个理想就是一个乌托邦。然而,一个完全依赖于个人动机的政治制度也许根本就不能实现任何一种理想。”(32)
三、新共和主义的未来
毫无疑问,当代共和主义的复兴绝不仅仅是新的学术生长点的挖掘和学术旨趣的转移,它多少投射出当代西方社会政治生活的变迁和困境。从根本上说,新共和主义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由代议机构、政党、利益集团主导政治生活的大众—官僚社会中,在一个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人员和资本高度流动、大众文化和现代媒体发展到极致的世界中,个人如何保持自由、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共同体如何维系自身的认同和凝聚力?
当代自由主义中以罗尔斯的正义论为代表的规范理论秉承康德主义的理念,坚持个人权利的优先性,试图通过福利国家的办法实现公平正义的理想;而以多元民主论为代表的经验理论则放弃了人民主权的民主原则,仅仅满足于代议制下的有限参与。
新共和主义者认为自由主义的这两个方面无法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他们试图通过发掘和改造共和主义这一古老传统来重振自由理想。因此,新共和主义是作为自由主义的一种批判力量或者说替代力量而出现的。但是,新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的;它是一种“后自由主义”的而不是“反自由主义”的政治言说。所谓“后自由主义”(post-liberalism)不仅仅是一个时序性概念,它还包含某种超越性的含义,亦即它只有在自由主义充分发展的语境中才能得到理解。
因此,新共和主义必须对个人主义和多元主义这两个现代社会的特征作出正面回应,并且继承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和平等主义的价值承诺;此外,新共和主义者还必须对共和主义本身作出彻底的理论重构,唯有如此才能达到超越自由主义的目标。否则,它难免要沦为一种政治乡愁或乌托邦。(33)
注释:
①共和主义复兴的背景及概况,参见拙文:刘训练,2006a,“当代共和主义的复兴”;新共和主义的基本论述。参见应奇、刘训练,2006,《公民共和主义》。
②Weithman,2004,pp.298~290.
③相关的批评和质疑参见Hankins,2000; Rahe,1992。
④麦考米克认为,从“混合政体”的制度和社会学属性来定义共和主义可以“使得整个历史上的共和主义更加容易确认,不管是从政治哲学的著作还是从政治现实的环境来看都是如此”(McCormick,2003,p.638)。
⑤克兰尼科指出:“共和主义在历史上是有闲者的意识形态,其公民身份概念是那些不需要工作,有时间投身于公共生活的人的特权。通过履行公共义务,独立的土地所有者可以实现他们作为人的本质”(Kramnick,1990,p.1)。
⑥McCormick,2003,pp.615~617.
⑦参见拙文:刘训练,2006c,“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一个思想史的考察”。
⑧例如,对哈林顿的不同阐释(Isaac,1988),对共和学派援引马基雅维利的质疑(McCormick,2003)。
⑨对这场争论的批判性评论参见Rodgers,1992; Bassani,2002。对这场争论的综合性评论参见Kloppenberg,1987; Horowitz and Matthews,1997。
⑩Haakonssen,1993,p.571.
(11)Herzog,1986,p.474.
(12)Bassani,2002,p.149.
(13)关于古典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继承关系,可参见拙文:刘训练,2006c,“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一个思想史的考察”。
(14)剑桥学派的两个主将波考克和斯金纳曾极大地推动了古典共和主义的研究,因此有不少学者认为,“语境主义”为共和主义的复兴提供了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基础,然而这也许只是一个误解。限于篇幅,这里不拟考察这个问题。不过可以指出的是,斯金纳对马基雅维利的诠释、波考克对洛克的贬抑以及对哈林顿重新解读,无一不受到批评。
(15)Sandel,1985,pp.39~40.
(16)Herzog,1986,pp.476~477.
(17)Pettit,1997,pp.10~11.
(18)〔美〕希尔斯著,傅铿、吕乐译,1991,第17页。
(19)Sunstein,1988,p.1589.
(20)〔美〕霍尔姆斯著,曦中等译,2002,第7页。
(21)自由主义理论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这里姑且作这样一个略嫌简单化的处理。
(22)关于新共和主义的内部分野,参见拙文:刘训练, 2006a,“当代共和主义的复兴”。
(23)参见布伦南和洛马斯基从共同善、政治参与和无支配自由三个方面对新共和主义所作的全面回应(Brennan and Lomasky,2006)。
(24)〔加〕金里卡著,刘莘译,2004,第539页。
(25)参见Patten,1996; Larmore,2004。
(26)参见拙文:刘训练,2006b,“后自由主义视野中的新共和主义”。
(27)例如,Sunstein,1988; Dagger,1997。
(28)Herzog,1986,p.482.
(29)Herzog,1986,p.484.
(30)参见Herzog,1986; Burtt,1993。
(31)Mansfield,2000,p.228.
(32)Nagel,1989,p.904.
(33)这只是对新共和主义可能出路的一个大致勾勒。事实上,它能否以及如何克服前文提到的那些局限与难题,这仍然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
标签:政治论文; 自由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思想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