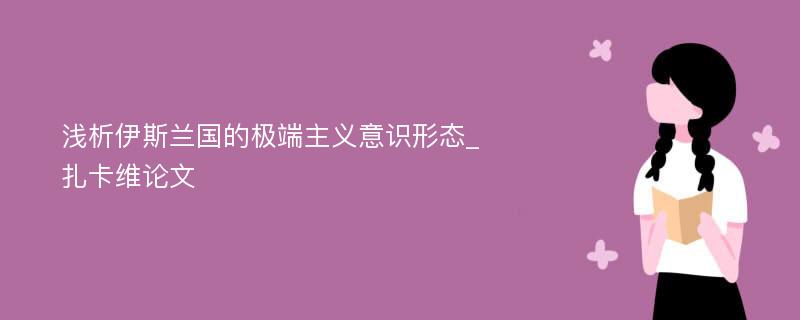
“伊斯兰国”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论文,极端主义论文,探析论文,意识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伊斯兰极端主义是伊斯兰主义中的激进和极端派别。伊斯兰主义作为一种宗教政治思潮和运动,其基本宗旨是反对西方化、反对世俗化,主张返回伊斯兰教的原初教旨、变革现存的世界秩序、推翻现存的世俗政权,建立由宗教领袖或教法学者统治的、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伊斯兰国家和秩序。①当代伊斯兰主义历来就有温和派与极端派之分,两者的共同目标都是重建伊斯兰教法统治下的伊斯兰国家、伊斯兰社会与伊斯兰秩序,但温和派主张采取合法斗争的和平方式,极端派则主张采取合法斗争与暴力斗争相结合的方式,甚至滑向恐怖主义。因此,从政治思潮的角度看,伊斯兰极端主义是当代伊斯兰主义中持激进或极端主张的思想观点、政治与社会主张的总称,背离宗教的和平本质,以宗教名义进行暴力恐怖活动,构成了宗教极端主义的本质特征。②宗教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的联系也在于此,即通过扭曲宗教教义为恐怖主义提供意识形态支持和社会动员手段。 当前,“伊斯兰国”作为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新形态,已经成为影响中东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安全的最大威胁。具有实体化、准国家化特点的“伊斯兰国”组织已取代“基地”组织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核心,并成为大规模恐怖袭击的主要发起者、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者,以及世界各地诸多恐怖极端组织的效忠对象。③脱胎于“基地”组织的“伊斯兰国”较之“基地”组织更为激进和极端,体现了伊斯兰极端主义发展的新趋势。 目前国内对“伊斯兰国”的研究多集中于其历史演变、影响及组织结构等问题④,但却缺少对“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深入研究。这也恰如美国中央司令部特种部队司令米切尔·纳格塔(Michael K.Nagata)少将所言:“迄今为止我们仍不了解‘伊斯兰国’,所以我们很难击败它。”“我们并未击败‘伊斯兰国’的理念,我们甚至并不理解它的理念。”⑤从某种程度上说,“伊斯兰国”的巨大影响力来源于其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和成功媒体策略的结合。在意识形态上,“伊斯兰国”主张以“圣战”方式在中东地区乃至更大范围内建立实施伊斯兰教法的所谓“哈里发国家”,对于陷入认同危机、生存危机和发展危机的边缘穆斯林群体,乃至陷入精神困顿的非穆斯林青年,都有较大的吸引力,加之“伊斯兰国”熟练运用现代媒体进行意识形态传播和人员招募,不仅使其人员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补充,对其表示效忠的分支机构也不断扩散。⑥ 当前,反对极端主义的“去极端化合作”已经成为中阿战略合作关系的重要内容。2016年1月,中国政府发布《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提出要在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搭建双多边宗教交流平台,倡导宗教和谐和宽容,探索去极端化领域合作,共同遏制极端主义滋生蔓延”⑦。因此,深入考察“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体系,准确掌握“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特点,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溯源 “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深受历史上各种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的影响。伊斯兰极端主义发端于中世纪的哈瓦利吉派和罕百里学派。进入近代以来,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思想源流主要有三大支流,它们分别是穆斯林兄弟会第二代思想家赛义德·库特布的极端思想,与沙特官方的瓦哈比教派相区别、自称“萨拉菲派”(“Salafist”,复古派、尊祖派,后文将对此进行详细论述)的极端思想,以及“基地”组织的极端主义思想,它们均构成了“伊斯兰国”极端主义的思想来源。而与上述极端主义思想存在密切联系的萨拉菲主义,尤其是圣战萨拉菲主义则构成了“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核心来源。 (一)中世纪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历史发端 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极端派别哈瓦利吉派(al-khawarij,意为“出走者”)。657年,第四任哈里发阿里的一部分追随者强烈不满阿里对大马士革总督穆阿维叶所做的妥协,遂愤而出走另组哈瓦利吉派。哈瓦利吉派有强烈的不容异己的倾向,从所谓“正信”的角度强调宗教信仰的绝对化,强迫人们必须接受其教义思想,否则即是叛教者,同时主张对“伪信者”从肉体上加以消灭,并以此为基本宗教信条之一。哈瓦利吉派不仅反对哈里发政权,而且以恐怖手段对待不赞同其宗教信仰和政治观点的穆斯林平民。⑧根据金宜久主编的《当代宗教与极端主义》一书的总结,哈瓦利吉派对极端主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它把宗教信仰绝对化,甚至将不赞成自己观点的穆斯林宣布为“不信道者”并予以排斥和打击。第二,把“真主主权”作为否定倭马亚王朝哈里发政治合法性的根本依据。第三,它宣称对不赞成其教义主张的所谓“伪信者”进行肉体消灭,泛化了伊斯兰教的“圣战”观念。⑨ 对当代伊斯兰极端主义影响至深的另一思想源流是中世纪的罕百里学派。以伊本·罕百里(780~855年)教长为代表的罕百里学派,具有明显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倾向,以固执、偏激、保守著称。该派强调严格遵从《古兰经》和圣训,主张从字面意思解释经文,否认类比和公议等含有理性成分的教法内容的地位和作用。罕百里学派所固有的宗教保守主义思想,构成了宗教极端主义的历史文化根源之一。尽管今天许多暴力恐怖组织的成员与该学派无关,但人们仍不能否认他们在思想上受其影响或存在某种渊源关系。⑩ 13至14世纪的伊本·泰米叶(1263~1368年)是新罕百里学派的重要代表。在信仰层面,泰米叶主张按照字面表义来解释经、训原文和教法典籍,以净化信仰的名义排拒外来的思想文化,反对思辨哲学和苏菲派哲学、反对圣徒崇拜、圣墓崇拜等苏菲民间宗教习俗等。(11)在如何看待“圣战”的问题上,泰米叶强调指出,即使对那些已经宣布接受伊斯兰教但拒绝伊斯兰教法的名义上的穆斯林,仍可视为“圣战”的对象。“正是14世纪的伊本·泰米叶,在圣战的第一个低潮期中激活了休眠中的圣战观。”(12)伊本·泰米叶是早期萨拉菲运动的发起者,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其保守、偏激、狭隘和不容异己的思想对后世影响至深。例如,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在题为《圣战:被遗忘的义务》的小册子中,就曾援引泰米叶的“教令”,宣称他们“处死”埃及总统萨达特的行为完全符合伊斯兰教。(13) (二)近现代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1.瓦哈比主义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影响 18世纪中叶以来,阿拉伯半岛兴起的瓦哈比教派成为沙特的官方意识形态,并在后来逐步分化为官方的瓦哈比主义和民间的瓦哈比主义,二者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影响也不尽相同。进入当代后,沙特官方的瓦哈比主义在国际上主要以推动伊斯兰教的宣教事业、援助和支持国际上的伊斯兰组织作为其施加影响的主要方式,泛伊斯兰主义的色彩十分浓厚,并在促进伊斯兰国家的团结与合作、维护穆斯林利益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国内,瓦哈比主义的宣教布道也不再像早期那样鼓吹“圣战”思想,同时也反对伊斯兰极端势力以宗教名义干预政治,以及从事反对王权的暴力恐怖活动。但是,沙特基于反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等世俗主义意识形态的需要,在利用“石油美元”推行泛伊斯兰主义的过程中,它开始收容伊斯兰国家政治反对派,通过各种渠道资助和支持世界各地的伊斯兰运动,甚至资助和支持激进或极端的伊斯兰组织。(14)例如,沙特曾收留了穆斯林兄弟会极端派理论家赛义德·库特布的弟弟穆罕默德·库特布,并为其提供保护。(15)阿富汗“塔利班”、“基地”组织在早期都曾得到沙特官方瓦哈比派的支持和资助。 沙特民间的瓦哈比主义,尤其是自称“萨拉菲派”的伊斯兰激进组织与极端主义的联系更为直接,并继承了瓦哈比主义的极端保守思想。民间的瓦哈比主义者往往在泛伊斯兰主义思想的掩盖下,积极输出瓦哈比派早年的宗教政治主张,鼓吹通过“圣战”手段,建立伊斯兰政权和伊斯兰国家,极力主张对“异教徒”实施“圣战”。(16)瓦哈比教派的创始人本·阿布·瓦哈卜认为,所有的什叶派都是不信教者(kufr),应对其实行“定判”(Takfir,判定某些人为异教徒),(17)这些思想构成了“圣战萨拉菲派”(后文将进行详尽论述)极端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同时也成为当今“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来源之一。(18) 2.穆斯林兄弟会理论家赛义德·库特布的极端主义思想 穆斯林兄弟会第二代理论家赛义德·库特布是现代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其代表作《路标》直接为伊斯兰极端组织提供了思想来源和精神支持。库特布对极端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在于他提出了赋予暴力“圣战”以合法性的两个重要概念。第一个概念即“定判”,其含义是判定某穆斯林的行为和思想违背伊斯兰教,即宣布某穆斯林为异教徒。第二个概念是“贾黑利亚”,即“蒙昧时期”(Jahiliyya,指伊斯兰教产生以前的阿拉伯社会),所有伊斯兰世界和西方的现存政治秩序都是“蒙昧”的体现,都应予以推翻,理想的政治制度是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体现真主主权的伊斯兰制度,即“哈基米亚”(Hakimiyya,即真主主权)。(19) 从穆斯林兄弟会中分化出的“伊斯兰圣战组织”、“伊斯兰解放组织”“伊斯兰集团”和“赎罪与迁徙”等组织都深受库特布思想影响,(20)库特布也因此被西方称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教父”。(21)库特布的思想影响了一整代埃及以及其他国家的圣战主义思想家。埃及圣战组织的领导人奥马尔·阿布德尔·拉赫曼以及后来成为“基地”组织领导人的扎瓦赫里都深受库特布思想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人在研究库特布的思想之后在阿富汗找到了将其思想付诸实践的机会,进而使圣战萨拉菲运动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2) (三)“基地”组织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 1979年的阿富汗战争的后果之一是它直接催生了“基地”组织,其“圣战者”多来自从埃及穆兄会或巴基斯坦“伊斯兰促进会”中分离出来的极端分子和激进派别,并得到塔利班政权的庇护,使其成为一股极具影响力的恐怖主义势力。“基地”组织的思想基础和价值信念来自于伊斯兰极端主义,本·拉登“圣战”思想的启蒙者就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极端主义思想家赛义德·库特布和阿卜杜拉·阿泽姆。(23) 本·拉登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及其向恐怖主义演变的典型特征主要有三:首先,本·拉登肆意曲解和歪曲伊斯兰教的信仰体系,把一切问题都解释、简化为宗教问题,并大肆煽动宗教狂热。其次,本·拉登极力鼓吹“圣战”,使“圣战”成为国际恐怖主义最重要的工具。就伊斯兰教而言,所谓“圣战”主要是指当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受到外部势力的严重威胁时,应当为保卫神圣的信仰而进行自卫性的反击。历史上的“圣战”通常是由国家元首或众望所归的宗教领袖发布命令。以本·拉登为代表的恐怖分子既不是合法的政治权威,也不是合法的宗教权威,但他们却随意以伊斯兰的名义宣布和发动“圣战”。最后,伊斯兰教反对针对无辜平民的攻击和杀戮,而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则将包括穆斯林在内的平民作为攻击对象,完全背离了伊斯兰教的基本精神。(24)本·拉登的恐怖主义思想令其思想导师阿泽姆都难以容忍,阿泽姆反对违背伊斯兰教义、针对非武装人员的暴力活动,这也是二者最终分道扬镳的原因。(25) 尽管“基地”组织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结合达到了相当极端的地步,但相对于脱胎于“基地”组织的“伊斯兰国”而言,其意识形态建构的能力尚远远落后于后者。例如,“基地”组织强调以打击西方(“远敌”)目标为核心的全球圣战,意味着它较少更为急迫地关注以何种方式实施伊斯兰教法,建立哈里发国家。在2004年,当“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领导人、“伊斯兰国”组织前身“统一和圣战组织”领导人阿布·穆萨·扎卡维提出建立哈里发国家的问题时,“基地”组织领导层明确表示反对,其解释是伊拉克建立“伊斯兰国家”条件并不成熟。又如,“基地”组织并不强调教派对立,强调不要因针对包括什叶派在内的平民过度使用暴力而疏远穆斯林民众。(26)因此,“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在意识形态和发展战略上始终存在尖锐分歧,这也是“伊斯兰国”最终脱离“基地”组织另立门户的根源所在。 (四)“圣战萨拉菲主义”:“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核心来源 事实上,前文所述的伊斯兰极端主义都与萨拉菲主义存在一定的联系,或者这些思想本身就是萨拉菲主义的表现形式,但鉴于萨拉菲主义的复杂性以及圣战萨拉菲主义对“伊斯兰国”的重要影响,这里有必要对萨拉菲主义(Salafism)和圣战萨拉菲主义(Jihadi-Salafism)做简要的专门分析。 “萨拉菲”(Salafi)在阿拉伯语中的原意为“祖先”、“先辈”,萨拉菲派(Salafist)的基本含义为“尊古派”,是产生于中世纪的保守宗教派别,主张严格奉行《古兰经》和“圣训”,特别强调净化信仰、尊经崇圣,其典型代表人物是中世纪罕百里教法学派的伊本·泰米叶。近代以来的伊斯兰主义运动深受萨拉菲派的影响,18世纪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教派成为近代萨拉菲派的先驱。萨拉菲主义是一个非常多样和复杂的意识形态。萨拉菲主义的核心主张包括根除偶像崇拜(shirk)、重申认主独一(tawhid)。萨拉菲主义者认为他们自己是唯一真正的穆斯林,同时认为偶像崇拜者已经偏离伊斯兰信仰的正道,崇拜所谓圣石、圣人、圣墓等都意味着叛教,其信徒即判教者。(27) 当代萨拉菲派的具体表现形式形形色色,但并非所有的萨拉菲派都主张采取暴力恐怖行为建立伊斯兰国家。当代的萨拉菲主义大致可划分为传统萨拉菲主义、政治萨拉菲主义和圣战萨拉菲主义三大派别。传统萨拉菲主义强调恪守传统宗教信仰和宗教礼仪,主张远离政治,也反对恐怖暴力行为。政治萨拉菲主义在强调宣教的同时,主张通过参政议政实现伊斯兰教法的统治,但反对暴力恐怖活动。圣战萨拉菲主义则主张通过发动“圣战”等暴力手段颠覆阿拉伯国家的世俗政权,建立伊斯兰教法政权。(28) 在20世纪后期,中东出现了受穆斯林兄弟会激进主义和萨拉菲排他主义影响的暴力组织。这些组织包括埃及的“伊斯兰圣战”组织(Islamic Jihad)和“伊斯兰集团”(Islamic Group),以及阿尔及利亚的“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the Salafi Group for Preaching and Combat),他们构成了当前“圣战萨拉菲”组织的前身。在意识形态上,他们都深受穆斯林兄弟会思想家赛义德·库特布激进主义思想的影响,其核心目标在于通过“圣战”推翻现行政权并建立“伊斯兰国家”。在圣战萨拉菲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约旦裔巴勒斯坦人阿布·穆罕默德·马克迪斯(Abu Muhammad al-Maqdisi)和叙利亚的阿布·巴斯尔·塔图斯(Abu Basir al-Tartusi)等人的思想对于圣战萨拉菲主义运动的发展有重要影响。(29)他们在早期都深受库特布极端思想的影响,后来逐渐转向萨拉菲主义,其思想的核心是赋予萨拉菲主义以暴力思想,进而推动了圣战萨拉菲主义的产生。(30) “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来源于为许多伊斯兰极端组织共同信奉的“圣战萨拉菲主义”,“伊斯兰国”的领导人对此也供认不讳。“伊斯兰国”的创始人阿布·穆萨布·扎卡维曾是马克迪斯的学生,并深受其思想影响。“伊斯兰国”的第二代领导人阿布·乌马尔·巴格达迪(Abu Umar al-Baghdadi)同样是坚定的圣战萨拉菲主义者,其讲话经常引用源于萨拉菲主义的权威观点。(31)例如,他在2007年发表讲话指出:“所有的逊尼派教徒特别是青年都应该参与圣战萨拉非主义运动,建立横跨整个世界的帝国”。“伊斯兰国”还明确将其从事的活动描述为“圣战萨拉菲主义潮流的组成部分”(32)。 “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体系——兼论“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分歧 圣战萨拉菲主义构成了“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但“伊斯兰国”在坚持圣战萨拉菲主义方面的强硬路线,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它与“基地”组织的鲜明区别。因此,有评价指出:“如果将圣战主义置于政治光谱下,‘基地’组织构成了圣战主义的左翼,而‘伊斯兰国’构成了圣战主义的右翼。‘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都坚持萨拉菲派神学,都赋予圣战运动以萨拉菲主义的特征。但是,与‘基地’组织不同,‘伊斯兰国’更加毫无妥协地坚持萨拉菲主义的信条,推行萨拉菲主义的思想。”(33) (一)顽固坚持把建立所谓“哈里发国家”付诸实践 许多伊斯兰激进组织都主张重建“哈里发国家”,但在思想认识和重视程度上却存在明显差异。例如,穆斯林兄弟会认为建立“哈里发国家”是一个长期目标而非近期目标,因此它在实践方面对重建哈里发国家的态度“相对淡漠”。(34)本·拉登把“基地”组织的恐怖活动视为建立“哈里发国家”的前奏,但他同时悲观地认为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无法看到这个国家。(35)但是,“伊斯兰国”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建立“哈里发国家”作为矢志不渝的信念,并强调立即付诸实施。 早在2002年扎卡维进入伊拉克之前,他就确立了建立“哈里发国家”的目标,而伊拉克战争的爆发进一步坚定了扎卡维在伊拉克建立“伊斯兰国”的目标。在很多讲话和声明中,扎卡维多次宣称建立哈里发国家是“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的战略目标。2004年,他在讲话中先后指出:“我目前正在伊拉克领导我的兄弟们进行圣战,其目标在于建立伊斯兰国家,即符合《古兰经》的国家。”“符合《古兰经》的国家已经成立在即”,“我们‘真主独一与圣战’组织(‘伊斯兰国’的前身,作者注)正在向敌人发动攻击,正在向不公平进行战斗,我们的目标是在地球上重建实施伊斯兰教法和易卜拉欣宗教的哈里发国家。”2004年10月,在扎卡维向本·拉登宣示效忠之际,他宣称哈里发国家“必将在我们手中建立”。(36) 2006年6月12日,“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宣布正式成立“伊拉克伊斯兰国”(the Islamic State of Iraq),由阿布·乌马尔·巴格达迪出任“哈里发”,其发言人穆哈里·朱巴里(Muharib al-Juburi)指出:“尽管偶像崇拜者和有经人(the People of the Book,指犹太人和基督教徒)联手反对先知,但先知却从麦加迁徙麦地那(622年)建立了伊斯兰国家,这是我们应该效仿的典范。”2007年1月,“伊斯兰国”的“伊斯兰教法委员会”发布了题为“就伊斯兰国的诞生昭告全人类”的声明,论证“伊斯兰国”的国家属性及其基于伊斯兰教法的合理性。“崭新的伊斯兰国家再现了伟大的伊斯兰教的强大与辉煌……今天的伊拉克领土将服务于实现伟大的伊斯兰蓝图……它的资源和财富足以在整个地区内掀起更伟大的伊斯兰浪潮。”(37) 2010年,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担任“伊拉克伊斯兰国”领导人后,也多次强调“伊斯兰国”的所谓“哈里发”国家属性。他于2012年指出:“我崇敬的穆斯林共同体:当我们宣布建立伊斯兰国之际,我们便不再悖逆真主;当我们矢志不渝地追求伊斯兰国的理想之际,我们便不再悖逆真主……伊斯兰国将是我们坚持的信仰和道路,它从未也永远不会被其他事物所取代”。(38)他还宣称“伊斯兰国”“正在以全新的姿态回归它所控制的地区并不断扩大……‘伊斯兰国’不承认人为的边界及伊斯兰国之外的任何国民身份。”(39) 事实上,“伊斯兰国”建立的所谓哈里发国家不仅遭到了包括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在内的整个国际社会的反对和唾弃,即使是其他圣战萨拉菲主义组织和宗教学者也都对“伊斯兰国”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其主张具体有二:首先,“伊斯兰国”仅仅是一个“战斗团体”,并非真正的国家,缺乏国家的政治能力;其次,巴格达迪自称“哈里发”不具合法性,他不能成为所有穆斯林的效忠对象,甚至称其为只有“小学水平”的“冒牌宗教学者”。(40) “基地”组织领导人扎瓦赫里认为,“伊斯兰国”和巴格达迪没有资格成为所有“圣战”团体效忠的对象,同时反对“伊斯兰国”兼并叙利亚“支持阵线”并成立“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据半岛电视台2013年6月的消息,“基地”组织领导人扎瓦赫里认为“伊斯兰国”兼并“支持阵线”的做法无效,强调二者仍然是各自独立的组织实体。但在巴格达迪看来,扎瓦赫里并不拥有对“伊斯兰国”的领导权,他本人才是至高无上的哈里发。2013年6月15日,巴格达迪发表声明对扎瓦赫里予以反驳。他声称“‘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不会屈从于任何压力”,“它也不会从任何它已经占领的领土上退缩,相反它的领地将继续扩大”。巴格达迪还表示,“伊斯兰国”拒绝承认“基地”组织的领导拥有法律上的合法性,并称这是“伊斯兰国”协商委员会和教法委员会协商后做出的决定。(41)由此可见,“伊斯兰国”顽固坚持其国家性质为“哈里发国家”,巴格达迪为所有“圣战”团体和穆斯林的效忠对象,这也是“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彻底决裂的原因之一。 建立所谓“哈里发国家”是“伊斯兰国”坚持不懈地追求,即使在2006年前后“伊拉克伊斯兰国”(“伊斯兰国”的前身)发展严重受挫的情况下,它依然毫不动摇地坚持其“建国”目标。因此,在追求“建国”方面,“伊斯兰国”的顽固性远远超过了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其他极端组织。 (二)强调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教派矛盾,煽动教派冲突 “基地”组织一直提倡所谓的“泛伊斯兰”团结,强调其圣战的对象是“叛教者”、腐败变质的阿拉伯政权、美国及其盟友。本·拉登认为,导致“乌玛”(Umma,穆斯林共同体)分裂的根源是穆斯林群体中基于民族、种族以及派系的划分,并一直强调穆斯林应当共同行动,避免教派内部互相残杀,共同打击其西方敌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内部战争都是重大错误”。(42)扎瓦赫里也一直反对穆斯林之间自相残杀,同时明确反对扎卡维对什叶派的屠杀。尽管“基地”组织也把什叶派视为误入歧途的“叛教者”,但扎瓦赫里主张“基地”组织应该对其进行传道,而不是杀戮他们,除非他们首先发起攻击。(43)在2005年,扎瓦赫里曾要求扎卡维不要攻击伊拉克什叶派及其清真寺,以避免引起穆斯林民众的反感。扎瓦赫里认为,对抗什叶派是无法避免的,但不可操之过急。(44)扎瓦赫里还告诫扎卡维,公开处决罪犯和什叶派教徒将导致穆斯林民众疏远“基地”组织。2013年10月,在伊拉克教派暴力冲突不断升级之际,他公开下令禁止“伊斯兰国”打击什叶派和苏菲派,强调“要集中力量打击国际异教徒的头目。”(45)阿布·穆罕默德·马克迪斯与“基地”组织一样主张渐进性的战略,不断强调赢得公众支持的重要性。(46) 但“伊斯兰国”则特别强调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对立,主张其首要的攻击目标是作为“叛教者”的什叶派穆斯林。“伊斯兰国”一直将什叶派视为不信教者和叛教者,其理论论证主要是由“伊斯兰国”的缔造者扎卡维完成的,其观点主要包括三方面: 首先,在神学层面,扎卡维不断引用包括伊本·泰米叶在内的逊尼派穆斯林权威的言论,证明什叶派偏离了伊斯兰教的正道。例如,扎卡维经常引用伊本·泰米叶的著名警告:“他们(指什叶派)是敌人。提防他们。攻打他们。天哪,他们撒谎”。在2006年扎卡维丧生前不久,他还在一次公开演讲上大声疾呼:“穆斯林绝不可能胜过或超过好斗的异教徒——比如犹太教徒、基督教徒,除非我们把诸如拉菲达(阿拉伯语原意为“拒绝”,意指什叶派,是扎卡维对什叶派的蔑称)等叛教者全部消灭。”(47) 其次,在历史层面,扎卡维不断强调“什叶派在伊斯兰历史上扮演的危险的、罪恶的角色”。例如,他认为16至17世纪伊朗建立的萨法维王朝(Safavid Dynasty)使伊朗皈依了什叶派,萨法维王朝成为“刺入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利剑”。他还认为什叶派在1258年蒙古军队攻陷巴格达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48) 最后,在现实层面,扎卡维不断强调什叶派的现实威胁。他认为,在伊拉克,什叶派正通过与美国人合作攫取伊拉克的权力。他鼓吹要通过对什叶派发动圣战把逊尼派团结起来。他指出:“在宗教、政治、军事等方面对什叶派进行攻击,向逊尼派揭示什叶派的野心,有利于激发逊尼派对什叶派的仇恨。如果我们将什叶派拖入教派战争的境地,就有可能唤醒漫不经心的逊尼派,促使逊尼派意识到巨大的危险,并致力于消灭什叶派。”(49)他还特别仇视伊朗什叶派。他指出,以伊朗为核心的什叶派正在通过建立跨越中东地区的超级国家追求地区霸权,“他们的野心是建立一个横跨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并将虚弱的海湾君主制王国纳入其中的什叶派国家。”(50)扎卡维甚至认为,什叶派对逊尼派的威胁超过了美国,因为“十字军占领者将在不久的将来消失”,但什叶派“作为逊尼派最迫近的危险的敌人”将长期存在,因此“什叶派对伊斯兰教的威胁及其破坏作用远远大于美国人。”在扎卡维看来,什叶派对逊尼派的仇恨无法消除,唯一的解决办法是通过战斗赢得对什叶派的胜利。(51) 扎卡维的反什叶派思想构成了“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被其继任者所继承。2007年3月13日,阿布·乌马尔·巴格达迪发表题为《我们的基本原则》的讲话,提出了“伊斯兰国”的19条原则,其中第二条便强调了反什叶派的原则:“对我们的信仰加以拒绝的人即什叶派是偶像崇拜者和叛教者”。(52)巴格达迪还曾直言,“伊斯兰国”将“首先对付什叶派……然后对付沙特王国及其支持者……然后才是十字军和他们的基地。”(53) 总之,对待什叶派态度和行动策略的不同,构成了“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分歧。对待什叶派的极端态度和激进立场,煽动教派矛盾和教派冲突,构成“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典型特征。在当今中东教派冲突加剧的背景下,“伊斯兰国”刻意强调教派对立和教派仇恨的做法,一方面反映了它利用教派冲突争取逊尼派支持,进而扩大其社会基础的机会主义图谋;另一方面也对恶化教派关系、加剧教派冲突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三)顽固坚持“异教徒定判”原则 “异教徒定判”(Takfir)是指对穆斯林中不信教者判处死刑的一种神学制裁,最早可追溯至哈瓦利吉派不容异己的极端思想。哈瓦利吉派要求人们遵循本派教义,并把犯有“大罪”和不赞成、不支持自己的穆斯林视为“不信道者”,即卡菲尔(Kafir),并对其予以打击和消灭。埃及的“赎罪与迁徙组织”也把不赞成其激进思想的穆斯林一律看作是“非穆斯林”或“叛教者”。(54) “伊斯兰国”顽固坚持所谓“异教徒定判”原则,它不仅把阿拉伯世俗统治者视为叛教者和圣战打击的首要目标,还把反对其主张的普通穆斯林视为叛教者,坚持对叛教者进行集体性的“异教徒定判”,并允许残杀妇女和儿童。(55)“伊斯兰国”认为,它正处在非穆斯林的包围之中,所有不支持其意识形态的国家和民族都是叛教者;凡不按照真主的法律进行统治便意味着叛教;对抗“伊斯兰国”等同于叛教;所有的什叶派穆斯林都是应该被处死的叛教者,甚至认为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也是伊斯兰教的叛徒。“伊斯兰国”在其信条中曾称:“我们认为举着各种旗号活动的世俗主义者,如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阿拉伯复兴主义以及什叶派穆斯林都是公然的不信教者,他们放弃伊斯兰教并脱离了宗教信仰。”(56) 2007年3月,“伊拉克伊斯兰国”的第二代领导人巴格达迪发表讲话,阐述“伊斯兰国”坚持的基本原则,并且重点阐述了如何确定异教徒和如何进行定判。他指出:“非信包括大的非信和小的非信两种类型,对非信者的裁判依据是他在信仰、言论和行为方面犯下的罪行。判定某一个体为异教徒并且判决他进入地狱要根据定判的条件”;“我们坚信应该杀死那些施展巫术和魔法的非信者和叛教者,我们也绝不接受他们的忏悔”;“我们认为那些参加政党、参与政治进程的人都是不信道的人和叛教者”;“我们认为为占领者及其向其提供任何支持诸如衣食、医疗等方面帮助的人都是不信道者和叛教者,他们也将因此成为我们攻击的目标并使其付出血的代价”;“我们认为这些国家(指世俗的阿拉伯国家)的统治者和军队都是不信道者和叛教者,与他们进行战斗的必要性大于与占领伊斯兰领土的十字军进行战斗。(57) “伊斯兰国”还把“异教徒定判”的对象扩大到所有非穆斯林地区和群体。2014年7月,巴格达迪声称:“当今世界事实上被划分为两大对立阵营,不存在第三阵营:一个是由穆斯林和圣战者组成的无处不在的信仰伊斯兰的阵营;另一个是卡菲尔(不信教者)和伪善者的阵营,它是由犹太人、十字军及其同盟以及其他民族和宗教所组成的卡菲尔的联盟,由美国和俄罗斯领导并被犹太人所鼓动”。(58) “伊斯兰国”对“异教徒定判”的极端泛化和集体化倾向远超过其他伊斯兰极端组织。例如,本·拉登的老师、“基地”组织的精神领袖阿卜杜拉·阿扎姆就反对将穆斯林群体内部的人视为不信教者并对其实施“异教徒定判”。“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在叛教者判定的标准上也存在分歧。“基地”组织仅将“异教徒定判”原则限于否认《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神圣性的个体行为,本·拉登就反对将某穆斯林群体视为叛教者,反对针对穆斯林群体进行“异教徒定判”。(59)而“伊斯兰国”却将贩卖酒类和毒品、穿着西式服装、不蓄须、在选举中投票(即使是投给穆斯林候选人)等行为都视为叛教行为,不论这些人是否是穆斯林,都应按照“异教徒定判”原则加以消灭,其残暴程度令“基地”组织也难以接受。 总之,“伊斯兰国”对“异教徒定判”原则进行了极端泛化与滥用,并以此为由屡屡对所谓“异教徒”和俘虏采用斩首、集体杀戮和活埋等血腥手段,滥杀什叶派、基督徒、亚兹迪人,其嗜血成性、手段凶残的恐怖行径远超过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所有恐怖组织,而“异教徒定判”原则无疑构成了“伊斯兰国”残忍消灭异己的意识形态基础。 (四)强调滥用暴力的“进攻性圣战” 伊斯兰教中的“圣战”即“吉哈德”(Jihad)并非仅仅意味着战争。在《古兰经》中,“吉哈德”的原意有“斗争”、“奋斗”和“作战”等多种含义和形式,十分复杂。(60)但简而言之,“吉哈德”从形式上有“大吉哈德”和“小吉哈德”,前者指言论和思想层面的斗争,后者指战争和作战层面的斗争。有穆斯林学者指出:“我们很多人相信,大吉哈德表示针对欲念和撒旦的吉哈德,而小吉哈德则是在战场上对抗不信伊斯兰教者。”(61)圣战包括进攻性圣战(Offensive Jihad)和防御性圣战(Defensive Jihad)两种典型的形式。进攻性圣战是穆斯林共同体的集体义务,防御性圣战是反对外来侵略者的个体义务。根据经典的教法学理论,进攻性圣战由穆斯林的统治者即哈里发发起,它被视为一种集体义务,要求要有足够数量的穆斯林成员参与圣战,以确保圣战的胜利。防御性圣战不必由穆斯林统治者即哈里发发起,由于它是一种个体义务,所有的穆斯林都应该参加。(62) 历史上,“圣战”的内容因时间地点不同而不同,(63)并且对实施“圣战”有严格限制,《古兰经》和圣训均有对战争行为进行法律和道德限制的规定,主要包括禁止攻击平民和非战斗人员、妇女、儿童、教士,应接受非穆斯林提出的缔结和平协定的要求,除非军事需要不得破坏财产,善待俘虏和孤儿,尊重人道原则和道德原则等方面的诸多规定。(64)要客观认识伊斯兰教的圣战观,必须结合数百年来伊斯兰教的历史实践加以认识,因为圣战思想与实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体现。(65)但是,当代伊斯兰极端主义却极力扭曲和滥用传统圣战思想,甚至服务于恐怖主义,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都强调“圣战”的重要性,但“伊斯兰国”更为强调进攻性圣战。“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都承认“防御性圣战”的必要性,他们都认为伊斯兰世界处在“叛教的”世俗统治者控制之下,并遭受西方异教徒侵略的威胁,因而有必要利用防御性圣战的道德和舆论力量团结伊斯兰,与侵略者展开斗争,维护伊斯兰世界的利益。“伊斯兰国”在其信条中声明:“我们相信在通往真主道路上的圣战是个体义务,从安达卢斯(66)的攻陷直到所有穆斯林土地的解放,对任何一个虔诚的或者不虔诚的人来说这都是一个个体义务。”(67) 但是,相对于“基地”组织,“伊斯兰国”更为强调进攻性圣战的重要性。“伊斯兰国”声称他们有义务实施伊斯兰教法中的进攻性圣战,并将其视为哈里发国应尽的集体性义务,叫嚣将偶像崇拜者和不信真主的国家作为“圣战”的主要对象,向非伊斯兰世界发动武力战争,从而不断扩大哈里发国家的疆域和影响力。2007年,“伊拉克伊斯兰国”的第二代领导人巴格达迪指出,圣战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圣战使偶像崇拜者在世界上不复存在”。在另一次演讲中,他更加明确强调了“进攻性圣战”的重要性。他指出,穆斯林要“在叛教的非信者的领土上对他们发动进攻,直至不再有迫害存在,进而保护至高无上的真主的启示”(68)。 围绕“圣战”的严重分歧构成了“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分道扬镳的重要根源之一。在“伊斯兰国”成立之初,“基地”组织领导人扎瓦赫里就反对扎卡维无限制地滥杀无辜,并要求“伊斯兰国”汲取20世纪90年代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武装集团”(Armed Islamic Group,GIA)因过度使用暴力而失去民众支持的教训,警告其军事机构的领导人要限制过分使用暴力,不要因此削弱民众的支持。(69)扎卡维的老师阿布·穆罕默德·马克迪斯也一直批评“伊斯兰国”过度使用暴力,认为实施斩首等暴力行为有损于建立“伊斯兰国家”的目标。他还特别反对“伊斯兰国”对什叶派进行杀戮和攻击。(70) 出于对“基地”组织的渐进战略和反对过度使用暴力等方面的不满,“伊斯兰国”开始疯狂地诉诸暴力,“它还通过社交媒体和其他网络平台引以为豪地展示斩首、绞刑、公开枪决、鞭刑等视频。此外,它把任何反对其教义的人都贴上异教徒的标签,通过所谓异教徒‘定判’赋予其大肆杀戮平民和反对者的行为以合法性。”2014年4月,“伊斯兰国”的发言人阿德纳尼发表声明指出:“‘基地’组织已经偏离了正道……今天的‘基地’组织已经不再是致力于圣战的‘基地’组织,因此它也不再是‘圣战’的基地。”“基地”组织已经转向“追随大多数的和平主义”,它已经“偏离圣战和认主独一”,转而强调“革命、大众性、起义、斗争、共和主义和世俗主义”。“伊斯兰国”还对“基地”组织的批评发起了一系列言辞激烈的反击,其内容涉及圣战义务、教义的纯洁性、穆斯林共同体(乌玛)和“圣战”的领导权等方面。“伊斯兰国”的声明所展示的双方的矛盾已经不再是早期一般意义上的分歧,而是要否认“基地”组织的合法性并取代“基地”组织对圣战的领导权。(71) 综上,“伊斯兰国”作为新一代极端组织和恐怖主义的代表,其意识形态建构能力远超“基地”组织等传统的极端组织和恐怖组织。在所谓的信仰层面和神学层面,它更重视以净化信仰、正本清源为名,用所谓经典的伊斯兰神学思想对其极端思想进行包装,尤其是它奉行的“异教徒定判”和“进攻性圣战”等极端原则均通过“引经据典”予以论证,使其意识形态更具隐蔽性、欺骗性和蛊惑性。在目标方面,它极端重视将建立所谓“伊斯兰国”和“哈里发国”付诸实践,直至“治国理政”,超越了传统极端主义批判能力有余、实践能力的特点,使其对全球“圣战”分子更具吸引力,其效忠者“索马里青年党”、尼日利亚“博科圣地”等极端组织也纷纷效仿,进而对中东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民族国家体系构成严峻威胁。在现实策略方面,“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构建非常善于利用和煽动教派矛盾,以扩大其社会基础。此外,“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强大渗透能力还在于其成功的媒体策略,但基于该问题的复杂性和本文的篇幅限制,本文不对此展开论述。 余论:“伊斯兰国”对伊斯兰教核心价值观的扭曲 “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形成深受历史上各种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的影响,体现出了强烈的不容异己、崇尚暴力的极端主义本质。如今,“伊斯兰国”已发展成为比“基地”组织更为极端的恐怖主义势力,而且拥有建构和传播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大能力。但“伊斯兰国”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不仅与伊斯兰教本身无涉,而且严重扭曲了伊斯兰教崇尚和平、倡导中正的核心价值观,对伊斯兰文明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并使去极端主义成为当今世界尤其是伊斯兰文明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 首先,“伊斯兰国”背离了伊斯兰教的和平精神。追求和平、仁爱是伊斯兰教的基本宗旨和原则之一。“伊斯兰”在阿拉伯语中意即“顺从”、“和平”;“穆斯林”意为“顺从者”、“和平者”。《古兰经》中有许多关于和平的表述,例如:“如果他们倾向和平,你也应当倾向和平,应当信赖真主。他确是全聪的,确是全知的。”(8:61)“伊斯兰国”在圣战萨拉菲主义的指引下,强调运用进攻性圣战的极端方式,挑起不同民族和教派间非此即彼、不容异己的残酷斗争,并对所谓的“叛教者”进行残忍讨伐和杀戮,这完全背离了伊斯兰教的和平传统,并对中东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其次,“伊斯兰国”背离了伊斯兰教谨守中道的精神。《古兰经》有许多关于“中道”的论述,如:“你们不要过分,因为真主必定不喜爱过分者。”(2:190)“恶行应得同样的恶报。谁愿饶恕而且和解,真主必报酬谁。真主确是不喜爱不义者的。”(42:40)这些经文表明,伊斯兰教绝不是极端激进的宗教,历史上和当今的各种极端主义完全偏离了伊斯兰教谨守中道的核心价值观。“伊斯兰国”排斥异己、极端保守和拒不妥协的意识形态是对伊斯兰教中道精神的背离。 最后,“伊斯兰国”对进攻性圣战的偏执和滥用,完全违背了伊斯兰教法中对圣战的要求。伊斯兰教反对针对无辜平民的攻击和杀戮,更不允许对穆斯林进行“圣战”。《古兰经》明确规定:“你们不要违背真主的禁令而杀人,除非因为正义。”(2:33)穆罕默德在圣训中还强调,即便是宗教信仰不同,只要对方不加害于人,就要与之和睦相处。他指出:“谁伤害非穆斯林,谁就不是穆斯林”;“谁伤害被保护民,谁就等于伤害了我”。(72)事实上,“伊斯兰国”对圣战的泛化和滥用,不仅遭到包括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在内的整个文明世界的强烈反对,甚至也超出了“基地”组织和其他圣战萨拉菲派团体能够容忍的限度。总之,“伊斯兰国”对所谓“叛教者”(如什叶派穆斯林)和“不信道者”发动手段残忍的“圣战”,完全是对“圣战”概念的扭曲和滥用。在极端的“进攻性圣战”观念的指引下,“伊斯兰国”不断升级其恐怖主义手段,制造了一系列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和惨绝人寰的杀戮事件。相对于“基地”组织的恐怖主义活动,其手段更为残暴,目标更为广泛,影响范围更大,它所实施的极端残忍的种族屠杀和斩首行为,不仅玷污了伊斯兰教和平、中正的核心价值观,更挑战了人类文明的底线。 随着“伊斯兰国”势力的扩张,其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也迅速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并且成为“伊斯兰国”的核心竞争力之一。遏制直至根除“伊斯兰国”,不仅需要国际社会在物质层面加强国际反恐合作,更需要在思想和精神层面开展去极端主义的国际合作,在意识形态上揭露“伊斯兰国”对伊斯兰教的肆意曲解和滥用,捍卫伊斯兰文化和平、中道的核心价值观。2016年1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埃及,并在阿盟总部发表重要讲话,他明确指出中阿双方将“在中阿合作论坛框架内召开文明对话与去极端化圆桌会议,组织100名宗教界知名人士互访”(73),这无疑将对推进中阿文明对话,共同开展中阿去极端化合作产生深远影响。 注释: ①金宜久:《论当代伊斯兰主义》,载《西亚非洲》1995年第4期,第32页。 ②吴云贵:《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辨析》,载《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17页。 ③刘中民:《国际反恐形势进入新历史阶段》,载《文汇报》2015年11月15日。 ④相关的代表性成果主要包括:王晋:《“伊斯兰国”与恐怖主义的变形》,载《外交评论》2015年第2期,第138~156页;曾向红、陈亚州:《“伊斯兰国”的资源动员和策略选择》,载《国际展望》2015年第3期,第103~121页;王雷:《“伊斯兰国”组织兴起与中东政治变迁》,载《亚非纵横》2014年第6期,第1~14页;董漫远:《“伊斯兰国”的崛起和影响》,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5期,第51~61页;田文林:《“伊斯兰国”兴起与美国的中东战略》,载《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10期,第24~30页。 ⑤Eric Schmitt,"In Battle to Defang ISIS,U.S.Targets Its Psychology",The New York Times,28 December 2014. ⑥刘中民:前引文。 ⑦《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http://www.fmprc.gov.cn/ce/cohk/chn/xwdt/wsyw/t1331327.htm,2016-01-20。 ⑧朱威烈等:《中东反恐怖主义研究》,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第25页。 ⑨金宜久:《当代宗教与极端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22~423页。 ⑩同上书,第423~425页。 (11)同上书,第445页。 (12)朱威烈等:前引书,第191页。 (13)金宜久:前引书,第432页。 (14)金宜久:前引书,第413页。 (15)John L.Esposito,Unholy War:Terror in the Name of Isla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07. (16)金宜久:《“瓦哈比派”辨》,载李玉、陆庭恩:《中国与周边及“9·11”后的国际形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6页。 (17)Abroad Moussalli,"Wahhabism,Salafism and Islamism:Who is the Enemy?",January 30,2009,http://conflictsforum.org/briefings/Wahhabism-Salafism-and-Islamism.pdf,p.5,2015-12-30. (18)Cole Bunzel,"From Paper State to Caliphate:The Ideology of the Islamic State",The Brookings Project on U.S.Relations with the Islamic World,Analysis Paper,No.19,March 2015,p.8. (19)Sayyid Qutb,"Signposts along the Road",in Rocanne Euben,and Muhammad Qasim Zaman,eds.,Princeton Readings in Islamist Thought:Texts and Contexts from al-Banna to Bin Lade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pp.129-144. (20)Gerard Chaliand and Arnaud Blin eds.,The History of Terrorism,Translated by Edward Schneider,Kathryn Puler,and Jesse Browner,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p.287. (21)John L.Esposito,Unholy War:Terror in the Name of Isla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56. (22)Haim Malka,"Jihadi-Salafi Rebellion and the Crisis of Authority",in Jon B.Alterman ed.,Religious Radicalism after Arab Uprising,Washington DC: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2015,p.14. (23)阿泽姆1941年生于巴勒斯坦,后加入穆斯林兄弟会,在大马士革大学教法学院获学士学位。1968年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学习教法学,获博士学位。在埃及期间,受到赛义德·库特布的兄弟穆罕默德·库特布的影响,成为一个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者。20世纪60年代末,库特布和阿泽姆在沙特阿齐兹国王大学教书期间,在该校就读的本-拉登曾聆听他们讲授的课程。1979年,阿泽姆因立场激进被逐出沙特后前往巴基斯坦,开始通过著书普及和推广“圣战”思想。See Walter Laqueur,No End to War:Terror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2003,pp.50-51. (24)详尽论述参见刘中民:《伊斯兰的国际体系观》,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5期,第28~29页。 (25)Rohan Gunaratna,Inside Al Qaeda:Global Network of Terror,Berkley Books,2002,pp.30,115. (26)Haim Malka,op.cit.,pp.16-18. (27)Cole Bunzel,op.cit.,p.8. (28)详尽论述参见包澄章:《中东剧变以来的萨拉菲主义》,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年第6期,第106~118页;Roel Meijer,Global Salafism:Islam's New Religious Movemen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9. (29)Rüdiger Lohlker and Tamara Abu-Hamdeh eds.,Jihadi Thought and Ideology,Berlin:Loges Verlag,2014,pp.16-36. (30)Cole Bunzel,op.cit.,p.9. (31)Ibid.,p.10. (32)Ibid.,p.7. (33)Cole Bunzel,op.cit.,p.9. (34)Richard Mitchell,The Society of the Muslim Brother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p.235. (35)Graeme Wood,"What ISIS Really Wants",The Atlantic,March 2015,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5/03/what-isis-really-wants/384980/,2015-04-10. (36)Cole Bunzel,op.cit.,p.15. (37)Cole Bunzel,op.cit.,pp.18-19. (38)Ibid.,p.7. (39)Ibid.,p.24. (40)Ibid.,p.27. (41)Cole Bunzel,op.cit.,pp.25-26. (42)钱雪梅:《基地的“进化”:重新审视当代恐怖主义威胁》,载《外交评论》2015年第1期,第127页。 (43)Ayman Zawahiri,"General Guidelines for Jihad",http://azelin.files.worldpress.com/2013dr-ayman-al-e1ba93awc481hirc4ab-22gener-al-guidelines-for-the-work-of-a-jihc481dc4ab22-en.pdf,2015-12-30. (44)"Zawahiri's Letter to Zarqawi(English Translation)",July 2005,https://www.ctc.usma.edu/v2wp-content/uploads/2013/10/Zawahiris-Letter-to-Zarqawi-Translation.pdf,2015-12-15. (45)"ISIS:5 Things to Know about the Iraqi Jihadist Group",CBC News,June 24,2014,http://www.cbc.ca/news/world/isis-5-things-to-know-about-the-iraqi-jihadist-group-1.2684540,2015-06-30. (46)Joas Wagemakers,A Quietist Jihad:The Ideology of Abu Muhammad al-Maqdisi,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p.82-84. (47)Nibras Kazimi,"Zarqawi's Anti-Shia Legacy:Original or Borrowed?",Hudson Institute,November 1,2006,www.hudson.org/research/9908-zarqawi-s-anti-shia-legacy-original-or-borrowed-#BkMkToFoot2,2016-01-18. (48)Bernard Haykel,"Al-Qaida and Shiism",in Assaf Moghadam and Brian Fishman eds.,Fault Lines in Global Jihad,London:Routledge,2011,p.194. (49)Bernard Haykel,op.cit.. (50)Cole Bunzel,op.cit.,p.14. (51)Ibid. (52)Ibid.,p.38. (53)Graeme Wood,op.cit. (54)金宜久:前引书,第423页。 (55)Mohammad M.Hafez,"Tactics,Takfir and Anti-Muslim Violence",in Assaf Moghadan and Brian Fishman eds,Self-inflicted Wounds:Debates and Division in Al Qaeda and its Periphery,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West Point,2010,pp.19-44. (56)Cole Bunzel,op.cit.,p.39. (57)Ibid.,pp.38-39. (58)转引自李捷、杨恕:《“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叙事结构及其影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2期,第9页。 (59)Anthony N.Celso,Jihadist Organizational Failure and Regeneration:the Transcendental Role of Takfiri Violence,Paper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Political Studies Association Meeting,Manchester,April 14-16,2014,https://www.psa.ac.uk/sites/default/files/conference/papers/2014/PSU% 20 presentation.pdf,2015-11-14. (60)详尽论述参见吴冰冰:《圣战观念与当代伊斯兰恐怖主义》,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6年第1期,第36~41页。 (61)R.K.Pruthi,ed.,Encyclopedia of Jihad,Vol.1,New Delhi:Anmol Publications Pvt.Ltd.,1st ed.,2002,p.61. (62)See Sherman Jackson,"Jihad and the Modern World",Journal of Islamic Law and Culture,Vol.7,No.1,Spring/Summer,2002,pp.1-26. (63)Haim Malka,op.cit.,2015,p.12. (64)Sheikh Wahbeh Al-Zuhil,"Islam and International Law",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Volume 87,Number 858,June 2005,pp.282-283. (65)关于“圣战”历史演变的详尽论述参见刘中民:《伊斯兰的国际体系观》,第23~25页。 (66)安达卢斯是指中世纪阿拉伯和北非穆斯林统治下的伊比利亚半岛和塞蒂马尼亚,也指半岛被统治的711~1492年这段时期。这片区域后在基督教收复失地运动中被半岛上的基督徒所占领,今天西班牙南部的安达卢西亚因此得名。 (67)Cole Bunzel,op.cit.,p.39. (68)Cole Bunzel,op.cit.,p.10. (69)Haim Malka,op.cit.,p.11. (70)Joas Wagemakers,op.cit.,pp.82-84. (71)Haim Malka,op.cit.,pp.26-29. (72)转引自马明良:《伊斯兰教的和平观》,载《中国穆斯林》2004年第6期,第34页。 (73)习近平:《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载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122/c1024-28074930.html,2016-01-30。标签:扎卡维论文; 萨拉菲论文; 什叶派论文; 伊斯兰文化论文; 中国伊斯兰教论文; 古兰经论文; 中东局势论文; 逊尼派论文; 伊拉克战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