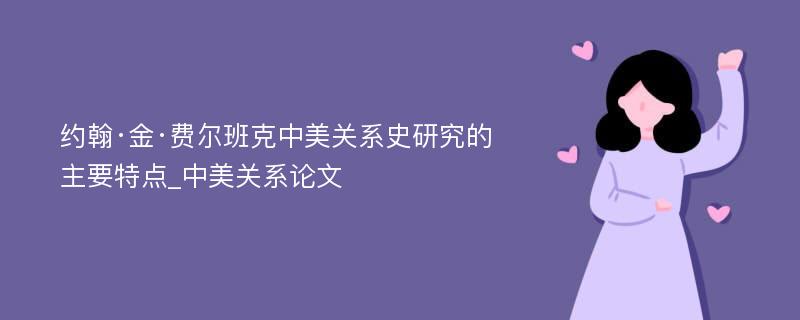
费正清中美关系史研究的主要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关系论文,主要特征论文,史研究论文,费正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是美国现代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开拓者、中国问题专家、对华政策的评论者。半个世纪以来,他对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中西关系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具有代表意义的学术成果,而他对于中美关系史进行的长期研究和探索,则更具特色。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对他在中美关系史研究领域中的治学态度和风格、治史原则和方法、学术主张和思想观点等,进行简要的分析和评论。
一、费正清在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中,力图做到反映历史真实情况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尊重历史事实是最起码的要求。作为中美关系史研究的专家,费正清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本着据实述评的态度敢于批判传统观点和当时的错误认识,在他所能达到的思想认识水平上,不断反思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学术主张,以力图达到客观地反映历史真实情况。
在中美关系史上,美国对华的侵略和扩张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但对于美国的历史学家来说,这并非容易解决的问题。而费正清在经历了中国革命、朝鲜战争和麦卡锡主义的冲击下,并在越南战争带来的大灾难的震撼下,思想认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越来越对美国过去在东亚的政策和行为持批评态度。这使他能从历史事实出发,改变长期以来美国学术界关于中美关系史不切实际的认识,直接了当地指出了美国对华关系中有扩张、侵略的一面。
他认为:美国是历史上最富扩张性的列强,它的扩张并不仅在于武器和商品,而且还在于技术、思想和社会文化价值观念〔1〕。他说过,美国的行为是总的西方帝国主义扩张行为的一部分,“美国向中国的扩张不仅是经济的、宗教的或民族主义的,而且是所有扩张性质的总和”〔2〕。他指出美国学术界有一种不足取的错误倾向,即把美国看成是帝国主义色彩不浓、更友好与更平等、而且还具有事业性和自主性的国家〔3〕。他毫无掩饰地说:“美国人是英国非正式帝国的小伙伴,但在英国的扩张过程中,有时也能起带头作用。”〔4〕他承认,作为西方文明侵略东方文明的一部分,美国人也继承了过去欧洲人在东亚进行侵略的各种遗产,包括英国的鸦片战争、贩卖苦力、炮舰外交和所有其它的东西,以及法国基督教徒好战的精神;因此,美国人不能只享有侵略果实而不接受这些侵略行动所带来的恶果,“同样要承认今天的罪恶,应消除我们无知的自尊感,接受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与生俱来的权力和罪恶的正常负担。”〔5〕费正清对于美国对华关系中这些尖锐的批评,对于端正美国人民的中美关系史观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在认真思考了中美关系史上这一重要原则问题的基础上,费正清对中美关系史上的门户开放政策和中美合作所事件等具体问题进行了比较符合史实的研究和分析。
费正清认为: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与19世纪末美国在海外的扩张和英国在中国统治地位的变化具有密切的联系,是美国向海外进行殖民扩张的必然结果。它把美国的理想主义和自身利益结合在一起,这是一项精心杰作。主张一切国家以机会均等的地位进行贸易,那是为了参加帝国主义争夺而在英国人放弃之后从他们那儿捡来的主张。他强调指出,“我们正在菲律宾实施帝国主义,与此同时,我们也在中国取代帝国主义。”〔6〕
他指出,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在1899年门户开放照会中,没有提到保证中国的领土完整,也没有限制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扩展。照会主要是关心保持中国的关税收入,保护外商在中国的利益,而不是中国的国家主权。只是到了俄国乘义和团事件之机开始占领满洲时,海约翰才在1900年的补充照会中提出中国领土完整的问题。这样,门户开放政策后来就发展成为两条主要原则,即“保护中国的完整以及一切外国人在中国都享有平等待遇”。但是,“说穿了,中国的完整这个原则只是一种策略,用来防止象俄国那样的其他国家攫取如满洲这样的中国领土而把我们排除在外”,“美国实际上无视中国的利益,而犯了大错”〔7〕。他认为,门户开放政策一方面“要求我们减少对中国人民的剥削”,另一方面又“试着去维护他们的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以至于我们在以后更易于对他们进行剥削”〔8〕。
在1982年出版的《回忆录》中,他对中美合作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提出了自己的评价。他认为,中美合作所确实部署过骚扰日军后方的行动,并为美国海军的登陆作了准备;但其弊端在于,当1945年国共内战爆发时,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他指出,“这就意味着美国‘过早地’正式加入了反对中共的活动”,这是美中合作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美国对华政策史上的一段丑闻〔9〕。他带有讽刺意味地说:“美国用以杀人的技术比用以改善人民生活的现代科技知识更快地输入中国。”〔10〕但是,费正清所了解的中美合作所的历史事实也是很有限的,他只是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如实地记录下来,而对于美蒋反动派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里犯下的监视、迫害、屠杀革命者和无辜百姓的滔天罪行,则没有进一步挖掘、揭露,使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够全面。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费正清是在经历了漫长而又痛苦的思想旅程之后,才好不容易得出了上述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因而他对中美关于历史遗产的清理是很不彻底的,在他的有关论述中,常常出现牴牾矛盾之处。
比如,他一方面承认美国在对华关系的历史上具有侵略扩张的性质,而在另一方面却否认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而且不赞成用帝国主义理论来分析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性质。
费正清说:“在我们心里深处,我们并不是帝国主义者。”〔11〕在现在来说,“帝国主义已接近于毫无意义的术语,因为它逐渐地几乎包含了所有西方与东亚联系的形式,是东亚人对东西方社会、文化冲突的一种感受。”〔12〕是“国家、社会甚至文化和文明之间广泛和全面的冲突”〔13〕。他所理解的“帝国主义”只相当于一种扩张或把它解释为殖民主义。他认为,“我们不像其他欧洲国家,在中国霸占一些区域作为自己的领地,而是坚持打开中美贸易门户的原则。我们执行‘我也要参与’的政策而没有去干名副其实的帝国主义,在1900年签订的开放条约中。我们主张‘中国的完整’的条款进一步说明我们没有受到帝国主义的污染。”〔14〕
费正清更愿意把美国对中国所进行的侵略活动和战争归结为强权政治,这就掩盖了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掠夺的经济根源,从根本上模糊了美国与中国之间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
这些互相矛盾的观点,大大削弱了他关于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客观性、真实性。力图做到反映历史真实情况,也只能作为他的一种追求罢了,由于种种条件的制约,费正清是不可能完全做到这一点的。
二、费正清站在美国政府的立场上,极力坚持从实际效果出发来评价美国对华政策,以最大限度地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原则
一般原则上说,国家利益是任何国家对外政策中最普遍最重要的因素。在世界政治中,国家利益原则成为判定和推断各国外交政策的尺度。美利坚民族以讲求实际著称于世,同时他们又非常重视信仰追求,因此,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矛盾地构成了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两个基本要素。从客观主义的立场来维护国家利益原则,就成为费正清评价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出发点。他正是运用这一原则,深刻剖析了40年代至50年代初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得失成败。
他首先对美国忽视中美文化关系的政策提出批评,认为发展这种关系才是美国长远利益的根本所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后,中美文化关系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仍未得到美国政府的足够重视,费正清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为了美国的长远利益,他尖锐地批评了政府这种短视的做法,极力呼吁美国政府重视对华文化关系,并积极参与对华文化交流的工作。
1942年12月4日,费正清从重庆向国务院政治顾问亨培克等人提交了一份论述中美文化关系的备忘录〔15〕,并称之为一份主张采取干预政策的文件。他反对美国对华文化关系规划始终只讲求采取何种手段,而不注意达到何种目的;只注意提供消息情报,而不提供反映社会道德准则的其它“文化媒介”,听凭美国生活方式自己去赢得销路。他强调指出,为了在两国之间建造一个共同的立场,“我们决不能反对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那是当地的需要,但我们同时也正在这里培养国际主义,这是对美国有利的”。费正清的这份备忘录没有得到亨培克等人的响应,这使他非常焦急。不久,他便把自己对这一问题思考的结果,再次写信给亨培克的助手希斯,一再呼吁为了美国的利益,必须支持和援助中国知识分子〔16〕。信中还提出了发展对华文化关系的具体计划,敦促美国政府官员尽快地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在信的最后他得出结论:“我们必需支持美国的权益,而不仅仅是为了保卫它们。在中国发展自由人应受的文科教育,就是一项美国的权益。”
基于以上认识,费正清在华为美国政府服务期间,一直将“援助”受美国文化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目标,并认为这一工作比对日作战更重要。他说:“就个人而论,我不反对抗日战争,只是认为抗战似乎并不比维护自由人应受的文科教育更加迫切。”〔17〕持这种观点的原因是,他觉得留美归国学生构成了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桥梁,正如他在前引给希斯的信中所说,“如果丧失他们,我们就将象我们面对俄国的处境一样,更加陷于一个不幸的局势之中。”
其次,费正清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政策进行抨击,认为这种政策违背了美国在华的根本利益。太平洋战争后期,随着世界局势和国共双方关系的不断变化,美国政府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逐步推行了一条扶蒋、限共、反共的反动政策,美国的对华政策在一步步地陷入国共内战的泥潭。赫尔利使华和马歇尔调处反映了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重要内容,费正清对此进行了抨击。
关于赫尔利使华,费正清认为:赫尔利坚决拥护全面支持蒋介石的政策是不明智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对双方人民都没有什么收益〔18〕。正如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说,赫尔利偏袒蒋介石“这个毫无必要而且愚蠢透顶的步骤把我们驱向了以冷战(反共产主义)作为外交政策问题‘解答’的窘境。于是,我们的伸缩余地更加小了,如果蒋介石在某日被击溃,我们势将被驱逐出中国,因为我们大多数人早已预见到蒋介石最后必然失败”〔19〕。他甚至说过,自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人就留下了对于中国采取愚蠢行动的30年纪录〔20〕,是美国的对华政策使其失去在中国的各种利益。
关于马歇尔调处,费正清认为其目的是为了调处即将爆发的内战,“在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这两个死敌间居中调停”〔21〕。马歇尔调处虽然在政治上失败了,但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加强了公开准备反共内战的国民党右派的力量,尽管马歇尔使华的最初目的不是要支持进行内战的国民党,但实际效果却与美国一贯的做法一样,在中国帮助国民党倒行逆施〔22〕。
除了对于赫尔利使华和马歇尔调处进行批评,费正清还分析了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破产及其根本原因。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在中国支持反对共产主义就是一场失败的战争。他说:“不管我们给蒋介石多少飞机和坦克,我们都无法把共产主义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抹掉。如果我们盲目反对革命,那么我们终将发现自己被群众运动赶出亚洲。”他指出,美国的对华政策实际上是容许邪恶势力破坏美国在中国培育的自由主义,而这正是美国的根本利益所在,在这里,美国陷入了自我矛盾,即使在战后的1946年,“我们仍在自我断送在华的机会”〔23〕。
再次,费正清反对美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遏制中国的政策,认为这种政策也难以实现美国在华的长远利益,随着中国革命胜利的到来,美国政府在短暂的观望之后,很快实行了一项不承认、孤立和遏制新中国的反共反华政策,这是美国遏制共产主义、进行全球扩张外交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战略方针指导下,美国朝野上下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出现了很大的偏差,如艾森豪威尔政府就认为,共产主义正在亚洲取得进展,而中国牌子的共产主义比苏联牌子的共产主义威胁更大〔24〕。费正清意识到美国政府的这种对华政策是错误的,为了澄清美国人民在中国问题上的错误认识,他进行了许多论证和解释工作。
1949年夏,费正清在哈佛大学举办的一次关于美国东亚政策的学术讨论会上指出,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也是一场社会革命,而不仅仅是一次夺权斗争或改朝换代;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共产主义是件好事,中共领导人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美国人应从中国革命中吸取教训。他认为,美国政府应改变与中共敌视的态度,停止支持蒋介石,更不要用美国军队去阻止中共解放台湾;应对中国新政权给予事实上的承认,在商业贸易和文化教育等方面与之保持联系〔25〕。60年代以后,费正清又曾指出,对中国的军事遏制必须同时进行建设性的接触,鼓励中国和平加入世界秩序中的外交、贸易、旅游、信息、裁军谈判、技术和文化交流〔26〕。总之,费正清极力主张美国政府应当正确认识中国的客观现实,从而制定出符合形势的对华政策,而遏制中国是难以实现美国在华长远利益的。
三、费正清的中美关系史研究贯穿着实用主义的功利原则,在研究工作中不懈追求对现实政治的指导价值
作为历史学家,费正清坚持研究中美关系和分析美国历史上对华政策的得失,主要目的在于为美国制定现实的对华政策和发展中美关系提供借鉴。他的“历史应有裨益于现实”和使“历史应成为对外政策的侍女”,将历史和政策适当紧密地结合起来的信念,在进行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实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费正清在中国问题研究的众多领域中,找到了一条指导现实社会的捷径——区域研究。他认为,长期以来美国的汉学研究只注重中国的语言和传统文化,对于近世以来的中国和中美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都未给予应有的重视,这种脱离现实的纯学术研究难以给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因此,他要求摆脱传统汉学的研究模式,在学术殿堂和现实世界之间架设一座认识的桥梁。他的代表作《美国与中国》一书,既是他从事区域研究的一项初步成果,也是他试图以学术研究影响现实政治的一个尝试。他自己曾经说过,他作此书的目的就是要让美国读者充分认识中国,从而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
在使“历史应成为对外政策的侍女”方面,费正清确实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如前所述,他几乎在每一个重要历史时期都发表时评文章或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他不厌其烦地论证实行现实主义对华政策的深刻原因、必要性以及所产生的良性后果,煞费苦心地劝诫美国政府接受他所提出的现实主义的对华政策方案。遗憾的是,这些理智的认识很快就被淹没在一片反共的歇斯底里之中了。
费正清不仅把自己的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紧密地结合起来,而且他对美国的学术界也寄予了同样的希望。50年代,由于麦卡锡主义的影响,中国问题专家不能正常地在现实政治中发挥作用,费正清对此感到忧心忡忡。面对这种状况,他对中国问题研究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作了一次深刻的检讨。他得出结论,如果要发挥中国问题专家在教育和外交政策方面的独特作用,就必须改变学术研究仅限于学术范围的状况,而应立足于中美关系和美国与东亚关系的现实,来开展具体的研究工作〔27〕。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国问题专家的自身价值。
60年代以后,费正清更加强调中美关系史研究与中美关系的发展二者是密切联系、相辅相成的。1968年,他在美国历史协会第83届年会上发表了题为《七十年代的任务》的主席演讲〔28〕,其中就反复重申了研究中美关系、美国与东亚关系的重要性。他说,“美国对中国以及中美关系的历史观,既可以帮助我们生存,也可以成为我们生存的障碍。”他主张,为了国家利益的实用主义动机和为了知识利益的人文主义动机,都应对中国历史和中美关系进行广泛的研究。直至1982年出版的《回忆录》中,他还有意识地强调,学术工作者应做出有助于国家利益的贡献。
费正清一贯主张学以致用,认为有价值的知识必须付诸实践,“不仅要提出一个伟大的思想,而且还要使它产生效用”〔29〕。这是无可厚非的,而且事实上越贴近历史事实的客观研究就越能对现实社会有指导作用。对费正清来说,他毕生从事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其主要课题也基本上是服务于美国政府的政治和外交政策的需要,因而他的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的联系过于密切,其学术观点也表现出明显的功利主义思想倾向,甚至为现实政治所左右,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有时为了迎合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需要,不惜曲解历史,变化观点来满足这种需要。这一思想倾向在费正清有关台湾问题的论述中表现得较为突出。
在台湾问题上,费正清的主要观点因不同的政治环境,在各个历史时期作了多次修改。
1949年前后,中国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费正清希望美国政府对台湾袖手不管,让中共去夺取台湾,对国民党只是继续提供经济援助而不给军援,“作为我们打算从中国脱身的一部分措施”〔30〕。
朝鲜战争的爆发使费正清的对台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他支持美国政府使用第七舰队保护台湾,并主张台湾独立,即“两个中国”的政策,他的理由是“北朝鲜的侵略导致我们派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巡逻,使该岛不致卷入战争,并防止来自大陆的攻击”〔31〕。他在《美国与中国》第二版中曾指出,美国应保证台湾的独立,台湾应“作为一个单独的国家,如果当地的人民独立的话”〔32〕。他认为,一个独立的台湾是1949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成果。
50年代末期,费正清的这些思想观点又发生了一次转变,他逐步从“两个中国”的立场改为“一中一台”。他提出用“自决和公民投票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采取中间的策略,与中共进行外交谈判,但谈判应有利于美国的利益,同时他又建议中共政府加入联全国〔33〕。
但是到了60年代,费正清又回到了台湾独立的立场。关于这一观点,他曾撰文指出解决中国问题方针之一是“要求台湾的独立得到认可”〔34〕。他认为,对于美国来说:“我们的目标是台湾独立的事实,而不在于名称”〔35〕,“美国的利益就是要保护台湾独立的实质”〔36〕。他进一步预测台湾的发展趋势,他指出:台湾的独立可称为“自治”,这种方式就是1915年以后被称之为事实上独立的西藏和蒙古自治那样。从历史发展来看,独立的西藏虽没有出现,但独立的外蒙却是存在的,因此,“自治”有两种历史发展趋势〔37〕。费正清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是不言而喻的。
到了70年代,费正清改变了他“一中一台”和“台湾独立”的主张,转而提出台湾应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的“自治区”,主张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处理台湾问题。在尼克松访华之前,费正清于1971年8月12日和1972年2月19日先后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有关台湾问题的文章,详细地论证了“北京统辖下的台北自治”的历史可行性。随后不久他又提出采取双重标准处理台湾问题,“对台北最根本的目标是维持现在这种经济政权的全岛的完整,而不是通过安全条约控制大陆”,而“对于北京,我们设想的主要目标是政治性的,或者人们所说的外交性的,……总之,创造一种局势,即声称台湾政权只不过是北京领导下的中国的一个省”〔38〕。他认为,“从历史上讲,台湾是中国滨海地区的一部分,它在政治上的发展大部分并不依赖大陆”,因此“在中国人的领土内,已经正常地存在了各种程度的自治,因此对于象台湾那样一个不同地区来说,实行某种程度的自治(地方政府)至少可能是讲得通的。”〔39〕
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经过长期的思想变化之后,费正清最终还是承认了应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但实际上他仍面临着无法解决的理论和现实的矛盾。他只好又提出了一个“大陆中国”和“海上中国”的所谓历史传统理论,用以解释当时美国政府所奉行的既承认“一个中国”但同时又与大陆和台湾打交道的双重对华政策的合理性。他说:“接受一个中国的理论,我们就不能不在形式上承认北京拥有台湾的主权。然而作为象中国人一样的现实主义者,我们应当承认近80年的历史事实,即台湾已经拥有一个分离的政权,不管怎样,我们可以称这个政权是自治的,并有无限期保存下去之势。……在主张‘一个中国’的形势下,平等地对待台湾也许对我们更合适。”〔40〕
从以上费正清所发表的有关台湾问题的各种思想观点来看,他只是在文字上作了一些修改,其实质内容却没有多大变化。在文字修改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两个绝对不变的原则:一是美国的利益,二是实用主义。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提出的有关台湾问题的思想主张,都是从冷酷理性出发,进行周密的利害计算的结果,既不涉及任何高远的理想或意识形态,也不夹杂一丝一毫的情感,更不是客观的历史事实的考证和研究。在这个问题上,他彻底地体现了美国实用主义的精神。
如上所述,费正清在中美关系史研究领域中有他自己的治史原则和方法,形成了他自己的治学风格,并提出了颇有见地的学术主张和思想观点。但是,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学者,他的有些看法与中国史家的认识是相去甚远的。如上文所提到的,他为帝国主义的扩张进行过辩护,曾一度主张台湾独立等等。另外,费正清的中美关系史研究也存在着一些无法克服的思想缺陷,他的有些学术观点甚至打上了某些殖民主义思想的烙印。比如他片面强调和夸大传教士在中美关系史上的客观作用,而很少谈或者避而不谈其主观目的和负面作用。
他认为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历史上是做了许多好事的,他们创办了医院和近代教育,并进行了一些改良活动,他们“所做的好事在许多方面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41〕。他们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是广泛和普遍存在的。“医药和医院的创建为近代中国医学的发展作了开拓性”〔42〕,教会教育培养了一批自由主义者,他们是“整整一代的改革者,许多人成为重建中国的领导者”〔43〕。
事实并非如此,大多数传教士也是殖民主义者,他们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是美国侵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830年美国派遣的第一个传教士裨治文秘密来到广州,直到1949年司徒雷登悄然离开南京的120年间,美国在华传教士同其他西方国家在华传教士一样,无不留下了许多帮助美国政府进行侵华活动的历史纪录。传教士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真正地要帮助中国进步,而是要对中国进行精神统治和培养代理人以便控制中国的发展。在他们为美国对外政策服务的同时,客观上也引进了西方的宗教和资本主义的文化知识,也培育了一批通晓西方文化的各方面人才。但这并不是他们的初衷,可以说,他们“完全是被卑鄙的利益驱使”,在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44〕。
费正清不可能看到这些,也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细致地分析和论证。但是他却用赞赏的口吻谈论传教士在中美关系史上所作出的“独特贡献”。他说:“论英雄,我们美国人不得不回顾那些不引人注目的开拓者,他们大多数是传教士,直到今天我们仍怀着他们当年的冲动向中国提供技术和灌输人权观念。”〔45〕在100多年的中美关系中,“我们传教士逐步获得了中国人的好感,包括……有限地宣扬美国自由梦想的美好未来。”〔46〕他特别希望传教士向中国提供技术和灌输人权观念的事业将能继续下去。
无论是费正清对传教士在中美关系史上客观作用的片面肯定,还是他对传教士所作所为的赞赏,都可以看出,他对于传教士所进行的这种“文化事业”是非常重视的,既体现了他只有中美文化关系才能更好地实现美国长远利益的思想观点,也反映了他思想深处残留的某些殖民主义思想。
所有这些无法克服的局限性,使费正清无法对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作出更加客观的分析和评价。
注释:
〔1〕〔5〕〔12〕〔18〕〔20〕〔38〕费正清:《认识中国:中美关系中的形象和政策》(China Perceived:Images and policies in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New york,1974)第97、95-96、99、14、14、137页。
〔2〕〔4〕〔7〕〔30〕〔31〕〔39〕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四版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20、220、220、223、256、338-339页。
〔3〕费正清:《十九世纪中叶的美国与中国》,见(美)欧内斯特·梅·小詹姆斯·汤姆逊主编《中美关系史论》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6页。
〔6〕《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上海)1991年版,第180-181页;并参看《美国与中国》第四版中译本有关章节。
〔8〕〔11〕〔13〕〔26〕〔34〕〔35〕〔36〕〔37〕〔41〕〔42〕〔43〕〔46〕费正清:《中国:人民的中央王国与美利坚合众国》(China:The People's Middie Kingdom and U·S·A Cambridge,Mass.1967)第112、110、78、143、54、63、78、79、51、135、135、51页。
〔9〕〔10〕〔15〕〔16〕〔17〕〔19〕〔21〕《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256-257、259、275-277、279-282、261、359、358页。
〔14〕〔40〕〔45〕费正清:《观察中国》(China Watch)中译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15、136、29页。
〔22〕〔23〕〔25〕陶文钊编选:《费正清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07-321、307-321、322-346页。
〔24〕杨生茂:《美国外交政策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1页。
〔27〕费正清:《歧义注:美国的亚洲研究》(A Note ofAmbiguity:Asian Studies in America.见The Journal of AsianStudies,V14,Nov,1959,No·1)
〔28〕见《现代史学的挑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9〕〔33〕(加)保罗·M·埃文斯:《费正清与美国人对近代中国的了解》(Paul·M·Evans,"John FairbanK and the American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a.Oxford,Backwell,1988)第6、184-187页。
〔32〕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二版中译本,第322页。
〔44〕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78-179页。
标签:中美关系论文; 费正清论文; 帝国主义论文; 美国与中国论文; 文化侵略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美国革命论文; 美国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政治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