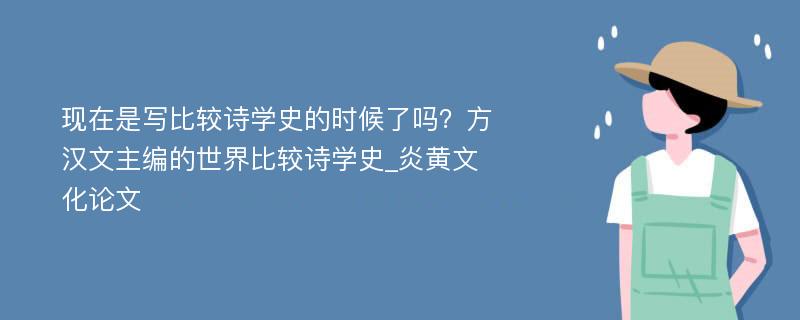
到了书写比较诗学史的时候吗?——评方汉文主编的《世界比较诗学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世界论文,方汉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比较诗学在目前国内比较文学界是一块充满活力的领域,有很多学校招收这个专业的研究生,也有很多优秀的论文和专著相继出版,但是,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我最近读到方汉文主编的《世界比较诗学史》,就标题而言,这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很有抱负的尝试——将世界各国的诗学理论进行汇总性研究,其封面上标明该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重大课题”,学术分量应该是很重的。但是读过之后,我们不得不很遗憾地指出该著是一次从材料到观点都完全失败的尝试。
一、比较诗学的三个领域
这部比较诗学史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通过比较诗学的途径完成一部大全性的世界诗学。作者在后记中说明:
本课题主要是对世界四大文学体系即中国、欧美、印度和阿拉伯—波斯以及它们的历史发展作出全面的比较研究。比较研究不同于一般的文学交流史,本课题以不同文化文学的差异和同一性为中心,从同一时期的历史特性和不同时代的演变过程的多维度上把握。从时限上将世界文学和文论史划分为史前、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五大阶段(公元前约10世纪至公元20世纪三千余年间)。对重要作家和理论家、重要流派、代表性著作进行了精当分析。重历史交流,也重美学分析。(方汉文主编《世界比较诗学史》,西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09页。以下引文凡出自该著者均只标注页码。)
从结构上说,该著试图将世界各国诗学分成四大版块和五大阶段,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遇到相当大的麻烦。比如,在四大版块之外有专章论日本古代诗学以及俄苏诗学,这就说明仅有四大版块还构不成世界诗学的整体,除了日本和俄苏之外还有很多民族拥有灿烂的文化,能忽略古希伯菜、非洲大陆吗?从时间分段来看,存在一种史前时期的文论史么?那是一种什么形态的文论呢?对此,该著并没有给予任何说明。实际上该著是将文论分为古代、中古、近代、现代以及当代五阶段,这也是通行的划分法,以此为框架,该著分别描述了六个版块即中国、欧美、印度、阿拉伯—波斯、日本和俄苏诗学的发展演化。此外,还有两章讨论中外诗学的相互交流即西方诗学与中国现代诗学以及俄苏诗学与中国现代诗学。在实际的论述过程中,该著基本上是对单一对象作一种静态的描述和分析,几乎看不到作者用一种全局性的世界性的诗学眼光来分辨这些民族诗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如果我们把分散在全书中的某一民族诗学抽取出来加以拼贴,实际上就成为这一民族的简明诗学史。比如,书中只有一章论日本诗学即“日本古代诗学”,完全可以把它抽取出来,而不会影响到该著的任何一部分;印度诗学有上古、中古和近现代三章,抽取出来可直接拼贴成印度诗学简史;中国诗学部分包括中国古代诗学的肇始、中国古代诗学、中国近代诗学以及“诗学交流”两章中的中国现代诗学四部分,也可抽取出来构成中国诗学简史;西方诗学包括古希腊雅典、中古以及“诗学交流”中的一点现代诗学及当代诗学,可拼贴成一本不全的西方诗学简史(因为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的诗学几乎没有论及)。这说明无论在宏观结构上还是微观论述上,全书只是在独立地、分别论述各民族的诗学,除了二章论中外诗学的相互交流外,几乎看不到任何“比较”诗学的印迹,更不必说什么“世界”诗学的印迹了。总之,与已有的大量国别诗学史、文论史相比较,它没有什么区别性的特征,也缺乏特殊的学术价值。即便把这部著作仅仅按照国别诗学来看,它也因其在材料、知识和观点上的欠缺甚至不准确而缺乏参考价值。
该著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一个明晰的比较诗学和世界诗学的理念。不明确“比较诗学”和“世界诗学”这两个概念就不可能写出比较诗学史或世界诗学史。美国学者迈纳(Earl Miner)在《比较诗学》里对“比较诗学”有一个朴素的认识:“一个学术领域,就像一个家族,对其界定可从整体特征着眼,也可从具体组成部分入手。比较诗学兼属诗学与比较文学两大家族。像其他跨文化研究一样,是个新生事物,方兴未艾。”① 比较诗学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来自于诗学和比较文学的嫁接。比较文学是从比较的、汇通的视域对各种文学现象的研究,诗学则是从综合的、理论的层面对各种文学现象的研究;比较诗学也采用比较的和汇通的视域,其对象则限制在诗学即文学的理论层面。比较文学的所有原则可以直接运用到比较诗学上来。比较诗学不是诗学的比较,而是理论问题的汇通研究。比较文学大致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以及跨学科研究三个领域,比较诗学也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领域:1.对理论的跨文化的事实关系研究,包括对一国理论对他国文学和理论的影响研究,即“理论旅行”的研究以及诗学翻译研究。我们不妨以“国际诗学关系史”来命名这个领域,如考察别林斯基对黑格尔美学的运用、佛教对中国诗学的影响等。2.对理论的跨文化的平行研究。这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国别诗学之间的差异、类同等关系的研究,如明确提倡比较诗学研究的艾田伯所从事的“总体文学”② 研究,钱钟书的跨文化、跨文类的诗学研究,以及迈纳基于三大文类的比较诗学研究等等,他们都是围绕着某个问题进行的汇通研究,而不是机械地将不同文化中的诗学概念作比较,因为诗学比较不是比较诗学,比较只是一种方法而已。3.跨学科的理论研究。20世纪以来文学研究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理论”的崛起③,传统的文学批评被各种新兴的“理论”击退,精神分析、符号学、性学、艺术史、政治学、人类学、自然科学等给文学研究提供了无数的概念和思想,启迪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引用马克思、弗雷泽、弗洛伊德、索绪尔、海德格尔、德里达、拉康等人的著作成为文学研究的时尚,要想从性质上给这些理论一个统一的界定几乎是不可能的。卡勒认为,这些理论就是一长串不同国籍的人名书写的一系列性质各异、学科不同的著作,使这些著作成为“理论”的惟一因素是它们具有跨学科的能力,“称为理论的作品具有超出自身领域的影响力”④。这些理论不仅跨越学科的界限,而且也总是不带护照做跨国旅行,当这些理论的影响力在文学领域发生效用时,就产生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理论”。这些概念和思想都是跨学科、跨国界的“理论旅行”的结果,因此,我们将其称为“比较诗学”也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今天就是用它们提供给我们的种种概念谈论文学,我们不可能仍然停留在“模仿”与“表现”、“言志”与“缘情”等古典概念的层面谈论文学,今天流通的文学理论本身就是具有世界性的文学理论。跨文化的比较诗学研究必须以今天的理论视域去把握国别诗学、民族诗学,进行解释学的视域融合,进而形成有解释力的可流通的诗学观念,最终汇入多元化的流动性的世界诗学的潮流中。
今天的比较诗学研究基本上分布在国际诗学关系史、跨文化诗学研究以及跨学科的“理论”研究这三个领域,而最重要的是最后一个领域,因为这是目前正在全球流通的诗学,人们在谈论它们、使用它们、修正它们,是最有解释力的诗学,也就是实际意义上的世界诗学。
《世界比较诗学史》所欠缺的正是这种世界诗学的眼光,它所谓的“世界诗学”只是数量意义上的总体诗学,没有实质意义。该著通篇未见国别诗学之间的互文性以及统摄国别诗学的世界性,没有关系,没有比较,没有汇通,没有融合。该著真正具有比较诗学特色的只有两章:“欧洲诗学与中国现代诗学”以及“俄苏诗学与中国现代诗学”。可是,国际诗学关系史是世界各个民族诗学长时段、全方位的互动,作为一部号称全面的世界比较诗学史是应该给读者提供一幅全面、清晰的路线图,绝不能仅仅局限在现代中国和欧洲以及俄苏诗学这两小块,而且,撰写一部世界诗学史首先要具备的是一种国际眼光、全球视域,应该平等公正地看待世界各国诗学,不应该处处体现出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立场。韦勒克的《现代文学批评史》虽然话题局限于欧洲范围之内,但是,读者看不出他的民族身份,他一视同仁地研究了现代欧洲各国的文学思想。
二、材料与知识的失误
该著在文献使用方面存在着更为严重的问题,很大篇章在材料方面连一般论文的基本要求都没达到。先看这一段:
“诗学”的胚芽在“诗”中!卫姆塞特·布鲁克斯以荷马史诗为例说过这样话:“自始以来的诗人,多喜欢谈论自己的作品,把文学见解写入自己的诗篇,所以,人类自有了诗歌,雏形的文学理论便相偕出现。”(第4页)
作者脚注如下:“[美]卫姆塞特·布鲁克斯:《西洋文学批评史》,转引自蒲友俊:《中国文学批评史论·先秦——魏晋南北朝卷》,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4页。”一句出自英语文献的直接引文,作者不但不参考英文原著,甚至不参考汉语译本,而是转引自一部中国学者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著作。这种转引再转引的情况通篇都是。
再看该著如何引用朗吉努斯《论崇高》一文(第141—145页)。作者使用的引文主要来自《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同时还转引自鲍桑葵的《美学史》、拉曼·塞尔登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上卷)等三本著作。短短五页文字,同一个文本,却使用了多种译本,五花八门,却不加任何说明。作者究竟是出于什么理由不引用同一个译本呢?何况,朗吉努斯《论崇高》一文的英文版十分容易找到,作者为什么不能对照英文统一译文呢?在同一章节里,本来是同一个概念,作者却不使用统一的名称,比如在论柏拉图一节里随处出现的关键词“理念”,作者随意使用“真形”(第25、28、34页)、理式”(第32、34页)、“形”(第25、34页)、“理性”(第27页)等多种名称,这些名称出现的时候又不加解释,读者怎么知道论述对象其实是同一个“idea”呢 ⑤?我们知道这个希腊词语是从动词的“观看”演化到“外表”,再成为柏拉图哲学中事物的“形式”的。汉语里也有几种译法,除了最流通的译名“理念”外,还有朱光潜的“理式”、罗念生的“原型”和陈康的“相”等译名。作者应该在仔细审辨之后选择一个译名贯穿始终,做到思路清晰,合乎逻辑。
作者不看原著,因此难免出错,比如:
正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这些剧作家暗示着一种把文学区别为独立性活动的努力,这种独立性活动实际上已经在其写作实践中形成了一种含蓄的诗学。”(第20页)
针对这个引文,作者提供了如下脚注:“[美]厄尔·迈纳:《比较诗学》,王宇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这段引文实际上在该书中译本的第18页,而不是第17页,原文也只是说“亚氏在其题名为《诗学》的著作中提到,这些剧作家……”,这段话根本不是对亚氏《诗学》的直接引用,熟悉《诗学》的读者应该知道迈纳这段文字的出处见《诗学》第一章。可见,作者在论述亚里士多德是没有好好阅读过《诗学》的,且看作者在另一处对亚里士多德的引用:
亚里士多德说:“与其说诗人需带几分疯狂,不如说诗人必须有天才,因为前者容易入迷,而后者则很灵敏。”(第22页)
注释中这段话不是引自原著,而是“转引自[法]塔塔科维兹:《古代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10页”,并且把被转引作者的国籍从波兰改为法国。类似情况很多。再看论托多罗夫的同一段落里的两处引文:
他将历史上对文学的功能与意义的认识归结为两种:“第一种是将文学作品本身视为认识的对象;第二种则认为每一部个别作品都是某种抽象结构的具体表现。”
正如托多罗夫所言:“诗学的客体并不是经验事实的总体(文学作品),而是一种抽象的结构(文学)。”(第387页)
两段引文,作者给出的注释分别是:“Tzvetan Todorov,Poétique,Seuil,1968,p.15.”和“[法]托多罗夫:《结构主义诗学》,转引自方珊:《形式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版,第258页。”作者确实查阅该书的法文原版了吗?显然没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两句引文其实是原作者的同一句话,只不过是两种不同翻译罢了,殊不知托多罗夫《诗学》的第一部分就是“结构主义诗学”!赵毅衡编选的《符号学文学论文集》里有这本小册子的完整译文,其中这句话译作:“有两种态度需要一开始就加以区别。第一种态度将文学作品视为最终目的;第二种态度则将各部著作看成是‘他物’的体现。”⑥
作者对文献的不熟悉,也会导致知识和观点上的错误:
巴特的《写作的零度》主要是为了体现他的符号学思想,他的这篇成名作就选自《符号学原理》一书。实际上,巴特的符号学理论早在《神话学》一书中就已经体现出来了。(第391页)
小小一段文字,错误迭出。首先是材料方面的错误,《写作的零度》出版于1953年,《符号学原理》出版于1964年,《神话学》出版于1957年,作者仅凭中译本《写作的零度》收录在《符号学原理》一书中,就说它选自《符号学原理》;然后是知识方面的错误,既然说巴特的符号学理论早在《神话学》一书中就已经体现出了,而最早的成名作《写作的零度》怎么可能又“主要是为了体现他的符号学思想”呢?事实上,《写作的零度》和《神话学》都属于巴特的早期作品,作者本人在《罗兰·巴特论罗兰·巴特》中说过他这一阶段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化的,主要致力于揭露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欺骗性,符号学思想在《写作的零度》中未出现,在《神话学》的主体部分也未出现。《神话学》一书收入55篇文章,前面54篇文章都是具体现象分析,最后一篇理论文章,题为《今天的神话》,是为了将前面的报刊文章整合在一起,给予理论的提升而写作的。传记作家路易—让·卡尔韦说得很清楚:“这篇文章延续了他在亚历山大时与格雷马斯的讨论,标志着他就像入教一样进入了符号学。但后记之前的54篇文章则属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类型,它们是随着1952至1956年间时事的发展写成的。”⑦ 可见,符号学思想进入罗兰·巴特的写作是从1956年的这篇《今天的神话》开始的,是在格雷马斯帮助下发现了索绪尔和叶姆斯列夫的“符号”、“外延”、“内涵”等概念后才开始的,正是从这篇文章开始,罗兰·巴特从“神话学家”的身份过渡到了“符号学家”的身份。
总之,全书在文献的使用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原始材料极度缺乏,大量使用第二手乃至第三手资料。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翻检一下行文中的注释和每一章后的参考文献,中国诗学部分文献的使用很随意,大都是市面上通俗的版本,新的研究成果大都阙如。外文材料的使用尤其罕见:古希腊雅典诗学部分的参考文献(第67页)没有一条外文材料,上古印度诗学部分(第84页)、中古西方诗学部分(第157页)、阿拉伯—波斯部分(第192页)、印度近现代诗学部分(第282页)、欧美诗学与中国现代诗学部分(第327页)都不见一条外文材料,俄苏诗学与中国现代诗学部分(第356页)有三条俄文参考文献,现代西方诗学部分的参考文献(第405页)也仅见三条,都是关于英伽登的三条英文材料,全书只有日本古代诗学部分的注释和参考文献(第231页)大量直接使用了日文材料,应该是惟一的亮点了。
该著对西方诗学的论述分为古希腊雅典诗学、中古西方诗学、当代西方诗学,可是,我不明白既然是“世界诗学史”,为什么要忽略西方文艺复兴至19世纪末这五百余年的诗学思想呢?新的模仿论,维柯的“新科学”,浪漫主义的主体论、表现论,现代市民剧理论,德国古典诗学,叔本华、尼采的艺术论等等,真的不重要吗?我们看看没有这一段的知识会犯什么样的错误。该著对西方当代诗学有三个概括,其中一个叫“反传统”:
首先是反传统。西方诗学在20世纪一改古希腊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传统研究理路,从研究作品的情节,转向作者本人,之后又转向文本、读者。如表现主义诗学对作者情感的描述,认为艺术即情感、即表现;精神分析诗学注重对创作心理的研究。它们都是反传统的。(第358页)
阿布拉姆斯的《镜与灯》对西方近代诗学做了精辟的分析和概括,其中对“灯”式的浪漫诗学(包括康德、谢林等德国美学以及英国浪漫主义思想)论述甚详。西方传统诗学在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镜”式摹仿诗学外还有这一时段的“灯”式表现诗学,20世纪初的表现主义是对后一传统的继承,怎么能够说是反传统的呢?而弗洛伊德开创的心理分析学派更不能大而化之地概括为情感论、表现论的诗学。
在具体论述中,该著也有相当多的遗漏。比如当代西方诗学部分,虽然时间只有短短的一百年,但是新论层出不穷,相互竞争也相互渗透,组织起来的确很棘手,一般以时间和学派为线索,也有以各种论题与辩论(issues and debates)的方式为线索的,如卡勒的做法⑧。不管什么线索,重要的思想和人物应该得到尊重。德里达的解构思想颠覆了西方整个形而上学思想传统,女性主义彻底改变了西方诗学的面貌,后殖民主义也重新改写了近代以来的人类知识图景,上述这些重要思想在一本通论性的世界诗学中是绝对不应该缺失的,那作者是出于什么考虑认为它们应该在他的著作中“失语”呢?
三、缺乏新观点造成的失语
在具体论述时我们没有看出该著采取了什么独特的视角,有什么独到的观点。如果没有什么独到的观点,至少也应该有新的材料补充旧论,或者以新的方式展开论述,可是,我们都见不到,见到的是十分陈旧的二、三手材料以及到处都能见到的常识性观点,而作者自己概括的一些观点又没有建立在详尽的材料分析上,大都是一些似是而非、大而无当的意见。以对詹姆逊的论述为例,作者先在“西方20世纪诗学概要”里对詹姆逊做了一个提要式说明:
以詹姆逊为代表的后现代理论家们,将目光投向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对当下的资本主义自身矛盾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与揭露,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立场,形成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文化诗学,用文化批判的视角审视当代社会。(第359页)
这段文字很含混,哪些人物是“后现代理论家们”?又有哪些人物是“以詹姆逊为代表的后现代理论家们”?他们都“将目光投向了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吗?他们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立场”吗?作者没有任何交代,而事实上其中的很多论断都是不成立的。
在具体论述詹姆逊的文字部分,作者提供了两小段宏观描述,先看第一小段:
他批评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研究组织构成而非内容,认为形式在解释面前实际上易于不知不觉地滑入内容,而不需要解释的情况本身就是一个亟待解释的事实。这样他就将对艺术的评论带向了后现代视阈。(第403页)
为什么说“形式”滑入“内容”,“不需要解释的情况本身就是一个亟待解释的事实”,“这样”,詹姆逊就将他“对艺术的评论带向了后现代视阈”呢?这个因果关系太强硬,没有任何说明、论证。我们知道对解释的追求是一种本质主义的主张,它预设了现象与本质的区分,正如德里达在《书写与差异》中所说:“一种解释追求解谜,梦想破译逃避符号游戏与秩序的真理与本源,视生存为一种流放而去经历解释的必要性。”⑨ 这种对解释的渴望构成了詹姆逊所谓的“现代主义文化”的基本特征,他称之为四种“深度模式”⑩。这怎么能是“后现代视阈”呢?后现代追求的恰恰是一种逃避真理与本源的符号游戏,用苏珊·桑塔格的话说就是“反对解释”。
再看第二小段:
詹姆逊强调后现代主义划分的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后现代主义是诸多风格中的一种,另一种则试图把后现代主义当成后期资本主义逻辑的文化的主导因素来理解。因此,他的后现代理论关注多元,关注当代社会文化现象,是一种文化诗学。(第403页)
这里的因果关系也十分突兀强硬,解释不通。为什么他强调后现代主义划分的两种观点就“因此”能推断出他的理论是一种“文化诗学”呢?什么是文化诗学?是不是凡是关注多元、关注当代社会文化现象的理论都是文化诗学呢?即便我们姑且承认这是一种文化诗学,又能说明什么问题,能帮助我们认识这种理论的什么方面呢?显然,作者的思路始终在词语的表面流转,根本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
最后再看看作者论述詹姆逊最关键的一段长文,这段文字告诉我们詹姆逊的思想核心就是他做出的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三个文化/社会历史阶段的划分,对此,作者先用五行文字做了概述,然后先后引用了两段文字做论述:
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他对后现代的特征作了经典概括:“新的无深度感,它在当代‘理论’和一个全新的形象文化或幻象文化中得到了延续;随之而产生的历史感的衰弱,不仅是指我们与公众历史的关系,而且关乎我们个人的时间感的新形式,这种时间感的‘精神分裂症’结构将决定时间型艺术的新型句法。”(第403页)
作者注明,以上引文出自王岳川等编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一书,该书出版于1992年,被收录其中的詹姆逊的这篇文章仅是“摘译”,这篇摘译存在不少问题。作者引用时不查看英文原文,至少也应该使用比较可靠的译本,比如张旭东1997年编译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也是很容易找到的本子。问题更严重的是这段引文并不完整,原文在“新型句法”后是一个分号,詹姆逊接着还谈到了后现代的情感、技术以及空间性三方面的特征,作者切掉了原作者分号之后的一半文字,可是,一段不完整的引文是不可能对后现代的特征做出什么“经典概括”的。作者自己大概也意识到这段引文说服力不够,于是,隔了两行又补充了如下一段间接引文:
80年代以来,他将注意力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后现代文化研究。他从七个方面对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概括:呈现审美通俗化和审美民众主义;消解深度模式,走向平面化;放逐主体性,趋向零散化;丧失个人风格,导致“拼贴杂凑”;抹去历史性,引向虚假历史意象的“复制”;抛弃关于未来的思考,崇尚形象的文化形式;取消批评附丽,陷于无法辨识的后现代文化空间中。(第403—404页)
作者注明这段文字参见蒋孔阳等主编的《西方美学通史》。在这段引文之后,作者只用一句话便结束了对詹姆逊的论述:“他坚持认为对后现代文化应该持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立场,他的理论因而也成了一种典型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诗学理论。”
两段文字,一段转引自《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一书摘译的詹姆逊本人的句子,一段间接引自《西方美学通史》一书对詹姆逊理论的概述,两段文字就这样拼接在一起,可是,二者之间根本就不存在时间的或逻辑的递进关系,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越来越”,因为这两段文字的内容都出自原作者的同一篇文章!作为一章的主体部分,作者应该有比较清晰的观点和基本流畅的论证,但是我们读到的是什么呢?各种引文的拼贴,基本以引用代替论述,然后点缀几句标语式的结论!
不仅对詹姆逊的“论述”如此,通读该著西方诗学的全部章节,大都存在严重问题,而且缺乏新的观点,基本上都是质量不合格的综述而已。作者对原始材料如此不重视,对新的研究成果更是置若罔闻,怎么可能有任何新观点或独到的见解呢?即便有任何独到见解,如此使用和组织材料,作者也无法合乎逻辑地展开论述。
这本《世界比较诗学史》是一次失败的尝试,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换个角度看,现在还不到写作世界性的诗学史的时候,韦勒克再生或许也写不出来,一个学者甚至一个团队的外语水平、材料功夫,以及比较诗学、世界诗学的观念都尚未成熟,很难去贸然尝试大而全的诗学史。其实,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也曾尝试过诗学史的写作。上个世纪末,让·贝西埃等人在学会的组织下主编了一部大部头的《诗学史》,该书明确限制在西方文化范围内,按照时间线索细致地分析了西方古代、中世纪、16世纪、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的诗学发展状况,最后回到20世纪诗学这个平台上,最后一部分,也只有这部分是按照诗学问题为线索组织的,围绕文本的生产、组织和接受等问题进行了汇通性的描述和分析,具有鲜明的比较诗学特色。作者在前言中说“拙著带有明显的比较色彩,但是却不想勾勒导致此种诗学建立的民族间的影响史和关系史。它仅介绍民族间背景和语言间背景基础上的西方主要诗学概况,并注意把拟定普遍性问题的愿望与对答案的相对性的清醒意识结合起来”(11)。借助国际性的大组织也没能写出一部世界性的诗学史来,这说明比较诗学事业任重道远,还需要更多的文化积累,现在要做的是局部性的、专题性的汇通研究。
那么,我们的作者为什么还要冒险尝试这样的鸿篇巨制呢?我们的学术体制为什么特别愿意支持、鼓励、肯定和奖励这样看似宏大的课题呢?该著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重大课题“东方与西方:文学的交流和影响”和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外比较文论和批评的历史阶段与类型学研究”的最终成果之一”(第407页),这是该著封面以及该著主编在后记中严肃、郑重的声明。这不值得我们深思吗?该著后记中还说,这项成果“历时四年之久”,期间组织了各种讨论、会议、报道等等,它是全体参与和关心这项课题的学者的“共同成功”(第406页)。可是,它的“成功”究竟表现在哪里呢?应该由谁来评判它的成功与失败呢?
在该著的前言里,主编也向读者提出了一个问题:“有什么理由不使具有伟大文明传统的中国学术走向世界呢?”(“前言”,第5页)这些激昂的文字表达了一个良好意愿,这也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当代中国学人的迫切希望:在世界学术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可是,很遗憾,从该著的正文中我们究竟听到了些什么样的声音呢?难道不是一些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失真的回声吗?依靠这些转引的文字和宛转的回声,中国学术真的能够走向世界吗?我相信,有解释力的理论话语是没有国界的,有解释力才能流通世界。与其为摆脱“失语”的焦虑而发出大而无当的声音,不如先耕作好自己的小片园地,是好果子自然会流通到世界市场的。
注释:
① Earl Miner,Comparative Poetic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p.238;中译文见迈纳《比较诗学》,王宇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2页。
② “la littérature générale”,译为“一般文学”更准确。
③④⑧ Jonathan Culler,Literary Theory: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1,p.3,p.121.
⑤ 文中有几处甚至只标注其拉丁语转写形式“eidos”,而不同时标注其西文的一般译名“idea”。
⑥ 赵毅衡编选《符号学文学论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86-187页。
⑦ 路易—让·卡尔韦:《结构与符号——罗兰·巴尔特传》,车槿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5页。
⑨ Derrida,Writing and Difference,trans.A.Bass,Routledge & Kegan Paul,1978,p.369.
⑩ 参见《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弗·杰姆逊教授讲演录》,唐小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0—162页。
(11) 让·贝西埃、伊·库什纳等主编《诗学史》,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标签: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诗学论文; 文学论文; 符号学原理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写作的零度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读书论文; 符号学论文; 后现代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