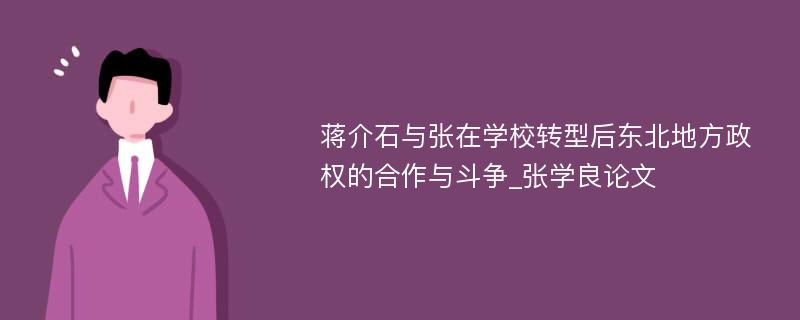
易帜后蒋张在东北地方政权上的合作与争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争斗论文,政权论文,地方论文,后蒋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06)05—0016—04
东北易帜后到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东北地方政权与蒋介石南京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独具特色的一个方面。东北易帜仅从原则上确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与东北的关系,至于东北地区未来在全国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及其中央化的过程,则要取决于张学良集团和蒋介石集团关系的进一步演变。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来说,当然不满足于形式上的统一,而是要逐步把东北真正纳入其统治之下;从张学良和东北集团方面看,则是要在南京国民政府统一之名下,尽可能保持东北的地方独立性。二者根本目的的歧异,决定了双方在关乎东北前途命运的政权问题上,既有合作、妥协,又有分歧、对抗。本文试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蒋介石南京政府对东北地方政权的渗透和妥协
在东北易帜时,蒋介石南京政府曾向张学良东北集团允诺:(1)南京拟在东北所设的政治委员会,应指派学良为主任委员。(2)国民革命军队伍不进入东北。(3)南京不干涉东北军政。(4)南京不在东北设宣传单位的分支机构。(5 )热河省划进东北,成为东北四省[1](P52)。但东北易帜后,蒋介石南京政府并没有忠实地履行上述对东北内政不予干涉的承诺,而是推行“统一”政策,对东北地方政权多方渗透和控制,同时,囿于当时的国内局势,又只能是适可而止。
首先,对东北地方政权的机构方面。1929年1月7日正式成立的东北政务委员会,是易帜谈判时双方妥协的产物,它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全权领导易帜后的东北四省,是易帜后东北的最高行政指导及监督机关,也是东北最高决策中心。由委员15人组成,内设总务、机要、政务、财务、蒙旗五处。其暂行条例规定,该会对中央未经明确规定的事项,在不抵触有关法令范围内,有因地因时制宜的权力,如遇紧急事变,得依出席委员三分之二决定,做成紧急处分办法[2]。可见,它每存在一天,就都意味着南京对东北的统治权是名义上的。
为此,1930年2月,南京政府标榜“军民分治”,决定撤销东北政务委员会,“所有省政府职权,完全归中央管辖”[2], 只是由于东北当局的坚决抵制才未能实现。但是,南京随后将其内辖的东北交通委员会划出,改隶国民政府,以分割和缩小其权力。1931年初,南京政府又修改了东北交通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东北路务办法:“东北各路联运帐目,铁道部随时可以调阅,东北各路联运会议由铁道部召集”[2],插手东北交通管理。
对于东北集团以“保障民权”为名,在易帜前夕设立的最高法院东北分院,由于东北集团自行规定该院具有终审权[3],使蒋介石南京政府深感这是东北“越俎代庖,分割中央司法权”[2],1929年1月22日电令取消,谓:“国家已经统一,各省政府均须一致。中央已经设置最高法院,处理全国民刑讼案,东北何得独外,东北设置最高法院东北分院之举,有碍统一,应立即取消,以符法制,将来东省民刑上诉案件,即为中央最高法院办理”[2]。随后,又电令张学良:“查法院组织法,本无最高分法院之设”,应即取消。否则不予承认[2]。因东北的坚持而未果。其后又对东北分院加以限制,即:自1929年3月1日以后不准再理民刑新案,否则,概作无效,至3月1日以前所受理各案也要赶期结束,嗣后各案即为最高法院办理[2]。
其次,对东北地方政权的体制方面。东北易帜后,南京政府不断要求东北在政权体制方面要与关内一致。在机构体制方面,实行省、县两级制。在官吏体制方面,对官吏的任免、考核、奖惩、官阶以及名称等,均做严格要求。如1931年3月, 南京政府颁布政令,规定:“(一)省政府以及大小各行政机关文官制官规,均须遵院部所定之章则办理。(二)各行政机关,对于所属人员,应实行功过之考核,以定奖惩。(三)省政部,应速筹办行政人员训练所,并将办理情形,尅日具报。(四)省厅对于公务人员叙奉,务须依照新旧奉给条例,不得超过定级数,考核法规定实行以前,每人进级只一次为限,不准冒滥”[2]。
再次,对东北地方政权的人事权方面。东北易帜前,蒋介石南京政府允诺不干涉东北的用人行政。易帜后,基本上是如此,发布的对东北政务委员会及各省政府的人事任命令不过是形式,但也不是一点变化没有。如在东北政务委员会15名委员中,加入了南京方面的何成浚、方本仁,就是最好的例证。何成浚系老同盟会会员,1925年起即跟随蒋介石左右,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参军长。方本仁曾任国民革命军第11军军长等职,1926年起深得蒋介石的信任,以其个人代表身份先后到北京、山西、沈阳、接洽主要政务。这一变化至少说明,在东北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已非清一色东北集团的人了。
当然,蒋介石集团在中央统治权面临严重挑战的岁月里,对东北地方政权的渗透、控制也只能是逐步的,甚至是试探性的,张学良东北集团强有力的抵制,使南京不得不迁就妥协,东北政务委员会和最高法院东北分院的保留即是明证。1930年2月1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决议,同意东北的请求,保留最高法院东北分院。10月,南京和东北商定待大局完全稳定,各省实行军民分治后撤销政务委员会,1931年初,南京又决定“时局尚未完全底定,加以北方善后诸多繁重,东北政委会决计保留,俟时局大定,军民分治后再行撤销”[2]。
二、张学良东北集团对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合作与抵制
张学良东北当局对蒋介石南京政府在东北地方政权上的“统一”政策,一方面,在表面和直接问题上适应这种“统一”,对东北地方政权进行了某些改革,在体制上与南京趋于一致;另一方面,在实质性和根本问题上,则将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对南京的渗透、控制予以防范和抵制,并伺机加以扩展。张学良东北集团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表示与南京合作,对东北各级政府的机构、体制及名称作了一定的改革,以适应南京的体制。在行政方面,裁撤道,实行省、县两级制,四省委员6至11人不等,一般内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四厅及秘书、公安二处。县亦大同小异,并将原县知事改称县长。废止省议会,“所有文卷全交省政府保存,议员由省政府酌量位置”[4](P109)。省议会是北洋政府时期省级政权机构的组成部分,作为省立法机关,对省政的运行起到规范和监督作用,当张氏父子和中央闹独立时,在形式上用它决定东北大事。将其取消,意味着服从统一。在司法方面,1929年初,张学良通令各级司法机关:“统一已成,政治及应划一……所有各级司法机关应即改称法院,其长官亦即改称院长”,今后各省区审理民刑案件要“遵用国府新发,以正统一”[4](P73、P76)。此外还令东北各级机关人员一律着中山装等等。
但是,在由谁掌握东北地方政权这一根本问题上,张学良东北集团则毫不含糊,与蒋介石南京政府公开争斗,以使东北地方政权牢固掌握在自己手中。
其一,牢牢控制人事权是掌握东北地方政权的根本所在。在张学良看来,东北地方政权即东北各级政府的官吏必须由东北集团的人担任。东北与南京易帜谈判时所提的条件之一就是:“内政仍由现职各员维持,概不更动”[5](P156),“政治分会及省政府人选概由张开单,经蒋转呈任命”,“所有在东三省任职者之生命财产,均予保护”[6](P222)。易帜后, 张学良也坦言:今后东北“地方行政”“依中央政府委任而行之”[7](P172),事实也是如此, 东北政务委员会及各省政府的高级官吏均由张学良提名,南京任命公布,由“东北各省区资望深重,富有政治经验者充之”[2],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东北地方政权的半独立性。
其二,对一些重要的权力机构坚决予以维系。机构和政权是表里关系,机构作为政权的实体,其存在与否,是政权存废的基本指标。东北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对蒋介石南京政府来说,本属权宜之计,易帜后的第二年即谋求裁撤,以使东北地方失去中枢,加以控制。张学良东北集团洞若观火,坚决抵制,多方拖延。先是要求待大局完全底定,各省军民分治后,方能撤销,后又以政委会撤销后具体办法尚未议定而拖延撤销时间。结果,该会不仅未能撤销,反而还扩大了管辖范围。1930年中原大战后,随着东北军入关,张学良取得处理北方善后问题的全权,东北和华北八省区的行政均在其节制之下。
最高法院东北分院的设立和保留,是张学良东北集团在东北地方政权上与蒋介石南京政府争斗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当南京政府提出撤销该院时,东北当局以四省案件积存甚多,要求缓撤[2]。中原大战前夕,张学良自恃东北举足轻重, 又向南京中央提出保留该院。中原大战后,东北更进一步将该院移设北平,管辖东北、华北八省区的司法事务。
三、结论
政权上的渗透和控制是蒋介石南京政府使东北地区中央化的标志,而牢牢掌握政权则是张学良东北集团能够保持半独立状态的根本。通过上述二者关系的考察,我们似可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二者在政权上的关系总体上是合作。东北承认南京的中央领导地位,南京也认可东北半独立政权的存在。这种合作统一,贯穿于从易帜后到九一八事变前整个这一时期,双方的矛盾和对抗也是在统一与合作的大背景下展开的,没有破裂合作,这与同一时期冯、阎、桂等其他几大地方军事政治集团同南京进行空前激烈、空前规模的武装冲突,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
第二,二者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蒋介石南京政府在东北地方政权上处处插手,东北最高政权机构中,也不再是千面一色。张学良东北集团从此再也不能无拘无束了,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蒋介石南京政府的掣肘。同样,张学良东北集团也把触角伸向南京中央,籍此影响南京政府的内外政策。首先,动辄向中央提出自己对国事的主张,如中原大战期间,张学良向蒋介石提出:政府与党部并立;改造国民政府;在最短期内召集国民会议等。这也是东北出兵支持南京的条件。其后,张学良又提出召开国防会议,提出确立全国军队统帅权案,内容主要是:“废止现在独裁的总司令职,统帅权归属合议制的国防会议,并声称坚决主张到底”[2]。其次, 将自己的势力侵入中央。不管是国民党中央,还是国民政府及军事机构,均有东北集团的人参与其中,先后任(兼)职者达20余人,如:张学良、张作相、王树翰、张景惠、刘尚清为国民政府委员;谷耀山、康季封、张国栋等为立法委员;王家桢为外交部次长;刘尚清为内政部次长;王树翰为国民政府文官长;张景惠为军事参议院院长等。就连南京中央的人事任免,也要受东北好恶的影响。外交部长王正廷的被撤换,就与张学良东北集团的态度有一定的关系。原因是在中东路事件和对苏交涉中,王执行南京政府的所谓“革命外交”政策而惹恼东北,张学良多次要求将其撤职,蒋介石虽未即时接受,但九一八事变后不久,王即被撤职,由一向受东北青睐的顾维钧继任。可见强大的东北地方集团的存在,已不容南京漠视。
第三,二者之间在东北政权上的这种合作与对抗,从本质上说是统治阶级内部中央集团和地方集团在利益、权力上的分配与争夺。不管是南京对东北的渗透和控制,还是东北对南京的合作与对抗,都是以各自的利益和权力为依归,贯穿于二者关系的全过程。如果说易帜谈判时双方的交易还不算在内的话,那么看一看中原大战后双方就国内和东北问题所达成的所谓谅解就一目了然了,其内容包括:“(一)冯玉祥、阎锡山必须出洋;(二)东省军队由张改组,俾与‘中央’所定制度符合;(三)东北军政张有全权,东省国民党部亦由张全权主持;(四)东北之财政机关归中央监督,国税除地租外,悉解‘中央’,铁路除吉黑、吉敦等路外,北宁、四洮、吉张三路归‘中央’直辖,惟东省之军政费归‘中央’拨付;(五)外交由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办理,但张可随时发表意见;(六)共同维持国内和平”[8]。由此可见,南京中央对东北地方政权虽有所渗透,但由于东北当局的顽强抵制,政权还牢牢掌握在东北集团手中。
第四,二者之间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既受制于双方所处的具体的客观环境,又取决于双方各自的主观条件和具体目标,有其深刻的主客观原因。
南京方面,从国内看,自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建立, 就一直为国民党派系纷争所困扰,处于严重的内部危机之中,蒋介石集团的中央统治权不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冲击和挑战,尤其是冯、阎、桂等几派大的军事集团,对蒋介石的中央统治权构成致命的威胁。第二次“北伐”之后,蒋介石集团与冯、阎、桂三派的矛盾迅速激化,随即爆发空前规模的新军阀战争,国民党内的其他反将派别也遥相呼应。刚刚易帜后的东北集团成为三派之外又一大地方派系,但其主要是谋求自保,没有取蒋而代之的野心,在地理位置上又远离南京,若要说是威胁的话,也仅算是潜在的威胁。此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也是南京政府统治的一个威胁。从国际看,1929年开始的资本主义世界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激化了帝国主义各国内部及各国之间的各种矛盾,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争夺也由此加强,尤其是日本在中国的势力迅速膨胀,在东北更肆无忌惮,成为南京政府外在的巨大威胁。南京政府建立后,把苏联化友为敌,反苏成为其对外政策的一个方面,使中苏关系不断恶化。从蒋介石集团自身看,其优势主要在经济和政治上,即占据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有江浙财团的支持;把持中央,居高临下;而在军事上当各地方实力派联合起来的时候并不占绝对优势,当时决对听命的黄埔系基本部队,大约30余万,与东北集团的军事力量基本差不多。这种内外环境和自身条件,决定了蒋介石南京政府在处理与国内各地方军事政治集团的关系时,基本上运用的是历代统治者行之有效的“远交近攻”谋略,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最直接最危险的威胁上,而对东北这个次要的、潜在的威胁,一方面,作为暂时的盟友,利用自己经济上、政治上的优势,拉住东北,为我所用,这是迫切的需要;另一方面,作为潜在的威胁,利用自己的政治优势,从经济、政治上削弱和控制东北,这是基本的目标。这两个方面是统一的。
东北方面,从国内看,易帜后,不论是蒋介石集团,还是冯、阎、桂各派,可以说都对东北尚未构成直接威胁,中国共产党的威胁更谈不到。从国际看,日、苏两国,特别是日本已成为东北最大、最直接、最紧迫的威胁。苏联与东北有很长的边界线,在东北的遗留问题也不少,加之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对立,以及南京政府的反苏政策,使东北与苏联的关系也日趋紧张。从东北集团自身看,刚刚易帜,百废待举,经济上面临严重困难,须治理改善;政治上,内部矛盾重重,张学良地位不稳,亦需整合强固,杨常事件的发生就是一个典例。在这种环境和条件下,张学良东北集团对蒋介石南京政府,一方面,作为中央政府,东北集团要表示统一的诚意,并借助南京中央的力量解决东北的外交问题;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威胁,东北集团又要抵制南京政府的“统一”,维持自己的半独立局面。这两个方面也是统一的。
标签:张学良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蒋介石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东北易帜论文; 国民政府论文; 西安事变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 北洋政府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