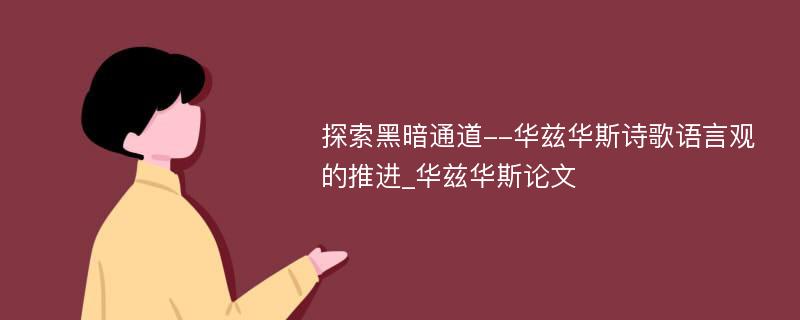
黑暗通道中的探索——论华兹华斯诗歌语言观的超前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兹华斯论文,超前论文,诗歌论文,道中论文,黑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61.07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3831(2000)02—0005—06
华兹华斯诗歌语言观的超前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对诗歌创作中语言的局限性与逆向作用的认识;二、对诗歌创作中感觉与思维的辩证关系的思考。华氏阅历广博,著作甚丰,其语言观不但散见于论述中,而且表现在诗作里,其间几经变化,有一个不断丰富、逐渐成熟的过程。本文拟追本寻源,结合其有关作品,探讨华氏诗歌语言观的超前性,揭示其对现代文论的启迪意义。
一
华兹华斯在论述和诗作中多次涉及诗歌创作中语言的局限性这一问题。早在1798年《荆棘》一诗的注释中,他就谈到了使用语言的双重困难,其一是“语言的局限性”,其二是语言使用者的“功力欠佳”。他强调说:“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认识到,很难有人在表达丰富激情的过程中不感到自己的功力欠佳,
不感到语言的局限性。
”(注:William Wordsworth,Wordsworth's Literary Criticism ed.W.J.B.Owen(London and Bost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4).97.)即使在景物描绘中,诗人也会遇到类似的困难。例如, 《序曲》(1850年稿)中的诗人在旅途中曾经看到一位姑娘顶着水罐, 在山道上迎风行进。诗人感叹道:
它其实只是
一个平常无奇的场景;而我却需要
人所不知的色彩和文字,
来描绘想象中那无尽的凄凉和忧郁……(注:William Wordsworth,"The Prelude," in Wordsworth:Poetiocal Works, ed. ThomasHutchinso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578.以下所引华氏作品用括号内页码表示出处,无特殊说明均指同书.)
这种“言不达意”的感觉并非由于诗人找不到恰当的言辞,而是因为那样的言辞“是人所不知的”。显然,语言内在的缺陷限制了诗人,使其难以用语言文字表达自己的意图和情感;所表达的对象处于一种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状态。我们从许多作品中都可以看到类似的例证:在《丁登寺》中,诗人发现,每当他试图用语言来表达情感时,其创造力便出现衰退的迹象。在《痴童》、《我们七岁》、《父亲轶事》中,与不善言词的孩童相比,滔滔不绝的成年人不禁相形见绌。
在1804年创作《序曲》(1805年稿)第6章的过程中, 华氏重温当年徒步穿过辛普朗山口的情景,不禁心潮起伏,浮想联翩,写下了有关想象力的著名诗篇:
多么神奇的想象力!它恰如凭空而来的
雾霭,悄然浮现在我的眼前,
浮现在我的歌中,那一力量
势不可挡,横亘
于前;我如坠云海,
绯徊不前,无力穿越其间。(注: William Wordsworth,
The Prelude,ed.Emest de Selincourt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99.)
在这里,华氏巧妙地回避了明显的时间概念,淡化了叙事成份,从而形成一种不受时空限制的文字效果,使这一篇章变成其情感经历的一种隐喻。它既表现了诗人穿越山口的经历,又再现了诗人在创造过程中的心境:诗行中孤独的旅行者既是那一事件的参与者又是此时回顾那一过程的诗人:“凭空而来的雾霭”既可指诗人途中所见环绕山峦的云雾,也可指诗人在回忆过程中所感受的困惑。Athwart 一语隐含着一种比喻:诗人象一名水手,诗歌如一叶小舟,浮现在前面的是某种庞然大物。
根据德塞林考特的考证,《序曲》(1850年稿)第6 章关于语言局限性的文字是在1839年以后的修改中增添的。(注:J.Douglas Kneale,Monumental Writing: Aspects of Rhetoric in Wordsworth'sPoetry (Linco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88).155.)比较不同手稿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创作经历的丰富,华氏对语言的信心反而降低了:
想象力——令人感到悲哀、难以胜任的
人类语言使我不得以如此称呼这种力量,
这一可怕的力量源自心灵深处
如同凭空而来的雾霭,
将孤独的旅行者包围起来。我不知身在何处;
徘徊不前,无力穿越其间……(p.535)
这里的关键是对“想象力”一词的描述。“令人感到悲哀的、难以胜任的人类语言”使诗人无法进行充分、精确的表达。在此之前的第 5章中诗人也对心灵的巨大力量和语言的局限性发出了哀叹:它们仍然是“异常脆弱的神殿”(p.522)。 华氏在此提出了两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其一,人类语言的局限性使诗人无法找到恰当的语汇对其进行命名;其二,“想象力”在诗歌创作中是一种“可怕的力量”。
严格说来,“想象力”并不是这种“力量”的比喻,它仅是用以表示后者的一个名称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一种换喻词或元词。无法对这一“力量”进行命名并非诗人的功底不够,而在于语言自身的局限性。正如华氏在1815年发表的《补遗》中所指出:“语言本身表达能力的贫乏是我们使用‘想象力’这一术语的根本原因。
”(
注:William Wordsworth,Wordsworth's Literary Criticism ed.W.J.B.Owen(London and Bost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4).211.)华氏曾多次力图从哲学角度对“想象力”进行探讨,但其结果均不尽如人意。这一点不难理解:想象力作为一种心理能力,很难加以精确定义。在华氏看来,想象力同人的情感和道德本性相连,与分析理性无关。虽然无法使用更确切的语言来对其加以描述,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对这一力量的崇敬和景仰。在他看来,想象力是神圣的,是诗人充满神秘色彩的个人经历的核心部分;舍此便不能进行诗歌创作。
我们知道,文学史上不乏有关诗歌和诗人局限性的记载,许多诗人甚至常常将“诗人的局限性”作为一种艺术策略或自谦之辞。例如,莎士比亚在其十四行诗中就多次以责备的口吻提及诗神缪斯的不足;弥尔顿在《利西达斯》中满怀歉意地说自己是在勉为其难的困境中创作该诗的;柯勒律治将其名诗《沮丧》比为一只笛子,声称它在没有发声的时候更具魅力。与其前辈相比,华氏思路超前性在于引入了“语言的内在局限性”这一重要观点。所谓诗人的“功力欠佳”其实是想象力超越了语言能力的限度,使其不能充分加以表达。这是语言内在缺陷所致,是诗歌这一艺术形式自身的特点之一。这一洞见与乔姆斯基关于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的理论几乎有异曲同工之妙,对20世纪文论关于文学话语的讨论具有不可低估的借鉴意义。
其次,华氏进而探索了语言在诗歌创作中的逆向作用。早在1810年,他就深深地意识到语言作为符号系统的潜在危险。他发现,与诗人的愿望相反,语言在创作过程中往往产生一种负面效应,使诗人的激情和想象大打折扣。他在《论墓志铭》系列文章之三中指出:“文字是一种可怕的工具,切不可等闲视之:它们对思想所起的支配作用超过其它任何外界力量。如果文字仅是思想的外衣而非其化身……那末它是一种逆反精灵(counter-spirit),持续不断地在暗中起到扰乱、颠覆、 破坏、 损害和分解的作用。 ”(注:
William
Wordsworth,Wordsworth's Literary Criticism ed.W.J.B. Owen( London and Bost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4).154.)
华氏认为,语言在诗歌创作过程中所扮演的“逆反精灵”的角色使诗人处于一种两难境地中。用他在《不朽的征兆》一诗中的词句来说,诗人如同禁闭在语言“牢笼”(the prison-house)之中的囚徒, 在使用语言符号的同时也被语言符号所限制。由此可见,创作过程中这种遭遇“凭空而来的雾霭”的经历反映了语言层面上的矛盾:“出处不明”,“眼前一片/黑暗”,没有参照;语言自身不得不在“隐形世界”(p.602)中去面对失去明确所指而带来的危机。于是, 语言的比喻性不再表示偏离,仅是一种差异而已。但是,正如雅各布森所说,语言的“文学功能高于其所指功能这一特点并不排斥其参照,而是使其具有多义性。”(注:Roman Jakobson,"Closing Statement: Linguisticsand Poetics," in Style in Language ed. Thomas
a. Sebeok(Cambridge:M.I.T.P,1960).371.)在《序曲》这样旨在探索诗人心灵成长过程的作品中,语言的多义性特点显得尤为突出。
从心理学角度讲,华氏所说“可怕的力量”并非想象力本身,而是存在于想象力之中的一种心理能量。人的想象力对这种心理能量进行提炼和加工,使其为诗歌创作服务。显然,这样的力量必需经过语言的过滤,经过诗人沉思的加工;华氏不可能直接面对心灵中这一“可怕的力量”。对华氏来说,不存在没有经过沉思的灵视。
在华氏看来,语言的颠覆作用表现在诗人的想象力与其感觉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在《序曲》(1805年稿)第1章中, 华氏曾经将存在与想象力之中的心理能量比作“一场暴风雨,一种冗余的能量,/震荡着它自己的创造物”(p.495)。在穿越辛普朗山口的诗行中, 它通过“颠覆”得以超越想象力的提炼和传输作用,直接呈现在诗人的五官感觉之前,使其顿觉头晕目眩,“眼前一片/黑暗”。换言之,这种心理能量顷刻之间对诗人的感官形成巨大冲击,其效果犹如晴天霹雳。它所揭示的“隐形世界”并非存在于客观自然之中,而是位于诗人的“心灵深处”;诗人籍此看到了藏匿在自己心灵深处的巨大潜能——“某种将要生存的东西”(p.535)。在华氏看来, 隐藏在心灵之中的这种力量并非深不可及,我们可以借助想象力和诗歌语言使其显现出来。它在想象力的作用下,可由诗人内心转而进入诗歌文本。诗人在《序曲》(1850年稿)第12章告诉我们,“只要语言能够充分表达”,他可以“赋予感觉以质感和生命”(p.578)。
值得指出的是,华氏所用“颠覆”一词具有多种意义,其中之一是对经验主义感觉论的质疑,对五官感觉(尤其是视觉)所占统治地位的挑战。这一洞见远远超出了他的同时代人。与其他浪漫主义诗人不同的是,华氏意识到了视觉的负面作用,他认为即使在儿童时期,眼睛也“象一条锁链束缚了他的感觉”(p.510); 眼睛是“我们五官感觉中专横的暴君”(p.576)。我们看到,在穿越辛普朗山口一章中, 产生于想象力的这种“颠覆”作用剥夺了视觉的特权地位。在华氏看来,只有在视觉暂时失去功能的情况下,心灵的眼睛才能获得最为清晰的灵视,只有在表示感觉的语言暂时失效的时候,想象力才能在大自然的作用之下得以任意驰骋。想象的“巨大魅力”并非来自“颠覆”的动作过程,而是存在于其巨大的力量之中。人的“命运”与其想象力密切相连;人类心灵的家园不在“隐形的世界”之内,而是根植于能够揭示世界真谛的想象力之中,与无限的天地万物同在(p.535)。
此外,华氏在上面诗行中所用“unfathered vapor”(凭空而来的雾霭 ) 一语也体现了他对语言所具有的 “颠覆 ”特性的认识 。unfathered一词本意为“没有父亲”或“失去父亲”的意思。这种用法可见于莎士比亚的作品之中。华氏熟知莎翁作品,在《序曲》(1850年稿)第3章中也使用了fathered一词来表示相反的意思(p.513)。在华氏看来,想象力的作用使诗人获得灵视;而语言由于自身的内在局限性,扮演了逆反精灵的角色,“持续不断地在暗中起到扰乱、颠覆、破坏、损害和分解的作用”。“否定父亲”这一比喻不仅形象地概括了语言的“颠覆”作用,而且亦向传统的作者意图观点提出了有力的挑战,从而为人们了解诗歌创作中想象力的作用开拓了更大空间。
对熟悉基督教文化的读者来说,华氏所用“否定父亲”这一比喻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按照《圣经》的说法,最大的颠覆者是违抗上帝旨义的撒旦。显然,对“天父”的颠覆是一种从根本上“否定父亲”的行为。一旦存在一个中心,就有其边缘的存在;只要存在主导因素,就有与其对应的次要因素。后者每时每刻都对前者的正统性和正当性提出挑战,力图颠覆其主导地位,以便取而代之。以文化史为例,文艺复兴是一个分水岭:此前是基督教塑造了西方文化;此后是对基督教的反思重塑了西方文化。文艺复兴之后的人文主义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基本上来自于西方人自己对基督教价值的反省、反抗和修正。一种对“正统”的偏离和颠覆于是逐渐又自成正统。文化史如此,文论发展亦如此。
再次,与同时代的论者不同,华氏还从诗人与读者两个方面对语言在诗歌创作中的逆向作用进行了考察。他虽然没有像现代语言学家那样自立理论体系,但其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对今天的文论研究仍旧不乏启迪。他在《补遗》中强调指出:“在诗歌中,影响读者情感的媒介是语言——一种受到无穷变动和任意联想(endless fluctuations and arbitrary associations)支配的东西。天才的诗人可以使其为自己的目的服务; 但是对心智功力欠佳者来说, 它们是难以驾驭的。 ”(注:William Wordsworth,Wordsworth's Literary Criticism ed.W.J.B.Owen(London and Bost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4).212.)他在《序曲》(1850年稿)中曾经感叹:“哦,文字的力量如此神奇,它们可以/仅凭约定就表示我们选择的意义!”(p.539)
华氏在这里提及的两个十分重要的概念——语言意义的“无穷变动和任意联想”特点和“约定性”——与索绪尔的语言观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由“任意的”和“差异的”符号所组成的系统。语言的“任意”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符号生成的过程中,能指与所指的结合是任意的,两者之间的联系不是必然的,而是约定俗成的;其二,在符号生成之后,符号与其所指的概念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必然的,带有明显的随机性和任意性。语言的“差异性”有两层意思:第一,符号的组成是一组差异关系;第二,符号组成的语言是另一种差异关系。一个词语只有处于水平的横组合与垂直的纵聚合的交叉点上,才能得以确立其符号功能。语言是一种表示差异的系统,一个词汇的意义取决于它与本系统内其它词汇的关系,与系统之外的因素没有关系。
华氏所追求的是一种朴素、简洁的诗歌语言,因为那样的语言具有一种综合能力,可以表达“语言与心灵各自的运动及相互之间的作用”,使人们得以遵循“本性中的基本规律”,保持“固有的激情”,表达“朴素的情感”。(注:John Williams,WORDSWORTH: Introduction,selection and editorial matter( Houndmills: THE MACMILIANPRESS,1993).16—17.严忠志.论华兹华斯的诗歌创作观.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6(2):16—23.)显然,华氏相信自己具有克服语言逆向作用的能力,可以利用诗歌来讲述经历,表达情感,传达思想。综观其创作活动我们看到,他力图在诗歌中向读者展现一种具有自然主义色彩的清晰性,而那样的清晰性正是他自己在心理上所迫切需要的。这是因为,诗人对外在清晰性的渴求恰恰反映了其内心的迷茫,反映了他企图以诗歌形式倾诉内心情感的强烈欲望。得益于其对诗歌语言的真知灼见,华氏在自己的创作中力图克服语言的逆向作用,以便表达对生活的感受。简言之,作为一位有创见的诗人,华氏试图挣脱惯性思考的束缚,跳出传统文论的框框,用大胆的、批判的眼光来审视诗歌创作的诸种因素,就诗歌创作中语言的作用提出了发人深省的见解。
二
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序》中指出,生活在乡村的社会下层民众所使用的语言比当时流行的诗意辞藻更富于“哲学”意味。这里的“哲学”指的是洛克的经验主义。华氏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洛克经验主义的语言观。洛克认为,既然一切知识最终与事物相联系,它必然是人的心灵通过五官感受外界事物的产物。人的知识有两个来源:通过感觉获得的外部世界的经验;通过反省达到的内心世界的经验。
但是,洛克在撰写被喻为现代科学认识论基本原则的《人类理解论》的过程中发现:他所面对的不仅是五官感觉,而且还包括文字写作本身;他所接触的不只是外界的事物,还有心灵本身。“我必须承认”,洛克写道,“当初开始撰写这部有关理解力的论文时(以及其后一段时间内),我根本没有考虑文字与它有任何关系。”他的结论是:“它们[文字]与人类的一般知识是不可分离的。至少可以这么说,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对事物的理解,影响心智对真理的理解与思索;它们如同可见物体得以通过的介质,其模糊性与无序性时常在我们眼前投下一层迷雾,从而对我们的理解产生影响。”其次,洛克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的聚集体,一种词汇的堆积形式。他十分重视语言的命名功能,将注意力集中在名词和形容词的特性上。从语言发展的角度看,洛克的理论适用于文化发展较为原始的民族;原始民族可以通过“命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欲望和要求。随着文明的演进,尤其是社会分工的细化和文化阶层的出现,对语言的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之便形成了能够表达较为复杂概念的语言体系。(注:Ross Woodman, "THE
PRELUDE AND THE FATE OF MADNESS,"in WORDSWORTH: Introduction,selection and editorial matter,ed,John Williams (Houndmills:THE MACMILLAND PRESS,1993).122—116.)
作为诗人,华兹华斯显然已经意识到洛克理论的局限性。一方面,他认为诗歌中要使用描写自然的语言,从而强调了感性认识的首要地位;另一方面,他认为诗歌中还应有表达沉思的语言,以此肯定理性认识的重要作用。在《丁登寺》、《序曲》等名篇中我们看到,第一种语言的使用者往往与自然是融为一体的,以文化水准不高的女性居多;其特点是清晰明了,罕见岐义,句法简单,变化不多。第二种的使用者则具有独立于自然的自我意识,往往为受过良好教育的男性;其语义具有多向性,受语境的制约较大,句法复杂,富于变化。
华氏所划分的这两种语言反映其对思维与感觉两者之间关系的认识,表现了两种不同的生存状态:一种是与自然连为一体的;另一种具有明显的个人身分意识。按照华氏的说法,我们的思想“反映我们过去的全部感觉”,(注:William Wordsworth,Lyrical Ballands,ed. R.L.Brett and A.R,Jones(London:Macmillam,1965).246.)感觉从外界而来,是由感性语言表示的。由此看来,无论人们的思维多么难以捕捉、难以传达,但与内容相比,表达其特性相对说来要容易得多。“具体经验是抽象概念的基础”,这一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华氏的论点:表达沉思的语言之所以有意义是由于其源于具体可感的事物,而那些事物是可以用语言加以描绘的。
显然,洛克和华兹华斯都面对一个问题,即如何对待隐喻性语言。他们俩人均对隐喻抱有浓厚的兴趣,力图使心灵和自然互为镜象。洛克的目标是使心灵成为自然的摹本;华氏的目标是使自然成为心灵的写照。这样一来,要么心灵就是自然;要么自然就是心灵。语言问题于是变成了隐喻问题。根据华氏在《前言》(1815)中的观点,隐喻“不是不在场的外界事物在心灵内的真实摹本”,而是在想象力作用下“心灵遵照某些特定规律,对那些事物产生作用,进行创造或建构的过程”。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由于想象力的运用使心灵脱离“真实的摹本”,这样的运用从某种意义上讲实际上是一种欺骗行为。华氏在《荆棘》的一条注释中说,如果人们不了解心灵的具体运作,想象力的运用将会导致迷信。换言之,隐喻形成一种华氏称为“虚浮的信念”。(注:William Wordsworth,Wordsworth's Literary Criticism ed.W.J.B.Owen(London and Bost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4).96.)
洛克认为客观现实存在于具体的事物之中,因此一切知识终结于具体的事物。心灵与自然不同,其本身并非像自然那样存在。洛克列举了描绘骑手与座骑这个例子。如果任其依据快乐原则(想象力)自由活动,心灵不会形成两者的真实摹本, 而是制造一个半人半马的怪物(centaur)。如果一个人“认为半人半马的的怪物表示某种真实的东西,那是自我欺骗, 将词语误为事物。 ”(注:Ross
Woodman,"THEPRELUDE AND THE FATE OF MADNESS,"in WORDSWORTH:Introduction,selection and editorial matter,ed,John Williams (Houndmills:THE MACMILLAND PRESS,1993).124—125.)华氏的观点与洛克不同。他充分肯定快乐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将其视为诗人应该始终遵循的根本原则。《〈抒情歌谣集〉序》认为,快乐是心灵对自身活动的肯定与回报,心灵直接以隐喻形式加以表达。其次,华氏没有混淆字面意义与比喻意义两者之间的区别,没有将文字误为事物。对他来说,文字只是符号而已,诗歌中的隐喻是心灵创造的产物;“快乐”存在于文字(而不是事物)之中。在创作过程中,客观世界与人的心灵可以达到完美契合,诗人可以处于一种心醉神迷的状态,不受外界刺激的制约,心灵毫无拘束,头脑中显现出充满诗意的灵视。而且,这种状态往往不是立刻出现在诗人观察了自然景物之后,而是产生于诗人心境平静时的回忆之中。
在此基础上,华兹华斯进而探讨了诗歌创作过程中感性语言与表达沉思的语言二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感性语言是表达沉思语言的基础。沉思需要推理及道德方面的术语,而这些术语同感性语言中的具体事物的名称相联系。这与利用代数等式求未知数的情形类似:由于人们已经知道具体名称的意思,籍此可以获得对推理及道德方面术语意义的初步认识;然后在阅读和对其使用的过程中,逐步完善对这类术语的认识;通过分析,最终可以使抽象概念的意义与具体概念相联系。于是,有关自然的概念便可成为表示反思、推理和道德这类概念的支点;感性语言便可使表示这些抽象概念的语言相对稳定下来。这在其名作《丁登寺》得到充分体现。诗人在大自然和感性语言中发现了自己“纯洁思维的锚地,/内心情感的滋养者、 向导和保护人, /道德品质的灵魂”( p.165)。舍此诗人便无法确立自己稳定的主体地位,无法展开其表达沉思的语言。
另一方面,华兹华斯认为,感情语言与表达沉思的语言可以相互转化。个体发生重现种系发生;个人思想的发展过程重现一个民族,乃至人类的演化历程。在《丁登寺》中的多萝茜身上,我们看到了两者之间的转化过程,看到了弥合两者差距的希望:“再过几年”,她将具备清醒的思辨能力,她的心灵将成为“所有美好形式的殿堂”(p.163)。 这里的多萝茜具有双重作用:她使用的感性语言为诗人的沉思语言提供稳固的意义基础与保证,此其一;在她身上形象地再现了诗人经历过的两种语言的转换过程,此其二。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和感性语言不是障碍,而是一种催化剂:它们引导人们从幼稚走向成熟,全心呵护和监督其健康发展。由此可见,感性语言存在于整个过程之中,舍此便不能确保表达沉思语言的意义,不能实现思维从简单到复杂的良好转变。
华氏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对自己现在和过去的感觉方式进行的思考能够改变现在的感觉方式吗?思维是否凌驾于感觉之上?或者说,感觉是否是思维的潜流?《丁登寺》中的诗人五年之前接触的“美丽的形象”给他以力量,帮助他度过了在城镇之中的“消沉时光”。在认知层面上,这种基于感觉的情感方面的支撑价值仅能“使心灵更为纯洁”而已(p.164)。那时,自然景物仅仅满足诗人的一种“欲望”、 一种“感觉”,停留在视觉、本能和情感层次上,与思维没有太大关系。诗人从大自然所受到其五官感觉和情感反应的限制,没有具体的目的,没有特定的观点。五年之后,大自然不再完全独立于诗人心灵之外,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它包含了诗人的五官感觉、感受和思维;诗人与大自然已经融为一体。他的五官感觉、思维和情感已经实现了统一。我们看到,诗人通过回忆“美丽的形象”,处于“愉悦的心境”之中,得以与大自然进行和谐的交流。此时,诗人心灵中的图象复活,大自然中的景物(过去的感觉)被转化到内心(现在的思维)之中。诗人此时的快乐来自两个方面:1、现在的感觉;2、对自己将来感觉方式的思考。在此过程之中,思维没有排斥感觉,而是对其加以充分利用。华氏使感觉主要与过去相联系,使思维主要与现在及将来联系。于是,回忆过去就是使其与现在相结合的过程,就是使感觉与思维相结合的过程。诗人籍此获得一种距离感,一种自我成就感。后笛卡尔二元论哲学认为感觉与思维是相互对立的,并且往往将后者置于前者之上;经验主义的感觉论一味强调感觉的重要地位,对思维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华氏思想的超前性在于将诗歌创作中的感觉与思维视为相辅相成的东西,认为两者互相依存,缺一不可,进而致力探索如何使两者融为一体。
海德格尔认为:“每个伟大的诗人做诗都出自于唯一的一首诗。”在对个别诗歌的“探讨和解释之间的交互联系中,始终包含着与诗人的那首唯一的诗的思索性对话”。他进而指出:“思与诗的交谈的目的在于揭示语言的本质,以便使凡人重新学会寓居于语言之中。”(注:海德格尔.诗歌的语言.刘小枫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海:三联书店,1991.1237.)作为文学和社会定位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华兹华斯的诗歌语言观反映了当时人们在维持共同文化生活过程中所面临的信心危机。那场危机源于18世纪的思想论战,其核心问题之一与话语是理性思维的表达方式这一认识相关。诗人约翰·济慈曾经感叹道:“我们在迷雾之中——我们眼下正处在这种状态——我们感觉到‘那种神秘之沉重’。此时出现了华兹华斯,他……探索了这些黑暗通道。我们如果得以生存下去继续思考,也将进行同样的探索。但是一位天才,其能力在我们之上。他会发现更多的东西,提出他的洞见——籍此,我得说, 华兹华斯的见解比弥尔顿更为深刻。 ”(注:John
Keats, Letters of John Keats,ed.Robert Gittings ( Oxford: OxfordUniversity Press,1975).95.)的确,华氏关于诗歌创作中的语言内在局限性和逆向作用的认识,关于感觉与思维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思考超越了其所在时代,不仅具有很高的文论史料价值,而且对今天文学话语的讨论也不乏借鉴意义。
*收稿日期:1999—10—08
基金项目: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资助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