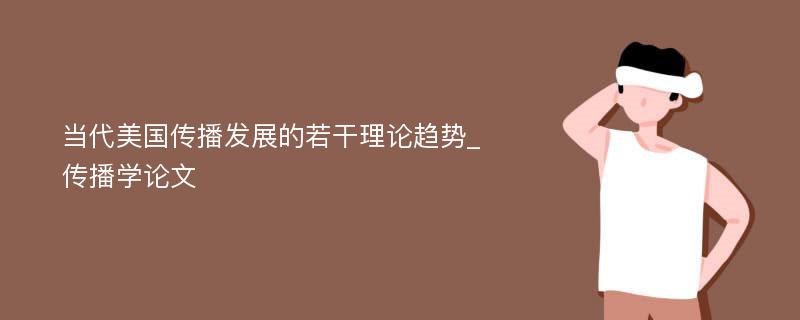
当代美国发展传播学的一些理论动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播学论文,美国论文,动向论文,当代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传播与发展的问题之成为理论关注的中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作为大众媒介迅速扩散到欠发达国家的一个结果,理论家们开始考虑媒介能否和怎样促进文化的传播和经济的发展。在美国社会科学中,D.勒纳、W.施拉姆、E.卡茨、E.罗杰斯等人是这个领域的开创者。席勒等人对之作了批判主义的反思,这一反思不仅得到英国等其他西方国家的批判主义者的支持,而且被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的研究者所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则为有关的争论和观点的阐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论坛和推动力。当今时代,世界背景中的美国发展传播学的理论研究又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总的来说,它们是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与通讯技术和信息加工方面的突破相一致的。
就传播与发展的理论探讨而言,由冷战时期美国国际开发署等机构所促成的以美国为基地的研究中心,从50年代到80年代,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的研究者以极大的兴趣参与进来,并形成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这可以从一批世界性的、专门或主要致力于传播与发展问题研究的杂志的出现中得到佐证。这类杂志有:《媒介发展》(伦敦)、《媒介亚洲》(新加坡)、《发展与传播评论》(泰国,现已停刊)、《Chasqui 》(基多——厄瓜多尔首都)、《发展传播杂志》(吉隆坡)、《第三条道路》(汉城)、《亚洲传播杂志》(新加坡),等等。在充满活力的、拓展性的研究中,诸如政治经济、大众文化、乡村发展、新闻传播、和平与安全等已经成为新的探讨课题。
对于美国来说,在发展传播学的理论研究方面,坐落在夏威夷大学校园内的东西传播研究所具有相当程度的重要性。它是由联邦政府所创建的、旨在促进美国和亚洲的知识交流和合作的研究中心的一个组成部分。70年代,施拉姆曾任这个研究所的所长,他和他的同事们在这里为亚洲学生提供奖学金,组织亚洲和美国的传播学学者的会议,从事研究,发表著作和研究报告。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这个大学的另一名传播教授马杰德.泰拉尼安(Majid Tehranian)成为发展传播学中引人注目的研究者,他先后发表了《发展理论和发展政策》、《传播、和平和发展:一个社群主义的观点》、《传播与发展》、《权力技术:信息机器和民主展望》、《来自耶路撒冷的信件》等论文和著作,并与他人合编了《世界和平的重建:站在21世纪的入门处》一书。泰拉尼安通过他的著作,努力表明我们关于社会、传播和发展的概念如何被20世纪知识生产中的“范式转换”所强烈制约。就是说,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信息社会和信息经济理论的发展,应该对原有的与传播和发展相关的各种概念和标准进行再思考。以美国为例:尽管这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和媒介发展水平在工业国家中排列最高,并就整个人的发展而言排列第六;但它在人的困惑和社会结构的软弱程度方面也是排列最高的国家,后者的明显表现是半文盲、吸毒、高犯罪率、失业等等。这表明,“美国社会沿着五个主要的社会断层线——阶级、种簇、性别、代际、宗教——而发生深刻的分裂。因此,整个民族的传播与发展的指标既可以表现在国家与国家的比较中,也可以隐藏在民族内部的差异当中。”(注:M.Tahranian,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in D.Crowley & D.Mitchell(ed.),Communication Theory Toda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275)
早期发展传播学中的创新扩散模式在当代的背景之下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如同丹·麦奎尔所说,罗杰斯的“主导范式”尽管存在着种种缺陷,但仍然“十分有用”。70年代末和80年代末,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分别进行了“创新比研究发展重要”和“扩散比创新更重要”的讨论。在当今社会,技术创新能力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意义尤其重大,因为它可以使技术发明迅速转化为产品和商品,从而使整个经济具有活力。就扩散和创新的关系来说,高新技术领域有比较密切的关联。人类已经在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空间、和海洋等六大领域取得了空前的进展。但是,实现大规模技术扩散的领域目前主要集中在前三类技术中,而后三类技术还大都停留在技术创新的阶段。相比之下,前三类技术在现阶段对世界经济发展的直接作用要大得多。社会学领域的研究者则从另一角度探讨创新扩散的问题,即将传播媒介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和媒介自身所具有的调节功能结合起来,考察媒介如何影响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建立,如何履行其社会参与和社会管理的功能。
传播在实现现代化道路中的作用问题仍然受到关注。过去30多年中,整个世界目睹了欠发达国家的某些惊人变化。南朝鲜、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国家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已经进入了工业世界的行列中。其他诸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个最不容忽视的力量是中国,自1978年“现代化政策开始启动”以来,它的年增长率大约达到10%。另一方面,大部分非洲国家、部分亚洲国家和拉美国家仍然在极度的贫穷中徘徊,它们所得到的往往是负增长。围绕着传播在这些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中的作用问题,仍然存在着经验主义和批判主义之间的激烈争论。前者是早期发展传播学理论的继续,其研究方法也往往是经验的,引出偏向市场解决和跨国公司向第三世界经济渗透的结论,认为媒介的参与是推进现代化的主要途径之一。后者则坚持主张这样的发展策略会加剧包括传播媒介在内的不平衡格局,其特征是通过全球性广告而导致的挥霍性消费、正常发展项目的搁浅、以及不公正的分工、不公平的分配和民族同一性的丧失,等等。迄今为止,现代化课题所面临的挑战在第三世界中已经引发出“超现代化” ( Hyper- modemization)、“ 反现代化” (
Counter-modemization)、 “选择性现代化和参与” ( SeclectiveModem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的争论;而在发达国家,则已经从“去现代化”(
Demodemazation) 转向“ 后现代化” (Post-modemization)的各方面问题的探讨, 这其中的纷争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关于传播与发展的理论进程。
相对于经验主义和批判主义两大学派,当代学者泰拉尼安提出了第三条“传播与发展的道路”,即“社群主义的”(commmunitarian)道路。他认为,与自由主义侧重于“自由”、马克思主义侧重于“平等”、极权主义侧重于“秩序”形成对比的是,这个模式所要保存的最高价值是“社群”,发达工业社会的环境保护主义、绿色和平运动,第三世界国家摆脱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的解放运动,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都可被视为它的表现形态。在传播与发展的问题上,它提倡将传播媒介作为内在的发展工具、而不是外在的发展工具来使用,为此,泰拉尼安提出了几个重要的方面:
(1)传播与发展的参与性模式要既有赖于传统的媒介, 又有赖于现代的媒介。泰拉尼安十分重视“参与性”传播的作用,他认为,通过真正的参与性传播行为可以达到对生活世界的理解,并最终达到公共领域的扩大。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发展传播学“将重点放在媒介上,忽视了人际和组织传播网络,包括诸如传统的和宗教的网络这样重要的联系”(注: M.Tahranian,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in D.Crowley & D.Mitchell( ed.) ,Communication Theory Toda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276.),而“社群主义的模式”强调将现代传播媒介的作用——这种作用可能是巨大的——置于人类传播的更大背景之中,它包括了意识形态构成,文化表达(口头的和非口头的),信息内容,以及人际的、组织的和媒介的传播渠道。因此产生出对于传播概念的重新思考。在泰拉尼安那里,“传播”被定义为通过口头和非口头的标志——这些标志借助于宇宙论、文化、内容和渠道而发挥作用——而交换意义的过程。他认为,这样才能够避免传播的媒介中心主义。与之相关的发展概念则在不拒绝量化测度的前提下,对从前的发展概念提出质疑。后者主要集中于一系列普遍运用的经济的、社会的或文化的指标,诸如人均收入、工业产值、城市化、识字比率、预期寿命、每千人中电视机的拥有量等等。泰拉尼安的模式要求改变论证的中心,即从成就等外在因素转向对内在因素的重视,也就是纠正对于物质产品的过分强调,更加强调人的发展。
(2)采用平行的、而不是垂直的传播途径,它是自愿结合的和网络性的,而不是单方向的和无反馈的。在泰拉尼安看来,平行的传播过程中存在着统一和整合的要求,因为“如果不使用一种混合语(lingua franca)和一批共同的历史记忆、神话和文学作品, 一个民族要吸收发展过程中的分裂后果,那将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注:M.Tahranian,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in D.Crowley & D.Mitchell(ed.),Communication
Theory Today, StanfordUniversity Press,1994,p.303.)也就是说,传播和发展的过程要求保存本土文化、民族特性与民族的自信心。泰拉尼安尖锐地指出,关于传播与发展的理论构建面临了某些不可克服的问题。而它们本质上是历史性的。显而易见,世界上各个国家代表着多种多样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它们之趋向于被普遍限定的发展指标的进步比率也是不同的,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存在一个传播、发展和民主的一般理论,以便阐述如此之多的不同国家的各种历史经历?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因此,社群主义模式鼓励多重的发展道路,即便所谓“高积累、高调动、高整合”——它是各种社会形态发展策略的修正与综合——的比较成功的经验,其“循环起伏的强度和持续性在各个国家显然也是不同的”。
(3)媒介技术的双重性以及选择性发展策略。 泰拉尼安引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说:“对世界市场的有限的或不平等的介入使发展中国家每年花费大约5000亿美元,这大约十倍于它们从国外帮助中所获的收益。同样,不平衡分配模式也表现在媒介的所有上:世界上大约10%的人拥有世界上大约 90 %的媒介。”(注:M.Tahranian,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in D.Crowley & D.Mitchell(ed.),Communication Theory Toda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279.)另一方面,他承认,诸如收音机、电视机、 录像机等不那么昂贵的媒介以及西方的节目还是以绝对的数量渗入欠发达国家。“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已经产生了矛盾的结果。一方面,它已经产生了由西方文化输出品所统治的一种全球“流行”文化。另一方面,它已经在世界上最遥远、最受压迫的人口中促使了民族和种族意识的加深。”(注:M.Tahranian,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in D.Crowley & D.MitcheLL( ed.) ,Communication
Theory Toda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297.)由此产生出选择性的问题。相对而言,泰拉尼安对于“选择现代化”的发展策略持赞同态度。他说,如果仔细地加以计划,选择性的参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能够为资本和技术的转换提供机会,而不必使民族经济过分地依附于外国的控制源泉。从泰拉尼安特别重视的和平与安全问题来说,采取选择性策略的国家往往已经经历了民族解放和社会革命的早期阶段,他们能够并且愿意以相对平等的术语相互商谈国际合作的有益条件。(注: M. Tahranian,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in D.Crowley & D.MitcheLL(ed.),Communication Theory Toda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300.)
在某种程度上,泰拉尼安的观点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代美国发展传播学的一些理论新动向,即从强调物的发展到强调人的发展,从大众媒介的中心地位到人际间的和可供替代的传播网络的重要,从对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各持一端的做法到强调传播与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的结合,等等。在他的论述中,有对于新的传播和信息技术的运用过程中所出现的不确定性的揭示,有关于近年来这一领域中的理论和实践所经历的巨大变化的综合性把握,也有以“新的复杂方式”对发展传播学所面临的主要的理论和政策挑战及其机遇进行探讨的尝试。而这一切都是与我们这个时代的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趋势相一致,与全球范围内多样化的文化交流和共存趋势相一致。就此而言,泰拉尼安提出和论述的问题具有当代的和世界的意义。当然,泰拉尼安的包括传播与发展的定义在内的许多观点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他对资本主义的传播制度和共产主义的传播制度的分析和评价也带有传统学派的意识形态偏见,而他关于传播与发展道路的一些具体设想——诸如“高积累、高调动、高整合”、需要从媒介技术的转换变更到媒介技术的跳跃等——则是初步的、有待进一步论证和加以补充的。
90年代中期,当代传播学研究者戴维·克劳利(D·Crowley)和戴维·米切尔(D·Mitchell)将泰拉尼安置于后大众媒介世界(a Post-Mass World)的传播理论框架中来讨论,认为在这位“值得注意的发展传播学理论家”那里,“我们发现:有关信息及其交换的思考范围扩大了,而且信息之生产和传播的可供替代的组织形式也得到了更高的评价”。(注:D.Crowley & D.MitcheLL(ed.),Communication
TheoryToda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22.)不管“后大众媒介世界”的论断能否成立,泰拉尼安的思想代表着发展传播学的一种比较新近的变化和趋向,这一点看来是可以成立的,其内容和意义看来也将引起进一步的研究兴趣和广泛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