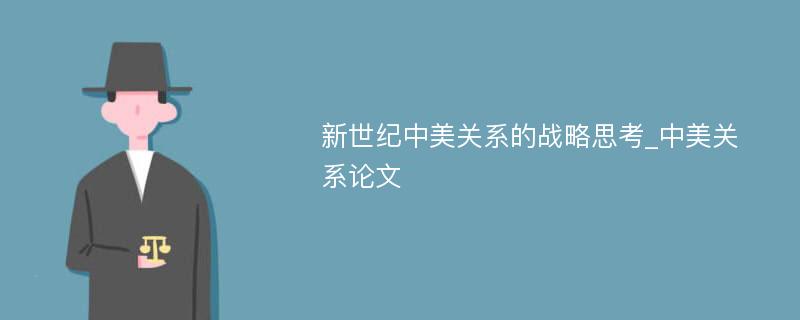
关于新世纪中美关系的战略性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中美关系论文,战略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所推行的以垄断资本全球化为本质的新霸权主义具有鲜明的全球性和扩张性,呈现出向全球辐射其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时代特征。而中国实行的以科技强国、发展经济为核心的复兴战略,正以锐不可当之势推动中国快速地融入世界体系,并成为世界多极化格局中的一极。这两股相向而行的势头同时对世界体系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从而使得中美关系已经超越简单的双边关系范畴,具有了地区层面和全球层面的重大意义。
长期以来,合作与对抗并存一直是中美关系的一个突出特征。隐含在这个特征下面的,就是两国在国家利益上所存在的结构性矛盾。这种结构性矛盾决定了中美关系的一切方面,导致双边关系始终在合作与对抗之间摇摆,从而也为中美关系构筑了成为对手或友国的两条通道。世纪之交,中美关系又一次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中美关系将何去何从,举世瞩目,也成为所有关心中美关系走势的学者所关注的焦点。
中美两国一直在努力进行变敌为友的角色调整
迄今为止,200余年的中美关系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和三个发展阶段。从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揭开中美关系的序幕之后,(注:李长久、施鲁佳主编:《中美关系二百年》,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中美关系经历了清王朝、蒋家王朝和新中国三个大的历史时期。在此期间,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非常复杂并发生剧烈变革,从封建的清王朝到资产阶级统治的国民党政府再到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走过的是一段由盛而衰、由衰而亡、由亡再兴的历程。与此同时,美国在摆脱了殖民地地位之后,逐步在北美大陆向西扩张,进而跨越墨西哥湾拿下拉丁美洲,而后越过太平洋进军亚太地区,最后横跨大西洋,挺进欧洲大陆,走过的是一条从殖民地、主权国、北美大国、美洲大国到西方世界领袖的辉煌历程,是一段由弱到强、由争霸到称霸的历史。这期间,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先是步英帝国后尘,进而后来居上,由小到大,在日、英、德、法、俄等各侵华列强中独领风骚。新中国成立后的中美关系又可分为三个阶段:从1972年之前的全面对抗到其后近20年的准同盟关系,至20世纪90年代风风雨雨的10年。在这三个历史时期和三个发展阶段,美国作为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强国,对中国始终推行了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政策。中国始终处于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欺压和盘剥之中。所谓美国居于中美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就是对美国在这200年间一直处于强势地位的写照。
美国在华利益和角色的调整难以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决定了中美关系始终在对抗与合作之间摇摆。对抗与合作并存、对抗多于合作是中美关系这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发生互动作用的主要体现。造成这种态势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在华利益和角色的调整没有能够反映出中国国情剧变和社会转型的时代要求,即当中国社会发生剧变和转型时,美国对其在华利益和角色的调整没有能够作出正确的选择。当国民党政权取代清王朝,实现了以一种剥削制度取代另一种剥削制度的时候,中国社会的性质没有根本改变,中国仍然属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也没有根本改变,因此,美国在华利益得以延续,美国作为中国的宗主国角色无须改变。然而,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发生了质的改变,而美国却没有适时调整其在华利益和角色。应该说,在1949年,历史给了美国一个修正其对华政策的机遇,然而,由于历史的和政治的原因,美国当局却秉承其一贯的对华政策,并发展到仇视乃至于企图以武力方式或和平演变的手段使新中国改变颜色。
中美关系进行积极的调整始于20世纪70年代,即所谓的“小球推动大球”以及后来的一系列互动关系。由于美国在中美关系中居于主动地位,因此,尼克松总统主动前来北京,开启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当然,这个历史性的突破也是中国方面努力的结果。随着中美建交,双边关系在80年代达到一个高峰,也就是所谓的准同盟关系。70~80年代的中美关系表明,中美两国在冷战后期,出于反对苏联霸权的考虑,都在积极调整各自在双边关系中的角色和利益,中美关系从一个下降通道进入一个上升通道,开始走上变敌为友的轨道。尽管在这个上升通道中仍然存在曲折甚至滑坡,但总体上是向前和向上发展的,最终实现了冷战后的首次中美首脑互访,并达成了“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共识。(注:《中美联合声明》,1997年10月29日。参见《努力建立中美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美关系处于可敌可友的不稳定发展期
中美两国对21世纪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伙伴关系”的定性,是双边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美国在积极改善对华关系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对中美关系极具破坏性的举措。那么,究竟如何看待这个“战略伙伴关系”?
从目前的态势看,起码可以对这个定性作如下的解读:第一,“建设性”反映了中国更深融入国际社会并发挥重大作用的意愿,同时也反映出美国欲将中国纳入其体系并使其变为同质性国家的企图,这是对互为友国而不是敌国的关键定性。第二,“战略”指的是中美关系必须从大局出发、从长远着眼、从共同利益着手。第三,“伙伴”既固化了变敌为友的愿望,也进一步确定了这种关系的上下限,即向上不结盟、向下不为敌,预示着中美关系今后将以合作为主,求同存异将成为处理双边关系的主要方式。当然,上述认识必须双方认可,并将不会随着领导人的更替而发生变化,这样的关系才可能平稳而健康地发展下去。
经过两国的共同努力,双方对发展双边关系的战略基础达成了如下共识:即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为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作出共同努力;增进两国间经济合作,谋求共同发展与繁荣。(注:朱成虎主编:《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趋势》,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156页。)作为中国而言,在今后50年内不与强国发生足以使经济建设停滞的大规模战争,是实现国家发展“三步走”战略的基本前提。而对于美国来说,在今后一个时期,维持对其有利的国际机制,是它建立“美国治下的和平”的关键,(注:资中筠:《“美国治下的和平”会出现吗?》,载袁明主编:《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转引自王逸舟:《霸权·秩序·规则》,载胡国成、赵梅主编:《战争与和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162页。)其中最主要的是阻止任何大国具有挑战美国的能力,因此,拉住欧、日只是实现了一半的目标,防止中、俄变成敌人则成为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关节点。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国的对华政策,其底线就是拉其为友、防其为敌。由此看来,在美国那里,“战略伙伴关系”其实就是可敌可友的二元可逆定性,美国在此基础上自然形成了“遏制加接触”的对华政策,体现了从目的、方式到手段上的双重性,从而最终导致这种可敌可友定性的三个特点:第一,中美双方以内在因素作为发展双边关系的战略支点,为双边关系的正常发展开辟了积极的航道。第二,这种定性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既为美国当前国内政党政治及其后变更政策预留了空间,同时,也给我国纵横捭阖带来了一定的周旋余地。我国既可利用美国拉我为友的愿望加速发展经济,也可利用其怕我为敌的心态进行积极斗争。第三,这种定性的可逆性反映了中美关系发展方向二元化与发展过程不稳定性的统一,如果双方走近一点,就可能成为朋友,合作将是双边关系的主流,如果双方距离拉大,就有可能成为对手,对抗将可能成为主流。
中美国家利益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中美关系二元可逆的发展方向
中美关系合作与对抗的并存与交替,其根本原因在于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存在结构性矛盾。这种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第一,美国建立单极世界霸权体系的战略筹划与中国的多极化主张尖锐对立,中国主张在主权平等原则基础上进行求同存异的合作,而美国企图以化异为同的方式建立和维持“世界共同体”。(注: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2版,200页。)第二,美国要建立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以不平等的新型国际经济分工为特征的全球经济体系,与中国倡导的建立平等、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背道而驰。第三,在双边关系上,中国实现崛起与美国遏制中国强大的矛盾在霸权稳定理论的框架内难以得到现实的突破。第四,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差异是一个植根于民族文化传统并主要引起政治纷争的根源。第五,中美两国在经济上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美国巨大的资本和技术优势与中国巨大的市场和劳动力优势构成中美经济合作的现实基础,但从发展角度看,也存在经济竞争甚至摩擦。
中美国家利益的结构性矛盾是引起双方所有对抗的根源,成为当前和今后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主要障碍。正是这种结构性矛盾构成了中美关系上升通道中的上方压力,从而导致中美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一直处于进退交替的发展状态之中。从本质上看,这种结构性矛盾也从根本上决定了中美双边关系的战略基础的脆弱性。一般而言,双边关系展开的条件是两国的内部需求或者是外在因素。由于历史的原因,在20世纪90年年代以前,中国共产党及新中国与美国所建立的双边关系,在战略基础的问题上,始终没有能够找到真正的支柱。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关系是建立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基础之上的。而美国虽与中共有所接触,却仍然给予国民党政府的限共反共活动以极大的支柱。(注:陶文钊著:《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236页、第256~257页。)在20世纪的50~60年代,中美关系主要在美苏争霸格局中运行,美国对华主要是遏制,中国采取“一边倒”政策,所以此时中美关系虽然维持了较长时期的谈判,但主流是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的对抗。(注:朱成虎主编:《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趋势》,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第31~62页。)到20世纪70~80年代,中美关系向前推进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共同反对苏联霸权的需要,因此才出现了以准同盟为特征的中美关系。
外在因素引发中美双边关系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也导致了它的两个特点,既不稳定性和短期性。历史表明,由于各种原因,中美两国当时都只能将发展双边关系视为权宜之计,这是中美关系在将近60年间几度起伏的原因所在。(注:朱成虎主编:《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趋势》,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第10页。)可见,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美两国开展双边关系,基本上是为了对付第三方或与第三方有关,只要外在因素发生变化,中美关系就受到影响。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美之间第一次切实感到需要从自身的角度来考虑双边关系了,因此,中美关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互相摸底的阶段,双方都在思考和探索,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到底在那里?
寻找战略基础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双边关系的战略支柱逐步从外在因素转向内部需求。然而,遗憾的是,两国在寻求合作基础的同时,也遇到了国家利益上的结构性矛盾。尽管中美两国积极努力地寻找合作领域,但正是在合作中双方发现了更多的分歧。当前,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虽然中美关系开始走上变敌为友的轨道,但这种发展趋势具有可逆性,即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具有二元化的特性。如果政策正确,谨慎运作,两国就可能在较长时期内成为互利的友国,如果政策失误,莽撞行事,也可能走向敌对。
中美应该避免而且也能够避免冷战
20世纪90年代,美国外交面对的重大问题就是俄罗斯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在美国国内,尽管主张对华友好的大有人在,但认为应该遏制中国的也不乏其人。(注:参阅[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俞正梁等著:《大国战略研究——未来世界的美、俄、日、欧(盟)和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68~73页。)因此,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对华政策始终在接触与遏制之间摇摆。总体说来,学术界似乎倾向于认为,美国是接触与遏制两种手段交替使用,以接触为主,边接触、边揭制。(注:俞正梁等著:《大国战略研究——未来世界的美、俄、日、欧(盟)和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75页。)事实上,美国采取了一系列遏制行动,如修改美日防卫指针、发展和部署NMD及TMD、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等等。其结果就是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中美两国是否会像美苏那样走向冷战?
面向新世纪的中美关系是否走向冷战,将主要取决于中美两国的政策。在当前的特定历史时期,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只能依靠制定符合客观历史条件的政策,并通过双方的政策互动,才可能避免走向冷战。
历史表明,居于强势地位的美国所采取的对华政策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定向性的作用,当然,中国的对美政策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历史上,美国曾经通过《望厦条约》开启了不平等的中美关系,通过“门户开放”政策实现了在中国的“利益均沾”,通过“扶蒋反共”的策略获得了在华特殊地位并埋下了与新中国对抗的种子,通过侵朝战争、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开始了对新中国的全面围堵。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出于遏制苏联霸权的需要开始调整对华政策,两国关系进入一个相对稳定和友好的合作阶段。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华采取“接触加遏制”的两手政策,在采取遏制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深化与中国的经济合作。美国国会通过了为中国加入WTO铺平道路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法案,就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举措。中国加入WTO是一件具有非凡意义的事件(尽管目前还没有最终加入),它对于中国、美国和世界来说,其影响远远不止于经济,而且还具有政治和战略的意义。对美国而言,1972年尼克松打开了中国的政治大门,2000年克林顿打开了中国的经济大门;对中国而言,1972年中国重返世界政治舞台,2000年中国在经济上融入世界。这两件事本身具有同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它们对台湾问题的解决也意义非凡。1972年我国进入联合国,台湾退出联合国,这是一种对立的、渐行渐远的格局,必然地导致近30年来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紧张。而中国加入WTO后台湾将跟进,这是一个渐行渐近的格局,为我国解决台湾问题打开了新的局面和思路。应该说,美国的这个政策举措与我建国时的美国对华政策虽无本质变化,但在方法上是有很大区别的。
但是,中美不致走向冷战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采取了不同于建国初期的对美政策,这个政策的根源就是改革开放的国策。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中国国际战略的目标就是营造一个有利的国际和周边安全环境,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上,依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广泛开展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关系。邓小平与毛泽东的政策是不一样的,无疑他们的政策都是符合历史规律的,但结果却是迥异。针对美国在新中国刚刚诞生之时进行的经济制裁和封锁,毛泽东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经蔑地说:“多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民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注:《毛泽东选集》,第1385页。转引自陶文钊著,《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472页。)所以,中国选择了“一边倒”的政策。而邓小平面对美国在1989年后的经济制裁,采取的是另一种战略,这就是更加开放的战略,首先是改革自身,同时对外开放。在国内,他解决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在对外政策方面,他提出中国不搞扩张和霸权、不搞势力范围、不搞军备竞赛。这样的政策从根本上将中美关系可能发生的全面对抗引向了经济合作、政治协商和安全对话的航向,从而改变了两国走向冷战的轨迹,扭转到经济合作与竞争的轨道。
当然,政策互动只是国家根本利益矛盾关系的一个反映,它在一定时期内可能会在为影响中美关系的主要因素,但中美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还须从国家利益的交汇点上去寻找。就目前而言,由于中美都采取了不同于以往的政策,因此两国将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冷战。针对中美关系趋于好转但又前途不明的现状,谋合作、避对抗应该成为中美双方制定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
标签:中美关系论文;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论文; 美国史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