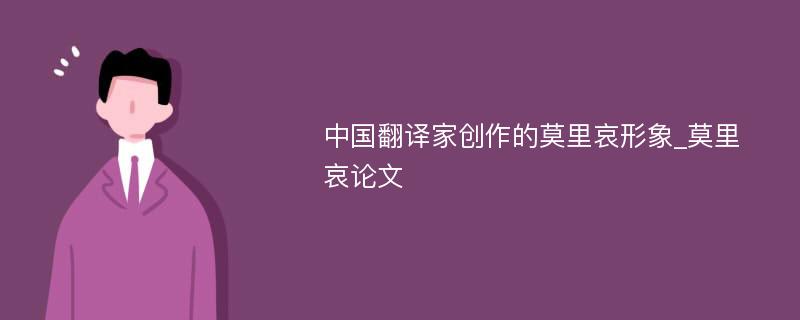
中国译者塑造的莫里哀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译者论文,形象论文,莫里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0)01-0083-06
由于莫里哀在法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所享有的巨大声誉,中国译者开始译介他的戏剧作品,同时也借助中译本的前言、后记等周边文本为中国读者塑造了一个独特的莫里哀形象。本文试图勾勒出中国译者笔下呈现出来的莫里哀形象,同时尝试探究这一形象塑造背后的深层动因。
1.莫里哀的中国形象
1886年,陈季同在法国出版了《中国人的戏剧》(Le théatre des chinois)一书,这部著作是用法文写作的,目的在于向法国读者介绍中国戏剧。此书前言的开篇之句就是对莫里哀的赞颂:
“莫里哀,这位人类最伟大者,堪称勇敢者的头领,他让所有无知做作、高傲自负、硬充才子的腐儒无地自容,他用讽刺取得的进步胜过多次革命的成果。[1](1)
这段话可能是中国人对于莫里哀形象的最早评价。作者强调了莫里哀的斗争精神,此后的中国译者也格外看重莫里哀的这一品质。但《中国人的戏剧》一书的言说对象却是法国读者,此时,中国读者对莫里哀还全然陌生,因为晚清时期的中国人主要是通过译作来接触外国文学的,没有译作发表,无论原作者在自己所处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占据如何重要的地位,都很难被异域的中国读者所了解。
五四时期,文学革命者激烈反对中国的传统旧戏,提倡借鉴外国话剧以建设中国的现代新剧。20世纪20年代以来,随着翻译莫里哀喜剧作品的增多,介绍莫里哀的文章也逐渐见诸报刊。[2]这些文章不仅介绍了莫里哀的生平与创作,而且也介绍了西方学界对莫里哀戏剧的评价。
然而二三十年代关于莫里哀的评价文章,大多数都是西方文学史著作中的转述和摘抄。这些文章中频繁出现的两个词语就是“大戏剧家”和“古典”。这种话语策略实际上是要借助作家的“文学声誉”以招徕读者。虽然称其是“大戏剧家”,当时却没有更多的中文译作可以证明其戏剧天才究竟体现在何处;将他摆在“古典”的位置,在文学进化论兴盛的五四前后无疑是“落后”、“保守”的代名词,虽然值得敬重,但是对中国当时正在进行的文学革命意义不大。直到焦菊隐、曾朴、陈治策以及李健吾这几个中国译者的出现,莫里哀形象才逐渐从一个空洞的“能指”变得具体化、实体化,具有了丰富的“所指”。分析这几位译者对于莫里哀的评述,可以发现他们所塑造的莫里哀形象有以下三个不同侧面:
1.1 形象之一:悲剧人生
在介绍莫里哀的生平和创作时,以上几位中国译者都提到莫里哀既是伟大的喜剧创作者,同时还是优秀的喜剧表演者。但是莫里哀的一生却充满了悲剧色彩:幼年丧母,因从事戏剧和父亲反目以至离家出走,欠债入狱,外省流浪,成功后遭人妒忌中伤,婚姻生活不幸,51岁就凄凉死去。早期的莫里哀喜剧译者如曾朴、焦菊隐、陈治策等人都对莫里哀的悲剧人生寄予了极大的同情,当读者在阅读这些中译本“序”、“跋”中对于莫里哀身世饱含同情的文字时,不知不觉间就拉近了与悲剧主人公的距离。曾朴于1927年翻译出版了《夫人学堂》,在译文后不仅节译了法赅(Faguet)《法兰西文学史》中关于莫里哀的部分,而且还根据当时他所掌握的材料写作了《喜剧大家穆理哀小传》。曾朴笔下的莫里哀生平显得格外悲情:
氏(指:莫里哀)自公布《夫人学堂》、《假面人》(注:即《伪君子》最初的版本)后,仇敌伺隙,同业操戈,几有四面楚歌之慨……[2](4)
氏得意之时代,始于四十岁时,而其不幸之命运,亦于其时来袭,所谓不幸者,即娶妇一事也;……[2](6)
1928年,焦菊隐为自己翻译的《伪君子》译文写了一篇长篇序言,发表在《北平晨报》的副刊上。[3]焦菊隐在序言中,将莫里哀喜剧与中国古代喜剧进行对比,认为两者在喜剧的假面下,骨子里都是悲的。这种“似喜实悲”的特点不仅是莫里哀喜剧的特点,同时也是莫里哀这个人物的特点。焦菊隐认为,莫里哀一生实堪怜惜:
生来虽是富裕,但是自己所赚的钱随手花掉,娶妻又不满意,演剧多受人压迫。即以其《伪君子》而论,不知费了多少努力,委曲求全,将剧本改作,埋没自己的意志,才得表演。他可以说到死也没有完全发挥他的天才[3](45)。
在塑造莫里哀的悲情形象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陈治策。他在《戏剧与文艺》期刊上主持一个小专栏“艺术趣话”,主要谈些文学名人的趣谈逸事。在他翻译莫里哀喜剧《伪君子》、《难为医生》前后,在此杂志上接连发表了一系列与莫里哀相关的文章:《莫利哀的惟一悲剧》、《莫利哀的婚恋》等。[4]他认为《没病找病》是莫里哀仅有的一部悲剧,这一论断不是基于悲剧、喜剧的戏剧类型来划分的,而是因为莫里哀带病演出《没病找病》,戏剧结束当晚旋即病重死去。此外,在谈论莫里哀婚恋的时候,陈治策将现实生活与莫里哀戏剧作品中的婚恋联系起来,认为可以将莫里哀的《妇人学堂》看作是他婚恋生活的写照。老夫少妻不甚和谐的婚姻状态、妻子的红杏出墙和丈夫的无奈气恼,在中国译者的笔下趣味横生。“以意逆志”这一中国文学批评原则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戏剧作品中虚构人物的台词在中国译者那里几乎被当做莫里哀本人亲口说出的历史话语。在这类“艺术趣话”的文章中,写作者和读者都不会去强求历史事实的准确无误,而是本着“趣味先行”的原则,只要能够吸引读者的眼球,就算与历史事实有些出入也无所谓。这些文章短小精悍,故事曲折动人,为中国读者接受“外喜内悲”的莫里哀形象奠定了心理基础。而且,喜剧职业与悲剧人生所形成的鲜明对比,震撼强烈,使人过目难忘。
1.2 形象之二:战斗精神
早在陈季同那里,就称呼莫里哀为“胆大的班头”[1](2),这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明代贾仲明在增补《录鬼簿》中对于元杂剧作家关汉卿的吊词:“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在法国,莫里哀既有勇于抗争、严肃讽喻的一面,也有迎合宫廷、滑稽笑闹的一面,他是一个复杂立体的矛盾组合。而在中国译者笔下,莫里哀性格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其强烈的战斗精神。曾朴在陈季同的指导下阅读过很多的法国文学书籍,其中就包括莫里哀的戏剧。曾朴撰写的《喜剧大家穆理哀小传》,很明显地继承了陈季同的观点,两人都对莫里哀顽强的斗争精神大加赞赏。曾朴之所以选择翻译《夫人学堂》,也是因为莫里哀生活的时代围绕着这部剧作产生了众多的争论和斗争,莫里哀的这部剧作本身实际上就是一份战斗宣言。20世纪二三十年代,莫里哀的剧作《伪君子》先后出现了朱维基、焦菊隐、陈治策和陈古夫等人的不同中译本,《伪君子》之所以被多次重译,与它所具有的社会斗争意义是具有很大关系的。20世纪在莫里哀喜剧翻译方面着力最深的译者当属李健吾。1949年,他在开明书店出版了8部莫里哀译作,在这8个中译本的“序”、“跋”和“译文题记”中,他一再强调莫里哀的战斗精神。李健吾在《可笑的女才子》序言中认为,“莫里哀攻击的不是运动,不是女才子,而是风气”[5](15)。他又据此总结莫里哀喜剧的任务是“要观众笑,但是要笑得有意义,最有意义莫过于让他们体味自己或者自己一群中的言行是非:作品本身是艺术,用意却为服务”[5](12)。李健吾还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理解莫里哀本人及其剧作的战斗精神,“《吝啬鬼》不仅是一出普通的风俗喜剧,而且正如巴尔扎克在小说里面所描绘,成为一出社会剧”,[6](5)。他称赞莫里哀的大无畏精神,认为“像莫里哀这样以进步的姿态攻击他应当侍候的主子们的,勇气应当分外足”[8](8)。莫里哀偏爱下等人,在剧作中贵族、资产者往往受到仆人的捉弄,对于这种情况,译者李健吾结合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有感而发:“中国自来多的是道学先生,前进的,落伍的,都看不惯笑剧式的捣乱胡闹”[9](5)。在50年代中期,李健吾专门写作了《战斗的莫里哀》一书,系统阐述莫里哀的战斗精神以及莫里哀喜剧对于中国现实的借鉴意义。
1963年,李健吾翻译的莫里哀《喜剧六种》出版,在译本序中,他再次强调莫里哀的斗争性。李健吾把莫里哀与西班牙剧作家维迦和英国的莎士比亚进行比较,认为:
洛贝·台·维迦和莎士比亚都曾写出造诣非凡的喜剧,但是把力量全部用在这一方面,把它的娱乐性能和战斗任务带到一种宽阔、丰盈而又尖锐的境地的,到底还是莫里哀。[10](2)
20世纪70年代末,《喜剧六种》在中国再版,在序言中,李健吾仍然坚持莫里哀的战斗性。80年代初,李健吾翻译出版《莫里哀喜剧》四卷本,在序言中,他以简洁凝练的语言重申并发展了此前对于莫里哀的定位和评价:
莫里哀是法国现实主义喜剧的伟大创始人。他的喜剧向后人提供了当时的风俗人情,向同代人提出了各种严肃的社会问题。这里说“现实主义”,因为这最能说明他的战斗精神。它又是法国唯物主义喜剧的第一人,他以滑稽突悌的形式揭露封建、宗教与一切虚假事物的反动面目。他不卖弄技巧,故作玄虚,而能使喜剧在逗笑中负起教育观众的任务。[11](1)
可以说,战斗精神构成了莫里哀形象的内核。李健吾坚持不翻译莫里哀的《凡尔赛即兴》等5部剧作,是因为那些都是宫廷消遣的玩意儿,没有太大的意义。莫里哀依附王权的身份与其战斗精神是存在一定矛盾的,为了强调战斗精神,就势必要限制翻译那些应王权要求创作的定制剧目。对于“定制之作”的排斥,也是中国译者翻译时的策略考虑。
1.3 形象之三:为艺术献身
莫里哀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就是戏剧式的死亡,最能引起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共鸣的就是为艺术牺牲的献身精神。20世纪30年代,陈治策在《莫利哀的惟一悲剧》这篇文章中聚焦莫里哀的死亡:
莫利哀一生所作的戏剧无一不是喜剧,他的最后一出笑剧名叫《装病》(Le Malade Imaginaire),出演时,他担任剧中主要角色,在台上大装病而特装病,弄得台下笑得不亦乐乎。演完,到了后台,他对一友人说道:“我刚才在台上只是假冒病人,可是现在我真病了。”他的友人还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哪知他的一个血管破裂,在演剧后一点钟内,他便与世长辞了。这是他一生的惟一悲剧。[4]
莫里哀带病演出《没病找病》,把戏剧看得比自己生命还要重要,最终可以说是死在舞台上。陈治策致力于改译、导演莫里哀的戏剧,无论20世纪30年代在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还是20世纪40年代在南京国立剧专时期,都和莫里哀一样同时具备编、导、演的三重身份,痴迷于戏剧。陈治策导演了莫里哀的《伪君子》,并使之成为全国各地戏剧院校和业余剧团的保留剧目。甚至陈治策的死亡方式也与莫里哀如出一辙——他死在西南人民艺术学院的排演场上,也为中国的话剧艺术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
焦菊隐对于莫里哀的死亡更是给予了无限的同情和哀挽,他这样记述莫里哀的死亡:
他(注:指莫里哀)一生不倦地努力戏剧,到最后的生命也是为戏剧活的。一六七三年他那剧团演出《幻病》(注:今译《没病找病》),他扮演主角。他是已经患肺病的了,他拼命地表演。当时往看此剧的人非常之多,一连演了四次。在第四次的时候,正在演到行礼的一幕,他刚刚说出一个字,忽然身上抽起筋来,大家把他抬回了家。他自己觉得不能延长生命了,就去请牧师来祝福,但是没有人肯来为这个嘲骂人的戏剧家祈祷。后来还没有等到牧师来到,他的血管已经破裂而死。那正是一六七三年二月十七日,他整活了五十一岁零一个月。当时巴黎的大主教下令各教区不准给莫里哀的遗体以天主教的葬仪。后来还是路易十四的命令,强迫他们下葬遗体。他们要求下葬必须在夜晚,并不能给遗体祈福或举行仪式。到下葬那晚,二百多莫里哀的朋友来执拂,伴随着棺材。民众去送葬的成千上万。[3](44-45)
焦菊隐的叙述,同时掺杂了后世小说家的杜撰之言,但无论真实还是虚构,都灌注了中国译者强烈的感情倾向。
李健吾在自己的文章中更是大加赞扬莫里哀对于艺术的纯粹痴迷,对于莫里哀的死亡也有相当文学化的记述:
他(注:指莫里哀)在公演三场(注:指《没病找病》一剧)之后,感觉异常疲惫,他对他的夫人和一位青年(由他培养后来成为大演员的巴隆Baron)讲:“我这一辈子,只要苦、乐都有份,我就认为幸福了。不过今天,我感到异常痛苦。”他们劝他身体好了再主演,他反问道:“你们要我怎么办?这儿有五十位工作者,单靠每天收入过活,我不演的话,他们该怎么办?”他不顾肺炎,坚持继续演出。他勉强把戏演完,夜里十点钟回到家里,咳破血管,不到半小时或三刻钟,就与世长辞了。这一天是1673年2月17日。[11](9~10)
李健吾的记述与焦菊隐的叙述有所出入,但更加注重细节的渲染,这得益于他对莫里哀各种研究资料的熟稔。关于莫里哀死亡的描写,他显然受到了拉格朗日(La Grange,约1639-1692)的《1659-1685莫里哀剧团账簿与大事记》和1682年版《莫里哀全集》序言的影响。李健吾在中国早期译者言说的基础上,不断重演莫里哀戏剧化的死亡过程,并以其生命重演了这一幕。李健吾作为中国的莫里哀研究专家和莫里哀喜剧的翻译者,他最终也是在伏案工作时与世长辞的,从而真正做到了为学术、为艺术献身。作为艺术工作者,陈治策、焦菊隐和李健吾这几位中国译者都服膺于莫里哀为艺术牺牲的献身精神。
2.莫里哀中国形象建构的成因
莫里哀形象本身就是丰富多彩的,形象的不同侧面在不同历史时期或隐或显。在他自己所处的17世纪,他的朋友布瓦洛、拉封丹等人都赞叹其戏剧天才,他的敌人则对他嫉恨中伤。而在国王看来,莫里哀也许只是供奉宫廷、逗笑凑趣的戏子。莫里哀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几个世纪以来的历史记述为我们留下了莫里哀的一些点滴事迹,不同的历史记述也因记述人立场角度的不同而各有差别。莫里哀作为一个喜剧作家和戏剧表演家,人们往往倾向于从他的艺术作品中找寻他藏在喜剧面具之下的真实面目,有时他被描述成《夫人学堂》中阿尔诺勒弗式的人物,有时他被描述成《愤世嫉俗》中阿勒赛斯特式的人物。然而,无论是喜剧性人物,还是悲剧性人物,莫里哀的形象都显得与他那个时代格格不入。中国译者塑造的莫里哀形象同时融合了历史事实和艺术虚构,而经过他们的翻译和阐释后,莫里哀的这一形象打上了中国文化的烙印。
中国译者译介莫里哀时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制约着莫里哀形象的塑造。对于莫里哀悲剧人生这一形象的凸显,集中在早期译者笔下。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曾朴、焦菊隐和陈治策等中国译者在翻译莫里哀喜剧时,读者对于莫里哀其人其事还是相当陌生的。中国译者在介绍莫里哀的时候,可以借鉴的资料也仅限于几种文学史和英译者对于莫里哀的介绍。在有限的史实面前,中译者以情起文,充分发挥文学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塑造了一个天才戏剧家命运多舛的一生。莫里哀戏剧化的死亡是其悲剧人生的终点,在早期中国译者那里得到了浓墨重彩的渲染。到了20世纪中后期,随着莫里哀研究的逐渐深入和资料的日益丰富,李健吾对于莫里哀生平的叙述较之先前的译者更加客观、准确,但对于莫里哀死亡的记述反而更加文学化。这种为艺术献身的精神随着历代译者的重复言说,也逐渐内化到中国译者的人生实践之中,陈治策、李健吾等人的死亡方式在精神实质上与莫里哀的死亡一脉相承,都是为戏剧而活。莫里哀的中国形象中,在20世纪一直延续不断的是对其战斗精神的塑造。
自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往往倾向于“别求新声于异邦”,输入外国文学以资借鉴、建设中国新文学。对于中国的传统旧戏,文学革命者批评尤为严厉,创建中国现代话剧的希望只能是借鉴西方。新知识分子们的留学经历为此种学习提供了可能性。介绍哪些剧作家,翻译哪些剧本,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因此剧作家和翻译剧本都是被赋予了重大使命而走进中国的。五四以来的社会问题剧,“以人生观为前提虽足号召一时,然一旦出现于舞台之上,则鲜有不失败者”[12]。宋春舫在自己开列的《近世名剧百种》的书目中,认为在中国观众水平尚还“幼稚”的情况下,为让观众切实感受戏剧的娱乐性,舞台应当上演滑稽戏。他推崇英国19世纪斯可里布(Scribe)的佳构剧和法国腊皮虚(La Biche)的轻喜剧,[13]但这两位作家的剧作娱乐成分居多,而社会意义稍显不足。力图创建中国现代喜剧的新知识分子们在寻求一个有足够号召力的榜样,以便开展戏剧运动。莫里哀的喜剧戏剧性和社会性兼胜,而且莫里哀本身声誉极高,有较高的号召力。虽然文学革命的主流是“厚今薄古”的,茅盾等人就认为当务之急需要输入的是欧美的新思潮、新理论,至于古典主义之类的作品可以稍缓译介。但就喜剧之类评介的层面而言,莫里哀是不二人选。为了使莫里哀剧作的翻译切合时代氛围,就有必要强调莫里哀与中国现实的契合,因此,莫里哀的战斗性在每个时期都会加以强调。唯有如此,莫里哀的正面光辉形象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才能保证其剧作的合法译介。尤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莫里哀的战斗精神与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的阐释方式,显然受到当时苏联戏剧界对莫里哀及其喜剧定位的影响。在苏联当时的《法国文学史》中,将莫里哀定位成一个“通过严格的、层层限制的古典主义诗学而为描写客观世界和人物的现实主义方法勇猛地开辟了道路的艺术家”,一个“从欧洲民间剧艺创作的宝库中深入地吸取滋养料来丰富自己、并善于运用生动的人民语言的伟大喜剧作家”。[14](55)莫里哀的战斗性和现实主义特性在20世纪50年代凭借着苏联的强势的文化资源,成为中国话剧界的阐释基础,直至20世纪80年代还具有持续的生命力,余响未绝。
莫里哀形象的塑造同时受制于译者的个性。这几位中国译者除曾朴外,大都具有留学的经历。陈治策留学美国,从英文转译莫里哀的剧作;焦菊隐、李健吾都曾留学法国,而且都与戏剧结缘甚深,一个是戏剧导演,另一个是创作戏剧。陈治策以趣味性的口吻谈及莫里哀的悲剧人生,实际上对于莫里哀本身是相当隔膜的,仅限于一般了解。他所翻译的莫里哀戏剧完全中国化了,你很难从译作的字里行间想象得到莫里哀是17世纪的古典主义作家。焦菊隐曾创办中华戏曲学校,在巴黎求学研究的也是中国传统戏曲,基于对中国戏曲的体认,当他在论及莫里哀剧作的时候,往往在与中国戏曲的比较中分析总结莫里哀剧作的民族特色。在他那里,莫里哀“寓喜于悲”的精神气质与中国传统的文人气质是一脉相通的,由于这种共同的心理基础,莫里哀的悲剧人生和喜剧艺术在中国具备了被接受的前提。李健吾从事莫里哀剧作的翻译时间最长,他对于莫里哀形象的塑造也更细致,更全面。他总结吸取了此前中国译者塑造的莫里哀形象,在以上三个方面无不详细描述。而且他以自己的翻译加强、固定了中国的莫里哀形象。他选择翻译的剧作兼有艺术性和社会性,在具体翻译时,通过序跋、题记和注释,展现莫里哀生活其间的法国17世纪的社会文化,减轻作品和作者对于中国“读者”的“陌生化”程度,提升了译作的可接受性,也使中国读者更加了解莫里哀,更加认同译者塑造的莫里哀形象。
当代形象学研究并不过分关注异国生成的形象的相似性,而更着眼于形象的相异性。研究的重点也从形象本身转向形象塑造者的主体。[15]文学翻译具有“操纵”和“改写”的权力,译者选择翻译哪些作品,有意排斥哪些作品,并通过译本“序”、“跋”、“题记”和“注释”等周边文本参与塑造异国文学形象。莫里哀中国形象的建构是在历史文化语境和译者个性的合力作用下产生的。特定的时代氛围和社会语境决定了莫里哀在中国只能以某一种形象出现,而不能以其他面貌出现。中国的译者基于自己的知识场和审美趣味,根据记载莫里哀事迹的历史事实和艺术创作,参与到莫里哀异国形象的创造过程中。莫里哀形象的塑造是个历时的衍进过程,这一形象体现了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知识阶层对于莫里哀这位古典主义戏剧家的社会总体想象。
标签:莫里哀论文; 戏剧论文; 李健吾论文; 艺术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伪君子论文; 焦菊隐论文; 喜剧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