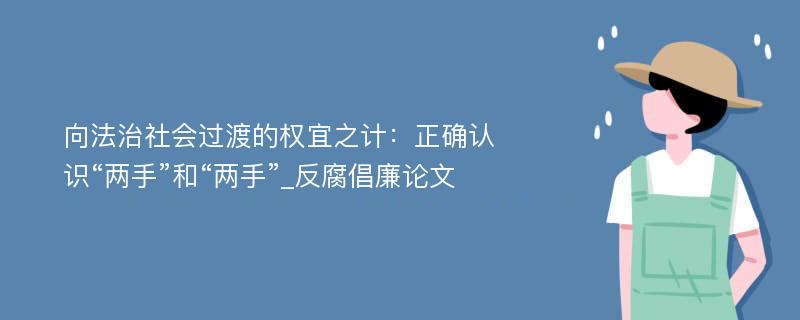
向法制社会过渡的权宜之策——正确认识“两规”、“两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权宜之策论文,正确认识论文,法制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两规”、“两指”措施在反腐败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它的议论乃至争论也随之而起。强调它重要的有之,议论它不合法的也有之。党的十六大指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小而言之,正确认识“两规”、“两指”,是正确接受和正确使用的基础;大而言之,正确认识“两规”、“两指”,有利于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
一、“两规”、“两指”的由来及发展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严重曲折,国内腐败现象呈多发高发态势。纪检监察机关临危受命,承担着查处严重腐败案件的重任。当时,虽然重任在肩,手段却只有一张嘴、一支笔。想要过河缺少桥,查办大、要案件没手段。在此尴尬的情况下,一些本来能够突破的大案要案,活生生地煮成夹生饭;一些本该绳之以法的腐败分子,眼睁睁地任其逃脱惩处。
在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的特殊时期,一种与腐败分子作斗争的重要手段、一种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所亟须的特殊调查措施——“两规”、“两指”也就应运而生。
“两规”最早见于1990年12月9日国务院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条例》(1997年5月9日废止),条例中明确规定:监察机关在案件调查中有权“责令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监察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1993年纪检监察机关合署办公。1994年5月1日施行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规定:调查组有权“要求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说明”。1997年5月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规定:监察机关有权“责令有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人员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就调查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监察法》用“两指”代替了原行政监察条例中的“两规”提法。
可见“两规”、“两指”措施,是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赋予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处共产党员和国家公务员(包括非公务员的监察对象)违犯党纪或政纪案件时可以采取的一种组织措施,是突破要案特别是疑难复杂案件的一种行之有效的重要手段。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时采用“两规”、“两指”措施,使之有法,用之有规,论之有理,言之有据。
“两规”、“两指”是反腐败斗争实践的产物,它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而不断发展、不断完善。
1998年以来,中央纪委、监察部相继出台了4个规范性文件,对“两规”、“两指”措施作了进一步的规范和完善。1998年6月5日出台的《关于纪检监察机关依法采用“两规”、“两指”措施若干问题的通知》对使用“两规”的手段、场所作了3条禁止性规定。2000年1月20日颁发的《关于纪检机关使用“两规”措施的办法(试行)》,对有关使用原则、条件、地点、程序、时间要求、责任追究等作了详细规定。2001年2月1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关于正确使用“两规”、“两指”措施的通知》对严格依法依纪使用“两规”、“两指”措施,再次提出要求。2001年9月28日《中央纪委关于进一步使用“两规”措施的通知》对“两规”的使用作了进一步修订、补充。
采取“两规”是非常严肃慎重的事情,纪检监察机关不能随意对调查对象采取“两规”措施。为此,中央纪委、监察部通过上述规范性文件,一是限制适用对象,只能对已掌握一些严重违纪事实及证据、具备给予纪律处分的涉嫌违纪党员或行政监察对象使用;二是限制适用阶段,只能在案件调查阶段使用;三是限制使用主体,只有一定级别、具备一定条件的纪检监察机关才能批准或使用;四是限制使用时限,从没有统一规定到从严掌握,并在申请使用时报批具体时限建议;五是限制使用地点,从无硬性要求到有具体规定。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加快、随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纪检监察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将同步加快,办案工作也将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
二、“两规”、“两指”的威力及成效
在反腐败斗争中,“两规”、“两指”的威力和成效也日渐显示出来。其威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来自一些基本证据的掌握。查办案件的基础是靠证据说话。没有证据,纪检监察机关不能立案调查,不立案也就不能采取“两规”、“两指”措施。可以这样讲,被调查对象都明白,凡是被采取“两规”、“两指”措施,纪检监察机关都是掌握了自己相当部分的证据;所不明白的是纪检监察机关掌握证据的多与少,而非有与无。在证据的威力下,不少人为争取一个好的态度而得到从宽处理,或多或少都会主动交代组织上已经掌握或尚未掌握的事实。二是来自被调查对象权力的暂停行使。权力在腐败分子手中,不仅是谋取私利的工具,而且是掩盖违法犯罪的保护伞。当组织决定对其采取“两规”、“两指”措施后,被调查对象的权力行使也就暂时中止了。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时段,一些知情者、受害者,不再受被调查对象权力的威慑,而大胆向组织揭发控告;一些涉案人员或受益者的违法乱纪问题,也失去了“保护伞”的庇护。三是来自信息的不对称。“两规”、“两指”期间,被调查对象惟一受到限制的是与外界的联系。这也是外界感到所谓的“神秘”与“特殊”之外。被调查对象不了解在此期间自己的违纪违法问题,哪些已东窗事发,哪些已铁板钉钉?即使案发前,被调查对象把对抗组织调查的方案研究得再严密,口封得再死,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也会使其处于一种必然的劣势地位,具有丰富经验的办案人员就会利用这种比较优势,从证据上、政治上、心理上、时机上精心设计,从中查找其弱点和破绽,予以突破。
“两规”、“两指”措施自施行以来,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发挥了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1990年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230多万件,结案220多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20多万人。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6万多人,厅(局)级干部5千多人,省(部)级干部近200人。从党的十五大到十六大前夕,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861917件,结案842760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846150人,其中开除党籍137711人。被开除党籍又受到刑事追究的37790人。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28996人,厅(局)级干部2422人,省(部)级干部98人。
通过运用“两规”、“两指”措施,纪检监察机关成功地突破了一批大案要案,查处了一批腐败分子,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海关总署原副署长王乐毅等,突破了湛江和厦门特大走私案,产生了很大的震慑作用,为国家挽回了大量经济损失,维护了党纪国法的严肃性,推进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有些腐败案件多发的领域如海关、金融、建筑等,案件多发的势头有所遏制。1999年以来,纪检监察机关收到的群众检举控告信件逐年下降。据国家统计局2002年在30个省(区、市)随机抽样入户调查,73.5%的群众对反腐败工作表示认可,69.1%的群众认为腐败现象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得到遏制,78.7%的群众表示对反腐败斗争有信心。上述三项指标,比中央纪委1996年的随机抽样入户调查结果分别高出11、13.4和20个百分点。2002年总部设在德国的透明国际组织在《全球腐败报告》中认为,中国政府采取的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的措施,“使人们对有效地反腐败抱有信心”。
三、“两规”、“两指”的中国特色
实践证明,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时期,往往也是腐败多发高发时期。“两规”、“两指”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是党的权力机关和国家的权力机关赋予纪检监察机关的一项重要权限,是两种体制转轨时期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所必须的理性选择和现实选择。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因此,评价“两规”、“两指”措施,当以“利一而害百,君子不趋其利;害一而利百,君子不辞其害”为借鉴。切忌以偏概全,感情用事;切忌臆想当然,超越阶段。
首先,“两规”、“两指”措施,直接触及的是腐败分子及其违法乱纪有关人员,维护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次,运用“两规”、“两指”措施所产生的副作用,在现阶段明显低于其正作用;其三,“两规”、“两指”措施,是特定时期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是从“人治”向“法治”过渡时期的暂时之策。
由政策而法规,由法规而法律,是解决“两规”与现行法律存在的某些冲突的正确途径。这方面香港的成功做法可资借鉴。1971年港英政府颁布了全新的《防止贿赂法案》,该法案扩大了犯罪概念的范畴和惩治范围,加重了刑罚。1974年2月,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到1977年10月,廉署在反贪污行动中逮捕了260名警官,与此同时也引起警务人员负面反应和强烈不满,导致数千警务人员游行示威,廉署总部遭到袭击,廉署职员受到凌辱,并威胁廉署如不削权,他们将停止警务工作。在此压力下,总督颁布了部分特赦令,要求廉署对1977年10月1日前的贪污行为停止追究。这种让步反而助长了部分警察的嚣张气焰,甚至提出解散廉署。总督不得不召开立法局紧急会议,通过了《警务条例》修正案,规定任何警官如果拒绝执行命令,即被开除,并不得上诉。当年的港英总督用法制手段平息“警廉冲突”的做法,应该为今天我们规范“两规”、“两指”所参照。香港廉政公署依法对公务员的生活及消费水平高于官职收入水平,或拥有的资产超出其官职收入,而不能做出合法解释的,可视为贪污,并即可对他们立案调查;法庭可下令将他们的财产充公等等,任何人均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而我们目前在这方面的立法还比较欠缺。从某种意义上讲,“两规”、“两指”措施是对现行法律法规和司法体制拾遗补阙的过渡办法,需要逐步法制化。
四、“两规”、“两指”所引发的思考
可以这样说,十几年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大案要案中,如果不是坚决而大胆地行使“两规”、“两指”措施,一些严重腐败案件就很难突破,人民群众对反腐败的信心也很难增强;如果我们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都能坚决按照中央纪律委监部的有关规定,注意宣传、严格执行并正确地运用“两规”、“两指”措施,一些不必要的疑惑就可以消除,一些可以避免的失误就不会发生,党内外对“两规”、“两指”措施就会更多一些理解和支持。
其实,采用虽明知小有不当,却实为有效的非常规做法,并非中国所独创。“两规”、“两指”作为一种非常规措施,在境外和国外也有与之相类似的措施。如,英国法律实行“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原则。但港英政府在香港市民此伏彼起的反贪污示威的强大压力下,为维护其统治,在1971年制定《防止贿赂条例》时,则改变这一原则,把举证责任交给犯罪嫌疑人,确立了“拥有无法解释之财产罪”。再如,美国“9·11”事件后,也出台了不少非常规措施。如对怀疑为恐怖分子的非本国公民设立秘密军事法庭,加大对穆斯林国家的移民和学生的调查力度,扩大电话监听范围,延长羁押时限等,虽有违宪和限制人权之嫌,但得到了国内大多数人的支持和理解。
“两规”、“两指”措施作为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自有其不得已之处。“两规”、“两指”措施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这种手段与纪检监察机关、特别是与党章赋予纪委的职责、任务以及纪委作为党内监督机关的政治地位不相符;二是这种手段的缺乏强制力与被调查对象已严重违法乱纪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不相符。世间任一事物,外延的扩大,必然是内涵的缩小。这些年来,为应对反腐败斗争之急,纪检监察机关在增加“两规”、“两指”调查手段的同时,办案的职能凸现了,监督的职能却明显缩小了。
然而,在当前“两规”、“两指”措施的存在却自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从现在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前,随着体制改革和措施改进的稳步推进,纪检监察机关行使“两规”、“两指”措施不仅会越来越规范,越来越严格,而且所适用的范围会越来越小,适用的频率会越来越低,适用的对象也会越来越少。在纪检监察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前,在司法机关突破领导干部腐败案件方面尚未获得更为相对独立的权力和更加有效的手段前,“两规”、“两指”措施可能还会沿用相当一段时间。同时,在这一改革的过程中,纪检监察机关也将从以办案为主逐步转到以监督为主,从而切实担负起《党章》赋予的监督职责,对党的执行机关及其成员实施党章规定范围内的有效监督。
标签:反腐倡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