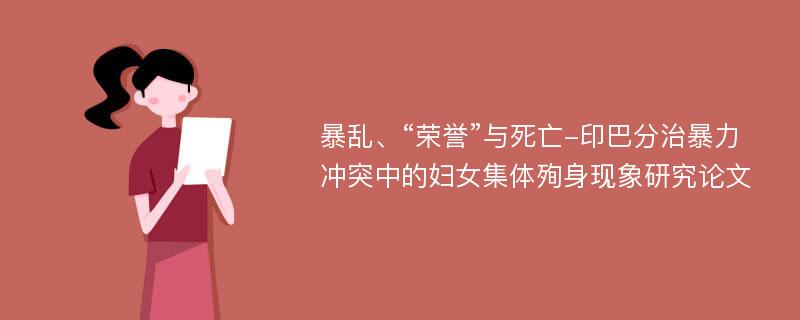
暴乱 、“荣誉 ”与死亡 *
——印巴分治暴力冲突中的妇女集体殉身现象研究
王伟均
(深圳大学 饶宗颐文化研究院,广东 深圳 518060 )
关键词 :印巴分治;妇女;集体殉身;裘哈尔;话语
摘 要 :1947 年印巴分治导致了一次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被迫迁徙运动,随之引发了一场场血腥而残酷的教派暴力冲突。在数次暴力冲突浪潮之中,印度与巴基斯坦妇女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不计其数的女性经历了比死亡更为悲惨的命运。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大浩劫中出现了大量妇女集体殉身的现象,其中既有女性自愿型的集体殉身,也有被男性亲属强迫性的集体殉节。促使这些现象发生的原因,既来自于印度中世纪拉其普特妇女集体殉节传统裘哈尔仪式的影响,又受到分治暴力冲突中频发的针对妇女的特殊暴力行为所引发的妇女自杀症候群的影响。而且,这些现象的出现,反映了存在于印度次大陆特殊社会背景下一系列沉重的性别、民族与国家话语。
1947年8月16日英属印度的划界分治,不仅创造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新独立国家,而且还导致了一次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被迫迁徙运动。根据信仰的划分,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被迫离开划分给穆斯林的巴基斯坦,进入了“新”印度,而穆斯林则离开印度教徒主控的“新”印度,被迫进入一个叫作巴基斯坦(西部和东部)的新国家。伴随这场巨大而混乱的迁徙运动而产生的是一场场血腥而残酷的教派暴力冲突。冲突的族群包括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冲突最严重的地区为孟加拉与旁遮普地区,多次出现宗族灭绝现象。分治所导致的迁徙运动和暴力冲突,“使一千二百万人被迫离开家园。将近一百万人丧生,大约七万五千名妇女被‘另一’宗教的男子强奸、拐骗、劫持、被迫怀孕,成千上万的家庭妻离子散,骨肉分离,房屋被烧毁,村庄被遗弃”[1](P 31)。
在数次暴力冲突浪潮之中,印度与巴基斯坦妇女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劫难,不计其数的女性经历了比死亡更为悲惨的命运。“大量少女和最具吸引力的妇女被绑架,有些常常在绑架者满足了一时兴趣之后就被抛弃,有些则被特殊的男性占有,最终在转宗后嫁给了他们。”[2](P 93)伴随绑架的还有虐待、毁容、肢解与强奸等诸多野蛮的性暴力,许多妇女甚至在遭受性侵后就被当场杀害。“根据官方的估计,印巴分治期间被绑架的妇女中,有5.5万印度穆斯林妇女和3.3万巴基斯坦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妇女。”[3](P 40)教派暴力冲突所引发的大量惨案与妇女遭受的现实恐惧,致使大量的妇女自杀、殉道。在这些妇女自杀、殉道的案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妇女集体殉身现象。
一 、印巴分治暴力冲突中的妇女集体殉身现象
时至今日,印巴分治时期“成千上万的妇女,包括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社会动荡期间被来自其他社群的男性绑架,已是公认的事实”[4](P 153)。从妇女的角度而言,印巴分治的历史是次大陆妇女在肉体和精神上都遭受严重侵犯的历史,然而妇女遭受侵害的历史一直被埋没于直接导致它的政治变故之中。
实际上,妇女作为印巴分治受害者的历史,是与早在地理疆域划分之前,因分治争议而产生的频繁暴力冲突同步的。印巴分治之前,穆斯林联盟为成立巴基斯坦独立国,制造了多起教派暴力冲突。1946年8月16日,为向英国人和印度教徒表明诉诸武力赢得巴基斯坦的决心,穆斯林联盟宣布这一日为“直接行动日”,并制造了1946年印度惨无人道的宗教大屠杀,致使旁遮普地区约有15万人被杀,包括大量的孩子、老人与妇女。“从1946年8月份开始,印度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公共暴力浪潮。以1946年8月为起点计算,这次公共暴力浪潮直至1947年3月的旁遮普大屠杀(the Punjab Carnage of March 1947)的爆发才结束。”[2](P 93) 而事实上,1947年3月西旁遮普爆发的教派大屠杀,还只是旁遮普地区教派暴力冲突的开始,它一直持续到10 月中旬,且在8月再次达到冲突的高峰。此次冲突,“夺去了上百万人的生命,一千多万人流离失所或蒙受财产损失,超过十万的妇女和儿童被绑架”[5](P 103)。1947年6月3日,当印度斯坦-巴基斯坦分治计划宣布时,分散在印度各地的穆斯林、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又掀起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暴力冲突浪潮。“仅1947年6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内,拉合尔市共发生纵火案150次,炸弹袭击25次,持刀砍人17次,谋杀暴力事件5次。”[6](P 79)一次次的暴力冲突,最终导致整个印巴分治期间数万名妇女被绑架或强奸。而妇女集体殉身现象,正是随着各地暴力冲突的爆发,一次次出现在印巴分治这段黑暗的历史缝隙之中。
1.自愿型集体殉身
在印巴分治所引发的大量暴力冲突中,1947年3月的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现属于巴基斯坦)地区教派大屠杀最为惨烈,穆斯林教派分子屠杀了许多非穆斯林村庄的所有村民。印度历史上最有名的托阿·卡尔萨(Thoa Khalsa)村锡克教妇女集体跳井殉身事件,就发生在这次教派屠杀运动中。这次为了家庭与锡克族荣誉以及妇女自身的贞操而自发组织进行的集体自殉事件影响深远,是分治暴力冲突中最为壮烈的事件之一。据印度学者伊安·塔尔伯特(Ian Talbot)记录,在这次事件中,“有超过100名锡克教妇女为抵抗穆斯林的侮辱跳井自杀,整个村子被彻底摧毁,小孩被杀后挂在树上,稍大的女孩则被轮奸惨死”[7](P 4)。而且,殉身的锡克教妇女在跳井之前,先是杀死了她们的女婴,然后再集体有序地投身井中。
小说与电影在还原这段历史上起到了极富创造力的副本作用。如比萨摩·萨尼(Bhisham Sahni)关于印巴分治的小说《塔马斯》(Tamas ,1974),以自己的亲身经验重述了此次事件的真实情境。她在小说中这样描述妇女们集体殉身时的情形,“几乎所有的女人都取下她们戴在头上的围巾,系在腰上。她们全都光着脚,神情激动。就如同中了魔咒一样,从谒师所(gurdwara,锡克教神庙)走出来”[8](P 292),然后井然有序地一一跳入井中。
由巴基斯坦导演萨巴依阿·苏马尔(Sabhia Sumar)拍摄于2003年的电影《沉默之水》(Khamosh Pani ),同样反映了锡克教妇女集体跳井殉身事件。不仅如此,影片还通过其中一名跳井殉身未遂的锡克教妇女,深层次地阐释了印巴分治暴力冲突下宗教和族群观念所导致的历史创伤和个人创伤。影片中的锡克教妇女,在跳井自殉未遂后被一名穆斯林男子救下,带到巴基斯坦,并同穆斯林男子结婚生子。丈夫死后,锡克教徒出身的她,很快被邻居和儿子送回印度,但是遭到了印度亲人的狠心拒绝。在族群身份的两难逼迫与无法找到安身之所的情形下,她最后选择再次跳井自杀。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除了分治教派暴力冲突所带来的历史创伤之外,还有宗教原教旨主义观念对她形成的逼迫,最终导致穆斯林儿子和锡克教徒亲族对她的双重抛弃。
微依那·达斯指出,在正常时期,印度次大陆的社会常态是处于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与性契约(sexual contract)这两大契约的平衡状态之中。建立在“社会契约”想象之上的民族国家,往往“把男人视为一家之长,为‘他们自己的女人’提供保护,使她们免遭敌对共同体的侵犯”[19](P 51)。“性契约”作为“社会契约”的对应物,神圣不可侵犯。两者共同制造了严格的妇女“纯洁性”和“荣誉”亲属关系准则。通过性契约,“女性作为性存在和生殖存在被安置在家庭中,位于‘正当’的男性统治之下”[19](P 27)。
在另一些案例中,为了同样的目的,不同教派所在村落的村民建造起巨大的火葬堆,妇女结伴或携带儿童一起跳入火海。“据印度政府成立的事实调查小组(The Fact Finding Team)记录显示,在拉瓦品第地区的贝瓦尔村(Bewal Village),许多妇女以献祭的形式于1947年3月10日殉身。她们取出自己的床单与被套堆成一堆,点上火,然后跳入其中。”[9](P 3)
根据我国小语种导游缺失的现状,本文提出互助外语导游这一概念,以期充分地将现有资源进行整合,探讨如何以创新的方式有效缓解外语导游缺失严重的问题,利用互助导游的创新模式改善市场上外语导游供需不平衡的困境。
这些妇女们的集体自愿殉身行为,被作为保护贞洁与维护教派荣誉的崇高之举与英雄事迹而广为传颂。而那些被异教徒侵犯劫后余生的妇女,则成为教派与家庭的耻辱以及社会唾弃的对象。
而除了纯粹的性侵害恐惧,最令妇女幸存者感到耻辱的,就是她们的身体被强奸者强行做上带有敌对方政治与宗教特点的印记,包括纹上“巴基斯坦万岁”(Pakistan Zindabad)或“印度万岁”(Jai Hind)的标语和印度教三叉戟或伊斯兰新月符号[15],如此永久地标志着她们各自所在的社区遭受的耻辱。瑞塔·曼昌达(Rita Manchanda)认为,“此类公共暴力事件的记忆镜像,可以在苏拉特(Surat)200名妇女被迫赤裸身体在一个谒师所跳舞或后1947年代印度发生的针对穆斯林妇女的集体性侵犯事件中寻见。那些萦绕在人们脑海中的记忆,往往讲述着为了避免被强奸的羞辱和噩梦,妇女被亲属杀死或集体‘殉身’而‘荣誉死亡’的故事。”[3](P 42)
2.他杀型集体殉身
除了妇女自愿集体殉身外,还有一种更为悲惨的妇女集体殉身形式,那就是强迫性的集体殉节,而其中最为残酷的是,集体殉节的执行者是女性自己的男性宗族或亲属。
印巴分治暴力冲突期间,针对妇女与儿童的袭击频频发生。“为了防止妇女与儿童在这些袭击中被抓获、绑架、强奸和改宗,似乎有无数的妇女和儿童被自己的父亲和兄弟‘拯救’,被屠杀。”[2](P 89)同样在拉瓦尔品第地区,“印度男子曼加尔·辛格(Mangal Singh),在自己村庄遭受的一次袭击期间,逐一斩杀了自己家中的17名妇女与儿童”[2](P 89) 。一些家庭甚至谈到,他们为了“挽救”宗教的纯洁而使几百名妇女“殉难”。“定居在阿姆利则(Amritsar)的一名逃亡者维尔撒·辛格(Virsa Singh),来自斯赫伊克普拉(Sheikhpura),开枪杀死了村中50-60名妇女,包括他的妻子、母亲和女儿以及村中所有被带到他面前的其他妇女。而杀死她们的原因,就是为了拯救她们。”[3](P 42)
有关印巴分治中妇女被自己的男性亲族斩杀的事件与现象,也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如绍纳·辛格·鲍德温(Shauna Singh Baldwin)的《身体的记忆》(What the Body Remembers ,1999),描述了类似的情景,反映了妇女被置于以维护宗教与文化尊严为核心的集体殉难时的处境。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被自身教派与家庭杀害的妇女的实际人数无处可查,因为这些事件,“大都不被当事人(行凶者或被施害者)及其社群视作暴力事件,反而作为英雄事迹传颂”[1](序文P 5)。
再者,新兴产业的创始人团队对企业的控制权有着较高的要求,单纯依靠风险投资基金支持的融资模式可能导致企业的公司治理冲突加剧,甚至导致核心技术团队的流失,不利于新兴产业的长期发展。以苹果的无人车团队为例,技术团队的离职导致无人车研发项目的中断,关键技术攻关的失败导致产品长时间内无法进入试运营阶段,错失了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苹果公司的无人车项目停滞不前时,竞争对手谷歌和特斯拉的无人车项目取得关键突破,苹果公司在无人车研发方面的产业布局陷入两难境地。因此,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对公司治理结构具有较高的要求,如何缓和金融资本与创始人团队需求之间的矛盾成为政府引导基金发展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
在很多案例中,妇女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集体性表现出了自愿被“拯救”的意愿,同意被教派与亲族施以刀斩、枪杀、焗死、绳勒、焚身、服毒等残杀手段。尤其在男性亲属的追忆叙述中,妇女们的这种集体性意愿尤为强烈。更为残酷的是,殉难的过程经常在家庭或村族全体成员的见证之下进行。在印度学者乌瓦什·布塔利亚(Urvashi Butalia)调研的一个案例中,受访者回忆父亲杀死家族中全部女人的过程时提到,当父亲和叔父向在场的妇女们表达宁可将她们全部杀死也不会同意她们被伊斯兰教徒掳走的誓愿时,女人们“没有一个人提出反对,她们没有别的意见,所有的女人都说,就把我们全部杀死吧……”[1](P 175)
耐磨复合刚玉的缺点为:① 抗冲击性能虽然有一定的提高,但和钢质衬板相比,抗冲击性能较差,若采用耐磨复合刚玉,应在容易出现冲击的地方用其它耐磨钢板代替;② 安装牢固性能不及其他衬板。
此外,整首诗歌采用象征手法对相关内容进行隐喻,从而形成多层次的表达形式和复杂的情感内容。多个意象如“橡树”、“木棉”、“凌霄花”等,意象新奇而具有陌生化效果,在文本语境中朦胧而极富意味,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致橡树》不仅完成了朦胧诗美的表达,更完成了舒婷对女性独立意识的强调和理想两性关系的建构。
二 、妇女集体殉身现象的原因探析
布塔利亚曾不止一次强调,印巴分治期间,妇女集体殉身或妇女被亲人杀害的故事不胜枚举。印度学者罗摩旃陀罗·古哈(Ramchandra Guha)也指出:“毫无疑问,分治的主要受害者是妇女,包括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妇女。正如尊敬的辛迪国会议员(Choitram Gidwani)所说的,‘没有任何一场战争,使女性遭受了如此之多的苦难。’女性被杀害、致残、侵犯和遗弃。独立之后,德里和孟买的妓院里挤满了女性难民,她们都因违背了家人的意愿而被抛弃沦落至此。”[10](P 107)这些发生于印巴分治时与分治后的历史现象,大多被印度的家庭、族群与宗族甚至是国家集体性地遗忘。然而,与此不同的是,印度妇女集体殉身现象却被赋予一种特殊的魅力而回荡在历史幽暗的森林,它被一些家庭、族群甚至是宗教群体视为“荣誉”之举。这种回荡并非巧合,而是有其历史的根源。
1.裘哈尔仪式的影响
印巴分治后,人们往往将暴力冲突中发生的系列印度妇女集体殉身现象,同拉其普特(Rajputs)妇女的集体牺牲仪式裘哈尔(Jauhar)相比照,认为印巴分治期间印度妇女集体殉身的行为,是拉其普特妇女集体殉节传统裘哈尔仪式的延续。英文日报《政治家》(The Statesman )在1947年4月15日曾这样报道拉瓦品第地区教派大屠杀中集体投井殉身的印度妇女:“她们看到男同胞不能继续保护她们了,就再度上演拉其普特人自我牺牲的传统。”[1](P 151)
印度历史上,战争频仍而残酷。在战争中,战败一方的男人通常被杀,儿童被卖为奴隶。而妇女,或被奸杀,或成为战利品。为了避免此类不幸降临至王室与贵族妇女,印度的拉其普特人发展出了一种妇女集体殉身的习俗仪式,这种仪式被称之为裘哈尔。这是拉其普特人集体采取的一种信仰表达仪式,是一种由其他族群男性触发或引起的妇女在精神和身体上的反抗。具体而言,是当拉其普特王国面对必然失败的战争,国王和将领即将赴死战场时,为了避免被侵略者占领、奴役和强奸,王国的王后和皇室女性自愿跳入火坑进行的一种自我献祭(self-immolation)。
妇女集体殉身的行为以及其他一些自杀行为,无论是自我献祭,还是服用过量农药,或其他常用的手段,既强调了这些妇女的脆弱性,也可以说是在面对男性权力时一种无奈的选择。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认为,类似拉其普特与其他民族妇女中流行的集体殉身行为,实际上是一种“摆脱穆斯林征服者难以形容的迫害的一种自救行为”。面对男性征服者暴力的妇女的自我殉身行为实际上是“把强奸作为‘自然行为’的一种合法化,最终将有利于对女性的独特的生殖器的占有”[20](P 149)。她同时谴责了印度男性打着“纯洁民族、保护姐妹”的旗号对印度妇女实施伤害。
微依那·达斯(Veena Das)认为:“在文学作品和大众的想象中,印巴分治的‘签名’是由印度和巴基斯坦一起上演的一场侵害妇女、集体强暴、集体拐骗,把受害妇女逐出家园,强令其追求英雄式的死亡,并实施灾后重建工作的悲剧。”[19](PP 17-18)在这场悲剧中出现的大批印度次大陆妇女集体自行殉身或被男性族群处死殉道的现象,同样是妇女在集体意识作用下做出的一项“选择”,这种选择背后反映了印度次大陆特殊社会背景下一系列沉重的性别、民族与国家话语。
在拉其普特人统治的契托尔堡(Chittor Fort)就进行过三次裘哈尔仪式,分别发生在1303年、1535年、1568年。其中,1303年的第一次契托尔堡裘哈尔仪式最为著名。“这次仪式的主人公为王后拉尼·帕德米尼(Rani Padmini),为了避免被德里苏丹王国的苏丹王阿拉丁·卡尔吉(Alauddin Khalji)俘虏,她和其他拉其普特妇女集体执行了裘哈尔仪式,使得这次裘哈尔成为了拉贾斯坦语诗歌歌颂的传奇主题。”[13](P 122)裘哈尔仪式之所以只发生在与穆斯林的战争之中,其原因一方面是印度教其他王国,例如马拉塔人(Marathas),会对被击败的人施以尊严性的对待;另一个原因据称有好几次,拉其普特人寻求和平,莫卧儿人答应了他们的条件,然而,当拉其普特人与他们的妻儿向莫卧儿人投降后,却屡遭凌辱屠杀。因而每次面临战败时,拉其普特人十分恐惧莫卧儿穆斯林敌人的恶名,担心噩梦会降临至他们的家人。2018年,反映1303年裘哈尔事件的历史电影《帕德玛瓦特》(Padmaavat ),因含有王后与穆斯林苏丹王情感纠葛的情节,在印度引发宗教暴乱,致使印度四个邦发生大动乱,且有数百名妇女向法院提出申请,允许她们集体自焚殉身,以此维护拉其普特王后与印度民族的纯洁性。
拉其普特氏族平民妇女和孩子后来也加入了这一仪式,每当王国与男人们无力抵御穆斯林外敌时,就集体举行这种仪式,以此躲避遭受凌辱的命运并表达她们的忠贞、勇敢与反抗。这一仪式逐渐发展成为中世纪时期拉其普特妇女为了从穆斯林入侵者那里拯救其荣誉而进行的大规模集体殉身仪式,拥有长达数个世纪的历史。
(3)植被混凝土团聚体在Yoder法及LB法处理下其MWD、GMD值和R0.25基本表现为SW>Yoder>FW>WS,其中湿润振荡处理的测定结果与Yoder法更接近。
对于裘哈尔仪式,由于与印度历史上十分著名的萨蒂仪式(Sati,寡妇在丈夫的葬礼上自焚)十分类似,也曾受到过严厉的批评。这些批评在非亚洲文化和非印度教的人身上尤为常见。它被认为是对女性非人性化的对待,对丈夫过于忠诚促使了殉身行为的发生。裘哈尔与萨蒂仪式很类似,譬如都采取火堆自焚的形式,都视火葬是一件极为重大的仪式,认为合适的火葬仪式可令死者的灵魂获得安息。这是印度教徒普遍采取的一种形式。这也是为什么在印度次大陆,穆斯林和英国统治者都曾试图阻止裘哈尔与萨蒂仪式。
但是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些重要的不同点。裘哈尔通常只发生在针对穆斯林入侵的战争期间,除了妇女还有儿童,且执行这一仪式时丈夫与妻子往往都还活着。此外,裘哈尔仪式采用集体自焚的原因在于,拉其普特妇女不愿意在死后再遭玷污,她们认为穆斯林入侵者不仅凶残,而且是恋尸狂。根据印度教传统,火神阿耆尼(Agni)象征着纯洁,可以驱走邪灵和恶魔等一切有害物,使用火是处理死亡的最佳方式。对于久经侵害的拉其普特妇女而言,莫卧儿帝国的穆斯林入侵者,就是恶魔一样的存在,唯有以火自焚,才能免遭再次侵害,保持纯洁。
裘哈尔仪式为印巴分治期间印度妇女的自愿集体殉身现象找到了合理的诠释。因为,集体殉身发生在与穆斯林的暴力对抗之中,首先可以清晰地昭示穆斯林凶残与恶魔的特性,强化民族叙事;其次蕴含和反映了印度妇女为维护族群荣誉所体现出的勇敢与殉道精神,这些妇女不仅以这种非凡的牺牲精神和力量使侵略者败下阵去,挽救了族群其他人的生命,同时也以此获取了殉难的永生。所以,人们将这种自愿型集体殉身现象中丧生的妇女的“牺牲”行为,“同拉其普特妇女在丈夫战死后采取的集体牺牲相比,在那种牺牲和这种牺牲之间引出一条直线联系并非反常之举”[1](P 162)。
2.针对妇女的特殊暴力行为的频繁发生
妇女集体殉身现象产生的另一个层面的原因,直接来自于分治暴力冲突中针对妇女的特殊暴力行为的频繁发生。对于历经其间暴力冲突的人们而言,分治带来的心灵割裂远胜于政治与地域上的分割,它打破了此前教派间共同维系的某种社会契约,制造了教派间的重大灾难与创伤。不同教派在这场冲突中,都有选择性地利用了一种片面的理论,指责对方杀害了本教派的教徒,强奸了本教派的妇女,因此必须以牙还牙,进行报复。以宗教基础为身份认同标志的妇女,成为教派敌对双方攻击的首要对象。“因此,在教派暴力冲突中,各教派争相糟蹋、劫持异教徒妇女。这些暴行包括轮奸、强迫女性裸体游街、在身体上刻画宗教标语、肢解器官、绑架、强制转变宗教信仰等。”[14](P 39)由此而引发的深层冲突及灾难性创伤与恐惧,促使妇女自杀症候群的产生与蔓延。
在这场分治暴乱中,伊安·塔尔伯特研究发现,“在暴力袭击过程中,暴徒会将妇女从人群中隔开,进行强奸和掳掠,男人则通常会被残忍地杀害。暴徒在实施屠杀和强奸后,有时还会割下受害者的头发、胡须甚至她们身上的器官相互炫耀”[7](P 10)。砍掉女性乳房或摧残妇女生殖器的暴虐行为,几乎发生在所有教派妇女的身上。“许多妇女的乳房被砍掉,其他一些妇女的生殖器遭到摧残与折磨——在大多数情况下导致妇女死亡。”[15] 在巴基斯坦女作家巴普西·西多瓦(Bapsi Sidhwa)的小说《分裂印度》(Cracking India ,1988)中,作者通过主人公冰果人断断续续的讲述,从一个侧面展现了穆斯林妇女遭受的凄惨情形:“车上的每个人都死了。被屠宰了。他们全是穆斯林。死人中没有一个女人!只有两大包装满女人乳房的麻布袋!”[16](P 159)
剥光妇女的衣物,强迫她们裸体游街,在当时是十分常见的现象。许多学者都曾对此有过讨论。帕拉什·高士(Palash Ghosh)认为剥光妇女的衣物,迫使她们在街上游行,是一种故意行为,目的就在于增强对妇女的创伤和羞辱。针对分治暴力冲突,他甚至更进一步指出,“所有年龄、种族和社会阶层的妇女,都受到了迫害、折磨和强奸”[15]。微依那·达斯(Veena Das)和阿希斯·南(Ashis Nan)甚至调查出,针对妇女的暴力,孕妇都未能幸免。“有些暴徒甚至取出孕妇肚中的婴儿,用砖块敲碎小孩的头部,割下受害者的器官相互炫耀。”[17](P 181)
如何正确引导、教育青年大学生,使其科学合理地利用课余时间,搞好学业管理;如何组织开展丰富多彩、有意义的课外活动,吸引更多学生参与,让他们在活动中增长才智、培养能力、促进身心健康发展、提升综合素质;如何使课内教育与课外活动相互协调,互为补充,产生良好的教育合力,进而提高学校人才培养的质量。这些都是值得学校教育工作者认真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基于此,我们以大理大学工程学院为例,对该学院学生进行相关问卷调查,通过对调查材料整理分析,剖析我校学生的思想动态与精神生活,得出调研结论,提出对策建议。
金正大集团总裁助理杨宏海表示:“青岛的大棚蔬菜发展已成规模,推广应用亲土1号,有助于快速改良当地土壤和品质提升。我们将下大力气选择上百个行政村打造亲土1号样板村,充分发挥亲土种植示范带动效应。”
妇女一旦遭受此类侵犯的悲剧,不仅身体上要遭受巨大的折磨,心理上不断自我谴责,而且还将遭受到亲族的唾弃,成为家庭与整个族群的最大耻辱。而这种来自家庭与宗族的压力,恰恰是妇女不论是否自愿,最终“选择”殉身现象中一个决定性因素。在许多更为悲惨的情况下,妇女的家庭和宗族无法忍受和接纳他们的女性亲族被强奸、遭受玷污和转宗。为了避免此类事件发生,维护家庭与宗族的“荣誉”,本族男性一方面会尽力渲染异族男性的暴虐和恐怖,同时强调“荣誉”殉身的好处与受到的赐福,并强迫妇女自行殉身或亲手杀死她们殉道。“有关丈夫、兄弟、侄子和儿子杀害了他们的女性亲属,以避免他们被强奸和强迫皈依耻辱的故事数不胜数。”[15]分治期间妇女的诸多他杀型集体殉身现象的发生主要源生于此。
因此,印巴分治时期的妇女,不仅面临着对于异族入侵施暴的恐惧,同时也面临着自己的家庭和宗族以道德绑架与“荣誉”为形式实施的内部暴力。
从表8、9结果显示,大鼠血液学指标各剂量组与生理盐水组之间大部分无显著性差异,部分有显著性差异及极显著性差异,但其数值在正常范围之内或无量效关系,故认为其差异无实际生物学意义。
在大多数女性主义者看来,很多妇女殉身的案例,不论是个体行为还是集体行动,都很难被视作一种自愿行为。“特别是羞耻与耻辱的观念已经被深深地根植于他们的家庭与社群,使得妇女内化了这些概念,宁可选择死亡也不愿活在耻辱之中。”[18](P 105)即便是受压力逼迫,殉身妇女的家庭或宗族成员往往矢口否认妇女们是被杀害。在家庭与族群集体合谋掩饰的背景下,维护“荣誉”所实施的暴力脱去了使大量妇女走上死路的暴力与强迫成分,取得了合法性,杀害妇女不再是暴力与罪行,反而成为一种英雄之举。因而,在众多妇女为了家庭、宗族不被玷污的自愿型集体殉身行为中,同样掩盖着男性的共谋。自愿殉身的过程中,妇女所设计的自己的死亡与献身,都处于男性族群的族群设计之中。而在他杀型集体殉身行为中,男性族群针对妇女的这种族群设计,通过外族入侵的语境渲染,则可以变得光明正大,赤裸而直观。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妇女的生与死在恐惧与“荣誉”的夹缝中始终处于一种悖论之境,而跟随妇女姐妹一起,在集体“荣誉”的光环渲染下,不论是为了保持贞洁甚或整个集体的名誉一起自愿殉身,还是央求男人成全她们的牺牲,集体被男性亲属斩杀“殉道”,都要比活在夹缝与悖论之中更为轻松。因为将长期内化于心的贞洁、名誉等观念作为责任来担负,已是灾难语境中她们最能肯定的东西。因而,无论是妇女自愿集体投火、跳井,或集体选择被男性亲属斩首等他杀型殉节行为,只不过是所有自杀或殉道他杀案例中更为壮烈的形式而已。
此外,民族领袖在暴乱中公开的妇女观表达,也是促使妇女们选择集体殉身的因素之一。《政治家》认为,当印度妇女在暴乱中感觉到他们的男人们不再有能力保护她们时,她们不仅复兴了拉其普特妇女的裘哈尔仪式,而且“她们也遵循了甘地先生对印度教妇女的忠告:在某些情况下,从道义上来讲,甚至自杀也比屈服更为可取”[1](P 151)。
本次会议主要就消费需求与产业政策,新时期如何推进消费升级,改革开放40年中国消费发展变迁回顾和展望,个性化消费与供给侧,改善居民消费与新时代经济发展,场景消费——新阶段、新范畴、新命题等多个中国消费转型期最敏感的话题,进行了详细解读和讲解。
三 、妇女集体殉身现象背后的性别 、民族与国家话语
尽管类似裘哈尔仪式的妇女集体殉身现象可追溯至更早(公元前336-323年)的亚历山大大帝进攻印度西北部时期,当时面临战败绝境的一个阿迦罗索伊族(Agalossoi)镇,“20000名男子、妇女与儿童集体投身于他们在镇上点燃的火堆之中”[11](PP 93-94)。但实际上,真正的裘哈尔仪式通常只发生于印度教拉其普特人抵御伊斯兰入侵者的战役中,特别是战争将要结束时。有史料记载的最早的裘哈尔仪式发生在公元712年,著名的阿拉伯将领穆罕默德·伊本·卡西木(Muhammad bin Qasim)攻占西印度信德地区,包围了当时的印度教王国都城达希尔(Dahir)期间。国王达希尔被杀,王后组织守卫都城数月,食物耗尽之后。王后与都城的妇女拒绝被俘虏,最后点燃火堆执行了裘哈尔仪式[12](PP 84-85)。
1.性别话语
在印度次大陆这样一片多元的宗教地域,妇女承载着不同于男性的鲜明社会角色。妇女既在社会生产与繁衍中发挥着物质重要性作用,同时又还代表着维系社会族群共同价值观念的范畴,关系族群荣誉和纯洁。“妇女也被认为比男性更传统,更保守,更有宗教信仰,因而被认为是社群基本价值观念的支撑。”[2](P 93)于是,男性往往通过妇女的纯洁和贞节来把持社群身份。正因为如此,在印巴分治暴力冲突中,女性的身体才会遭受到一种性别化的集体敌意。穆斯林、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在实施暴力或报复行为时,往往故意去寻找其他宗教的女人来强奸和绑架。这是对男性权力的一种炫耀,男性在妇女的身体上实施复仇,也在妇女的身体上庆祝胜利。
裘哈尔原本是著名的拉其普特国王王宫中的一个特殊的房间,名为“裘哈尔·贡德”(Jauhar Kund)。裘哈尔具有“勇气”“珠宝”或“财产”的意思,象征着拉其普特妇女勇敢坚贞的品质。战争期间,这一房间敞而不闭。一旦面临战争必败的情势,集体献祭仪式就会在这一房间内举行。在举行裘哈尔之前,王后与其他妇女在房间内以罗望子(酸角)染手,集体呼喊“巴瓦尼必胜!”(Jai Bhavani)的口号,而巴瓦尼是杜尔迦女神(Durga Maa)的另一个名字。然后,她们在裘哈尔·贡德的墙上印上自己的手印,随即举行裘哈尔仪式。仪式主要在夜间进行,期间,婆罗门祭祀会吟唱吠陀颂歌。拉其普特妇女们会穿上婚纱,手牵自己的孩子,跳进巨大的火葬堆自我献祭,以此表明她们宁可赴死也不愿被侵略者夺取贞洁的态度。裘哈尔仪式结束后的第二日清晨,拉其普特男子会举行萨卡仪式(Saka)。所有的拉其普特男子都会沐浴更衣,穿戴藏红花衣,在前额上涂抹上裘哈尔仪式结束后妻子和孩子自焚后的灰烬,一般是大三昧(Maha Samadhi)的灰记,口含一片图尔西叶(tulsi leaf),然后以一种赴死的心态离开宫殿,像战士一样奔赴战场,歼杀敌人。
ACL是肾上腺海绵状扩张的淋巴管组织构成的良性畸形。其中女性患者发病率高于男性,59%患者为右侧单发,平均直径8.86 cm,平均发病年龄39.5岁[2]。ACL病因学机制至今未能明确,较被认可的假说有:淋巴管的畸形、淋巴管的囊性扩张、淋巴管至临近静脉的堵塞、错构瘤的囊性化生[3]。
沉降监测是进行路基沉降与变形控制的方法,具体的施工流程如下所示:施工准备→观测布点→结构的统计和分析→结果综合分析→判定地层结构的稳定性→地层安全动态分析、提供设计与施工建议书、上报设计与监理单位→反馈设计、施工→是否改变设计、施工方法→新的设计、施工方法。在进行作业的过程中进行数据的检测,科学合理的预测软土路基沉降量以及发展规律,进而为路基的加固提供基础的方案 [4]。
然而,印巴分治及其所导致的暴力冲突,将这种常态打破了。以妇女的身体作为战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相互之间开展的一场为了控制具有性和生殖能力的妇女的战争,致使“性契约”严重错位,从而扰乱了两个新建国家建构彼此新“社会契约”的一切可能性。男性社会主导的妇女集体殉身行为,不论是自愿型集体殉身还是男性执行的他杀型集体殉身,都可以视作两个新生国家的男性企图阻止这种“性契约”错位的极端努力。
2.民族话语
印巴分治暴力冲突,使得妇女的公民身份被吞噬,作为性与生殖力存在的层面被凸显,最终沦为敌对民族强行占有的对象,而这一问题恰恰事关民族荣誉。民族荣誉的维持与恢复,同样依赖于对妇女性功能与生殖功能的控制。“在民族冲突和性暴力方面,女权主义研究指出,妇女的身体被敌对社区的男人视作一片可以征服的领土。”[18](P 105)其原因在于以宗教基础为社会认同的印度次大陆,“性契约”与“社会契约”共同创造的妇女“纯洁性”与“荣誉”传统观念认为,妇女的贞洁是教派民族荣誉的象征,她们的身体承载着宗族繁衍的神圣职责,是一个教派族群中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对教派分子而言,侵犯柔弱的异教徒妇女、强迫异教徒妇女改变宗教信仰,不仅可以显示本教派的男人气概,而且是羞辱异教民族男人的最好方法。”[21](P 134)
于是,当分治暴力冲突爆发时,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教徒争相糟蹋和强奸对方民族的女人,以此满足征服、凌辱对方宗族男性社群的精神想象。在一些极端的案例中,“许多妇女是在寺庙或者清真寺里被强奸的,从一个民族主义者基于民族和宗教的纯洁性的角度来看,无疑构成了双重侵害”[18](P 105)。这些针对妇女的暴行,在印巴分治暴力冲突的语境中建构起某种叙事修辞,即“它将对民族的强暴等同于对这个民族的女性的强暴”[19](P 72)。这种具有象征性的民族报复心理,是导致印巴分治期间数万名妇女遭受劫持与强奸的深层原因。而保护本教派妇女的身体不被玷污,既关系着男人的尊严也关系着宗教族群的荣誉。这是导致分治暴力冲突中为避免本民族妇女免遭劫持与强奸的民族纯洁情结所在,是促使大量妇女集体殉身尤其是他杀型妇女集体殉身现象出现的内在因由。
布塔利亚曾不止一次地重申,关于妇女集体殉身的故事不胜枚举。从印度民族主义历史话语的角度来看,印度妇女集体殉身和其他一些自杀故事,蕴含挽救他人生命意义的壮举,促使侵略者在她们强硬和勇敢的牺牲面前败下阵来,不仅体现了印度教与锡克教民族的英勇和果敢,同时也彰显了这些妇女“甘愿”“放弃”自己的生命为宗教献身的英雄气概。尽管她们已死,但作为一种象征,决定牺牲她们生命的功劳,经过男性修辞策略的不断阐释,既被视作一种勇敢、果断的民族献身行为,同时也被诠释成使她们摆脱比死亡更可怕的厄运的一种幸运之举。
从传统的印度教社会共识而言,“妇女是一个社群身份认同的特权持有者,也是其界限的制定者,被绑架的妇女就成为了越界和社会、文化以及政治界限背离的象征”[4](P 154)。因此,积极地将妇女的集体殉身行为作为家庭、民族与国家荣誉的象征来叙述与纪念,既可以把妇女限制在男性所规定的非暴力范围之内,使她们作为受害者脱卸掉身上暴力和主动的责任,同时,对于那些杀死自己的妇女——妻子、姐妹和女儿们的男性而言,他们拯救了妇女以及民族的荣誉,同时也阻止了越界的发生。这类针对妇女集体殉身所采取的修辞策略,排除了男性行为中所蕴含的暴力成分,妇女以及她们的身体就合法地转变成了承载民族荣誉的容器,同时又凸显了男性维护村族与民族荣誉的果敢,从而将这个民族建构在男性气概之上。
杨先生吃完烟,又从口袋把烟盒掏了出来。我有些着急,他还要吃啊?杨先生把烟盒递到我们面前,指着上面的人像说:“这是马占山将军,你们听说过吗?”
3.国家话语
微依那·达斯认为,印巴分治时期,苦难被性别化,“苦难的性别化”(gendering of suffering)使被绑架与遭受侵害的妇女长期位于男性化民族的国家想象之中,从而促使民族国家话语得以出现于这一时期[19](P 27)。
从一个国家的主权生成层面而言,有序的家庭生活与合法的生殖秩序,保证了家庭作为国家主权的基础来源。妇女及其身体是社会维持荣辱观念的意识形态基础,同时也是家、国赖以维系权力网络的物质基础。布塔利亚认为,印巴分治“提供了把妇女塑造成国家荣誉象征的理论基础”[1](P 147)。因为印巴分治以教派为依据,国家的建构也基于此,被男性控制于家庭内部的各教派妇女的身份认同也基于此。当分治暴力冲突爆发后,不仅妇女作为教派、民族荣辱观念的意识形态基础特征得以凸显,成为他族男性攻击和本族男性保护的对象;同时,妇女作为维系家、国权力网络的物质基础特征也被凸现出来,甚至成为破坏或维护的重点。
印巴分治或印度与巴基斯坦两个国家建构的黑暗面在于,以教派认同为国家建构基础的双方,有着漫长的纷争历史,都清楚妇女在对方荣辱观念中的意识形态基础作用和在权力网络中的物质基础作用,因此有意识地对敌方民族妇女实施攻击、劫持与强奸,目的就在于破坏敌方家庭生活与合法生殖的秩序以及国家建构的基础来源。同时,分治所产生的敌对双方,不论是印度教徒、锡克教徒与穆斯林,都有意识地将妇女的母亲角色与生殖功能与民族国家大业的建构和文化传统的保护联系起来。妇女的身体成为民族与国家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的象征,国家的荣誉被象征性地寄托在妇女的身体之上。这样,国土的被切割被隐喻为国家母亲的身体受到侵犯;同时,国家的妇女的被劫持和强奸以及她们被迫离开家庭、教派和祖国,不仅是家庭、宗族和民族的损失,也是国家遭受凌辱的象征。例如在印度教民族主义修辞与话语中,“印度教和锡克教妇女被穆斯林男人强奸和劫持,构成了谴责巴基斯坦野蛮、不文明、淫荡的背景。从印度的领土(或印度母亲的身体)上形成和分离出了巴基斯坦这个国家,就成了纯洁的印度教妇女遭受强暴的暗喻”[1](P 140)。
此外,从一个国家父权制度建构的层面而言,在印巴分治的暴力冲突语境中,当妇女被性侵、绑架与避免妇女被性侵、绑架暗示主权的功能被夸大时,与此关联的故事就会成为这一语境中基本的故事,超越教派与民族话语,用来描述两个国家如何被建构及其与父权制度的关系。即便是在印巴分治的大语境中,主权继续从家庭中获得生命。作为被规制在家庭中的妇女,如果男性在其作为一家之长的实践中不能对其实施有效的控制,那么国家自身就会丧失生命。遭受侵害妇女的形象与之关联的问题,之所以会如此突出,是因为它关涉两个新生国家的父权对女性的性权力和生殖权力的控制,这种控制奠定了两个国家起源的基础。在异教徒妇女身体上纹上“巴基斯坦万岁”或“印度万岁”标语的现象,是这种控制权力的争夺反映在国家话语层面的极端表现。
由此可知,在印度次大陆这场充斥着妇女集体殉身现象的悲剧背后,无论是“性契约”与“社会契约”的平衡、民族气慨的塑造还是国家荣誉与权威的建构,实际上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三者皆建基于男性对于作为性与生殖力存在的妇女的控制之上。不胜枚举的印度次大陆妇女“选择”集体殉身的现象,只不过是印度次大陆男性集体性对妇女实施控制与规训而形成的一种症候,是次大陆男性重构对妇女控制权的集体性体现。从国家层面而言,“其实就是把国家当作中介,重建丈夫或父亲的权威”[19](P 48)。
对于次大陆上这两个新成立的国家而言,合法化的“社会契约”被认为是必须由男性建构的,因此男性只有通过把女性的性权力和生殖权力牢牢地安置在家庭中,才能维持和恢复他们自身作为一家之长与契约建构者的地位。被绑架与侵害的女性形象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如果能够将男性置于一家之主地位(不是亲属制度意义上的,而是为了国家意义上)的性契约处于危险的境地,那么社会契约就无法成立。”[19](P 35)
在分治暴力冲突来袭与男性家长地位即将崩塌之时,妇女集体殉身这种为“纯洁性”和“荣誉”而死的集体性“壮举”,加之男性对自身在此过程中发挥的“英雄式”影响的渲染,使妇女们牢牢地被继续安置在家庭与社区之中,使作为国家权威必要基础的“父亲”的权威得以继续保持。“性契约”与“社会契约”的平衡在这种以牺牲妇女为代价的象征性控制之中,也得到了一种精神性的维持。基于这种精神性的平衡,男性“从而把这个民族塑造成为一个男性化民族”[19](P 35)。 这种精神性的平衡在印巴分治后两国遣返被绑架的妇女过程中得到了更为突出的体现。对于两个新生国家而言,唯有如此,“父亲”的权威才会更加牢固,民族的男性气概才会更为显著,国家建构的基础才会更加坚实。
我国从改革开放至今,经济快速增长,居民收入不断提高,逐渐从一个人均GDP不足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并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取得这些瞩目成就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经济增速的回落、贫富分化、生态破坏、腐败多发、金融体系脆弱,这些符合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正是中国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 、结语
印巴分治暴力冲突是人类历史上因以教派为依据进行国家建构而导致的一场血腥而残酷的灾难。妇女在这场灾难中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与创伤,她们或被他族男性强奸、劫持和杀害,或被迫离开家庭、教派和祖国,或死于她们自己设计以及与本族男性一同设计的殉道计划之中。妇女集体殉身现象在众多妇女死亡故事中最引人注目,这些壮烈而沉痛的死亡现象背后,隐含着一系列沉重的性别、民族与国家话语,暴露出印度次大陆特殊社会长期存在的性别、宗教与民族矛盾。实际上,妇女自杀现象的出现,印巴分治及其导致的暴力动乱只是其表面的、直接的原因,真正导致妇女在这场分裂冲突中被肆意地作为复仇暴力的牺牲品的根本原因,是印度次大陆女性——不论是穆斯林妇女还是印度教、锡克教妇女——自古以来低微的社会地位。即便是在这些妇女的内部,也因为教派的原因存在着明显的分化,同样作为受害者的穆斯林妇女被排斥在了各种话语之外,几乎在印巴分治的历史叙述中不可见。
印巴分治暴力冲突停止之后,如何恢复分治带来的破败局面成了两个新成立国家工作的中心。妇女的安置与重返问题是国家恢复工作中的重点。从后期的恢复情形来看,遭受绑架与侵害幸存下来的妇女,“通常又经历了再次或三次伤害:第一次是她们遭受绑架;第二次是印巴分治后出现的许多违背她们意愿而将她们‘重返家园’的案例;第三是她们在遭绑架后和被重返家园前所生下的孩子,被新的家庭剥夺或被原初的家庭拒绝”[22]。这些暴力继续存在于印度次大陆妇女的日常生活与集体记忆中。在后印巴分治的许多年里,众多妇女被侵害的故事不再为人提起,那些经历过苦难幸存下来的妇女们自身也拒绝去回忆这些往事。这些故事里隐藏着很深的道德力量,暴力冲突中针对妇女身体的侵犯,将人性中的邪恶面赤裸裸地呈现出来,是无法用语言言说的。男性在印巴分治暴力冲突中所犯下的错误,被妇女慢慢深藏进内心,妇女们饮下所有的痛苦,通过沉默的编码隐瞒了男性的罪恶,同时也保护了她们免遭道德力量的侵蚀。唯有许多妇女集体殉身的事件,却通过家庭叙事和族群赞歌的方式流传了下来,时不时穿透印巴分治“血流成河”“尸横遍野”这样一类司空见惯的大历史叙事,被记录在某些民族主义与女权主义的历史档案之中。
[参考文献 ]
[1][印度] 布塔利亚·乌瓦什著,马爱农译.沉默的另一面[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2] R.Brass,Paul.The Partition of India and Retributive Genocide in the Punjab,1946-47:Means,Methods,and Purposes[J].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2003,5(1).
[3] Manchanda,Rita.Book Review on Borders & Boundaries:Women in India’s Partition(Menon R.,Bhasin K.)[J].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99,58(3).
[4]Panjabi,Kavita.Book Reviews:Ritu Menon and Kamla Bhasin,Borders and Boundaries:Women in India’s Partition.New Delhi:Kali For Women.1998.274 pages.Rs.300[J]. Indian Journal of Gender Studies ,1999,6(1).
[5]Ahmad Chattha,Iiyas.Partition and It Aftermath :Violence ,Migration and the Role of Refugees in The Socio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Gujranwala and Sialkot Cities ,1947-1961 [D].New Delhi: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2009.
[6]Ilahi,Shereen.The Radcliffe Boundary Commission and the Fate of Kashmir[J].India Review ,2003,2(1).
[7]Talbot,Ian.The Deadly Embrace Religion ,Politics and Violence in India and Pakistan 1947-2002[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8]Sahni,Bhisham.Tamas [M].New Delhi:Penguin Books India,2001.
[9]Lester,David.Suicide and the Partition of India:A Need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J].Suicidology Online ,2010,(1).
[10]Guha,Ramchandra.India after Gandhi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s Largest Democracy [M].Picador,2008.
[11]Smith,Vincent Arthur.The Early History of India from 600B .C .to the Muhammadan Conquest ,Including the Invasion of Alexander the Great [M].Oxford:Clarendon Press,1914.
[12]Chatterjee,Partha.Empire and Nation :Selected Essays [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0.
[13]Weinberger-Thomas,Catherine.Ashes of Immortality :Widow -Burning in India [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
[14]曾林华.1947年旁遮普教派暴力冲突研究[D].西华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15]Ghosh,Palash.Partition of India and Pakistan:The Rape of Women on an Epic,Historic Scale[EB/OL].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2013-08-16.http://www.ibtimes.com/partition-india-pakistan-rape-women-epic-historic-scale-1387601.
[16]Sidhwa,Bapsi.Cracking India [M].Minneapolis:Milk Weed Editions,1991.
[17]Das,Veena and Nan,Ashis.Violence,Victimhood and the Language of Silence[A].The World and the World :Fantasy ,Symbol and Record [C].Veena Das(ed.),New Dehi:Sage,1986.
[18]Gonzalez,Manchon B..Women and Ethnic Cleansing:a History of Partition in India and Pakistan[J].Gender Technology &Development ,2000,4(1).
[19][印度]微依那·达斯著,侯俊丹译.生命与言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0][美]佳亚特里·斯皮瓦克,陈永国译.属下能说话吗?[A].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1]Srivastava,Sumit Saurabh.Revisiting Partition,1947:Gender,Community and Violence[J].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98,(4).
[22]Major,Andrew J..“The Chief Sufferers”:Abduction of Women during the Partition of the Punjab[J]. South Asia Journal of South Asian Studies ,1995,31(Sup 001).
Riots ,“Honors ”and Death :A Study on the Indian Women ’s Collective Immolation Phenomenon in the Violent Conflict of Partition of India
WANG Wei-jun
(Jao Tsung -I Institution of Culture Studies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
Key Words :partition of India;women;collective immolation;Jauhar;discourse
Abstract :The Partition of India in 1947 led to a large-scale forced migration movement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which also led to a large number of bloody and brutal sectarian violence.In the wave of several violent conflicts,women in India and Pakistan suffered unprecedented difficulties.Countless women experienced more tragic fate than death.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emergence of the phenomenon of lots of women’s collective immolation during the carnage,included not only women’s voluntary collective immolation,but also obsessive collective sacrifice forced by male relatives.The causes of these phenomenon,both from the impact of the India medieval Rajput women’s collective self-immolation traditional ceremony Jauhar,and also the impact of women’s suicide syndrome caused by specific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violent conflict of Partition of India.Moreover,the emergence of these phenomenon reflects a series of heavy gender,national and national discourse in the special social background of India.
中图分类号 :D441 .9
文献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4 - 2563 (2019 )02 - 0106 - 10
作者简介 :王伟均(1984 - ),男,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研究方向:印度文学与文化、中印文化交流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印度英语小说中的底层叙事研究”(项目编号:17 BWW039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 :绘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