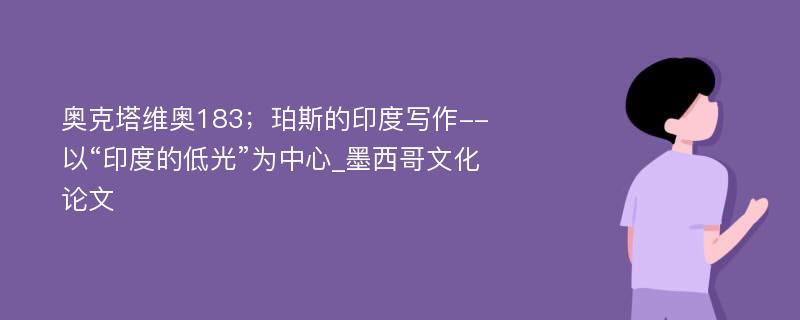
奥克塔维奥#183;帕斯的印度书写——以《在印度的微光中》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微光论文,印度论文,帕斯论文,奥克论文,维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诺贝尔奖获得者,墨西哥著名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1914-1998)一生游走于多种文化之间,20世纪60年代的印度之旅对他影响尤深,从哲学思想到诗学观念都受到印度宗教、文化的深刻洗礼。但是,国内学界对这位诺奖得主的研究仍不多见,对他的印度书写更罕有关注。实际上,在帕斯创作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诗集《东山坡》和诗论《猴子文法学家》就是这段印度岁月的重要收获,本文要着重探讨的著名游记《在印度的微光中:诺贝尔桂冠诗人帕斯的心灵之旅》(Vislumbres De LA India)更是他旅居印度观察与感悟的结晶。帕斯在书中坦承:“我在印度接受了数年的教育,而且不局限于书本。虽然这种教育只是略涉一二,也会永远仅止于皮毛,但仍使我受益匪浅。那是一种情感的、艺术的、精神上的教育。它的影响力在我的诗、散文,以及我的生活中皆历历可见(In Light of India 23)”。 帕斯西班牙语原著的书名Vislumbres De LA India被英译者译为In Light of India,虽然英文译名没有忠实地将Vislumbres De LA India直译作《印度一瞥》,但是in light of“在……的光照下”、“鉴诸……”的深层义涵更好地体现出帕斯对印度文化一种谦逊的、感激的、“接受教育”的态度。本文就将通过对这部作品的深入剖析,探讨帕斯笔下印度乌托邦形象产生的根源,以及由其复杂的身份认同带来的文化心态:“有根基”的世界主义。 一、异域期待与诗性言说 帕斯和印度有着特别的因缘,1951年他作为墨西哥驻印度大使的助理秘书,首次抵达印度。1962年,又以墨西哥驻印度大使的身份重返新德里,直到1968年为抗议墨西哥政府镇压学生民主运动愤然辞职,奉使印度长达六年时间。与印度直接、深入地接触,使得帕斯的人生与文学创作受到了深刻的影响。 帕斯是拉美第一位有印度生活经历,直接与印度文化进行交流的诗人。他对印度文化的最初了解主要是经由一些欧美作家、东方学家的原著和其在拉美少量的译本,如《微光》中曾引用的弥尔顿、穆瑞的作品。帕斯的好友,法国著名诗人亨利·米肖对佛教、道教思想和东方美学精神的推崇也使帕斯受到很大影响。而20世纪初,美洲文化的亚洲起源说在人类学、考古学界得到一定认可的事实,让熟稔拉美学界动态的帕斯对印度的观察与研究,某种意义上也带上寻根意味(德维斯·巴尔德斯、里卡多·梅尔加鲍64)。因此,帕斯的印度想象被先在地赋予了一种好奇感、亲切感以及东方学家眼中带有的神秘亮色。 第一次在孟买市区游览,帕斯就被“耀眼的美刺得张不开眼”(12)。那纯真而又神秘、古老而又充满生机的印度文明就像远方发出的一道黎明微光,在满眼惊奇的诗人眸中闪耀,他的笔下常常流淌着极富诗意的描写: 我永远忘不了有一天下午,我无意间漫步至一座小清真寺中。寺里空无一人。墙壁是大理石打造,壁上刻有《古兰经》的经文。上方是平静祥和的蓝天,只有偶尔一群绿鹦鹉飞越,才会打破这股静谧。(18) 帕斯一直将时间视为文学经验的核心,努力寻求对“现时”的强烈体验,“只有很难得的几次,我体验到那种时间之门轻轻打开,万物与我为一的状态”(qtd.in Adam)。而在印度这个小清真寺静谧的午后,诗人就体验到这种状态。 相比很多西方观察家来说,帕斯对印度的评述就公正得多。“衣衫褴褛的流浪汉”与“仪貌堂堂、垂视众生的老者”(10),“粪便与茉莉”,“百合花柄般纤细的少女的笑声”与“坐在拜火教圣者雕像下的麻风病患者”(10),这些看上去如此冲突的图景,被帕斯平等地摄入文字,没有任何过渡地并置在一起。这与作为诗人的帕斯对诗歌意象的深刻见解是分不开的,“每一个意象——或每一首由众多意象组成的诗——包含着许多矛盾的或不一致的含义,它包容着这些含义,或使之协调而无损各种含义的存在”(《帕斯选集》(上)318)。这种调和体现出了帕斯展示同时涌现的矛盾意象的超现实主义态度。但同时,传统的东方思想也浸润了帕斯的诗学理念,“在诗集《东山坡》中帕斯就已经接受了二元对立、矛盾冲突仅仅是幻相,此即彼,彼即此,俱为空的佛教思想”(Bhattacharya 17)。帕斯认为,东方思想这种“此即彼”的圆融境界迥异于西方传统的逻辑思想,而它恰恰是“诗歌的根”。在最终成书于20世纪90年代的《微光》中,可以看出不仅东方的诗歌技巧融入了帕斯的诗学理念,这些技巧所要表达的世界观,特别是佛教的世界观更深刻地影响了帕斯,它使帕斯对印度社会表象的观察不失中正,进而对印度民族纵欲又禁欲、渴求物质又崇尚贫苦的复杂特性也有了准确的把握和理解。 对印度各种艺术,帕斯也有诗人独特的感受和理解:“五味杂陈,不分先后”(86)的印度料理,让帕斯从中发现了所有印度艺术品都奉行的对“整一性”(unity)的热爱。实际上,复杂冲突的“味”最终统一于“喜”的最高体验是印度“味论”的核心思想。帕斯虽没有深入到这一层面,但他凭借诗人敏锐的直觉把握住了渗入印度料理和其他各种艺术品的这一审美特点。印度的拉格音乐是一种回旋变奏曲式,回旋主题不断出现,仿佛生命的轮回,而插部则将回旋主题的素材进行变奏,带来灵魂的超越感。帕斯从中领悟到的“完整与空白”(138)正是拉格音乐带来轮回感与超越感的魅力所在。诗人的通感还使帕斯发现,这种完整与空白的张力超出了音乐,同样体现在印度的诗歌与哲学当中。 对于梵文诗歌的评价,尤见帕斯精深的诗歌艺术修养。帕斯评价梵文诗歌是一种“思想与感官、抽象意念与纵情声色出人意料地结合”(142),“它使人类的两大能力:视觉与理解力,趋于一致”(144)。梵文诗创造出的工笔画式的观感与浮雕式的触感,对于一直关注诗歌的视觉感受与空间创造的帕斯来说,无疑极具吸引力,虽然他也指出梵语的细致使它难以达成中国与日本诗歌令人赞叹的留白。性爱的快感是梵文诗的重要主题,但是其内在精神中肉欲与爱情的结合,感官与心智的对话,身体与宇宙的同一也给予帕斯极大的触动。帕斯认为灵魂与肉体的关系在西方思想中对立甚至恶化了,而梵文诗的性爱描写中洋溢着充满激情与生命力的爱。“正是通过思想和性爱的结合,帕斯才使那些关于诗歌的持久思考具有直接的可感性”(《帕斯选集》(上)560),对帕斯这位伟大的爱情诗人来说,欣赏与学习梵文诗的乐趣不言而喻。 二、原乡镜像与光照体验 “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同时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让·马克·莫哈39)。作为自我创造物的“他者”形象,如同一面镜子,具有同时表现“他者”也映射自我的双重功能。帕斯对印度的一见倾心除了他特别的诗人气质使然,更重要的是,印度的历史现实成为墨西哥的文化镜像,对墨西哥社会的思考引发了帕斯对印度相似问题的关注。在乘火车穿越印度平原时,他就想到了墨西哥革命中铁路沿途尸横遍野的场景与印度1947年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大屠杀,“印度的荒诞使我想起了另一种荒诞:我自己的国家”(15)。 让·马克·莫哈在论述比较文学形象学的方法论时,将作家对异国形象的塑造划分为两种类型:意识形态形象与乌托邦形象。意识形态形象“将群体基本的价值观投射在他者身上,通过调节现实以适应群体中通行的象征性模式的方法,取消或改造他者,从而消解了他者”(35),“相反,乌托邦的描写则具有颠覆群体价值观的功能。这种由于向往一个根本不同的他者社会而对异国的表现,是对群体的象征性模式所作的离心描写”(36—37),虽然意识形态形象与乌托邦形象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辩证转化的,但是从帕斯的印度书写中,我们更容易读出一种印度乌托邦形象。帕斯也注意到印度社会“荒诞的”一面,但他更希望从印度种种独特的文化价值观念中寻找启发,他对作为原乡镜像的印度相关问题的思考与理解从而为我们呈现出印度形象的另一面。 对比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政治乱象,帕斯认为印度人很好地继承了英国政治的遗产。独立战争并未使拉美国家走上现代之路,反而造成军阀割据和长期内战。“相较之下,印度不是经由武力抗争获致独立,而是凭借长期的民主进程。因此,它避免了地方军阀坐大”(130)。他同时也指出,印度的殖民地模仿行为是“依据英国体制的原则而对英国统治进行批判”(103),模仿也成为被殖民者的抵抗策略,正如霍米·巴巴所说,“模仿既是相似也是威胁”(86)。印度人的模仿并非可笑的崇洋媚外,而是从英殖民者手中拿来了现代政治体制,实现了国家独立,开创了政教分离、民主政治的新传统。 对印度的种姓制度,帕斯也有不同寻常的见解。他注意到种姓的“主要特色之一就是它们抗拒改变”(60),但是却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这种“不变”的价值。在帕斯眼中,印度的种姓以其超强的凝聚力,形成了“同舟共济的社会”(59),使得人们能够不变地维系着与宗教、地域、语言、祖先、亲属的关系,相亲相爱,同甘共苦,不致在现代个人主义的泛滥中陷入“孤独的迷宫”。 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过往历史与当下发展的关系,也是帕斯的印度书写着力思考的问题。帕斯意识到印度人对历史传统的暧昧态度,而这正是由他对墨西哥现代化问题的长期关注引起的,“两国都面临一个对我们自己的传统充满敌意的计划。现代化是由批判我们的过去开始的”,“它与过去决裂,又试图抢救过去”(80)。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演说《对现时的寻求》中,帕斯指出:“现代性将我引向自己的开端,将我引向远古。决裂变成了和解”(《帕斯选集》(上)569)。与过往“和解”,找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桥梁,正是有着广阔心灵的诗人在多年的游历与思考中,为同样陷入现代性困境中的墨西哥与印度试图找到的出路。 “在印度,认为时间是幻觉,而在西方,唯一的真实就是时间,就是说,是进步和对未来的征服”(《帕斯选集》(下)568),帕斯非常欣赏这种与拉美的环形时间观和西方的线性时间观迥异的印度时间观,并希望能以此矫正日益极端化的西方现代时间观,卸下现代人与时间赛跑的负担。同时,大乘佛教特别是龙树思想对过去、现在、将来时间概念的否定,启发了帕斯自己极具深度的“现时”观念,这一观念最终成为诗人现代性思想的核心。对于帕斯来说,现代性不再是一个统一的、稳固的、延续的时间流,它是正在进行地无休止地探寻每一个具体的“现时”意义的概念。复杂的印度国情让他认识到,即使处在同一个社会,不同宗教、种族、社会阶层的人也可能并不生活在历史长河的同一阶段,把握住个别的、冲突的、鲜活的“现时”才是务实的态度。 按照形象学的观点,“在按照社会需要重塑异国现实的意义上,所有的形象都是幻象,如同所有的虚构作品都是按照一个更高层次的现实主义重塑现实一样”(让·马克·莫哈39)。帕斯的光照体验正是源于对同为古老文明,又同样经受了殖民帝国的长期统治,本土文化受到极大伤害的印度一种“理解之同情”。将印度在发展中的成败作为照亮墨西哥知识分子头脑的一缕微光这种潜意识,使得帕斯对种姓制度等印度政治、文化现象的理解难免有失理想化。即使在种姓制度已然消弱的今天,“贱民”与“婆罗门”等高种姓之间也很难找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怀”,相亲相爱、同舟共济的关系从来都只是存在于同一种姓内部。高低种姓之间在日常生活习俗、社交、婚姻、职业、教育等方面至今仍然藩篱重重,自我封闭、相互隔离的种姓圈子并不能形成整个社会的凝聚力,种姓歧视、暴力冲突甚至成为割裂社会的离心力。而种姓政治化对印度宪法中明确的世俗主义、政教分离的立国原则更是形成莫大的威胁,事实上,“教派主义的兴起明显地与帕斯进步民主、兄弟情怀、理性批判的理想背道而驰”(Gonzalez-Ormerod 536)。试图从印度文化中寻找借鉴的帕斯恰恰忽视了这些。虽然类似种姓的等级制度在世界上许多民族都存在过,但种姓制度在印度能够绵延千年却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根源,“业报轮回观是这种等级安排的思想稳定器,世袭、内婚、职业限定等方式又对社会等级不断加以黏合和强化,使得种姓制度具有天意神授、不容置疑的宗教性,又富有生活实践、易于操作的世俗性”(郁龙余95)。脱离了印度的文化语境,种姓制度在今天的其他民族已经不可能存活,遑论借其疗救现代个人主义的痼疾。 三、有根基的世界主义 “有根基的世界主义”是当代美国著名人文学者夸梅·安东尼·阿皮亚提出的一个概念。“有根基”的世界主义者不排斥给予特定地点的人民首要的关注,但同时能充分尊重和聆听不同民族人民的声音,“归属于我们的分支,热爱我们在社会中所属的小社团,是公共情感的第一原则。我们朝祖国和人类的爱前进,它是这一系列中的第一个环节”(Burke 202)。阿皮亚在论述“有根基的世界主义”时,曾借用穆勒的一句话表达这种世界主义的理想,“迄今为止,受过教育的人很少在不犯错的情况下培养出一种好品质,不断地将他们自己的观念与传统、与其他地方的人的经验比较是不可或缺的:没有哪个国家不需要向其他国家学习,不管是特殊的艺术或实践,还是它自己较弱的品格的本质方面”(337)。帕斯就是少有的具备这样观念和素养的作家,立足于源远流长的墨西哥文化,同时将其置于广阔的世界视野之中,从世界多种文化的烛照中获得对墨西哥文化观念的启发。 帕斯的祖母是印第安人,母亲是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的移民,他在一个土著文化与欧洲文化相交融的环境中度过了童年,自幼学习法语,接受法国和英国式教育。对于印(印第安)欧混血的帕斯来说,虽然没有经历过移民的迁徙,他也深切体会到独立后的墨西哥人强烈的孤独感,“墨西哥人既不愿意当印第安人,也不愿意当西班牙人,同样也不愿意当他们的后代,而是否定他们。他只是断定自己是一种混血的抽象,是一个人。他重新回到了乌有。他要从自身开始”(《帕斯选集》(下)59)。 虽然存在身份认同的难题,但是帕斯努力走出困惑,超越孤独。他发掘墨西哥古老的神话传说、民间艺术、风俗习惯,寻找传统与现代的接点;他一方面热爱西班牙语,另一方面又清晰地认识到,欧洲语言在移植到美洲后,重新生长并发生了变化;对于印度、日本、中国等东方国家文化,他也非常着迷,在他的作品中,“印度或日本经验的存在如同阿兹台克人的年历存在一样自然”(《帕斯选集》(上)559)。可以说,帕斯是一个思想上的“游牧人”,他一直在从各个民族的不同文化中积极地汲取养分。卡洛斯·富恩特斯就曾评价帕斯是“墨西哥的儿子,拉丁美洲的兄弟,西班牙的继子,法国、英国、意大利的养子,日本和印度的真正亲密客人,美国的私生子(因为现在我们都是),帕斯向文明的所有接触开放”(Fuentes 38)。 对于帕斯来说,真正的墨西哥认同“不应该仅仅围绕着清晰的传统意识,和对墨西哥大革命的理解,而应将墨西哥置于与拉丁美洲、进而与整个世界的价值关联中”(Hoy 370)。在对阿兹台克历史的研究中,帕斯发现了墨西哥人“孤独”的传统基因,而在对世界现代文明的探索中,帕斯洞察到,“孤独”是现代人的普遍生存状态。当代的种种危机,并不在于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冲突,而在于现代性内部的矛盾。帕斯对墨西哥社会文化的现实关怀因为在世界语境中的思考而深化,而对世界现代性问题的考察也由立足于墨西哥民族心理的剖析扩展为沟通人类心灵的探索,在帕斯的身上,“有根基的世界主义”文化心态得到了最佳诠释。 对帕斯来说,虽然印度之旅并没有使他放弃对墨西哥文化本源性的认同,然而这位墨西哥作家却为亚洲的文化影响力震慑:“亚洲起源说不能使我信服,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如果说我的理智否定它,但我的感觉却接受它”(德维斯·巴尔德斯、里卡多·梅尔加鲍64)。理智上的不信服并不代表帕斯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相反,《微光》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帕斯对印度文化难以掩饰的亲切感,体现出他对印度文化一种积极探索,充分理解和欣赏的世界主义的态度。 虽然帕斯对印度的了解始于从欧美友人、东方学家著作中所感知的异域情调,但是正如奥默罗德所指出的那样,帕斯竭力选择东方学家罕有涉足的地方旅行,努力探索无论地理空间上、还是精神世界中尚未被触及到的印度,他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开自己无意识中的东方主义倾向,像一个寻找真理的朝圣者一样理解印度(Gonzalez-Ormerod 533—534)。所以,虽然多有学者对帕斯的印度观察提出东方主义、精英主义的诟病,但从根本上说,对这些倾向有着清晰意识并主动避免的帕斯,在《微光》中表现出的是一种深藏着对祖国墨西哥的现实关怀,同时又超越民族局限,深入印度,观照世界的文化心态,“包含着由理智的思索与审美立场相结合而产生的态度,对其他民族、其他地域以及不同的文化体验,尤其是对来自不同民族的文化体验的开放态度”(约翰·厄里256),正如其著名诗句所说,“所有的名字不过是一个名字”(《帕斯选集》(上)65)、“每个房间都是世界的中心”(《帕斯选集》(上)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