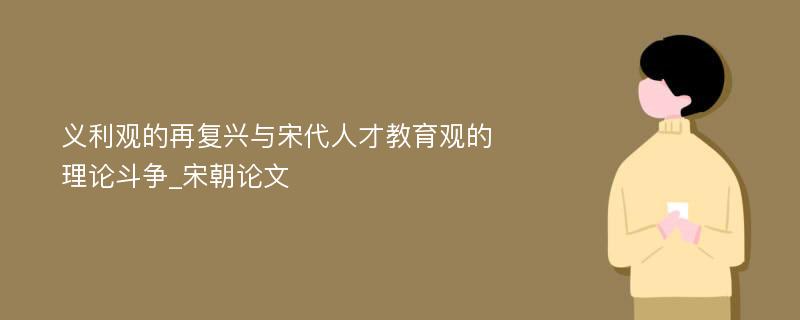
“义利之辩”再兴与宋代人才教育观的理论争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义利论文,宋代论文,理论论文,人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1)01-0104-06
如果说“义利之辩”的第一个高潮出现在“百家争鸣”的先秦时期,那么其第二个高潮无疑出现在学派林立的宋明时期。义利观的不同必然表现出人才观的差异,进而折射出各自人才教育理论旨趣的分歧。出自富国强兵的目的,范仲淹、李觏、王安石、陈亮、叶适均不同程度地提出了“事功型人才”理想和以实学为旨趣的人才教育主张;与之相反,二程、朱熹则基于封建社会统治长治久安的目的,坚持由内圣而外王的“道德型人才”范式,并设计了一整套以伦理为本位的人才教育理论。
一、“三冗”问题凸显、王朝统治危机与“义利之辩”再兴
“义利之辩”曾是先秦百家争鸣的重要论题。它之所以在宋代学术界再度掀起波澜,绝非空穴来风,而是现实社会剧烈变革的产物,是对宋代官吏冗滥问题的直接反映,是特定时期人才与教育重建的必要环节。
通过“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的宋太祖赵匡胤深知拥兵自重的危险性,他不仅亲自导演了“杯酒释兵权”,削弱了武将的军事权力,而且确立了“偃武修文”、“重文抑武”的文教政策,声称:“宰相须用读书人。”[1]为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宋代最高统治者热衷于科举选士制度,录取名额不断增加,企图通过大量吸收寒俊,扩大并增强王权的统治基础。据学者何忠礼对北宋科举取士人数的统计:“北宋自太祖至徽宗八朝的166年间,共开科69次,取进士、诸科34125人,每举平均取士达495人,每年约为206人,相当于唐代平常年份取士人数的三至四倍多。此外,尚有制举和特奏名没有统计在内。”[2]科举取士人数的扩大确实强固了宋代专制王权的统治基础,打击了豪门世族,使“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理想成为可能的现实,有利于社会阶层的良性流动和社会秩序的和谐建构。但需要指出的是,盲目地增加录取名额和过于随意的“特奏名”显然不利于封建社会官员队伍的理性成长;而普遍流行的“一人入仕,则子孙亲族俱可得官”的恩荫制度[3],不仅极大地扩充了宋代官员的数量,而且必然严重地败坏人们心目中的清官循吏形象。许多品行欠佳、能力低下者得以混迹其中,致使吏治质量严重下降,官吏素质问题很快突显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时,“重文轻武”的文教政策也严重地削弱了军队战斗力,武将没有独立的指挥权,面对强悍的外敌威胁,只能以盲目扩充军力来虚张声势,致使“冗兵”也成为社会一大毒瘤,而“冗官”、“冗兵”所带来的巨大消费——“冗费”,也就与日俱增。
面对愈演愈烈的“三冗”并进,宋代逐渐走上了“积贫积弱”的不归路。宋代也是封建经济由唐代“农奴制向宋代封建租佃制转化”的一个重要变革期。[4]其经济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国家土地所有制的衰落和土地兼并行为的愈演愈烈。“大地主阶层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大致在千分之三四至千分之六七之间,而所占土地却在百分之四五十。”[5]他们对土地的贪婪和掠夺严重地压迫了广大农民的日常生活空间,大量农民被迫流离失所,甚至揭竿起义,阶级矛盾异常尖锐。与阶级矛盾相契合,宋王朝所面对的民族矛盾亦十分复杂。辽与西夏的不断侵扰,是宋代最高统治者挥之不去的心病。为了求得边疆的安宁,宋代统治集团逐渐形成了“守内虚外”的军事策略,不惜以大量白银和绢丝换取边疆的暂时和平。
针对如此严重的内忧外患和积贫积弱,李觏、范仲淹、王安石等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提出涉及经济、政治、科举、教育的改革变法主张,并由此引发了义利之辩,乃至王霸、理欲之争。在北宋,李觏、范仲淹、王安石不仅公开言利,而且不同程度地开展了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兴学教育改革,但这样的改革却很快遭到二程、司马光等道义论者的激烈反对。同理,在南宋,陈亮、叶适的功利主义教育观念主张,也遭到理学家朱熹等人的直接批判,从而引发了影响深远的“义利王霸之辩”。事实上,义利、王霸、理欲之争不只是一般的哲学论争,更是关系到人才培养和社会风气的教育论争,这些论争显然有助于人们去重新思考封建社会急剧变革时期的人才素质、类型及其教育问题。
二、事功型人才与宋代事功派的人才教育求索
事功型人才的提出乃特定时代之使然。面对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无论是北宋的范仲淹、李觏、王安石,还是南宋的陈亮、叶适,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富国强兵之策,致力于以实学为旨趣的人才教育探索。
作为封建社会的开明士大夫,范仲淹对当时北宋所处的国势民力有着深切的忧思与体悟。尤其对把持一方的地方官员——县令、郡长之基本素质,范仲淹更是予以大胆的抨击。他说:“某观今之县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识之士。”[6]在范仲淹看来,当时的县令、郡长实已普遍腐败,他们多半热衷于攫取自己的个人利益,很少施惠于民。官员素质之所以如此恶劣,固然有许多主客观原因,但宋代开国80余年来“重文抑武”、“只取不养”的文教政策失误,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有鉴于此,范仲淹在“庆历兴学”期间特别强调士子必须先“学”而后“仕”,规定:“旧举人听读一百日,新人三百日,方许取解。”[7]为了培养读书人敦厚务实的精神,范仲淹进一步要求把培养官员的基点放在地方官学上,强调只有通过有计划的兴学运动和教育改革,才能真正解决人才难得的问题。
事实上,范仲淹不只是教育改革家,同时也是教育理论家。在坚持儒家伦理本位的基础上,范仲淹十分重视功利实学的阐发。当他得知胡瑗“苏湖教学法”不仅设经义斋以“讲明六经”,而且设治事斋,“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8],便很快决定将这一“明体达用”之学引入太学,并聘请胡瑗为太学学官,以期对宋代的官方养士中心——太学进行必要的实学改造。事实证明,范仲淹所表彰的“苏湖教学法”,及借鉴其法对太学所进行的改革,对培养高层次的人才起到了重要作用。黄百家赞誉道:“先生之教法,穷经以博古,治世以通今,成就人才,最为的当。”[9]
出自富国强兵的政治理想,李觏一反“贵义贱利”的儒家正统观点,认为“利”、“欲”并非不可言,强调:“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10]在他看来,孟子“何必曰利”说乃偏激之论,认为治国之实离不开“财用”,而富国之要即在“强本节用”。但遗憾的是,赵宋王朝正是在如何“强本节用”的问题上缺乏必要的应对之术。李觏说:“食不足,心不常,虽有礼义,民不可得而教也。”[11]应该指出,这种立于经济基础之上的礼义之教是值得肯定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李觏思想的民本论和唯物论因素。正是从“务本”、“富国强兵”的目的出发,李觏对“尊王贱霸”的俗儒之见颇有微词,极力为霸者的功业辩护,他说:“儒生之论,但恨不及王道耳,而不知霸也强国也,岂易可及哉?”[12]至于恩荫制度而导致的官员冗滥,及其所享受的免役等特权,李觏亦深恶痛绝。此外,李觏对于当时论资排辈的官僚体制也大惑不解,他说:“不求功实,而以日月为限,三年而迁一官,则人而无死,孰不可公卿者乎?”[13]
针对如上的吏治腐败,李觏十分注重吏治的教育基础,提出了注重“效实”的人才教育主张。李觏说:“国不一官,官不一事,何从而得其实?盍责之主者乎!县焉何实,责之郡;郡焉何实,责之诸道。……如是人人莫敢不自尽。”[14]李觏十分赞赏尧舜时代的教化盛境,并对后世不重学校教育的现象提出强烈批评。有鉴于名实不副的北宋教育现状,李觏强烈要求变革更张,重建儒家教育的经世治国使命,主张通过实实在在的名师分业教学和学生德业考察,以获取其理想中的治国安民之实才。
与李觏一样,王安石也具有强烈的富国强兵的政治理想,他突出了以中小地主阶级利益为主体的国家功利主义导向,从而为其以实学为旨趣的人才教育张本,并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变法。利益分配失控是北宋的重要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为大官僚、大地主的“兼并”之家对社会财富的过多占有,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同时,由于冗官、冗兵、冗费带来统治机能弱化和社会分配不公,也激化了社会矛盾,亟待进行利益再调整。正是出自这样的目的,王安石一反“羞于言利”的儒家正统观念,大讲有利于变法改革的“民之所利”。他说:“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盖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15]在他看来,通过变法改革,盘活国库财用,真正做到“以义理天下之财”,这种有利于“民之所利”的经济改革之利,有何不可谈之理?在王霸问题上,王安石肯定“王”与“霸”有共同之处,他说:“仁义礼信,天下之达道,而王、霸之所同也。”[16]他的社会政治理想仍然是“王者之道”,不过,他的王道理想带有明显的功利特征——“虽不求利,而利之所归”。
需要指出的是,王安石并非保守派司马光所攻击的“头会箕敛搜刮民财”之言利小人,而是站在中小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对社会财富的生产、分配进行必要的改革,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改革理想。事实上,王安石“因民之所利”的经济改革理念与新王道政治理想,归根到底都离不开强有力的变法之士与致用之才。没有高层次的人才教育支撑,任何改革变法都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实施与贯彻。但遗憾的是,当时赵宋王权最缺的就是安邦治国的经世之才。王安石指出,虽然本朝已享“百年天下无事”之福,但内里的空虚则是有目共睹,而要改变这一状况以“合乎先王之意”,又严重缺乏有用之才。职是之故,王安石提出了人才教育、管理、选拔、任用等一整套“陶冶而成之”的战略构想,蕴涵着十分丰富的人才教育智慧,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与北宋的李觏、王安石相呼应,陈亮、叶适是南宋著名的功利主义教育家。他们不仅提出了与理学家截然异趣的义利、王霸说,而且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以实学为旨趣的“成人”观,从而突显了事功派人才教育理论的独特追求。
在义利、王霸的问题上,陈亮反对将二者进行人为的割裂,主张在正视功利效果的前提下使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他并不讳言功利,强调“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17]。陈亮特别声称,自己是义利、王霸的统一论者,暗指理学家朱熹反而有将二者割裂之嫌。他说:“诸儒自处者曰义曰王,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说;说得虽甚好,做得亦不恶:如此却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如亮之说,却是直上直下,只有一个头颅做得成耳。”[18]与陈亮同道,叶适也不排斥功利,同样是义利、王霸的统一论者。对于朱熹将董仲舒的“正其义(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写入《白鹿洞书院揭示》,叶适深表不以为然,他说:“仁人‘正义不谋利,明道不计功’,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尔。”[19]
针对当时理学教育存在着严重脱离实际的空疏之弊,陈亮明确指出:“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雠,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20]当朱熹从“性命”之学的理学教育视角,要求陈亮“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21]时,陈亮不得不表明其有别于“醇儒”的“成人”教育观。他说:“亮以为:学者学为成人,而儒者亦一门户中之大者耳。秘书不教以成人之道,而教以醇儒自律,岂揣其分量则止于此乎?不然,亮有遗恨也。”[22]在陈亮看来,他无意于反身内求,做一个空谈性命的“醇儒”,而相信客观外物本身就有“道”的存在,主张通过对天下万物的考察和对社会历史的探求而致用于现实世界。他反复声称自己只想学“做个人”,学做一个能够经世致用的堂堂正正的人。
和陈亮一样,叶适也深刻感受到脱离实际生活的教育之弊。他对当时南宋学用脱节的人才教育十分痛心,声称:“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笃行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益也;立志而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23]正是从培养经世实才的目的出发,叶适强烈要求将取士与养士有机地结合起来,让那些“卓然成德”的好学之士走上仕途。
三、道德型人才与宋代理学家的人才教育建构
与事功派关注功利价值和事功型人才不同,宋代理学家突出了道义价值与道德型人才。他们不遗余力地推崇儒家纲常伦理,并将其上升至本体论的“天理”高度,严守“义利之辩”,贯彻“穷理灭欲”的理学教育纲领,注重心性修养,致力于“内在超越”的人才教育追求。
作为王安石的同时代人,程颐、程颢不赞同王安石对北宋社会经济、政治进行的利益调整和改革,称其为“兴利之臣”。程颢说:“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尤非朝廷之福。”[24]在这里,程颢十分明确地将王安石以“理财”为核心的变法改革,笼统地扣上了“兴利”的帽子,并与“尚德”对立起来,以为兴“利”必灭“义”,必践踏其崇高的道义理想和人格追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二程对“介甫之学”深以为惧,以为“坏了后生学者”。[25]为了将后生学者引向正路,二程沿着周敦颐、张载所开创的以“天道”证“人道”的路径,进一步将儒家纲常之道上升至本体的高度。程颢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26]与高扬的“天理”相反,二程对人的物质欲望和利益追求进行了十分严厉的贬斥,并提出了“穷理灭欲”的道德规训。理欲的互斥必然伴随着义利的对峙。程颢说:“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27]程颐也说:“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人皆知趋利而避害,圣人则更不论利害,唯看义当为不当为,便是命在其中也。”[28]在这里,二程不仅将义与利人为地对立起来,而且将“义”与“命”联系起来,当作绝对道德律令。为了进一步强化“利”的危害性,二程甚至要求将人的功利欲念消灭在萌芽之中,声称“敬义夹持,直上达天德自此”[29]。
无论是“穷理灭欲”的规训,还是“敬义夹持”的教诲,二程竭力将“后生学者”引向其理想中的内圣境界。二程说:“人皆可以为圣人,而君子之学必至圣人而后已。不至圣人而自己者,皆自弃也。孝者所当孝,弟者所当弟,自是而推之,是亦圣人而已矣。”[30]综合论之,二程心目中的“圣人”形象并不神秘,亦即恪守纲常伦理、注重心性修养的内圣式、道德型人才,这种人才范式奠定了后代理学人才教育建构的基本方向。
作为二程特别是程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朱熹不只最终完成了纲常伦理的本体建构,自觉地将北宋理学家业已开展的义利、王霸、理欲之争进一步推向极致,同时,针对现实吏治腐败和科举教育流弊,提出了旨在造就“醇儒”的理想追求。
如果说二程从可感触的现实生活中确实体验到一种道不远我的“天理”存在,那么朱熹则直接把这个“天理”上升至宇宙本体的理论高度。他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31]正是出自对“天理”世界的本源性和永恒性的信仰,朱熹始终严守正统儒学的义利、王霸之辩,并进而上升至理欲之争。朱熹十分赞赏董仲舒“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训示,把它作为“处世之要”写入其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他认为,“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32],强调为学之士当不得不予以高度关注,要求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可先有个利心,才说着利,必害于义。圣人做处,只向义边做”[33]。
与这一唯义而行、重义轻利的道义论相契合,朱熹在王霸之辩中坚持王道政治,反对霸道政治。在朱、陈的“义利王霸之辩”中,陈亮首先对近世诸儒所区分的“三代以道治天下”、“专以天理行”,“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专以人欲行”表示极大的反对,并为汉唐叫冤。然而,王霸之辩事关道统与政统的微妙关系,朱熹力持以儒家道统说为依据,以义利、理欲之辩为准绳,对专制帝王统治提出严厉批评。他说:“当谓‘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于古今王霸之迹,但反之于吾心义利邪正之间,察之愈密则见之愈明,持之愈严则其发之愈勇。”[34]在这里,朱熹显然坚守了孟子以来以德力、义利区分王霸的思想,进而从理欲高度进行阐述,所论虽然是汉唐霸政,其中却隐藏着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与其反复申论的“格君心之非”的思想是一致的。
事实上,义利之辩与理欲、公私之争也是天然地胶着在一起的。朱熹明确指出:“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循人欲,则求利未得害而随之。”[35]诚然,朱熹并没有全盘否定人的基本欲求,但超越名分的一己私欲则被严厉地禁止。他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36]在朱熹看来,理与欲决然对立,强调“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37]。
朱熹何以竭尽心力于义利、王霸之争?归根到底乃出自于对当时南宋统治危机的深刻忧虑。作为理学家,朱熹深知“民为邦本”的道理,极力反对不顾民间苦乐的“聚敛掊克之臣”。在他看来,士大夫素质之所以普遍欠佳,与科举教育的流弊及其中所蕴藏的功利主义导向有关。诚然,朱熹并没有绝对地反对科举制度,但他特别强调要先学好“义理”之学,再参加科举考试。他说:“科举之习,前贤所不免,但循理安命,不追时好,则心地恬愉自无怵迫之累。”[38]然而,功名的巨大诱惑不唯使举子“心有怵迫”,更可能导致整个国家统治的弱化和混乱。朱熹说:“大抵今学者之病是先学作文干禄,使心不宁静,不暇深究义理,故于古今之学、义利之间不复能察其界限分别之际,而无以知轻重取舍之所宜。”[39]
与科举流弊相呼应,当时南宋的学校教育现状也不容乐观。朱熹指出,熙宁以来,由于功利主义习气的极度弥漫,“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开之以德行道艺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祗以促其耆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40]。有鉴于科举制度的严重弊端,特别是其中所浸染的功利主义导向,朱熹深感重建“义理”之教的重要性,强调只有重建义理纲常之教,才能根本改善官吏队伍的素质水平,挽救封建统治危机。
不难看出,朱熹由义利、王霸、理欲之争切入,经由对现实统治危机及科举教育弊端的反省,必然导向其义理纲常之教的重建和对“醇儒”境界的不懈追求。其心目中的“醇儒”,就是以义理纲常为核心的道德“内圣”。朱熹说:“大凡为学,且须分个内外,这便是生死路头!……向内便是入圣贤之域,向外便是趋愚不肖之途。”[41]毫无疑问,这种“向内”功夫之能是“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类的心性修养,其“内圣”理想与陈亮注目“外王”事功适成强烈对照;这也是朱熹何以要陈亮放弃功利追求,“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伴随着“义利之辩”的再兴,以范仲淹、李觏、王安石、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派与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派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价值论争,并就高层次人才的标准、模式及其教育路径展开了各具特色的学术探索,其理论锋芒直指现实的社会发展与变革。应该肯定,他们苦心经营的教育学术观点均有其合理之处,二者博弈的最终结果是理学家占了上风,理学及其教育哲学被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正因为如此,中国社会发展进一步强化了其内圣型伦理本位价值导向,从而对此后数百年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收稿日期:2010-11-23
标签:宋朝论文; 朱熹论文; 范仲淹论文; 王安石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义利观论文; 读书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理学论文; 李觏论文; 宋明理学论文; 科举制度论文; 儒家思想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