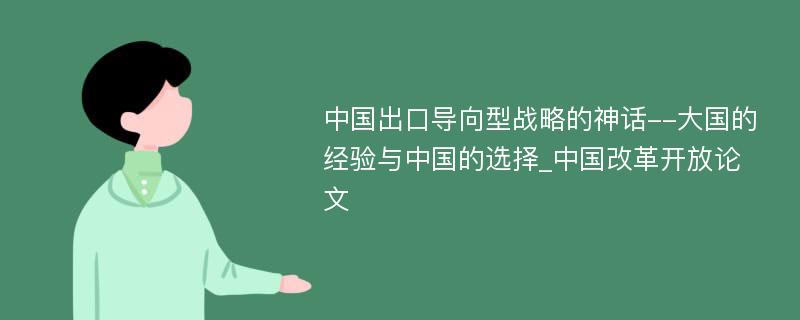
中国出口导向战略的迷思——大国的经验与中国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迷思论文,中国论文,大国论文,中国出口论文,导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表2显示的指标看,中国的开放度十分高,远远超过美国、 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对中国经济来说,出口只起到一个间接的作用,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的增长更多依靠内部规律。
如果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实际规模,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总体贡献应该远不如本表反映的数据那样大。
2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起步于农村改革,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和农产品市场的逐步放开,培养出广阔的市场。
没有原来的基础,80 年代中国的投资和消费双膨胀模式无论如何是无法持久的。
在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严重危机的30年代, 美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国土整治工程。
90年代成为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 至今仍然饱受金融危机的煎熬,10年前挑战美国经济的豪情已经荡然无存。
大国发展必须处理好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关系, 出口导向和单纯的投资主导可以取得一定时期的高速增长,却最终要面对内需扩张的转换。
在外汇短缺解除之后,中国对出口既得利益者的倾斜有所改变,但并没有根除。
出口导向的思想继续主导学术和政府的思维, 将利益分配格局继续偏向东部沿海地区,很可能违背大国经济发展的规律,令中国贻误崛起的时机。
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一蹶不振,1997年7 月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随后骨牌式地蔓延到韩国、台湾和香港等地。人们在讨论东南亚金融危机深层原因的同时,将注意力集中到这些地区共同的出口导向战略上,也怀疑中国会不会遇到同样问题。本文认为,过去20年中国经济成长,出口并不是主要的推动力,经济增长更多来自投资和消费等内需。所谓“中国出口导向型增长奇迹”,只不过是一种神话。对比国际经验,作为一个大国,中国要在全球崛起,从长期看还需走以内需为主的道路。当前,在亚洲金融风暴和国内经济低迷的背景下,部分深受出口导向思维影响的经济学界和政府人士把眼光放在外部市场,把经济复苏的希望寄托在出口和外资上,在外部环境和外部市场被破坏时出现悲观情绪,要求人民币贬值,要求向出口部门倾斜更多的利益,而忽视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基础,忽视了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规律,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
一.中国出口增长奇迹:名与实的差异
出口增长奇迹的表现
1978年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微不足道。当时,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出口排在世界第32位。经过80年代的改革,1985年以后中国出口有显著的增长。1978—1996年,中国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5%左右。中国出口额在世界的排名,从1978年的第32位,跃居到1995年的第11位。出口的大幅度增长,反映出中国出口竞争能力的加强。可以说,在这10多年里,中国出口创造了一个增长奇迹。对这个奇迹的描述,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的话最有说服力,(注:1995年11月,巴尔舍夫斯基在美国众议院听政会上的讲话。)“随着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超过日本对美顺差,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状态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令美国无法承担下去了”。中国出口的崛起,及其对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影响日益扩大,是不争的事实。
80年代以来,在中国出口高速增长的同时,邻近的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经济也赢得了出口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热点。将中国的出口表现与它们进行比较,更能显示中国出口增长的奇迹。如表1所示, 1980—1985年,中国的出口还处在起步阶段,与实现出口起飞的韩国和台湾相比,稍显逊色,增长率和总量都比后二者低。当时的东南亚国家,因1982年拉丁美洲债务危机的阴影,基本没有走上出口增长道路,总体出口表现退步。1985—1990年,是亚洲地区出口的黄金时机,泰国表现最为杰出,中国居第二位,增长速度稍高于韩国和台湾,高于东盟四国的平均数许多。1990—1995年,韩国和台湾的出口增长速度下降,中国出口表现与泰国、马来西亚同时位居前列,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居中。合起来,将1994年与1980年对比,中国的出口增长了585%, 与泰国相当,居于全球最高之列。由于中国出口基数较大,到1994年出口的总数,相当于东盟4国的78%;而1980年,中国出口仅相当于东盟四国的37 %。因此,10多年来,中国出口增长速度步入世界最快的行列,不仅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增长较快的东南亚地区,这是人们公认的,也是中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的主要论据之一。而且,中国出口数量增长,伴随着结构改善,走了一条从资源性产品为主(1985年以前)、到纺织品、服装和鞋类为主(1985—1993年),再到机电产品(1993年以后)为主的升级道路,出口的增长和结构改善,基本与中国的比较优势吻合。
表1 1980—1994年东亚、东南亚地区的出口增长情况(单位:亿美元)
国家或地区 1980 1985 1985/1980 1990
韩国 175 303
173% 650
台湾 198 307
155% 672
泰国 65
71
109% 231
印度尼西亚
239 18678% 257
马来西亚 130 154
118% 294
菲律宾57
4681% 82
东盟四国 491 45793% 864
中国 181 273
151% 629
国家或地区1985/1980 1994 1994/85 1994/90
韩国214% 960
317% 148%
台湾219% 930
303% 138%
泰国325% 447
629% 193%
印度尼西亚 138% 395
212% 154%
马来西亚191% 569
369% 193%
菲律宾 178% 135
293% 164%
东盟四国189% 1546
338% 179%
中国230% 1210
443% 192%
注:东盟四国指的是上述的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四国。新加坡和香港属于城市经济,其出口又有相当高的转口因素,不在这里比较。
出处:ASLAN DEVELOPMENT BANK,
KEY INDUSTRIES OF DEVELOPNG ASIAN AND PACIFLCECONOMIES,1995
出口导向战略的另一个重要论据是中国的出口依存度不断升高。从表2显示的指标看,中国的开放度十分高,1980年出口依存度只有6.0%,1990年达到17.0%,1994年竟高达23.8%,远远超过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表2 中国出口依存度的衡量
年份国民生产总值(亿元)出口额(亿美元)
1980 4470 181
1985 8562 274
1990 17686 621
1993 34172 918
1994 437991210
1995 576831488
1996 638001510
年份 出口依存度外贸额(亿美元) 外贸依存度
19806.0%381 12.6%
19859.5%696 24.1%
1990
17.0%
1154 31.6%
1993
16.8%
1957 35.8%
1994
23.8%
2367 46.6%
1995
21.6%
2809 40.7%
1996
19.6%
2899 37.8%
出处:《中国统计摘要》1997年
名义与实质的差距
但是,如此高的开放度与人们的直觉显然不相符合,中国经济中不可能有超过1/5的部分是为外部服务的。
第一,是国内生产总值的统计问题。从国内生产总值统计的基本框架看,中国的统计方法和指标与国际基本相符。但是第三产业的统计范围明显小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在传统计划经济统计中,往往忽略第三产业的统计,目前中国的统计方式虽然正向市场经济方法过渡,但在时效上存在明显滞后性。同时非贸易产品主要是农村居民的非货币收入项目统计不全面或者未能统计在内,虽然按照一般国家的统计口径,这部分收入也不计入国内生产总值,考虑到中国农村人口占80%的国情,如果不统计,将会缩小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规模。因此,考虑上述因素,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被低估了20%左右,相应中国的出口依存度则被高估了四个百分点。
第二,是汇率和购买力平价问题。目前中国出口依存度主要由市场汇率来衡量。虽然中国的市场汇率生成机制比较合理,但现在的市场汇率并不能反映人民币的真实购买力,依据购买力平价的计算方法,人民币汇率仍有严重低估的可能性。考虑到市场汇率的局限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1993年开始,用购买力平价估算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如果用购买力平价估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美元价值,无疑会远远大于用市场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各种不同、同时很有争议的估算方法这里不再赘述);按照国外的测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购买力比按官方汇率折算的数目要大一至二倍。
实际上,单从汇率的稳定性来看,也能说明这一名义的出口依存度需要具体分析。过去,人民币的汇率不稳定,需要不断贬值,造成出口依存度在名义上不断急速上升。1994年人民币的大幅度贬值,在很大程度上夸大了出口依存度,使其从1993年的16.8%上到23.8%, 升幅达7个百分点。显然,这与经济的实际开放度没有太必然的联系。 果然, 1994年贬值和汇率改革后,人民币汇率趋于平稳并逐渐升值,出口依存度迅速下降,1995年下降到21.6%,1996年又下降两个百分点, 为19.6%。
剔除这两方面的因素,据笔者的估计,中国的出口依存度1996年大致应该在10%左右。在这两者之外,还有第三个值得注意的因素,就是中国出口中加工贸易的比重很高。1996年, 中国的加工贸易出口为843.3亿美元,增长14.4%,远高于总体出口1.5%的增长率, 占总出口的比重达到55.8%,1997年这一比重仍然高于50%。加工贸易带给中国的只是附加价值,过高的加工贸易比重会夸大中国的出口依存度。加工贸易是以来件装配和来料加工为主导的贸易方式,在加工过程中,中国收取的外汇(工缴费)有限。1996年,中国加工贸易的附加价值增值率仅为26.2%。因此,中国外贸的实际规模远远不如海关统计的数据之大。相应地,实事求是地讲,考虑到加工贸易比重过大,中国出口增长奇迹可能没有上述分析那么明显。
对于出口乃至外资对中国经济的贡献,香港有学者进行过比较复杂的计算,(注:胡敦蔼:“对外开放:神话与事实”,《香港社会科学学报》, 1995年7月专号。另外,陈文鸿长期以来也有这方面的研究。)得出的结论认为,国内官方和主流学者所提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国内经济正在迅速走向外向化,以及在改革开放期间国民经济是由出口带动的,更不能肯定外资和外商投资显著改善国内经济效益和促进经济发展。而且,中国为了吸引外资和拓展出口,对经济特区、开放区、技术开发区和涉外企业、单位和经济活动提供各项税收、物资、人才供应和管理、制定价格、外贸和其他经营方面的优惠,而这些优惠政策的负面效应却由国内的非开放地区承担,在外部效应方面有非常大的负作用。
对中国经济来说,出口只起到一个间接的作用,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的增长更多依靠内部规律。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于内需
数据分析
一般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始于1978年,表3 很清楚地显示出,1980—85年间中国的出口基本没有太大增长(1978—1980年出口的大幅度增长主要来自第二次石油危机的提价因素,直到1985年中国出口还是以资源性产品为主)。很显然,直到1985年,出口对中国经济并没有太大贡献。可以说,出口的真正增长是1985年以后的事,而大规模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则是1986年以后的事。而中国经济的增长始于1978年,从这个角度看,1986年以前的经济增长基本完全由内需推动。
表3 中国外贸的增长变化(亿美元)
年份出口值 年增长度(%) 进口值 年增长率(%)
1978 97.50
28.40 108.93 51.0
1979136.60
40.20 156.75 43.9
1980181.19
33.80 195.50 24.7
1981220.07
14.30 200.17 2.56
1982223.211.36 220.1510.01
1983222.26
-0.43 192.85
-12.27
1984261.39
17.61 274.1028.14
1985273.504.63 422.5254.15
1986309.42
13.14 429.04 1.54
1987394.37
27.45 432.15 1.01
1988475.16
20.49 552.6827.89
1989525.38
10.57 591.41 7.01
1990620.91
18.18 533.45-9.80
1991719.10
15.81 637.9119.58
1992849.40
18.12 805.8526.33
1993917.638.031039.5028.99
1994
1210.38
31.901156.9311.30
1995
1487.70
22.911320.7814.16
1996
1510.661.541388.38 5.10
1997
1827.00
20.941423.60 2.54
出处:《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7,《中国统计摘要》1998
根据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表4计算了中国的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在这项分成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简单计算中,利用每项的增量除以当年GDP的增量, 可以得出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初步结果。
通过这个计算,可以看出80年代后期以来,净出口的贡献逐渐转变为正面效应,净出口从过去受投资和消费大幅度波动而被动调整的局面慢慢改观,趋向于主动影响整体增长。在经济不景气的1990年, 对GDP增长的贡献竟高达37.53%,在宏观调控刚刚推行的1994年, 也达到11.0%,而在宏观经济趋于下滑的1997年,贡献上升到19.16%。 在这两个周期,出口都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增长起过重要作用。在此之外,基本都是内需起主导作用。而且,由于人民币购买力被低估,以及国内生产总值统计方式的不完善,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从简单的数据,利用简单方法计算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应该是不完善的。如果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实际规模,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总体贡献应该远不如上表反映的数据那样大。
表4 净出口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
年份 消费的贡献投资的贡献 净出口的贡献
197981.19 20.56 -1.75
198074.73 24.26
1.01
198195.12 -2.57
7.45
198255.94 30.49 13.60
198365.17 41.70 -6.87
198461.94 42.61 -4.55
198566.26 56.36 -22.62
198657.36 34.30
8.34
198755.04 28.82 15.54
198865.39 40.18 -5.57
198967.90 34.05 -1.95
199043.63 18.83 37.53
199160.14 36.24
3.62
199261.23 46.23 -7.46
199348.98 62.08 -11.08
199458.90 30.10 11.00
199554.26 37.33
8.41
199654.30 46.94 -1.24
199755.56 25.23 19.16
出处:根据《中国统计摘要》1998年计算
表4显示出, 中国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还是来自消费和投资等内部因素,实际上,结合经济体制改革和工业化的进程,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过去20年经济增长的动力。
经济增长的内部源泉:改革、供给和市场的良性循环
2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起步于农村改革,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和农产品市场的逐步放开,培养出广阔的市场,“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老三大件在全国范围内的普及,为80年代前期原有军事工业转向民用工业提供了良性的需求。80年代前期,中国的国有企业利润率是改革开放以后最高的。同时,这种良性需求也带动了乡镇企业的飞速发展。1984年以后,改革进入城市,随着城市居民收入的增加,在80年代中期形成了对“电视机、冰箱、洗衣机”新三大件的排浪式需求。由于中国原有的工业基础无法支持新三大件的生产,由中央部委到地方政府大规模投资,出现了急速的家用电器进口替代工业化浪潮,各地大上加工项目。整个80年代,中国经济出现“投资和消费双膨胀”的特点,整体经济实力在1984—1988年间越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个阶段,由于中国经济处在转轨过程中,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更多地来自生产方面,即供给短缺。因此,提高生产效率和地方工业化积极性的改革大大刺激了供给的扩张,满足了短缺的市场,改革、供给和市场之间呈现良性循环,改革和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这可以称为改革和增长的蜜月期。当然,这里还需要强调前30年积累下来的工业基础、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没有原来的基础,80年代中国的投资和消费双膨胀模式无论如何是无法持久的。
应该说,80年代中期的进口替代工业投资,存在严重的重复建设情况(最典型的例子是全国共引进了115条彩电生产线), 即使经过1989—1992年的治理整顿,到90年代初期中国已经出现了市场疲软和部分加工工业生产能力过剩、特别是以家用电器为代表的消费品生产能力过剩局面。另一方面,80年代的投资只注重加工工业,而在基础设施方面,前30年的积累基本耗尽,国民经济出现交通运输、邮电、电力供应、能源和原材料等方面的瓶颈。因此,90年代经济增长的重点便转移到基础设施和重化工业。
1992年开始,随着中央将基础设施建设的收益权下发给地方,加上房地产热的兴起,中国出现了新一轮投资高潮。按当年价格计算,1993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比1992年增加了56%,当年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占62%,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高速公路、发电站、铁路干线、电话光纤、大型的原材料和上游工业企业加速建设。在制造业方面,中国进入了以家用轿车投资为代表的重工业替代阶段,其标志是1994年国务院通过的“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提出要建立包括汽车、电子、石油化工、机械等支柱产业,实现国民经济的重工业化;在基础产业方面,出现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浪潮,开发区和房地产项目在全国随处可见。这股投资热潮一直持续到1995年,1994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为30%,1995年为20%。根据有关研究,投资经费大约会有60%转化成为消费资金,在投资热的作用下,消费升温,带动了中国经济1992—1995年、乃至整个“八五”期间的高速增长,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房地产和股市的泡沫。
然而,八五期间的高速发展,伴随的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过渡。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的运行机制、政府行为、企业行为和消费者行为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最重要的特征是出现了从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的转变(比较温和的说法是“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化”)。这样,对经济增长的制约由原来的供给因素转变为市场因素。从1996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了全面的生产能力过剩局面,经济处于周期下降的过程中。这个时候,正好碰上中国银行取消对外贸贷款的“三不政策”、财政部降低出口商品的增值税退税率、海关取消外资企业进口自用机器设备的关税减免、对加工贸易实行贸易保证金台帐制度等措施全面推行,由来以久的出口优惠政策几乎一下子被取消。因此,外贸部门和沿海地区的要求利用出口推动经济增长的呼声十分强烈,而主流学术界从90年代初开始大力宣传亚洲四小龙的出口导向经验,此时这些观点已经深入人心,使人们将希望寄托在出口和外资身上。
纵然如此,从现阶段出口和内需的关系来看, 即使出口的作用在1997年有较大提高(如当年有近400亿美元的顺差), 出口对整体经济的贡献依然不到两成,内需还是十分重要。正因为中国经济是内部需求为主带动的,中国经济可以避开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便不是我们侥幸没有开放资本帐户,而是我们有庞大的内部需求、完整的产业结构、良好的内部经济循环。否则,单纯依靠出口和外资导向,外围因素一有风吹草动,中国经济肯定在劫难逃。所以,从这个角度考虑,即使开放了市场和资本帐目,中国经济也不见得会出大问题,尤其是实质经济不会出现根本问题。对有关出口和内需的认识,目前似乎到了一个转折的关头,由于这几年来国内经济出现的过剩状况,消费不景气、投资不振,加上大规模的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改革,改革不再像过去那样在短期内直接推动增长,80年代改革与增长伴生的蜜月期结束,使人们对内需增长丧失信心;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周边采取出口导向战略的地区纷纷贬值,人们更担心这种恶性贬值会威胁中国的出口增长。因此,中国经济到底依靠什么走向21世纪,需不需要将注意力完全放在出口上,内需还有无前途,便是当前迫切要回答的问题。
三.中国经验与中国的环境
从战略角度看,全世界有三个大国——美国、俄罗斯、日本。它们的发展道路和成败经验对中国有重要的启示。
美国和苏联的道路
美国能够在独立后100年就成为世界头等经济大国, 走的是以内需扩张为主的道路。美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路线,是通过引进大量移民,不断开发中西部地区,造就国内统一市场。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一方面长期实行高关税政策,保护本国的制造业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对全国范围内交通运输网络等持续投入,为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基础设施和内部投资,造就庞大而深远的经济腹地。
美国独立初期的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一位著名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在《论制造业的报告中》,他积极主张国会通过高关税来保护本国的制造业。南北战争结束后,以工业为基础的北方获胜,对制造业有利的高关税政策得以继续维持和提升,1889年国会通过的麦金利关税法,使平均关税上升到49%的水平。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美国内部虽然有不少争论,但总的趋势是关税水平不断上升(1861年至二战前夕的平均关税税率约为40%),使美国的工业能够独占本国不断扩展的国内市场,也造就了全世界最强大的制造业,为美国经济的崛起打下了坚实基础。
从19世纪初开始,美国进行大规模的交通网络建设。在19世纪前期,主要配合当时的水路运输,建立了伊利运河为主的水运网络,使东西部市场衔接起来;1840年以后,铁路运输成为美国投资和交通运输的重点,1869年便建成了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之后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铁路网络,铁路营运里程超过30万公里。铁路投资的总额,1876年近40亿美元,1920年竟然达到200亿美元。20年代、特别是二战后, 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美国又在全国范围内兴建高速公路网。在美国经济发展的整个历程中,出口占的比重非常小,19世纪的出口主要以农产品为主;一战前开始出口汽车等制造业产品;美国出口大量增加,则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严重破坏了欧洲的生产能力以后的事。总的说来,出口一直没有在美国经济成长中占据导向性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严重危机的30年代,美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国土整治工程,例如人们熟悉的田纳西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胡佛水坝、大古力水坝等,对相对落后的地区进行了有效的开发和整治。
从上个世纪末期到苏联诞生前夕,俄罗斯虽然是全世界幅员最大、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但综合实力在国际上并不领先,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德国法西斯、与美国进行长达40年的冷战,得益于30年代的重工业化。这次重工业化进程,虽然饱受人们诟病,也被主流经济学描述为资源浪费、被政治学者刻划为残酷无情,但从国家战略利益的角度看,是奠定苏联现代化的基石。从技术上,它采用当时西方最现代化的设备;从企业组织行为上,是20年代最流行的托拉斯生产方式;从动力看,依靠的是大规模的内需推动经济超高速增长。正是这10多年的发展,使其工业基础彻底摆脱旧沙俄的烂摊子,成功地避开了全球蔓延的30年代大萧条。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苏联大力加强了对乌拉尔山脉以东地区的开发(包括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等),使苏联经济获得了广阔的腹地,奠定了世界强国的基础。当然,70年代以后的决策失误,导致苏联经济开始衰落并最终解体。苏联失败的根源,是将大量的资源倾注到以军事工业为主力的投资之中,形成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能力未能为消费服务,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得不到合理解决,经济增长无法从消费方面得到持久支持,使整体经济在与美国的争霸中失去后劲,最终在80年代末期被拖垮。但以俄罗斯的潜力看,它在中期内再度崛起也不是天方夜谭。
日本从成功走向失败
50年代,围绕经济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问题,日本经济学界和政界曾经爆发过激烈的争论。由于日本是一个人口过剩、资源不足的小国,日本政府终于采取了“贸易立国”的策略。1960年,日本的对外贸易总额只有85.5亿美元,1970年猛增到38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16.2%,贸易成为经济增长的支柱之一。在贸易立国的战略下,日本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是企业为提高出口效率进行大规模的设备投资。50年代中期起,在出口景气带动下,日本各大企业放弃和更新所有陈旧设备,新建的重化工业项目一年比一年旺盛。钢铁、造船、石油化工、家用电器等新产业相继诞生和发展。其中钢铁业第二次合理化(具有大型高炉、氧气吹顶转炉炼钢法的生铁和钢材生产一条龙的新型钢铁厂大量投产),带动了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投资呼唤投资,革新诱导革新等良性循环的出现,其效应爆炸性地扩散到国民经济中去,日本接连出现了1955—1957年(31个月)的“神武景气”,1958年至1961年(42个月)的“岩户景气”,1962—1964年(24个月)的“奥林匹克景气”,以及1966年至1970年7月(57个月)超大型的“伊装诺景气”。1960年和1961 年的设备投资增长率分别高达38%和41%。就设备投资年均增长率看,1961—1970年西方国家分别为:美国3.9%,英国4.7%,西德5.7%, 法国9.1%,意大利5.2%,加拿大5.4%,日本却高达15.2%, 相当于其他国家的二至三倍。60年代晚期,日本企业实现了国际最高水平的设备巨型化和自动化。如年产量800—1000万吨的钢铁厂,50 万千瓦大容量火力发电机组,年产量30万吨的乙烯成套设备,专业生产轿车的汽车制造厂等。为了支持设备投资浪潮,日本在国内铺设公路,整顿完善港湾设施,系统推出了《新全国综合开发计划》,进行了大规模的国土整治工程。
经过石油危机之后,1980年日本通产省正式提出“技术立国”的战略口号,宣告日本已经完成战后的“追赶现代化时代”,正迅速迈进“世界一流国家的时代”,“技术立国是日本奋斗的目标,有效利用头脑资源进行创作性的技术开发,提高竞争能力和经济实力,才是日本的必由之路。”1985年,美国联合西方国家压迫日元升值,日本的出口和工业生产下降,形成了日本经济中所谓的“日元升值危机”。针对这一形势,1986年,日本发表了著名的《前川报告》。报告指出,在日元大幅度升值的背景下,日本对自己的传统经济政策和生活方式实现历史性转变的时刻已经到来。日本的当务之急是实现经济结构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扩张型”的转移,在产业结构上实现由“夕阳产业”向“朝阳产业”的转移。
然而,技术立国和内需扩张型的发展道路并没有成功。整个80年代日本走的依然是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老路,尤其是在1987—1991年再次进行了庞大的出口型设备投资。尽管日元升值使日本人暴富,但国土狭小、资源短缺的日本居民生活水平与西方国家不可同日而语。日本的实质内需没有增长起来,却刺激起了资产过度膨胀的泡沫经济,房地产和股票价格飙升。1990年开始日本的泡沫经济破灭,使90年代成为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经济增长率在发达国家中从第一位跌到最后一位,至今仍然饱受金融危机的煎熬,被日本国内称为“第二次战败”,10年前挑战美国经济的豪情已经荡然无存。
日本经济失败的原因很多,(注:有关日本经济的问题,作者即将出版的著作《日本经济神话的破灭》有详细论述。)例如产业政策失误,忽视个人电脑的发展,导致制造业失去主流消费品生产,日本经济的技术追赶政策走到尽头,金融市场开放缓慢以至活力不足,企业税收负担沉重等等。然而,更深入研究日本出口导向战略的失败,有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内部机制。第一,国际市场无法容纳更多的出口,日本无法保持过去的增长速度,意味着围绕出口进行的设备投资面临生产能力过剩的结局,进一步导致为投资融资的金融体系出现问题,而原来以高增长为基础的终身雇佣制等企业管理模式当然成为经济发展的包袱;第二,从里根时期的美国和撒切尔夫人时期的英国开始,西方国家改变了凯恩斯主义作法,恢复到供给学派的刺激供给,减少规章制度和税收,使生产效率提升,国际上供给竞争更加激烈。这样,经过10多年时间后,双方的竞争优势出现逆转,日本的税收在西方国家中居于较高水平(企业所得税高达46%),规章制度繁琐,原来引为自豪的官僚体系(通产省、大藏省等)成为企业创新的桎梏,东京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落后于纽约和伦敦。而这个过程的关键是,日本的国内消费和市场一直无法开发出来,内部消费无法带动经济增长,过去出口以及为出口而形成的设备投资机制也无法顺利运行,整个经济出现停滞趋势。
中国的环境
三个国家的发展大致有以下过程: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必须有一个积累过程,形成工业化浪潮,为经济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美国的积累依靠的是移民、对本国市场的保护、从欧洲借入的资金等因素;苏联的积累依靠的是30年代斯大林的工业化,通过对农业的剥夺和东部资源的开发形成;日本的积累是依靠有利的国际环境,实行出口导向。初期的积累完成后,在此基础上形成投资与积累的良性循环,可以带动经济长期(如30年)增长:美国是大规模的国土整治和交通运输网络的建立,苏联是用于开发资源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冷战用的军工投资,日本是为出口进行的设备投资。最后,到投资形成规模、整体经济有一定实力时(美国在20年代、苏联在70年代、日本在80年代),必须注重消费,给经济增长提供强有力的新动力。在最后阶段的政策选择不同,是三个国家今天表现不同的重要原因。美国经济中消费的比重一直很高,许多投资也是以居民消费为最终目的,经历过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美国经济中消费的比重更大(当然,消费过度有害处),这与凯恩斯经济哲学是一致的;日本侧重出口和投资,对消费重视不够,始终无法形成内部消费和投资的良性循环,一旦外部环境大变,就会出问题;苏联则根本不重视消费,单靠投资和开采资源是无法持续下去的。
实际上,过去几十年中国一直在吸收各种模式的长处。中国50年代的工业化,基本将苏联集中一切资源推动工业化的经验和长处全数吸收。可以说,没有苏联模式,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工业化,也没有今天中国经济起飞的基础。近20年来的对外开放和刺激出口,有日本经验的浓厚痕迹。80年代中期以来的消费和投资双膨胀,可以看到美国高速发展时期的影子。
但是,从上述历史经验看,大国发展必须处理好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关系,出口导向和单纯的投资主导可以取得一定时期的高速增长,却最终要面对内需扩张的转换,转换不过去很容易出现危机。昔日的苏联解体、今天的东亚金融危机就是典型,导致这些地区几十年的奋斗前功尽弃。就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已经完成了初步的积累,还可以走一段时间的内部投资,但这些投资在更大程度上应该是为配合内部的消费服务的,为下一阶段消费的持续增长打下基础。
应当看到,在冷战结束后的国际经济政治背景下,放弃内需市场不开发,全力推行出口导向可能是一个灾难。第一,国际市场难以维持出口的高速增长。金融危机后亚洲市场收缩将是一个长期趋势,中国开辟亚洲出口的压力会很大。从长期看,北美洲自由贸易区和欧洲联盟的出现和深化,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区域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的出口可能是祸不是福。从全球范围看,今后一段时期生产过剩的局面将会持续下去,对出口导向是明显不利的。
第二,从短期看,根据美国的统计,1997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高达497亿美元,美国的容忍程度是有限的。从战略角度考虑, 美国迟早会像80年代对日本那样对中国施加强大的压力。长达20年的日美经济冷战以日本失败告终,日本失败的根源在于美国控制了市场和游戏规则的制订权。这个顺差继续累积下去,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美国和中国爆发经济冷战的可能不是降低,而是越来越大。一旦美国关闭市场,中国沿海庞大的加工能力将何处去?
第三,过分突出出口导向势必强化中国经济的内部矛盾。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重心主要在东部沿海地区,这些年培育出来的市场,只造就沿海和部分内地大城市、交通干线的3—4亿人口,而没有造福于全国12亿人口。就以广东等省和特区局部成功的出口导向战略来说,现在已经完成了第一轮的资金积累,而资金来源既有来自国际市场来的,也有来自内陆省份的剩余价值,而香港更实现了内地、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的剩余价值。在这种格局下,中国的二元结构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在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恶化的趋势,东部和西部、沿海和内地、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而以目前内部不协调的经济结构,单靠这3—4亿人口的市场,已经无法吸收越来越庞大的生产能力了,东部沿海产业发展也失去了后劲。所谓的重复建设、产业同构、市场饱和,仅是问题的表象而已。继续用过去的思路推动沿海的出口导向,将利益更多地倾向于沿海,只会加重整体经济的二元结构。从长远看,不利于国家的战略利益和长治久安。
实际上,过去中国的出口政策有一个强烈的进口驱动因素。在改革开放以后相当长时间内(一直到1993年底的汇率并轨),中国的出口实质是为进口服务的。由于国内需求强劲,进口需求极为旺盛,中国的外汇储备一直处在短缺的状态,1980—1981年、1985—1986年都曾因为外汇短缺而大规模取消已经签订的设备引进计划,进而影响到全国的投资计划。在外汇短缺的情况下,出口的首要目标是外汇,为了得到外汇,需要不惜一切代价扶持出口。在这种环境下,中国传统的出口部门和出口地区获得了相当大的政策优惠,这种政策倾斜一直持续到1996年中国外汇储备超过1000亿美元为止。在外汇短缺解除之后,中国对出口既得利益者的倾斜有所改变,但并没有根除。今天如果重提出口导向,很可能在政策上再重演过度向出口部门和地区倾斜利益的局面,加重宏观经济调整的负担。
四.中国的战略选择
国土整治工程
应该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基础已经具备,初步的积累业已完成。农业方面可以做到自给自足,工业方面基本的消费品和投资品完全有富余,资金方面从90年代中期出现存差,中国经济正处在从局部起飞到结构转换、均衡发展的转折过程中。在这个转折的关键时刻,美国经验最值得学习。要成为一个强国,必须有深远的经济腹地、广阔的内部市场,开拓中西部的资源和市场成为当务之急。中国要持续发展,内需主导将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性规划。
没有强有力的基础设施投资,没有出口等外部积累,单靠农业和矿产品资源的开发是无法启动经济的。由于现在的市场利益分配格局已经剥夺了中西部地区自我积累的权力,中西部地区开发的核心应是中央政府主导的大规模的国土整治工程,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个建设计划,应该和美国上个世纪西部地区的铁路网建设,二战后的高速公路网建设;30年代苏联在乌拉尔地区的投资;70年代的日本列岛建设计划等等相提并论。说到底,今天在中西部地区进行国土整治工程,就是要使该地区的资源能够资本化,利用中央权威将沿海地区的利益向中西部转移。而且,开发中西部绝对不是为了投资而投资,而是要形成投资和内部消费的良性循环,为内陆地区的8亿人口营造购买力基础, 使中国经济能够均衡地发展。
实际上,90年代中期国土整治已经展开,新疆地区的石油资源开发、京九铁路、南昆铁路、三峡大坝和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是其中的代表。但是,这些耗资不小的项目应该只是更大规模的国土整治工程的开端。在21世纪面前,在庞大的中国经济规模面前,以中央政府目前调动资源的能力,原来的规划必须改变和扩充,加入更多、更全面的项目。例如,关系到西北地区生态改善的南水北调工程,关系到华北平原安危的黄土高原改造计划,关系到经济起飞和国家安全的西南和西北地区公路、铁路网络的建立等,都需要国家从战略的角度加以研究,尽快形成合理的方案,付诸实施。
中部地区城市化
在完善基础设施、改善自然生态的同时,要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建设。大规模的国土整治工程,依靠的是中央政府的国家意志。有了比较好的生态环境,中西部地区发展还只有一个外部环境,今后长期而持续的发展必须在内部形成合理的机制。积极开展城市化,将农民从农村解放出来,是中西部地区完成自我积累的必经阶段。
笔者的建议是在县城的基础上,鼓励农民进城,组建一批10万人左右的城镇(10万人是城市实现规模经济的起点,10万人才可以突破城市化的门槛限制)。通过在城市内部派生出新的需求,形成新的增长点。将县城从1—3万人扩大到10万人,需要一定的房地产和道路等基础设施,带动钢材、水泥等的需求;而城市形成10万人规模后,又会派生出教育、医疗、电信、交通、商业、金融等服务需求,创造就业,形成良性循环。从资金来源看,除了初期用于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的启动资金需要从银行贷款外,部分资金可以通过出售户口、土地等方式获得,也可以由政府出面发行债券,其中的关键是要鼓励进城农民自行投资,结合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力量进行,估计这个过程3—5年即可完成。中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必须引起政府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其成败与否,应该是中国经济发展能否顺利从沿海走向内陆的关键所在。
推动消费的持续增长
从全国范围看,从长期看,消费必须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流(发达经济60%以上是由消费推动的),这意味着今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点将是推行需求管理,突破市场对供给的制约。在这个领域,笔者认为有三个问题值得重视:
一是稳定消费者的心理预期。近年来,由于国企、政府、福利等方面改革的推行,人们的就业观念、福利观念、教育观念发生空前变化,加上通货紧缩的出现,令人们对未来的消费预期明显改变,对经济增长出现严重打击。因此,如何在短期内,稳定人们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消费预期,树立消费信心,是政府必须考虑的问题。
二是在金融改革中,有必要引入消费信贷的概念。消费的持续增长,必须依靠银行和金融体制的支持,特别需要消费信贷的支持。在发达国家,消费信贷是银行的一个重要业务,而此项业务在中国却是一个空白。当前在城市实行住房、汽车的分期付款,今后对农村市场实行家用电器分期付款,是形成持久的消费增长的前提条件。
三是要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处理好城市和农村消费、高档和大众消费品的关系。消费增长,必须是大多数人的消费。城市工薪阶层和广大农民的排浪式消费,才是消费的主流,才是消费持续增长的真正基础。为此,处理好收入分配政策、完善税收政策,需要提到政府的议事日程上。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有关政府的作用、财政平衡等方面的经济哲学必须重新思考。
结论
过去2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并非来自出口导向。本文在这个时候对所谓的出口导向提出反思,并不是因为它是既成事实,而是因为它逐步主导了学术界,深入影响了政府的决策。如果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出口导向的思想继续主导学术和政府的思维,将利益分配格局继续偏向东部沿海地区,很可能违背大国经济发展的规律,令中国贻误崛起的时机。
当前,中国政府强调扩大内需,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这种转变,只是在外部金融危机的压力下,在内部周期的作用下的偶然选择,是一种纠偏举措,是在被动地寻找经济增长点。实质上,对比大国的经验和过去20年的发展历史,扩大内需有其深刻的必然性。如果中央政府能够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将短期的反周期行为与中长期的战略规划结合起来实施,主动提出、良性规划内需的扩张过程,应该更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标签:中国改革开放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对外贸易依存度论文; 国内生产总值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消费投资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