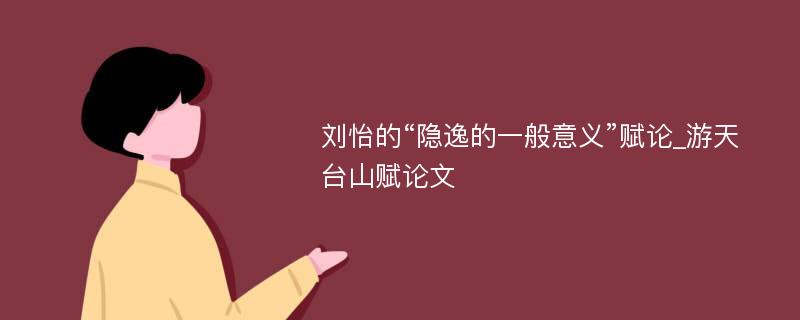
刘壎《隐居通义》的赋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刘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唐、宋以来,江西物阜民丰,在文艺和学术方面,人才辈出。宋元之际的刘,和生活于元初的祝尧〔1〕,都是本籍江西而于辞赋批评上有重要贡献的人物。刘、祝二人标榜“古赋”,剖论取径,刘力倡“风骨”之说,而祝尧强调根本于情而绾合辞理,并由此构建独特的赋论系统。二氏所论,虽规模大小不同,就照顾范围而言,刘壎亦远不及祝尧,但都是会心有得,论赋的深度远迈前人;不让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专美。作为开风气的人物,刘壎不但丰富了赋论的内涵,于古代文论的范畴增添了砖瓦,是研治宋元文论极值得重视的对象。就本世纪的研究状况说,刘壎的诗论已渐受重视,但在赋论方面,仍有待探索。本文就《隐居通义》勾勒刘壎赋论大体,所以抛砖引玉,以祈刘氏的成就获得适当的注意。
刘壎(1240—1319)字起潜,江西南丰人;年三十七宋亡,落落不偶;十八年后人仕,始署建昌路学正,至七十岁迁为延平路学教授;延祐六年卒,年八十。 〔2〕《隐居通义》三十一卷成于晚年,通论诗、古赋、文章、骈俪四体,大都属读书和阅世的体会,颇有神解,纪昀《四库提要》每多征引以为衡文的制断。其中卷四和卷五专属“古赋”,首冠总评,缕述有关古赋的看法,是刘论赋的纲领;然后甄录十六篇宋元辞赋,附缀序论说明背景和优劣,是刘壎赋论的重要组成部份,价值不下于抽象理念的阐绎。先列举所选定篇目如下:
傅自得《秋花草虫赋》;《味书阁赋》;《丽谯赋》;《训畲赋》;
陈文定公《怀皋赋》;
杨万里《浯溪赋》,
黄庭坚《毁璧》;
宋璟《梅花赋》;又一篇;
桂舟谌公《落月赋》;
欧阳修《述梦赋》;《哭女师》;
苏辙《御风词》;
苏轼《昆阳城赋》;
吴镒《义陵吊古赋》;
邢居实《秋风三叠》。
所选都是刘氏及身和两宋的作品。因此,对《隐居通义》两卷“古赋”的内容,切不可望文生义,误以为是两汉辞赋的讨论。刘透过作品的诠选以说明创作主张,乃是古代文论的传统。《隐居通义》的辞赋批评,既可视为研治宋辞赋的材料和线索,也是探索刘壎赋论的依据。
一、风骨苍劲、义理深长:以黄庭坚为典型的诠赋标准
《隐居通义》卷四古赋的“总评”,是刘壎赋论纲领所在,透露了刘壎对辞赋创作的基本主张。先迻录于下,随后分析说明。总评谓:
作器能铭,登高能赋,盖文章家之极致。然铭固难,古赋尤难。自班孟坚赋《两都》、左太赋《三都》,皆伟赡钜丽,气盖一世;往往组织伤风骨,辞华胜义味;若涉大水,其无津涯,以浩博胜者也,六朝诸赋,又皆绮靡相胜,吾无取焉耳。至李泰伯赋《长江》、黄鲁直赋《江西道院》,然后风骨苍劲,义理深长,驾六朝,轶班、左,足以名百世矣。
近代工古赋者殊少;非少也,以其难工,故少也。其有能是者,不过异其音节而已,而文意固庸庸也。独吾旴傅幼安自得深明《春秋》之学,而余事尤工古赋。盖其所习,以山谷为宗,故不惟音节激扬,而风骨义味,足追古作。愚亦素喜山谷诸赋,诵之甚习,每与此先生文会剧谈,至意气倾豁处,此先生辄曰:“相与读山谷赋,可乎?”因振袂同声朗诵激发,觉沆沆生齿颊间。呜呼!文明之世,有此真乐,今无是矣。盖吾旴以诗者:黄希声、黄伯厚、利履道、赵汉宗诸人;以古文名者:张诚子、刘信翁诸人;而以古赋名者,幼安一人而已。今其年八十有三,苦未疾多蹇步,乱离间阻,文会阔疏,因思此老畴昔谈词如云,山鸣谷应,今则无复此奇士矣。景定壬戌岁(1262),郡太守钱侯应孙招予,与幼安客郡斋,同游平远台。幼安雄辩倾坐,听者为竦。其后交游诸公贵人,问与幼安聚会之日常多,而议论常合,乃思其人而不 得见,因追寻其所作古赋一二,姑载于此,以备遗忘,且以示诸儿,使知吾旴有此前辈,又知古赋之精工者不得多云。〔3〕
刘壎于“古赋”一目,不以时代为取尚;于汉晋大赋有肯定,也有保留,问题在这种为后世赋家视为典则的作品有“组织伤风骨,辞华胜义味”的严重缺点。刘壎所说“古赋”,自然不是汉晋大赋,而是心目中理想的赋体。这种现象,和韩愈倡导的“古文”取义相同。“古”和时代无关,只是借以标举一种端正文风的资藉。若望文生义而批评韩愈或刘壎“复古”,便完全摸不着边际。
刘壎通览赋史,确定黄庭坚的辞赋具备了“风骨苍劲,义理深长”的特色,视之为心目中“古赋”的理想典型。刘壎所推崇的文友傅自得,“尤工古赋”;在所录傅自得作品的后序,刘壎誉之为“独步当世,是为大手笔”。刘壎如此激赏傅自得,实因傅自得的作品瓣香黄庭坚,所谓“盖其所习,以山谷为宗,故不惟音节激扬,而风骨义味,足追古作”。傅自得作品不但具备仰昂的声情,也包蕴“风骨”和“义味”这古赋典型的两大要素,深得黄庭坚的神髓。值得注意的,是《隐居通义》所收录黄庭坚的作品,只有《毁壁》一篇。刘壎序说:
近世骚学殆绝,惟韩文公作《罗池庙碑》歌辞,世以为有“骚体”。又李太白诗云:“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世以此语酷似。至宋豫章公用功于《骚》甚深,其所作亦甚似,如《毁璧》一篇,则其尤似者也。
视《毁璧》为黄庭坚的代表作。刘剖析黄庭坚辞赋取径所在,以为渊源于屈赋,深蕴一股悲怨情怀,刘壎引朱熹的序已明白说《毁璧》“其词极悲哀”。则所谓“风骨苍劲,义理深长”的古赋特色,实根植于悲情,风骨和义理皆本之而出。刘壎所要求于古赋的,不是汉晋大赋的铺张扬厉,而是《楚辞》悲怨的情怀。风骨的苍劲,和义理的深长,乃是从悲怨之情自然流出。卷五于桂舟谌公《落月赋》后序说:
此桂舟谌公为故友范去非作也。奇丽悲咤,趣味深长,足与《毁壁》并驾。
刘壎认为《落月赋》能够比美典型的《毁璧》,评之为“奇丽悲咤,趣味深长”,极表赞赏之情。若运用训诂的互文法,则刘壎所倡风骨和义理(或义味)便可从《落月赋》的评语中求得较具体的理解,“奇丽悲咤”与“风骨苍劲”可视为义近,而“趣味深长”跟“义理深长”亦可互文。如是,则风骨取喻于从悲情流出的奇丽表现,而义理乃属相关于人情的趣味。
二、悲怆与激扬:傅自得的影响
刘壎以黄庭坚的《毁璧》为古赋典型,对这篇范文进行仔细的评析
此词三章,一章言其失爱于姑也;二章言其死而不免于水火也;三章言其死后山川寂寥也,每章以“归来兮逍遥”句结之。卒章疑有误字。公作此词,清峭而意悲怆,每读令人情思黯然。
作品所表现的悲怆感情,令读者深受感动。卷二甄录了欧阳修的《述梦赋》,序谓:
其词哀以思,似为悼亡而作者。(《古赋辩体》卷三引)
又载欧阳修《哭女师赋》,刘壎评说:
以上两篇(包括《述梦赋》),悲哀缱绻,殆骨肉之情不能忘邪!
选载欧阳修这两篇叙述悲哀情怀的作品,已足见选者好尚。刘壎又选了吴镒的《义陵吊古赋》,以为“殊苍劲有风骨”,缀评语说:
此赋幽然而深,黯然而光,读之令人凄然而悲。
吴镒赋深具风情,也是悲怀的表现,令读者“凄然而悲”。刘壎所倡的风骨,实与悲怆情怀密不可分,从赋选和评论中充分显示这审美倾向。
刘壎在《总评》里忆叙与傅自得相与朗读黄庭坚赋,“振袂同声朗读激发,觉沆瀣生齿颊间”,这种激扬感情,乃自然流出肺腑,非矫励所能致。呼应之间,读者必然先具备这种情怀,于是读赋的时候给引诱出来,乃至声情畅茂,不啻己出。刘壎以悲怆为本的“风骨义味”要求古赋,也视黄庭坚的作品为古赋的样板,若从读者角度看,持论者亦必然具备这样的情愫。先从刘壎极为心折的传自得说起。
《总评》中刘壎称傅自得为“奇士”,能够“雄辩倾坐,听者为竦”,就此已见傅自得的卓牵。刘壎对傅自得的文章,有这样的评价:“幼安本以笺表见知诸公间,然四六殊不及赋笔。”又说他“深明《春秋》”,“尤工古赋”。可见傅自得之作古赋,非徒舞弄文辞,其中显示了他的才情和学问。卷六诗歌类录傅自得《四诗类苑序》,其中有论赋的一段文字:
发于性情为真;本乎王道之正,古之诗也。自《风》、《雅》变而为《骚》,《骚》而赋。赋在西京为盛,而诗盖鲜。故当时文士咸以赋名,罕以诗著。然赋亦古诗之流,六义之一也。司马相如赋《上林》,雄深博大,典丽隽伟,若万间齐建,非不广袤,而上堂下庑,具有次序。信矣词赋之祖乎。扬子云学贯天人,《太元》、《法言》与《六经》相表里;若《甘泉》诸赋,虽步趋长卿,而雄浑之气溢出翰墨外,则子云无之。他日自悔少作,或出于是。至若王荆公谓赋拟相如为未工,朱文公又谓雄赋止能填上腔子,岂以其文之不工,记之不博哉!正如追逐模拟,其气索尔。自后作者继出,各有所长,然于组织错综之中,不碍纵横奇逸之势,则左太冲之赋《三都》,视相如尚几焉,当时文士皇甫士安则为之序,刘渊林、张孟阳则为之注。夫文人相轻,从古而然,而一时巨擘,皆左袒敛衽,精金良玉,自有定价,岂待时改世易而后有顾者与谭不及见之恨哉!
傅自得工于古赋,论赋亦自有见地。惟论赋取司马相如,视为极则;认为左思《三都》自有价值,以为差近司马相如。而司马相如辞赋的特色,在于“雄浑之气溢出翰墨外”。就好尚而言,刘壎赋论未可视为傅氏的余影。诠赋内容虽然有异,但不碍相得之情。刘壎惟钟情于傅自得的作品,于赋论别有所见。创作和评论,始终是存在一段距离。以傅、刘为例,文学相知不等如持论相同。因此,对待文学集团,便须分别看待,不能以某一成员的主张视为共同倾向。刘壎赋论具有独创性,是绝无疑问的。
三 历朝赋家论评
刘虽未有讨论历代赋史的专篇,但在《隐居通义》中的序评文字,亦间涉古代赋家的品评和名篇的分析,加以组合排次,也可见其大体。即使未足以反映赋史全局,而其中很多意见颇为精到,实会心有得之语,足以为研治赋史者提供参考。
屈赋之为辞赋大宗,殆不可诬。刘虽未直接论屈赋,但论到古赋典型的黄庭坚,谓: 宋豫章公用功
宋豫音公用功于《骚》甚深,其所作亦甚似,如《毁璧》一篇,则尤似者也。
《毁璧》之视为典范之作,精神命脉则直承屈赋。可见屈赋于刘心目中的主导地位。这种归依屈赋的态度,和傅自得宗主司马相如大异其趣。刘壎身处易代之际,于屈赋必然存在一种隐微的会心。
于汉魏六朝,刘特表班固和左思,《总评》谓:
自班孟坚赋《两都》,左太冲赋《三都》,皆伟赡钜丽,气盖一世。往往组织伤风骨,辞华胜义味,若涉大水,其无津涯,是以浩博胜者也。
认为班、左的京都赋有凌跨一代的恢宏气魄,但往往受制干结构和辞采,有损古赋所应具备的风骨和义味。卷五有《三赋》一节,专论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东晋孙绰《游天台山赋》和宋鲍照的《芜城赋》,总评优劣所在,文谓:
后汉王文考作《鲁灵光殿赋》,晋孙兴公作《游天台山赋》,宋鲍明远作《芜城赋》,皆见推当时,至谓孙赋掷地作金声,贵重可知。
由今观之,三赋虽不脱当时组织之习,然孙赋 则总之以老氏清静之说,鲍赋则惟感慨兴废,王赋则惟颂美本朝,各极其趣也,文考最为英妙俊敏,溺水死时二十余耳。《后汉书》载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人;有子延寿,字文考,有俊才,游鲁作《灵光殿赋》,时蔡邕亦造此赋,未成,见延寿所作赋,奇之,遂阁笔。兴公名绰,太原人,仕晋为著作郎、廷尉卿。明远名照,宋世祖时为中书舍人,后事临海王子顼为荆州,照为前军掌书记任。子顼败,为乱兵所杀。有才无命,往往如此。
对王延寿和鲍照,惜才的成份较多,缕叙生平,已见悯惜之怀。至于三赋,虽评之为“各极其趣”,终未得诩为典范。同卷又评江淹《别赋》说:
江文通作《别赋》,首句云:“黯然而销魂者,别而已矣。”词高洁而意悠远,卓冠篇首,屹然如山,后有才者不能及也。惜其通篇止是齐梁光景,殊欠古气。此习流传至唐,李太白诸赋不能变其体,宋朝、国初亦然。直至李泰伯《长江赋》、黄山谷《江西道院赋》,出而后以高古之文,变艳丽之格;六朝赋体,风斯下矣。然文通此赋首句,虽千载之下,不害其为老。
刘壎于六朝赋甚不以为然,《总评》已明示“六朝诸赋,又皆绮靡相胜,吾无取焉耳”,这是对六朝赋总的评价。但对于《游天台山赋》和《芜城赋》,刘壎也是另眼相看,没有完全否定其价值。对待江淹《别赋》也是这样,肯定起笔的老辣,虽全篇都是“齐梁光景”的绮艳铺排,亦不因此而全盘否定。刘壎这种批评态度是可取的。
对于唐赋,刘壎不太许可,认为是“齐梁光景”的余波,即使如李白这样大才的作家,亦未能一洗颓态。而六朝的绮靡,波宕所及,以至于宋、元,于诸唐赋中,刘壎特别欣赏开元宰相宋璟的《梅花赋》。卷五选评谓:
昔人谓广平(指宋)铁石心,乃能宛转作此赋。
是说以宋如此硬朗的人物,也能写出这样委宛动人的作品。《梅花赋》为宋少年自抒衷情的作品,借赋寒梅以表现脱俗不群的高洁情怀,赋文所说的“岁寒独妍”、“独步早春,自全其天”,都是深有寄托,取则《橘颂》,抒述怀抱,宛转不直露,而真情贯注,非堆砌组织之文。刘壎虽主风骨劲健,但于表现方式,仍倾向于婉转,例如卷五选录的《落月赋》,便评为“词旨深婉”。《梅花赋》正是以宛转述情而为刘壎所赏。即使如此,《梅花赋》相对于古赋的准绳,即本悲怆情怀所体现的风骨苍劲和义味深远,仍存在距离。可以说,汉魏六朝隋唐五代,没有一篇作品足以阑人标准而成为典范。
刘壎于宋元赋,则另眼相看。虽然六朝余波仍在,但亦相继出现一批作家和作品,足以比匹古人。卷五欧阳修《述梦赋》的序谓:
欧阳公《秋声赋》清丽激壮,摹写天时,曲尽其妙。《憎苍蝇赋》次之,用事写情,俱无遗憾。又有《述梦赋》,其词哀以思,似为悼亡而作者。
举述欧阳修三篇典范之作,极表欣叹之情。又评欧阳修《哭女师赋》“悲哀缱绻,殆骨肉之情不能忘邪!”都是肯定欧阳修作品的价值。对苏东坡也显示欣赏的态度。卷四评苏轼《山中松醪赋》说:
东坡赋《山中松醪》,有曰:“遂从此而入海,眇翻天之云涛。”句语奇健,可以见其胸次轩豁,笔端浩渺也。
知微见著,以小见大,刘就赋文二句拟容苏轼作品的整体特色。卷五收录了苏轼《昆阳城赋》,序评之为“殊俊健痛快”。大体而言,刘壎欣赏的是苏赋健朗俊拔的格调,欧阳修和苏轼作品的风貌恰成强烈的对比,但刘壎均予以肯定,因为悲怆和和健朗都是为刘壎所力倡,一篇并存固佳,各得一体也是上乘。刘壎亦同时甄录了邢居实的名篇《秋风三叠》,序谓:
邢居实字迻夫,苏黄同时人,幼负美才而早夭,人以比李长吉。尝赋《秋风三叠》。昔尝爱之,岁久而忘,今偶复见,谩载于此。山谷尤惜其才,尝哀以诗曰:“诗到随州已老成,江山为助笔纵横;眼看白璧埋黄壤,何况人间父子情。”盖迻夫殁时,其父犹存也。
缕叙邢居实“幼负美才而早夭”事,又引黄山谷悼词助哀,可见刘惜才的衷情。对这位“人比李长吉”的年青才俊的作品《秋风三叠》,刘壎亦特别指出优劣所在,于作品评语谓:
此三章盖亦步骤古诗而为之者,颇有思致。又尝赋《王昭君》,有曰:“安得壮士霍骡姚,盔取呼韩作编户。”予详此《三叠》,虽为人所称,终非自出机杼,超轶绝尘。如山谷《龙眠赋》有云:“道渺涉兮骖弱,石岩岩兮川横;日月兮在下,风吹雨兮昼冥。”又云:“我为直兮棘予趾,我为曲兮不如其已。”似此语老苍峭劲,不犯古人,真伟作也。
刘虽然惋惜邢居实的“有才无命”,但以古赋的准绳权衡,《秋风三叠》还是有不足之处,关键在于“终非自出机杼”,即欠缺了独创性,以致未能“超轶绝尘”。可见作品之能否卓拔超群,作者应具备独创的能力,此即《文心雕龙·辩骚》所说的“自铸伟词”的能耐。刘壎举黄庭坚的作品证明,说明“老苍峭劲,不犯古人”的创造性转化,是黄赋独步的因由。评语中的“老”字,是刘壎极究意的风格特色。论江淹《别赋》首句,便说“虽千载之下,不害其为老”。“老”有老练之意,用于作品批评,凡炼意锻字之讲究而又浑化入神的,都可以“老”字拟容。刘壎举黄庭坚佐说,显示邢居实在文字的锤练上火候未足,例如评吴镒的《义陵吊古赋》,说:
时有当裁截处,傥更锻炼而旴敛之,使归峻洁,则前无古人矣。
足见刘重视文字的锤练,这可以说是江西派诗风在赋学上的体现。
刘对江西诗派祖师黄庭坚推崇备至,《总评》谓:
至李泰伯(李觏)赋《长江》,黄鲁直赋《江西道院》,然后风骨苍劲,义理深长;驾六朝,轶班左,足以名百世矣。于卷五江淹《别赋》评说:
直至李泰伯《长江赋》、黄山谷《江西道院赋》出,而后以高古之文变艳丽之格,六朝赋体,风斯下矣。
刘一直认为李觏的《长江赋》和黄庭坚《江西道院赋》是赋史上的大手笔和转捩点,六朝绮丽余波至二氏,始为所超轶。所谓“高古”,具体而言,即《总评》所说的“风骨苍劲,又理深长”。对待李觏和黄庭坚,刘壎更推崇后者。《毁璧》评语谓:
近世骚学殆绝。(中略)至宋豫章公用功于骚甚深,其所作亦甚似。
说明黄庭坚的辞赋自《楚辞》中转化出个人独特的色彩,遥接《楚辞》的坠绪。而卷五苏辙《御风赋》序又说:
山谷先生作《枯木道士赋》,深得《庄》《列》旨趣,自书之,笔力奇健,刻石豫章。其篇末题云:“子由此以王事过列子祠下,作《御风词》,子瞻问文作何体。曰:‘非诗非骚,直属韵《庄周》一篇’。学者当熟读《庄周》《韩非》《左传》《国语》,看其致意曲折处,久久乃能自铸伟词。”此山谷语也。今得《御凤词》读之,其旨趣正与《枯木道士赋》相似。
从黄庭坚批评《御风赋》的观点,反映黄庭坚辞赋之所以一振颓风,开出高古一格,不独资借《楚辞》,还广泛汲取先秦典籍的优点,《庄子》、《韩非子》、《左传》、《国语》无不精熟,这样方能左右逢源,化腐为奇,而“自铸伟词”,必须经过一段努力和锻炼的工夫。在邢居实《秋风三叠》后评中,刘已指出黄赋用语的“老苍峭劲,不犯古人”;所谓点铁成金,黄庭坚“自铸伟词”的自觉和实践,不但以诗矫厉一代,即使辞赋也成就卓绝。朱熹认为黄庭坚“恁地著气力做,只是不好”〔4〕,批评黄庭坚过分锤练,不够明白。从朱熹的批评看,著意于文词的确是黄赋的特色。刘视之为自振靡风的典范,而稍后的祝尧于《古赋辩体》中亦秉持朱熹的评价,取向的分别是十分显然的。
刘于南宋以迄元初的赋坛十分留意。《隐居通义》收录了杨万里的《浯溪赋》,序谓:
诚斋先生杨文节公万里尝作古赋,然其天才宏纵,多欲出奇,亦间有以文为戏者,故不录,惟《浯溪赋》言唐明皇父子事体,厥论甚当,因录其词。
杨万里也是卓荦之士,所作辞赋表出“奇”的特色;惟刘颇嫌部分作品“以文为戏”〔5〕,故弃而不录,于此可见选者对辞赋矜慎的程度;但过份维护,也许有点矫枉过正。刘认为《语溪赋》得“事体”,于后缀的评语中自表取义所在。文谓: 诚斋此赋出意甚新,殆为肃宗分疏者。灵武轻举,贻笑后代,其讥议千人一律,而此赋独能推究当时人情国势,宛转辨之,犁然当于人心,亦奇已。结语乃步骤《后赤壁赋》;开户视之,不见其处。亦本唐人《湘灵鼓瑟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中间有日“观马嵬之威挫,涣七萃之欲离;殪尤物以说焉,仅平达于巴西”,此四句形容绝妙。
刘壎认为杨赋能摆落庸俗的议论窠臼,从“人情国势”的客观形势审视玄宗和肃宗的关系,为唐肃宗自立事翻案;赋文谓玄宗时“天厌不可以复祈,人溃不可以复支”,已没有能力统治天下,即使处死贵妃杨玉环,亦只能保有“巴西”一隅,大势已去,本自昭然。若非肃宗即位灵武,号令勤王,则天下非复唐之所有。杨万里的翻案文章,深为刘所赏。《浯溪赋》结笔谓:
已而舟人告行,秋日已晏,太息登舟,水驶于箭,回瞻两峰,苍芒而不见。
把如此重大历史事件收结得这样空灵,真极尽运思之巧妙,所以刘评之为“出意甚新”。杨赋可说是古赋中自出杼机之典范。
对于元赋,刘独许傅自得,认为傅赋深得黄庭坚的神髓,风骨苍劲而义味深远,推誉为“大手笔”。《隐居通义》著录傅赋凡五篇之多。详近略远,取法两宋,是刘壎对待赋史的态度。
四、余论
刘壎论古赋,不论从深度和广度言,都足以在文论史上占一重要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刘壎虽标榜“古赋”却不是惟古是尚,而是力主自出杼机的创意;推崇黄庭坚,因为黄赋推陈出新,自铸伟词,一扫六朝靡丽的余波。在刘壎的赋学理念中,古赋跟时代无关,所谓“古”,是“高古”的意思,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悲怆情怀,而表现为“风骨苍劲”和“义味深远”。这样的诉求,是身处易代之际的感情反应。刘壎强调所心仪的傅自得精通《春秋》。这《春秋》的华夷之辨,不可能不引起亡种的愁绪。标榜奇人奇士,这份慷慨,不会蓦然生发。稍后的祝尧,亟主温柔敦厚。这种分歧,与时代密切关连。如果说刘壎的赋论烙上深刻的时代印记,绝不为过。
经过刘壎和祝尧的阐释,有关“古赋”的概念越加丰富和明晰。若从情的原点而言,以“诗为赋”的精神都是一致的。这种认识,对于赋体的理解无疑大有助益;而于创作实践和批评的过程中,充分了解到主体的重要性,自然有主次伦脊,不至于衍漫无所措了。在赋论发展上,刘的赋论和祝尧的赋学先后比美,为元代文论史平添耀目的光彩。亦由于赋体认识更为明确,这对于文体论的发展,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注释:
〔1〕有关祝尧的生平和赋论,详拙著《祝尧〈古赋辩体〉的赋论》,载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学术季刊》第十二卷第一、二期,一九九四年十月。
〔2〕有关刘生平行谊,本王德毅、李荣村、潘柏澄等合编的《元人传记资料索引》,页一八零九。北京:中华局影印台北新文丰一九八二年版,一九八七年,刘壎一生行实,详见龚望曾的《刘水村年谱》,附见于道光十年刻爱余堂刊《水云村吟稿》.
〔3〕本文征引《隐居通义》,用《海山仙馆丛书》本。
〔4〕《古赋辩体》卷三引,详参拙文《祝尧〈古赋辩体〉的赋论》。
〔5〕“以文为戏”自存在特殊的功价,不能一概否定。拙著《韩愈文统探徽》第三章详论,可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