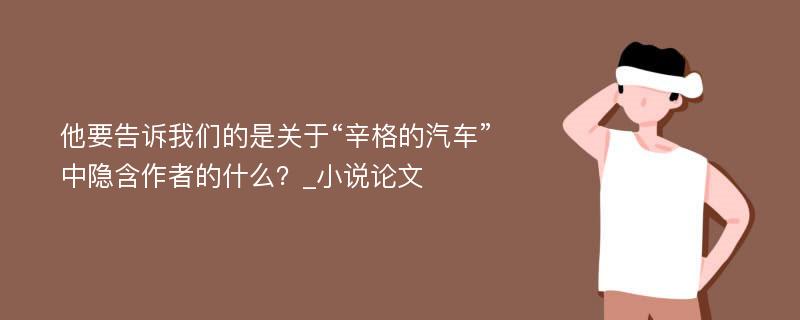
他要告诉我们什么——论辛格《汽车》中的隐含作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他要论文,告诉我们论文,作者论文,汽车论文,论辛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8-0143-04
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1904-1991)是位出生于波兰的美籍作家,一生写过许多著名的短篇故事和长篇小说。1978年因“他的充满激情的叙事艺术,这种艺术既扎根于波兰犹太人的传统,又反映了人类的普遍处境”荣获诺贝尔文学奖。[1](P601)辛格被称之为当今世界上最会讲故事的人之一。他的短篇小说语言朴实、简短、生动;叙述手法传统、精湛,其风格像个老人坐在咖啡桌旁娓娓讲述一个个或亲历或听来的故事。辛格反对对自己的小说做出心理分析或任何解释;他注重的是事实和描述。辛格的哥哥告诫过他一项创作原则:事实永远不会过时或陈旧,但评论总会成明日黄花。他本人也曾经说过:“我一直喜欢故事中的紧张气氛。我喜爱的是:一个故事应该是个故事,应该有头有尾,应该有预示结尾的某种气氛……在我看来,一个故事仍然是读者愿听,想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故事。如果一开头,读者就猜出了一切,即使故事叙述得再好,我认为这故事也不成其为故事。”[2](P346)他的短篇小说《汽车》正是这一原则的体现。读者不仅不能从小说的开头猜出结尾,就连在结尾处,读者感到的都是一种不解与茫然。读者不知道作者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作者的意图是什么。作者完成其叙述任务后,拒绝做出任何解释或心理分析,留给读者的是一连串的悬念和无尽的想象。
《汽车》描写的是一辆从日内瓦出发的旅游汽车,要穿越整个西班牙游览,整个旅途需要12天。其间,作者通过场景的变化——汽车座次调换和入住的旅馆——展开了几个人物的面貌和关系:有塞琳娜和她的丈夫银行家鲁道夫,马克和他的母亲麦塔琳夫人,还有作品中的“我”和麦塔琳夫人的关系。
和“我”比邻而坐的第一个人物是塞琳娜。她是个外貌世俗、浓妆艳抹的犹太女人。她首先和“我”搭话,说明自己的身世:她曾被关押在集中营,出来后嫁给了一位银行家,并皈依了基督教,但她并不信任何宗教,也不爱她的丈夫,她丈夫也不爱她,但不愿意跟她离婚,因为不愿意与她分割财产。之后汽车停到一个不知名的旅社,“我”被马克邀请和他的母亲一起吃晚饭,于是就有了“我”对马克和他母亲的了解。马克是个14岁的男孩,在伦敦上学。他母亲麦塔琳夫人是亚美尼亚人,嫁给了一个比她大40岁的商人,他们曾婚姻幸福,丈夫已经去世,现住在土耳其,那里有她丈夫留下的生意。读者后来还会了解到这个少年老成的马克很有主见和雄心,他特意安排各种场合要“我”和他母亲接触,以便将来成为他的继父;他甚至管制和监护着他的母亲,担当起他父亲的责任;他要去读剑桥或耶鲁大学的商学院。他热情、周到,使“我”不好拒绝他的要求;他又很任性,如果母亲不听从他的,他会以自杀威胁。作者还通过和这对母子的交谈,显露了“我”的部分信息:“我”是个具有美国身份的犹太作家,来自波兰,用意地绪语写作,是个素食主义者。“我”是个坦率、诚实的人,总是告诉别人“我”真实的情况。小说最后,我们还知道“我”是为了忘掉在美国的一个女人才来这次旅行的。
第二天在旅车上,“我”被安排与银行家鲁道夫维耶霍夫坐在一起。这是个典型的银行家的形象:穿着讲究、举止规范、知识渊博。后来这位银行家开始向“我”倾泻他的怨气,他妻子是如何自相矛盾:他——一个基督徒,娶了一个刚从集中营里出来的犹太人,经历了种种压力和困难,而他的妻子却骂他反犹太人;她骂别人反犹太,而她自己却说了很多犹太人的坏话;她把自己扮成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同时却用最恶毒的语言来谴责女性,等等。当“我”问这位银行家他以前怎么没有看到这些缺点时,他说这正是他自己也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就连他为什么告诉“我”这些,他都觉得莫名其妙,按照瑞士人保守的个性,是不会家丑外扬的。他解释说经过十年的婚姻,他妻子没有变成真正的基督徒,他却几乎成了波兰犹太人,经常站在犹太人的立场批判犹太领导人。在“我”和银行家交谈完,进入一家西班牙饭店吃饭时,塞琳娜在饭店门口就赶上“我”,询问是否她丈夫向“我”说她什么,并确定她丈夫一定在谈论她,说她丈夫是个病态的说谎家,他所说的没有一个字是真的。当我告诉她,她丈夫表扬她作为女人她非同一般地有趣时,塞琳娜表示了怀疑。
故事写到这里,主要的人物都已经登场,且他们的性格也都展露完毕。故事进一步发展,主要描写了“我”和那对母子关系的进展。在马克的安排下,“我”不断地有机会和他母亲接触,并相互产生了欲望,但“我”最终克制了自己的欲望,知道和这位商人的妻子结婚是不可能的,如果只保持情人关系,她的儿子马克也许会实施报复。“我”和麦塔琳夫人的关系一开始就受到塞琳娜的警告,她告诉“我”这是个圈套,并且那位母亲和她所谓“儿子”的关系值得怀疑。后来她向“我”又证实了那对母子的不正常关系:服务员看见他们睡在一张床上,他们是情人而不是母子,她再一次警告“我”正钻进圈套里。“我”知道这个女人有点妄想狂,但她的话仍然让“我”震惊,谁知道呢?她说的可能是真的呢!“我”决定尽快逃离这辆汽车,上了开往Biarritz的火车,在火车的餐车上,“我”又意外地遇见塞琳娜。“我”和她交谈起来,当“我”问她为什么总是让车里人等她时,她解释说她也不知道,她感觉被魔鬼所驱使,误入一个又一个圈套里。她好像对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有预感,现在在她谈完她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宿命论后,预感到自己将很快死去。当“我”表示我吃完饭时,塞琳娜说“不像我们坏运气的汽车司机那样,那些追逐我们使我们变得疯狂的力量有的是时间”。
故事就此结束,没有明显的主角或配角,每个人物都分担几乎均等的份额。留给读者的是无尽的遐想和疑惑。让读者感到这辆故事的列车刚刚开始,就戛然而止,有点像急刹车,让人有些找不着北。全篇笼罩着一种神秘、悬而未决的气氛。
读完这篇带有现代主义特征的小说后,我们不禁要问,作者到底想要表达什么?通过这篇短篇小说,隐含作者的意图是什么?我们知道这几个人物都非常逼真、有趣,有自己独特的鲜明性格,且每个人背后都有一大堆故事,作者只是摘取了在旅途中几天的情景来展示他们的部分特征,这显然不是小说的真正意图。所谓隐含作者,根据布斯的理论:“隐含作者”为“作者的第二自我”,作者的一个“隐含的替身”。作者在写作时,不是在创造一个理想的、非个性的“一般人”,而是一个“他自己”的隐含的替身。[3](P82)根据笔者对布斯理论的理解,隐含作者不仅是指作者的替身,还可以是小说的中心意图,即中心思想,它代表着作者在他/她创作的小说中的意志、态度和他/她想传达的思想。[3](P83)那么在这篇短小精悍、以断裂式方式结束的小说中,其隐含作者到底是什么?它在哪里?
从小说篇幅的分布来看,作者着笔较多的是塞琳娜这个人物。她打扮俗气、艳丽,语言尖酸、刻薄,有些妄想狂;她还有点女巫般的、神奇的预测能力,小说有几处提到她这种能力。这种预测能力也许是她妄想狂的结果,也许是她真实具有的能力;在她第一次向“我”谈及麦塔琳夫人和她儿子时,她就指出:“我不太确定这个男孩是否是她的儿子。他们之间好像存在某种不自然的关系一样。”[4][P215)后来她又通过服务员的眼睛证实了她的猜想;不过她的话的真假也无从判断,连叙述者“我”也不知道是否应该相信她。这一切又增加了这个女人的神秘气息;同时她自己也说她像是被某种神秘的东西所控制,就像魔鬼附体,做出她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的举动。在故事结尾又是以她那神秘的、女巫般的话来结束:“那些追逐我们使我们变的疯狂的力量有的是时间。”这种力量到底是什么?是不可言说的命运?是妖魔?是撒旦?还是欲望?读者和小说中的这两个人物都不清楚。
笔者认为小说中的隐含作者是想通过塞琳娜这个人物表达一种命运的神秘感、一种宿命论。人有时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由某些神秘的力量来牵引着,就像塞琳娜自己所说:一切都是注定好的,每一件事,每一个字,每一个想法。有的评论者认为塞琳娜代表了在纳粹的种族压迫下人性的扭曲。[5]笔者倒不这么认为,因为在小说中作者通过塞琳娜的丈夫银行家鲁道夫维耶霍夫反驳了这一观点。他有这么一句:“我告诉自己是集中营和漂泊的生活毁了她的神经,但我也见过其他从集中营里出来的女人,她们都沉静、有修养、令人愉悦。”如果把塞琳娜的性格、举止归为纳粹压迫下的结果,显然和这句话有逻辑矛盾,她的特点不具有共性,是属于塞琳娜个人的,她并不能代表从纳粹集中营逃脱出来的那些女人。塞琳娜是辛格笔下受神秘力量驱使的人之一。他们往往缺乏信仰,迷失自我,批判、咒骂和对抗周围的一切;同时他们内心又遭受煎熬,没有归宿感。
事实上,对妖魔鬼怪的描写一直是辛格短篇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如在《辛格访谈录》中,他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我把魔鬼、精灵当作文学的象征符号来用的,但我拿它们作象征符号是因为我对它们有感情。如果我对这些东西没有感情,就不会用它们。我仍然怀有这样一种想法,认为我们周围弥漫着各种神秘力量,我就是怀着这种想法长大的,今天我仍然摆脱不了它们。”辛格的魔鬼可分为两类,一种是人类之外存在的魔鬼,辛格由于受成长环境的影响一直相信它们的真实存在;另一类是人性中的心魔,一种邪恶的、非理性的力量。它们是辛格所说的文学象征符号,是他用来“说明人性中存在着导致让人不断走向毁灭的一种反常力量”。[6](P190)本篇中的塞琳娜就饱受心魔的折磨,她不接受基督也不相信犹太教,长期遭受失眠的痛苦,被神秘的力量所驱使,做出了连她自己都欲罢不能的事情。这种心魔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它来自于哪里?以笔者之见,它或许来自于信仰的缺失,或因物欲的膨胀,或原于对性欲的引诱。一旦这种心魔控制了人心,人就会做出脱离人本性的事来。就像辛格的另一篇短篇小说《不被看见的人》中的内森,他受魔鬼的驱使,与他的相处50多年的妻子离了婚,娶了年轻、美貌的女佣,结果却落了个颠沛流离,凄惨死去。
小说中另一个隐含作者,是关于犹太人的情性欲世界。根据叙事学的原理,关键词汇出现的频率越高,就越可能成为小说的主旨。小说中多处提到人的性欲和性欲相关的词汇。如银行家鲁道夫维耶霍夫和他妻子塞琳娜之间的情欲。纵然塞琳娜有百般的缺点和不是,他还是迎着种种阻力娶了她。当叙述者“我”问他为什么会这样时,他提到她其中一个好处——她有吸引男性的魅力:性欲强,有奇异的想象力,能让他发狂。他们的白天很糟糕,但夜晚却很疯狂。可能这是塞琳娜吸引银行家的唯一原因,因为他再没提到她的其他好处。而这位银行家本人的性取向,按他妻子的说法是:她丈夫是个性变态,潜在的同性恋,爱听她和其他男人的故事,听完后,又咒骂她。最让人感到震惊和疑惑的是麦塔琳和她“儿子”马克之间的奇异关系。通过塞琳娜的描述,这对母子不是真正的母子而是情人的关系。作者提到的另外一处情欲是麦塔琳夫人和比她大40岁的丈夫之间的。麦塔琳夫人曾向“我”描绘了她那巨人般的丈夫:他有狮子般的意志,巨人般的力量,一天能喝15杯的苦咖啡,烟从早抽到晚,否则能活一百岁。他让她筋疲力尽以至使她对性爱产生厌倦。他去世时,她曾感到轻松,总算能松口气了。其实从小说中心人物的角度来讲,麦塔琳夫人丈夫的情欲如何完全可以不在作者要描述的范围之内,他不是乘客,是乘客中一位妇女已经去世的丈夫,但作者通过麦塔琳夫人的描述,使读者看到了一个精力旺盛、性欲强烈的中年商人。巧合的是,这位商人和塞琳娜还有叙述者“我”一样,都是犹太人。
真实作者之所以这样安排,是为了突显犹太人的情欲世界,通过对犹太人这一特定人群的描写,展现情欲对整个人类的生活、命运的影响。在强烈情欲的驱使下,大40岁的商人娶了他办公室里刚来的职员。在同样情欲的驱使下,理性而保守的银行家、基督徒鲁道夫维耶霍夫力排众议,娶了从集中营里逃脱的犹太人塞琳娜。此外叙述者“我”和麦塔琳夫人之间也产生一种欲望,“这种欲望不是爱情甚至也不是情欲,而是某种类似动物的一种欲望”。随着双方不断地接触,这种欲望不断地升级,尽管“我”很想和这位夫人有点故事,但“我”最终控制了这种欲望,因为马克可能会杀掉任何一个对他母亲不敬的人。“我”终于用理智终止了一段没有结果的欲望。即使是不爱丈夫也不信宗教的塞琳娜也还保守着爱的秘密,她胸前戴着的黑色十字架,暗示着她对某段感情的忠贞和怀念。甚至是在小说的最后,塞琳娜幻想着她命运的结束是在一夜狂欢后,她的情人拿刀刺向她的胸脯,她认为这是爱的行为。
综观小说的全局,描写犹太人的情欲世界,或者说犹太人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情欲斗争,是这篇小说的另外一大主题。他们的情欲充满诱惑、矛盾,失望甚至罪恶;他们受情欲的摆布而脱离了生命原有的轨迹。叙述人“我”也在思考这一点:“我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对的,他们避免看到女性!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每一个遭遇都导致罪恶、失望和羞辱。”[4](P562)叙述者的这句话也表达着本篇隐含作者的对男女情欲世界的失望、矛盾的观念。爱与性一直是吸引辛格的两样东西。对于辛格小说中的性爱主题,辛格自己曾说过:“人总得触及人的本性,这不是愿意与否的问题。我认为,恋爱和做爱最能触及人性。这时,会懂得关于生活的许多东西,因为在恋爱和做爱中,一个人的性格最容易表现出来。”[2](P338)并且辛格对性爱的描写不仅是为了揭露人类的本性,更有的时候是“为了弘扬犹太传统的伦理道德。”[6](P215)但是,辛格的情欲是有限度的,如果他们的情欲超过一定的规范,超出了社会伦理道德的边界,他总是让他们跌得粉身碎骨。从他对另外两个短篇《短暂的星期五》和《血》的结局的不同处理手法上可以看出:“前者为符合犹太伦理道德的情爱和性爱而死,所以,辛格让这对虔诚的夫妻升入天堂;后者则为违反犹太伦理道德的色欲而亡,因此,辛格让这对丧心病狂的男女受尽折磨,最后悲惨死去。”[6](P214)
因为这篇小说独特的创作风格与写作手法,有评论家把辛格归为现代主义小说家的行列。辛格断然否认这种说法,他不愿意被纳入任何主义里面。但小说无论从创作手法——情节上的悬止和虚无主义的主题思想都有着现代主义的迹象,这种痕迹并不能因辛格的主观拒绝而被否认。是不是现代主义,这不是辛格所关心的事情,他所关心的是作品要有娱乐性,要吸引读者的兴趣;同时让人们重拾对上帝的信仰和传统观念的信任,他认为这正是一位作家应有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