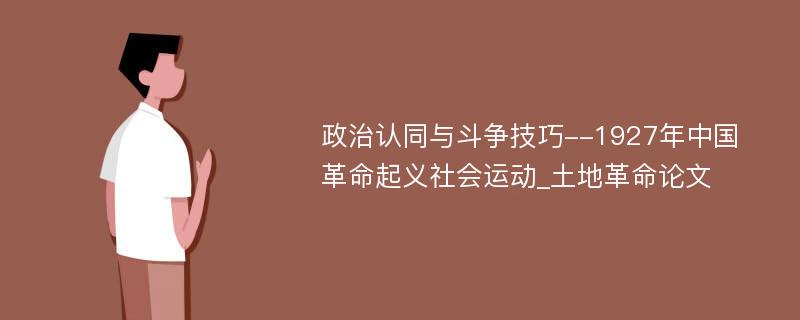
政治认同与斗争手法——作为社会运动的1927年中国革命暴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暴动论文,年中论文,手法论文,政治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3)06-0019-13
中共党史学界普遍认为1927至1928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系列武装起义(或暴动),是其后土地革命的先声。党史学界对革命暴动的学术重要性已经给予高度关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尚缺乏整体性的综合分析①。笔者认为,除南昌起义外,各地武装起义都是对“八七”会议精神的响应和发扬,具有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应具备综合考察的基础。同时,笔者认为引入社会运动理论的相关框架,对这些起义作微观分析,有助于剖析暴动进程的内在机理和演进脉络,深入对这一问题的理论认识。
“社会运动理论”其实是对传统经典革命研究的反动。“二战”后欧美新兴的新社会运动,提醒学者们以逆传统常规的视角,关注那些在社会动员的广度与深度甚至对抗程度上并不逊色于经典革命进程的“新社会运动”。从20世纪末期由苏联、东欧所谓“民主化”浪潮开始的,直到本世纪初十年仍然方兴未艾的一系列全球性的社会冲突,以其暴力因素的重新回潮和斗争手法的不断翻新,更进一步丰富了社会运动理论的实证基础。当暴力斗争的最集中体现“革命”仅被作为“社会运动进程”来理解时,暴力革命中的一些内在机理可以得到更深入的剖析。因为“当某一革命轨迹中所发生的情形被看成是许多因果机制交互作用的结果时,革命轨迹中所发生的种种(现象)才能更好地得以理解”②。笔者不揣浅陋,拟以上述思路为线索,从政治认同、斗争手法两方面,以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下简称秋收起义)、黄麻起义和广州起义为个案,对1927年革命暴动做综合分析,以期增加学术界对土地革命史的学术认知。
一、1927年中国革命暴动中的“政治认同”
1、暴动的“社会运动基础”。作为社会运动的革命暴动,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运动基础”。这种基础,一方面体现为暴动领导者对起义前政治形势,特别是“政治机遇”的分析,同时还隐含着暴动领导者对革命暴动可能造成的影响及未来前景的预期。“社会运动基础由一些运动组织、网络、参与者以及累积起来的文化人造品、记忆与传统组成,这些因素均有助于社会运动活动的开始”③。对于1927年革命暴动而言,社会运动基础意味着革命形势,“包括某一特定政权内部发生的明显分裂,与之相伴的每一个政党都分别控制着该国某些重要地区或某些统治工具”④。国民党和共产党分别拥有各自的政治资源。前者拥有作为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成果的合法政权,以及相对成熟的政治经验,特别是居压倒性优势的正规军事力量;后者则自认为可以把大革命时期的工农运动天然地转化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共产党甚至因此乐观地认为革命仍然处于高涨的阶段。南昌起义和“八七”政治局紧急会议后,中共中央对形势的评估相对乐观,认为革命形势有利于暴动和使革命重新走向高潮。如“八七”会议后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决议案就认为:“据一般的客观形势看来,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其胜利是极不稳固的。而革命之重新高涨,不但在最近期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免的”。⑤
尽管中央认为南昌起义的条件是成熟的,但事后证明:“就时间说,未能暴动于长沙事变,工农群众激昂有力,又逢河南有事,而武汉尚多同志武装之时,而暴动于国民党三派联合成熟的工农及军事力量削减与消沉之时;就空间说,不能暴动于工农有力军事要点之两湖,而暴动于工农不甚觉悟,形势不好,军实无源之江西”⑥。所以,南昌起义时机的选择其实并不理想。但考虑到起义所依赖的正规军事力量仅有贺龙和叶挺二部的尴尬现实,以及张发奎欲借九江会议之机扣押叶、贺的危急情势,起义仍然是必要的。问题在于选择南下广东的进军方向,不能充分利用既有的社会运动基础。南昌起义拥有1927至1928年共产党领导的各次武装暴动中人数最多也最正规化的军事力量,但是即使以如此正规的军事力量作为主要动力,若无工农群众运动的呼应,也很难有所作为。南昌起义军南下途中,由于“沿途全无农民运动,加以反动派的宣传,所以沿途农民闻风而逃”,甚至“因受AB团的宣传,对我们更加仇视,数日不见一人”。⑦
而秋收起义则充分证明,农民的革命情绪并没有如中央所设想的那样高涨,能够天然成为暴动的社会运动基础。起义军“所到之地,农民并未起来,远不及北伐军到时农民的踊跃,大多数农民甚恐慌不敢行动,恐怕军队失败大祸临来的心理充满了农民的脑筋”⑧。大革命失败后,湖南的白色恐怖十分严重,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省政府、省党部对于铲除暴徒,排除共产,遏制工农运动完全秉承唐、何意旨,正在进行,省城公安局之厉行清乡查户口颇为可怕”。⑨白色恐怖高压之下的农民运动,显然很难复制北伐战争后受到广东革命政府鼓励的合法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辉煌。但是,大革命失败后,农民虽然畏惧白色恐怖,可是对现状的不满和对农民运动昔日辉煌的怀念,使他们仍然有可能支持共产党的暴动鼓动。“佃农的二五减租也没有了,租金利息也没有了,地主的帐又要还了,说话也无从前自由了,土豪的屋子仍旧进去不得了,手工业工人的工价也减低了,因此农民渐渐感觉,土豪劣绅到底是欺骗他们的,暴徒专政的时候,实在要好一点。因此他们怨恨而思念共党了,希望共党卷土重来”⑩。这种局面仍然是可以被共产党人寄予希望的社会运动基础。
黄麻起义前的社会运动基础,则比湖南的情形乐观许多。湖北的秋收暴动使湖北农村呈现出鲜明的阶级斗争态势,从而为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奠定下社会运动基础。大革命后的湖北,“在乡间,只要提起打倒土豪劣绅,绝对没有人反对;农民对付土豪劣绅,也不似从前采取儿戏手段,绳子政策,而直接处死,并没收其财产,焚毁其房屋,杀戮其家人”(11)。黄麻起义前的黄安,农村阶级斗争壁垒森严,形成各自军事化的对立局面,尤其有助于革命暴动形势的酝酿和形成。“阔人老爷们有阔人老爷们的组织,穷苦的朋友有穷苦朋友们的组织。阔人老爷们的最有力量的组织是枪会……穷苦朋友们的组织是协会、秘密的‘胁富会’、有刀枪和来复枪的‘防务会’、义勇队及专门杀土豪劣绅的没有名义的团体”(12)。特别是,黄麻起义前,黄安党组织已经在当地农民群众中拥有较深厚的影响。“党争取了县教育局的领导地位,动用‘至诚学款’大量开办公费学校和乡村贫民夜校”,扩大党对群众的组织和影响,同时党“通过清算委员会的组织,清查黄安的义仓及平粜委员会”(13),与土豪劣绅展开经济斗争。这一切都提高了党在农民中的威信。
广州起义前,广东省委本来希望借助南昌起义军的南下,为广东的革命暴动顺理成章地铸成有利于全省暴动的社会运动基础。但是,南昌起义军不幸溃败于潮汕地区,这迫使广东省委更加强调广东自身的条件,认为:“这完全是根据于广东工农群众的伟大力量与剧烈斗争,及广东封建资产阶级之不能稳定而自行崩溃之实际状况。贺叶军队的失败并没有增加敌人的稳定,反而更引起剧烈的内部冲突”,特别是省委分析认为:“李黄张已成为鼎立之势,而直到争夺广东政权之斗争益烈,火拼之期愈近”(14)。起义前夕,广东省委准备借“在目前张李战争当中,张内部又将发生分化,这就是朱晖日与黄琪翔由暗斗而至明争之酝酿”的时机起义。而陈璧君衔汪精卫命要求广州当局解决受共产党影响的教导队的危急形势,更加紧了起义准备的进程。(15)
所以,尽管中国共产党人很难再享有“大革命”时代合法的工农群众运动所必然伴随的政治动员的便利,但是仍然具备发动武装暴动的“社会运动基础”。过分强调所谓敌我客观力量的悬殊,无益于对革命暴动的科学分析。
2、“政治认同”的界定。政治认同对于社会运动组织者推进其运动进程至关重要。“斗争政治的参与者始终操纵、谋划、修改和重新解释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斗争各方的身份”(16)。政治认同的目的正是为了使行动者获得某种身份,“它将人们与某些社会情境而不是其他人联系起来,通过将这些人吸收进那些情境来激活这些身份”(17)。在1927年革命暴动中,共产党人通过唤醒工农士兵暴动者的阶级情绪,以及大革命前后工农运动既得利益实现和丧失的反差,实现对他们暴动者的身份赋予。为此共产党人适时抛弃了国民革命的招牌,而树立起土地革命的旗帜。
在革命暴动中,政治认同,特别是涉及敌我对立营垒的身份赋予,能够起到有效动员工农群众参加暴动,鼓舞其暴动情绪的作用。
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并未断然放弃国民革命的宗旨,即便是在“八七”会议时仍然在强调应继续高举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可在之后的暴动实践中,这一宗旨很快被湖南、湖北两省的秋收暴动所抛弃。起义者正式举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旗帜。
南昌起义期间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便以国民党正统自居,宣称:“此革命委员会之职责,在继续本党革命之正统。于最短期间,当确立一革命之新根据地,以便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一切党国大计,重新选举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以便指导全国革命运动”(18)。起义失败后,旗帜问题成为起义领导人和中央负责人发泄对起义失败不满的出气筒。张国焘就抱怨:“政权形式则尚欲利用国民党旗帜,故主张县区乡政府则建设工农占百分之九十的政权,上级则主张利用国民政府名义,并主张用各县市革命委员会名义以及以左派清党的办法改组国民党,召集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盖欲与汪精卫等争正统也”(19)。由于“八七”会议时南昌起义挂国民党旗帜的消极结果还没有显露,所以共产党领导人仍然认为:“南昌这次政策是对的”,只是强调:“我们的政策不要依靠到几个国民党的领袖上,而是依靠到国民党的群众上面。现在不应退出国民党,与国民党决裂时,要在国民革命成功社会革命时才能提出”(20)。甚至在“八七”会议中被推选为临时中央负责人的瞿秋白也认为:“在革命暴动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此政府仍用国民党的名义,但我们要占多数,成为了农民独裁的政权,乡村中要农会政权”。为避免与南京、武汉当局混淆,“我们要告诉群众,武汉南京北京政府都是反革命的”。(21)
中央的观点最初深刻影响了正在积极组织暴动的湖南省委。湖南省委一度要求“各级党部起来宣布唐生智的省市党部为伪党部,拥护徐特立等组织的秘密省党部,使之成为指导全省的中心”。同时“各级党部尽可能留在现有的党部内奋斗”,甚至在被清洗的情况下“仍须尽可能留一部分在唐的国民党内起党团作用”,(22)可见湖南省委根本没有另立门户的意识。但是湖南省委很快就改弦易辙,在1927年8月20日致信中央表示:“在工农兵苏维埃时候,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因为“从前我们没有积极的取得国民党领导权,而让汪蒋唐等领导去,现在即应把这面旗子让给他们,这已经完全是一面黑旗。我们则应立刻坚决的树起红旗”。(23)但是中央仍然坚持原议,以“中国现在仍然没有完成民权革命”为理由,坚持“仍然以国民党名义来赞助农工的民主政权”。(24)然而,湖南省委坚持己见:“取消国民党只要无产阶级的力量大,左派小资产阶级仍然可以来革命。取消国民党并不成问题”(25)。值得庆幸的是,1927年8月底中央通过的两湖暴动决议案终于要求各地暴动组织者抛弃国民党旗帜,“暴动组织在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湖北分会之下,军事方面乡村用农民革命军,城市用工人革命军名义,简称农军、工军,合称工农革命军”(26)。
广东省委对革命旗帜的认识,则是在总结南昌起义的教训时得到的。广东省委认为:“国民革命军之名义立即废除”。暴动后军队称工农革命军,“一律废除青天白日旗改用红旗,以斧镰为标志,与国际旗同”。(27)
由于1927至1928年的武装起义是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的先声,因此在暴动中,起义领导人无不鲜明宣告土地革命的宗旨,用以号召工农士兵群众参加暴动。南昌起义总指挥贺龙便公开宣告:“中国的国民革命,第一个使命就是要实行土地革命”。他有意识地在自己的部队中鼓动起土地革命的情绪:“我们的下级官长尤其是士兵同志,十有八九都是贫苦的农民出身。我们此次革命的行动,既是为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问题而奋斗,自然就是为解决我们自身问题而奋斗”(28)。
但是,南昌起义过于温和的土地政策受到了中央言辞激烈的抨击。中央批评南昌起义军“关于土地问题提出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地主的主张,这是非常之大的错误,这证明没有土地革命之决心”(29)。这与起义领导人对南昌起义的总结不谋而合。刘伯承认为土地政策的温和,是因为“在当时,以为拿出来了我们的真面目及政治主张,恐怕吓退了小资产阶级,抽了革命联合战线的力量”(30)。
在“八七”会议前制定的中央秋收暴动大纲中,关于土地问题形成了完整的方案,不仅使土地分配方案更加明晰,而且与农民夺取政权的努力相联系。中央要求在暴动中“以农会为中心,号召一切接近农民的社会力量于其周围,实行暴动,宣布农会为各地的政府”。然后在这一农村政权的领导下开展土地革命,“对祠堂庙宇一切公地及五十亩以上之大地主一律抗租不缴,对五十亩以下之地主实行减租,其租率由农民协会规定以佃七东三为大致的标准;自耕农土地不没收,自耕农及已取得大地主田地之佃农应对其革命政权交纳田税,税率由农民协会决定之;农民协会组织土地委员会决定土地之分配”(31)。“八七”会议表示要在土地斗争中,为揭露国民政府“二五”减租的虚伪面目,“必须提出实行完全抗租的口号以答复国民党中央和政府这一骗人的决议案和命令”(32),以彻底区别于国民党的土地政策。毛泽东基于他大革命时期的农运实践和农村调查,在会议上明确表示:“大中地主标准一定要定”,标准为50亩。他认为“小地主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对小地主的政策如果犹豫不决,会影响整个土地工作的深入进行,因此“现在应解决小地主问题,如此方可以安民”。毛泽东还预见到富农问题的复杂性,指出:“富农、中农的地权不同,农民要向富农进攻了,所以要确定方向”(33)。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则认为土地问题“应由农协自己来解决”,因为土地问题具有某种地方特性(34)。
秋收起义前,湖南省委针对土地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毛泽东发展了他在“八七”会议上的方案,提出必须没收地主土地而不是仅仅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以吸引农民。“没收土地的办法,要由革命委员会制定一个土地政纲,将全部办法提出,要农协或革命委员会执行;这个没收土地的政纲,如对被没收土地的地主,必须有一个妥善的方法安插”。(35)毛泽东的方案立足于在革命政权建立的基础上全面推进土地分配。最后湖南省委拟订:“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在内,归之公有,由农协按照‘工作能力’与‘消费量’两个标准,公平分配于愿得地之一切乡村人民”(36)。
湖北省委对土地革命问题的认识远比中央和湖南省委的认识激进。湖北省委号召各地在秋收暴动中坚决“实行抗租抗粮抗捐,健全并扩大农民武装及农协组织,发展流寇式的军事行动,普遍杀戮土豪劣绅,没收土豪劣绅大中地主及一切土地”(37),迅速从经济斗争上升为土地革命。在暴动计划中,省委要求各地“即时没收地主一切财产,并用很简单的方法,将土豪劣绅大中地主的土地及一切公地分配给贫苦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湖北省委的土地政策重在实用,强调“这是初步的分配,并不是科学的分配,手续愈简愈好,分配了土地,农民就会为保有其所得的土地而自动的起来斗争的”(38)。
广东省委在土地问题的认识则相对温和。在省委拟订的暴动后各县市工作大纲中,仅仅提出“没收以靠田租为生活者之土地,其限度以三十亩或五十亩为大致标准,由当地农会决定之”。田租最多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39)但是此议受到中央严厉指责。中央认为“广东的暴动必然要实行达到没收地主的土地。我们无所谓减租不减租,我们根本就不交租,一开始即提出抗租的口号,由抗租而进到没收地主土地”(40)。
虽然强调土地革命的意义,但是暴动组织者并不放弃通过日常经济斗争鼓动暴动的可能性。如广东省委指示南路党组织,“南路适遇灾荒,农民生活更苦,我们即可召集各区乡农民大会,解决今年交租及明年谷种问题……并组织灾荒救济委员会,情知把财产来救济灾农”,从而“借此以鼓起农民群众的暴动”。(41)
总之,通过树立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旗帜,以及鼓吹土地革命的意义,共产党人有效地促进了工农士兵群众的政治认同,引导他们走向暴动推翻国民党统治的道路。
二、1927年中国革命暴动的“斗争手法”
中国革命暴动的斗争手法,一方面具有法国大革命以来城市暴动的特点,另一方面仍然延续了中国农村骚乱的传统。前者自然是倡导十月革命道路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必然选择,主要体现为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中通过巷战对政治中心城市的夺取;而后者又是在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基础上农民革命的顺理成章的发展结果,集中表现为秋收起义和黄麻起义中攻打政治中心城市和乡村骚乱的结合。此外,当时中共党内关于暴动的动力问题,即究竟是以正规军事力量为主动力,还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军队仅是助力的争论,实际上正是有关上述斗争手法的理论分歧。实践证明,在中国工农普遍缺乏军事训练和军事动员的条件下,革命暴动的动力不可避免地选择以正规军事力量为主动力。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都证明了这一点。而黄麻起义尽管缺乏正规军事力量,但当地大革命时期就已经形成的阶级战斗局面,以及革命者对准军事化组织的控制和利用,能够有效弥补正规军事力量的不足。
1、有关暴动动力问题的争论。尽管南昌起义完全属于兵变性质,但是中共中央仍然期待起义中普遍的农民暴动局面的出现,认为“贺叶公开与反革命分裂,一到广东即可引农民的暴动,但粤省委仍应以农民为暴动主力,只有如此,然后才能使贺叶的军队更加改变其性质,更成为革命的军队。如果广东两湖三省的农民暴动都起来了,全国即可改变一个形势,进到土地革命的时期”(42)。中央虽然肯定“叶贺军队的力量,较之普遍零碎的农民军,要强得多,这民众暴动的副力可以有很大的作用”,但是仍然批评他们“是旧式的雇佣军队,不加入工农分子使之改观,是不能担负革命任务到底的”。(43)中央还于1927年10月上旬致函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要求“叶贺军应与农民军合起,直奔广州,沿途不能停滞观望,此时再一犹豫,势必完全消灭,应以尽量多余枪械,沿途武装农民,扩大军队,一直杀去”(44)。南昌起义军在东江地区失败后,中央总结到:“叶贺军队的革命战争,不过是全国民众暴动中的一个强大的副力”,因此中央对南昌起义军的失败结局并不悲观,反而认为:“革命的基础力量始终并不是叶贺的军队,而是工农群众,现在叶贺军队固然失败了,工农民众的力量还却正开展,对于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必要之认识正在与新旧军阀国民党的剧烈的斗争之中,日益广泛而深入于工农群众”。(45)“八七”会议也明确表示:“农民运动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他们应当是农民协会的中心,农民暴动之中应当以贫农为主力”(46)。中央关于两湖暴动的决议案也坚持认为:“土地革命必须依靠真正的农民的群众力量,军队与土匪不过是农民革命的一种副力”(47)。为此,中央指示湖南省委在暴动中“应以农民军事力量最大的地方,并且是战争地势最便利的地方为出发点”(48)。中央也指示广东省委:“相信农民为暴动的主力,坚决的领导他们继续不断的暴动”,而对于南昌起义军余部,则“应积极拥护农民暴动,剩余之枪支尽数武装农民,不可靠之部队以农民改编”。(49)
秋收起义前,湖南省委也专门讨论过起义的动力问题。毛泽东坚持他在“八七”会议上的意见,认为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因为暴动目标是要夺取政权,而“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强调“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50)可见,毛泽东是坚决主张以正规军队为主要动力的。
但是毛泽东的意见在当时显然孤立。大多数地方党负责人更多附和中央以农民为暴动主力的意见。如湖北省委就认为,“暴动应当以农民群众做主力来领导,在暴动中来影响军队,利用军队是可以的,万不可以军队来做主力的”(51)。广东省委则要求“一切军事行动许听暴委或革命委员会之命令,军事同志只具参谋之资格。不可违背命令”(52),显然也没有把正规军事力量作为暴动的主动力。广东省委甚至强调“暴动必须是农民群众的大爆发,而不是少数农军或士兵的行动”(53)。
但是,无论是南昌起义还是秋收起义,实际上都是以正规军事力量作为主要动力得以发动的。广州起义则因为起事仓促、计划不周,而导致斗争动力的易手。“此次暴动省委原订计划,必须先发动群众的总罢工,然后举行暴动,就是要一群众为中心的暴动,后来以客观环境的逼迫,不得不提早暴动,而改变原定计划以军队为主力”(54)。这充分证明暴动终究是一项需要专门技能的军事活动。只有黄麻起义基本落实了中央和湖北省委以农民为暴动主力的初衷。但是即便如此,参加起义的农民事实上已经经过了一定程度的军事化动员。
2、正规军事力量的作用。像军队、警察这类暴力专家,“遵循自己的逻辑。他们通常从事剥削和机会累积,有时候牺牲自己普遍的雇主或支持者”(55),这在军阀混战的中国是司空见惯的政治规则。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在没有建立起自认为以工农运动为基础的革命军以前,始终并不绝对信任参与暴动的既有正规军事力量。但大革命时期的工农武装并不天然转化为熟练的暴力专家,起义中现成的正规军事力量即暴力专家也暂时难以达到共产党人理想的要求。所以在军事力量问题上,与暴动动力问题一样,呈现出历史现象的复杂性。
作为南昌起义军主力之一的第二十军,成分就十分复杂,“一、二两师的军官很多反动的。他们最不满意的就是第三师,因为第三师是共产党员在里边当师长,内里的军官也多半是CP分子,兵士也占四分之一,并且贺军长时常是夸奖第三师,抵触他们”(56)。二十军军阀习气浓重,“所幸其部下封建思想极浓厚,自师长以下莫不视贺氏为神人”(57),高度依赖贺龙个人的权威。起义军素质不高,“拉夫者有之,抢人鸡子者有之,而尤以二十军之甚”(58)。总之,南昌起义军虽然是纯粹的正规军事力量,主要军官拥有军长贺龙和师长周逸群这样坚定的革命者,但是尚未改造成为真正的人民革命军队,仍然还是“大半非同志领导,而无政治认识的军队”(59)。
南昌起义的经验使中共中央深刻认识到:“雇佣军队决不是革命的靠得住的工具”,因此党“应当想种种方法武装工农”,因为这是“造成新的革命军队之中心势力”(60)。中共中央领悟到:“现在我们在军队中的工作,应该是要做兵士的工作”。军队中的工作必须改变,因为如果“各样各色的坏分子都包括在内,绝不能实行土地革命”。正确的军队建设应该是“工农群众与兵士群众联合起来,要使敌人的枪杆子变成土地革命工农的枪杆子”。(61)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由他同时批评“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推断,(62)他所说的“军事”更接近正规军事力量。
与南昌起义相反,在广州起义中,在各部分武装力量中表现最好的还是正规军队。“教导团方面千多人,仅有百多个同志,动作起来都能领导一致的动作,而且都勇敢”(63)。问题的关键其实恰恰在于这“百多个同志”,体现了共产党的领导作用。
可见,上述暴动动力问题的关键,其实根本在于军事力量中无产阶级党性的体现,军事素质或正规化的水准并非决定性因素。
3、工农群众的军事化。和中央期待农民普遍参加暴动相反,南昌起义军并未得到工农群众的拥护,“一进广东界却使人大失所望……到了大埔已经有工农讨逆军的组织,并且准备暴动已经两三月之久,但是只有很弱的极幼稚的军事技术的布置,全未注意煽起群众的工作,更未注意群众的组织”。三河坝也“全无农会的组织”。汕头工人“表现地非常之弱”,甚至在起义军准备组织500名工人义勇队取代旧警察时,“经过三天的号召仅得七十余人,并且都不甚愿意,因为饷项睡食等等都不如意。可见群众的阶级觉悟非常之弱”。(64)在东江地区起义军吸收当地农民以做补充的计划也归于失败,因为“农民其意重在本乡中寻得土地,愿意从军者少”(65)。这说明土地革命必须首先激发起当地农民的政治兴趣和革命热情。南昌起义军显然还没有领悟到工农武装割据的真谛。
与此同时,在“八七”会议上,中央认真反思了过去对工农军事化工作的教训,坦陈:“中央始终没有认真想到武装工农的问题,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中央军委对此完全没有工作,没有提及一般共产党员的军事训练,这实是我党第一等重要的责任;没有提及有系统的聚集那零星散乱的工农武装队,使成为一有组织的坚固力量,以便做发展革命的真实的拥护者,没有想尽办法的去得武器,以武装工农”(66)。会议期间中央关于农村问题的总策略的指示,敦促“各地党部应当用种种方法使农民接受军事训练,获得武装”,号召“用种种方法夺取地主阶级和一切反革命派的武装,武装农民;勇敢的有训练的农协会员有组织的投到军队中接受军事训练并用种种方法时时进行破坏其组织夺取其武装的工作”,同时认可农民武装以如挨户团等“合法的名义存在”。(67)
湖南省委充分利用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成果,将之转化为工农武装,并且在秋收暴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省委要求各地党组织在“工农自卫军已不能公开存在”的情况下,以“编成合法的挨户团;次之则上山;再次之则将枪分散埋于土中”的方式保存工农武装,并“要用种种方法取得武装,并且秘密的从事武装训练;设法打入团防局,有组织的投入军队”(68)。任弼时建议“应扩大各地农民武装组织,加强武装技术与训练,有计划的解除乡村中团防的武装,捕杀土豪劣绅;扩大工人武装组织,加增武装技术和军事训练”(69)。湖南省委的军事工作分三方面进行:“一是对于已经露面之义勇队自卫军之类;一是尚在灰色或潜伏状态中的团防挨户团及掩埋之枪支之类;一是国民革命军中党的工作”(70)。湖南省委的军事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日后参加秋收起义的武装中,形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的平江工农武装就一度拥有江西省防军的灰色身份,形成第二团的安源工人武装也拥有矿警队的公开面目。
与农民运动既有武装的成功保存相反,在大革命中风光无限的湖南工人运动则惨遭新军阀摧残,被完全压制而难以形成军事化。湖南省委称:“他们知道我们在工农下层群众中还有点力量,故计划上规定不许组织各业工会,欲使我们现有的下层自然消散”(71)。
但事实证明,由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自然地转化为真正军事化的革命武装并非轻而易举,他们在秋收暴动中的表现仍然差强人意。如为配合秋收暴动而举行的长沙近郊农民暴动,只是“因图解决九峰的团防失败,农民争斗的勇气几乎消灭,号称近郊农民领袖的滕代远同志,在农民中亦拒绝其居住,长沙暴动的力量去了五分之三”(72)。暴动过程中平江农民武装的表现也是如此。在起义军攻打平江失利时,“农人知势不能抵抗,同时胆小,乃纷纷退却,所幸未伤一人。此等军队,未经训练,当然不听指挥,没有勇敢,不约而四散矣”(73)。在攻打萍乡县城时,以安源工人为基础组建的第二团,“军队中的成分充满了土匪,老兵作战极不勇敢,参加的工人梭镖队,反先进城,军队不仅不继进应援,反而开枪打前进的梭镖队”(74)。
黄麻起义前,黄安、麻城两县的农民已经初步实现了军事化动员。麻城乘马岗“有人民自卫军,有快枪七八十枝,一说百余枝,有几枝驳壳,能号召群众2万人,行动时能同指挥者1万人”。黄安七里坪“有群众二三万人,快枪四五百枝。杀了很多土劣,没收土劣之财产,即用以打梭镖。有同志戴季伦戴克敏及党校学生在那里指挥”(75)。黄安和麻城的农民不仅初步实现了军事化动员,而且在惨烈的斗争中日益提高了斗争技能。“他们不分昼夜的去提土豪劣绅,他们捉土豪劣绅不分大小,均是科罚烧房子分田。他们很勤快的侦探反动派,很敏捷的捉土豪劣绅,很勇敢的打土豪劣绅的‘红学’”,特别可贵的是他们已经树立起鲜明的阶级意识,“打破了极深的宗法观念,他们彼此称呼是同志”。(76)这些斗争“锻炼了原始的农民武装,涌现了许多有组织才能的干部,他为后来创立的工农革命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77)。
在这一过程中,群众大会这一经典斗争仪式,不仅是宣传党的政策的公开场合,也是鼓舞群众斗志,甚至是对工农实行军事化的重要手段。湖北省委指示黄安县委,“开各县农民代表大会,应不分界限,河南光山商城等各县农民代表亦须参加,并派代表到各处鼓动暴动,很快的要造成鄂东割据局面”(78)。
广州暴动作为一次纯粹的城市暴动,理所当然地试图发挥工人运动的政治潜力。在起义爆发后,苏联方面高度肯定广州起义的工人阶级性质,强调“这次起义与叶挺和贺龙领导的起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在这次起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不仅有军队和农民群众,而且还有工人群众”(79)。不过,在暴动前,广东省委对工人武装并没有绝对的信心。在关于暴动后各县市工作大纲中,广东省委提出在“解除一切反革命武装”的基础上,“工农普遍武装起来,并依军事编制组织之”。工农军一部分编为政治警察,其余改组为国防军,“成为真正工农革命军”,并特别强调“武装农民以贫农为中心”。(80)这表明,此时工人的地位并不突出。然而,广东省委在暴动前也曾经试图发掘工人政治示威这一经典斗争手法的潜力。如1927年11月18日,广州市委组织的工人示威,虽然“给工人群众有很大的影响,引起工人积极起来打工贼,进攻反动工会,并予张发奎黄琪翔以很大的打击”(81),但是轻易地被暴力弹压。显然这一斗争手法在大革命失败后难以有效复苏。
但是即便如此,广州起义仍然尽最大努力对工人做了军事化动员。然而遗憾的是,工人在起义中虽然付出极大牺牲,但是仍然暴露出军事化程度低下的弱点。暴动中“虽然有一两千赤卫队武装起来作战,但是数量上还是很少,组织力极弱,军事技术的训练尤其缺乏”。(82)军事训练不足严重影响了工人武装的战斗力:“赤卫队之最好者为农工纠察队分子,这部分赤卫队能有好的干部指导,与正式军队一样的有战斗力,至其余的赤卫队就差多了,来领枪的是非常踊跃,都是争先恐后的,但是有的能放枪,有的不能放枪,甚至有携长枪而带短枪子弹的,有带短枪而带长枪子弹的,有的携了枪便回家去的”,这是因为中国工人不像西方,平时有军事训练的机会。(83)在起义前负责对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做军事训练的徐向前也反映这支多为手工业工人的联队,“革命热情很高,但毫无军事素养,许多骨干连枪都没摸过”(84)。另外,工人武装因为事先缺乏编制计划,在起义中出现指挥无序的状态。“赤卫队在编制方面,以前是依工会而分的。……另一方面军队是依人数编的,工人却不懂这种方法……结果依人数编了。这种编法对工人来说是一个突然改变,使工人不习惯”。工人封闭的自我意识也说明他们并没有真正地具备觉悟的阶级意识。“因为工人不懂军事,所以特派军事同志当指挥,但是工人不相信别人只相信工人领袖”(85)。工会组织在整个起义过程中毫无作为。广州起义历时只有三天,还没有足够的时间通过赤色恐怖来摧毁旧秩序。但是在恽代英看来,工会作用的缺失才是革命骚乱不足的重要原因。他质问:“应当明白允许各工会有权捉拿枪毙他们所知道的反动派……应当明白允许各工会对于他们所需要的房屋或粮食用品,有权自由没收征发……应当明白允许各工会干涉商店,应当明白允许各工会向苏维埃政府领取枪支”(86)。
总之,尽管作为暴动主要动力的正规军事力量表现并不完美,但是为暴动后人民革命军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而工农武装力量虽然没有能够在暴动中实现主要动力的作用,但在经历革命洗礼后锻炼了军事技能,融入到创建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时代洪流中。
4、作为暴动标志性特征的“骚乱”。“骚乱”类似“机会主义的暴力”,“主要发生在现存政治控制的边缘地带,或者在权威监控的真空地带,或者在现存制度监督与控制的破裂点上”(87)。共产党人恰恰利用了这样的边缘地带、真空地带或破裂点,那就是国民党正规军事力量和乡村半军事化的土豪劣绅团防之间的接缝处。共产党人试图利用国民党正规军事力量未对团防援助到位之机,实现暴动夺取政权的目的。因此,共产党暴动领导人如此鼓励行动者在暴动中充分制造骚乱便不难理解。骚乱作为破坏旧秩序,并引起敌方混乱以便于暴动者夺取政权和扩大政治影响的手段,被起义领导者不断强调。暴动中的骚乱固然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破坏,但是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客观情势下,革命力量如果不能尽量扰乱反革命力量控制的社会秩序,并以此鼓舞群众斗志,就不可能顺利捣毁反革命的暴力机器,实现夺取政权的根本任务。
南昌起义爆发后,中央即指示湖南省委主要通过暴动响应南昌起义,“实行扰乱湘政府的金融,鼓动兵士闹饷要求发现洋,破坏水陆交通,捣毁城乡税收机关,炸毁军事机关”(88)。起义军南下后,中央批评南昌起义军“所到的地方,对于豪绅资产阶级所采取的策略,并不是猛力摧毁他们的组织和政权,都大半偏于犹豫妥协的策略,并未猛力歼灭土豪乡绅,并未完全解除他们的武装,摧毁他们的金融机关,摧毁他们的交通网络。不敢坚决的实行没收征发的政策,却用军阀筹款的老办法和他们和平磋商”(89)。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更是批评南昌起义军没有通过制造骚乱局面,搅乱敌方统治秩序,因而建议起义军在日后“要放胆去干,不应象以前太规矩,要平民式的干,不要有仁慈,打破好人的观念,对土豪应该乱杀,绝对不要恐怕冤枉了”。他甚至建议他们去做政治流寇,“不应象过去只注重掠夺政治经济的中心,他们每到一地,便要杀土豪劣绅,帮助农民起来便要组织工农政府,扩大宣传,我们不是希望一定要这个政权能够稳固多久”(90)。
中央在部署秋收暴动的过程中,不断指示各地党组织在暴动中,通过制造革命骚乱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如中央指示湖南省委,暴动之前,“在离城较远一点的乡村即应杀戮土豪劣绅反动的大地主,提高农民革命的热情”。暴动开始后,“首先即须征集所有的力量攻打某乡区的中心城市,杀戮政府的官吏”。暴动中“即须掘断铁路,破坏水陆交通,占领或破坏邮政机关,割断所有的电线,造成敌人的绝端恐慌的状态,然后才可便于暴动的发展”(91)。各地的革命暴动基本上贯彻了中央的意图。醴陵县委组织农民暴动配合秋收起义部队的行动,尽量制造暴动气氛,“西乡焚烧豪绅房屋一栋,杀豪绅二名……南乡烧豪绅房屋三栋,杀土豪三名、劣绅二名,罗团连长三名……二区焚屋一栋,杀一名。东二区一带围罗定驻军一排”(92)。长沙近郊农民举行暴动响应秋收起义,“分河西、河东两方进行”。河东方面“共解散团防局五处,杀土豪劣绅二三人”。河西方面,“解散团防局二处,没收厘金局一处,杀土豪劣绅五人”。(93)
湖北省委号召各地在秋收暴动中,应“建设各区集中指挥的机关,组织农民游击队,用造谣及流寇式的武装行动暗杀土豪劣绅,造成了乡间的大恐慌,以镇压土豪劣绅复起的凶焰,恢复农民斗争的勇气及组织”。鄂东、鄂南党组织要“集中武装力量,破坏水陆交通断绝军队运输及杂粮的供给,并扰乱其后方”。各地暴动要“煽动农民抗税抗捐,组织米粮燃料出境,拒绝使国库券及中央钞票,捣毁税收机关及交通机关,并没收其财产以引起广大农民群众对反动政府土豪劣绅剧烈冲突”(94)。省委指示鄂东党组织,“先派负责同志以革命委员会名义向各方活动,按照客观环境,如能实现最低目的时,即组织特务组于最短期间一路杀去,并散发口号;各地同志,就地在下层鼓动,以他们自己的力量,没收地主财产,接收乡村政权;客观条件成熟,即引起农民力量进攻县城夺取县政权”。可见,骚乱是暴动的必须步骤。省委认为骚乱是鼓舞群众斗争的最有效手段,“在各乡组织游击队,10人至多15人一组,出没无常杀土豪劣绅,烧地主的房子等。因为如此才能引起农民总的争斗的兴趣”。(95)省委对黄蕲区的指示也大略如此:“将忠实勇敢的同志组织农民游击队、暗杀队,大举骚动。每队由五六人至一二十人,有枪一二枝即可行动,出没无常的杀土豪劣绅大中地主并没收其财产,抗租抗税,尽量扰乱或破坏交通邮电税收等机关”(96)。
在湖北省委给黄安县委的指示中,重复着同样的意义:“不必用尽力量先攻黄安县城,而是反攻黄麻四乡的反动势力,发展四乡的农民暴动。一面组织小股游击队,到四乡去杀土劣,造成赤色恐怖,使军队不敢下乡;一面马上召集黄安麻城罗田商城各县农民代表大会,鼓动农民,并派人到各县发动暴动”(97)。黄麻起义后,为扩大暴动影响,黄安特委命令鄂东军南下发展。“特委命令南下各同志准备一个星期的工作以组织多少农民,杀多少土豪劣绅,烧多少土豪劣绅地主的房子,没收多少财产土地四项为核算标准,并且鼓励他们积极斗争,于最短期间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鄂东军南下后,“经桃花区至八里区烧了几家土劣的房子,并且提了一个大土劣家属男女老小七人,并没收了三四千块洋钱,当即回县城”。(98)革命暴动中的骚乱成为暴动发展不可缺少的环节。
鉴于南昌起义军沿途并无摧毁封建地主阶级在乡村中统治秩序的情况,广东省委要求在广东的暴动中,“工农革命军所到的地方,应有拼死绝不反顾的决心,尽死力发动农民武装起来争夺土地与政权,大杀土豪劣绅,务使其寸草不留,宁枉杀不姑纵”。党组织应鼓励农民群众的暴力行为,“工农如果发生无组织的焚烧抢劫杀戮,应以同情的态度引导其归于有组织的行为,务使其杀敌效果的英雄斗争为阶级斗争,决不能加以无理的制止或危害”(99)。只是在广州起义中,由于起事过于仓促,上述暴力行为并没有得到普遍的实施。
总之,“骚乱”的制造恰恰是革命暴动的标志性特征之一。过分强调暴动中“骚乱”现象的非理性,甚至简单定性为“左”倾盲动的表现,并非客观而科学的分析方法。
5、暴动的“斗争周期”。革命暴动作为社会运动,不可避免具有斗争周期。斗争周期的主要特点是:“集体行动倾向以发起者向无关群体和对手的扩散。无关群体会响应成功挑战的示范影响,或至少避免镇压;对手则会制造对抗运动”(100)。而社会运动进入遣散期的关键在于动员力度的减弱,“最简单的原因可能就是力量衰竭”(101)。在1927年至1928年革命暴动中,斗争周期因各地起义的具体进程而不同,但是它们不约而同地必然进入遣散期则是共性。因为随着革命激情在骚乱阶段的释放,暴动理所当然地要达到某种结果。而何时进入这种遣散期,则各有动因。
南昌起义进入斗争周期的遣散期,其实早由其南下重建广东根据地的战略所决定。起义前敌总指挥叶挺公开声明广东是起义的既定目标,因为“广东为总理四十余年从事革命的根据地,它的地理及社会较适合于革命的生存”(102)。这与起义仍然打着国民革命旗帜是一致的。南昌起义军真正进入遣散期,还在于进入东江地区后,并未能够如中央所期待的掀起广东革命的高潮。虽然“近之如梅县、兴宁、五华、高陂、澄海、潮阳、普宁、惠阳、海陆丰等县,远之如海南、西北江方面的农民暴动,以及潮汕的工人炸弹案破坏潮汕路等等,都是工农群众联合军队努力奋斗之表现。但因消息隔绝,我军行动迟缓,未能协同动作,影响于军事者不甚重大”。缺乏全局观和对广东局势过分乐观的预期,是起义进入遣散期的根本原因。(103)正如起义领导人之一朱德总结的:“党的军委当时也曾选派干部到黄埔军校学习,好些人成了红军的骨干。但这些同志,当时只有北伐的经验,缺乏游击战争的经验,不知道把军队在群众中扎根,不知道到处下蛋,壮大自己力量”(104)。但是,南昌起义在经历遣散期的洗礼后,最终完成了开辟土地革命新道路的历史使命。在南昌起义开始后中央致起义前委的信中指出:“南昌暴动,其主要意义,在广大的发动土地革命的争斗。因此,这一暴动,应当与中央决定之秋收暴动计划汇合为一贯的斗争”。(105)在中央看来,南昌起义只是革命高潮的新起点。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后在朱德领导下,与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开始了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征程,从而实现了中央的初衷。
而广州起义失败后,广东省委指示:“从广州退出之赤军和赤卫队须在花县清远英德等处帮助农民暴动造成一割据局面”(106)。历史发展也基本证实了上述设想。广州起义部队的余部一部分参加了东江苏维埃斗争,一部分与南昌起义朱德部队汇合。黄麻起义形成的鄂东革命武装,也成为日后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主力。
总之,作为社会运动的革命暴动,虽然经历了遣散期的挫折,但是不约而同走向了创建农村根据地、建立工农红军和实行土地革命的苏维埃运动。
综上所述,在1927年革命暴动中,共产党领导者通过放弃国民革命和国民党的政治招牌,树立中共土地革命的旗帜,成功地统一了工农士兵暴动者的政治认同,领导他们举行了一系列以土地革命为目的的革命暴动。在斗争手法的运用上,共产党人陷入了暴动动力究竟是依靠正规军事力量还是工农群众的争论之中。在暴动过程中,共产党人通过鼓励工农士兵起义者制造革命恐怖性质的骚乱,有效扰乱和摧毁了乡村豪绅的统治秩序,锻炼了他们的军事技能。由于起义各自的弱点,这些暴动不同程度地进入遣散期,但是不约而同走向了创建农村根据地、建立工农红军和实行土地革命的苏维埃运动。
注释:
①唯一对1927~1928年武装暴动做综合研究尝试者为黄琨:《革命与乡村:从暴动到乡村割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该书仍然在重复传统党史著作对革命暴动为“左”倾盲动错误表现的指责。特别是该书反复强调共产党方面力量的薄弱和国民党方面的压倒性镇压力量之间悬殊的对比,似乎革命暴动根本就是多余的无意义的政治行为。
②[美]道格·麦克亚当、西德尼·泰罗、查尔斯·蒂利:《斗争的动力》,李义中、屈平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59页。
③[美]查尔斯·蒂利、西德尼·泰罗:《抗争政治》,李义中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40页。
④[美]查尔斯·蒂利、西德尼·泰罗:《抗争政治》,李义中译,第192页。
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1927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29页。
⑥《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末记》(1928年6至7月),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56页。
⑦《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经过与教训》(1927年10月),《南昌起义》,第85页。
⑧《任弼时报告:关于秋收暴动的情况与计划》(1927年9月27日),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协作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4页。
⑨《中共湖南省委给润兄并转中央的信》(1927年7月23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32页。
⑩《秋收暴动之始末:潘心源向中共中央的报告》(1929年7月2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20页。
(11)《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湖北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1927年10月),红安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黄麻起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3页。
(12)《黄安县委关于黄麻暴动经过情形给中央的报告》(1927年12月14日),《黄麻起义》,第78页。
(13)《郑位三:红色的黄安》,《黄麻起义》,第135页。
(14)《中共广东省委通告:关于最近工作纲领》(192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广州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64页。
(15)《中共广东省委报告:关于张李之战及广州暴动之准备和策略》(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第114~115页。
(16)[美]道格·麦克亚当、西德尼·泰罗、查尔斯·蒂利:《斗争的动力》,李义中、屈平译,第71页。
(17)[美]查尔斯·蒂利:《集体暴力的政治》,谢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页。
(18)《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宣言》(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第20页。
(19)《张国焘报告》(1927年10月9日),《南昌起义》,第165页。
(20)《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报告》(1927年8月7日),《八七会议》,第54页。
(21)《中央常委代表瞿秋白的报告》(1927年8月7日),《八七会议》,第71页。
(22)《中共湖南省委目前工作的计划》(1927年7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27页。
(23)《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信》(1927年8月20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50页。
(24)《中共中央复湖南省委函》(1927年8月23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55页。
(25)《彭公达同志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1927年10月8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99页。
(26)《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1927年8月29日),《八七会议》,第150页。
(27)《中共广东省委通告:关于最近工作纲领》(1927年10月15日),《广州起义》,第66页。
(28)《贺龙告全体官兵书》(1927年8月),《南昌起义》,第36页。
(29)《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为叶贺失败事件》(1927年10月24日),《南昌起义》,第58页。
(30)《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末记》(1928年6至7月),《南昌起义》,第145页。
(31)《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1927年8月3日),《八七会议》,第103页。
(32)《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1927年8月11日),《八七会议》,第39页。
(33)《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的发言》(1927年8月7日),《八七会议》,第73页。
(34)《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关于农民斗争决议案的发言》(1927年8月7日),《八七会议》,第74页。
(35)《彭公达同志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1927年10月8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96页。
(36)《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信》(1927年8月20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51页。
(37)《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湖北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1927年10月),《黄麻起义》第29页。
(38)《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湖北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1927年10月),《黄麻起义》第57页。
(39)《暴动后各县市工作大纲》(1927年8月20日),《广州起义》,第32页。
(40)《中共中央致南方局并转广东省委信》(1927年9月9日),《广州起义》,第37页。
(41)《中共广东省委通告:关于组织暴动建立工农兵政权问题》(1927年11月25日),《广州起义》,第86页。
(42)《中央政治报告》(1927年9月15日),《南昌起义》,第50页。
(43)《中共中央最近政治状况报告》(1927年10月),《南昌起义》,第64页。
(44)《中共中央致南方局暨广东省委信》(1927年10月上旬),《南昌起义》,第51页。
(45)《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为叶贺失败事件》(1927年10月24日),《南昌起义》,第57~58页。
(46)《八七会议农民运动决议案》(1927年8月),《八七会议》,第40页。
(47)《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1927年8月29日),《八七会议》,第148页。
(48)《中共中央复湖南省委函》(1927年8月23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54页。
(49)《中共中央致南方局并转广东省委函:关于叶贺军队失败后广东的工作及善后工作》(1927年10月12日),《广州起义》,第60页。
(50)《彭公达同志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1927年10月8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97页。
(51)《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湖北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1927年10月),《黄麻起义》,第53页。
(52)《中共广东省委指示各区县目前应注意之十件事》(1927年9月22日),《广州起义》,第46页。
(53)《中共广东省委通告:关于组织暴动建立工农兵政权问题》(1927年11月25日),《广州起义》,第86页。
(54)《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广州暴动问题决议案》(1928年1月),《广州起义》,第249页。
(55)[美]查尔斯·蒂利:《集体暴力的政治》,谢岳译,第38页。
(56)《赵惆:关于南昌暴动中二十军的斗争情况报告》(1927年10月22日),《南昌起义》,第107页。
(57)《周逸群报告:关于南昌起义问题》(1927年10月30日),《南昌起义》,第120页。
(58)《张国焘报告》(1927年10月9日),《南昌起义》,第164页。
(59)《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末记》(1928年6至7月),《南昌起义》,第156页。
(60)《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1927年8月21日),《八七会议》,第135~136页。
(61)《中共中央政治报告》(1927年9月15日),《八七会议》,第157页。
(62)《毛泽东关于共产国际代表报告的发言》(1927年8月7日),《八七会议》,第58页。
(63)《聂荣臻对广州暴动的意见》(1927年12月15日),《广州起义》,第177页。
(64)《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经过与教训》(1927年10月),《南昌起义》,第93页。
(65)《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末记》(1928年6至7月),《南昌起义》,第155页。
(66)《八七会议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1927年8月),《八七会议》,第34页。
(67)《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1927年7月20日),《八七会议》,第87页。
(68)《中共湖南省委目前工作的计划》(1927年7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30页。
(69)《任弼时报告:关于秋收暴动的情况与计划》(1927年9月27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89~90页。
(70)《中共湖南省委给润兄并转中央的信》(1927年7月23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33页。
(71)《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1927年8月5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33页。
(72)《彭公达同志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1927年10月8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04页。
(73)《平江报告:暴动之经过与现状》(1927年9至10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16页。
(74)《中共湖南省安源市委工作报告》(1928年5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17~118页。
(75)《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湖北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1927年10月),《黄麻起义》,第56页。
(76)《黄安县委关于黄麻暴动经过情形给中央的报告》(1927年12月14日),《黄麻起义》,第80页。
(77)《郑位三:红色的黄安》,《黄麻起义》,第137页。
(78)《中共湖北特别委员会致黄安县委信》(二)(1927年12月12日),《黄麻起义》,第68页。
(79)《工农的广州》(苏联真理报1927年12月13日),《广州起义》,第142页。
(80)《暴动后各县市工作大纲》(1927年8月20日),《广州起义》,第32~33页。
(81)《广东政治报告(二)》(1927年12月5日),《广州起义》,第101页。
(82)《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广州暴动问题决议案》(1928年1月),《广州起义》,第250页。
(83)《聂荣臻对广州暴动的意见》(1927年12月15日),《广州起义》,第176页。
(84)《徐向前:参加广州起义》,《广州起义》,第417页。
(85)《陆定一向共青团中央报告广州暴动的经过及广州共产青年团在暴动中的工作》(1927年12月29日),《广州起义》,第187页。
(86)《恽代英:广州暴动与工会》,《广州起义》,第391页。
(87)[美]查尔斯·蒂利:《集体暴力的政治》,谢岳译,第134页。
(88)《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1927年8月5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45页。
(89)《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为叶贺失败事件》(1927年10月24日),《南昌起义》,第58页。
(90)《张太雷报告:八一事件之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1927年10月15日),《南昌起义》,第99页。
(91)《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1927年8月29日),《八七会议》,第151页。
(92)《邓乾元对于醴陵暴动经过的报告》(1927年9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91~92页。
(93)《彭公达同志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1927年10月8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04页。
(94)《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湖北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1927年10月),《黄麻起义》,第28~29页。
(95)《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湖北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1927年10月),《黄麻起义》,第42~43页。
(96)《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湖北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1927年10月),《黄麻起义》,第48页。
(97)《中共湖北省委致黄安县委的信(三)》(1927年12月25日),《黄麻起义》,第71页。
(98)《黄安县委关于黄麻暴动经过情形给中央的报告》(1927年12月14日),《黄麻起义》,第85页。
(99)《中共广东省委通告:关于最近工作纲领》(1927年10月15日),《广州起义》,第67页。
(100)[美]西德尼·泰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吴庆宏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94页。
(101)[美]西德尼·泰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吴庆宏译,第198页。
(102)《叶挺告第二方面军同志书》(1927年8月3日),《南昌起义》,第27页。
(103)《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末记》(1928年6至7月),《南昌起义》,第154页。
(104)《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1944年),《南昌起义》,第178页。
(105)《中共中央致前委信》(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第40页。
(106)《立三给中央的报告》(1927年12月28日),《广州起义》,第236页。
标签:土地革命论文; 南昌起义论文; 政治认同论文; 政治论文; 革命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地主阶级论文; 武装论文; 国民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