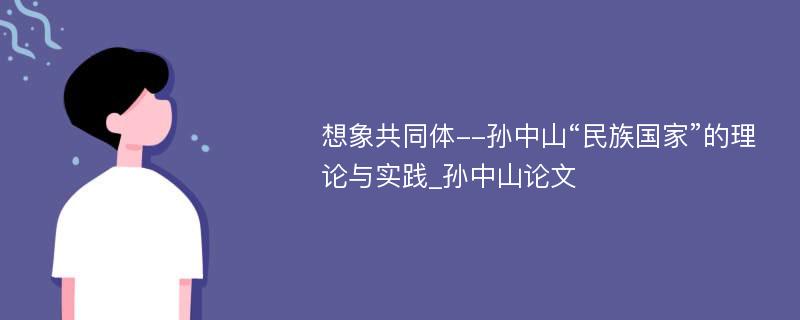
想象的共同体——孙中山的“民族国家”理论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同体论文,民族论文,理论论文,国家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世纪中叶,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迅猛扩张,中国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逼下被迫拉进了保国保种的现代化进程。在亡国灭种的忧患中,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纷纷把目光投向域外,并对欧洲后封建社会的行为制度和模式——“民族国家”产生了极大的认同感,“故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1]。“民族国家”作为近代民族主义的终极目标,成了近代中国一个主导话语和现代神话,成为“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的分界标。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把民族国家称为“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认为:“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是有限的,同时也是享有主权的共同体。”[2]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是现代性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一种新的话语形态和历史实践,“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它就像是一个家(roof),在它下面,可以遮风避雨;它又像是一个壁炉,在严寒的日子里,靠近它,可以暖和我们的手”[3](P2)。
但是,直到孙中山开始其“为众生谋幸福”的救国方案之前,清季的“民族国家”话语还只能说仅仅是一种“未来想象”和“公共话语”,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和可供操作的实践方案,是孙中山的出现,将“民族国家”从“未来想象”最终拉进了现代实践中。
一、从“排满”到“共和”:孙中山“民族国家”理论的历史建构
从19世纪末到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的民族国家思想经历了不断的演进过程。大致说来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创型期:兴中会成立之前 1893年冬,孙中山在广州约集郑士良等商讨革命事宜时,初步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华夏”的民族主义纲领。孙中山认为造成中国落后的原因“其咎在满人”,所以他把推翻满人政权放在革命的首位,并“徐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者”[4]。当时,孙中山并没有提出“建立民国”之说,其民族主义思想还没有冲破传统的华夏意识的束缚。
(二)构型期:兴中会时期 经过前期革命经验的总结,这时孙中山已把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结合起来,从而突破了传统的华夏民族意识的藩篱。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明确提出斗争宗旨:一,集会众以兴中;二,振兴中华;三,伸民志而扶国宗。[5]在近代中国第一次响亮地提出了“振兴中华”的著名口号。不久,香港兴中会成立,孙中山在章程中公开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加进入会誓词中。从此,孙中山就把他的反满主张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即创立合众政府的奋斗目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意识,这正是其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基本特色。
(三)初型期:同盟会时期 1905年8月,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又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革命宗旨定为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并在《〈民报〉发刊词》中归纳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这样,他就把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民族主义成为资产阶级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
(四)定型期:辛亥革命以后 早在著名的《〈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就明确地把“外邦逼之”和“异种残之”并列为民族主义“殆不可须臾缓”[6]的原因。至1924年,在著名的《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孙中山进一步指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氏族一律平等。”[7](P698)这样,由最初的“驱除鞑虏”,到“反满”,到只反对少数“害汉人的满州人”,并进而提出“五族共和”、“民族同化”的主张,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由原来的单纯“反封建”进而包含了“反帝”、“民族独立”的现代民族主义思想,也基本奠定了现代中国追求“民族国家”的实践方略,以至于后来毛泽东也宣布完全赞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解释。
二、“民族”与“国家”的纽结:对近代“民族国家”的叙述延伸
自“民族主义”一词最先在15世纪的德国出现,对它的界定和诠释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从词源学意义上来讲,民族国家就意味着一民族建一国家,民族与国家是重合的。中国近代以来关于“民族”的解释也多强调其人类学定义,忽略其政治学上的涵义,故无法把“民族”和“国家”、“民族主义”联系起来。如曰:“凡同种之人务独立自治,联合统一以组织一完全之国家是也。”[8]梁启超也说:“民族建国问题:一国之人,聚族而居,自立自治,不许他国若他族握其主权,并不许干涉其毫末之内治,侵夺其尺寸之土地,是本国人对于外国所争得之自由也。”[9]只管片面,且言说方式各异,但从这些言论中,仍然触及到了民族国家建构的两大课题:国家主权的建构和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这种理解非常有代表性。在《民族主义》第一讲中,孙中山说:“什么是民族主义呢?……我可以用一句简单话讲,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7](P725)在此,“国族”是“民族”和“国家”的合体,进一步深究,即是以单一民族为主体建一国家。为什么这么说呢,孙中山说:“就中国的民族说,总数是四万万人,当中参杂的不过是几百万蒙古人,百多万满洲人,几百万西藏人,百几十万回教之突厥人。外来的总数不过一千万人。所以就大多数说,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同一血统、同一语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习惯,完全是一个民族。”[7](P729-730)在此,孙中山的早期民族主义思想中很明显彰显出“大汉族主义”的倾向。这种思想对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在某种程度上有激发以“人种、生活方式、语言、宗教、风俗习惯”为连接方式的共同体形成的直接效应,但无疑也具有潜在的分裂中国的危险。
所幸的是,后来孙中山没有把民族主义和民族革命局限于种族复仇主义的范围内,而是把反满民族革命与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民权革命紧密结合起来,他充分认识到要与西方各民族竞争,中国必须统一各民族,建立一个强有力秩序。这一认识给民族主义赋予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容。在《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中,他反复强调:“民族主义,并非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更不是“要尽灭满洲民族”,“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谓民族之统一。”[7](P155)因此,“反满”斗争实质上是反对封建专制和民族压迫的斗争。这正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精华:建立一个汉族管理下的独立自治的民族共同体,继而在此共同体指引下,实现全民族心理、物质、社会等事关民权、民生的建国方略。1912年1月确定的中华民国国旗包括五种颜色,每种颜色代表着共和国内的一个主要民族,象征着孙中山民族话语的现代转型。
“民族国家”的形成,最主要的标志是国家“主权”概念的形成,即国家是由人民组成的社会,占有一定的领土,不受外来侵略,拥有一个有组织的政府。对此,孙中山通过“三民主义”的实践,《建国方略》、《民族主义》等多部篇章的阐释建构起其“国家主权”的理论框架:“有三大原则焉:一曰中华民族自主(即不受外族之统治);二曰政府受人人[民]之支配;三曰国家财富受人人[民]之支配。”[10]很明显,孙中山是以现代民族国家的要求来建构他的理论的,正如霍布斯鲍姆指出的:“只要‘国家’和‘民族’在思想意识上与已经建立组织、统治民间社会的国家和民族相吻合,那么国家方面的政治就是民族方面的政治。”[11]从这里可以看出,孙中山在世界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国家主权概念,给现代“民族”提供了外在的、可以检测的和可以衡量的标准,而“民族”也给国家主权的建构提供了内在的合法性根据。至此,孙中山将民族革命与求国家主权的独立结合在一起,构想出未来“共同体”——“民族国家”的模样:“总之,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达了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美的国家。”[7](P121)
三、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折中”:在双重文化认同中的理性抉择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讨论自我意识的产生时极为深刻地指出,与笛卡儿或费希特设想的相反,自我意识不是一个当下的“自觉”。“我思”是结果,而不是前提,一般的自我意识感在于一个先在的个别自我感,而个别自我感又在于我们与他人的交往。由这交往我们进入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他人。黑格尔用了主奴关系的寓言来说明这一点:主人和奴隶只有相互承认才能获得他们各自的自我认同。[12]同样,民族意识或民族认同也必须在与世界这个“他者”的交往中萌生,只有在认识了世界之后,中华民族才能真正拥有“自我”。由之便出现了20世纪初,中华民族国家建构中的一大难题:政治、文化认同的两难选择。
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与国家观的确立需要认同西方近代启蒙运动以来的政治文化,而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又需要借助传统文化,这二者之间存在相当的张力,似乎难以兼容。这种情况特别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随着国人的现代性追求愈益迫切,“全盘西化”论盛行,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矛盾日趋恶化。
对此,作为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理论的实践者之一,孙中山后期在各种场合多次宣讲关于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取舍问题。1921年他在广东省第五次教育大会发表演说,其中提到:“不知世界主义,我中国实不适用。因中国积弱,主权丧失已久,宜先求富强,使世界各强国皆不敢轻视中国,贱待汉族,方配提倡此主义,否则汉族神明裔胄之资格,必随世界主义埋没以去……故兄弟敢说中国欲倡世界主义,必先恢复主权与列强平等;欲求与列强平等,又不可不先整顿内治。”[13]时隔三年,1924年孙中山在讲《民族主义》第4讲时,再度详细阐述了对当时世界主义的批评,他说:“我们今日要把中国失去了的民族主义恢复起来,用此四万万人的力量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这才算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天职。……我们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之后,才配得来讲世界主义。”[14](P223-226)
以上两次演讲,孙中山主要是强调中国目前尚不宜提倡世界主义,只能宣扬民族主义。他认为世界主义不适用当时中国的重要原因,是中国早已进入世界主义,并且饱受其害。在近代世界,失去民族思想是导致中国遭受列强侵略的重要原因。而中国历来没有民族主义,只有天下大同思想,这是不少近代中国知识者的共识。如梁启超在1899年12月23日《清议报》第33册《饮冰室自由书·答客难》一文中道:“有世界主义,有国家主义,无义战非攻者,世界主义也;尚武敌忾者,国家主义也。世界主义属于理想,国家主义属于事实;世界主义属于将来,国家主义属于现在。今中国岌岌不可终日,非我辈谈将来道理想之时矣。”蔡元培也认为:“我们不谈世界主义,谈民族主义;民族达到了,才好谈世界主义。”[15](P494)这可以说与孙中山是不谋而合。
但是,孙中山虽然主张民族主义,却并不否认世界主义,他认为世界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而民族主义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如果不能用民族主义图生存,到了世界主义发达之后,便会被淘汰。因此,民族主义是眼前的及时雨,世界主义是前路的指明灯。其间的“折中”和连接线即是由本民族解放向世界各民族解放的进化:“中国四万万人是亚洲世界主义的基础,有了基础,然后才能扩充。所以我们以后要讲世界主义,一定要先讲民族主义,所谓欲平天下先治其国。把从前失去了的民族主义从新恢复起来,更要从而发扬光大之,然后再去谈世界主义,乃有实际。”[14](P231)
蔡元培后来评论三民主义的中庸之道、调和折衷时说:“持国家主义的,往往反对大同;持世界主义的,又往往蔑视国界,这是两端的见解;而孙氏的民族主义,既谋本民族的独立,又谋各民族的平等,是为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折中。”[15](P576)在孙中山的“折中”中,总是理智大于情感,反思多于宣泄,现实重于想象。
四、抑“个”重“群”:解民族国家的两副面孔
在民族国家的创建中,“个”与“群”的关系处理同样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现代民族国家“是一种有着明确讲解的政治体制,其中代表民族——人民(the nation-people)的主权国家不断扩展自己的角色和权力”[16](P6-7)。民族国家的建设具有两面性:民族国家的“群”——国家自由的一面和个人本位的“个”——个人自由的一面。在现代“国家”中,大多数情况下,“群”、“大众”、“人民”、“兄弟”、“同志”都可看作一种政治能指,直接指向作为“国家”主权合法化的首要地位。因为“民族主义也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来实现它的统一目标。民族主义需要的国家权力必须是没有竞争者的权力”[3](P112)。而“民族国家建设的自由的一面不同于它的民族主义一面。它是友好的、仁慈的;在大部分时间里,它都是充满着微笑,而且它的微笑是诱人的”[3](P113)。
“自由、平等、博爱”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最响亮的口号,也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的精髓。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孙中山,在发起和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过程中,也毅然举起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1906年,他在《军政府宣言》中称其革命主张“虽纬经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7](P107)。
孙中山所说的“自由”,包括了国家的自由和个人的自由。
所谓国家的自由,实质上是指国家的独立。孙中山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受列强的压迫,失去了国家的地位,不只是半殖民地,实在已成了次殖民地,要做各国的奴隶,国家很不自由。面对国家的不自由状况,孙中山满怀忧虑和愤懑,因而极力主张恢复和争取国家自由。早在1894年上书李鸿章时,孙中山就提出“国以民为本”。[4](P17)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他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又明确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并将“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17]写入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此,无论是“民”还是“国民”,其语义上的模糊和复数性,都直接指向“国家自由”、“民族自由”的事实。而且,孙中山终始都在为之奋斗,“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7](P128)孙中山在临终遗嘱中对自己所作的这一总结,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也足见他对国家自由的关注和重视。另一方面,孙中山在考察了西欧和满清个人权利的现状后,极力倡行民权主义。为了实现“主权在民”,孙中山提出人民应实际握有四大政治权力,即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也就是所谓“直接民权”。他对直接民权十分重视,将它看作实现“主权在民”的最好形式。通过对直接民权的规定,使人民不再是“徒有政治上主权之名,没有政治上主权之实”,而是“把政治上的主权,实在拿到人民手里来”[18]。与此同时,孙中山又指出,人民要享有一系列作为个人应该享有的自由权利,这些权利既不能被剥夺,也不能被让予。例如他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明确提出:“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14](P124)认为这是人民应该拥有的基本权利。
就国家自由与个人自由的关系而言,孙中山一方面认为,国家自由重于个人自由,个人自由必须服从国家自由,为了国家的自由,甚至要牺牲个人的自由。他说:“要把我们国家的自由恢复起来,就要集合自由成一个很坚固的团体。”[14](P283)这里所说的“集合自由”,就是要牺牲个人的自由,结成团体,去争取国家的自由。在孙中山看来,“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要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由”[14](P282),他极力反对绝对的个人自由,认为个人自由必须服从纪律,服从国家自由的许可;另一方面又往往把国家自由和个人自由对立起来。他认为,个人自由和国家自由是两个互不相容的东西,个人自由太多,势必影响国家自由的实现。他提出,自由“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14](P282)。
联想之前梁启超所说的“群治”,毛泽东所反对的“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的自由主义[19],近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似乎给我们展现了这样一种必然逻辑:在个体身份认同和国家身份认同的大合唱中,现代个人只能侧身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结构之中,个人无法脱离现代的社会结构和“游戏规则”而单独存在,在享受共同体为其提供的“确定性”和“安全感”的同时,感受被共同体“同质化”的压力:“同化的压力的目的是剥夺掉他者(the others)的他者性(otherness):使他们与其他国民的大部分难以区分开,完全消化他们并把他们的习性消融在一致的国家身份认同的复合体中。”[3](P114)
也许,这正是“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标签:孙中山论文; 想象的共同体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民族主义论文; 民族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