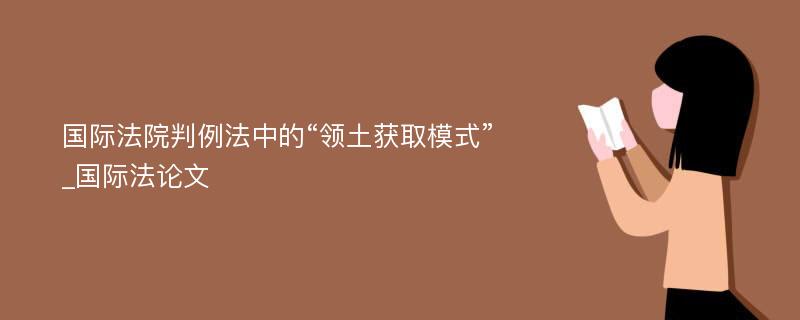
国际法院判例中的“领土取得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判例论文,领土论文,法院论文,模式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什么是国际法认可的有效取得领土的方式,如何对这些方式进行科学的分类,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从实践的角度看,国际社会并没有系统的涉及领土和边界争端的国际法编纂,①国际法院(下文简称法院)如何适用国际法来裁决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领土和边界争端,值得认真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法院的判决具有宣示和发展国际法的作用。中国与周边国家仍有一些待解决的领土和边界问题,认真研究法院的判例,了解法院的法律思维,把握其法律推理的过程,对于我们妥善处理相关问题也是有益的。本文以国际法院审理领土争端案件的判决书为主要材料,研究法院在判决中实际适用的“领土取得模式”。②本文无意系统地探讨领土取得理论,也无法对具体案件进行深入研究。因为“规制领土变更的法律规则和程序是整个国际法体系的核心”,③只有站在国际法的发展和进步的高度才能加以考察。每个案件都涉及大量复杂的历史、地理、条约等因素,用一篇论文的篇幅不可能对一系列的案例做深入的研究。研究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实际适用的“领土取得模式”,或许对于领土取得理论和法院案例的进一步研究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一、“领土取得模式”的概念与学说
“领土取得模式”是指国际法承认为有效的国家取得领土主权的途径与方式。在什么情况下,要具备哪些事实,国家要从事何种行为,才能确立对抗其他国家的对于某一领土的主权要求,这是“领土取得模式”这个概念所包含的问题。
“领土取得模式”与“title”这个术语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不同的语境下,“title”这个术语具有诸如权利、主权、权利根据、徽号、名号等不同的含义。詹宁斯认为,“title”的基本含义是:“法律承认其创设权利的既成事实”。④国际法院分庭在“边界争端”案中指出:“title”这一术语“同时包含两方面的意思:确立权利存在的任何证据;该项权利的实际渊源。”⑤布朗利认为,“title”是指“构成一项权利的原因或基础的所有事实、行为或情势。”在国际法上,其实质是“对抗其他国家的领土主权主张的有效性”。⑥“title”与“主权”概念也有密切的关系。“主权这个术语在国际法上既用来描述‘title’这个概念,也用来描述源于‘title’的法律权限。”⑦因而,“title”既可被用来指称主权,也可被用来指称作为主权主要表现的管辖权的渊源。所以,“title”这个术语的主要含义用中文表达就是“权利根据”。很多英文文献也经常用“roots of title”、⑧“roots of territorial title”⑨来明确表达“权利根据”的意思。中文文献中也有将“title”译成“徽号”的。如钟建闳译卢麟斯著《国际公法要略》称,“凡取得领土之徽号,非出于发现,乃出于占取。占取者兼并连居留之谓也。”⑩所谓“徽号”,就是“名号”、“头衔”的意思,是与国家的国际人格相关的。作为国际法上的“人”,国家有其“名号”。作为国际法上的“人”的“领土”,领土也有其“名号”。总之,在不同的语境下,“title”这个术语包含主权、权利、事实、行为、情势、徽号、名号等意思。
讨论国际法上领土取得的方式,实际上就是讨论需满足哪些事实国家才能取得领土的主权或命名权。所谓“领土取得模式”,实际上就是国际法认可的取得领土主权的“根据”。就国家间领土和边界争端问题的司法解决而言,“领土取得模式”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如果某些“事实、行为或情势”构成领土主权的原因或基础,对于这些“事实、行为或情势”进行科学的分类,我们就能对“领土取得模式”做出清楚的陈述。这无疑会便利国际司法机构准确地适用法律,从而有助于国际关系中领土争端的法律解决。许多学者进行过这方面的努力,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没有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领土取得模式”学说。
传统国际法上有所谓的“五种取得模式”学说。但布朗利指出:“许多教科书都会列举出包括有效先占、添附、割让、征服和时效在内的取得模式。这个目录不仅不精确,而且并不能充分地反映出法庭的工作方式。”(11)布朗利还认为,“取得模式”是“一个过时的反映一战以前学术倾向”的术语,“整个取得模式的概念在原理上是不正确的,只会使对于真实状况的理解更加困难。”(12)在“权利根据”这个标题下,布朗利列举了八个小标题试图描述领土取得的不同方式,即“根据条约的割让和转让”、“根据保持占有原则的国家权利继承”、“以国际社会名义进行的处置”、“废弃或放弃”、“裁决”、“有效先占”、“取得时效”、“默认和承认”。(13)布朗利本人承认,这种列举只是出于表达内容的方便而不是严格的学术分类。(14)芬威克指出,“法学家对于权利根据的数目和特征有着不同的看法,但在实践中,先占、添附、时效、自愿割让、征服、和平条约、同化等都是得到国家承认的权利根据。”(15)
关于“权利根据”的数目和名目还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必须看到,清楚地说明“领土取得模式”面临着许多困难。一个困难涉及领土取得的主体和客体特征,即领土的取得是现存国家对无主地的取得,还是现存国家之间进行的领土转移,或者是新国家的产生而取得的领土。对此,林德利做了这样的区分:主权国家之间的领土转移,以及主权国家取得无主地。现存主权国家之间的领土转移方式有:割让、征服、时效、国联委任统治制度下的放弃。主权国家也可以通过先占和添附取得无主地。(16)关于新国家的产生问题,詹宁斯认为,传统的五种模式学说描述的是“基于现存主体间财产转移的民法模式,而对于新国家产生这种情况没有说明。”(17)布朗利也认为有必要考虑新国家产生的情况,认为“权利的主要渊源事实上在于国家的独立及其作为独立国家被承认。”(18)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看,新国家的领土取得问题与继承独立时的领土状况有关,受权处理领土争端的法庭需根据新国家独立前殖民当局的法律法规等或前殖民宗主国之间做出的领土安排裁决争端。
“征服”是否仍是领土取得的模式之一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就当代国际法而言,根据《联合国宪章》等法律文件,“征服”显然不能被认为是合法的领土取得模式。但是这只能是就将来或《联合国宪章》等有关文件具有普遍约束力之后而言的,对于过去以此种方式取得(若某国如此声称)而现在存在争议的领土,征服能否被看成一种合法的模式,则是需要考虑的问题。此外,对于将来而言,如果征服、强制割让不能作为合法的领土取得模式,那么,“在不能有效地制裁武力的使用且某种形式的强制管辖争端体系出现之前,有必要考虑这么一种情况:某国非法使用武力成功地实现了对领土的占领且此种情势可能长期持续,此种情势能否被看成是合法的领土取得模式?”詹宁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际社会以承认或其他形式的认可表现出同意的意志,该国可以说是因巩固而取得了权利根据。”(19)这里,国际社会“行使了一种准立法的职能”。(20)这样,在“征服”退出之后,我们可能就要让“国际承认”加入进来。而“国际承认”作为一个可适用法律规则显然不能令人满意。(21)
也有学者试图将不同的模式与国际法基本原则联系起来。施瓦曾伯格认为:“规范领土取得的规则主要是那些支撑主权、承认、同意和善意等原则的规则。通过这些规则的相互作用,相对权利可转化为绝对权利。随着权利的绝对化,权利根据的多元化也更加明显。在一个典型的案例中,国际法院恰当地将这种时间演化中的渐进过程描述成历史权利的巩固。”(22)“权利的巩固通常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任何权利在初始阶段一定是相对的,权利人总是设法使之绝对化。随着权利的不断绝对化,权利的基础也越来越多重化。”(23)这样,不同的领土取得方式通过一个叫做“权利的巩固”的概念整合在一起。这种整合对于我们理解领土取得的国际公法特征(而不是私法特征),以及领土取得与国际法基本原则之间的关系显然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这样一来,我们很可能就整个失去了“领土取得模式”的概念,对于国际司法机构清晰地适用国际法规则裁决争端也不会有帮助。
那么,国际司法机构在实践中究竟是如何适用法律以裁决争端的,下文将以国际法院的审判实践为据进行讨论。
二、国际法院判例
本文以国际法院成立以来做过实质判决的全部或部分涉及领土和边界争端的案例为研究对象,一共为十四个。根据《国际法院规约》,或者,在当事方协议提交争端的场合,主要根据管辖权得以确立的特别协定,结合具体案情,法院考察过条约、地图、裁决、保有合法占有物原则(uti possidetis juris)(24)、主权行为、历史权利的巩固、时效等权利根据。
(一)条约
几乎所有的案件都涉及不同时期、具有不同法律地位的条约。若能确定在当事方之间存在解决领土问题的有效的国际条约,经确定条约用语的含义,法院即可据此条约裁决争端。
确定争端地区是否存在有效处置的国际条约是一件基础性的工作。在“关于利吉丹岛和西巴丹岛的主权归属案(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中,印尼的主权主张主要依据1891年6月20日为“确定婆罗洲上荷兰领地与英国保护国之间的边界”而缔结的《专约》第四条:“从东海岸上北纬四度十分点,边界线继续沿该纬度向东,穿越塞巴蒂克岛(the Island of Sebittik):该岛位于北纬四度十分以北的部分无保留地属于英国北婆罗公司,以南的部分属于荷兰。”(25)法院运用参考上下文、条约的目的和宗旨等解释方法,得出结论认为,条约确定了双方至塞巴蒂克岛最东端的边界,并未确定进一步向东延伸的分界线。法院还认为,起草条约的准备资料和当事双方嗣后的行为确认此结论。(26)因此,印尼的主张不能得到支持。
在“卡西基利/塞杜杜岛案(博茨瓦纳/纳米比亚)”中,根据当事双方《特别协定》第一条,法院被请求“根据1890年7月1日《英德协定》和国际法的规则与原则,确定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在卡西基利/塞杜杜岛附近的边界和该岛的法律地位。”(27)两国的主要分歧在于1890年《英德协定》第三条第二款“主河道中心线(the centre of the main channel)”的解释。法院考察了各种解释因素,确认“主河道中心线”为乔贝河的北河道且该河道的谷底线为两国的边界线。(28)
“某些边境土地的主权案”主要涉及1843年荷兰与比利时两国签署的边界专约的解释问题。在荷兰与比利时边境地区,属于比利时领土的巴埃勒—杜克区(Commune of Baerlie-Duc)的一些地块嵌在属于荷兰领土的巴埃勒—纳索区(Commune of Baarle-Nassau)当中。属于比利时的地块不仅孤悬于比利时主体领土之外,各个地块之间也互相脱节。从1836年起,两国边境地区的地方当局着手探讨确定确切的边界。1841年3月22日,两个地方当局之间签署了一个《区备忘录》(communal minute),其中规定:“第78至111号(含首尾两号)地块属于巴埃勒—纳索区”。(29)该文件是荷兰方面提出的,比利时对该文件的真实性未予质疑。在地方当局交涉的同时,根据1839年《伦敦条约》的规定,两国联合建立一个确定两国边界的“混合划界委员会”。1842年11月5日两国签署了一份《边界条约》(1843年2月5日生效)。该条约第14条规定:“涉及巴埃勒—纳索区(荷兰)和巴埃勒—杜克区(比利时)及其道路的边界现状应予维持。”1843年8月8日,两国签署的《边界专约》第一条规定,两国确定的边界由一个“说明性记录”(descriptive minute)加以确定;第三条规定该说明性记录构成条约的一部分。(30)而“说明性记录”的第90条第二部分规定:“第78至90号(含首尾两号)地块属于巴埃勒—纳索区。第91和92号地块属于巴埃勒—杜克区。第93至111号(含)地块属于巴埃勒—纳索区。”(31)这里的91和92号地块就是两国争端的标的物。
比利时认为,根据1843年的《边界专约》及“说明性记录”的规定,所涉争端地块的主权属于比利时。1842年《边界条约》中“边界现状应予维持”中的“现状”就是“说明性记录”所规定的对象。荷兰则认为,1843年《边界专约》的条款只规定应维持现状却并未确定何为现状,因此,应根据1841年的《区备忘录》来确定现状为何,据此,91和92号地块的主权应属荷兰。
法院要处理的核心问题是,1843年《边界专约》及“说明性记录”是否有效地确定了该争端地块的主权?法院经过对案情的分析得出结论:1843年《边界专约》有意图而且确实确定了两国间争端地块的主权归属。根据专约的条款,本案所涉争端地块的主权应属比利时。实际上,法院接受了比利时对“现状”一词的解释。
在“领土争端案(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乍得)”中,乍得主张,1955年8月10日《法兰西共和国与利比亚联合王国友好睦邻条约》确定了利比亚与乍得两国的边界线。(32)利比亚并不否认该条约的有效性。(33)利比亚则提出了历史继承权利等主张。
法院认为,为确定两国间是否存在条约边界,需要考察“1955年条约”第三条以及该条所引述的附件。(34)该条规定:“缔约双方承认: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的领土为一方,利比亚领土为另一方,双方的边界源自利比亚联合王国成立时有效的国际文件,这些文件的目录附在换文中(附件Ⅰ)”。(35)附件Ⅰ列举了六份文件。(36)由于附件Ⅰ所列举的部分文件在利比亚独立时已不再有效,利比亚认为该条款并未有效地确定两国的边界。法院则认为,条约的解释应考虑条约用语的通常含义、条约的目的和宗旨、有效性原则等。通过对“承认”、“边界”、“有效的”等用语的解释,法院确认:“1955年条约”“构成双方确定其边界的协定”。(37)根据“1955年条约”第三条以及该条所引述的附件,法院确定了两国间边界线走向。(38)
关于“1955年条约”的地位,法院表示,除非经双方同意,边界应保持稳定,即使“1955年条约”失效,该条约中有关边界的规定仍继续有效,边界规定“具有自己的、独立于1955年条约命运的生命”。(39)因此,在进一步确认当事方嗣后并无新的领土安排之后,对于双方在诉讼中提出的其他问题,如历史继承、保持占有原则的适用性、占有的有效性、势力范围、腹地学说、时际法规则等,法院认为无需考虑,因为“1955年条约完全确定了利比亚与乍得之间的边界”。(40)
(二)地图
法院对“柏威夏寺案”的裁决引起很多争议,法院裁决的确切根据并不是很清晰。案情大致如下:1959年10月6日,柬埔寨向法院提交了请求书,就柏威夏寺主权归属问题对泰国提起诉讼。泰国对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反对,法院于1961年5月26日判决法院对该案有管辖权。争端双方一致认为,争端源于1904-1908年间法国(作为当时柬埔寨的保护国)与暹罗间进行的边界解决,即柏威夏寺的主权归属取决于1904年2月13日的边界条约以及该日期之后的事件。(41)1904年2月13日条约的第一条对暹罗与柬埔寨边界的总体走向做出了原则规定。关于争端所涉的扁担山脉地区,该条规定,两国的边界为“森河和湄公河盆地与蒙河盆地之间的分水岭”。第二条规定成立一个“混合委员会”完成划界工作。(42)根据该条约组成的“混合划界委员会”于1905年1月举行了第一次会议,1907年1月19日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43)“混合划界委员会”对于扁担山脉地区划定了什么样的边界,却没有会议记录可以查询。(44)法国官方安排了四名官员从事地图的制作和出版工作,其中三位是“混合划界委员会”成员。1907年秋制图工作完成,法国一家出版公司印刷出版了地图。(45)
柬埔寨认为,地图是以“混合划界委员会”的名义并代表该委员会所制作和出版的。根据该地图所标明的边界线,柏威夏寺位于柬埔寨领土范围内,因此,柬埔寨对柏威夏寺拥有主权。泰国则认为,第一,地图并非“混合划界委员会”的工作成果,不具有约束力;第二,地图存在实质性错误,地图所示界线并非条约规定的分水岭,“混合划界委员会”无权做此更正;第三,泰国从未接受地图所示涉及柏威夏寺地区的界线;第四,如果说泰国接受了该地图,那是由于泰国错误地相信地图所示的界线与条约规定的分水岭一致。(46)
法院面对的问题:第一,地图是否具有约束力;第二,地图是否被泰国接受;第三,地图的“错误”是否导致地图无效;第四,即使地图被泰国接受,且不因其“错误”而无效,但若地图所示界线确实与条约规定的分水岭不一致,应如何定夺。
关于地图是否有约束力的问题,法院认为,没有证据表明,地图所示界线是根据“混合划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因而在地图出版之时对于双方不具有约束力。但问题的关键是:当事方是否接受了该地图以及地图所标明的边界线,从而赋予地图以约束力。“即使‘混合委员会’并未批准和接受扁担山脉东段的划界,两国政府也可以利用‘混合委员会’技术官员的工作成果而接受对该地区的划界”。(47)法院对有关事实审查后认为,泰国在1908-1909年间确实将该地图作为划界工作的成果接受了。(48)泰国主张,泰国从未接受该地图线,理由是,泰国对该地区一直行使着主权权力。法院认为,泰国所列举的行为都属于地方当局的行为,不具有改变中央机关态度的作用。(49)1930年,一位泰国亲王访问柏威夏寺,受到柬埔寨法国殖民当局的正式接待,表明泰国事实上承认了柬埔寨对于该地区的主权。(50)法院还认为,即使对于当时是否接受了该地图存有疑问,根据嗣后的事件和泰国的行为,泰国也不得主张其并未接受。(51)
关于地图的“错误”是否导致地图无效的问题,有两个层面。第一,“错误”是否导致泰国一方“接受”或“同意”的无效;第二,“错误”是否导致地图作为边界文件无效。关于第一个层面,法院认为,如果“错误”是由自己的行为造成的,或情况足以让自己知道出现错误的可能性,而未采取措施加以防范和检查,这种“错误”并不导致接受或同意无效。关于第二个层面,法院认为,条约中使用的“分水岭”,只是客观地描述边界的明显而便利的方式,没有理由认为当事方赋予“分水岭”以特别重要的意义。当事方的宗旨在于寻求边界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接受地图线符合条约的宗旨。即使地图线与条约所说的分水岭不一致,只要泰国接受了地图线,该地图线就具有优越于条约的地位。(52)实际上,法院的判决书并未处理地图线与分水岭是否一致的问题。顾维钧法官在异议意见中主张,应派独立机构实地调查分水岭线,看来该主张未得多数法官认同。(53)
法院认定,泰国接受了地图线作为两国边界线,泰国不得反悔,即使地图线与条约规定不符也不影响地图和地图线的效力,进而做出了有利于柬埔寨的判决。
在解决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间关于白礁岛的争端的过程中,法院认为,马来亚和马来西亚在1962年至1975年间出版的六份地图“可视为确认马来西亚认为白礁岛处于新加坡的主权之下。”(54)尽管地图在该案中并不具有独立的权利根据的地位,但对于法院确定马来西亚的官方意图显然有重要影响。(55)
(三)裁决
在“西班牙国王1906年12月23日做出的仲裁裁决案”中,法院着重分析了西班牙国王所做仲裁的有效性。经过对有关证据的分析,法院指出:“通过明示的声明和行为,尼加拉瓜承认仲裁为有效,尼加拉瓜不可否认这种承认或质疑裁决的有效性。”(56)实际上,法院认为,仲裁的有效性并不依赖于当事方的承认:“在法院看来,即使尼加拉瓜没有做出重复承认的行为——法院已断定存在这些行为且这些行为使得尼加拉瓜不得依赖于无效性的控诉,即使控诉在适当的时间提出过——仲裁裁决也应该被承认为有效。”(57)
法院明确界定,法院在该案中的职能是确定该仲裁是否有效,而不是宣布该仲裁的对错。(58)毫无疑问,有效的国际仲裁具有“已判事项”的地位。甚至不符合“国际仲裁”定义的政治裁决也可具有决定案情的作用。
在卡塔尔和巴林之间涉及海瓦尔群岛(the Hawar Islands)的争端中,法院指出,双方的争端涉及四个法律问题,包括:英国在1939年所做裁决的性质与有效性;原始权利的存在;有效行为;保持占有原则的适用性。(59)
法院首先考察第一个问题。1939年7月11日,英国常驻海湾政治代表代表英国政府正式通知卡塔尔和巴林两国统治者:英国政府裁定,海瓦尔群岛属于巴林而非卡塔尔。(60)巴林据此主张主权。巴林认为,1939年英国政府的裁决应被认为是仲裁裁决,根据“已判事项不重开”原则,国际法院无权审查另一个法庭的裁决。(61)法院并不认为1939年英国政府的裁决具有国际仲裁裁决的性质和地位,同时,英国政府的裁决也并非没有法律效力。(62)通过对有关事实的考察,法院认定:“巴林和卡塔尔同意英国政府解决双方涉及海瓦尔群岛的争端。因而,1939年的裁决应被视为自始即对两国有约束力的裁决,而且,自1971年两国不再接受英国保护之后,该裁决仍有约束力。”(63)法院据此裁决裁定海瓦尔群岛的主权属于巴林,(64)对于本案涉及的其他法律问题,法院认为无需考虑。(65)
上述两个判例清楚显示,国际法院视“裁决”为有效的权利根据。
(四)“保有合法占有物”原则
在“边界争端案(布基纳法索/马里共和国)”中,国际法院分庭对“保有合法占有物”原则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分庭指出:该原则的“实质是要确保尊重取得独立时的领土边界。这种边界原来只不过是同属于一个主权之下的不同行政区或殖民地之间的划界,通过适用‘保有合法占有物’原则,这种行政边界转化为充分意义上的国际边界。”(66)分庭还说,该原则“不仅仅是属于一个特别的国际法体系的特殊规则,而是一个一般原则,逻辑上与任何地方发生的取得独立的现象相关联。”(67)
在新独立国家间没有领土协定的情况下,要确定独立时的领土状况,只能根据殖民时期殖民当局确定行政分界的有效法律(在新独立国家独立前同属于一个宗主国的情况下)或不同殖民宗主国之间的有效条约。在很多情况下,由于无法通过考察殖民时期有效的法律文件确定殖民时期的划界,法院只能求助于考察殖民时期的有效行为,即殖民地“行政当局的行为,作为殖民时期对某地区有效地行使领土管辖的证据。”(68)在“边界争端案(贝宁/尼日尔)”中,“当事双方都未能成功地提供基于殖民时期法规和行政文件的权利根据”,法院转而考察殖民时期有关地方当局的“有效行为”即行政行为。(69)法院分庭正是根据这些行为认定,两国独立时在尼日尔河地区的边界线是该河的主航道。(70)
在“陆地、岛屿和海上边界争端案(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参加诉讼)”中,关于几个有争议岛屿的主权,双方都主张权利根据是“保有合法占有物”原则。(71)稍有不同的是,洪都拉斯主张,保持占有是唯一可以适用的法律。而萨尔瓦多主张,在适用保持占有原则的同时,也可以考虑后殖民时期作为主权基础的有效占有的事实,后者不仅确认而且强化了自己的权利。(72)分庭认为,“确定岛屿主权的起点毫无疑问是1821年的法律占有情况”。(73)但是,“就这些偏远、人口稀少、经济意义不大的地区的归属问题而言,殖民时期法律很可能不能给出清晰、确定的回答。因此,考察独立之后一段时间里新国家针对这些岛屿的行为就是适当的。那个时候提出的要求,对于要求的反应或无反应,有助于显示当时对1821年法律占有状况或当时的状况应该为何的看法”。(74)经过考察双方提出的证据,分庭认为,双方提出的涉及殖民时期的法律和行政行为方面的证据“零散而且模糊”,无法据此做出裁决,只有考察独立后双方的行为。(75)
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案中,有关“有效占有和控制”的证据、“主权的显示或行使”的证据,以及另一方对此种占有或主权行使的默认,被视为争端当事国有权继承西班牙对于所涉岛屿主权的证据。(76)
在“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加勒比海领土与海洋争端案(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中,法院对于“后殖民时期有效行为”的处理手法有所不同。在该案中,尼加拉瓜主张,所涉争端的浅滩在两国独立时没有归属,因而不可能确证1821年时这些浅滩的合法状况,应寻找其他根据。根据邻接原则,尼加拉瓜拥有原始权利。(77)洪都拉斯主张,基于“保有合法占有物”原则,洪都拉斯拥有这些浅滩的原始权利,其“有效行为”确认了这种权利。洪都拉斯还主张,如果法院认定两国都不拥有基于“保有合法占有物”原则的主权,洪都拉斯方面的“有效行为”可以作为更好的权利主张根据。(78)法院认为,“如果没有基于‘保有合法占有物’原则的权利根据,法院将寻找基于后殖民时期有效行为的替代权利根据。”(79)该案判决中,这些“后殖民时期有效行为”不是作为独立时领土状况的证明或延续,而是作为独立起作用的根据,并以此为据判定洪都拉斯享有争端浅滩的主权。
(五)主权行为
几乎所有的案件都涉及当事方所主张的主权行为的评估问题。主权行为在不同的情况下具有不同的作用。从法院的判例来看,法院判决大体上遵循这样的模式:若能确定有效的权利根据,除非得到权利所有人的认可,主权行为不能对抗确定的权利根据;若能确定主权行为得到权利所有人许可,如接受、默认、承认等,法院根据具体案情,确定当事方之间是否达成了事实上的协定;若无法确定有效的权利根据,也缺乏明确的许可证据,法院则需考虑,某一当事方是否因更多的主权显示而拥有更好的权利根据。
在“某些边境土地的主权案”中,针对荷兰提出的“主权行为显示确立的主权”的观点,在法院已确定比利时享有条约权利的前提下,法院指出:除非能证明比利时自1843年以来一直未行使权利或比利时1843年以来默认了荷兰所声称的主权行为,否则不能认为荷兰因行使主权行为而取得了主权。(80)法院分析双方提交的证据后认为,比利时自1843年以来确立的主权并未消失。(81)法院以十比四的票数,做出了支持比利时主权主张的裁决。
在“喀麦隆和尼日利亚间陆地和海洋边界案(喀麦隆诉尼日利亚:赤道几内亚介入)”中,法院确定:“在1931年之前,英国和法国确实划定并同意了乍得湖地区的边界”。(82)针对尼方提出的“有效统治”行为,法院指出,“某些行为——公共卫生和教育机构的组织、司法——可被视作主权行为。法院需指出的是,由于喀麦隆早已拥有该地区的主权,法律检验的关键点是喀麦隆是否默认了主权的转移。”(83)法院对有关事实考察后认为,“喀麦隆并未默认而放弃其主权。因而,尼日利亚的有效统治行为在法院看来只能是不合法的行为,权利的所有者应该占先”。(84)
在“白礁岛、中岩礁和南礁的主权归属案(新加坡/马来西亚)”中,法院确定,柔佛苏丹对双方争执的白礁岛在1844年之前拥有主权。但是,法院需要确定关键日期(本案中法院确定为1980年)白礁岛的归属情况,也就是说,在1980年之前的一百多年间,白礁岛的主权是否发生了转移。法院宣称:“主权转移可由两国以协议进行……协议可以是以条约形式出现的,也可以是默示的、以两国的行为表现出来的。国际法并未就此规定具体的形式,而是强调当事方的意图。”“在某些情况下,拥有主权的一方对另一方的主权行为或领土主权显示的明确宣示未做反应,领土主权也可能发生转移……拥有主权的一方如对另一方的显示领土主权的明确宣示不能接受,就应该做出反应。未做出反应可等同于默认。默认,即隐含的承认,体现为被另一方理解为同意的单方面行为。也就是说,如果有必要对另一方的行为做出反应而未做出反应,那么,沉默也是一种表态。”(85)法院根据双方的行为确认,双方对白礁岛的法律地位逐渐形成了一致的意见,并据此判定,至1980年时,白礁岛的主权属于新加坡。(86)
在判决印尼与马来西亚关于利吉丹和西巴丹两岛的争端中,法院在无法确定条约和继承权利的情况下,考察了双方提供的主权行为证据。(87)“法院注意到,马方所依赖的行为——包括以自己名义从事的和英国从事的——数量并不太多,但具有多元化的特征,包括立法、行政和准司法行为。其涉及的时间很长,在对更大范围的岛屿实施管理的背景下,显示出针对该两岛行使国家职能的意图。法院也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当这些行为实施时,无论是印尼还是其被继承国荷兰,都未表示异议或抗议。在1962年和1963年,英国北婆罗洲当局在这两个岛上建造灯塔,即使印尼认为其目的是保障航海安全(在北婆罗洲之外水域,灯塔对于航海安全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如果认为该两岛是自己的领土,这也是不寻常的行为,印尼应该提醒对方说建造灯塔的地点是印尼的领土,但印尼没有行动。”(88)马来西亚的主权行为和印尼的不作为相互作用决定了案件的判决结果。
在“明基埃和埃克荷斯群岛案”判决中,经考察有关条约和文件,法院不能确定存在双方主张的古老权利或原始权利,“法院的意见是,具有决定性重要性的,不是源于中世纪事件的间接的推测,而是与占有明基埃和埃克荷斯群岛有关的直接证据。”(89)通过对双方提供的针对该两群岛行使的主权行为的证据进行考察,法院一致裁定:在可以取得的范围内,英国对这两个群岛拥有主权。(90)
(六)历史权利的巩固
在“喀麦隆和尼日利亚间陆地和海洋边界案(喀麦隆诉尼日利亚:赤道几内亚介入)”中,尼日利亚对乍得湖地区的一些村庄提出主权主张,其根据之一是“尼日利亚和尼日利亚国民的长期占领构成历史权利的巩固。”(91)尼日利亚提出,该国国民长期在该地定居,传统首领行使了权力,该地区与尼日利亚有历史联系,其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和平地行使了行政管理,喀麦隆默认了尼日利亚对争议地区的和平的主权行使。(92)针对尼方提出的事实,法院认为,乍得湖地区的边界早已经由有关条约划定,尼日利亚对于主权属于他国的地区行使统治权力的行为,这些行为“必须作为违法行为(as acts contra legem)评估其法律后果”。(93)
关于“历史权利的巩固”,法院指出:“历史巩固理论极富争议性,它不能取代国际法上已确立的权利取得模式,这些模式考虑许多其他重要的事实和法律变量。‘渔业权’案判决中提到的‘历史巩固’是与领海的外部界线相关的,不能据此认为对于陆地的占领可优先于确定的条约权利。而且,尼日利亚所列举的与乍得湖地区村庄有关的事实和情形只持续大约二十年的时间,即使按其所依赖的理论来说,也是太短了。尼日利亚关于此问题的论点不能得到支持。”(94)
对于尼日利亚以“历史巩固”作为对巴卡西半岛地区主权主张的根据,法院亦予拒绝。(95)
(七)时效
在“卡西基利/塞杜杜岛案(博茨瓦纳诉纳米比亚)”中,纳米比亚主张,如果不能根据1890年条约取得该岛的主权,那么,“通过对该岛持续的、排他性的占领和使用,从本世纪初以来对该岛主权管辖权的行使,以及贝专纳兰(Bechuanaland)和博茨瓦纳统治机关充分的知晓、接受和默认,纳米比亚对该岛拥有时效的权利。”(96)法院认定,“纳米比亚未能确切地证明:纳米比亚或其前任当局针对该岛实施了纳米比亚提出的可证明时效权利存在的国家权力行为”,(97)因而不支持其时效主张。
但是,时效是否构成领土取得模式之一,法院并未做出清晰的阐述。一方面,法院声称:“就本案而言,法院并不关心取得时效在国际法上的地位,也不关心时效取得领土主权应满足哪些条件”;(98)另一方面,法院又说:“在法院看来,《特别协定》中提到的‘国际法规则和原则’,不仅授权法院根据这些规则和原则来解释《1890年条约》,还授权法院独立地适用那些规则和原则。因此,法院认为,《特别协定》并不阻止法院对纳米比亚提出的有关时效的论点进行审查。”(99)这里,法院显然把“时效取得”理解为国际法规则和原则的一部分。不清楚的是,如果法院据以确立管辖权的《特别协定》只授权法院根据特定的条约而不泛泛地授权法院依据国际法规则和原则进行判决,法院是否可以对“时效取得”的论点进行考察。
(八)非法使用武力
不得非法使用武力取得领土,应已具有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地位。对于过去以非法使用武力(如果非法性质可以确定的话)取得的领土,今天是否可认为有效,则是一个问题。
在涉及祖巴拉岛的争端中(“卡塔尔和巴林之间海洋划界和领土问题案”),巴林主张,1783-1937年间,巴林对该岛拥有充分的得到国际承认的主权(基于有效占领;当地居民对巴林统治者的效忠;英国对巴林主权的承认等事实)。巴林声称,在1937年,卡塔尔当局使用武力将忠于巴林且作为巴林统治者在祖巴拉的权力代表机构逐出该岛,这是非法使用武力的“侵略”行为。根据国际法,即使卡塔尔此后事实上控制着该岛,这种事实上的占领也不能构成合法的权利根据。(100)卡塔尔则主张,自1868年之后,巴林在该地区无任何官方行为,卡塔尔对该地行使了主权行为。巴林所主张的权利无论如何只是属人的而非主权的权利。(101)卡塔尔1937年的军事行动是在本国领土上针对部分异议分子的控制行为,得到英国的认可。(102)
法院根据1868年9月6日缔结的哈里发酋长(Ali Bin Khalifah)与英国常驻海湾政治代表之间的协定的条文认为,英国并不容忍巴林以海上军事力量支持其对祖巴拉的主权主张的做法。(103)1868年后,巴林新的统治者从未处于对该地直接行使权力的地位。巴林与该地某些部落的关系只是属人的效忠联系而非主权行使。(104)法院据此指出:“在1868年以后的时期中,卡塔尔酋长对祖巴拉的领土权力逐渐巩固;1913年英国与奥斯曼《关于波斯湾和周围领土的公约》认可了卡塔尔酋长对祖巴拉的领土权利;这种权利在1937年决定性地巩固了。卡塔尔酋长在祖巴拉地区的行动是在本国领土上行使权力,而非巴林所声称的非法对巴林使用武力。”(105)据此,法院以全体一致裁定卡塔尔对该地拥有主权。(106)
由于本案中法院并未认定巴林所指控的“侵略”性质,所以未就非法使用武力的法律后果进行评估。在法院审理的所有案件中,没有一个当事国以“征服”或“有效使用武力占领”作为主权主张的根据。“征服”是否构成历史上一种有效的领土取得模式以及今天是否应予承认,无法从法院的判例中得到答案。从国家不愿以此为据提出主权主张的表现似乎可以看出,“征服”不应构成有效的领土取得模式。
三、结论
在本文所研究的提交国际法院审理的争端案件中,当事方都不认为所涉争议的领土属于无主地,(107)所以,法院未曾就“无主地”地位及其相关的“先占”模式做出过裁决。由于少有当事方以“时效”作为取得领土的根据,从现有的判例中,对于国际法院是否以“时效”为领土取得模式之一,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由于从未有当事方以“征服”作为权利根据,似乎可以认为,即使在非法使用武力取得领土不得认为有效这一规则具有习惯国际法地位之前,“征服”也不应成为有效取得领土的方式。法院从未以“历史权利的巩固”作为判决的依据。“历史权利的巩固”可否成为领土取得模式之一,法院显然采取了保留的态度。在国际法院解决领土和边界争端的司法实践中,根据具体的案情,作为独立的据以判决领土主权归属的权利根据,法院实际适用的模式有:条约、地图、裁决、保有合法占有物原则、主权行为。
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五十九条,法院的判决仅对案件当事方有约束力。尽管如此,作为联合国主要司法机构,法院承担着“陈述和重述法律”的职能。(108)法院也经常援引以前的判词作为判决的支撑。所以,研究法院的判例,对于我们把握领土取得国际法的内容无疑是有价值的。另一方面,判例研究不能代替理论探索。国际法院只能适用“实然法”而不能宣示“应然法”,只能裁决依法所提交的争端而不具有普遍的强制管辖权,因而,国际法院判例所涉及的领土取得规则最多也只是领土取得国际法的一部分。领土的稳定与变更事关国际关系的稳定与发展,从国际法的发展和进步的观点出发,系统地阐述和解释领土取得规则体系,应是国际法学的重要任务之一。而研究法院判例已陈述的规则,应可作为国际法学进步的一个可靠的阶梯。
注释:
①在许多案件中,当事双方对争端的性质提出不同的主张。在利比亚与乍得的争端中,利比亚主张争端的性质是领土争端,而乍得认为属于边界争端。从争端解决的角度看,这两种争端没有本质区别。法院在回应利比亚的主张时指出:“‘确定’领土就是确定其边界。”参见Territorial Dispute (Libyan Arab Jamahriya/Chad),Judgment,I.C.J.Reports 1994,p.26,para.52。在“柏威夏寺案”中,国际法院的判决书说:“法院受理的争端标的是柏威夏寺地区的主权归属,要解决这个领土主权问题,法院必须考虑两国在该地区的边界线。”参见Case concerning the Temple of Preah Vihear (Cambodia v.Thailand),Merits,Judgment of 15 June 1962:I.C.J.Reports1962,p.14。从国际法学的角度看,领土争端与边界争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中边界争端“特别适合于裁决或仲裁解决”。参见Robert Jennings,"The Acquisition of Territory in International Law",in Collected Writings of Sir Robert Jennings,Vol.2,The Hague/London/Boston: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98,pp.944-946。
②据笔者所见,国际法院从未阐述过到底有哪些“模式”,但很确定有“国际法上已确立的权利取得模式”,参见Land and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Cameroon and Nigeria (Cameroon v.Nigeria:Equatorial Guinea Intervening),Judgment,I.C.J.Reports 2002,p.352,para.65。
③Robert Jennings,"The Acquisition of Territory in International Law",p.934.
④Ibid.,p.936.
⑤Frontier Dispute (Burkina Faso/Republic of Mali),Judgment,I.C.J.Reports 1986,p.564.
⑥Ian Brownlie,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Sixth Edi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119.
⑦Ibid.,p.119.
⑧Ibid.,p.128.
⑨G.Schwarzenberger,"Title to Territory:Responses to a Challenge",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51,No.2,1957,p.314.
⑩卢麟斯:《国际公法要略》,钟建闳译,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第32页。
(11)Ian Brownlie,The Rule of Law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The Hague/London/Boston: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98,p.153.
(12)Ibid.,pp.126-127.
(13)Ibid.,pp.153-155.
(14)Ian Brownlie,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pp.127-128.
(15)Charles G.Fenwick,International Law (Fourth Edition),New York:Appleton-Century-Crofts,Division of Meredith Corporation,1965,p.404.
(16)M.F.Lindley,The Acquisition and Government of Backward Territory in International Law,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26 by Longmans,Green and Co.,Ltd.Reprinted by Negro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69,pp.1-2.
(17)Robert Jennings,"The Acquisition of Territory in International Law",p.939.
(18)Ian Brownlie,The Rule of Law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p.53.
(19)Robert Jennings,"The Acquisition of Territory in International Law",p.1002.
(20)Ibid.,p.997.
(21)“承认”因主体、客体、情势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法律和政治意义。实际上,各种权利根据都包含着不同意义上的“承认”因素。所以,在司法层面上,具有不同意义的各种承认肯定是国际司法机构考虑的重要因素,但不能把所有的模式都放到“承认”这个标题下。而在立法层面上,某种集中化的“国际承认”或许可以起到类似立法的作用,但在目前的国际关系现状下,关于是否存在“国际立法”机构,显然有不同的看法。
(22)G.Schwarzenberger,"Title to Territory:Responses to a Challenge",p.324.
(23)Ibid.,p.311.
(24)该术语有许多译法,本文中许多地方简称为“保持占有”。
(25)Sovereignty over Pulau Ligitan and Pulau Sipadan (Indonesia/Malaysia),Judgment,I.C.J.Reports 2002,p.645.
(26)Ibid.,p.668.
(27)Kasikili/Sedudu Island (Botswana/Namibia),Judgment,I.C.J.Reports1999,p.1058.
(28)Ibid.,pp.1100-1101.
(29)Case concerning Sovereignty over Certain Frontier Land,Judgment of 20 June 1959:I.C.J.Reports 1959,p.216.
(30)Ibid.,p.215.
(31)Ibid.,p.216.
(32)Territorial Dispute (Libyan Arab Jamahiriya/Chad),Judgment,p.15.
(33)Ibid.,p.20.
(34)Territorial Dispute (Libyan Arab Jamahiriya/Chad),Judgment,p.20.
(35)Ibid.,pp.20-21.
(36)Ibid.,p.21.
(37)Ibid.,p.27.
(38)Ibid.,pp.33-34.
(39)Ibid.,p.37.
(40)Ibid.pp.38-40.
(41)Case concerning the Temple of Preah Vihear (Cambodia v.Thailand),Merits,Judgment of 15 June 1962,p.16.
(42)Ibid.,p.16.
(43)Ibid.,pp.17-20.
(44)Ibid.,p.18.
(45)Case concerning the Temple of Preah Vihear (Cambodia v.Thailand),Merits,Judgment of 15 June 1962,p.20.
(46)Ibid.,p.22.
(47)Ibid.
(48)Ibid.,p.32.
(49)Ibid.,p.30.
(50)Ibid.,pp.30-31.
(51)Ibid.,p.32.
(52)Case concerning the Temple of Preah Vihear (Cambodia v.Thailand),Merits,Judgment of 15 June 1962,pp.34-35.
(53)Ibid.,p.100.
(54)Sovereignty over Pedra Branca/Pulau Batu Puteh,Middle Rocks and South Ledge (Malaysia/Singapore),Judgment,I.C.J.Reports 2008,p.95,para.272.
(55)Ibid.,p.96,para.275.
(56)Case concerning the Arbitral Award Made by the King of Spain on 23 December 1906,Judgment of 18 November 1960:I.C.J.Reports 1960,p.213.
(57)Ibid.,p.214.
(58)Ibid.
(59)Maritime Delimitation and Territorial Questions between Qatar and Bahrain,Merits,Judgment,I.C.J.Reports 2001,p.75,para.110.
(60)Maritime Delimitation and Territorial Questions between Qatar and Bahrain,Merits,Judgment,I.C.J.Reports 2001,p.81,para.132.
(61)Ibid.,p.76,para.111.
(62)Ibid.,p.77,para.114,117.
(63)Ibid.,p.83,para.139.
(64)Ibid.,p.85,para.147.
(65)Ibid.,p.85,para.148.
(66)Frontier Dispute,Judgment,I.C.J.Reports 1986,p.566.
(67)Ibid.,p.565.
(68)Ibid.,p.586.
(69)Frontier Dispute (Benin/Niger),Judgment,I.C.J.Reports 2005,p.127.
(70)Ibid.,p.133.
(71)Land,Island and Maritime Frontier Dispute (El Salvador/Honduras:Nicaragua Intervening),Judgment,I.C.J.Reports 1992,p.556,para.330; p.558,para.332.
(72)Ibid.,p.558,para.332.
(73)Ibid.,p.558,para.333.
(74)Ibid.,p.559,para.333.
(75)Ibid.,p.563,para.341.
(76)Ibid.,p.579,para.368.
(77)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 between Nicaragua and Honduras in the Caribbean Sea (Nicaragua v.Honduras),Judgment of 8 October 2007,p.26,para.76,http://www.icj-cij.org/docket/files/120/14075.pdf,2010-04-02.
(78)Ibid.,pp.26-27,paras.79-81.
(79)Ibid.,p.37,para.124.
(80)Case concerning Sovereignty over Certain Frontier Land,Judgment of 20 June 1959:I.C.J.Reports 1959,p.227.
(81)Ibid.,p.230.
(82)Land and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Cameroon and Nigeria (Cameroon v.Nigeria:Equatorial Guinea intervening),Judgment,I.C.J.Reports 2002,p.341.
(83)Ibid.,p.353.
(84)Ibid.,pp.354-355.
(85)Sovereignty over Pedra Branca/Pulau Batu Puteh,Middle Rocks and South Ledge (Malaysia/Singapore),Judgment,I.C.J.Reports 2008,p.50,paras.120-121.
(86)Ibid.,p.96,paras.276-277.
(87)Sovereignty over Pulau Ligitan and Pulau Sipadan (Indonesia/Malaysia),Judgment,p.678.
(88)Ibid.,p.685.
(89)The Minquiers and Ecrehos Case,Judgment of November 17th,1953:I.C.J.Reports 1953,p.57.
(90)Ibid.,p.72.
(91)Land and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Cameroon and Nigeria (Cameroon v.Nigeria:Equatorial Guinea Intervening),Judgment,I.C.J.Reports 2002,p.349,para.62.
(92)Ibid.,pp.349-350,para.62.
(93)Land and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Cameroon and Nigeria (Cameroon v.Nigeria:Equatorial Guinea Intervening),Judgment,I.C.J.Reports 2002,p.351,para.64.
(94)Ibid.,p.352,para.65.
(95)Ibid.,p.414,para.220.
(96)Kasikili/Sedudu Island (Botswana/Namibia),Judgment,p.1101.
(97)Ibid.,p.1106.
(98)Ibid.,p.1105.
(99)Ibid.,p.1103.
(100)Maritime Delimitation and Territorial Questions between Qatar and Bahrain,Merits,Judgment,pp.64-65,para.73-76.
(101)Ibid.,p.66,para.81.
(102)Ibid.
(103)Ibid.,p.67,para.84.
(104)Ibid.,p.67,para.86.
(105)Ibid.,p.69,para.96.
(106)Ibid.,p.69,para.97.
(107)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关于白礁主权争端案中,新加坡在《诉状》和《辩诉状》中都没有明确地声称白礁的法律地位是无主地,但在《答辩状》和口头聆讯中,新加坡把白礁说成是无主地。参见Sovereignty over Pedra Branca/Pulau Batu Puteh,Middle Rocks and South Ledge (Malaysia/Singapore),Judgment,I.C.J.Reports 2008,pp.29-30,para.40。
(108)A.S.Muller,et al.,eds.,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The Hague: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97,p.4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