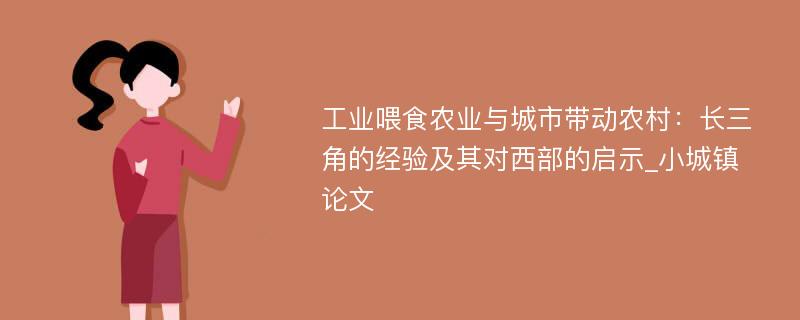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验及其对西部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江论文,其对论文,乡村论文,启示论文,三角洲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731(2006)02-0011-08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是我国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型。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和世界著名的河口三角洲地区,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和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改革开放以来,这一地区在体制转型和外向型经济的推动下,经济快速增长,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区域内工农差距与城乡差距呈现缩小的趋势,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内向经济一体化和外向经济一体化的核心区域。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快速增长,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越来越高,不仅对全国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而且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总结和研究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态势、模式、机制和经验,对全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发展路径与政策选择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对西部地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发展路径与政策选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长江三角洲地区与西部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比较
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体现,通过比较长江三角洲与西部地区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城乡关系,有助于我们总结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高速发展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一般经验。
1.长江三角洲地区与西部地区工业化的比较
分析工业化水平的指标有很多,本文主要选取了工业增加值、人均工业产值、工业化率以及产业结构作为主要的衡量指标,其中工业化率是指工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而产业结构是指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各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通过对2004年长江三角洲地区与西部地区的有关数据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见表1),长江三角洲地区两省一市的工业产值远远高于西部地区十二省市区的工业产值。2004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工业增加值为16588.69亿元,而西部地区仅为9527.6亿元;2004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工业化率为48.7%,而西部地区则为34.5%,从人均工业产值来看,2004年长江三角洲地区为12304元/人,而西部地区仅为2667元/人;从第一、二和三产业占GDP的比例来看,2004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和西部地区均为“二、三、一”的产业结构状况,但是西部地区第一产业的比重为19.5%,高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6.5%。
表1 2004年长江三角洲地区① 与西部地区工业化的比较
地 区
工业增加值 工业化率/% 人均工业产值
/亿元 /元/人
长江三角洲 16588.69
48.7 12304
上海 3492.89
46.9 25929
江苏
7714.4
50.1 10370
浙江
5381.4
47.9 11460
西部地区 9527.6
34.5 2667
内蒙古 1015.66
37.4 4234
广西 1044.83
31.5 2265
重庆
927.51
34.8 3343
四川 2165.22
33.0 2679
贵州
574.62
36.1 1521
云南 1053.36
35.6 2396
西藏
15.43 7.3
567
陕西 1064.81
36.9 2864
甘肃
576.22
37.0 2207
青海
158.64
34.1 2931
宁夏
186.340.5 3189
新疆745 33.9 3792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版整理计算得出
2.长江三角洲地区与西部地区城市化的比较
城市化水平一般可反映地区工业化在发展过程中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集中程度,对其进行测度的方法主要有复合指标法和主要指标法,本文采用对城市化表征意义最强且便于统计的主要指标法,从人口、地域范围两个方面比较长江三角洲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比较2004年长江三角洲地区与西部地区的有关数据(见表2),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非农业人口为5345.2万人,西部地区为7588.85万人,虽然从绝对值上西部地区是高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但西部地区在面积上、总人口上都是远大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从城市化率来看,2004年长江三角洲地区为38.47%,而西部地区仅为21.83%;从地域范围来看,2004年长江三角洲地区每万平方公里城市个数为3.36,而西部地区仅为0.25。由此可见,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远远落后于长江三角洲地区。
表2 2004年长江三角洲地区与西部地区城市化的比较
地 区 非农业人口 城市化率每万平方公里
/人 /%
的城市个数
长江三角洲 53452271 38.473.36
上海 10975964 81.161.21
江苏 30235656 41.963.75
浙江 12240651 26.743.13
西部地区75888509 21.830.25
内蒙古 9023660 38.240.17
广西
9015595 18.460.88
重庆
7858322 24.990.61
四川 19143365 22.270.66
贵州
6065709 15.830.74
云南
6942033 16.410.44
西藏419824 15.970.02
陕西917498 24.890.63
甘肃
5895845 22.740.40
青海
1468093 29.450.04
宁夏
2077457 35.191.35
新疆
7061108 36.670.13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5》,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版;《中国统计年鉴2005》,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版整理计算得出
3.长江三角洲地区与西部地区城乡差距的比较
本文主要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偏差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两个方面来比较长江三角洲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城乡差距(见表3)。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偏差是指工业化率与城市化率的差额,2004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偏差大小为10.18%,西部地区为12.71%,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2004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为7982.30元,而西部地区为5860.30元,绝对数额上的差距并不能完全反映问题。因为西部地区农村、城镇居民人均收入额本身都是远低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由此造成长江三角洲地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高于西部地区;从农村、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来看,2004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分别为38.3%、37.2%,两者间相差不多,而西部地区分别为50.6%、38.9%,之间相差11.7%。可见,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乡差距是小于西部地区的,虽然长江三角洲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相差不多,但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却存在很大的差距。
表3 2004年长江三角洲地区与西部地区城乡差距的比较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地 区 工业化与
城乡居民 农村居民 城镇居民
城市化人均收入 家庭恩格 家庭恩格
的偏差差距/元尔系数尔系数
长江三角洲 10.187982.30 38.3
37.2
上 海 -34.289616.49 34.6
36.4
江 苏8.125728.08 44.0
40.0
浙 江
21.128602.32 39.5
36.2
西部地区 12.715860.30 50.6
38.9
内蒙古
-0.795516.62 42.7
32.6
广 西
13.006384.77 54.3
42.3
重 庆9.816710.55 56.0
37.8
四 川
10.765190.94 55.7
40.2
贵 州
20.27 5600.5 58.2
41.1
云 南
19.187006.69 54.0
42.4
西 藏
-8.687244.76 64.0
45.6
陕 西
12.045625.95 42.4
35.9
甘 肃
14.225524.52 48.0
37.1
青 海4.615362.02 48.5
35.7
宁 夏5.284897.82 42.0
37.0
新 疆
-2.815258.49 45.2
36.1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版整理计算得出
二、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态势、模式和机制
1.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基本态势
按照发展经济学的原理,工业化与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主题。但是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伴,因为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主题是发展现代工业,现代工业大都建立在城市,经济发展的重心在工业和城市;“当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之后,经济发展中的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和现代化相伴随的”[1] (P7),需要在现代化的基础上,建立起现代化的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实施工业反哺农业的战略转型,推进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和乡村一体化的现代化。
长江三角洲是我国工业化水平最高、城市化水平最高、城市体系最完备的地区之一。长江三角洲地区2004年末人口为7469.54万人,非农业人口为5345.2万人,占总人口的40.94%[2] (P265),城市化水平比全国平均水平41.8%高出4.72个百分点,上海高达74.62%。GDP为13739亿元,人均GDP为18393元。区内有大、中、小城市54个,1396个建制镇,每万平方公里有3.36个城市,平均每1800km[2]就有一座城市,不足70km[2]就有一座建制镇。由于农村城镇化和乡村工业化的发展,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目前的基本态势是:
(1)乡村城镇化的发展实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城乡的良性互动。大力发展小城镇,在小城镇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城市经济社会的良性互动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基本特征。小城镇吸纳农村劳动力面广量大,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载体。农村城镇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农业产业化发展可以从经济上彻底打破传统农业所依赖的自然经济基础,使其面向市场,走上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之路,而小城镇可以有效连接城市与农村,为农业现代化与产业化提供载体。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小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是通过乡镇企业的发展来实现的。目前长江三角洲地区小城镇建设的重点已经由数量扩张转向了产业发展,通过城镇的产业扩张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通过乡村城镇化和乡村工业化推进工业化进程。20世纪80年代长江三角洲将小城镇作为县域产业结构优化及乡村工业化的增长极,90年代又进一步加强城镇之间的联系,建立了联系较强的城镇化体系,从而带动广大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实现了城乡良性互动。
(2)乡村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城乡经济的联系。乡村工业化的发展不仅可以有效连接城市和乡村,实现城乡经济的一体化,而且可以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乡村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一方面会缩小城乡差距,从而减弱乡村人口流迁的拉力和推力,促进乡村城市化;另一方面,又会促进劳动者素质和迁移能力的提高,在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差距仍然存在的条件下,乡村工业化又有助于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加强城乡经济的联系。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工业化是通过乡村工业化的方式推动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长江三角洲地区农业的快速增长和结构的转变,为这一地区乡村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生活消费品的短缺和改革开放以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为长江三角洲地区乡村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推动因素。市场化进程的加深、制度创新为长江三角洲地区乡村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市场环境。而且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乡村工业化是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民营经济的发展可以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打破农村发展农业、城市发展工业的传统观念,促进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增强了城乡经济的联系。
(3)区域一体化推动了城乡的一体化和城乡经济的互动发展。区域一体化发展是促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途径。长江三角洲的乡镇、村及村以下,工业产值占全国同一类型总数的38.8%,大部分县及县级市的乡镇工业产值已超过整个工业的一半,苏南和上海郊县则占2/3,在农村工业总产值中,工业已占80%-90%以上。特别是近几年以来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使得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和集约化发展尤为突出。2004年上海的人均GDP为四川、江西、安徽的6.39倍、6.35倍和5.87倍,浙江、江苏的人均GDP为四川的2.62倍和2.32倍。通过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最终将目前的城市工业、乡镇企业和农业联系在一起、把区域中的城市、城镇和乡村三元结构推向一元,加强了劳动力中的城市工人、乡镇企业工人和农民与产权方面的个人、集体和国家之间的联系。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增强了区域经济各单元之间的联系,形成了城乡经济互动发展的新格局。
(4)政策激励的正确性使区域内工农差距和城乡差距呈缩小的趋势。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以及工业反哺农业不仅取决于:“国家的社会经济环境、农业资源禀赋,而且取决于一系列政策激励的正确性,包括政策路径、决策层偏好、城乡利益集团的力量格局等因素。”[3] 长江三角洲地区在经济增长呈现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总体呈缩小的趋势”[4] (P2)。在政策导向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是按照城乡的融合与互动思路发展的。在江苏和浙江经济发展过程中,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凭借着特殊的体制背景和区位优势,以乡村工业化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模式使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迈上了新的台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以向非农产业转移,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格局得以打破,单一的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得以向多职业、多阶层的现代社会结构转变,根深蒂固的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得以改变。这种政策上的导向使得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内城乡差距呈现出缩小的趋势。
2.长江三角洲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模式
长江三角洲地区在以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市)化为主体推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重视工业与农业、城市和乡村的协调发展。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方面形成了乡村工业化与城镇(市)化协调城乡发展的模式,这一模式的内容有:
(1)乡村城镇化协调城乡发展。根据刘易斯(Leuis)提出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农业的落后在于传统农业部门存在着无限的劳动供给,而资本和土地资源却相对稀少,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城乡经济的二元分离发展。中国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具有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典型特征。要想促进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实现城乡经济的协调互动发展,就必须将过多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去,这就是城镇化或城市化。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实践中开创了乡村工业化和发展小城镇的道路来协调城乡经济的发展,通过发展乡镇企业进行农村工业化,实现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形成了乡村城镇化协调城乡发展的思路,这一思路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第一,乡村城镇化,把城镇化建设和乡村工业化相结合,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第二,剩余劳动力的流出使得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促进了农业产业化进程,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第三,带动了农村产业结构的升级,提高了农村工业化水平,促进了非农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其典型特征是在乡镇企业发展的同时就地发展了小城镇,由此创造了乡村城镇化模式。在这一模式中,乡镇企业承担了很大一部分城镇建设和社区建设的费用,使乡镇居民集中居住。农民有了非农收入可以自筹资金发展小城镇,促进民间城市化的发展,这样不需要国家的财政支持,农民就可以通过发展乡镇企业自己转移自己,离土不离乡,实现了农村城镇化。从协调城乡关系的角度分析,在乡村城镇化模式中,农村与城市间增加了小城镇,城镇成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中介点”。这使得城市对乡村的影响力可以通过小城镇来增强和扩散,既起到了放大城市作用的效果,又使城乡联系进一步加强。这些随着乡镇企业发展而形成的小城镇,不仅是吸收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重要场所,也是改造传统农业的载体,在城镇发展非农产业,使城镇成为周边农村的中心,通过“由中心向外围的扩散”[5] 实现城乡经济的一体化。
(2)城镇的城市化协调城乡发展。长江三角洲区域是经济发展整体水平最高,也是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最为协调的区域。这个区域城乡关系的协调性与其城市化水平特别是其城市现代化水平密切相关。研究这一地区的城市化可以发现,单纯靠行政手段将农村人口变为城市人口并不是城市化的全面反映。城市化不仅包括人口转移的内容,而且也应该包括产业聚集和企业聚集以及城市容量的增加、城市功能的提升等内容,城市化应该提供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真正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镇化发展的基础上,长江三角洲地区又针对小城镇偏小和过于分散,其城市功能太弱的弊端,进行撤乡并镇,发展中心城镇,进一步推进城镇的城市化,同时在城镇注重发展服务业,由此使城镇功能得到进一步提升,促进了城镇的城市化,形成了城镇的城市化协调城乡发展的思路。城镇成为现代化要素向农村扩展和辐射的中间环节,农民不进城市就能在城镇中享受到城市的现代文明和经济生活,促进了农民的市民化。城镇城市化可以说是城市化与城镇化的衔接,城市和乡村借助具有真正城市功能的城镇的连接实现了城乡一体化。在这一模式中,建立都市圈,推进都市圈内的城镇城市化和区域一体化。都市圈是指一个或多个大的核心城市以及与这些核心城市具有密切社会、经济联系和一体化倾向的相邻城镇与地区组成的城乡复合体。在这一模式中,中心城市与周边城镇的一体化程度高,形成了产业的分工与协调,目前长江三角洲地区已经形成了以上海、南京、杭州为中心城市的都市圈,都市圈的形成是中心城市与周围地区双向流动的结果,都市圈按经济与空间、环境功能的整合需求及发展趋势构筑了相对完善的城镇群体。都市圈使得过去城市与城镇的“中介点”关系变成了现在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直接连接关系,极大地提升了中心城市的带动和一体化功能,使中心城市在区域经济增长和协调城乡关系中的作用更加突出。
(3)工业化与城市化共同协调城乡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化离不开城市化。因为发展工业必须重视规模经济和集聚效益,城市化可为工业在一定地域的集聚和形成合理的生产规模提供较好的投资环境和销售、流通市场。“农村的发展离不开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城市发展也离不开农村的促进和支持。”[6] 城市化和工业化协调发展带动乡村是世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共同规律,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带动农村经济能带出“双赢”的结果。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产生的积聚效应,可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同时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所产生的扩散效应使更多的资金、技术、人才流向农村,实现城乡良性互动,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800至1000美元时,便开始由工业“反哺”农业,而长江三角洲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高,较早就进入这个阶段,形成了工业化与城市化共同协调城乡发展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模式。长江三角洲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相比较,工业化的发展速度快,工业结构变化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000美元以上,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工业经济结构中占比较高的比重,制造业在保持长期快速稳定增长的同时,其内部结构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促进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改善。
3.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机制
城乡经济发展的差距“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基本事实”[7]。而且“市场机制并不会自动地解决三农问题,使农村经济摆脱落后困境,必须引进政府有形之手”[8]。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是通过政策的引导和激励,发挥城市和城镇对乡村的带动,以及城市和城镇对乡村的产业扩散和辐射带动来实现的。其基本机制有:
(1)拉力机制。城市在发展过程存在两种类型的作用力,即向城市中心集聚的向心力和从城市中心向外扩散的离心力。由于它们的非平衡运动,故产生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通过极化效应促进中心城市的发展,中心城市再通过扩散效应带动腹地的发展。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和产业扩张,就业容量增加,城市的“拉力”就会加大,进而促进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与充分就业。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实施以县级和省级重点中心城镇为主要载体的农村城镇化战略,促进了生产要素向这些城镇的集聚,通过产业扩张与就业容量的增加,形成了工业带动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拉力机制。
(2)推力机制。从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来看,不仅存在着拉力机制,而且也存在着推力机制。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吸引了城市生产要素向农村的流动,进一步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而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在经济收入的驱使下,为了生存也不得不流向城市,这样便产生较大的推力,进一步加强了城乡互动关系。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以城镇化为重点,推进了小城镇的发展,城镇密度比较高,城镇分布比较广,农民亦工亦农,既提高了农民收入,又增加了区域经济的联系性,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提供了一种推动力。
(3)市场机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市场机制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核心的调节作用。据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研究中心的测算,2003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整体市场化程度为76.18%,江苏的市场程度为76.07%,浙江的市场化程度为78.38%,上海的市场化程度为73.48%[4]。由于市场化程度高,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使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和工农业之间能够自由流动,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了城乡一体化,消除了城乡之间的壁垒。同时市场化的进一步发展为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提供了市场销售和流通组织支持,形成了城乡统一的大市场,疏通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农产品的流通渠道,促进了农产品的市场销售。随着农村流通组织的成长,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市场销售和流通组织支持也逐步建立。
三、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一般经验总结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上海、江苏、浙江两省一市目前在国内率先实现了现代化和小康,在城乡一体化、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有:
1.以城乡经济的互动发展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 城乡互动是指城市与乡村在区域发展中,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动态过程。城市的发展来自于广大农村区域的支持,而随着城市的成长壮大,城市有责任和义务帮助农村摆脱困境,促进与拉动农村区域增长,而广大农村又是城市未来发展的巨大潜在市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依赖于广大农村,城乡互动是城市和乡村经济发展的前提。城乡互动发展使城市要素、产业与职能向农村区域有序扩散,即通过市场机制,使资源、资金、技术等要素在城乡地域空间上,在不同产业间有序流动和优化组合,促使城乡经济持续发展。这不仅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动力与物质保障,而且为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开辟新的路径。城乡互动的发展改变了城乡分割的体制和政策,消除了二元经济结构,实现了农村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逐步彻底解决“三农”问题。长江三角洲地区城乡经济的互动发展从区域社会整体利益和公众的基本需求出发,将这一地区城乡的生产和生活纳入区域社会生态系统中,协调了城乡两大集团的经济利益格局,不仅形成了安定的社会环境,而且为城乡创造了公平的发展环境和生存空间,通过城乡经济之间的互动发展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坚实基础。城乡互动发展在承认城乡文化异质性和互补性的基础上,用现代化的文化价值观将城乡文化和价值统一起来,把乡土观念和现代城市文明有机结合起来,有利于农民市民化进程的加快。
2.以农村城镇化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推进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 关于中国的城市化战略,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是实行大城市引导战略,二是农村的城镇化战略。很多人主张以大中城市为主的战略,因为大城市经济效益高。而小城镇虽然在经济效益方面比不上大中城市,但是农村的城镇化却有利于城乡的融合,同时小城镇的发展可以提高乡镇企业的集聚效应,成为农业产业化、现代化进程中高度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的载体,成为农村与大城市联系的纽带和中介,而且小城镇建设成本低,适合农村非农产业和人口的转移。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城市化发展中实施了以大城市为龙头,以中心城镇为载体的农村城镇化战略,在短时期内使县城和重点城镇形成经济增长极,增强了城市、城镇和农村之间的联系,实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以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为目标,稳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因为区域经济的集聚效应不仅在于城市规模,而且主要在于区域经济的联系性,通过实施以中心城镇为载体的农村城镇化战略,形成空间优化的城市和城镇层级体系,提高区域经济的联系性。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空间结构优化的城市和城镇层级体系中形成了不同层次的城镇扩散圈层,第一扩散圈层是苏州、无锡、常州、昆山、杭州和宁波。这一圈层的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较大,工业化水平高,乡镇企业发达,乡村工业化水平高,普遍成为当地的经济支柱和财税来源。第二扩散圈层是南京、嘉兴、绍兴、江阴和镇江。这一圈层产业结构处于“二、三、一”阶段,第二产业中的加工制造业发达,工业发展迅速,主要向机械、电子、精细化工等方向发展。第三扩散圈层是扬州、南通、湖州和舟山。这一圈层的乡镇企业发展较晚,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较大,产业结构水平较低,与第一、第二圈层相比属于边缘地区。因此,从总体上来看,在以农村城镇化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通过中心城镇的这种扩散效应中强化了区域经济的联系和城乡经济的联系。
3.以乡镇企业的集聚化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来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 长江三角洲全区土地面积占全国的1%,人口占全国的6.25%,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21%,其农村工业化是通过乡镇企业的发展而推动的。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浙北的萧山、绍兴、鄞县也做了相同的尝试,乡镇企业加速了这一地区的农村工业化进程,使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迅速恢复了活力,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乡镇企业迅速发展,使其已成为农村工业化的主要基础和最具活力的生长点,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并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支柱,为中国的农业工业化、农村现代化和乡村城市化开辟出一条道路。可以说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是伴随着乡村工业化的发展而崛起的,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乡村工业化不仅改造了传统农业,提高了农民收入,而且进一步加速了城乡经济的融合和相互推动。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反哺农业经历了两个阶段:早期阶段是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反哺农业、农村家庭成员进入乡镇企业获得比农业更高的收入,农业税费负担由乡镇企业负担。农村社区建设费用、农田基本建设费用由乡镇企业统筹。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乡镇企业和农村工业化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农村工业化和乡镇企业采取园区经济的发展模式,促进了生产要素的集中和资源优化配置,形成了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交融和相对集中,打破了长期以来按行政区划发展经济的模式,促进了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化的进程。园区经济模式主要是利用了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所带来的经济外部性。乡镇企业以小城镇作为园区经济的载体,不仅使这些小城镇交通运输、通信网络设备等基础设施得到改善,并且能够接受大中城市的辐射,同时还能对广大周边农村地区产生一定辐射作用,使农民实现“进厂又进城,离土又离乡”。小城镇通过园区化的经济功能提高了乡镇企业的集聚效应和经济容量,乡镇企业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工业体系和开放性的产业集群,地方政府成为反哺农业和农村的主体,用发展乡镇企业得到的收入加强对农业的科技投入、加大农业基本建设投入,推动农工商组织体系一体化,带动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四、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经验对西部地区的启示
目前西部地区存在着严重的二元经济结构,“在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工业和农业分离发展,城乡分割”[9] (235),由此形成城乡差别的加大和农业的边缘化发展,使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大大落后于长江三角洲地区。西部地区现已总体上进入到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借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验,积极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发展战略转型。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经验对西部地区的启示有:
1.以农村的城镇化推进西部地区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西部地区与东部长江三角洲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也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态势,长江三角洲地区城乡差距逐步缩小,而西部地区的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借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验,西部地区要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就必须加快发展小城镇,提高城镇化水平和质量。在广大西部农村地区推进城镇化,重点发展中心城镇,实现城乡一体化。西部地区很多地方地广人稀,居住太分散,不能形成集聚效应,发展不了工业,只能发展传统的农业。通过城镇化,让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工业,可以将分散的农民集中起来,让农民居住在基础设施较完备的城镇,既可以提高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又可以促进农民的非农化和市民化,提高农民收入。在西部城市缺乏的地区,要重点发展中心城镇,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吸纳更多的农村人口,达到规模经济。在规划城镇区域时,要注意吸取东部地区的经验教训,一定要强调城镇集中,小城镇、分散的城镇都不能达到规模经济,形成不了地区的经济中心、市场中心、信息中心、服务中心,处处建城镇还会浪费耕地,损害农业。
2.以城镇的城市化加快西部地区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 从动态过程来看,城市化分为三个阶段:“人口的城镇化、城镇的城市化和城市的现代化”[10] (P373)。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低,突出表现在城市的规模小,城市太分散,不能形成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极。因此,西部地区城市化首先要增加城市的供给,在人口城镇化的基础上重点建设中心城市,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发展极,推进城镇的城市化,加快西部区域一体化进程。西部的大城市,应该发挥其发展极的作用,加快其市场化改革进程,注重发展服务业,提升城市功能,通过各种优惠政策来吸引集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要素和能量。因此,借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验,通过城镇的城市化来联系城乡经济,在城市相对集中的区域,要统筹规划,相互协调,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增强其辐射力,推进区域一体化,运用城市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扩散和带动效应实现西部的工业反哺农业和城市带动乡村的战略实施。
3.以农村工业化推进西部地区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 农村工业化是城镇化的推动力,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是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特别是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过程。借鉴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经验,实现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西部地区的农村工业化要在发展传统工业的基础上,优化产业结构,进行现代工业的改造。西部地区政府应该为农村工业化制定完善的配套政策法规,主动开发新项目、新技术,吸引建设资金,还要提供足够的金融支持,让更多的优质企业上市,从资本市场获得资金来源。东部地区发展乡镇企业的经验可以借鉴到西部,鼓励农民自己创办企业,发展民营经济。同时借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验,西部地区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过程中,要以发展乡镇企业、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途径来加快西部地区的乡村工业化进程。在资金缺乏的情况下,创办乡镇企业的资本原始积累可以通过从东部打工就业的一部分人中获得。西部地区政府应该强化建设西部、建设家乡的观念,制定优惠政策,让有了一定资本和技术的农民工回到西部,发展乡镇企业,以民间资本为主体推进西部的农业工业化进程,实现西部地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战略转型。
注释:
①长江三角洲的概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从广义上讲是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的统称;从狭义上则特指“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的会员城市,含上海、无锡、苏州、杭州等16个城市。本文所指的是广义上的长江三角洲,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两省一市。
标签:小城镇论文; 农村人口论文; 城市经济论文; 地区经济发展论文; 城镇人口论文; 三农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农村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