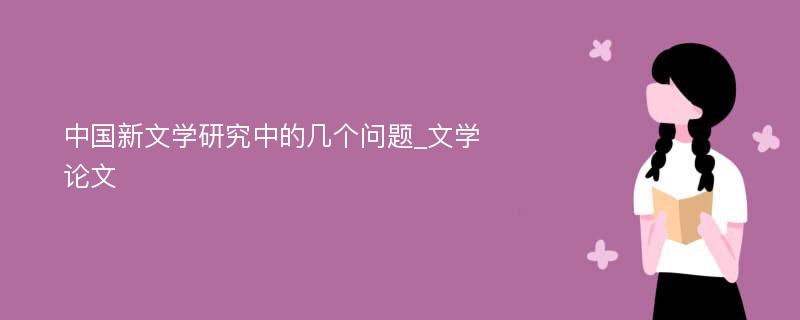
新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中国论文,几个问题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文学研究已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对不同历史时期文学的认识和评价并非没有相异的意见。其中涉及全局性的问题值得深入讨论。
一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文学与政治历来有密切的关系,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建国初十七年曾要求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过于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给文艺工作带来不利影响。所以邓小平同志在新时期指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同时,他又指出,“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20页。)然而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后来又出现了一种观点,即认为文艺就是文艺,与政治无干,文艺应该归位,应该疏离乃至脱离政治。这样的理论观点强调文艺的审美本质,而否定文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其他层面的本质。持这种观点的人甚至认为,文艺与政治关系密切就不是好文艺。因此,为政治服务的文艺就应基本加以否定,也因此,他们就不但贬低和否定十七年文学,乃至贬低和否定新时期与政治关系密切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以及近期的反腐倡廉文学,乃至包括像《抉择》这样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优秀作品。
文艺所以不能脱离政治并历来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是因为政治是经济利益集中的表现,它涉及社会生活中每个人的利害。除了不识事的儿童,所有人包括作家在内,都难免有一定的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和政治感情。特别在政治斗争尖锐的年代,更是很少人能够不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被卷入政治斗争。同时,人们,也包括作家,不独会受到政治斗争的影响,还会受到政治家、政党和政府的影响,包括一定的政党和政府的文艺、出版等各种政策的影响,还包括来自政党、政府和政治家的直接政治干预的影响。因而每个时代都会有大批作家的作品涉及政治,自觉不自觉地为某种政治服务,使文艺产生作用于政治。古今中外皆如此。恩格斯就说过:“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但丁和塞万提斯也不逊色;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现代的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倾向的作家。”(注:《致敏·考茨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85页。)
今天我们自然不应该再提倡文艺都要为政治服务,因为这样非但限制了文艺题材和主题的宽广领域,而且助长了急功近利的粗制滥造。但对于历史上存在的曾为一定政治服务、产生作用于政治的文艺作品,恐怕还要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认为凡提倡为政治服务的文学就没有好文学,就统统要不得。
首先,要区分文学是为什么样的政治服务的,是为进步的政治服务,还是为反动的政治服务。如对十七年文学的评价就遇到这个问题。建国初十七年的政治固然发展了“左”的错误,但总体方向是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的,而且1957年之前的政治路线也是基本正确的。在政治问题上历史方向的正确,具有头等意义。推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劳动人民的统治,采取措施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政治方向从历史的发展看,当然是进步的。今天我们虽然承认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坚持的仍是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十七年文学除了明显宣扬左倾路线的外,应该说大多数作品是为人民为社会主义这个大方向服务的。其次,十七年诚然提倡文艺为政治服务,也确实产生了许多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品,但不能说十七年的所有作品都有政治内容,都为政治服务;也不能说为政治服务的作品就一定都是概念化公式化的。有一种误解,仿佛十七年的作家只知为政治服务,而不知文学为何物,对文学艺术的特征和规律一概不把握。事实并非如此。不要说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冰心、曹禺、丁玲、艾青、臧克家、赵树理、柳青、周立波等老作家深谙文学的特征和规律,就是王蒙、刘绍棠、李瑛、公刘、邵燕祥、李国文等当时还年青的作家,不也通晓文学的特征和规律吗?他们都有谈论文学特征与规律的文章,而且也都写出过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当然,其中有些作家的作品也难免有概念化公式化的部分,毕竟我们也不能以偏概全。当时的文学理论著作尽管也讲文学要为政治服务,讲党性原则,但同时也讲文学的艺术特征和规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社会生活和文学艺术“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里讲的从现实美到艺术美的升华就是文艺创作的本质特征和规律。不过,文学作品的优劣还取决于作家本身的艺术天赋和才华以及有无丰富的生活体验,创作的优劣并非都由作家的理论认识来决定。
十七年的文学有许多为政治服务的作品,也是很优秀的作品。像巴金的《英雄儿女》、老舍的《龙须沟》和《茶馆》、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孙犁的《风云初记》、梁斌的《红旗谱》,还有诗歌中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祝酒歌》,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雷锋之歌》,散文中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等,都是脍炙一时的名篇,至今仍不愧为新中国文学表现时代真实和时代精神的代表之作。十七年文学中还有不少并非为政治服务,也没有什么政治内容的作品,如陈翔鹤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唱挽歌》和秦牧的知识性散文《艺海拾贝》等。
放开眼光看,历史上为政治服务的或有强烈政治倾向的许多作品反而是不朽的。除了上引恩格斯所列举的,我国文学史上从屈原的《离骚》到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几乎同样可以找出长长一列与政治关系密切的作家和作品。中国的儒家主张“民为邦本”,故屈原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杜甫的《兵车行》等大量诗歌都与当时政治密切相关,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竟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诸如此类关心人民疾苦、乃至“国家安危,匹夫有责”等深具人民性和爱国主义的政治立场,被视为民族正气,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共鸣,正非偶然。所以,笼统地把为政治服务的文学无分析地一律打入冷宫,判为“非文学”,实乃偏颇之极、决非正确的意见。实际上,新时期文学中的许多优秀作品也是具有强烈政治内容并为一定政治服务的。伤痕文学的代表作《班主任》、反思文学的代表作《天云山传奇》、改革文学的代表作《乔厂长上任记》,还有茅盾文学奖历届获奖的大多作品如《将军吟》、《芙蓉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东方》、《冬天里的春天》、《沉重的翅膀》等,难道不都是与一定的政治密切相关吗?!
对于历史上表现反动政治观点和倾向的作品,也要作具体的分析。有的作品政治思想倾向反动,但作为文学的文本却有它独到的文学价值,或生动地反映了某种现实生活,或艺术形式上有所创造,在文学史上恐怕也不能完全否定。在指出其思想倾向错误的同时,也要实事求是地肯定它对文学发展的一定贡献。只有那些政治思想倾向错误和反动,艺术上又无可取的作品才应该给予完全否定的评价。否则,我们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就会真正制造出“空白”论,或大部分的“空白”论。
二 文艺真实性与思想倾向性的关系问题
人们曾说真实是艺术的生命。可见,真实性问题在评价文艺高下的重要性。但评价作品除了真实性,还有倾向性问题,而且真实性与倾向性并不完全统一。在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有人认为十七年文学不仅缺乏真实性,连倾向性也错误。例如认为农业合作化运动就是错误的、失败的,歌颂合作化就不应该,也不真实;歌颂新英雄人物不写缺点,描写现实只歌颂光明、不暴露黑暗,搞理想化和假大空,同样既不真实,又有倾向错误的问题。实际上,这种观点不仅涉及十七年文学的评价,也涉及到其他时期的不少文学作品的评价。
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是延安时期就争论过的老问题。现实生活按照辩证法是永远既有光明面,也有黑暗面的。因为光明与黑暗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历史真实当然也包含这样的辨证内容。只是有的时期光明面可能大于黑暗面;另一时期则可能黑暗面大于光明面。严格地说,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不可能只是歌颂光明而不暴露黑暗。一部作品歌赞正面人物就不可能不揭露反面人物。如果不写反面人物就难以衬托出正面人物。许多人物身上又既有优点,也有缺点。这种状况在建国初十七年文学中,或在新时期二十年文学中都有反映。硬说十七年文学全部都只歌颂光明,不描写黑暗;或硬说新时期文学全部都只揭露黑暗而不表现光明,皆不符合文学的历史实际。
在真实性问题上要看到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对于文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素有“再现说”与“表现说”的区分,后来又出现“形式说”,但此说也没有完全否定一定形式总反映一定的现实内容。艺术真实虽应反映历史真实,却不等同于历史真实。第一,艺术真实本质上是作为创作主体的虚构,是诉之想象的虚假形象世界;第二,艺术真实容许对现实生活印象进行集中、概括和理想化,只要这种假想的形象世界能让读者和观众信以为真并感染他们;第三,由于作家采取的艺术创作方法不同,反映同一历史真实对象的艺术形象,如用现实模本来衡量,必然会有种种差异。所以具体作品的创作中,是以歌颂光明为主,还是以暴露黑暗为主,是如实地去写事件和人物的优点与缺点,还是只写优点而略其缺点,乃或以夸张的理想化的笔法去写优点或缺点,这自然主要都取决于作家作为创作主体的选择。这种选择既受到整个时代氛围的影响,也受制于作品创作的主观目的和作家自身的思想局限。悲剧与喜剧、颂歌与战歌,就会因目的的不同而有相异的处理。当一个光明面占主导,全社会充满明朗、欢乐的氛围,颂歌在文学领域风行的时代,涌现大批以歌颂光明和先进的正面人物为主的作品是合乎历史上文学发展的规律的。反之,当黑暗面在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全社会充满悲愤、哀婉,悲剧成为流行的文学形式的时代,暴露黑暗和负面人物的作品居多,那同样也合乎文学发展的规律。建国初涌现大量颂歌,是前者的证明。而建国前国统区出现大量哀伤、悲愤的文学,则是后者的证明。新时期伤痕文学的涌现正与“文化大革命”十年的黑暗灾难分不开。
但作品的文学价值并不单纯取决于歌颂与暴露兼备,或以何者为主。两者都可能出现好作品或坏作品,关键在于文学描写和艺术形象造型是否真实感人,也还在于站在什么立场去歌颂或暴露,以及被歌颂或暴露的对象是否值得歌颂与暴露。《诗经》中的《生民》和《公刘》都是歌颂周人始祖的颂歌,屈原的《九歌》也大多是颂,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虽然内涵丰富,就其主要意义而言,也是英雄的颂歌,它们都没有被认为不真实并因此丧失文学的意义和历史地位。相反,这些作品在我国和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均无可争议。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中像藏族、蒙古族史诗《格萨尔》、蒙古族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也都是英雄颂歌,难道不都属于中华民族文苑的瑰宝吗?这些作品中的艺术真实,有许多正是理想化夸张化的,所写的主要英雄并不都一定写缺点。历史上许多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往往都这样。《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聪明智慧是理想化夸张化的,曹操的形象在阴险、狡诈、狠毒方面也是理想化夸张化的。我们决不能用现实主义的真实观去衡量浪漫主义或现代主义的艺术真实性,也不能用浪漫主义或现代主义的艺术真实观去要求现实主义的作品,这应是常识。对古代的或外国的文学是如此,对当代中国文学的要求恐怕也应当如此。
有人把建国初的颂歌比为明代的“台阁体”,我不能赞同这种意见。把新中国作家对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领袖,包括对毛泽东的歌颂,等同于封建文人学士对封建时代帝王的歌颂,这就完全混淆了不同的时代和立场。这里不是说十七年的颂歌都是好的。有许多那个时期的颂歌概念化公式化,缺乏文学描写的生动性,艺术上不能打动人,文学史上自然没有它们的地位。但对毛泽东的颂歌,乃至对焦裕禄和雷锋等英雄人物的颂歌,又确有写得好的,感情真挚充沛,形象真实生动,语言精炼而富于感人的表现力,怎么能说它们就一定不真实,就一定要不得呢?!我们知道,毛泽东有大功,也有大过,但功大于过。这已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他是20世纪中国的伟人,也是20世纪世界的伟人。对于这样的属于劳动人民的革命领袖进行歌颂,特别是在夺取全国民主革命胜利后的建国初,真正对人民对革命有感情的作家作出颂歌的反应,难道都要一律加以指责和贬低吗?
不错,十七年或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的文学作品歌颂和暴露都错了的作品并非不存在。例如混淆敌我,把不是敌人的同志说成是“右派”或“右倾机会主义”,把老革命一概说成“走资派”,把“造反派”一律粉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这样的作品当然就不应该肯定。实际上在新时期文学中也存在歌颂和暴露不适当的问题。例如有段时间对于暴发的个体户和企业家,不问他们的思想境界与道德行为如河,乃至对损人利己和违背社会主义道德的行为也无原则地加以渲染和吹捧,还有像所谓“宏观性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中的有些作品那样,把社会现实中的黑点集中起来加以扩大化,仿佛我们的社会已经烂透了,毫无希望了。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对这类作品无疑也需要认真分析,分别给予不同的评价。当然,在新时期文学中有许多作品对于现实黑暗面的揭露,比十七年文学是更普遍也更深刻了。这与社会现实的现状并非无关,更与作家对现实问题的长期认识和透彻了解也有密切关系。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壮大和巩固,也使人们精神上对揭露黑暗面的承受能力大大提高了。今天自然没有人会把尖锐地揭露黑暗面的作品像五十年代那样看成“右派”放出的“毒草”。但对于这类作品的评价也要看它的实际文学价值,看它的艺术形象真实感人的力量,而非只要揭露就一律叫好!事实上有许多这样的作品文字粗糙,文学性很差,缺乏真实感人的艺术张力。
说到那些描写农业合作化的作家作品,也要看到具体情况的不同。有写合作化初期的,也有写人民公社化的;有文学水平高的,也有文学水平低的;有歌颂的对象是正确的,也有歌颂的对象是错误的。如果笼统地断言这些作品表现了当时“左”的错误,认为今天取消人民公社便说明合作化运动的失败,并推断出作家描写的生活和人物就都不真实,就应该予以否定,那恐怕难以服人。事实上,1957年前农业合作化尽管发生过“左”的倾向,但总体上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只是提倡“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才造成生产力的破坏,这种破坏还与大炼钢铁等大跃进的错误分不开。新时期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并没有完全否定合作化的成果,土地仍然国有,村办企业等集体经济仍然存在和不断壮大。江苏的华西大队、北京的窦店大队等许多村庄更仍然坚持集体经济的道路,并获得很大的成绩。今天,家庭联产承包的局限已使得许多农村又重新走向集约化的经济。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重要的是反映这些运动的文学作品是否写出了历史的真实,写出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才会出现的人际关系和人们的思想感情;另一方面还要看作品文本所具有的文学价值的高低。
文艺作品的艺术真实性与思想倾向性并不是一回事。描写真实的作品,其倾向性可能正确,也可能不完全正确,乃至有相当的错误。列宁在评价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时就既赞扬托氏对俄罗斯农村历史图画的真实描写无以伦比,同时又指出他作品中的思想倾向性的局限,乃至反动。反之,一部作品的思想倾向有问题,也并不等于它的真实性一定有问题。同是列宁在评论被他称为“忿恨得几乎要发疯的白卫分子阿尔卡季·阿维尔钦柯”的小说时,既明确指出他的反革命倾向,又肯定和称赞他写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和人物形象是如何“十分逼真”。(注:《一本有才气的书》,《列宁全集》第33卷,第103页。)谈到十七年表现农业合作化的文学作品,要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比如赵树理的《三里湾》、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三位作家对合作化的描写是有差别的。但不能说他们的作品没有反映当时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真实,更不能由此进一步否定他们所达到的文学水平和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所应占有的地位。
赵树理是20世纪中国的一位重要作家,从《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到《三里湾》等,他以一系列的作品提供了迥异于前人的小说文本,以饶有地方风味的农村口语和富于幽默感的叙述,深刻地表现了我国农村各种农民在特定时代的精神状态,生动地反映了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时期的农村历史变动。他的创作包括《三里湾》为克服新文学的过于欧化的语言叙事,促进我国文学大众化民族化风格的建构,作出重要的贡献。柳青也是曾为新文学贡献了像《种谷记》和《铜墙铁壁》这样农民韵味很浓的作品,《创业史》虽未全部完稿,它却是试图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对前人有所突破和创新之作。它的描写风格和语言由于将农民口语和丰富的书面语交汇熔铸而见清新和优美,从而超越了赵树理的局限,继续将小说的大众化和民族化向前推进。他和赵树理写的都是合作化的初期,通过示范,稳步发展的健康时期。周立波也是新文学的重要作家,他的《暴风骤雨》以东北农村口语描写土地改革,获得广泛好评,《山乡巨变》反映的是合作化后期,即反对“小脚女人”、出现“左”的急躁冒进错误的时期,作家歌颂邓秀梅、批判李月辉,支持“左”的倾向当然不正确。但作品对各种农民的描写异常生动真实,且以浓郁的湖南乡语和细腻的描写风格影响了大批后来的“湘军”。这三位作家的才情和风格各异,但他们长期深入农村生活和对农民的极度熟悉,使他们成为继鲁迅和沈从文之后的真实描写我国农村的大师。他们的作品确实歌颂了新时代的新人新事,批判了反对合作化的种种旧农民。这种思想倾向今天看来也仍然是基本正确的。像梁生宝那样渴望共同富裕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农民就应该歌颂,反对合作化运动的富农姚士杰、富裕中农郭振山就应该批判,即使到今天,反对集体富裕,损人利己,以邻为壑,一心个人发家致富的人,从社会主义利益的价值取向来看,难道还不该批评,反应该去歌颂吗?邓秀梅与李月辉尽管有矛盾,他们在赞成合作化上却是一致的。《山乡巨变》肯定他们这一点还是正确的。上述三位作家的真实艺术描写不愧为“时代的镜子”,从中人们可以看到20世纪中国革命中农村阶级关系的变动与农民运动所表现的时代精神及其优点和弱点。就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而言,这三位作家都是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代表,他们与来自延安的其他作家的作品一起,事实上开创了中国文学的一个新时代,即以工农兵为主人公的人民文艺的时代。
认为合作化运动失败,相应文学作品就应否定的观点所以站不住脚,这是因为姑不论合作化是否失败,如果某种历史运动失败,描写这种运动的作品就要否定,按照这种逻辑,那么描写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和歌颂义和团、辛亥革命的文学作品岂不也一概得否定吗?因为历史证明这些运动也都实际失败了。进而还可以推断描写机会主义路线错误而导致的“大革命”失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在白区革命组织被破坏的作品也统统要否定了,这样一来,还有什么作品值得肯定呢?
倘若我们把视野更拓宽一些,自然不能认为法国1789年的革命者结果纷纷上了断头台,波旁王朝后来又复了辟,雨果的《九三年》就得否定;或者美国的南北战争中南方失败了,名作《飘》就不应载入文学史。还有宋江起义难道不也是失败吗?如果我们因此就认为反映这场起义的《水浒传》也应否定,那不是很荒谬吗?文学史到底不是政治史,政治及其路线的是非成败固然要加以认识,但在文学史中并不重要,文学史最重视的应是文学价值,即作品是否以文学的审美形式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包括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的真实,还有作品所支持和歌赞的人物的精神境界对人类是否具有恒久的珍贵价值。如果是,那么政治上的谬误虽应指出,毕竟不能因此而否定作品的文学地位。
三 文艺与人性、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
文学是人学,它以人的思想、情感、性格、行为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自己描写的中心。因此,它必然无法回避对人性的认识,也必然要有对待人持何种人道主义的态度问题。建国初十七年把人性等同于阶级性,否定人的共性;同时对于人道主义也一概批判,甚至一律冠以“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帽子。自然是片面的,不正确的。文化大革命中人性沦丧,兽道横行,不能说与以往认识的偏颇没有关系。十七年的文学作品中个人利益和个性发展不仅受到忽视,倘若有作品表现,如话剧《布谷鸟又叫了》、小说《英雄的乐章》或《我们播种爱情》,还与人道主义一起受到批判。那时只提倡表现阶级仇、民族恨和集体主义的革命豪情。虽然这些方面不是不应该表现,但这种表现也要通过个性化才有感人的力量。而新时期的20年,由于改革开放,西方思潮日益泛滥。有人又从对人性、人道主义的呼唤走向抽象人性论,并且混淆传统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界限,张扬个人利益至上的人道主义,鼓吹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否定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公而忘私的道德理想,甚至把雷锋精神斥为“非人性”。持此思想倾向者便大肆贬低和否定十七年文学。而某些坚持共产主义道德理想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者,对新时期的许多文学作品也往往采取否定和批判的态度。因而正确对待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的关系,在当代文学研究中非常重要。
在理论界多年的探讨中,人们大多认识到人性既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也是民族性、阶级性和个人性的统一,还是社会意识、文化意识与生命意识的统一。人既处在社会关系和自然关系交叉的历史之网中,正如马克思所说,对具体的人性只能历史地考察,“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④每个时代的具体个人都处于一定民族、阶级、社会集团,包括党派、家庭、朋友关系的网络中,具体人的人性无不具有不同的一定网络关系的影响,因而总是同中有异的。古代奴隶主随便杀害奴隶,被认为是合乎人性的行为,今人就无法赞成。建国初的17年和新时期的20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两个时期在大方向上虽都为人民为社会主义,也都为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但毕竟两个时期的社会结构,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都存在某些差别。17年从多元走向一元;后20年则从一元走向多元。雷锋精神在五、六十年代共产主义精神昂扬的社会主义集体中产生,在八、九十年代私有经济的公司里便难以为人们所理解,但绝不能说雷锋精神就不合乎人性。今天商界存在的损人利己、唯利是图,其实在私有制的社会里已存在几千年,而对此,雷锋那样的青年革命军人却恰恰不理解或很难理解,所以,我们不能说雷锋的人性就是非人性,只有私人企业家的人性才是人性。反之,当然也不能说只有雷锋的人性才合乎人性,而商人的人性就不是人性。实际上就是商人的具体社会关系也不会完全一样。有的商人由于受到的教育或其他影响的不同,也有并不惟利是图,乃至积极奉献社会的。陈嘉庚就是历史上突出的范例。因此在文学的研究中站在今天某一集团唯利是图的立场去否定雷锋的人性,而只承认唯利是图才是人性,那就陷入抽象人性论的泥坑。
产生自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道主义在历史上起过伟大的进步作用。它鼓舞了世界许多国家的人民起来为推翻封建制度,争取人的自由、平等、博爱而斗争。但这种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础正是抽象人性论。它把资产阶级在特定时代的人性当作人性的普遍要求。马克思主义曾经肯定过这种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进步作用,并揭露过它到了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以后的虚伪性。马克思主义通过论证无产阶级革命如何在夺取政权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最终达到消灭工农、城乡、脑体劳动的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去实现人类个性充分发展的真正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目标。这是建立在辩证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科学的人道主义,即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它把个性解放的要求与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集体利益的要求统一起来的人道主义。站在这个立场上,我们完全不必也不应该去否定十七年文学中提倡社会主义集体精神和共产主义道德理想的作品,因为这样的作品中所揭橥的崇高精神境界,将会贯穿和照亮历史的未来。但对那个时期文学忽视尊重个人合理利益以及不承认传统人道主义在反封建方面仍具积极的历史作用而一概加以批判的偏颇和局限,则确实应有认识。对于新时期文学中所出现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要求,要如实地把它看作是多种经济成分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产物,但同时又要清醒地正视它属于历史进程促进生产力发展和一定阶段社会进步的恶的部分。对那些不能全面把握人性,或把趋向私有化的人性当成普遍人性,或把人的生命意识和本能当成全部人性的作品,也必须指出它们对于现实人性认识的偏颇和局限。在人性、人道主义问题上如果我们不能划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线,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就容易成为西方资产阶级思潮的俘虏和应声虫。
江泽民同志在1996年全国文代会和作代会上的讲话中说:“文艺要讴歌英雄的时代,反映波澜壮阔的现实;深刻地生动地表现人民群众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伟大实践和丰富的精神世界。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在自己的作品表演中,贯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崇高精神,鞭挞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在党的十五大的政治报告中他又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今年他提出“三个代表”,即“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应该说这都是我国各族人民前进中最重要的历史导向,也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最重要的价值取向。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在文艺与政治、真实性与倾向性、人性与人道主义等重要问题上坚持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上述历史导向和价值取向,应该说是十分重要的,因而也是我们需要不断深入学习和讨论的。
标签:文学论文; 政治论文; 文艺论文; 人性论文; 政治倾向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艺术论文; 山乡巨变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