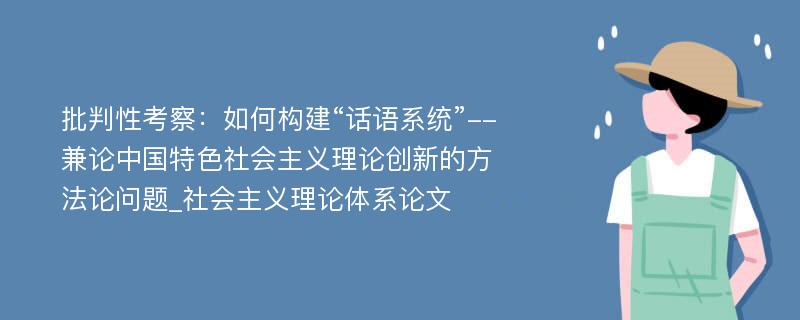
一种批判性的审视:“话语体系”何以能打造——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中的一个方法论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批判性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话语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804(2013)04-0012-08 近年来,为了克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话语危机,各种强烈要求打造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呼声此起彼伏。然而,细微观之,在这种“热闹”的表层下却隐藏着一种深刻的学术危机,即:理论创新在整体上乏力,所以不得不在话语上大做文章。实际上,新的学术话语只是真正的理论创新的副产品,根本用不着去专门“打造”。如恩格斯所言:“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①这就是说,“术语的革命”内含在“新见解”中。进而言之,脱离理论内容的真正创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是打造不出来的。当然,笔者并不否认学术话语及其变化有其自身的特点,但这种特点归根结底是受理论创新规律制约的。要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话语目前的危机有客观、清醒的认识,必须首先批判性地审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内容创新的羁绊。因此,这里提出的问题是:造成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内容创新在整体上乏力,从而导致其学术话语危机的原因是什么。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打算对其中两个最主要的原因(至少从目前来看)加以批判性审视。 话语的主体是人。学术话语的主体是学者或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工作的人。学术话语变革是学术话语主体理论创新及其思维方式变革的直接表现。而这种理论创新及其思维方式的变革绝不是一种纯粹的“话语打造”问题。在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工作的人的学术活动中,首先重要的是学者的价值观。对当代中国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工作的人来说,价值观就是指对待“中国问题”的立场和诉求②。 众所周知,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发展的十字路口上,各种价值观的冲突深深地映现在学界的方方面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面临抉择。我把存在于中国学界的各种价值观大致分为五类。 一是中国“利益固化”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试图把我国改革开放在一定时期内所出现的“双轨制”凝固化和制度化,其主要表现是以各种方式拒绝和阻碍推进全面改革。如果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何谈理论创新。在《资本论》第1卷英文版的序言中,恩格斯批判了古典经济学把除了农业和手工业以外的所有“产业”都归结到“制造业”这个术语中的做法的非科学性和非历史性。这种做法掩盖和抹杀了经济史上两个大的、本质不同时期的区别,“即以手工分工为基础的真正工场手工业和以使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业时期的区别”。由此,他指出:“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做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做是永恒的、最终的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③我以为,在当今中国发展的转折关头,“利益固化”的价值观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创新的阻碍作用最大。这不仅仅因为这种价值观的一些主体控制着许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舆论方面的资源,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基础。 二是中国“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期望以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来改造中国社会,其主要表现是:把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视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路径。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可以算这方面的一个主要代表。把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视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路径,与马克思所说的“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④不是一回事。前者带有“制度性”模仿的特点,而后者则是强调建设新的社会形态的基础性因素。中国的“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往往打这方面的“擦边球”,使人们难以对其有清晰的认识,如它常常在解决“中国问题”方面提出向西方国家学习。应当承认,目前我国在发展的转折时期的确需要批判性地借鉴西方国家有益的经验,但问题是:这种价值观在“向西方国家学习”的口号下,不仅仅是要照搬西方社会发展的“细节”,而且试图把“基本制度”羞答答地“偷运进来”。为此,中国“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把西方学界已经“过时”的和还“没有过时”的术语,一股脑儿搬运进来,在中国学界“兜售”得非常彻底。它往往把对“中国问题”的分析作为对西方理论范式的“注释”,即用“中国经验”证明西方理论范式的“普适性”。 三是中国“民粹主义”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试图开倒车,全面恢复“文革”及其以前的中国社会状况,其主要表现是:打着关注社会底层的旗号,以批判社会不公、腐败横行、道德缺失等为借口,全面否定中国改革的现实和历史。一般说来,中国的“新左派”是这种价值观的主要代表。“关注社会底层,批判社会不公、腐败横行、道德缺失”等,这本身并没有错,问题的关键是其中所体现的价值导向:否定中国改革的现实和历史。为此,中国“民粹主义”价值观在其术语上具有浓厚的“文革”色彩和或多或少的西方“新左翼”之形。应当承认,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中的确存在种种愈演愈烈的矛盾和问题,但这是由改革贯彻的不彻底引发的,与要不要改革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中国“民粹主义”的价值观在方法论上往往把这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混为一谈。事实上,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根本不存在要不要改革的问题。 四是中国“复古主义”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在文化上具有强烈的“怀旧”心态,试图通过以在当今时代确立中国传统文化主导地位作为主要手段,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其主要表现是:主张把中国传统文化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可以缓解乃至消除当代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冲突。这种价值观有三个特点:“文化决定论”——祈望用纯粹的文化来化解当代中国乃至世界所存在的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此其一。其二,“中国文化中心论”。这实际上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翻版。其三,“幻觉式”的时空错位,以为当代社会的矛盾和问题在古代不存在,故就应该在思想观念上回到古代(似乎思想观念一回到古代,当代社会的矛盾和问题就不存在了)。中国“复古主义”价值观的问题所在,应是不言而喻的。正因为如此,这种价值观的学术用语离“现代中国”乃至“现代世界”是很“遥远”的。当然,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优秀成分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资源⑤,对此绝不能小觑,但这与中国“复古主义”价值观的主张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五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价值观。恩格斯在1890年8月21日致奥托·冯·伯尼克的信中说道:“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⑥因此,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价值观最根本的特点就在于:把中国社会主义社会视为“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坚持把不断深化改革视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我认为,这种价值观在当前的主要表现是:强调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等的全面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展开,以此使中国全面超越“瓶颈”状态(当然,在具体操作层面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这种价值观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发展过程视为“间断性”与“非间断性”有机统一的过程。它既不菲薄改革以前的历史,也绝不留恋过去;既不美化改革的现实,也绝不因改革中的问题而退缩;既拒斥亦步亦趋地走西方社会发展道路,也注重批判性地汲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 毫无疑问,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应选择第五种价值观,拒斥前四种价值观。因为,归根结底,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真正创新只能出自于这种价值观导向。然而,就我个人认为,目前问题的严峻性在于:由于种种原因,第五种价值观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创新中有被“边缘化”的危险。我以为,至少从目前来看,这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创新的一个问题。 说到这里,如果再回到本文开头所说的“深刻的学术危机”,即“由于理论创新在整体上的乏力,而不得不在话语上大做文章”,那么蕴涵在其中的意思也就更明确了:把打造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作为一种独立的口号提出来,这本身就是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创新危机的直接表现。在一定意义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在学术话语方面表现出来的“苍白”,是其内容“苍白”的直接表现。或许有的人会对笔者的上述看法提出质疑:难道新的理论或理论创新不需要新的话语吗?当然需要,但它不是独立打造出来的,而是内容创新的一种自然显现。如果我们不解决“内容”问题,而只是在“内容”的表现形式方面“下工夫”,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目前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不是内容丰富而话语缺失的问题,而是整体创新乏力但却把“话语打造”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的问题。在这种表面繁荣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价值观和“中国问题意识”的缺失。“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⑦话语危机乃是思想乏力的直接表现。如果我们不在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上全力以赴,而只在“话语打造”上大张旗鼓,其结果必然是使思想越来越贫乏。 由上可见,人文社会科学工作主体的价值观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导向作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价值观的确立程度,在整体上决定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程度。当然,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价值观并非是明确后就能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中自然而然地确立起来的,它需要通过一系列中介环节才能在具体的理论创新中表现出来,其中最为重要的环节就是“理论彻底”。 在当前中国学界,“话语打造”是与“理论自觉自信”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现在的逻辑是:只有理论自觉自信,才有“话语打造”;只有“话语打造”,才能坚持理论自觉自信。实际上,这两者没有什么直接的内在联系。理论自觉自信缘于理论彻底。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⑧何谓“理论彻底?”我以为,它有两个相互联系的基本特征:理论的科学性,理论的相对完备性。当然,“理论彻底”是相对的,它永远不是一个完成了的状态。 对于当代社会主义中国来说,“理论自觉自信”首先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自觉自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自觉自信是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理论自觉自信的核心。如果缺乏对这一理论的自觉自信,那么我们的“理论自觉自信”就会遇到严峻的挑战。目前我国从上到下非常强调理论的自觉自信,这也从一个层面说明,我们遇到了“理论自觉自信”方面的危机。而克服这种危机是根本不可能靠“话语打造”的,而要靠“理论彻底”。只有理论彻底,才有理论自觉自信;只有理论基于现实、批判现实和超越现实,才有理论彻底。那么,既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彻底”吗?我的回答是:既“彻底”又“不彻底”。无论否认前者还是否认后者,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说它“彻底”是指:在科学揭示当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及其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方面是彻底的。说它“不彻底”是指: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深入以及解决“中国问题”的迫切性日趋凸显,既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难以全面阐释当前中国深层矛盾形成、发展和解决的复杂性,故在一些重要环节上需要创新。因论题和笔者能力所限,本文仅打算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中的一个重要方法论问题陈一管之见,以进一步说明: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引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远不是所谓“话语打造”问题。 笔者这里所说的关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中的一个重要方法论问题,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问题。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这是完全正确的。从方法论上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必须有一个衔接点,否则,“辩证统一”就没有学理根据,从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学理依据也就无从谈起。何谓“衔接点”?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衔接点”就是指“交汇”场所,这个场所显示了“统一双方”有差异的融合。这个“衔接点”是需要学界下苦功夫、花大力气来研究的。我以为,这里首先必须在方法论上搞清楚“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各自的确切涵义是什么。 何谓“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1874年,在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中,俄国民粹主义中最激进流派的代表彼·特卡乔夫⑨,责备恩格斯对“俄国没有‘丝毫知识’,相反地,只表现出‘愚昧无知’”,断言:俄国既没有无产阶级,也没有资产阶级,因而“可能轻而易举地、比西欧要容易得多地实现社会革命”。恩格斯1875年4月在《人民国家报》第43、44和45号上发表连载文章,在驳斥特卡乔夫谬论的过程中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作了这样的概括:“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野蛮人和半野蛮人通常也没有任何阶级差别,每个民族都经历了这种状态。我们决不会想到要重新恢复这种状态,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状态中必然要产生阶级差别。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可以持续下去,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甚至倒退。但是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程度。可见,就是从这一方面说来,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断言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那就只不过证明,他还需要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⑩毫无疑问,恩格斯以上所精辟概括的由马克思和他共同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是科学的。 何谓“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我以为对其可以作这样的简单概括: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发展到一定阶段上(即“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和现代化因素在中国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受列强的各种方式的干涉以及军阀割据和腐败统治的阻碍,中国既无法获得民族独立和解放,也走不了相对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故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和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选择了走新民主主义发展道路,并在取得全国胜利的7年后开始进行了最初的社会主义建设,尔后,通过曲折中的发展和挫折(从中汲取了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最终在一定的国际环境中走上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之路。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延伸的必然结果。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凸显的是“真理性”;“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凸显的是“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强调的是一个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不可逆性。而在考察“科学性”与“必然性”间的辩证统一、揭示其“衔接点”时,最忌讳的就是或用前者去硬套后者,或把后者作为前者的一个简单例证。我以为,如果要正确考察“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辩证统一、揭示其“衔接点”,就必须构建新的解释系统,而这种解释系统既不能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中直接搬来,也不能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中直接搬来,否则就会出现种种不能自圆其说且容易被各种错误思潮钻空子的“漏洞”。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其真理性一直被近现代世界历史及其发展总趋势所证实;“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其必然性是断然不可能为各种“假设”所推翻的。但问题是:资本主义及其发展程度,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之间的一道似乎难以跨越的“屏障”。为了“消除”这一“屏障”,基于不同理念的解释系统便应运而生了。其中有两个解释系统在我国学界最具有代表性。 第一种解释系统的思路:“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东方社会发展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这是我国学界解释系统的一种思路。应当说,这一解释系统思路有其一定的合理因素,对我们在一定时期内认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从而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有一定意义的。但其也有明显的“漏洞”。随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这种“漏洞”越来越凸显出来。首先,马克思晚年“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设想,其对象指的仅是已经被俄国资本主义包围的、尚未解体的“俄国村社”,而不是整个俄国(在当时的马克思看来,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虽然尚未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实际上,马克思对“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所设定的条件是非常科学和严格的,如:西方无产阶级率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俄国的人民革命在适当的时候发生(与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相配合”)等。惟其如此,其内部还尚未有资本主义因素的俄国农村公社才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否则“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就是一种民粹主义的空谈。可以认为,马克思关于俄国农村公社“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条件特别是“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的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在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俄国革命形势中的一种表述,也可以认为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的重要补充。因此,其二,从“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引申出所谓“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是很不严肃的。至少今天的世界历史发展表明,东方社会或非欧社会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发展道路。所以,其三,把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视为“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视为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代表,当然也就是不科学的。 第二种解释系统的思路:社会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产物→任何民族国家都必须成为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中国特色的“社会民主主义”或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即便要搞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社会主义”,那也是以后的事情。应当说,这种解释系统的思路在整体上是错误的,其主要缘由是:把资本主义及其发展同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混为一谈,把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等同于资本主义制度;同时无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间的联系。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是正确的,并一再被当代世界历史发展所证明。没有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范围的发展,就不可能有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但问题是:对于某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来说,在具备了一定的条件下如何通过自身的努力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把社会生产力和整个社会发展到使消灭阶级差别成为真正的进步,而不至于使“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在各个方面“死灰复燃”(这对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经济相对落后国家威胁最大)的程度。这在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中是不能找到现成的具体答案的,必须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之间构建新的解释系统。这一解释系统的核心内容就是:批判性地汲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但必须尽可能地减少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所经历的一切可怕波折和苦难,从而真正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这正如列宁所言:“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11)进而言之,“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显示其本来应有的面貌。 对上述“核心内容”的确定,是以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这样一种复杂关系为其逻辑前提的,即最初的不很成熟的局部性的社会主义的发展(12)、批判性地汲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与铲除内部所存在的封建主义的因素和力量间的关系。20世纪初期以来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表明:对既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大、最严峻的挑战往往不是来自于资本主义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来自于其内部存在着的大量的前资本主义的因素和力量(它们深深地积淀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围绕着“核心内容”,上述解释系统至少应对四个相互联系方面的问题作出科学回答(或探索):如何科学定位最初的不很成熟的局部性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间的关系?如何科学定位最初的不很成熟的局部性的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腐朽、没落的因素和力量间的关系?如何科学定位批判性地汲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与发展资本主义的关系(包括在什么意义上和如何发展资本主义)?在观念上层建筑方面如何正确地体现对上述这三种关系的引导和驾驭? 对这四个相互联系方面问题(第一个方面问题是这四个相互方面问题中的核心)的科学回答,是正确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辩证统一“衔接点”的四个重要构成环节。我以为,如果这四个相互联系方面的问题在方法论上搞清楚了,那么我们不仅会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的规定性,同时也会在全面、正确认识“中国问题”方面把已取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果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而伴随这种推进,我们也必将会在解决“中国问题”方面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 当然,上述这四个相互联系方面的问题,涉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关系的方方面面,故对其全面探讨,并作出科学回答(这既是一个重大的基础理论性课题,又是一个重大的现实性课题),是本文所不能完成的,也是笔者所不能胜任的。但至此,笔者撰写该文的目的应该说是讲清楚了,即:不要执著于什么“话语打造”,而要树立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价值观,踏踏实实地研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中国问题”,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并以此来带动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性发展。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在国际学界获得自己应有的话语权。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页。 ②我曾在有关文章中指出,“中国问题”由两个相互联系的部分构成:“中国‘从何处来’”和“中国‘往何处去’。”“中国问题”的历史跨度是相当大的,其内容涉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并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但至少在目前和可以预料的将来,“中国‘从何处来’”是指:目前在全球化发展中的中国所遇到和积累起来的深层次的、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矛盾和冲突是如何形成的。这些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愈演愈烈,从而构成了发展的瓶颈。在这个瓶颈中,我们既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基本解决的问题(如“官本位”或“等级本位”体制的问题)所严重困扰,也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如真正实现从形式到内容的平等、自由、公正、正义等)所严重困扰。“中国‘往何处去’”是指:目前我国如何走出发展的瓶颈,即发展的具体路径和方向在哪里。“中国问题”既有其独特性,也有其世界历史性。(参见叶险明:《马克思哲学的话语革命与中国哲学的话语危机》,《哲学研究》2012年第12期)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7页。应当说,在“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方面,我们还是做得远远不够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笔者将另撰文细论。 ⑤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请参见叶险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与当代中国先进文化》,《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2008年第1期。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8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25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页。 ⑨俄国民粹主义大体分为三大流派:“宣传派”(拉甫罗夫为代表),“暴动派”(巴枯宁为代表)和“夺权派”(特卡乔夫为代表),其中以特卡乔夫为代表的“夺取派”最为激进。当然,这三个流派在基本思想原则上是息息相通的,即:崇尚人民运动,美化农村公社,把俄国社会特点绝对化,企图通过所谓特殊道路(公社途径),绕过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9~390页。 (11)《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52页。 (12)笔者这里所说的“最初的不很成熟的局部性的社会主义”,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种世界历史性的表述。标签: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社会价值观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理论创新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科学论文; 中国社科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