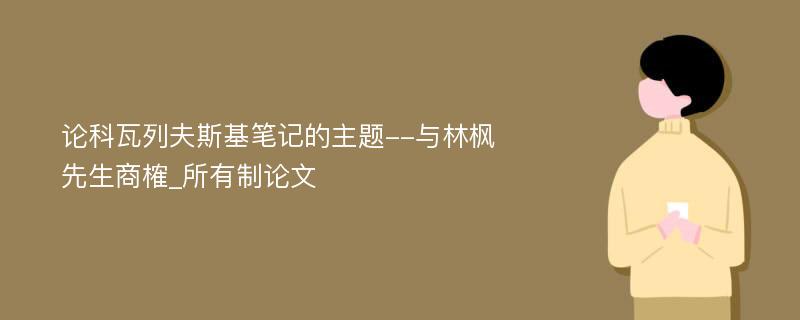
也谈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主题——与林锋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基论文,也谈论文,列夫论文,笔记论文,主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0)08-0075-08
拜读林锋先生的《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主题新探》①(以下简称“林文”)一文,有启发,但更多的是疑虑与困惑。笔者不敢苟同林文所言柯瓦列夫斯基笔记② 主题是“探索人类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③ 的说法。因为通读林文,丝毫也看不到有说服力的材料来证明其论点的正确性,却常常发现林文对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甚至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以下简称《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的误读。以下就围绕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的主题,同林锋先生商榷并求教学界同仁。
一
林文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介绍柯瓦列夫斯基从事公社及其所有制问题研究,进而创作《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的“思想动力”、“研究思路”、“研究目的”等问题。这些问题尽管也很重要,但毕竟是属于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的问题,而非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的问题。可以说这方面的考察对于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主题而言,只能是属于外围方面的探索。
而林文的第三部分,实际上也是离开对柯瓦列夫斯基笔记文本的考察,重点在于论述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与马克思晚年其他笔记④ 的关系上。
林文真正涉及柯瓦列夫斯基笔记文本的是在其第二部分。这一部分共有七个自然段,却有五个自然段并非从柯瓦列夫斯基笔记文本来进行“主题新探”的,只是到了这一大部分的最后两个自然段,才触及到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的文本。就是在这最后两个自然段中,在总共只有四个引言中,真正只有两个引言是来自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但这两个引言也仅仅是马克思的摘录而非马克思写下的评注。而另外两个,一个是引自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⑤;另一个没有完整引自柯瓦列夫斯基笔记,只是作为“参见”⑥ 而已。
真令笔者难以置信,林文仅仅依据这寥寥无几的文本根据就探求出了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的主题。笔者拜读林文并对照柯瓦列夫斯基笔记,发现即使是林文仅有的两处引文,却还存在着对马克思摘录本意的误读。
林文是这样引述的:“比如,在印度,‘公社所有制不是某个地区独有的,而是占统治地位类型的土地关系’,‘除印度以外,保存下来的古老形式的土地所有制痕迹要算阿尔及利亚最多。在这里,氏族所有制和不分居家庭所有制是占统治地位的土地所有制形式’”。⑦ 在引述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的上述两段话后,林文就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对这些国家的公社及其土地所有制的材料作大量摘录,其意图十分明显,就是试图以这些国家的公社及其土地所有制形式中大量残存的原生公社、原始土地公有制痕迹为线索和依据,来揭示和还原人类原生公社及其土地制度的本来面目和基本特征。”⑧ 在此,笔者不赞成这种为达到论证自己观点而近乎于用断章取义的方式来对文本进行引用与解读。其实,如果我们认真研读柯瓦列夫斯基笔记,就不难发现林文所引第一段的引文,马克思在作摘录时,其真正“意图”并非如林文所言。
林文第一段引文的那一段话,在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的“Ⅱ·英属东印度”的“(E)英国人的专横统治及其对印度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影响”⑨ 中。只有忠实于文本,才能对引文作出正确的解读。笔者在此不妨引用马克思在这一部分的相关摘录与批注来说明问题。其实更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是马克思的批注,这也许会较为真实地探究出马克思的本意。
马克思在摘录“公社所有制并不是某个地区独有的,而是占统治地位类型的土地关系”这段话时,前面特意加了个评注:“英国‘笨蛋们’逐渐意识到”⑩,这表明马克思对英国统治者的蔑视。因为印度在被英国征服之前,还完整地保存着大批的农村公社。“这些团体往往都是由同一世系和共同占有而联合起来的数千人组成的”(11)。而现在,英国的统治者“出于政治的和财政的考虑”(12),却要蓄意地破坏公社土地所有制。英国人采取旧土地登记和土地局部订正的措施,对农民进行直接的掠夺。表面上看,“其目的是在扩大公社土地占有制的原则;进行订正的出发点也不是私人土地占有制,像以前那样,而是把公社土地占有制当作占统治地位的类型。占有的时效被承认是土地属于农村公社的不可争辩的证据,而对于声称对土地有所有权的私人,则要求他提出购买土地或穆斯林政府赐予土地的文字契据。”(13) 但实质上,正如马克思批注所指出:“于是,公社所有制原财上得到了承认;实际上被承认到何种程度,过去和现在总是要看‘英国狗’认为怎样做才对自己最为有利。”(14) 英国政府是用强制手段把农村公社分为分区的,而且,在大多数公社中采取各种措施,“明确规定各人在耕地中应有的份地和每个纳税者在公社应纳的总税额中所占的份额。”(15) 英国人之所以把公社按区分割,就是要削弱互相帮助和互相支持的原则,然而,“这是公社——氏族团体的生命攸关的原则。”(16) 因为“地广人多的公社,特别有能力减轻旱灾、瘟疫和地方所遭受的其他临时灾害造成的后果,往往还能完全消除这些后果。他们由血缘关系、比邻而居和由此产生的利害一致结合在一起,能够抗御各种变故,他们受害只不过是暂时的;危险一过,他们照旧勤勉地工作。遇到事故,每一个人都可以指望全体。”(17) 英国人正是看到了这一原则对于公社成员的重要性,才把公社分割为面积小得可怜的分区。英国政府“把公社土地分割为各分区以后,接着就是把大多数公社和分区的耕地也分割为各个家庭的私有财产。”(18) 如此一来,就使公社原有的共同责任和亲属原则被破坏殆尽。马克思写下批注评论说:“这种情况,在农村公社被强制分割以后就完全消失了”(19)。马克思在此主要是摘录柯瓦列夫斯基原著中有关描述英国殖民者是如何采取各种手段破坏印度原有的公社土地所有制,同时还表明了马克思的看法。应该说,柯瓦列夫斯基笔记自始至终都充满了对外国殖民主义者破坏公社土地所有制的野蛮行为的严厉谴责。所以,马克思在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中,把柯瓦列夫斯基原书内的小标题“英国在东印度的土地政策及其对印度公社土地占有制解体所产生的影响”、(20)“法国征服时期阿尔及利亚土地占有制的各种形式”(21),统统改成“英国人的专横统治及其对印度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影响”(22)、“法国人的专横统治及其对当地集体土地占有制衰落的影响”(23)。对殖民主义者野蛮行径的谴责,这一点,马克思在这一部分摘录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因此,林文所引述的马克思那一段的摘录,绝非要表达林文所断言的“意图”。
在林文第二部分的最后一个自然段中,林文提出这样的看法:“马克思在这一笔记中,还运用比较研究法,探索了原始公社在人类历史上的演进轨迹、解体过程以及土地私有制的起源过程。在运用上述方法揭示原始公社的发展轨迹及土地私有制的起源过程上,马克思和柯瓦列夫斯基具有一致性。”(24) 笔者根本无法赞同林文的上述看法。因为,第一,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的主旨根本就不是“揭示原始公社的发展轨迹及土地私有制的起源”。关于这一点,林文的第一部分中就存在着错误看法。林文的第一部分着重引用《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前言”中的三段话,说明“柯瓦列夫斯基研究公社及其土地所有制问题、创作《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主要是与他探索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的理论初衷、研究目的有关”。(25) 笔者认为,柯瓦列夫斯基对于自己著作“研究目的”的表达并不在“前言”中,而是在该书的“绪论”里。柯瓦列夫斯基在“绪论”里明确写道:“我一次又一次地研究过我们通常称之为封建化过程的那种复杂历史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封建化过程,并没有构成某个民族或种族绝无仅有的特点。如果说这一过程对于日耳曼——罗曼世界以外古老生活方式的解体所产生的影响,至今还没有弄清楚的话,那只是因为西欧大多数历史学家和法学家,对于欧洲东部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土地关系的发展进程,都还了解不够的缘故。为了在某种程度上填补这一空白——这就是我出版本书第一分册的任务。”(26) 这就明白无误地表明,柯瓦列夫斯基创作《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其主旨就是指出: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公社土地所有制在不同程度上都经历了与西欧一样的封建化过程。
第二,马克思运用的方法与柯瓦列夫斯基根本不同。柯瓦列夫斯基为了论证其理论主旨,常常把亚、非、美洲各古老民族社会历史的演变同西欧作机械的类比,而这则是马克思所坚决反对的方法。马克思在作摘要时主要采用如下的方式进行处理。一是予以删除。马克思在写作柯瓦列夫斯基笔记时,就全部删去了柯瓦列夫斯基原著中的“绪论”,以后凡是遇到柯瓦列夫斯基作这种比附的地方,马克思就将其予以删除。例如:马克思删去了柯瓦列夫斯基在描述14世纪印度菲罗兹统治时期赏赐土地给军官、行政官员、僧侣和慈善机关所说的一段话:“由此可见,在菲罗兹统治时期印度在封建制度方面所完成的变革,与加洛林王朝秃头查理所进行的变革大体相同。”(27) 二是提出批评。马克思在对柯瓦列夫斯基“封建化”问题上批评最多。特别是,当柯瓦列夫斯基把公元8至18世纪印度的阿拉伯统治者和莫卧儿王朝封赠军功田(采邑),实行公职承包制、荫庇制都说成是“封建化”的时候,马克思写下了大段的评语对柯瓦列夫斯基进行了批评(28)。三是进行改写。柯瓦列夫斯基对于印度土地所有制的封建化过程有个结论性的表达:“我只是想说明:在英国人占领时期印度的封建化过程还远远没有完成”,(29) 马克思在作摘要时,就把“封建化过程”改写为“所谓封建化”(30)。
二
笔者认为,要正确解读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的主题,首先还是要以文本作为主要依据。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柯瓦列夫斯基原著中的前两章,马克思将原著中的两章的标题分别改写为:“美洲红种人(他们的公社土地占有制)”(31) 与“西班牙在西印度的土地政策及其对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大陆公社所有制的瓦解所产生的影响”(32),然后分2小节进行摘录。第二部分实际上是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的主干部分,它包括了柯瓦列夫斯基原著的第三至七章的丰富内容,马克思用“Ⅱ·英属东印度”(33) 的标题作为统揽,然后分为(A)(B)(C)(D)(E)5个小节进行摘录。第三部分是摘录柯瓦列夫斯基原著的最后两章,马克思冠之以“阿尔及利亚”(34) 的标题,然后分为2小节进行摘录。以下就以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上述三大部分的划分为序,试探求其主题。
在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第一部分第1小节中,马克思首先摘录有关人类社会的原始群状况:“人类社会的原始群状况,没有婚姻和家庭;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共同生活和相同的营生(如战争、狩猎、捕鱼);另一方面,则是母亲及其亲生子女之间的骨肉关系。”后来“由于这种状态逐渐自行瓦解,就发展出氏族和家庭。”“随着单个家庭的组成,也产生了个人财产,而且最初只限于动产。”(35) 如马克思所批注与摘录的,随着岁月的流逝,时间的推移,私有财产的范围日益扩大,由衣物、工具、武器发展为个人驯养物、个人猎获物,包括战俘、奴隶、妻子等等(36)。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私有财产产生的初期,土地并没有私有化。接着马克思从土地占有制形式来考察人类原始群状态中的土地占有制。发现在整个墨西哥和秘鲁定居的红种人部落中,在其被西班牙征服之前,土地占有制的最古老形式是“氏族公社”(37),这种公社称为“卡尔普里”。“卡尔普里的土地是全体居民的共同财富。”(38) 氏族土地占有制瓦解的重要因素是“份地”形式的出现。当然,“份地”并不是自开始就有的,直到苏里塔时代才出现“份地”。(39) “份地”的出现促使原土地占有形式瓦解,这种情况,在西班牙人来之前就已存在,西班牙人的到来只是加速其瓦解的进程。
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第一部分的第2小节也就是柯瓦列夫斯基原著的第二章的内容。马克思在此的摘录,集中于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西班牙在西印度群岛的土地政策;二是西班牙的这些政策对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大陆公社所有制的瓦解所产生的影响。“西班牙人的最初政策,目的在于消灭红种人。”(40) 到了16世纪初,迫于形势和利益的需要先后推出“瓜分制”和“监护制”。“根据瓜分制度,整个墨西哥在16世纪下半叶被划分为80个区。”(41) “瓜分制度,换言之,即将印第安人变为奴隶,现在则代之以监护地制度。”(42) “监护地制度”就是西班牙当局在原来按等级品位而划分的大小不同占领区内,增派特别联络员,它是由西班牙“皇家印度事务委员会”(43) 派驻各占领区的“特使”。无论是瓜分制还是监护制,都是在承认西班牙殖民当局最高统治的前提下,强占殖民地的领土,宣布为西班牙所有。或是划区独占,或是在各级占领者之上、之外再增派监督员,其目的就是尽可能多地使钱财、税贡进入国库和殖民者的私囊。马克思在此部分的摘录中,特别注意西班牙人的政策对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大陆公社所有制的瓦解所产生的影响。“早在16世纪中叶,在墨西哥和秘鲁的许多地方,农村公社已不复存在了。但它还没有完全消失。它存在于查理二世的立法中:‘公社财产包括由该居留地的印第安人占有之财产,这种财产应当用之于公,保存在该地并应予以增加。’公社也出现在现代旅行者的记述中。”(44) 在马克思看来,农村公社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印第安人眷恋这种最适合于他们的文化阶段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另方面是由于在殖民者的立法中(与英属东印度不同)没有使公社成员能够出让属于他们的份地的法令。”(45)
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的第二部分也可说是其主要与重点部分。马克思在此摘录了柯瓦列夫斯基原著中的第三至第七章,共计5章的丰富内容。按李毅夫、金地译的《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来看,这5章共计有94页,而其余4章加起来也不超过61页。而若以《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一书中的柯瓦列夫斯基笔记来进行计算,则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的第二部分内容占有75页之多,而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内容加起来也只有46页。而且不仅仅如此,马克思在此围绕公社土地所有制这一核心问题,大量摘录:集中考察了与这一核心问题紧密联系的,诸如公社演变、土地制度、社会性质及其发展道路等重要问题。
——概述演变历程。马克思在摘录柯瓦列夫斯基原著的第三章时,首先将其原标题的“土地占有制”(46)改为“土地所有制”,用“(A)按历史上发生的顺序看印度现代公社所有制的各种形式”(47) 作为小节标题。在摘录这小节的最后部分,马克思对公社的演变历程进行了概括性的复述和补订。马克思写道:“总之,过程如下:(1)最初是实行土地共同所有制和集体耕种的氏族公社;(2)氏族公社依照氏族分支的数目而分为或多或少的家庭公社[即南方斯拉夫式的家庭公社]。土地所有权的不可分割性和土地的共同耕作制在这里最终消失了;(3)由继承权[即由亲属等级的远近]来确定份地因而份地不均等的制度。战争、殖民地等等情况人为地改变了氏族的构成,从而也改变了份地的大小。原先的不均等日益加剧;(4)这种不均等的基础已不再是距同一氏族首领的亲属等级的远近,而是由耕种本身表现出来的事实上的占有。这就遭到了反对,因而产生了:(5)公社土地或长或短定期的重分制度,如此等等。起初,重分同等地包括宅院(及其毗连地段)、耕地和草地。继续发展的过程首先导致将宅旁土地[包括毗连住所的田地等等]划为私有财产,随后又将耕地和草地划为私有财产,从古代的公共所有制中作为beauxyestes(美好时代的遗迹——编者注)保存下来的,一方面是公社土地[指与已变成私有财产的土地相对立的][或者原先只是附属地的土地],另一方面则是共同的家庭财产;但是这种家庭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也越来越简化为现代意义上的私人的(单个的)家庭了。”(48)
——考察土地制度。马克思在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第二部分的“Ⅱ·英属东印度”(B)、(C)两个小节中着重对印度的土地所有制关系进行了考察。(B)小节主要是从土地关系史层面进行考察。其跨越时间很长,从公元前9世纪“直到莫卧儿帝国时期(1526-1761年)”(49)。而(C)小节则侧重对土地制度中主要类型——教田和军功田(采邑田)——尤其是对军功田进行了重点考察。马克思之所以重视对军功田有关资料的摘录,是因为在柯瓦列夫斯基看来,军功田特别是地亩税促进了印度的封建化,马克思对此持不同看法。柯瓦列夫斯基笔记较详细地摘录了有关军功田方面的资料。柯瓦列夫斯基笔记记叙了三种类型的军功田。第一类军功田“把土地或有一定收入的项目分配给受田人,作为其完全独有的财产。”(50) 这类军功田的特点是以被征服田、荒地为基础,宣布其归征服者国家所有,再由伊玛目分赠给有功军民,占有者只须缴纳一定的地亩税就可以了。第二类军功田也是由伊玛目所恩赐,归军功人员个人所有,但在权限、时间上都有限制。这类军功田,“在最优惠的情况下,亡人的家庭也只能指望从当局方面领取终身的赡养费。”(51) 第三类军功田是指在一定领地的一定特权,比前两类则更为逊色。按规定受田人“有权与领地管理机关一起享有下述设施:(1)采矿工业,(2)盐、石油、硫磺等矿产地,(3)道路、集市、磨坊。这些设施中,有一些设施的享用权只是以征收某种款项的方式实现的;例如,集市、道路等等就是这样。”(52) 对于军功田在印度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马克思没有同意柯瓦列夫的观点,柯瓦列夫认为,在穆斯林征服者统治之下,军功田的授予使先前的土地“占有者由自由人变为依附人,同时,他们的占有也由对自主地的占有变为封建的占有。”(53) 马克思对这种说法不能接受,认为:“柯瓦列夫斯基整个这一段都写得非常糟糕”(54)。
——揭示社会性质。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第二部分“Ⅱ·英属东印度”部分的(D)、(E)和第三部分“阿尔及利亚”,涉及了对一些古老亚、非国家社会性质的揭示。农业社会的性质主要是由土地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的。柯瓦列夫斯基考察亚、非等一些古老国家的公社土地所有制的演变过程,认为这些变化是封建主义性质的。作为欧洲中心论者的柯瓦列夫斯基,照搬西欧模式,认为印度的封赠军功田(采邑),实行“公职承包制”和“荫庇制”,就是西欧意义上的封建主义。对此,马克思写下了晚年笔记中最长的一段批注,对柯瓦列夫斯基提出了严厉批评:“由于在印度有‘采邑制’、‘公职承包制’(后者根本不是封建主义的,罗马就是证明)和荫庇制,所以柯瓦列夫斯基就认为这是西欧意义上的封建主义。别的不说,柯瓦列夫斯基忘记了农奴制,这种制度并不存在于印度,而且它是一个基本因素。(至于说封建主不仅对非自由农民,而且对自由农民的个人保护作用,那么,这一点在印度,除了在教田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很小的)(罗马——日耳曼封建主义所固有的对土地的崇高颂歌,在印度正如在罗马一样少见。土地在印度的任何地方都不是贵族性的,就是说,土地并非不得出让给平民!)不过柯瓦列夫斯基自己也看到一个基本差别:在大莫卧儿帝国特别是在民法方面没有世袭司法权。”(55) 那么,像印度这样的一些亚、非古老国家究竟是什么样性质的社会呢?马克思把印度视为“实行非资本主义生产并以农业为主的国家”。(56) 而在谈及阿尔及利亚时,则用“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57) 来表达。可见,马克思是反对柯瓦列夫斯基根据一些非本质的特征把亚、非一些古老国家的社会比附为西欧的封建社会形态。这就是马克思在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中对这些国家社会性质的揭示。
——谴责殖民行径。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的“Ⅱ·英属东印度”中的“(E)”部分是马克思对柯瓦列夫斯基原著第七章的摘录。在这里,马克思指出“英国人的专横统治”(58) 并没有促进新的社会因素的产生,而是给被压迫的国家与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英国统治者在印度人为地破坏公社所有制,扶植大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整理”等政策,除了使当地居民陷于破产,迫使“农民举行一系列的地方性起义”(59) 之外,根本就没有在农业中发展什么资本主义经济,他们在长期的“专横统治”中“任何有利于农业的事都没有做。”(60) 而且,由于英国统治者破坏了公社土地所有制,使得公社所有者分裂成了“原子”,“也就人为地破坏了公社的人员组成和公社的建立在邻里关系上的团结原则”(61),他们由此而失去了原有的公社和其他各种统一体的依托,加上侵入公社的“高利贷者尽其所能在公社社员中支持并挑起新的纠纷”,使当地居民深陷无休止的“法律战争”(62)之中。马克思认为,英国殖民者对印度公社制度的破坏,将使印度社会开始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63)。这场战争无疑将使印度社会进入一个漫长的痛苦的过程。尽管马克思的这些话是在摘录有关印度情况时写下的,但无疑是对柯瓦列夫斯基笔记所涉及亚、非国家历史命运的写照。这难道就是他们未来的命运吗?而这个问题始终萦回于晚年马克思的脑际。
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的第三部分包括柯瓦列夫斯基原著最后两章的内容,马克思冠之以“(Ⅲ)阿尔及利亚”(64) 的标题。此部分马克思着重在于摘录、考察阿尔及利亚的公社占有制以及法国殖民化带来的影响。它由两小节构成。在第一小节“(A)阿尔及利亚在被法国征服时期的各种土地占有制”(65) 中,马克思首先考察了阿尔及利亚残存的公社土地占有制。马克思记下:“除印度以外,保存下来的古老形式的土地所有制痕迹要算阿尔及利亚最多。在这里,氏族所有制和不分居家庭所有制是占统治地位的土地所有制形式。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最后还有法国人长达若干世纪的统治——如果不算最近的一个时期,即从官方说自1873年法律以来的时期——都没有能够摧毁血缘组织和以血缘组织为基础的地产不可分和不可出让的原则。”(66) 这表明,原始公社土地占有制在非洲大陆同样存在过,同样的漫长,同样的符合规律。马克思认为:“如任何地方一样,各种集体形式的土地占有制的解体是由内部原因引起的;在阿尔及利亚的卡比尔人和阿拉伯人中,这种解体过程由于16世纪末土耳其对该地的征服而大大加速。”(67)
在第三部分的第二小节“(B)法国人的专横统治及其对当地集体土地占有制衰落的影响”(68) 中,马克思首先驳斥了法国殖民者认为在阿尔及利亚确立私有制是他们历史功德的荒谬观点。马克思在摘录“确立土地私有制,是政治和社会领域内任何进步的必要条件”这一句话的中间,插入了“在法国资产者看来”(69) 这么个批注,表明了马克思的看法和立场。“法国人在征服阿尔及利亚部分地区以后所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大部分被征服的领土为(法国)政府的财产。”(70) 而且,法国殖民者还通过各种方式使阿尔及利亚氏族土地尽落入其囊中,这才是法国资产者所宣扬的在阿尔及利“确立”私有制的实质。法国人入侵阿尔及利亚所实行的一系列政策,遭到阿拉伯人、卡比尔人的强烈反对,反对殖民者破坏他们的宁静生活和残酷掠夺,反对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斗争的焦点是土地。也正是由于这种斗争和复杂的现实,法国人“觉察到仍然具有充分生命力的公社——氏族土地所有制这一事实。”(71) 这样,瓦解、摧毁公社占有制就成了法国殖民政策的目标。
通过上述对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的大致梳理、概述,不难看出柯瓦列夫斯基笔记所要研究、探讨的主题根本就不是林文所言的“是探索人类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72) 马克思在此着重要研究的是亚、非、美洲等古老国家的公社演变、土地制度、社会性质及其发展道路等问题。这实际上就蕴含着思考和探讨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未来前景等问题,否则很难设想,马克思在此后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等重要著述中,对俄国未来的发展前景、社会革命道路等问题会有那么多深刻思考与闪光思想,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在本文的第三大部分作重点论述。
三
林文的第三部分提出了这样的看法,认为“晚年马克思正是以摩尔根笔记为核心,以其他四个笔记为辅助,全面、系统地探索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与梅恩笔记、拉伯克笔记、菲尔笔记一样,其实都是马克思晚年最后时期为实现‘根据世界人类学最新成果,系统探索和制定唯物史观——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理论’的宏伟研究计划而作的重要辅助性笔记。”(73) 笔者不赞成林文的这种说法。因为这不仅是对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主题的误读,同时也降低了对柯瓦列夫斯基笔记重要意义的认识。
笔记认为,对于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主题的把握,在注重文本考察的同时,还必须把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其他的读书札记以及一些已发表的和未发表的文献、没有寄出的信件结合起来考察,并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进行分析,(74) 才能充分认识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的主题与重要意义,才能把这份遗产中的精华筛选出来,并融会贯通,从而探索出一位革命家暮年仍孜孜不倦地苦心攻读的真正用意所在。根据现有文献资料来看,与柯瓦列夫斯基笔记联系紧密的材料有:
(1)《印度史编年稿》。它是与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穿插地写在同一本笔记上。(75) 马克思在摘录《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的第四章“印度土邦罗阇时代的土地关系史”之后,中断了对该著作的摘录,而转向对印度历史书籍的阅读并写成《印度史编年稿》。之后又回到《公社土地占有制》的研读和摘要。马克思之所以对印度史进行涉猎,是同他研究《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有直接联系。“马克思在研究印度土地所有制形式交替时,编写了编年史,以便扼要地陈述这个国度广袤的领土上的历史事件的具体进程。”(76)“在编年稿里,马克思就印度18世纪后半期和19世纪前半期的土地关系和英国统治对印度土地关系的影响作了极详尽的叙述和分析。”(77) “马克思在摘要中经常用编年稿中的材料同柯瓦列夫斯基著作中的材料作对比,订正并纠正柯瓦列夫斯基的材料。”(78)
(2)菲尔笔记。由于菲尔的著作同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特别是东方村社的长期关注直接相关,所以马克思于1881年8月—9月对菲尔的《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一书作了仔细的研究,写下了菲尔笔记。菲尔笔记把原书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孟加拉现时的农村生活;第二部分是锡兰的农业经济;第三部分是印度雅利安人社会土地制度的演化。由于菲尔用一些十分具体的材料描述了雅利安人村社的基本轮廓(如家庭经济账目、地产登记册、税务表格和财产目录),因此,马克思主要是从菲尔那里撷取一些关于东方社会的具体材料,同时对他的一些错误观点进行了批评。菲尔对村社情况的描述令马克思满意,但马克思也同样对菲尔的“西方中心论”进行了批判。菲尔在论述东方农村中的家庭和公社的关系时,把东方的公社和社会的关系看做是封建主义,马克思对此批评道:“菲尔这个蠢驴把村社的结构叫做封建的结构。”(79) 应该指出的是,菲尔笔记和柯瓦列夫斯基笔记,其重点都是在于探讨亚、非、美洲国家的土地制度、村社结构和社会生活等一系列社会发展问题。因此,它们都不应该列入“探索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的“辅助性笔记”中。
(3)《关于俄国1861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写作时间大概为1881年底—1882年。(80) 马克思在札记中不仅利用官方公布的材料、俄国作者的许多著作,还引用了已经系统化了的实际资料,对俄国1861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一些根本问题作出重要的结论。这篇札记不仅揭示了俄国1861年改革的历史过程,更揭示了所谓“(农民)解放的真正实质。”(81) 马克思指出:“从前在农奴制时期,地主关心的是把农民当做必要的劳动力加以支持。这种情况已经成为过去了。现在农民在经济上依附于他们原先的地主”。(82) 因此,与其说是改革,不如说是剥夺。
(4)《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它大约写于1877年10-11月间(83)。尽管这是一封并未寄出的信,但却承载着马克思深刻的理论思考以及对俄国发展道理的研究分析。马克思反对将《资本论》所述的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模式生搬硬套到俄国等其他非欧国家头上。在这封信中,马克思严厉批驳了米海洛夫斯基对他思想的曲解。马克思指出:“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84) “因此,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85) 在1881年3月8日给查苏利奇的信中更是明确指出:《资本论》所描述的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86) 而且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还对俄国发展道路作出具体分析。“为了能够对当代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精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87) 实际上,这暗示了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有可能超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设想。
(5)《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1881年2月16日,俄国女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写信给马克思,说马克思《资本论》在俄国革命者中极受欢迎,同时也引起了热烈争论,特别是土地和农村公社问题的争论。她请求马克思能够拨冗谈谈对俄国农村公社命运以及俄国发展前景的看法。“假如你能说明,你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有的命运以及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给予我们的帮助会是多么大。”(88) 为了解开俄国发展前景的历史之谜,马克思先后为回信起草了三份长篇草稿,可谓殚精竭虑。尽管马克思的正式复信很短,但三份草稿同样蕴含着丰富内涵,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一个新颖闪光的思想: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信中认为,俄国“农业公社天生的二重性使得它只可能是下面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私有原则在公社中战胜集体原则,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89) 正是基于上述的考察,马克思进一步得出结论:“现在,我们暂且不谈俄国公社所遭遇的灾难,只来考察一下它的可能的发展。它的情况非常特殊,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在整个欧洲,只有它是一个巨大的帝国内农村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组织形式。土地公有制赋予它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它的历史环境(资本主义和它同时存在)又给予它以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90)
(6)《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1882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为在日内瓦出版的第二个俄译本写下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在此再一次就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问题提出看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有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任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91) 这就是说,如果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帮助,俄国可以不经过西欧那样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是晚年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思想。
从上述所列的材料看,它是一组相对独立的研究系列,其称谓可以定为:俄国与印度等国家土地制度、社会性质、发展道路系列研究。这一系列研究是在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柯瓦列夫斯基笔记居核心和首要的地位。这一系列研究有着自己明确的、独立的研究重点与对象,其研究重点与对象是探索俄国、印度等国家公社土地制度、社会性质、发展道路以及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社会革命道路等问题。所以,它不应归属到以摩尔根笔记为“核心笔记、首要笔记”的“探索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92) 中,若是那样,只会造成对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主题的误读,并降低了对柯瓦列夫斯基笔记重要意义的认识。笔者认为,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的主题就是探究东方社会的公社土地制度和未来发展道路问题。这样看来,与其将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主题说成是“探索人类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不如看成是“探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未来前景问题”(93),还更为贴近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主题的本意。
注释:
① 林锋:《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主题新探》,载《人文杂志》2008年第1期。
② 所指与林文相同,即《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
③⑤⑥ 林锋:《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主题新探》,载《人文杂志》2008年第1期,第36、39、40页。
④ 所指范围与林文相同,即《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亨利·萨姆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一书摘要》、《约翰·菲尔爵士〈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一书摘要》。以下分别简称为“柯瓦列夫斯基笔记”、“摩尔根笔记”、“梅恩笔记”、“拉伯克笔记”、“菲尔笔记”。
⑦⑧ 林锋:《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主题新探》,载《人文杂志》2008年第1期,第39、39页。
⑨⑩(11)(12)(13)(14)(15)(16)(17)(18)(19)(22)(23) 《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9、90、91、91、90、90-91、91、92、92、92、92、79、109页。
(20)(21) 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李毅夫、金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15、144页。
(24)(25) 林锋:《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主题新探》,载《人文杂志》2008年第1期,第39、37页
(26)(27)(29) 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李毅夫、金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9、100、111页。
(28) 参见《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8页。
(30)(31)(32)(33)(34)(35) 《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9、1、10、25、100、1页。
(36)(37)(39)(40)(41)(42)(43)(44)(45)(47) 《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4、6、7、7、10、11、12、14、21、21-22、25页。
(46) 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李毅夫、金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50页。
(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 《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6-37、42、59、61、61、63、63、78、94、117-118、79、83、84、86、99页。
(63)(64)(65)(66)(67)(68)(69)(70)(71) 《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98、100、100、101、106、109、109、110、113页。
(72)(73) 林锋:《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主题新探》,载《人文杂志》2008年第1期,第36、40页。
(74) 参见叶志坚:《“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称谓质疑——与王东、林锋先生的学术对话》,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2期,第114-115页。
(75)(78)(79) 《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51、551、385页。
(76)(77) 马克思:《马克思印度史编年稿》,张之毅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1、8页。
(80)(81)(8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654、463、463-464页。
(83)(84)(85)(8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28、341-342、342、774页。
(87)(8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0、857页。
(89)(9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50-451、451页。
(9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1页。
(92)(93) 林锋:《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主题新探》,载《人文杂志》2008年第1期,第40、3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