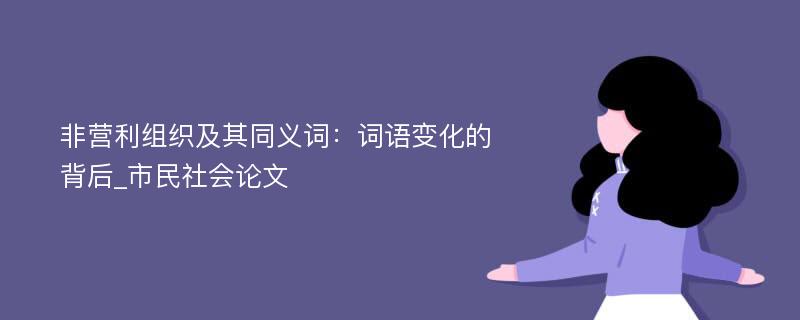
非营利组织及其近义名词:语词变幻的背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词论文,名词论文,组织论文,近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860(2009)03-0080-05
十年前,当有人说非营利组织在中国只是学术概念而非法律概念时,这种说法无可指责。但这种老生常谈在今天却有些不合时宜。事实上,“非营利组织”这一称谓不仅在中国的学术著作或教科书中频繁出现,而且还在具有法律效力的官方文件中悄然现身。1998年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分别使用了“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和“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2004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使用了“非营利性法人”。如果说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使用的上述措辞与“非营利组织”一词还多少有些差距的话,2004年财政部颁布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则明确使用了“民间非营利组织”这样的概念。这样,非营利组织在中国已经鱼跃龙门,从纯粹的学术概念摇身变作官方正式认可的法律概念。在这种概念属性的变换之中,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在诸多与非营利组织相同或相近的舶来概念之中,为什么只有非营利组织这一称谓进入了官方的法眼,成为立法文件所正式使用的术语?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浏览一下从西方世界舶来的与非营利组织涵义相同或相近的其他概念。
一、指向非营利组织的近义名词
“在美国,为数众多的据称是非营利的组织构成了美国社会的一个部门——这些组织通常被称作非营利部门,此外还被称为第三部门、独立部门、慈善(charitible)部门、志愿部门、博爱(philanthropic)部门及免税部门。人们想当然地认为非营利机构扮演着一种与政府和私人营利部门有别的角色,但这些名称大多带有误导性或片面性。许多非营利组织与政府或私营企业有很密切的项目关联和财政关联,远远谈不上是独立的。不是所有非营利组织都带有慈善性质或对志愿者存在依赖性,也不是所有慈善组织都主要依靠私人的善举来支撑。同时,这些非营利的组织可以是、而且常常是盈利的”[1](P2)。
实际上,对于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社会组织,学者描述的用语不统一及用语有缺陷的现象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并非美国社会所独有。“南杰(Najam)曾列出了世界上48个称呼非营利组织的名称,但作者指出,就是这样的名单也还远远没有穷尽非营利组织的称谓”[2](P1)。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非政府组织”是比“非营利组织”更早冲入国人视界的近义名词。而对于非政府组织同样存在着用语不统一的现象。“依照英国学者的观点,除了非政府组织(NGOs)和国际非政府组织(或称非政府间国际组织)(INGOs interhational NGOs)之外,与此有关的组织名称和类型还有:公民社会组织(CSOs,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社区组织(CBOs,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s)、捐助型非政府组织(DONGOs,donor organized NGOs)以及国内非政府组织(DNGDOs,domestic nongovernment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s),等等”。[3](PP3-4)
实际上,上述名词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后从英语国家舶来的与非营利组织相近的概念。除此之外,从非英语国家舶来的近义概念、改革开放前舶来的近义概念以及中国本土的相近概念同样让人眼花缭乱,如社会组织、民间组织、中介组织、公益组织、群众组织、公民组织、群众团体、社团、社会联合、非商业组织,以及社会资本、民办非企业单位、行业组织等。甚至对于非营利组织还存在非赢利组织、非盈利组织三种不同的书面表达。所有这些涵义相近、指向交叉、侧重有别的概念插花间竹般地涌进中国人的阅读空间,并为争夺话语权(尤其是官方认可权)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暗战。时至今日,尽管预料这场有关非营利组织的语词博弈的最终结局还为时尚早,但民间组织和非营利组织这两个名词已经占得先机。1998年民政部社团管理局更名为民间组织管理局,表明了官方对“民间组织”一词的偏爱,而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前述行政法规、规章则表明官方对“非营利组织”一词的认可。在这场语词博弈之中,“非政府组织”一词遭遇冷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个中缘由发人深省。
二、“非营利组织”与“非政府组织”
与“非营利组织”一词相比,“非政府组织”一词无疑曾拥有诸多优势。首先,联合国宪章及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早已明确使用“非政府组织”一词。联合国宪章第71条明确规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得采取适当方法,俾与各种非政府组织会商有关与本理事会职权范围内之事件。此项办法得与国际组织商定之,并于适当情形下,经与关系会员国会商后,得与该国国内组织商定之。”“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1952年的第288(X)号决议中为非政府组织下的定义是:‘任何不是根据政府间协议建立起来的国际组织均应视为非政府组织。’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联合国在1996年通过了1996/31号决议,将非政府组织定义为:在地方、国家或国际级别上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的、自愿公民组织。也就是说,它不仅承认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同时也承认在各国或地区活动的非政府组织,并允许各国和各地区的非政府组织以自己独立的名义参与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会议,并通过在经社理事会使之具备咨询地位,进而可以间接地在联合国表达自己的主张”[3](P20)。从国际法律文件对“非政府组织”一词的使用级别及使用频率来看,“非营利组织”一词很难望其项背。可以说,在国际范围内考察,“非政府组织”一词较“非营利组织”拥有更高的认可度。
其次,国际上较有影响的非营利组织更认同自己的非政府组织的身份,如绿色和平组织、大赦国际、国际红十字会和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等。
再次,“非政府组织”一词较“非营利组织”更早引发中国人对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社会组织的关注。1992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使“非政府组织”和“NGO”在中国正式出版物上的出现频率骤然上升。在进入21世纪之前,“非政府组织”一词在中国的人气之高远甚于“非营利组织”。
最后,“非政府组织”较“非营利组织”一词更受关注公民社会的中国学者及活动家们的偏爱。究其原因,可能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中国,许多关注公民社会的学者及活动家都是先接触“非政府组织”一词,后接触“非营利组织”一词,“非政府组织”一词较“非营利组织”有明显的先发优势。另一方面,国际非政府组织往往是这些中国学者和活动家们的精神导师和资金后援,这些国际组织对“非政府组织”一词的偏爱使这些中国学者和活动家更习惯使用“非政府组织”一词。
尽管“非政府组织”较“非营利组织”一词拥有上述优势,但在中国的立法文件(包括法律、法规、规章)中却难觅“非政府组织”的踪迹。反倒是“非营利性法人”、“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在法规规章中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可见,在获得中国官方的认可方面,“非政府组织”一词已被后发先至的“非营利组织”一词抢得先机。而这种局面的形成可能主要受以下几方面的影响:第一,有关非政府组织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联合国宪章中所提及的非政府组织最初是指国际非政府组织,或称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尽管后来联合国将非政府组织的范围扩大到国内非政府组织,但将非政府组织理解为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传统观念在一些人心中已根深蒂固。这样,用“非政府组织”一词来统指国际和国内非政府组织会与这些人关于非政府组织的传统观念相抵触。
第二,媒体对非政府组织的关注视角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对抗通常会引起媒体的普遍关注,而且对抗方式越激烈,媒体的关注程度就越高。这样,非政府组织对政府的独立性及其对政府批评乃至对抗,成为一些人对非政府组织的第一印象——其影响所及,非政府组织在某些人眼中甚至成为“非议政府的组织”。
第三,有关全能政府的政治文化的影响。在一些人眼中,“非政府组织”一词突出其“非政府”性,这本身就是对政府控制力的挑战,而非政府组织对政府某些社会服务功能的替代也构成对政府的资源配置权的挑战。这样,基于潜意识中的有关全能政府的政治文化,“非政府组织”一词很容易会引起一些官员的心理拒斥。在笔者看来,“非政府组织”一词对非政府性的不加掩饰的张扬,是其在中国难以被立法文件所正式采用的主要原因之一。相比之下,“非营利组织”一词尽管存在一定程度的误导倾向——易使人误以为该组织应当无利润、无盈余并提供免费服务,但其在政治上的正确却无可置疑。这样,“非营利组织”一词能够超越“非政府组织”,成为官方用来指称公民社会组织的法律名词,也就不难理解。
三、“市民社会”、“公民社会”与“民间社会”
在中国内地发生的这场指称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社会组织的语词博弈中,除了“非政府组织”与“非营利组织”的捉对厮杀之外,对civilsociety和nonprofit organization的不同译法也同样深有玄机。众所周知,在新中国成立后,对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著作的翻译已不再是基于学术自由或学术兴趣的个人行为,而是有导向有组织的公务行为。由国家组织的对马恩等经典作家的翻译几乎成了翻译行业的标准模板。尽管马恩的母语是德语,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官方出版的马恩选集和马恩全集中,与英文civil society相对应的德文词汇的标准译法是“市民社会”而不是“公民社会”。受此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学者多把civil society译为“市民社会”。但大致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人几乎不约而同地摒弃“市民社会”的译法,转而以“公民社会”取而代之。在这译风突变的背后,笔者认为可能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经典作家对市民社会的批判。马克思对黑格尔笔下的市民社会的批判使市民社会蒙上了一层贬义色彩。而马克思作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精神导师的地位,使任何与其思想公然相左的观点都要承担相当程度的政治风险。这样,如果把civil society仍译为“市民社会”,译者对市民社会的赞美和向往就与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形成尖锐的对立。在经历了新中国建立之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及政治风波之后,许多中国学者的政治神经已变得异常灵敏,对政治风险的预警和规避已成为一种本能。而把他们向往和赞美的civil society译为“公民社会”,则巧妙地避免了与马克思形成直接对立,从而为鼓吹公民社会打开了一扇政治上的方便之门。
第二,汉语中“市民”一词的贬义色彩。在古汉语中,“市”指交易,以市为业长期被视为末业,以此为业的人赚再多的钱也没地位。而市民不是指以市为业的人,就是指与市毗邻而居的人,无论哪一种,都属于“喻于利”的“小人”,是“喻于义”的“君子”的对立面。这就难怪孟母三迁中的第二迁就是把孟子迁离“市”。一句“市井之徒”把“市民”一词的贬义色彩表达得淋漓尽致。受此影响,在现代汉语中的“市民”一词仍然难以完全消除其贬义色彩(如“小市民”)。这样,对civil society赞誉有加的学者们自然不愿意选用带有贬义色彩的词来作为civil society的中文对应词。从语言心理学的角度看,“市民社会”的译法遭遇冷落也就在情理之中。
第三,“市民”所具有的“城市之民”的涵义,难以把广大的中国农村人口囊括其间,其包容性逊于“公民”一词。
第四,“市民”缺乏“公民”一词所表达的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精神。现代civil society的一个核心理念在于民众对于国家和社会事务(即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但“市民”一词本身体现不出民众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积极参与,而“公民”一词作为公共事务的“公”与民众的“民”的结合,直观地传达出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精神。
在笔者看来,无论是把civil society译为“市民社会”还是“公民社会”,都掺杂着明显的感情成分,前一种译法着意在贬,后一种译法着意在褒。这两种不同的译法实际上反映出两种不同时期的政治时尚及学术时尚。而作为civil society的客观、中性的译法——“民间社会”①,却在这时尚的变幻中悄无声息地被扫地出门。
四、“非赢利组织”、“非盈利组织”与“非营利组织”
对同一英文词组的不同译法之间的纠葛还出现在对nonprofit organization的翻译上。无论“非营利组织”、“非赢利组织”还“非盈利组织”,都是英文nonprofit organization的对应名词。这三种不同译法之间的此消彼长也同样值得探究。
据笔者的观察,“非赢利组织”和“非盈利组织”这两种译法,可能早于“非营利组织”一词的出现,至少在数年前,“非赢利组织”和“非盈利组织”要比“非营利组织”一词更为流行。不过,最近几年,“非营利组织”的译法获得了更多人的青睐,并大有将“非赢利组织”和“非盈利组织”这两种译法赶尽杀绝之势。“非营利组织”的后来居上,主要得益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词义上看,“盈利”与“赢利”可以互通,有名词和动词两种用法——作为名词指“企业单位的利润”,作为动词指“获得利润”。“营利”则仅有动词的用法,指“谋求利润”。[4](PP1634-1635)显然,“盈利”与“赢利”看重是否有利润这一结果,而“营利”则看重是否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前者重“迹”不重“心”,后者重“心”不重“迹”。这样,若采用“非赢利组织”或“非盈利组织”的译法,判断一个组织是赢/盈利组织还是非赢/盈利组织,其标准在于该组织是否“获得利润”这一结果;若采用“非营利组织”这种译法,判断一个组织是营利组织还是非营利组织,其标准则在于该组织是否以“谋求利润”为目的。而显然,现代意义上的nonprofit organization的判断标准并不在于该组织是否“获得利润”这一结果,而在于该组织是否以“谋求利润”为目的。这在英文中的另外一个指称非营利组织的词组——not- for- profitorganization身上表达得尤为明显。这样,采用“非营利组织”的译法比采用“非赢利组织”或“非盈利组织”的译法,更符合nonprofit organization的本义。
其次,从词语的流行人群上看,“非赢利组织”和“非盈利组织”这两种译法主要常见于经济学尤其是会计学领域的著作之中,这反映出这两种译法主要在经济学背景的人群中流行。而“非营利组织”的译法最初主要被有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背景的人群所采用,后来则被国人所广泛采用。随着时间的推移,非营利组织的政治及社会功能越来越受国人的重视,非营利组织由初期的经济学的边缘研究对象逐渐成为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热点研究领域,对非营利组织的话语权也随之从经济学界移出。对nonprofit organization的翻译,由“非赢利组织”或“非盈利组织”变为“非营利组织”,不仅体现出一种词义上的正本清源,而且也反映出国人审视非营利组织的主流视角由经济学的视角向非经济学的视角转变。而伴随着这种主流视角的转变,非营利组织的非经济功能超越了其经济功能而越来越受国人的重视。
再次,从大众的用词习惯及文字变迁的角度上看,文字的简化是大势,生僻繁杂的字词通常会被大众所弃用。据此,受笔画繁杂的“赢”字的拖累,“非赢利组织”的译法最先被淘汰应当在情理之中。与营利的“营”相比,盈利的“盈”虽然笔画不多,但在常规阅读材料中出现的几率却较低,因而相对较生僻。这样,“非盈利组织”在与“非营利组织”的竞争中落败也符合语言文字的发展规律。可以说,“非赢利组织”和“非盈利组织”这两种译法尽管一度在经济学界流行,但这两种译法在选词上的不经济却不利于其在公众中的流行,其结果甚至连经济学界也逐渐将其弃用,转而采用选词方面更经济的“非营利组织”的译法。
应当说明的是,对非营利组织及其近义名词的上述考察,目的并不在于梳理这些语词的变迁脉络,而在于探讨非营利组织这一西学理念在中国这样一个异质文化的环境中遇到了怎样的引导、牵制和约束,借此从一个侧面,管窥时下的中国人对方兴未艾的非营利组织有着怎样的怕与爱。而正是这种深藏于国人心中的怕与爱,决定了中国非营利组织规制的方向。
收稿日期:2008-12-05
注释:
①“民间社会”最初是台湾学者对civil society的翻译,为大陆的历史学家所接受,并在研究中国近代的民间组织时加以广泛使用。这是一个中性的称谓,但在不少学者特别是在政府官员眼中,它具有边缘化的色彩.——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标签:市民社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