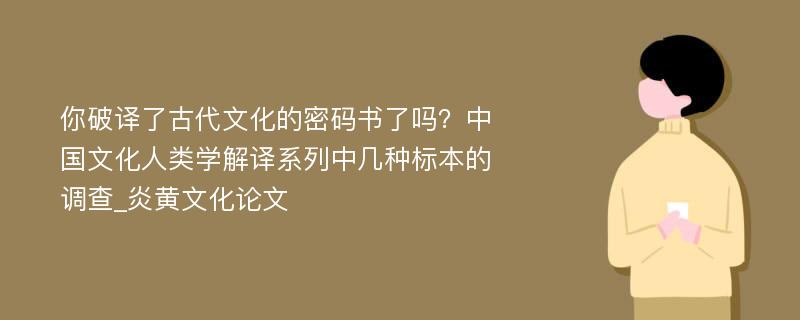
有没有破译上古文化的密码本?——《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几副标本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上古论文,标本论文,中国文化论文,密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中外古今文野雅俗都有“共同语言”。这,特别体现在神话和神话思维中。或以为这就是后设性、普遍性的“元语言”。这种元语言及其语法,神话思维及其原型意象和模式,具有某种解析或推绎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充当破译上古文化的“密码本”。叶舒宪等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便凭借这种文化人类学的密码本,就“永恒回归与《老子》”、“失乐园与《山海经》”、“幻想游历与《楚辞》”、“圣俗消长与《诗经》”、“引譬连类与《说文解字》”、“中心象征与《中庸》”的潜在对位关系做了独特的考察,并对这些号称神秘的典籍进行了独创性和现代性的诠释。
关键词 上古文化 元语言 神话思维 破译
叶舒宪、萧兵、王建辉主持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简称系列)。已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四种,将出三种。
为什么叫做“破译”?
首先,他们选择的是中国上古神秘色彩较浓、疑难较多的几种典籍,企图用以人类学为主的多学科理论和方法加以探讨和解释。这种读释有点像现代通讯里的解码,所以姑称破译。必须承认,这个名称不免惊世骇俗,甚至哗众取宠,但也不尽如此。
当代科学的发展是分工精细而又联系广泛,边缘化趋势非常明显,必须定对象而跨学科,人文科学已进入“文献/地下/田野”三重证据或多重证据的时代。这,《系列》作者已发表过多篇文章,兹不赘言。
其次,为什么要用“人类学”来破译?这,不仅因为作者们多是案头型文化人类学工作者,也不仅因为研究人类(或“主体”)自身的人类学是国际显学和21世纪的主导学科,最重要的是前述疑难除了语言文字以外多属时代—文化的隔膜,多跟原始性社会构造、思维范式相关,运用文化人类学(它主要以后进人群组织及其文化为对象)可谓轻车熟路,事半功倍。
那为什么叫“破译”?是否有“密码本”?这就看怎么说了。
现代重要通讯一般要用密电码。由数学家或电脑之类按照一定的对位序列将莫里斯明码编制成极难解译的密码,局外人当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它总有规律可依,所以世界上没有破不开的密码,需要的只是时间和技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军在太平洋频频败北,就很因为他们的密码被中美专家所破译而不自知。密码最简便的读法当然是对照密码本加以还原。所以密码本可谓密中之密。《红灯记》的原名就是《三搜密电码》。那么,远古文化的神秘到底有没有可供对照破译的“密码本”呢?
在特定意义上,有的。这是因为,思维发展有规律性的范式,全人类——不分中外古今文野雅俗——有“共同语言”,这就是与思维发展相应的普遍性、 后设性和基元性的“语言”(或称之为“元语言”, metalanguage)。这种元语言在原始、原始性的“神话思维”里保存和体现得最为完整,最为“强大”,最为鲜活。神话思维,不但蕴涵着互渗性的原逻辑和意象群,也不但有“模式”和“语法”(结构)可寻,而且直到现代都还保有它的生命、活性和魔力——以致可以“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谁不知道“长生不老”,“死而复生”或“春荣冬枯”,“朝出暮落”?
一切生命都要有死亡,个体死亡后其生命不但由集体来“承继”或“延续”,在幻想性思维里还能复活。
人有生老病死,悲欢离合;月有死生晦朔,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太阳更是朝起暮落,死而复生,“撰余辔兮高驼翔,杳冥冥兮以东行”。
一年有四季,春暖夏热秋凉冬冷;草木禾稼更是春荣夏盛秋熟冬亡……
应律兮合节。它们都是循环性的变化运行,有律则可寻;再参之以大量的神话传说故事风习,
人类学者称之为“永恒回归”(Eternalreturn)或“永久循环”。 这是神话思维里最重要的原型(Archetype),也是元语言最明显的模式(Pattern)。于是, 人们或视之为文化的“密码本”,借助它的推绎功能,来译读古代神秘典籍里某些暗藏的“密码”。
现在我们来观察若干个案或标本。
标本第1 号:“永恒回归”与《老子的文化解读——性与神话学之研究》(萧兵、叶舒宪,1994年)
《老子》说,“反(返)者道之动”。“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体现的就是“永恒回归”的神话观念。 叶舒宪绎述埃利亚德(M.Eliade)《永恒回归的神话》时说,由于在元语言和神话思维里, “一切生命和一切运动都开始于创世神话所讲述的‘神圣开端’——也就是《老子》中所说的‘古始’或‘无极’状态。人类社会便只有通过神话和仪式行为周期性地回归到那个‘神圣开端’,象征性地重还或重演创世活动——时间和空间的肇始,万物的创生——才能确保世界(包括自然和社会)的延续和有效更新,重新获取生命力和运动的动力”。
《老子》的“复”与“返”,所谓复归于朴,于无名、于无极、于无为,或者向往小国寡民、结绳而治,从根本上说,都可以认为是希图回到“原初的美妙”或“神圣的开端”,以期同宇宙融为一体。“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从而重建或再造世界及其秩序。
这样从神话学或性文化的角度解读《老子》,海外已有尝试。像德国的罗塞尔,美国的吉拉道特,日本的井简俊彦,还有台湾的杜而未,都有专著。可在大陆,这是破题儿第一遭。
叶舒宪们认为,《老子》在中国上古哲学里固然几乎是唯一达成最高抽象或终极追求的逻辑体系,但是依然没有洗净神话思维的彩色。它那跟规律或逻各斯同构的最高范畴——道,仍然跟它的原型意象水乳交融,常常互置或互喻。诸如混沌(原气),玄牝,谷神,水,道路,乃至葫芦(匏:朴),昆仑,特别是太阳(太一,或日行之道)……都是道范畴的初始原型;它们不但具有创世或解构神灵世界的功能,而且体现着“永恒回归”的观念和宇宙生命之脉动。他们认为“道”与“易”都努力反映太阳和月亮、男人和女人、天空和大地的阴阳互动,所谓太极(太一)、两仪(阴阳)和四象(四面神)都可以由此得到破解。
萧兵们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揭示,无论是“帝”还是与道异质同构的“玄牝”都以女阴或大母神为母型,谷神及水之根喻都是这种原始生殖力的寓托。“原父母”的好合即交欢能够导致雨水的丰沛和土地的蕃庶和人类的繁殖,它们跟“道”的诞生、茁长及推导、演绎相表里,相律动。所以《老子》一书充满了阴柔或母性的眷恋。洋溢着赤子之心,生命之爱和青春的向往,原初的追忆。至于气之提升,精的保存,灵力(mana)的升华,性经验的抽象,乃至气功、养生、修炼等等启示,虽似细枝末节,却仍是上述泛生殖崇拜的必然推衍与体现。
再如《老子》第25章所说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它可能是混沌一原气,是宇宙开辟之先飞旋舞动的星云般的粒子团或弥漫物质;但也可能是太阳,所以说“独立而不胶,周行而不殆”。太阳是光力热和一切地球生命的源泉。因此“可以为天地母”。它们都是“道”的原型意象。所以即令未知其名,也可字之曰“道”;或因其独立、伟奇、煊赫,而强为之名曰“大”。在《吕览》和《淮南王书》里这个“大”写作“大一”,亦即“太一”,“太一”的原型也正是太阳(可以参看萧兵的《楚辞新探》和叶舒宪的《中国神话哲学》)。
这不但体现着“周行不殆”的“回归”母题,还证明着道的“气律二象性”乃至“心物二元性”。
标本第2 号:“失乐园”与《山海经的文化觅踪》(1996年)
萧兵早在《山海经:四方民俗文化的交汇》里揭示,《山海经》的编整人患有“乐园情结”(Patadise Complex)。
西文的Paradise ——“乐园”。 据莫尼汉(Elizabeth B.Moynihan)和胡克(S.H.Hooke)等的介绍,源于古波斯语, 意思是有围墙的花园,通常指有小树环生的波斯式园林。当然,“乐园”本身的起源要古老得多。
胡万川教授提交给“中国神话与传说学术讨论会”(1995年,台北)的论文《关于乐园和失乐园神话的一些探讨》里有详细的介绍。顺便说一句,《破译系列》作者萧兵等得到邀请,郑在书、叶舒宪教授还参加了这次盛会。
学者们指出,《旧约·创世纪》里的未被污染和毁坏的,体现原初美妙的“乐园”的来由。据胡克(B.H.Hooke)等的介绍, 它原来是阿卡德人(Akkadian)的语词:edinu, 意思是“平野”或“草原”(亦指缺少树木之处)。阿卡德人曾征服苏美尔人(Sumerian)。其语词和观念对中东的神话当然会有影响。伊甸的东边建有园林,林深川媚,风景怡人,在缺水少木的半草原半沙漠地带显得美丽神奇,所以被认为是“神能”创造的奇迹。这一点跟祁连—昆仑草木葱茏的小环境在西北的荒漠衬托下所显现的华美十分相似。
坎贝尔(J.Campbel)则认为Eden是希伯来人的用语, 原来是“欢喜之地”、“愉悦之处”的意思。
《山海经》,据萧兵的见解,最可能由青齐早期方士把四方民俗文化记录、传说汇集起来,加以编整而成,跟稷下之学颇有关联;其体例、风格、语言大体统一,却不像作家文学如楚辞那样有明白的主导思想。内容也比较驳杂,比如所谓中心就有“昆仑”、“建木:都广之野”、“河洛”等好几处。但是,有一个“主编”可以肯定,只是不知道他是谁。过去说作者是大禹、伯益、夷坚,或随巢子、邹衍,甚至于印度人、巴比伦人、欧洲人、中亚人,那都是不可靠的。说它描写到美洲、甚至欧洲、澳洲、非洲(参看《淮阴师专学报》1994年第4 期发表的胡远鹏《山海经:揭开中国和世界文化之谜》),都没有多大根据。倒是历史学界从中发现斯基泰草原—骏马之路,发现希罗多德《历史》与荷马史诗里的“独目人”,也许有些道理(参看萧兵《中国文化的精英》)。
国外的学者一般把《山海经》之类的书叫做“想像地理学”(Imaginative Geography)。萨伊德(Edward W.Said)说, 想像地理学最大的特点是把自己国土外的地方的种种情形加以怪化甚至丑化,尽力加强自我和非我的差异或区别。一般说,这种差异跟距离成正比:距离越远,了解越少,自然“差别”越大,“怪异”越多。例如《山海经》里的《山经》部分多写中国本土,相对平实,山川、物产大都有迹可按;《山海经》(尤其是《海外》诸经)就多靠传闻或想象,主要记载各种怪物、奇事或神怪。
韩国梨花女子大学中文系郑在书教授参考这个理论,在他参加“中国神话与传说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再论中国神话观念:读〈山海经〉以文本》里提出,这部分肯定有一个编整者,也肯定有一定的编辑意图或思想。他说:
这本书原来是由民间的巫师之类写成,但最后才在〔中原〕中心主义高潮时期(战国),由官方学者赋予说明,此一事实强烈地暗示出此书之多样性极有可能是受到某一特定观念源流的洗礼。
这个观念就是“自我中心主义”之下对域外各民族的越远越强烈的异化或怪化。这在后代的以郭璞为代表的注释家笔下愈演愈烈,使得“其记述方式〔变〕为把他者的本体性寓言化,歪曲其真正的差异性,因而把文本(text)的多声的(polyphonie)唤起能力单声化”。这多少有些像“华夷之辨”的强形式:民族沙文主义。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事实。但这不排斥编整者存在乐园幻想、乐园情结。奇妙的是,距离与美妙同样构成正比:距离越大,想象越烈,期望越大,幻景越多。《山海经》的乐园,时间接近“原初”,空间则在“远西”。这在逻辑上、史迹上,倒跟前述“草原之路”暗合。
《山海经》一般用古简的散文,但是一写到昆仑、西海或都广之野等“西部文化区”的丰富物产和华美景物。幻觉仙境,就情不自禁地押起了韵。这就是编者门向往的乐园。
所谓乐园本应该是“原初的美妙”(perfetion of Begining),指的是《老子》式的混沌或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浑朴的原始社会。这种浑沌,像《庄子·应帝王篇》所写,被时间之神倏忽所穿刺,死亡了;这就是原始社会及其“完美”的解构或“解体”(pralaya ),
学者们称之为“乐园的失落”(Lost of paradise)。可以参看叶舒宪《庄子的文化解构》。
“失落”就要重建,转移或恢复。所以弥尔顿《失乐园》之后还有《复乐园》。《山海经》里的“泛昆仑文化区”就是这种新造的乐园,属于比较进步的形式。
乐园可能有现实性的母型即模特(model)。 学者们曾忙着为伊甸园、为桃花源、为巴比仑空中花园或悬圃(hanging Garden)寻找母型。萧兵《楚辞与神话》曾在唐兰、闻一多等论证基础上竭力证成神话昆仑的母型是“祁连”山。而《山海经》和《楚辞·离骚》里的“西海”,可能是昆仑文化区的展延。但萧兵曾经臆测,阿特兰提斯(Atlantis),即大西洲“乐园”的传说可能远远通过草原之路投射到中国的“昆仑—西海—西王母之国”上来,此说曾受到严厉的质疑,却不是毫无道理。因为《竹书纪年》曾反映大西洲覆灭之灾的余波,而《山海经》等又证明中国先秦时期跟西方世界就有因子水平上的文化交流(该书副题就是《先秦国际交流》)。当然这些都只是假设,有待批判或证明。
据悉,这部分研究的框架已经完成,将由叶舒宪、萧兵跟韩国的郑正书教授(哈佛大学博士后)协作进行。
标本第3 号:“幻想游历”与《楚辞的文化破译》(萧兵,1991年)
作者的《楚辞研究》已有七种,这本书介绍跟“元语言”或“神话思维、联系最紧的“幻想游历”或“幻境追求”的母题。
《离骚》的秘密便集中在一点上:追求——对光明的乐园式追求。仅仅用传统技法解不开这个谜:诗人为什么基本上朝着太阳飞行?英国人霍克斯有名作《求宓妃之所在》,说仪式化的游历有宇宙论的意义,神游是为了获得、巩固或加强“法力”,希望成为“宇宙的主人”,实际上也是“复乐园”的一种形态。
这种似奇实正的论述本质上并不错,对于《远游》尤其合适,但是这结论却又游离于《离骚》话语系统之外,很难理解。日本学者竹治贞夫称《离骚》为“梦幻式叙事诗”,也触及这个关键:追求。美籍华裔学者王靖献(杨牧)用《离骚》和斯宾塞《仙后》做比较,说:“屈原的追求是离家而去的寓托性历程,是一次西向的放逐。”这个放逐是仪式性的,是纵横二向的乐园回归:纵的是,渴望回归古代美政之“黄金时代”(亦即复返“原初的美妙”或神圣开端);横的是向仙国的“求婚之行”和旧乡的复返。可以说,这些都从普遍性思维模式和“元语言”的角度把握住了古代哲学诗人浪漫飞行和乐园情结的本质。可惜,我们仍有漫无边际的语境“失落”之感。
《破译》的作者认为更重要的“密码”暗藏在诗人的生辰名字里。“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不仅有年代学的意义。摄提是掌理太阳之星,就是“重华”帝舜(见于《史记·天官书》),孟陬指的是娵訾氏常仪(常娥),所谓“贞于”就是太阳神正好进入月亮神之宫,某一天诗人诞生了——“庚寅”正是中国的太阳圣节(参见姜亮夫的统计分析)。所以作为太阳神血裔的诗人能够遵循太阳运动轨范名正则而字灵均并跟作家名平而字原相应,他始终慕恋光明,始终朝着太阳“神游”。这种神游恰好跟作者的悲惨遭遇以及世俗的肮脏相对立、相碰撞,从而加强了美政理想的强烈性与悲剧性。然而,三次飞行追求以光明为象征的真善美而不得。他又想“陟升皇之赫戏”,希望回归、认同自己的太阳祖先,但又被思乡的现实感情拉回到不能容纳追求者的地面,最后不得不投进冰冷黑暗的水府,以惊心动魄的“明暗—热冷—美恶”的对照锻铸太阳诗人的悲剧。在这个意义上,《离骚》可以理解为“太阳神鸟的悲歌”。这项令人瞠目的解读,至今得不到几乎所有传统研究家的承认,但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驳倒他,似乎也没有人做驳斥的尝试,不知道是默许还是默杀。
《招魂》,作者依照埃利亚德、坎贝尔和凌纯声、张光直等提供的思路,更多地从萨满的“魂游”辞与泛太平洋文化里的“招魂术”出发,揭示巫术—神话思维里的生死二元对立,探索所谓鬼话—神话—仙话—人话的文学源流,而对招魂仪式里的禁避/导引及其文学表现或影响略有发明。其实,《招魂》里对亡魂的“禁制”与“引导”,也可以视为消极的或逆向的“游历”,回返欢乐的人间则是世俗性的“复乐园”。这一切都将屈原赋“虚变”的浪漫性与“实恒”的世俗性紧紧揉合在一起,而绝没有抹煞其现实的经历、背景、寓托或意义。
标本第4 号:“圣俗消长”与《诗经的文化阐释——中国诗歌的发生研究》(叶舒宪,1994年)
这本书的核心可一言而蔽之:诗言寺而寺言诗。叶舒宪首先对殷墟卜辞里的ㄓ字(寺字所从)进行统计分析,揭示其为祭祀之名。后来,“人们用ㄓ与手会意造出寺字,用来表示祭仪主持者”(第144页)。 但是,寺人却指阉人,最早的宦官,这是为什么?作者通过世界上古史里的自阉巫师之制,“从巫史与尹寺同源方面发掘作为知识分子原型的祭仪主持者(寺)与‘诗’的隐秘关系”。《诗经》最古老部分是雅颂,雅颂的前身多属祭歌,祭歌则多为阉割的巫史尹寺所作——这是诗歌起源的一条途径。这真使人目瞪口呆。是信口开河,无的放矢吗?《诗经》却明明说:“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变风变雅之声里,不时泄漏着这些堕落了的巫史尹寺的哀音。
叶舒宪的诗歌发生学理论,包含艺术的“圣”与“俗”之二重起源及其互动。他努力追溯从法术、咒诅到祭歌、情辞的演变过程,推演《诗经》祝咒性修辞手段与原始性猎咒、医咒、爱咒和反咒的潜在联系,由咒与祝、巫与史的分化探讨“美刺说”的由来和所谓“六义”的发生。所以,这部著作不限于《诗经》或中国“诗”的诞生的途径,而且广涉整个人类及其思维和宗教、神话、艺术的起源。整个美学界和理论界都应该关心它。
叶舒宪认为,汉语里的“诗”跟歌、谣不大一样,“诗原本是具有祭政合一性质的礼仪圣辞”(第158页), “颂”最接近“诗”的本义;“雅”有“正”义而近于诗;“风”却是歌谣而不是寺人所作的“言”。孟子所谓“王者之迹息而诗亡”,按照现代人类学的理解,意味着“诗和礼一样,原本是王者统治权即神权的确证,王者的衰败自然使诗和礼由官方向民间转移,这也是由神圣向世俗的转移”(第159页), 于是才有一般意义诗歌(包括风诗)的诞生。这个说法几乎跟大陆现有的全部文学史、文艺理论完全对立,我们也暂不能把它证实或证伪;然而他说,寺人(或其种种传人)“在正规场合赋诗献诗,本有代神传言的性质,只因王道衰微之后,寺人的监督作用表现为歌谏诗谏”(第159页),却是不移的事实。
标本第5 号:“引譬连类”与《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臧克和,1994年)
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事实上已被看做中国文字学和文化学的经典。因为中国文字以象意为核心的“六书”系统,以鲜明而又深邃的意象展示着整部中国文化史。尽管殷周甲骨卜辞的发现和金文的再认识,推翻了《说文》的某些旧说解,不治甲金无以治《说文》;但不知《说文》更无以知中国文化。本书作者揭示,“取象构形”是中国文字的最大特征,《说文》正以意象的解析来展示中国式的系统—逻辑思维与神话思维。全书以社会性,审美性,神话性意象系列为考察单位,推溯其源头发生,追踪其演变史迹,跟萧兵的《中庸的文化省察》同样试图建构“单位观念史学”;在操作上,联系形符,对应声符,参照《说文》里相辅相成的两个“语义场”(视觉的听觉的),打破文字形体界障,观其会通,别其层次,明其关联,出其真诠。此正如叶舒宪所评述:“文化人类学把语言现象放在思维、符号、文化的有机结合部来加以观照,可谓站得高,看得远。”
例如《说文》弓矢意象系列便鲜明地透露其与神话思维及巫术仪式的密切关系。作者认为,甲骨文“吉”本从矢,家有弓矢表示“吉利美善”(参见刘志基说)。弓箭象征男性,作者举出《礼记·内则篇》和珞巴族民俗为证(如果进一步采撷描写民俗学资料,便可以更有力地证明矢象男根,射喻交媾)。他还引用钱钟书之说,论证矢还可以转化为“祸患”(第293页),如“疾”之从矢而与摹拟巫术相关。 这确是发人所未发。射候(箭靶)之侯也从矢而“取象于人”。所谓射“不宁侯”或画“不宁侯”更是咒诅性的,是“氏族社会利用神权举行的一种巫术仪式”(第318页),就好像后世扎个草人,写上敌对者的生辰八字,以箭射之便可置其于死地一样。这还涉及黑白二种恋爱巫术,作者引用《晋书·文苑传》,顾恺之悦邻女而怨其不从。“乃图形于壁,以棘针钉其心,遂患心痛”,这是黑巫术;弗雷译《金枝》所说,马来人追求冷美人,咒曰,我要射他那漂亮的心房,则是白巫术。如钱钟书《管锥篇》所说,“疾”之从矢,合之鬼蜮含沙射影之说,“则吾国古人心目中之病魔以暗箭伤人矣”。这些都精彩而新颖。萧兵《楚辞新探》考释《天问》伯益之暗害后启,“皆归射鞠,无害厥躬”,是类似的摹拟巫术,罗列文献、民俗颇多,而上举材料几乎全被忽略。当然,萧兵所述,本书也大多未曾注意。可见学问之切磋交流辨难是何等重要。
标本第6 号:“中心象征”与《中庸的文化省察——一个字的思想史》(萧兵,1996年)
从一个“中”字生发出一段50万言以上的思想史来,这在大陆还比较罕见。海外称之为“单元研究”或“个案研究”,有点儿解剖一只麻雀的意思。实际上古已有之,基本上是某一标本或单一对象的通考。作者称之为因子研究。所谓因子(element )是文化史的不可再分割的最小意义单位,例如语言学上的词,艺术学上的形象。中国文字基本上属于所谓“意象”系统,每个字往往构成一个“意象”,可以从中分析出、演绎出“意义”乃至“历史”来。正如陈寅恪先生为沈兼士释“鬼”做的审查报告所说的, 研究一个字就是撰写一部文化史。 作者萧兵在他的70多万字的大书《傩蜡之风》(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里已就“傩”字做过大胆的尝试,臧克和《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更有众多的发明,这部《中庸的文化省察》做得更详细的是在人类学及其友邻学科视角下的思想文化方面的究索。这也许是因为,“中”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关捩性的字眼,它不但联系着“庸”、“史”、“忠”等内含相关的文化字群,而且像多面晶体那样耀目地闪射着中国人的众生相。但是否能自许为“思想史”,则有待公论。
作者用广义的“神圣中杆”来解说“中”的基本构造(它的椭圆边框本也是神圣的天人中介物,并且有规范、标示中杆的功用),认为它是世界性中心象征物在文字上的表现。作者由黄土崇拜、黄色人种、黄帝传说等构成的环境讲到自我中心幻觉和中庸文化产生和蕃育的“水土”及其正负面;还从民俗神话学的角度专门分析了作为中心意象符号的中极之星、盖天之顶、天柱、天梯以及世界山、世界树、世界脐等等的神话性质及功能。其中有的神话意象像世界脐等为海内学术界素未触及,有的则有更独特、更深入、更引人入胜的讨论。作者还以周人等为了避免灾难、为了镇伏别族而择新都、定天保而依天室为例,结合亚形明堂、社庙和火塘、中霤的布置,揭示群团只有占据世界中心,融入宇宙,才有可能建构新的权威、信仰和秩序,乃至“再造”世界、重构宇宙。这也是前述的元语言或神话思维一大观念,一大范式,也不妨看做密码本之一叶。这种“中心象征符号”系统具有创世功能和宇宙论价值的理论,虽然是埃利亚德等所建立,在海内学术界的集中应用和拓展,如果不是初次也是相当罕见的。它为神话学与历史学、哲学的冲突交融提供着新的样本或靶的。
这套《系列》苦苦寻求的就是上古文化的“密码本”,力图从元语言和神话思维之把握与推绎对中国典籍进行现代性的破译与诠释。当然,许多哲学之谜,艺术的母题,神话的寓意直至现世的行为或话语的背景,不一定都能够通过他们的持续工作得到破解。但是,系列作者们认为,在古人和今人、外国人和中国人、后进人和先进者之间都有“共同语言”。这种元语言或思维范式或共时结构的“密码本”,能够帮助我们解读许多神秘,许多疑难。它又往往不局限单个的标本而具有某种普遍的意义。正如系列的说明所讲:
现代人类学从对单一的文化对象的调查和实证性研究转向对文化系统——蕴含着意义、象征、价值和观念的系统——的总体把握,并将跨文化的比较分析逐渐提升到文化模式的发现与概括。也只有找到了凝聚着“系统”之生成与转换规则的“模式”,作为总体的“文化”才能得到深层解释和理性的破解。
这可能就是他们的理论追求。正是借着这种普遍性、规律性的元语言或思维范型,或者所谓原型意象模式的演绎—推导功能,他们努力使以微观考释见长的传统考据学所难以深入认知的原始性文化“密码”在跨文化的比照分析和透视之下得到译解,从而使所谓“国学”重新确立在世界文化序列中的位置,并且能够更广泛地与国际学术对话和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