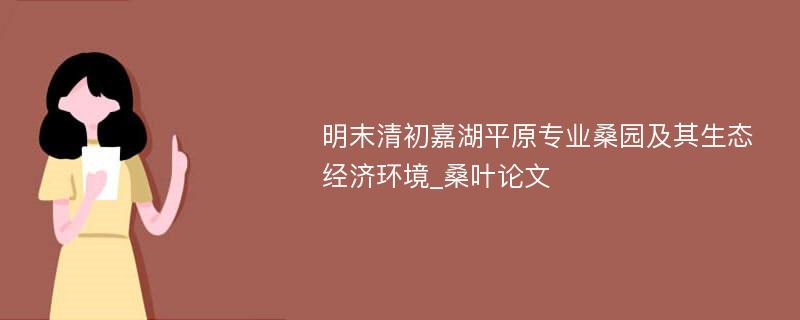
明末清初嘉湖平原的专业化桑园及其生态经济环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桑园论文,明末清初论文,平原论文,生态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205(2009)04-0026-11
明中叶以来,嘉湖地区所产“湖丝”,在国内外负有盛名。明末清初,蚕桑业在这片“北不逾淞,南不逾浙,西不逾湖,东不至海,不过方千里”的地区独盛起来①,并成为嘉湖平原的主导经济产业。宋元时期嘉兴一带的蚕桑业还未兴起,“苏、秀两州乡村,自前例种水田,不栽桑柘”②。湖州的蚕业生产则主要集中于安吉、武康等西部丘陵山区,“本郡山乡,以蚕桑为岁记,富室育蚕有至数百箔,兼工机织”③。山区民户以养蚕为要务,“彼中人惟藉蚕办生事”④,植桑更是不遗余力,“富家有种数十亩者”。与西部山乡相比,东部的平原低洼区为水乡,“并种紵及黄草纺绩为布”。此时平原地区的蚕业仍未兴起,织物仍以苎麻和黄草为主原料,“黄草布,出东乡有极轻细,织成花纹者,暑月可以为衣”⑤。西部山区地带蚕桑业的发展迅猛是因为山区高亢地带“无干旱水溢之苦”⑥,而平原区域“众溪交流,地势平下,素号泽国”⑦。因上承太湖湖水的浸溢,西接苕溪水倾注,东部岗身地区又受海潮影响,故常受水涝之害。“桑地宜高平不宜低湿,低湿之地,积潦伤根,万无活埋。(按语:高平处亦必土肉深厚乃可)”⑧。这种长期积水的水利环境,不利于桑树的种植,只有在平原圩田区域中,圩岸和其它零散的高地土墩可以利用来植桑。所以,平原区域早期的桑园主要集中于圩岸。宋元时期的诗文中留有许多关于圩岸桑园的描述,桑与麦是宋元文人笔下,江南春季两种最常见的农作物。范成大游至湖州,写下:“落日青山都好在,桑间荞麦满芳州。”⑨元时方澜经由石门时,也曾留下“桑迳绿如沃,麦风寒不已”的诗句⑩。这些描写的都是春季圩岸桑园与圩内麦田相间的景观。
明中叶以后,蚕桑业在嘉湖地区内部集中区域已由山区转移到平原区域,七里丝逐渐成为“湖丝”中的名牌产品(11)。“七里”又称“辑里”,本为湖州南浔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据朱国桢的记载,万历年间“湖丝惟七里者尤佳,较常价每两必多一分”(12)。明末以来七里丝也是优质湖丝的代名词。嘉湖平原的蚕丝业后来居上并且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原因在于其区域内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当地良好的水质资源是湖丝的品质保证,“其地载水作丝者亦只如常,盖地气使然”。隆庆、万历年间缫丝技术的改进,使织品的多样性增加,七里丝无论在品质上,还是在花样上,都在市场上取得了优势地位,“其法益加讲求,为法愈密,所产甚良,前后几二十年,岁无败者”。如朱国桢所说,万历年间,七里丝在国内外丝绸市场上的地位已无可替代,这种地位一直保持到近代,在世界蚕丝市场七里丝仍负有盛名。钱天达这样总结:“至辑里区则概括湖州以东,崇德以北,嘉兴以西,太滨一带。”(13)可见,七里丝的产区主要集中于湖州的归安、德清、南浔一带。《乌青文献》记载,四乡蚕业“西路为上,所谓七里丝也,北次之”。这里的西路,指的就是乌青镇以西的湖州一带,北部的震泽、盛泽等地多机户,也多赴西路湖州菱湖、南浔等地“买经纬自织”(14)。
在湖州的蚕业集中区域,“诸利俱集于春时看蚕,一月之劳而得厚利”(15)。蚕业的大发展必然引发集中的桑叶生产,但就植桑所需的地理环境而言,太湖南岸的嘉湖平原并不俱备良好的植桑条件。“浙西地形,杭据上游,嘉稍下,湖最下,譬之釜也,杭,釜之口也,嘉,釜之中也,湖,釜之底也,故受水之害为尤甚”(16)。凌介禧将嘉湖平原的地形描述成一个四周高,中间低地釜形盆地,其中嘉兴稍高,北面湖州的为低湿中心,“水积其中,势若盘盂。设遇雨潦则环湖低田悉皆淹没”(17)。这种碟型洼地的地形特征,容易形成长期积水的环境。
明中叶以来,在江南丝织业市场的推动下,以湖州为中心的嘉湖地区蚕业规模不断扩大,原本不利于植桑的嘉湖平原却发展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蚕桑经济繁盛地区。对于嘉湖地区蚕桑经济的发展,已经有诸多学者在相关的研究中论及,如范金民在其江南丝绸史的研究中描述了蚕桑生产商业化与专业化的基本过程;樊树志对江南市镇史的研究中亦涉及到蚕桑业的专业化问题;日本学者田尻利在对清代农业商品化的研究中,着重讨论了清代嘉湖地区的桑叶贸易经济。另外,滨岛墩俊、王家范、李伯重、陈学文等在相关的研究中,也都涉及到对蚕桑专业化问题的讨论(18)。本文试着从植桑与生态经济环境的角度出发,探讨明末清初嘉湖地区专业化桑园区域形成的地理原因。本文将研究的时间段集中于明隆庆至清康熙初年。明季自隆庆海禁开放以来,中国蚕丝大量输出海外,江南的蚕桑经济逐渐卷入世界市场(19),至清康熙厉行海禁,江南丝织品的国外贸易又有一个短暂的衰落期(20)。在明末清初的这段时间内,因国内外市场对丝织品需求的增加,江南所产的丝与丝织品大宗输出。巨大的国内外丝业市场,繁荣的蚕业经济是嘉湖平原专业化桑园得以产生和集聚的前提(21)。
一 专业化桑园的形成
明季以来,国际市场上对湖丝的需求渐涨,湖丝成为丝货中出口的大宗。到万历、崇祯年间,湖丝基本上垄断了国内外的生丝市场。(22)本国内部的官营制造点中,生丝原料也多来自嘉湖。“凡织花文必用嘉湖,出口出水,皆干丝为经,则任从提截,不忧断接,他省者即勉强提花,潦草而已”(23)。湖丝质地优良,较其他地区所产蚕丝韧性尤其好。天启、崇祯年间,海禁废弛,湖丝在海外市场得到更加迅速的推广,“至蚕桑所成,供三尚衣诸织局,衣被华夷,重洋绝岛,翘首企足”(24)。湖州逐渐发展成国内外为丝织原料的主要供应地,隆庆、万历以来,蚕桑利厚,“吴、越、闽、番至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砾。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25)。在繁盛的蚕业经济刺激下,蚕丝业中心对桑叶的需求猛增,桑树的种植开始在有限的旱地上四处扩展,如德清一带,嘉靖年间已是“桑稻连畴,烟火连接”的景象(26)。这时期嘉湖平原植桑业发展的趋势是一方面在丝业发达的地方地尽其利,另一方面丝业欠发达的周边地区开始为丝业中心地提供桑叶。
嘉湖地区有几个丝业的中心和次中心,在这种地区差异也导致了蚕业区与植桑区的分化。第一个产丝中心是菱湖、南浔、双林等地,这里是嘉湖平原内的中心低洼地带,水域面积广阔,难有旱地。“三乡概湖荡,积水之区,田不可耕。幸赖一二桑地,聊以存生”(27)。蚕业兴盛之时,“家家门外桑阴绕,不患叶稀患地少”(28)。双林地区亦“自墙下檐隙以及田之畔池之上,虽惰农无弃地”(29)。这些地区因水多地少,“桑地大部分在荡埂、圩埂上,整片的很少,水涝发生时,树干浸泡在水中,表土经久雨后地力消失,桑根暴露”(30)。所以当地桑叶供应远不能满足养蚕的需要,“本地叶不足,又贩于桐乡、洞庭”(31)。这里养蚕所需的大部分桑叶都依赖于外部市场的供给。
另一产丝中心为震泽、盛泽镇等地。震泽、盛泽一带位于嘉兴府北部,属淀泖湖区低地,“秀邑之腹里及偏北隅,最为卑洼”(32)。蚕业兴盛之时,此地蚕户也须购叶于外。《醒世恒言》中记有嘉靖年间,盛泽镇上蚕户施复远赴洞庭山买桑叶时发生的故事。
“那年又值养蚕之时,才过了三眠,合镇阙了桑叶,施复家也只勾两日之用,心下慌张,无处去买。大率蚕市时,天色不时阴雨,蚕受了寒湿之气,又食了冷露之叶,便要僵死,十分之中,就只好存其半。这桑叶就有余了。那年天气温暖,家家无恙,叶遂短阙。且说施复正没处买桑叶,十分焦躁,忽见邻家传说洞庭山余下桑叶甚多,合了十来家过湖去买。施复听见,带了些银两,把被窝打个包儿,也来乘船”(33)。
赴洞庭山买桑叶,一则路程太远,二则需要担当太湖中风浪的危险。所以在嘉湖平原内部,崇德(清康熙年间改称石门)、桐乡成为当时嘉湖地区养蚕所需桑叶的主要供应地。“叶莫多于石门、桐乡”(34)。因这一地区的相对大运河以西和以北地区,地形稍高,可植桑的旱地和可以转化为旱地的高地较多。徐光启讲:“湖州之圩低,其港常阔,人惮于增外,仅为修内,故水益阔易冲,而湖州多淹;崇、桐土高,其港常窄,人惮于开外,日为填出,故水益窄易涸,而崇、桐多干。”虽同为水网平原区,但崇德、桐乡一带地势总体上比湖州要高2米左右(35),这一带较湖州低乡具有更好的排水条件,发展植桑更具比较优势,“湖州地下无土,崇、桐地高土多”(36)。当湖州桑叶供应满足不了本地区蚕业大规模发展时,处于湖州府边缘的崇德、桐乡高地的地理优势立即凸现出来,植桑业逐渐集聚于此区域内。
张履祥居住的桐乡杨园村就在这一片高地之中。张履祥有田“半百亩之入”(37),张履祥经营的规模并不大,“岁耕田十余亩,地数亩,种穫两时,在馆必归,躬亲督课”(38)。张履祥亲自从事劳作,除自留耕作的植桑地之外,仍有多余的桑地出租给佃户。张履祥的租佃契约条例中记载有桑地用于出租,“某字圩地几亩几分几厘,额该租桑银几两几钱几分几厘,内收绵十分之一”(39)。崇、桐地区地高土多,能直接利用来种桑树的旱地较西部湖州更多。在平原圩田区植桑,旱地是最为稀缺的资源,《补农书》称:“桐乡田地相匹,蚕桑利厚;东而嘉善、平湖、海盐,西而乌程、归安,俱田多地少。”(40)桐乡一带水利条件也较其他地区优越,张履祥讲,“吾里田地腴美,宜桑谷而不病水旱”(41)。这使大面积的桑园集中于此地,在其区域内形成了独特的以桑园为主体的景观模式:“地皆种桑,家有塘以养鱼。村有港以通舟,麦禾蔚然,茂于桑下。”(42)李日华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三月十四日路经桐乡城时,看到的也是“绕城桑柘,犬吠竟夕,恍如深村”的景观(43)。
相比之下,处于低乡湖州的大部分地区则不具备这种植桑的地理优势。张履祥业称湖州一带少有旱地,“田宽而土滋”,张氏因这里地势相对于其所居住的桐乡为下,长期积水,又将其称之为“下路湖田”。这些“湖田”因潜水面高,冬季常处于淹水状态,土壤多发育成潜育性水稻土,且不宜种植春花,“湖州无春熟,种田蚤(早),收获迟,即米多于吾乡”。在这样的土壤环境下,农民将肥料全部都投入到单季稻作上,使之高产。张履祥称这些湖州低乡的水田,“有亩产三、四石者”(44)。这种亩产达千斤以上的丰产的水稻田,尚可供应邻郡杭州,王士性称杭州“城中米珠取于湖”。湖州的高产稻田不仅可以养活支持本地的大量人口,为养蚕业的兴盛提供充足的劳动力条件,同时由于当地的稻田不适合春花作物,又使春季有大量的闲暇劳动力空置出来,头蚕的养育在农历春季四月份,正好利用了这一空余劳动时间。王士性讲“湖多一蚕,是一年两有秋也”(45),就是说养蚕解决了当地春季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养蚕业又推动植桑。依附于养蚕业的植桑业,既然受制于湖州低乡不宜种桑的地理条件,不得不寻求新的发展途径,即在嘉湖平原内部形成区域分工:湖州低乡成为养蚕较为集中的地区,崇德、桐乡、海宁高地成为植桑较为集中的地区。
嘉湖平原内部高、低乡之间的地理差异是导致养蚕业与植桑业分离,专业桑园得以集聚的根本原因。“崇、桐、海宁之间,烟火相接,河港具存,又皆平壤,高卑之势不大相去,实非他州之比”(46)。明中叶以来,在湖州低乡地区高度繁荣的蚕丝业刺激下,专业桑园在大运河以东,以南的高阜地区扩展,至正德年间,桐乡一带早已是“高原树桑麻,下隰种禾稼,尺土无旷者”(47)。专业化桑园在地理区域上集中于崇德、桐乡、海宁,即今大运河以东,沪杭线以西这一近似平行四边形的区域内,这种集中分布的格局一直保持到上个世纪50年代(48)。
专业化区域分工得以实现,也因嘉湖平原作为水网平原区,内部具有极为便捷的水运交通条件。桑叶贸易的即时性要求快速的运输条件,嘉湖地区四通八达的水路,使专业桑园中出产的桑叶,在蚕忙时节,可以通过运河及各支港,将桑叶快速运至周围的市镇进行交易。桑叶买卖是鲜货贸易,其作为商品贩卖极易腐坏,夜间温度较低,低温在一定程度上能使桑叶保持在运营中的新鲜度,所以蚕农一般选择“夜泛轻航买女桑”(49)。如果到白天,气温升高,“则叶蒸而烂,不堪饲蚕矣”(50)。桑叶运输的路途亦不能过长,“如买叶于数十里外,而储之不得不坚,则须于中道放风。放风者置有风无日之处,发而松之也。约行二十余里,便须放风一次”(51)。由于传统时代水运运输速度及桑叶运输时间上的限制,决定了供给大规模蚕业需要的专业桑园必须向蚕业中心聚集,所以大量的专业化桑园是在紧依丝织业地区的边缘地带出现。
二 专业化桑园的经营与生态经济
植桑与养蚕都是极具生态脆弱性的行业,这种脆弱性在一定程度造成了传统桑叶贸易的期货特征。万历间湖州乌程人朱国祯说:“湖之畜蚕者多自栽桑。不则预租别姓之桑。俗曰稍叶。”(52)桑叶买卖一般发生在农历四月春蚕养育期间,嘉湖地区当地人称买卖桑叶为“稍叶”:“有余则卖,不足则买,谓之稍。”(53)明末以来,太湖南部地区产生发达的桑叶贸易,甚至出现了桑叶投机。日本学者上原重美认为,养蚕的不稳定性和当地人对栽桑养蚕的投机型心理造成了桑叶的买卖,桑叶贸易并非出于栽桑技术上的发展而带来的正常商品流通。田尻利认为,一方面有大量的人在养“空头蚕”,一方面大量人在专业植桑。正是“空头蚕”的养育支撑了嘉湖地区桑叶贸易的盛况(54)。
中国传统的农家蚕桑经济中,栽桑与养蚕是相对平衡的,在嘉湖地区,这种平衡被打破,有识之士虽提倡“栽与秒最为稳当”,但靠买桑叶饲蚕的“看空头蚕”现象仍十分普遍(55)。因为饲蚕的桑叶可以通过市场购得,这使嘉湖地区农家的养蚕规模,不必受制于桑地农作,当地农家可以依据丝茧的市场价格情况,扩大其养蚕的经营规模,一年之中,有多少人养空头蚕,即有多大潜在的桑叶需求。正德年间,德清等地桑叶买卖已十分普遍,“每清明后蚕育,群扎而聚于市衢以卖,早晚先后时价不同”。叶行为专门进行桑叶贸易的中间商,“鬻桑盛时呼为叶行”(56)。买卖之时许多人投机叶市,囤积居奇,桑叶交易过程中,中间商哄抬桑叶价格,使叶价波动很大,“价随时高下,倏忽悬绝,谚云:仙人难断叶价”。万历年间,乌程朱国桢一位姓章的邻居即“豫占桑价,占贱即畜至百余斤,凡二十年无爽,白手获厚”(57)。在如此发达的桑叶市场上,专业化较强的桑园经营必然会追求经济效益,强化其集约化生产。
专业化桑园的规模,各种农家,各有不同。一般情况下有两种专业化桑园,一种是雇工经营的桑园,一种是小农经济下的专化化桑园。雇工经营的专业化桑园以归安茅坤所记录的例子最为典型。双泉靠植桑致富起家,桑园规模达到数十万株。
“君起田家,子少即知田,年十余岁随府军督农,陇亩间辄能身操畚锸,为诸田者先,其所按壤分播,薙草化土之法一乡人所共首推之者。已而树桑,桑且数十万树,而君并能深耕易耨,辇粪菑以饶之,桑所患者蛀与蛾,君又一一别为劖之拂之,故府君之桑首里中。而唐太史应德尝铭其墓曰:唐村之原有鬰维桑兮生也,游于斯死以为葬兮。盖善府君之治桑而没,且歌于其墓也。而不知于中君之力为多,故其桑也亦一乡人所共首推之者。君之田倍乡之所入,而君之桑则又什且伯乡之所入,故君既以田与桑佐府,君起家累数千金而羡其继也,君又能以田与桑自为起家,累数万金而羡”(58)。
双泉在经营过程中,还十分注意桑园的肥培管理,“辇粪菑以饶之”,他从各处载粪壅来施肥于桑地,达到高产的效果。专业化桑园经营需要大量的肥料投入,春天向桑地施肥,每亩“垃圾必得三、四十担”,传统时代,一家一户所积攒的农家肥根本无法满足其桑园的肥料需求,更不用说经营大规模专业化桑园。寻找这些肥料,“平望一路是其出产”。平望因碾米业发达,作坊用牛来拉碾,在牛来回拉转的路上垫有碎草和土,经牛来回践踏后,与牛的粪便混在一起,这种肥料叫“磨路”,肥力很大,是买来壅桑地的上好肥料。夏伐后的桑树应即时施肥,当地称此时施肥叫“谢桑”,及时施“谢桑”肥,桑树以后发出的枝条才可能茂盛。因谢桑在蚕事繁忙之时,一般选择“在近镇买坐坑粪”。即到附近的镇上去买厕肥,“上午去买,下午即浇更好”(59)。这些市镇所产出的废物,被附近的乡村利用起来施于桑地上。
双泉对桑园的专业化管理十分成功,“府君之桑首里中”。这也让他获利甚多,“君之田倍乡之所入,而君之桑则又什且伯乡之所入”。可以看出,他对水田的经营,规模远远小于对桑园经营的规模,其依靠桑园经营所积累的财富十倍于治田经营所得。因植桑利润远高于种田,南浔的荘元臣则完全放弃了水田的经营,集中精力将二十亩地经营为专业桑园。荘元臣在其《荘忠甫杂著》“治家条约”中写道:
“凡桑地二十亩,每年雇长工三人。每人工银二两二钱,共银六两六钱。每人算饭米二升,每月该饭米乙石八斗,逐月支放,不得预支。每季发银二两,以定下用。四季共该发银八两。其叶或稍或卖,俱听本宅发放收银。管庄人不得私自作主,亦不许庄上私自看蚕。如沈澳要讨租田,照例七石还租。其载下用,须发竹筹与沈澳,每一载米交一筹。计一季收筹几根,以验载数多寡。仍发自家一人,眼同去载,以报浅满虚实,则无由作弊矣。欲种菱,可量发菱种银三钱,不得过多。其桑条二叶,俱归本宅,管庄人不得有份。其看叶人,量与种银四钱,以赏其劳,有失即责令赔偿不贷。”(60)
荘氏有桑地二十亩,沈澳代为管理。荘氏所经营的桑园所产桑叶“或稍或卖”,并且“不许庄上私自看蚕(养蚕)”。由此可见,此桑园以专供出售桑叶为目的。专业化桑园经营另一个例子是《沈氏农书》提到的沈氏的桑园,这种桑园已经专业化到雇工经营,甚至还有专门剪桑的雇工和包捉桑虫之人。“长工每一名工银五两,吃米五石五斗,平价五两五钱,盘费一两,农具三钱,柴酒一两二钱,通计十三两。计管地四亩,包价值四两”。陈恒力等认为:“包价值四两”是指这四亩桑地如果自己不雇人耕种,包给人家耕治,需付工银四两,现在自己雇工来家耕治,就可以省了这四两银子的开支(61)。李伯重则认为“包价值”为桑园主包卖桑叶的预约定金,也就是说这四亩桑园雇人耕治后,能获利至少四两的卖桑叶的预约定金(62)。对“包价值”的意义虽有争论,但沈氏的桑园与茅氏及庄氏的桑园一样,都属于大农场雇工模式的经营。明末清初嘉湖地区的土地占有情况如张履祥所言,“四十亩之家,百人而不得一也。其躬亲买置者,千人而不得一也”(63)。张履祥也曾提到:“归安茅氏,农事为远近最,吾邑荘氏,治桑亦为七区之首。今皆废弃。”(64)可见至少到清朝初年,这种以大规模庄园形式出现的专业化桑园在嘉湖地区并不典型。
一般的小农家庭而言,既没有如数的土地,也无法获得相对应数量的资金、肥料与劳力投入。张履祥称:“吾里田地,上农夫一人止能治十亩。”(65)其好友邬行素过世,张为邬遗下老母、寡妻、幼子策划如何经营生计,“瘠田十亩,自耕仅足一家之食。若雇人代耕,则与石田无异。若佃于人,则计其租入,仅足供赋税而已。……莫若止种桑三亩,种豆三亩,种竹二亩,种果二亩,畜池鱼。……计桑之成,育蚕可二十筐”(66)。这里规划的桑地只有三亩,且与其它旱地作物并列,更体现小农经济种植多样化的特点。育蚕二十筐,以一筐蚕需叶八个计(67),共须吃叶三千二百斤,也就是说这三亩桑地平均亩产叶的水平为千斤。上文所提种桑三亩,实际上也是一年中一个劳动力在一亩桑地上劳力投入的极限。由此可见,小农经济的桑园规模往往正好是其养蚕需求的偶合。这种小农桑园的维持,需要付出很大的劳动力。小农桑园虽也有一定的专业化,却更普遍且更与小农经济相联系。但这种桑园更具有商品化和专业化生产的特征,有点像1980年代农村的专业户,一方面有专业化的种植,同时还兼业养蚕和其它农作。
对小农户来说,植桑投入的劳动时间长,收益见效慢。尤其是对湖州府低乡的小农家庭来说,植桑还需面对的是抵抗频繁的自然灾害的风险。明末以来,嘉湖地区自然灾害频繁,“自水利不讲,湖州低乡,稔不胜淹”(68)。一遇雨涝灾害,“何则水淹田地,禾败而桑亦枯也。种桑必五岁而后可蚕,是天荒一载,桑淹五年,故一遇水灾,致数年逋欠”(69)。而“桑之大利,总以十年为率”,育成一株“渐高七尺零”的高刈桑树(70),从育苗到成形,育成周期为10年(71);蚕的养育周期短,如果只养春蚕,所需时间为一个月左右。相比之下,养蚕较植桑所担负的风险更小。所以在湖州,小农选择只养蚕,不植桑,或只种少量的桑树。如南浔一带直到民国时期至1950年代,当地的农民仍喜欢养空头蚕(72)。
一般的小农家庭要扩大植桑规模绝非易事。养蚕的规模却可相对地扩大,因为养蚕所需的时间短,扩大规模只需增加短时间内劳动的强度,所需投入的资金可通过借贷的方式获得,在丝茧收益丰厚的年份,可立即获得回报。明末孙铨这样描述小农种桑的艰辛:“每地一亩种植桑柯,终岁勤动工以百数计。运泥培粪,修枝去虫,寒暑不辍,费银有余,一或堕失,五、六年始或可复,至于育蚕之际,男妇勤劬,寝食无暇,大小协力,柴炭工食,烦费尤难,少或怠忽,工本倍失矣。”(73)种植一亩桑地,每年“动工以百数计”。如果要管理三亩桑地的耕作,这几乎占据了整个农民一年中的时间。所以,一般的家庭,最多也只是种桑三亩左右,并且肥培管理上远远不可能达到《沈氏农书》中所提要求的水平。这种传统在吴兴地区一直保持到民国时期,“大约每户有田十亩,桑地即占其三、四”(74)。
桑园经营对小农来说也面对着生态变化,小农会根据生态的变化配置市场要素。桑叶价格低廉之年,农户蚕桑业上所得收入不足抵消对桑地的投入。“十五年丝绵稍稍得价,而叶贱如粪土,二蚕全白无收。所留头叶在地,并新抽二叶,几及一半生息,悉剪耗耘耕抛地,反费工食”(75)。小农无法对市场做出准确的把握,在桑叶供应过剩之年,多余的桑叶纵使用来养二蚕,且二蚕丰收,也收不回经营桑园时所投入的资金。一般情况下,当地通过稍叶的方式,农民可以将风险转嫁给市场,使桑园获得稳定化的收益。“梢者先期约用银四钱,谓之现梢,既收茧而偿者约用银五钱,再加杂费五分,谓之赊梢”(76)。这样通过定货的方式,使蚕户将养蚕的风险也转之于市场未来的收益。如果无人梢叶,农户还能通过多养二蚕来消耗多余的桑叶。《沈氏农书》提及:“近年夏叶竟无稍主,不得不稍养几筐二蚕,以防二叶丢空。”按当地的习惯,并不养二蚕,在当年桑叶无人购买的情况下不,沈氏不得已而养二蚕,养二蚕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桑叶的浪费。
一般的小农进行蚕桑经营时,均衡考虑资金、劳力的投入和桑叶市场价格的变化,灵活地在养蚕与桑叶买卖之间作出选择。购叶饲蚕的一个重要生态因素是蚕病问题,对农户来说,首先要担当养蚕后期的患蚕病风险,蚕成之后,还要考虑丝价的涨跌。桑叶价格奇高之年,直接售桑叶比买叶饲蚕更有利润。这种情况在专业化桑园集中的崇德、桐乡地区最为常见:
“崇西北十九都与湖之归安接壤,有余二,余四兄弟各育蚕十五筐,时嘉靖元年叶贵甚,余二兄弟尽欠叶,乃相与语曰,叶贵难买,即买叶得丝,不如卖叶得价,乃相与倾蚕于垃圾潭中,以泥盖之,乘早采叶驾舟来崇行至三里桥,忽水中跃一大鱼入舟,余四急以平板掩之,二人大喜,既至崇,则叶价贵益甚。”(77)
余二、余四两兄弟一共养了三十筐蚕,他们的桑叶不够,本来需要从市场上购买不足的桑叶来饲蚕,但当年桑叶价格又特别高,两兄弟计算花高价买桑叶饲育这三十筐蚕缫丝所得的收入,不如将自家现所持有的桑叶售出所得利润多,同时还能规避当年养蚕缫丝的辛劳,他们索性将蚕作了垃圾而将自家桑叶采了卖钱。
三 桑争稻田
嘉湖平原是水网圩田区,圩田因堤岸而成,“于大岸稍低处植以桑苎,谓之抵水”(78)。当地人通过在水中起堤以成圩岸,圩岸植上桑树又可起到固堤的作用。“近河之田,积土可以成地,不三、四年而条桑可食矣”(79)。因旱地基本上集中于圩岸,桑园一般也集中于圩岸上。“侬家有地十亩宽,半在陌头半墙下”。在湖州的南浔、菱湖等地,地势低洼,旱地少,村庄一般也坐落在圩岸区,这些地区的桑园大都分布在屋基地前后,河港两旁的高地上,如南浔沈炳震所描述的:“舍南舍北皆栽桑,千株万株绕屋旁。蚕多叶少行且尽,南塍一稜还沧桑。”(80)圩田内“界以埂,分为塍,久之皆成沃壤”(81)。塍和埂都是圩田中的高地,农民一般在田塍和田埂这些高地也种上桑树。
石门、桐乡一带旱地较多,桑园几乎分布在所有的旱地上。万历年间的崇德,“上下地必植桑,富者等侯封,培壅茂美,不必以亩计,贫者数弓之宅地,小隙必栽,沃若连属”(82)。1950年代的崇德县,桑树几乎栽在任何高地,如旱地、田埂、屋前屋后、道旁、河流两岸都是桑园(83)。明末以来,由于专业桑园经济在此区的发展,石门一带出产的桑苗也随之著名,被其他地区普遍引种,“轻船三板过南亭,蚕女提笼两岸经。曲罢残阳人不见,阴阴桑柘石门青”(84)。清初朱彝尊曾写道经嘉兴南亭一带,看到当地种的桑树都是石门的品种,到1950年代,专业化桑园集聚的崇德县,形成了“土壤零碎,水田、旱地交错,横埂、地墩、田角很多,水田、旱地高低不平,道路弯曲狭小”(85)的乡村景观。
在桐乡,桑园一般分布于两个地方,村子住宅附近的桑地为“内地”,远离村庄的桑地为“外地”。桑园中依据肥培条件而产量不同,“每亩采叶八、九十个”的为上好桑地,这种桑地一年必须施四次肥料,罱两次泥,深耕细作,并且桑地要经常除草,桑树也要经常捉虫。这种产量高的专业桑园一般分布在村子附近或路旁等易于运肥施肥和耕作的地区。“新填地和近水地埂”则用来压条培育小桑苗(86)。在1950年代的桐乡县屠甸镇桃园乡,屋脚门前的高地因肥料来源广,一般都发展成专业桑园,桑地并不套种或种植其他粮食作物,因为近人家,要防鸡食。其他肥料来源便当的近河圩头、近田田埂也被利用来做专业桑园。靠田近的田埂地,因挑稻干泥方便,也是发展专业桑园的好地点(87)。这种田中的桑埂地一般高出田面1—3米,与水田相互交叉,形成“桑基稻田”和“平原丘埂”地貌。
桐乡一带的平原圩田区种桑,必须对地面加以人工的改造。种桑之前须先治地,治地是指栽培桑树的培土过程。要保证桑根不在积水的环境下,必须投入大量的劳力开埨。“埨”是嘉湖地区农民的术语,即从地中开沟,将土叠加到沟边的高地上,“埨”与“垄”相近,但垄较高凸,埨较低平。“地将栽桑,须锄地分埨,使无积水”(88)。栽桑之前要在旱地中挖沟堞土,形成畦垄。嘉湖平原水网平原区,地下水位高,必须通过不断地叠加土层给桑根提供较为干燥的生长环境,桑树的根系才能发育良好。植桑之前还必须把地块培成比平地高出几尺的高台,培育适合桑树生长的地基,这样“治地”,每亩培高一尺约需50万斤土,培高5五尺需土250万斤(89)。
培土之后的桑树初植,需要大量施用稻干泥,《沈氏农书》提到要提高新压条的桑秧的成活率,“宜新填地,或近水地埂,冬天挑稻干泥一次”(90)。稻干泥易发根,种桑秧的时候,“开六寸深平潭,宜大不宜小。一人持秧枝放准潭中,将根理挺铺直,如有长根,亦须将潭开长,根不宜曲,一人垦取田中稻干泥,铺压根上,继以地上燥泥,盖满其潭,以足踏平,再用手将桑枝轻轻一提,再覆上细泥,略踏之”(91)。稻干泥能促进根系快速发育,施稻干泥一般用灌施的形式,这样可防止养分的流失。桑树发根之后,地上部分要发育好,还得通过施河泥、人粪等作为追肥,改良桑园土壤结构,提高土壤肥力。“用河泥,半干垦转,敲碎最肥,为益尤巨。一岁中雨淋土剥,专借此泥培补”(92)。传统时代肥料来源缺乏,桑农需要用大量的河泥来补偿桑园生长所消耗的地力。《沈氏农书》的《逐月事宜》中记载,罱泥是当地农家经常性的工作,“侯干挑在远地,泥干趁晴倒坯,晒曝如菱壳样,敲碎如粉方肥”(93)。罱来的河泥经过干燥处理后,作为肥料填加在原来的桑地土壤层之上。“河泥须用舟向市、村河中罱起,每年能以河泥浇复两次,则桑叶必盛。一次在二、三月间,正欲茁芽之先,一次在秋末冬初,均需平铺地面有五、六寸厚”(94)。
在圩田中地势低洼的里进田和溇心田植桑,需通过挖深池塘,将塘泥培高地基。《补农书》“策溇上生业”中就讲了一个里进田开发的例子:
“鑿池之土,可以培基,基不必高,池必宜深。其余土可以培周池之地。池之西或池之南,种田之亩数,略如其池之亩数,则取池之水足以灌禾矣。池不可通于沟,通于沟,则妨邻田而争起。周池之地必厚;不厚,亦妨邻田而丛怨。池中淤泥,每岁起之,以培桑竹,则桑竹茂而池益深矣。”
这段话讲的是张氏为里进田开发所做的策划。张氏强调,“凿池之土以培基。基不必高,池必宜深”,就是利用溇沼本来的地势,将溇港凿深为池,用池中取出的土培基。培基即叠土将地面抬高,一是培房基,一是培地基,地基一般用来种桑。在圩田内的低洼积水区域植桑,必须将地基垒成高台,否则桑树无法存活。里进田中因为长期地下水位高少有人居住,经过这样数年的培基之后,可以“筑室五间,七架者二进二过,过各二间。前场圃、后竹木、旁树桑。池之北为牧室三小间,圃丁居之。沟之东,傍室穿井”。这样经过常年的培高地土,里进田也可植桑定居。
头进田和二进田稍高,桑园主要是以箱子田的形式发展。箱子田指四周为堆叠成较高的种桑旱地,中间是长方形的箱子形状的低平水田(95)。明末清初是嘉湖地区蚕丝业大兴盛时期,蚕丝业的繁荣带来日益增长的桑叶需求,专业化桑园的植桑开始向稻田进军。治地种桑,比种田得利丰厚得多,“地之利为博,多种田不如多治地”(96),这一点明末以来已为当地所共识,导致农民人为地将桑地由圩岸向稻田扩展。桑树是深根性植物,在嘉湖水网平原区,圩田中的稻田因地势低洼,并不具备植桑的条件。农民需要培高地基来植桑,而非直接在稻田中种桑树。明末以来,“桑争稻田”在微地形地貌上的展开,往往是以高地桑田为出发点,逐步以蚕食的方式向周边水田侵蚀。农民年年罱河泥和挑稻干泥来堆叠桑地,稻田被越挖越深,而桑地则被逐年培高。低洼的稻田与高亢的桑埂地镶嵌,成箱子状,稻田与桑地的高差可达2米左右。在一个圩田中,头进田、二进田、里进田中间也隔着桑埂,桑埂地呈狭长的条带状,插花在稻田之间(97)。这些桑埂改变了原来的水网圩田内的地形地貌,使其较规整的景观逐渐被破碎,如1956年的嘉兴建成公社,平均每块田面为三十亩,在这三十亩田中间又各有小田段,大田块与大田块、小田段与小田段之间,都隔着桑埂(98)。
除位于圩岸的桑园存在时间较长外,稻田中的桑埂都是以培高原稻田中的田埂而新填出来。这些桑埂面积一般几分大小,多为长条状,且分布零散。明末清初的桐乡地区,当地农民长期在稻田中挑泥给桑地施肥,“计岸土取土于田,岸宽则田窄小”(99)。田埂上的桑园处于离居住地较远的水田中间,积肥运肥比较困难,“罱泥固好,挑稻干泥亦可省工”(100),当地农民一般采取挑两旁稻田中的稻干泥的办法来给田埂桑园的桑树施肥。位于田埂的桑园,表土一般不深,且易淋失,每年冬天需通过挑稻干泥来给桑地加土。由于稻干泥发根能力强,在桐乡县屠甸镇,改造生产不良的专业桑园,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挑稻干泥。甚至像在桃园乡港子头、三路头这样近河港圩头上的专业桑园,因土壤流刷,表土层薄,仍是用从附近稻田挑稻干泥来加土的方法来加土(101)。
年年挑挖稻田中的泥土来施肥于桑地,使桑地两旁的水田耕作层变浅,养分缺失,且田底高低不平,耕作不便。结果导致当地稻田粮食产量不高。张履祥称清初桐乡“田极熟,米每亩三石,春花一石有半,然间有之,大约共三石为常耳”。桐乡一带特别丰收的年份的稻田产量为四石半,平常的年份春花加米的产量才三石。与之相比,湖州一带的水田一亩,能收四、五石。上文中提到湖州种春花尚不普遍,那么这一亩的产量指的就是产米量(102)。设若处于平常年份的一般水平,湖州水稻的平均产量,也几乎为桐乡的两倍左右,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50年代。
嘉兴县洪合乡就是一个专业桑园集中的典型地区,当地因产桑叶量大,一直被称为“叶山”,甚至到1950年代蚕桑经济极其衰落的时期,仍有桑园1870亩左右。据当地的调查资料,民国十年前后,当地双园(桑园)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65.57%,超过水稻面积的17.57%,那时茧价每斤为7—8角,每担鲜茧价值75元左右,当时米价每石为7元,蚕茧大米的比价为1∶10.7,因此大大促进了双园(桑园)肥培管理的积极性。加上那时的水田产量不高,虫害严重,每亩水稻田仅能收200斤到280斤的稻谷。当地农民对水稻产量有“石伯伯”,“石二老相公”的说法,形成了“重蚕双(桑)轻水稻”的现象(103)。
综上,可知“桑争稻田”所表现出来的,并非土地利用上的桑地耕作完全取代稻田耕作,而是专业化桑园经济发展过程中,培植桑园时取土取肥于稻田,使稻田减产。康熙年间,何金蔺路经此地,曾记下,“余行桐乡道中桑圃间,提筐者忘其劳苦,甚是适言,吾乡以蚕代耕者十之七”(104)。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桑争稻田”是当地的植桑经济排挤稻作经济的结果。
四 小结
嘉湖平原蚕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明末清初是十分重要的阶段,专业化桑园的经营模式,区域的集聚在此时间段内形成。高度繁荣的蚕桑经济,推动了蚕桑业内部养蚕业与植桑业的分化。由于地理条件上的限制,旱地成为嘉湖平原蚕桑业发展中最为稀缺的资源。崇德、桐乡一带处于嘉湖平原低地中相对较高的区域,地理环境上是嘉湖平原内部最适宜植桑的区域,在湖州蚕丝业的推动下,大量专业化桑园在本区内出现。专业化桑园在区域内的集聚使嘉湖平原蚕桑业的进一步分离,蚕桑业的分离又导致了养蚕业和植桑业的规模化。总之,专业化桑园经济的形成顺应并强化了蚕桑业内部的分工和协作,并给“湖丝”这一地区品牌提供了持久的竞争力。在植桑产业集中的区域,农民长期以来培土植桑,改变了专业桑园集中区域的农业经济结构,塑造出以桐乡为代表的水网平原地区高低不平的地面景观。
注释:
①[清]唐甄:《潜书》下篇下《教蚕》,续修四库全书945册。
②[宋]程俱:《北山小集》卷37《乞免秀州和买绢奏状》,四库全书本。
③嘉泰《吴兴志》卷20《物产》,嘉业堂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
④[宋]陈旉撰,万国鼎校注:《陈旉农书校注》卷下,(北京)农业出版社,1965年,第55页。
⑤嘉泰《吴兴志》卷20《物产》,嘉业堂刊本,成文出版社,1983年。
⑥[宋]陈旉撰,万国鼎校注:《陈旉农书校注》卷下,(北京)农业出版社,1965年,第55页。
⑦嘉泰《吴兴志》卷20《物产》,嘉业堂刊本,成文出版社,1983年。
⑧[清]沈练著,仲昴庭辑补,郑辟疆、郑宗元校注:《广蚕桑说辑补》卷上《培养桑树法十九条之桑地说》,(北京)农业出版社,1960年,第1页。
⑨[宋]范成大著,富寿蓀标校:《范石湖集》卷3《香山》(吴王种香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5页。
⑩[元]方澜:《石门夜泊》,[清]沈季友撰:《槜李诗繁》卷38,四库全书本。
(11)稽发根:《湖丝—辑里湖丝源流考》,《农业考古》2003年第3期。
(12)[明]朱国桢:《涌幢小品》卷2《蚕报》,(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4—45页。
(13)钱天达:《中国蚕丝问题》第1章《概论》,黎明书局,民国25年。
(14)张炎贞:《乌青文献》卷3。
(15)[明]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卷13,(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
(16)[清]凌介禧:《东南水利略》卷5《中国水利志丛刊》,(扬州)广陵书社,2006年。
(17)[明]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卷10,(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
(18)范金民:《江南丝绸史研究》,(北京)农业出版社,1993年;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与变革》,(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日]滨岛敦俊:《明代江南农村社会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王家范:《晚明江南士大夫的历史命运》,《史林》,1987年第2期;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陈学文:《明清时期湖州的丝织业》,《浙江学刊》,1993年第3期。
(19)全汉升:《自明季至清中叶西属美洲的中国丝货贸易》,《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新亚研究所,1972年。
(20)范金民认为,日本江户时代对华丝需求减少也是原因之一。范金民:《江南丝绸史研究》,(北京)农业出版社,1993年,第278页。
(21)据李伯重的估计,到17世纪初,江南丝输出量每年达11000担左右。李伯重:《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11页。其他相关研究参阅,吴承明:《论明代国内市场和商人资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5集;范金民:《明代江南丝绸的国内贸易》,《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清代江南丝绸的国内贸易》,《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
(22)全汉升:《自明季至清中叶西属美洲的中国丝货贸易》,《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新亚研究所,1972年,第451—472页。
(23)[明]宋应星著,潘吉星译注:《天工开物译注》卷上《乃服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99页。
(24)光绪《嘉兴府志》卷32《艺文二·张东侯郡守屏风记》。
(25)顾炎武:《日知录》卷10《纺织之利》。
(26)嘉靖《德清县志》卷3《食货考》。
(27)[明]孙铨:《上郡守论田地六则》,[清]孙志熊撰:《菱湖镇志》卷42《事纪》。
(28)[清]董蠡舟:《稍叶》,民国《新塍镇志》卷3《桑》。
(29)[清]蔡容升原纂,蔡蒙续纂:《双林镇志》卷14《蚕事》。
(30)吴兴县农林局:《雨涝后桑园管理经验》,1954年,湖州市档案馆,W73—7—10。
(31)[明]朱国桢:《涌幢小品》卷2《蚕报》,(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5页。
(32)[清]王凤生:《浙西水利备考》,《秀水县水道图说》,(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
(33)[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卷18。
(34)[清]汪日桢纂:《南浔镇志》卷21《农桑》,董蠡舟:《稍叶》。
(35)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水利电力部太湖流域管理局:《太湖流域水系与地形图》,1987年。
(36)[明]徐光启撰,石声汉校注:《农政全书校注》卷3《农本·国朝重农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76—77页。
(37)张履祥著,陈祖武点校:《杨园先生全集》卷8《与孙商声》,(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44页。
(38)苏惇元:《杨园先生年谱》,张履祥著,陈祖武点校:《杨园先生全集》附录,(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498页。
(39)张履祥著,陈祖武点校:《杨园先生全集》卷19《耕赁末议》,(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71页。
(40)张履祥辑补,陈恒力等校释:《补农书校释》(增订本),(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101页。
(41)张履祥著,陈祖武点校:《杨园先生全集》卷48,(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42)[清]孙嘉淦:《南游记》,[清]张潮辑:《虞初新志》卷17。
(43)[明]李日华著,屠友祥校注:《味水轩日记》,(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67页。
(44)张履祥辑补,陈恒力等校释:《补农书校释》(增订本),(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101页。
(45)[明]王士性撰,周振鹤点校:《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66页。
(46)张履祥辑补,陈恒力等校释:《补农书校释》(增订本),(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163页。
(47)正德《桐乡县志》卷9。
(48)《杭嘉湖地区土地利用图》,严重敏等:《杭嘉湖地区水土资源的综合利用问题》,《地理学报》,1959年第25卷第4期。
(49)[清]张燕昌:《鸳鸯湖棹歌》,[清]王昶:《湖海诗传》卷41,嘉庆刻本。
(50)乾隆《海盐县志图经》卷1。
(51)[清]沈练著,仲昂庭辑补,郑辟疆、郑宗元校注:《广蚕桑说辑补》卷下《饲蚕法六十六条》,(北京)农业出版社,1960年,第45页。
(52)[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2《蚕报》,(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5页。
(53)[清]孙志熊撰:《菱湖镇志》卷12《蚕桑·稍叶》。
(54)田尻利:《清代农业商业化の研究》第6章《太湖南岸地方にぉける桑葉壳買》,汲古书院,1999年。
(55)[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2《蚕报》,(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5页。
(56)正德《新市镇志》卷1。
(57)[明]朱国桢:《涌幢小品》卷2《蚕报》,(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5页。
(58)[明]茅坤:《玉芝山房稿》卷10《文林郎大宁都司参军亡弟双泉墓志铭》,四库存目本;张大芝、张梦新点校:《茅坤集》卷23《亡弟双泉墓志铭》,(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681页。
(59)张履祥辑补,陈恒力等校释:《补农书校释》(增订本),(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12、56、57页。
(60)转引自[日]滨岛敦俊:《明末江南乡绅の具体像》,谷口规矩雄、岩见宏编:《明末清初の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9年,第192—195页。
(61)张履祥辑补,陈恒力等校释:《补农书校释》(增订本),(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1、47、54、66页。
(62)李伯重:《对〈沈氏农书〉中一段文字的我见》,《中国农史》,1984年第2期。
(63)张履祥著,陈祖武点校:《杨园先生全集》卷8《与徐敬可》,(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27页。
(64)张履祥辑补,陈恒力等校释:《补农书校释》(增订本),(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152页。
(65)张履祥辑补,陈恒力等校释:《补农书校释》(增订本),(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148页。
(66)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上海)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民国28年,第8页。
(67)张履祥辑补,陈恒力等校释:《补农书校释》(增订本),(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81—82页。
(68)张履祥辑补,陈恒力等校释:《补农书校释》(增订本),(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132页。
(69)[清]凌介禧:《程安德三县赋考》卷2,同治三年木活字本。
(70)[清]朱点辑:《东郊土物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
(71)[清]沈练著,仲昂庭辑补,郑辟疆、郑宗元校注:《广蚕桑说辑补》卷下《杂说九条》,(北京)农业出版社,1960年,第62页。
(72)吴兴县农林局:《南浔区蚕桑生产情况》,1956年,湖州市档案馆,W73—9—43;开叶船,参阅汪日桢纂:《南浔镇志》,董蠡舟,《稍叶》:“三眠后买叶者以舟往,谓之开叶船。”
(73)[清]孙志熊撰:《菱湖镇志》卷42《事纪》,引明孙铨上郡守《论田地六则》。
(74)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上海)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民国28年,第29,103页。
(75)张履祥辑补,陈恒力等校释:《补农书校释》(增订本),(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170页。
(76)张炎贞:《乌青文献》卷3。
(77)万历《崇德县志》卷12《蚕桑》。
(78)[明]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18《沈啓隄水岸志》,四库全书本。
(79)张履祥著,陈祖武点校:《杨园先生全集》卷6《与曹射侯一》,(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69页。
(80)[清]汪日祯撰,蒋猷龙校释:《湖蚕述》卷末,(北京)农业出版社,1987年,第125、133页。
(81)[明]朱国桢:《涌幢小品》卷6《隄利》,(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38页。
(82)万历《崇德县志》卷2《物产》。
(83)崇德县政府农林科:《一九五二年崇德县养蚕工作总结》,1952年,桐乡县档案馆,30—1—155。
(84)[清]朱彝尊撰:《曝书亭集》卷9,四部丛刊本。
(85)桐乡县崇福公社普规办公室:《用土壤普查成果制定今年丰产计划》,1959年,嘉兴市档案馆,59—1—007。
(86)张履祥辑补,陈恒力等校释:《补农书校释》(增订本),(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75、76、113页。
(87)桐乡县屠甸人民公社:《本社关于桃园管理区水田、旱地、花白、桑林、什地土壤种类方面汇总普查表》,1959年3月—1959年4月,桐乡县档案馆,87—1—138。
(88)[清]沈练著,仲昂庭辑补,郑辟疆、郑宗元校注:《广蚕桑说辑补》卷下《饲蚕法六十六条》,(北京)农业出版社,1960年,第1页。
(89)陈恒力等:《补农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83页。
(90)张履祥辑补,陈恒力等校释:《补农书校释》(增订本),(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101页。
(91)[清]汪日祯撰,蒋猷龙校释:《湖蚕述》卷1,(北京)农业出版社,1987年,第18页。
(92)[清]汪日祯撰,蒋猷龙校释:《湖蚕述》卷1,(北京)农业出版社,1987年,第28页。
(93)[清]张履祥辑补:《补农书校释》(增订本),(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61页。
(94)[清]章震福:《广蚕桑说辑补校订》卷1,农工商部印刷科刊印,光绪三三年。
(95)宫春生:《太湖地区土地类型特征》,《太湖流域水土资源及农业发展远景研究》,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北京)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65页。
(96)[清]张履祥辑补,陈恒力等校释:《补农书校释》(增订本),(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101页。
(97)桐乡县农业区划委员会:《桐乡县农业综合区划》上册,桐乡县农业区划委员会办公室编印,1985年。
(98)陈恒力等:《补农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23页。
(99)民国《南浔志》卷4《河渠》。
(100)张履祥辑补,陈恒力等校释:《补农书校释》(增订本),(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60页。
(101)桐乡县屠甸人民公社:《本社关于桃园管理区水田、旱地、花白、桑林、什地土壤种类方面汇总普查表》,1959年3月—1959年,桐乡县档案馆,87—1—138。
(102)陈恒力编注,王达参校:《补农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7—29页。
(103)《嘉兴专署关于嘉兴县洪合乡五星农业社蚕桑调查研究工作的总结报告》,1957年,湖州市档案馆,68—9—19。
(104)何金蔺:《课蚕》,康熙《桐乡县志》卷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