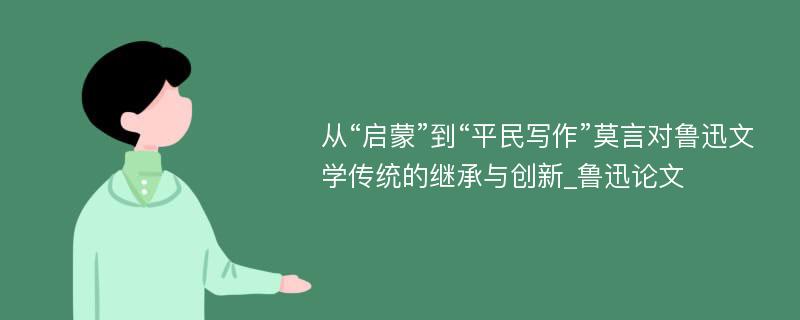
从“启蒙”到“作为老百姓写作”——莫言对鲁迅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老百姓论文,传统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5)01-0006-07 在近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鲁迅先生的影响无疑是最为巨大的。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毫无保留地表达了他对鲁迅的肯定与推崇: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① 在这短短的一段文字中,毛泽东连用七个“最”字,极其强烈地反映了他对鲁迅的看法,赞美之情溢于言表。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中,人们一直沿袭着毛泽东对鲁迅的认识,并以此作为衡量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的一个重要标杆。 然而,在2012年10月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有些人对鲁迅的态度与评价似乎有些怀疑与动摇起来。这并不仅仅在于,鲁迅在从事他的文学活动时诺贝尔文学奖已经设立而他并无获此殊荣,而且还在于,莫言与鲁迅的文学观念不尽相同,甚至还有截然相反的地方。这不能不令人心生疑虑:到底是应该沿着莫言的文学路子走下去,还是应该继续坚持鲁迅的方向?他们两人的文学观念谁更符合文学的实际? 这确实是文学研究者在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因为,它不仅有助于澄清人们在文学观念上的认识误区,而且也有利于未来当代文学的更好发展。 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鲁迅曾经这样明确地表示过他的文学观念: 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② 在这里,鲁迅的文学观念很显然是工具论的。他在意的并不是小说自身,而是在于小说可以改造国民性,可以启蒙大众,可以唤醒民众。一句话,这仍然是中国传统文以载道观念的翻版,区别只在于,在古代,文以载道主要是通过诗、文,而到鲁迅这里,小说也可以承载起教化的功能。鲁迅先生这种工具论的文学观念,萌生于20世纪初在日本仙台医专读书时期。在一次偶然的教学幻灯片中,他看到一群神情麻木的中国人,在面对被砍头的同胞时只是围着看热闹,深受刺激:“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他觉得:“第一要者,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③于是,决定弃医从文,以文学为武器改造愚弱的国民的魂灵。在日后的文学创作中,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祝福》、《风波》、《肥皂》、《白光》等作品,大多践行着他的文学启蒙主张,积极参与到20世纪中国社会思想与文化的变革之中。 而莫言的文学观念却是与鲁迅的上述观点恰恰相反,甚至是有意针锋相对。 2001年,他在苏州大学所作《试论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的演讲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与“启蒙”、“改造国民性”相反的文学主张,即“作为老百姓”写作: ……为老百姓写作,也就是知识分子的写作,这是有漫长的传统的。从鲁迅他们开始,虽然也是写的乡土,但使用的是知识分子的视角。鲁迅是启蒙者,之后扮演启蒙者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谴责落后,揭示国民性中的病态,这是一种典型的居高临下。其实,那些启蒙者身上的黑暗面,一点也不比别人少。所谓的民间写作,就要求你丢掉你的知识分子立场,你要用老百姓的思维来思维。④ 循着“作为老百姓写作”的思路,莫言认为真正伟大的作品必定是毫无功利的创作:“作家千万不要把自己抬举到一个不合适的位置上,尤其在写作中,你最好不要担当道德的评判者,你不要以为自己比人物高明,你应该跟着你的人物脚步走。”⑤他举我国伟大的二胡演奏家阿炳的例子。作为穷困潦倒、双目失明的瞎子,阿炳没有把自己当成贵人,甚至不敢把自己当成一个好的百姓,这才是真正的老百姓的心态,这样心态下的创作,才有可能出现伟大的作品。因为在莫言看来,《二泉映月》中那种悲凉是发自灵魂深处的,是触及了他心中最疼痛的地方的。 在以往研究者通常的认知与观察中,“启蒙”与“作为老百姓写作”是鲁迅和莫言俩人最为醒目的文学印记,是俩人文学观念的核心;而且,其距离还是那样的南辕北辙! 不过,如果细细分析他们俩人的文学观念,全面而系统地梳理他们的文学追求,并深入研究他们的文学创作,我们却又能惊奇地发现,他们的文学观念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脉相承的,是并不矛盾的。在这里,既涉及鲁迅文学观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的问题,也关联到莫言对鲁迅文学传统的个人化理解与深入把握。 先说鲁迅文学观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由于“极左”路线时期对鲁迅长期的美化与神化,在人们一般的观念之中,鲁迅就是一个战斗者的形象,他的文学观念无疑是革命的、启蒙的,是为人生的。然而,通读《鲁迅全集》后你会发现,其实鲁迅的文学观念是极为复杂的、矛盾的。⑥ 在各个不同时期,鲁迅的文学观念就有不同的内容。20世纪在日本仙台医专留学时,是鲁迅“启蒙”文学观念形成的起点。他曾这样自述:“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⑦这种热情,促使他翻译了《域外小说集》等一批被压迫被迫害的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到“五四”时期,他怀着毁坏“铁屋子”的希望,一发而不可收地创作出了《呐喊》、《彷徨》中的二十余篇小说,并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旗手地位。由于《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小说长期收入我国中学语文课本,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而在“五四”时期,又是鲁迅为人生的启蒙文学理想最为淋漓尽致地实践的时候,因而,人们便似乎形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鲁迅的小说是启蒙的,是改造国民性的。1919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家,是能引路的先觉,不是‘公民团’的首领。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品,是表记中国民族智能最高点的标本,不是水平线以下的思想的平均分数。”⑧“引路的先觉”,正是鲁迅对现代作家的要求,以及他对自己的期许。其后,鲁迅对这种启蒙文学观念的表达似乎并未中断,而是时时提起。例如,1933年,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得更为明确:“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做不过是‘消闲’的新式别号。”⑨ 以上论述难免给后来的研究者造成一种错觉,认为鲁迅是一个彻底的文艺工具论者,他是始终不渝抱定“为人生”、“为启蒙”的小说主张的。 然而,其实不然。 尽管我们可以在“五四”新文学运动高涨时期,发现鲁迅是一个启蒙主义运动的热情鼓吹者与倡导者,不过,时隔不久,在“五四”运动退潮时,他的热情便大大地衰退了,以致由原先的大声“呐喊”,转而变为疑虑重重的“彷徨”。他当时的感觉是:“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自然也有人认为文学于革命是有伟力的,但我总觉得怀疑。”⑩与前几年“引路的先觉”的自负与自许相比,现在的心境又何止是判若云泥!1927年,他在广州所作的一次有关文艺与革命的演讲中,这样袒露着他对于文艺功能的认识:“在这革命地方的文学家,恐怕总喜欢说文学与革命是大有关系的,例如可以用这来宣传,鼓吹,煽动,促使革命和完成革命。不过我想,这样的文章是无力的,因为好的文艺作品,想来多是不听别人的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从心中流露出来的东西……”(11)这种对文学“无力”感的认识,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例证,而是在“五四”退潮直到他去世时经常流露出来的一种情绪。对于“左联”倡导的无产阶级文艺,他感到:“……先前原不过一种空喊,并无成绩,现在连空喊都没有了。新的文人,都是一转眼间,忽而化成无产文学家的人,现又消沉下去,我看此辈于新文学大有害处。”(12)至于“遵命文学”,更是令鲁迅不堪:“……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地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地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13)甚至,在鲁迅先生临去世前不久,他在写给许广平的遗嘱中还这样交代:“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14)在这里,尽管明显有着他对三十年代乌烟瘴气的文坛乱象的愤激之意,一种难以抑制的情绪化表达,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他在此对文艺的启蒙功能、教化功能已经大大消隐了,乃至彻底失望了。 一个令今天的读者颇觉困惑的问题是:既然如我们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鲁迅的文学观念是复杂的、混合的,并不是那么单一的、明净的,那么,在绝大多数的读者心目中,为什么仅仅只留存下一个为人生的、启蒙的鲁迅先生的形象呢?为什么一提起他,人们总会首先想到勇于担当、改造国民性的鲁迅呢?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归纳起来无非是以下两点:一是前面提到的,鲁迅文学创作的辉煌时期正是他抱定文学启蒙主张的人生阶段,他的代表性名作如《阿Q正传》、《狂人日记》、《药》、《孔乙己》等等,都是创作于这一时期;二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时代和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阶段,人们对鲁迅的学习与宣传进行了过于片面化的引导与发挥,以致这种影响短时间内仍然无法完全消除。而这,自然极大地影响到人们对鲁迅文学传统的理解与接受。 其实,对于鲁迅文学传统的准确把握与认识,还有另外一个极佳的角度,那就是研究鲁迅的文学史观,具体地说,就是他的小说史观。 与现代文学中其他大师不同的是,鲁迅还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文学史家,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的重要开创者。他的《古小说钩沉》、《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编著,显示了他扎实的古典文学功底与清晰的文学史观。他对文学的功能、价值与作用的认识,在其中有着真实的记录。 在《中国小说史略·唐之传奇文》一篇中,他认为唐传奇是中国小说史的辉煌部分。“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15)在鲁迅的心目中,“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托讽喻以抒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16)在这里,显而易见的是“叙述宛转”、“文辞华艳”和“文采和意想”,构成了鲁迅对于唐传奇充满敬意的原因。而到了宋代,传奇中充满教训意味,令人生厌。他在《唐宋传奇集序例》一文中,这样评价宋传奇:“宋好劝惩,庶实而泥,飞动之致,渺不可期,传奇命脉,至斯以绝。”(17)好劝惩,多教训,以致传奇小说中本该具有的“飞动之致”,在宋代渺不可寻,最终,也导致了传奇的衰亡。这种重艺术而轻思想的观念,应该是鲁迅小说史观的基本特色。 在《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一讲中,鲁迅还这样评价着《红楼梦》、《儒林外史》和清末谴责小说。对于《红楼梦》,鲁迅的肯定是无以复加的:“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人,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由《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18)对于《红楼梦》这部中国小说史上最伟大的巨著,鲁迅的肯定标准是“如实描写”、“并无讳饰”,至于小说的主题与微言大义,见仁见智,自然无需主观推测。而对于讽刺小说《儒林外史》,鲁迅则认为作者吴敬梓“多所见闻,又工于表现,故凡所有叙述,皆能在纸上见其声态;而写儒者奇形怪状,为独多而独详。”(19)在此,鲁迅对它的推崇是在于“变化多而趣味浓”、“工于表现”和“见其声态”,而并非是作者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与讽刺小说本身。至于晚清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所谓谴责小说,鲁迅先生则认为差得远了。“……描写社会的黑暗面,常常张大其词,又不能穿入隐微。”(20)虽名为讽刺小说,其实已等同于谩骂了。尽管名噪一时,但终不能进入一流文学经典的行列。这是鲁迅小说史观的基本基调。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与把握鲁迅文学传统的特质与内涵。作为一个具有崇高社会理想的作家,鲁迅是愿意将文学作为武器,倾全力投身于民族与国家的振兴之中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也认识到这是“唯心”之论,文学的作用也只能如一箭之于大海;尽管作为一个杰出的文学史家,他深深地知道文学应该少劝惩,少教训,少教化,不过,在风沙扑面的虎狼社会,他又不愿意躲进象牙之塔,而放弃自己的社会担当。为此,鲁迅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满怀着激愤和忧伤。 最后,他将杂文作为自己主要的文学武器,像匕首和投枪,向罪恶的社会发出他的怒吼与控诉。由此,他的启蒙,他的为人生的文学传统,在后来的读者眼中,也愈益显得耀眼与夺目。 莫言比鲁迅小74岁。鲁迅去世19年后,莫言才在山东高密东北乡出生。然而,时间上的差异却并没有阻碍他们在文学传承上的紧密联系。 据莫言自述,大约七八岁时,他就开始阅读鲁迅了。“第一次读鲁迅是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哥放在家里一本鲁迅的小说集,封面上有鲁迅的侧面像,像雕塑一样的。我那时认识不了多少字,读鲁迅的书障碍很多。……但《狂人日记》和《药》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我自然不懂什么文学理论,但是我也感觉到了,鲁迅的小说,和那些‘红色经典’是完全不一样的小说。”(21)莫言的大哥管漠贤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学生,热爱文学,他留在老家的是一本当年十分流行的《鲁迅选集》。而当时正是主题先行、文学中充满政治意味的所谓“红色经典”泛滥的时期,年少的莫言,准确地感到鲁迅的小说是与“红色经典”格格不入的。由此,引起了莫言对鲁迅的热爱与敬佩。 年岁稍长,到“文革”时期,鲁迅的作品更是成为莫言的珍爱之物。“那岁月正是鲁迅被当成敲门砖头砸得一道道山门震天响的时候。那时的书,除了《毛选》之外,还大量地流行着白皮的、薄薄的鲁迅著作的小册子,价钱是一毛多钱一本。我买了十几本。这十几本小册子标志着我读鲁迅的第二个阶段。”(22)那时一个物质条件极其匮乏的时期,饿得连一顿饱饭都难吃上,然而,莫言还是节衣缩食,买了十几本鲁迅的小册子,其喜爱程度可见一斑。“这一阶段的读鲁是幸福的、妙趣横生的。除了如《故乡》、《社戏》等篇那一唱三叹、委婉曲折的文字令我陶醉之外,更感到惊讶的是《故事新编》里那些又黑又冷的幽默。尤其是那篇《铸剑》,其瑰奇的风格和丰沛的意象,令我浮想联翩,终生受益。……一个作家,一辈子能写出一篇这样的作品其实就够了。”(23)对于鲁迅的敬意,溢于言表。 莫言最推崇的是鲁迅的短篇历史小说《铸剑》。他觉得这不仅是鲁迅最好的小说,甚至还是中国最好的小说。“第一次,从家兄的语文课本上读到鲁迅的《铸剑》时,我还是一个比较纯洁的少年。读完了这篇小说,我感到浑身发冷,心里满是惊悚。那犹如一块冷铁的黑衣的宴之教者、身穿青衣的眉间尺、下巴上撅着一撮花白胡子的国王,还有那个蒸汽缭绕灼热逼人的金鼎、那柄纯青透明的宝剑、那三颗在金鼎的沸水里唱歌跳舞追逐啄咬的人头,都在我的脑海里活灵活现。”(24)在空旷的田野上,莫言常常不由自主地如小说中的人物那样大声歌唱:阿呼呜呼兮呜呼呜呼——这是鲁迅的原文;后边是他的创造——呜哇啦嘻啰呜呼。歌声嘹亮、高亢,在莫言的引领下,几乎是半个县的孩子都学会了这歌唱。 对于群星闪耀的中国现代文学,莫言最佩服的是鲁迅和沈从文两位。他直言道:“五四时期那么多作家,也就是鲁迅、沈从文可以称为文学大师。老舍就有点勉强,他的作品良莠不齐。张爱玲也很难说是一个大师级的作家。”(25)当时,他自谦地认为,即使再奋斗二十年,他也不可能达到鲁迅的水准,而老舍嘛,奋斗二十年,可能与他有些作品一样好。他对鲁迅有着真切的了解与认识。“鲁迅一直是我们的榜样,但被误解甚多,长期被当成棍子打人,其实,那些把鲁迅当成棍子的人,正是鲁迅深恶的。”(26) 1988年,他在给张志忠所著《莫言论》所作的“跋”中,披露了一段他抄在红皮本子上的鲁迅语录,以此作为他对文学的理解:“……文艺是纯然的生命的表现,是能够全然离了外界的压抑和强制,站在绝对自由的心境上,表现出个性来的惟一的世界。忘却名利,去除奴隶根性,从一切羁绊中解放出来,这才能成为文艺上的创作。必须进到与那留心着报章上的批评、算计着稿费之类的全然两样的心境,这才能成为真正的文艺作品。因为能做到的仅被心里燃烧着的感激和情热所动,象天地创造的曙神所做的一样程度的自己表现的世界,是仅有文艺而已。”(27) 这段被莫言作为座右铭抄在红皮本子上的鲁迅语录,莫言说是出自鲁迅翻译的一位日本文艺理论家之口,在他心灵深处感到“真是好极了”。在这段座右铭中,文艺是一种超越于名利、教化的纯然的生命表现,它不能算计“稿费”,也不必留心报章上的批评,而应该是“全然离了外界的压抑和强制”的自由心境的结晶。我们发现,被莫言奉若至宝的这段文艺隽语,是无功利的,非工具论的。在莫言文学观念的形成中,他吸收的是鲁迅文学传统中的一个方面。它不是启蒙的,也不是为人生的,而是“从一切羁绊束缚中解放出来”的纯正态度。 循此思路,莫言进而还思索起鲁迅作品的优劣,进行着高下之分。 他感到:“……鲁迅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但是鲁迅这种伟大的思想是和他的小说不太相配的。鲁迅后期的杂文中的思想锋芒,看问题的透彻深刻,应该是超越了他前期小说的思想水平的。但由于种种原因,鲁迅没有写出和他后期思想相匹配的小说。”(28)他认为,伟大的小说都是思想大于形象的,作家未必要先成为一个哲学家和思想家才可以写作。他反问道:沈从文的思想先进、深刻吗?张爱玲的思想先进吗?深刻吗?然而,他们不都是照样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吗?他进一步断定:“鲁迅不适合写长篇小说,就是因为他太有思想,思维太清楚了。长篇小说需要一种模糊的东西,应该有些松散的东西,应该有些可供别人指责的地方,里面肯定有些败笔,有些章节可以跳过去。”(29)鲁迅早在20年代中期就曾有创作长篇小说《杨贵妃》的打算,然而直到去世仍未动笔,原因肯定多样,但莫言指出的鲁迅过于深刻的思想,应该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对于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莫言认为其中有《铸剑》那样极为出色的篇章,然而也有“败笔”:“他经常把一己的怨怼,改头换面,加入到小说中去。如《理水》中对顾颉刚的影射,就是败笔。……油滑和幽默,只隔着一层薄纸。”(30) 有发自肺腑的崇拜,也有自己冷静、清醒的分析,鲁迅文学创作中的经验与教训,构成了莫言在继承与接受时的重要借鉴。 不过,对于同样也生活于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中的莫言来说,他想始终保持文学上“绝对自由的心境”,其实也是不可能的。在这里,他也势必面临与鲁迅一样的困扰。 他坦陈:“我自己虽然非常清醒地知道,小说应该远离政治,起码应该跟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形,使你无法控制住自己,使你无法克制自己,对社会上不公平的现象,对黑暗的政治,发出猛烈的抨击。”(31)比如在1987年他所写的那部长篇《天堂蒜苔之歌》中,就以非常激烈的态度,对政治进行了干预。他以三十五天的时间,义愤填膺地写出这部为农民鸣不平的急就章。同年冬天,他有感于社会上流传“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做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么一种说法,以弱势群体的教师为内容,创作了长篇小说《十三步》,替教师说话。1993年,在长篇小说《酒国》中,也有对政治的尖锐批评。他自述道:“虽然用了曲折的笔法,但是作品骨子里还是表现了对社会上的腐败现象、腐败官员的一种深深的愤怒。直到2009年,他在长篇小说《蛙》中,尤其是在最后一章的荒诞剧中,对计划生育造成的社会乱象加以讽刺与抨击。 在这里,莫言显然又回到了鲁迅的又一个文学传统。他想创作一种超越的、闲适的、远离政治的作品,然而,现实的刺激却使他无法躲避、无法逃离。他发现,在这一文学传统当中,也仍然是鲁迅做得最好: ……在这方面鲁迅先生做得最好,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鲁迅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主将,他对社会的批判、对旧的封建主义的批判、对旧文人的批判不遗余力,像投枪、烈火一样。但鲁迅一回到文学创作上来,他立刻又抛弃了口号式、宣传式、活报剧式的那种浅显,立刻直面人心,直视着人的灵魂。他把历史、革命作为背景来描写,他的着眼点,始终围绕那些处在革命浪潮中的人物,写人在革命中的表现、人在革命中灵魂所发生的变化、人在革命大潮中的命运变迁。(32) 具体到文学作品,莫言认为鲁迅的《阿Q正传》之所以能塑造出那样深刻的灵魂,就在于鲁迅掌握了文学的规律,没有像当时一批普通作家那样,写一种非常肤浅的图解革命的小说。而他2001年出版的长篇《檀香刑》,自己也承认“在构思过程中受到了鲁迅先生的启发”(33)。他在小说中,将《檀香刑》写成了一个巨大的寓言,他觉得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个人都会在不同的时刻,扮演着施刑人、受刑人或者观刑人的角色。在主题意向上,这与鲁迅反复描写的“看客”心理直接相联。莫言认为,读者在对这三种角色不同心境的感悟中,自然会引发出“对历史、对现实、对人性的思考”。(34) 对历史、现实和人性的思考,自然牵扯到作者的劝惩、教训、启蒙和为人生。莫言对鲁迅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吸引,自然也是丰富的,多样的。 2006年,也就是在莫言正式提出“作为老百姓写作”口号的五年之后,他在一次与鲁迅研究者孙郁的对话《说不尽的鲁迅》中,对自己的主张进行了反思与修正。“严格地来讲,‘作为老百姓写作’这个说法也经不起推敲。因为目前,你不管承认还是不承认,肯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老百姓,跟我家乡的父老,还有城市胡同里的老百姓,还是不一样的。我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口号,是基于对我们几十年来对作家地位的过高估计,和某些作家的自我膨胀……”(35)也就是说,他提出这个口号并不是故意要与鲁迅有所区别,故意针锋相对。他仍然觉得无法超越鲁迅,无法摆脱鲁迅的文学传统对他的巨大影响。 不过,他也认为在人生理想与个性、习惯方面,各个作家都会有所不同。他觉得:“有作家是愿意过寂寞生活的,不想参与社会生活,也有的作家非常热心于社会生活,愿意当人民的代言人。我可能介于两者之间。”(36)他认为前者如沈从文,后者如鲁迅,而他则是不前不后。这种折中、调和与公允,也使莫言的文学观念显得更为真切地贴近于文学,贴近于社会。他声称:“我的意思是说,作家还是应该时刻提醒自己,使作品相对地超脱一点。即使要描写政治,最好不要直接去描写政治事件,而应该把事件象征化,应该把人物典型化。只有当作品里面充满了象征,你的人物成为典型的时候,这个作品才是真正的文学作品。否则的话,那些政治内容特别强烈的小说,很快就会时过境迁,价值大打折扣。”(37) 在这段近乎辩证的表述中,我们显然可以发现:其中有着对鲁迅文学传统与经验的借鉴与吸收,同时,也有着他自己个人独特的理解与创新。这应该是莫言与鲁迅文学传统同中有异的方面吧。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 ②《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1页。 ③《呐喊·自序》。 ④⑤(26)(28)(29)(31)(32)(34)(37)《说吧·莫言》(上卷),海天出版社2007年版,第75、74、106、248、95、243、105、99、244页。 ⑥笔者曾有《论鲁迅文学观念的复杂性——兼及鸳鸯蝴蝶派的评价问题》一文,对鲁迅文学观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有系统而详尽的论述,读者可一并参阅。该文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6期。 ⑦(17)《鲁迅全集》第10卷,第161、141页。 ⑧《随想录四十三》,见《鲁迅全集》第一卷,第346页。 ⑨《鲁迅全集》第四卷,第511页。 ⑩《鲁迅全集》第3卷,第423页。 (11)《革命时代的文学》,见《鲁迅全集》第3卷,第418页。 (12)《鲁迅全集》第12卷,第23页。 (13)《鲁迅全集》第13卷,第211页。 (14)《死》,见《鲁迅全集》第6卷,第612页。 (15)(16)(18)(19)(20)《鲁迅全集》第9卷,第70、70、338、335、335页。 (21)(25)(33)(35)(36)《说吧·莫言》(中卷),海天出版社2007年版,第371-372、275、377、384、38页。 (22)(23)(24)(27)(30)《说吧·莫言》(下卷),第248、248-249、338、317-318、244页。标签:鲁迅论文; 鲁迅全集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文学论文; 莫言诺贝尔文学奖作品论文; 莫言作品论文; 红楼梦论文; 读书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狂人日记论文; 孔乙己论文; 文艺论文; 铸剑论文; 阿q正传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