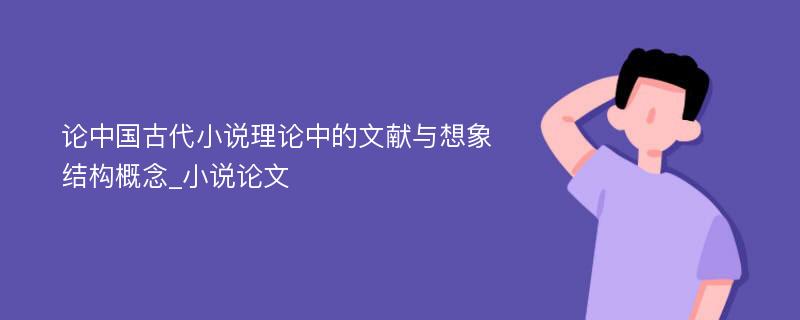
试论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中的纪实与虚构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纪实论文,试论论文,理论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分析和评论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中纪实与虚构这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小说总的发展趋势是由纪实到虚构,因而虚构派的观点是进步的,纪实派的观点是保守的。
关键词 志人志怪小说 唐传奇 虚构派 纪实派
虚构是小说创作一个重要的特点。在小说发展的历史上,小说由纪实到虚构却经历了一段曲折的道路。从纪实和虚构的角度对小说的界定是截然相反的。有人认为:“小说者,纪实也”①。另一派意见与此针锋相对,认为“小说者,虚拟者也。”②这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和研究领域长期争议的一个问题,而以明清时期争论最为激烈。我们回顾一下小说演变发展的历史就会明白其源远流长的状况。
“小说”一词最早出自《庄子·外物》,与后世小说的含义完全不同,是指一些无关大道的辩巧之言。以后班固《汉书·艺文志》也提到小说,并指出“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但从班固小说类别中的十五种书的内容看,有神话传说,有野史杂记,甚至也有讲养生之术的书,与我们现在理解的小说含义也不太一样。总之,汉以前所谓小说被视为雕虫小技,杂拼起来的闲言碎语,从纪实与虚构角度考察没有什么意义。
紧接着是汉魏六朝志人志怪小说。这一时期小说所记故事有真实的人的历史,也有鬼神灵怪,“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③实际上当时的人们把志人志怪小说中的记载看作是真实的事情,实录的性质与历史记载不加区别。比如志怪小说《搜神记》编写者干宝“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缀片言于残阙,访行事于故老”,④记录鬼神异事与人间常事四百六十四个(原书已散佚,此据后人编撰的二十卷本),自以为此记载系真实不诞。如果说志怪小说古人看均系实录而今人看当属虚构的话(即“多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⑤志人小说则可视为标准的实录了(今人古人看均系实录)。刘义庆《世说新语》有许多这方面的例证,如所记裴启《语林》一事即可略见一斑:裴启《语林》记述了汉魏两晋上层人士言谈轶事,读者争相传读影响很大,但后来发现所记谢安的两句话失实,人们便再也不传读《语林》。⑥由此可见志人小说的实录性质。由于汉魏六朝小说在人们心目中是纪实的,所以小说与经史含混不清,小说作者常常从史书中取材如干宝《搜神记》卷六第四十九条有关汉桓帝元嘉中京都梁冀妻子作“愁眉”“啼妆”等装束文字系全抄《后汉书》卷一三《五行志》,而有些史官如房玄龄等修《晋书》时又居然从一些小说如《世说新语》中取材。总之,史书与小说材料互为通用比比皆是,以至二者失去界限。这种情况说明了小说孕育之初与史书密切相联的情况。同时也说明此时小说的不成熟,缺乏与史书明确区分的特点。
汉魏以后的唐传奇在小说史上有着划时代的重要地位。它突破了志怪小说谈神说怪、志人小说“残丛小语”式的记叙人物言行笑貌的范围,摆脱实录传统即真人真事局限。这首先表现在唐传奇揭去了志怪小说“纪实”的面纱而恢复了它虚构的本来面目。其次表现在对真人真事的加工方面。第三表现在它把现实中的真实仅仅作为一种导引,整篇作品由导引而生发开去进行虚构。第四唐传奇的虚构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完全凭空构想,“欲以构想之幻目见”,“时时示人以出于造作,不求见信”。⑦总之,由于唐传奇虚构的特点,和魏晋小说大量引入史书相比,唐传奇小说开始不再垂青于史学家,我以为这恰恰表明了小说的成熟,表明了小说与史书的区别并以其自身特点独立出来。所以鲁迅先生对此高度评价:“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⑧“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⑨胡应麟的“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和鲁迅先生的“始有意为小说”,都指出了唐传奇与六朝志人志怪小说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作者有意识地不受真人真事局限,发挥虚构才能,自觉地进行小说创作。虚构性的引入,使唐传奇成为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小说的这个转折点上,纪实与虚构的问题引起了古人们的争论;也正是从唐传奇开始,中国古代小说出现了纪实与虚构两大派别。对于唐传奇的虚构,人们褒贬不一。有的认为唐传奇“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⑩是第一流的小说;而有的却鄙视唐传奇,斥为“传奇体耳。”(11)这些不同的看法,到明清及近代小说创作的日益发展阶段,争论更加激烈。小说创作到底是纪实还是虚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下我们在纷争中梳理出几个主要派别的观点,并进行适当的分析和评论,同时也表明笔者的观点。
首先是虚构派。认为小说创作,虚构是其特点,不能把小说中描写的情节、人物,和现实生活对号入座,也不能从历史书籍记载的角度去考证小说中描写的内容。这种观点正确地理解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符合文学自身的规律,在小说发展史上它推动了小说这种文学体裁的形成和发展,使小说由雏型很快成熟,由与经史含混不清状态中独立出来成为一种具有鲜明特点的文学体裁。
叶昼,中国古典小说评点家的先驱,在纪实与虚构的问题上,明确提出了他的主张。他说:“《水浒传》事节都是假的,说来却是逼真,所以为妙。”在这里,假和真充满了丰富的艺术辩证法,“事节”即指生活真实,从生活真实的角度去看《水浒传》中描写的内容,“都是假的”,即现实生活中没有这种真人真事。“说来”是指写进作品的内容人们阅读的时候,由现实生活上升到文学作品,人们阅读时却感到“逼真”。这种“逼真”,不是指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之“真”,而是一种规律之真、情理之真、本质之真,按亚里士多德的话说是一种“合情合理的不可能”,(12)这种“合情合理的不可能”正是我们文艺理论中讲到的一种“艺术之真”,一种“事膺而理真”之真。(13)叶昼还说:“天下文章当以趣为第一。既然趣了,何必实有其事,并实有其人?若一一推究如何如何,岂不令人笑杀?”(14)“趣”,是古代小说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有人专门就此作过一些研究。我以为,“趣”是古人对欣赏文艺作品之后的一种审美感受的描述,这种感受含有艺术真实的成份,而艺术真实和美感是有关的,人们欣赏艺术作品如小说以后,引起审美的愉悦,这在叶昼看来就达到了小说创作的目的了,又何必去追究现实生活中是否真的存在小说中描写的人和事呢?列宁说过:“不要求把作品当作现实。”(15)别林斯基也说过:“艺术中的自然完全不是现实中的自然。”(16)叶昼的观点确实对小说的艺术特点已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叶昼还进一步指出了小说中虚构的情节之假必须符合生活之真——即符合“人情物理”,而不是象“说梦说怪”(第九十七回总评)那样,如果生活中根本不可能的人和事也以虚构为幌子写进作品,那就“都假了,费尽苦心亦不好看”(第十回总评),由此他点评六十五回时说:“此回文字极不济,那里张旺便到李巧奴家?就到巧奴家,缘何就杀死他四命?不是,不是。即王定六父子过江,亦不合便撞着张顺,张顺却缘何不渡江南来接王定六父子?都少关目。”叶昼点评以上情节有背生活逻辑,不符情理,所以“不济”。这种观点已接近当今文艺理论中的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虚构——即从生活真实上升到艺术真实的一种艺术手法,虚构的确切含义应是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融合,离开生活真实谈虚构不行,离开艺术真实谈虚构更不行。
叶昼以后是金圣叹。金圣叹的小说理论主要见于他关于《水浒传》的点评,包括楔子和七十回的每回回前总评,双行夹批和眉批,其评点篇幅之长,理论分析之细,在《水浒传》评论历史上前无古人。在纪实与虚构问题上,金圣叹认为小说不同于历史著作。历史著作是“以文运事”,而小说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因文生事却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17)他以这种观点评价《水浒传》,认为“七十回中许多事迹须知都是作书人凭空造谎出来。”(18)“一百八人,七十卷书都无实事”。(19)“凭空造谎”出来的事迹,“都无实事”的七十卷书,却受到了金圣叹的极高评价,对其作者施耐庵金圣叹更是推崇,这本身就体现了金圣叹进步的小说观。金圣叹对《水浒传》的研究和评论,是我国古代小说理论宝库中的一份厚产,在纪实与虚构的观点上,他属于虚构派。
后来的张竹坡也是主张小说可以虚构的。他在《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六十三里说道:“作金瓶梅者,若果必待色色历遍,才有此书,由金瓶梅又必做不成也。何则?即如诸淫妇偷汉,种种不同,若必待身亲历而后知之,将何以经历哉?”这里,表明张竹坡反对把《金瓶梅》描写的世情当作生活中实有其事来看的观点,同时也涉及到小说创作中依据生活情理加以想象、进行艺术虚构,涉及到作者对生活体验的两种方式等等问题。在文学创作中,作品中描写的内容有的是作者亲身经历,有的可以是作者在各种直接和间接生活经验基础上的一种想象即虚构。如果把作品中描写的内容全部看成是作者亲身经历,《金瓶梅》写不出,很多作品也写不出,这实质上仍然是把小说与纪实相联的观点。张竹坡认为:写小说可以“假捏一人,幻造一事,虽有风影之谈,亦必依山点石,借海扬波。”(20)点石必依山,扬波须借海,形象地说明虚构要以生活为基础,说明了虚构的科学性。
《红楼梦》的点评文字有三十五条署名“脂砚斋”,而目前发现的最早抄本“甲戌本”、“已卯本”、“庚辰本”都题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所以学术界一般把早期抄本上的所有评语统称为“脂评”,显然“脂评”由多人评点组成,评语形式有回前回后批、夹批、眉批、侧批等,而“脂评”数量最多的署名是脂砚斋和畸笏叟两个人。“脂评”在小说虚构问题上也持肯定观点。由于内容多,这里不一一列举,其中如:“事之所无,理之必有”,“合情合理”、“近情近理”,“至情至理”,“天下必有之情事”等等,这些和叶昼、金圣叹、张竹坡等人的“虚构观”具有一致性。特别是脂评第十九回(《庚辰本》)中有一段对宝玉的评语是这样的:
按此书中写一宝玉,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又写宝玉之发言,每每令人不解,宝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独于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今古所有之小说传奇中,亦未见出这样的文字。于颦儿处更甚。其囫囵不解之中实可解,可解之中又说不出理路……。
这段评语指出了宝玉这个人物的虚构性。这种虚构以生活真实为基础,即“不解之中实可解”。然而这种虚构又不完全等同于生活真实,即“未目曾亲睹者”“可解之中又说不出理路。”这正如“镜中花、云中豹,林中之鸟,穴中之鼠,无数可考,无人可指,有迹可追,有形可据。”(21)
以上虚构派肯定小说虚构的特点,这派观点顺应了小说由纪实走向虚构这种发展演变的潮流。事物的运动性决定小说作为一种体裁的运动性,“各领风骚数百年”,没有运动就没有发展。另外,虚构派的观点确定了小说的价值。小说描写的内容不能等同于生活,不能纪实于生活,生活虽然丰富多样,小说创作虽然也离不开生活,但如果亦步亦趋地摹仿生活,成为生活的纪实,就会如黑格尔所言,正如一只小虫爬着去追赶一头大象,小说之花会逐渐枯萎、凋谢。文学之所以是文学,小说之所以不同于历史书籍,就在于它是对生活真实的提炼,它是对历史材料的加工,它有作者审美理想的渗入——这即虚构。事实上也是如此,正是虚构性的出现,才使小说真正具有了自身的品格而独立,才使小说具有了如叶昼所说的“趣”的那种独特的审美效果。所以虚构派的观点在小说史上起到了良好的促进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形成的重要作用。我们可以把虚构手法引入小说创作看成中国古典小说的重要转折点。
其次是纪实派。纪实派的观点与虚构派针锋相对,指责小说虚构,指责小说描写内容与史书不合等等。这派的代表人物以毛宗岗和纪昀为代表。毛宗岗晚于叶昼、金圣叹。他虽然就小说叙事方法的理论条理化方面在金圣叹的基础上有所发挥,但在小说的虚构问题上,他的观点是保守的、倒退的。(毛宗岗评《三国演义》迟于金圣叹评《水浒》约三十年),毛宗岗在托名金圣叹的《〈三国演义〉序》中评价《三国演义》的优点是“据实指陈,非属臆造。”据此,他认为《西游记》“捏造妖魔之事,诞而不经,不若《三国》实叙帝王之事,真而可考也。”结论是:“读《三国》胜读《西游记》”。其实《三国》和《西游记》相比,在毛宗岗眼里也许算是纪实的,实际上《三国》仍是小说,并非完全纪实,有人从历史角度对它的情节进行考察,也提出了许多批评。毛宗岗父亲毛纶与儿子的观点一致,他贬低《水浒》(因为《水浒》虚构)而推崇《三国》,毛纶说:“《水浒》题目不及《三国志》。……《水浒》所写萑符啸聚之事,不过因宋史中一语,凭空捏造出来。既是凭空捏造,则其间之曲折变幻都是作者一时之巧思耳。若《三国志》所写帝王将相之事,则皆实实有是事,而其事又无不极其曲折,极其变幻,便使捏造亦捏造不出。”(22)这种主张小说纪实的观点可以看作是一种正统的观点。在毛氏父子的整个评点文字中,这种“小说实录”观比比皆是——如四十八回评,五十三回评,八十五回评,百一十六回评,二十七回评,九十二回评等。
任《四库全书》总编撰者十三年的纪昀,在小说纪实与虚构问题上也是持这种观点。纪昀曾用著书之体例去苛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这说明他站在目录学家的立场,还没有将文学创作同学术著作严格区别。纪公《阅微草堂四种》和蒲松龄的《聊斋》,由于作者对文学与生活关系理解不同而运用了不同的创作方法和体例,这两部书对比阅读,《聊斋》“通人爱之,俗人亦爱之,竟传矣”,而《阅微草堂》“文字力量精神别是一种,其生趣不逮矣。”我以为这种评价是公正的。“生趣”即审美效果或审美感受,对象缺乏“生趣”也就不能算作审美对象了。事实上在纪昀的眼中,他不认为虚构是文学的特点和长处,以虚构为主的唐传奇,被他逐出小说之列。“小说家言,必以纪实研理,足资考核为正宗。(23)所以他常常从历史角度对小说情节加以考证,这也是纪实派的一个共同特点。纪昀曾从对小说情节考证的角度提出小说是叙事体,叙事体的叙述方式取决于叙述者身份,而叙述者身份就决定了小说情节是否真实可信的观点。比如,《飞燕外传》题为伶玄著,而伶玄之妾樊通德是赵飞燕姑妹樊嬺的弟子不周的女儿,通德给伶玄讲飞燕故事,伶玄书写成文,实质上《飞燕外传》是间接的由樊嬺讲的故事,因此小说中对赵氏姊妹与汉成帝床笫生活的细致描写符合樊嬺身为皇帝身边女官(为丞光司帟)了解皇帝后妃私生活的身份,所以是可信的。由此纪昀对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提出了批评,认为《聊斋志异》细致入微描写男女欢情(即“燕昵之词”“媟狎之态”),又不是人物自述,作者又不可能看见,这就很不真实。其实这种指责对于小说创作是非常苛刻的,纪昀根本不了解小说创作可以想象可以虚构。如果真按他的这种观点创作小说,小说题材将受到极大的限制,小说本身也将和历史记载,和一些纪实性的备忘文字没有区别。所以鲁迅先生曾对此分析:“纪晓岚攻击蒲留仙《聊斋志异》……两人密话,决不肯泄,又不为第三人所闻,作者从何知之?所以他的《阅微草堂笔记》竭力只写事状,而避去心思和密语。但有时又落了自设的陷井,……他的支绌的原因,是在要使读者信一切所写为事实,靠事实取得真实性,所以一与事实相左,那真实性也随即灭亡。如果他先意识到这一切是创作,即是他个人的造作,便自然没有一切挂碍了。(24)鲁迅先生点到了问题的实质,小说的真实性不是“靠事实来取得”,小说中描写的内容也并非就是作者亲身经历或者亲眼目睹。《红楼梦》第二十七回写薛宝钗听了红玉和坠儿的悄悄话后一段心事,作者曹雪芹怎么会知道——按纪昀观点?小说创作中作者可以任意选择叙述角度,根据生活逻辑想象虚构,这正是小说创作魅力之所在。纪昀观点实在是小说发展史上的一种倒退,相当陈旧。
事实证明,小说由纪实走向虚构符合文学本身的特点。反对变化,因循守旧,错误地理解文学的本质,正是“纪实派”形而上学思维的表现。
第三,虚实相半派。这是一种折中的看法。认为小说创作真真假假,虚实各半。这种看法对小说虚构的特点有一定的认识,但认识比较模糊,态度不坚决,甚至前后观点矛盾。明人谢肇浙说过这样一段话:“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古今小说家如《西京杂记》、《飞燕外传》、《天宝遗事》诸书,《虬髯》、《红线》、《隐娘》、《白猿》诸传,杂剧家如《琵琶》、《西厢》、《荆钗》、《蒙正》等词,岂必真有是事哉?近来作小说稍涉怪诞,人便笑其不经,而新出杂剧,著《浣纱》、《青衫》、《义乳》、《孤儿》等作,必事事考之正史,年月不合,姓字不同,不敢作也。如此,则看史传足矣,何名为戏?”(25)以上所引,有两个观点:第一,小说创作须虚实相半。第二,小说创作不必受“实”的限制——“岂必真有其事哉!”这两个观点不太一致,有些矛盾。叶朗先生在《中国美学史大纲》里,把谢肇浙归入虚构派(在《中国小说美学》里也是这样)。我以为谢肇浙不能完全归入虚构派,他还没有真正领会虚构的具体含义,虽然他偏于虚构派,但纪实的影子在他上面这段话里也有迹可循。这里可以看出传统文学观的顽固性,可以说谢肇浙与金圣叹只有一步之差,如果他在“事太实则近腐”(26)的基础上再向前走一步,认为小说创作即虚构为其特点的话,那他就会先金圣叹一步进入虚构派的行列,可惜谢肇浙到此止步了。
谢肇浙以后的金丰,这种情形表现更加明显。《说岳全传》题“仁和钱锦文氏编次”,“永福金丰大有氏增订”,金丰作序。这篇作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的序文保存了金丰的小说理论观点。金丰认为:“从来创说者不宜尽出于虚,而亦不必尽出于实。苟事事皆虚,则过于诞妄,而无以服考古之心;事事皆实,则失之平庸,而无以动一时之听。”(27)这段话,虚实相半派的摇摆性十分清楚。小说要“实”,是为了“服考古之心”,这使我们想到毛宗岗认为《三国》“堪与经史相表里”的看法。他们的理解——小说的“实”,就是与历史考古相联,他们对小说创作中虚构与纪实的理解是机械的。他们不明白小说中的虚构可以事事皆虚,然而这事事皆虚在某种意义上看(即艺术真实)又是事事皆实的道理。艺术虚构,虚与实是统一的,虚实相半派的观点虽然偏于小说创作中的虚构,但对虚构中虚与实的统一性注意不够。
第四,虚实分家派。
这种观点偏于保守。主张小说要实就实到底,要虚就虚到底,不要在一篇小说中虚实相半。清代乾隆年间的章学诚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凡演义之书,如《列国志》、《东西汉》、《说唐》及《南北宋》多纪实事,《西游记》、《金瓶梅》之类全凭虚构,皆无伤也。”(28)这种看法承认小说可以虚构,也承认小说可以写实(演义之书即小说中一种),这就把小说(特别是演义小说)和史著又混淆起来,(史著应纪实)。“实则概从其实,虚则明著寓言”,所以章学诚对《三国》七分实事三分虚构的作法进行批评,认为造成了观众惑乱。我们认为,章学诚的看法值得商榷。我们首先要明白“演义之书”如《三国演义》是小说,小说就可以虚构,就不可以从历史的角度去进行考证,章学诚把《三国演义》之类等同于历史著作,忽视小说与历史著作的区别就在于虚构与否,其荒谬性是明显的。虚实分家派观点究其实质是主张小说纪实的。有的人虽然没有明确表示这种观点,但实际做法却证明其也有这种思想,如明代学者胡应麟,他曾给小说分类时首推纪实性的志怪小说,但他又把虚构性的唐传奇放在第二类,而与此同时他又列举了“杂录”、“丛谈”、“辩订”等第三类,胡应麟把以上三类统统算作小说(虚实是完全分开的)。这种分类方法本身也使我们看得出虚实分家派的影子。
追溯远一点,宋代的李昉似乎也有这种情况。他编篡五百卷《太平广记》,把有无故事性(虚构)作区别“小说”的尺度,专收传奇志怪和轶闻琐事作品,可是又把单篇的唐传奇称为“杂传体”放到全书之末,好象又忽视小说虚构而看重纪实的“笔记体”。这种矛盾的现象说明在小说创作由纪实到虚构的演变这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中,人们的认识难免有含混而导致行为的矛盾,把纪实与虚构割裂开来形而上学地理解二者关系正是这种情况的一种反映。
以上,我们就古代小说理论史中纪实与虚构观点进行了考察、分析、评论,并把着重点放在明清小说理论中纪实与虚构观点的四派意见上。这四派意见,又重点分析介绍了虚构和纪实两派。我们认为:虚构派的观点是进步的;纪实派的观点是保守的;而虚实相半派和虚实分家派的观点则动摇于先进与保守之间——相半派偏于虚构,分家派偏于纪实。我们只是大致分出几派意见,这种分法的科学性可以进一步探讨。实际上在每派意见内部情况很复杂,观点也不尽一致,甚至同一个人的观点前后也不一致,仔细鉴别、分析、梳理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中这一问题是一项十分繁杂的工作,笔者浅尝辄止吧。总之,从“纪实”到“虚构”,从主观臆造、搜奇记逸到面向现实精心创作——这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发展总的趋势。
探讨古代小说理论中的这个问题不是毫无意义。我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和新时期文学中的小说创作都曾程度不同地涉及到这个问题。就小说本身的发展看,小说发展到今天——把虚构作为小说创作特征之一在课堂上讲授的今天,在创作界却仍然出现了许多声称纪实性的小说(有的称为“报告小说”),当然我们也同样可以理解成是作家的一种托辞或技巧——和古代作家(如唐传奇作家)遵循的“依托”传统一样,但实事求是地看,这样的理解有时也有悖于现在小说创作界,因为目前的小说创作中确实存在着一种“纪实性”的返祖现象,甚至从体裁演变的角度,报告文学和小说的区别也越来越模糊似也属此问题。这些文学现象本身就说明从小说理论史角度探讨这个问题的必要性。
注释:
① 《新世界小说新报》第二期《论科学之发达可以辟旧小说之荒谬思想》,引自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
② 《小说丛话》定一语,引自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
③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④ 《晋书·干宝传》
⑤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三十六“二酉缀遗”
⑥ 参见刘义庆《世说新语·轻诋篇》
⑦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⑧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⑨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三十六
⑩ 洪迈《容斋随笔》
(11) 参见陈师道《后山诗话》
(12) 亚里士多德《诗学》
(13) 冯梦龙语
(14) 《水浒传》第五十三回回末总评
(15) 参见《十月》文艺丛书,1987年2月号 P197
(16) 《别林斯基全集》第六卷 P527
(17)(19) 《水浒传》第十三回评语
(18) 《读第五才子书法》
(20) 《金瓶梅寓意说》
(21) 脂评《庚辰本》第46回
(22) 《第七才子书总论》
(23) 邱炜萲《客云庐小说话》引自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
(24) 鲁迅《怎么办》
(25)(26) 《五杂俎》卷十五
(27) 钱彩《说岳全传·序》
(28) 《丙辰札记》
标签: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水浒传论文; 金瓶梅论文; 三国论文; 读书论文; 聊斋志异论文; 金圣叹论文; 飞燕外传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