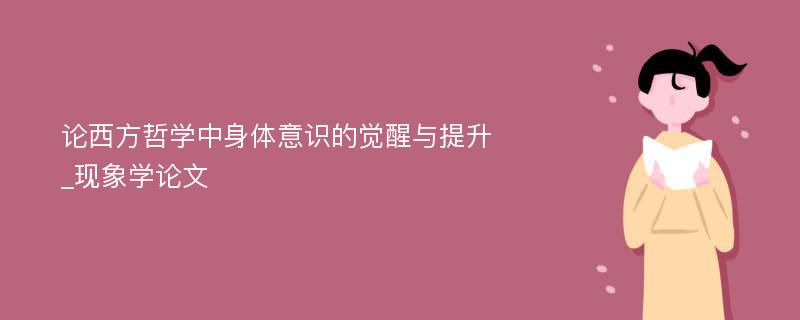
论西方哲学中身体意识的觉醒及其推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论文,身体论文,西方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7)02-0084-008
身体的本源意义及其当下命运不仅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而且在哲学与思想领域也赢得了相当的理论兴趣。这对以后现代观点为标识的理论家与思想家而言,尤其如此。身体问题是那么深刻地牵涉到每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而又是那么深刻地把责任推给个人的主观性,似乎为每一个体所无法回避。不过,后现代思想家们通过对西方哲学史上自柏拉图以来扬心抑身的传统观念的批判与瓦解而展开的对身体问题的关注与推崇,除了尼采的权力意志—身体哲学的影响之外,由胡塞尔所开创的20世纪的现象学传统显然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与思考线索。
身体(肉体、欲望、冲动等)问题的言说注定要与灵魂(心灵、理智、意识、理性等)问题的探讨相对应而得以展开。不过,在柏拉图以来直至20世纪之前的西方观念史上,身体向来处于或者被压制或者被遗忘的阴影之中。准确而言,也就是处于灵魂、理智、精神、意识、理性诸概念的阴影之中。而柏拉图无疑就是此一身心格局的始作俑者。作为第一个比较清晰而明确地建立起灵魂理论的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根据(理智)可知世界与(感觉)可见世界的区分,对灵魂与身体及其关系问题进行了类似的处理。他认为,灵魂是不可见、非形体的独立的实体自身,灵魂与肉体的结合是理念扭曲与堕落的结果,而不是灵魂的本原状态。任何依赖身体的思考,都不是接近真理与知识展现方式的有效通道。相反,只有当灵魂通过不断的返观自照之持续努力摆脱了身体的污染与干扰,灵魂才能自得其所。换句话说,灵魂本质上是理性的、思维的元素,而身体则是其通向真理、知识与智慧之途的障碍与桎梏。因此,“如果我们要想获得关于某事物的纯粹的知识,我们就必须摆脱肉体,由灵魂本身来对事物本身进行沉思”[1—p64]。而要真正断绝灵魂与肉体之间的交往,即实现二者之间的最终分离,死亡——当然是肉体的死亡——无疑是唯一的也是最佳的选择。只有当死亡降临之时,才能彻底消除身体及其冲动、欲望所造成的混乱与不堪,从而使灵魂如释重负并全神贯注地接受一切纯粹的真理与知识在我们面前的“昭然若揭”。这也就是灵魂在柏拉图式的宇宙中的终极命运。
至于身体,不仅在知识领域是障碍,而且在伦理领域是罪恶,是不受欢迎的欲望之肉与苦难之源。在柏拉图看来,人是理性的存在者,人的至善是灵魂的和谐状态,是理智的满足,是心灵的幸福。而单纯的身体快乐不是人真正的生活,而是仅有肉体感受性的牡蛎般的生活,甚至它的欲望及其满足正是尘世间大多数战争、仇恨、苦难、邪恶等的罪魁祸首。所以,身体及其大多数活动乃是我们需要加以防范和抑制的对象——无论是就获得真理来说,还是对于通达至善而言,俱是如此。可见,身体与灵魂问题,在柏拉图那里即使没有完全处于坚决对立的关系之中,扬心抑身的大致格局也是清晰可见。
此一身心格局中的柏拉图主义在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而奥古斯丁无疑在其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首先要注意的是,奥古斯丁在身心关系问题的态度上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在形而上学和自然观领域中,他出于维护“肉身复活”、“道成肉身”等基督教教义的谨慎考虑,主张参照肉体的实体性来解释灵魂,兼顾人的内、外两种向度。另一方面,在伦理学领域,当他在人与上帝之间的互动关系中来思考问题的时候,推崇灵魂、贬低肉体的柏拉图主义就表现得淋漓尽致[2—p164]。关于后者,奥古斯丁虽然不像柏拉图那样有意无意地否认肉体的实体性地位,但是仍然明确指出,就人作为被上帝按照自身而创造出来并注定得到拯救的万物之灵而言,灵魂体现的乃是凡人之中的神性,而肉体则是原罪的容器,邪恶的根源。因此之故,我们要想真正成为上帝之光的受体与道德实践的主体,充分接近宇宙万物的精神之源,完全获得至高上帝的眷顾与赐福,显然首先就必须尽可能地把自己从肉体及其欲望中解脱出来,专注于灵魂自身及其内在生活。换句话说,上帝与魔鬼、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之间的斗争在人这里就体现为灵魂与肉体的对决。人既是各种争斗持续上演的现实场所,也是激烈争夺的主要对象。由此,在奥古斯丁神学哲学的教谕中,关于灵魂与身体的关系中孰是孰非、孰轻孰重的问题也就一目了然。
柏拉图-奥古斯丁主义的扬心抑身论传统到了笛卡尔所开辟的近代意识哲学尤其是在其认识论范畴中几乎被发挥到一种登峰造极的地步。首先,就笛卡尔那个为近代哲学奠定基调的、作为“令人无法拒绝的反思的洞见”而提出的直观命题“我思故我在”而言,这个“我思”之我,“我的灵魂,也就是说我之所以成为我的那个东西,是完全、真正跟我的肉体有分别的,灵魂可以没有肉体而存在”[3—p82];而“我在”之我,也绝非肉体之我,而是“我感觉”、“我意欲”、“我想象”中的抽掉一切外部经验内容的、纯粹的“我”。简言之,“我”就是“我思”。这里,明显主张一种“无身的思维”。即“尽管整个精神似乎和整个肉体结合在一起,可是当一只脚或者一只胳膊或别的什么部分从我的肉体截去的时候,肯定从我的精神上并没有截去什么东西”[3—p90]。当然,作为一种典型的身心二元论,笛卡尔哲学对于身体的实体性地位是进行了充分肯定的。但是,无论如何,身体的有效地位与作用也就是仅仅局限于一架依照自然本性进行运转的机器而己。它与思维的确定性、知识的可靠性——这是近代哲学主要努力的根本方向——是始终无缘的,也注定无所作为。
笛卡尔之后的近代西方哲学似乎都没有走出这种扬心抑身的坚硬格局。哲学家们最杰出的智识活动大多集中在“知性改进论”、“人类理智论”、“人类理智新论”、“纯粹理性批判”、“精神现象学”诸多课题上。至于身体、肉身、欲望、冲动之类的问题似乎很少有资格或机会进入哲学家的视野。譬如,身体在康德哲学中基本上就难觅踪影,在黑格尔哲学中也仅仅是作为灵魂的外在化、个体化而略有提及。对于他们来说,最需要关注的是灵魂的原理和活动,是知性的力量和工作,恰恰是这些对象才是“一切势力中最惊人的和最伟大的,或者甚至可以说是绝对的势力”[4—p21]。
由上观之,不难看出,身体在柏拉图所开启的灵魂之伟大旅程中,基本上一直处于郁郁寡欢、默默无闻的失落之境,处于哲学家对宁静性、纯洁性、确定性等的偏爱与追寻的巨大漩涡之中,从而无法获得自身的体面、尊严与地位。这的确是一件不幸的事实、一种艰难的遭遇。而此一问题的根源也似乎主要缘于身体自身:在古希腊,变化的身体无法领会超绝的理念;在中世纪,欲望的身体无权接近荣耀的上帝;在近代,盲目的身体无力发现可靠的知识。因此,身体的被压制、被抛弃、被遗忘、被放逐的当然命运也就注定不可避免。而这一命运的转机,即使不能说是首先,那么也是不容忽视地悄然发生于20世纪由胡塞尔所开辟的现象学传统之中。
而在追析胡塞尔所开辟的现象学传统对于身体问题的处理方式及其变化之前,我们还需简要地考察一下尼采在这方面的贡献与作用。
尼采及其哲学都堪称西方哲学史上一个标准的另类。他在“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中所进行的针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全面挑战,当然也就包括对扬心抑身的传统格局的强力颠覆。在尼采看来,向来为传统形而上学和基督教权威所推崇的灵魂、精神、意识等既不是永恒不变、完整统一的,也不是独立自在、纯洁向善的。“意识是人类与生俱有的秉赋中最晚也是最近发展的,因此也是最为粗略与这些发展中最没有力的一环。无数的错误皆源于意识……简单地说,只用意识,人类必定会走向崩溃和毁灭”[5—p71]。“我憎恨狭窄的灵魂有如魔鬼,那些灵魂既不生善,亦不生恶”[5—p39]。恰恰相反,唯有总是被不恰当地忽略与诅咒的、与动物共同分享的生物性身体才是人类最重要、最真实的本己力量。“我完完全全是身体,此外无有,灵魂不过是身体上的某物的称呼。身体是一大理智,是一多者,而只有一义。是一战斗与一和平,是一牧群与一牧者。兄弟啊,你的一点小理智,所谓‘心灵’者,也是你身体的一种工具,你的大理智中一个工具,玩具。”“兄弟啊,在你的思想与感情后面,有个强力的主人,一个不认识的智者——这名叫自我。他寄寓在你的身体中,他便是你的身体。”[6—p27~28] 由此,理智、灵魂、意识等只不过是偶然性的、工具性的,而身体才是中心性的、支配性的。这种中心性、支配性不仅在于我们通过身体而存在,而且决定我们通过身体而透视整个世界。这也就意味着,那些与身体感知、身体经验密切相关的原初性生活体验、创造性想象形式、实行性生命内容等才是应该着重关注与追求的对象。
但是,当尼采进一步提出“超人”、“强力意志”等概念,并且把动物性的、充溢着压倒性冲动与激情的身体直接等同于强力意志,宣扬一种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即一种自我反复的冒险游戏,这就不可避免地将他特别倚重的当下之身体经验与身体视角最终拖入否定性的虚无深渊,并且造就一种新的末世论形而上学——根据海德格尔的解读,即强力意志本体论的形而上学。不过,无可否认的是,尼采的身体观显然也对包括福科、德勒兹、德里达等在内的后现代理论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在考察身体意识的觉醒及其推进这一重要课题上,虽然我们无意于也不可能将尼采的身体观处理为一个西方哲学史上的偶然事件,但是本文的着力点仍然将主要限制在从传统哲学或者甚至说传统形而上学内部的发展线索来考察这一问题的缘起、衍进与变化。亦即着力于从胡塞尔所开创的现象学传统来切入问题。
在现象学传统中,身体与躯体的概念是存在着比较严格的区分的。就胡塞尔而言,一方面身体是与躯体相对应的概念,一方面又是与心灵相对应的概念,它构成“躯体”与“心灵”的结合点。所谓躯体,一般首先用来标识空间物理事物,广延性是其核心;而在较为狭窄的意义上,尤其是在胡塞尔的陌生感知即对他人的感知的分析中,又常被用来专门指称人的身躯,即其物理组成部分。譬如,在对他人的感知中,当一陌生躯体与一陌生意识联结在一起,从而构成一个陌生主体的心灵与肉体的统一时,他人的身体便得以被立义亦即被构造出来。身体的构造同时也就意味着他人或他我的构造[7—p277]。胡塞尔的理由或者说思路是这样的:世界不仅缘于自我的纯粹意识之构造,而且涵纳别的纯粹意识之成就。亦即他人也是世界的有效存在、世界经验地向自我意识显现的客观性保证与必要性条件。而他人的成立在于,“每一个自我都有一个身体”,“当我的躯体的身体往回关涉到它自己时,它就具有了他自己的那个处于中心的‘在这里’的被给予性方式;每一个另外的躯体,即‘他人’的躯体,则都具有在那里的样式。这个‘在那里’的方位可以通过我的动觉而得到自由地改变。因此,在我的原真领域内,一个空间的自然就是在这种方位的变化中构造出来的,而且是在与我的作为感知地发生着作用的身体状态的意向相关性中构造出来的”[8—p159]。要言之,我有一身体,并且此一身体与自我意识“结对”而生;我又意识到别的身体,通过别的身体向本己之身体的呈现而以共现的方式可以把握到相应的他人意识。于是,一个完整的“他人”在这种类比统觉中就得以被构造出来。
在此,身体感知与身体经验显然成为纯粹意识通达“他人之心”、确立“主体际性”并完构“世界视域”的重要基础与机缘。身体议题由此也当然成为一切严肃的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无论是思考语言、知识问题,还是讨论生产、交往问题——无法回避之重要课题。至于一些学者所着力批评的方面,譬如论证方式的可疑性、异质性的身体与意识之间类比通道的不可能性,以及理论后果的有限性、被压缩在纯粹主体际意向的本质描述中的身体之无历史性和乏文化性等问题,更为重要而合理的评价在于,只要我们考虑到这是在具有强大传统和深远背景的意识哲学内部而自觉地给出的一种身体视野与身体态度,我们就无论如何也不能低估甚至漠视这一视野与态度对经典的身心格局的冲击力量及其对现代哲学乃至后现代哲学的启示意义。
胡塞尔之后海德格尔的此在现象学为了进一步走出“自我封闭的心智”的阴影而将现象学的工作领域从意识立场扭向了存在立场。在其早期著作《存在与时间》关于此在的基础存在论的分析中,“此在”虽然不直接就是人,但也绝非人之外的什么东西;而对世间的其他存在者样态“现成在手”、“使用上手”的描述,对此在的基本存在方式“现身”、“领会”以及此在之整体存在结构“向死而在”等的分析,似乎也都或多或少地透露出某种身体的气息,尤其是当我们注意到这一切都是在海德格尔一再强调的非隐喻的情形下给出的理论表述。当然,此一时期,作为肉身存在的身体之正面的存在论地位还远远没有得到肯定性的论述。因为,海德格尔明确指出,作为一空间性物体的肉身存在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生命“既不是某种纯粹的现成存在,但也不是此在”,“把此在看作为(在存在论上未经规定的)生命和任何别的什么东西,决不能使此在在存在论上得到规定”[9—p58~59]。所以,在此在的存在论结构的建构过程中,关于“烦”、“畏”之类基本情绪的阐述相对于事实性层面的此在之存在样态的肉身生命而言就占据着明显的优先地位。但是,这样一来,《存在与时间》所赋予此在的基本存在方式即“现身”或“设身处地样态”如何能够得到有效地说明与理解?所以,作为肉身存在的身体之本己的存在论地位的给出及其论证就势不可免。而无论是出于主动还是基于某种影响,我们都很容易在海氏的巨著《尼采》中获得此一分析的明确印证:“作为自我感受(Sichfühlen)的感情恰恰就是我们身体性存在的方式。身体性存在(leiblich sein)并不意味着:在心灵上还有一种负担,即所谓身体;而不如说,在自我感受中,身体自始就已经被扣留在我们自身之中了,而且,身体在其身体状态中充溢着我们自身。我们并不像我们在口袋里带着一把小刀那样‘拥有’一个身体。身体也不是一个物体,一个仅仅伴随着我们的物体,我们马上可以——明确地或不明确地——把它确定为同样现成的东西。我们并非‘拥有’(haben)一个身体,而毋宁说,我们身体性地‘存在’(sind)。”[10—p108]“我们并非首先是‘生活’着,而后还有一个装备,即所谓的身体;而毋宁说,我们通过我们的肉身存在而生活着。”[10—p109]
而萨特哲学同样基于现象学的研究路数,在自在与自为、为我与为他的框架内提出了身体问题。一方面,他更为彻底地清除了胡塞尔先验现象学中作为意识活动中心的“自我”概念,将纯粹意识理解为“虚无”;另一方面,在牵扯到人的实在问题的时候,他又将身体作为综合自在与自为、为我与为他的重要环节推上了前台。“他人为我所是的对象和我为他所是的对象都表现为身体。”[11—p396]“作为自为的存在和作为为他的存在的身体……身体的这两个处在有区别并且不相干的两个存在层次上的形态,是不可互相还原的。自为的存在完全应该是身体,并且完全应该是意识:它不可能与身体统一。同样,为他的存在完全是身体;那里没有统一于身体的‘心理现象’;身体后面什么也没有。”[11—p400] 在这里,身体虽然似乎仍然处于某种功能性的位置,但无论是就认识论的立场而言,还是从存在论的意义角度来看,身体毕竟不再是某种完全的障碍与灾难——尽管萨特最终得出的“他人就是地狱”的结论有些特别。
同为法国人的梅洛-庞蒂接受其同胞兼同行萨特“自我不是意识的中心和意义的来源而是一种成就”的观点,然而将其理解为一种身体的成就。因为“我的身体才是有意义的核心”,是把秩序与意义赋予我在其中运动的世界的“不可或缺的器具”。他也极为推崇胡塞尔的意向性观点,但主要给出的是一种身体意向性。在他看来,“现象学最重要的成就也许是在其世界概念或合理性概念中把极端的主观主义和极端的客观主义结合在一起……现象学的世界不应该被单独放在一边,不应该变成绝对精神或实在论意义上的世界”[12—p16~17]。基于对现象学此种理解,梅洛-庞蒂以身体概念——前期是“身体图式”、后期为“肉体”,但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内在一贯性与相通性——为核心建构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身体现象学。
在梅洛-庞蒂看来,身体本身就是一个与世界和他人处于不断互动和对话中的主体,在身体知觉的深处存在着为任何理智的反思所无法达到的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以及自在与自为的统一性。“我的身体作为一个自然主体、作为我的整个存在的一个暂时形态的情况下,我是我的身体。因此,身体本身的体验和反省运动完全相反,反省运动从主体中得出客体,从客体中得出主体,仅给予我们身体的观念和观念的身体,而不是身体的体验或实在的身体。”[12—p257] 而一切以主观自我或纯粹意识为指向的传统思维的问题根源就在于无法理解或根本没有注意到身体本身的交错性与暧昧性。一方面,身体在知觉场域以自己的方式原发地激起被知觉者的景象,知觉也从所给予者那里获得已潜藏着的感受。身体与事物始终处于一种原本的接触之中,是所有对象的交织之处。另一方面,伴随着一切东西都体现于身体并且与身体一道生活,对于纯粹意识而言,“在身体离开客观世界和在纯粹的主体和客体之间形成第三种存在的同时,主体也丧失了它的纯粹性和它的透明性”[12—p441];对于身体知觉而言,“身体内容是某种含糊的、偶然的和不可理解的东西”[12—p139]。一句话,作为“存在的元素”,作为前概念、前逻辑、前度量的东西,它是“理智意识的盲点”。而正因如此,身体才能够作为一种基源性和创造性的力量而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显然,这里的身体已不能仅仅视为经验意义上的存在,因为梅洛-庞蒂甚至还在晚期未完成的《可见与不可见》中提出了一种“世界之肉”的观点。
综上所述,从胡塞尔、萨特的功能性身体到海德格尔的形式化此在再到梅洛-庞蒂的基源性肉体,身体问题在现象学传统中的位置越来越清晰可见。进一步也可以说,尽管身体问题在现象学传统中或多或少还有一些意识思维、本体论立场甚至知识论图谋的痕迹在内,但是这一线索暗中对于身体问题在后现代哲学中全面登场与大力推进仍然将贡献出无可否认的催化力量与启示意义。
后现代的论题非常广泛而分散,但是对于无论是以后结构主义的化身还是后现代理论的先锋来指称的欧陆哲学家福柯、德勒兹、德里达等人而言,身体问题不折不扣地成为格外醒目的聚焦点之一。即力图通过对传统的身心二元、心尊身卑、扬心抑身的坚硬格局之更为激烈的解构和超越,进一步强化现象学传统对身体问题的持续关注。而这一决定的最终出现,不仅是因为现象学本身意味着“丰富的可能性”,而且在于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以及梅洛-庞蒂等现象学家已经在身体问题方面所进行的卓越而不懈的努力。
首先,就福柯而言,他早年曾经接受过海德格尔的著作与梅洛-庞蒂的课堂启蒙与影响,后来也几乎把自己全部著作的定位都导向于对笛卡尔哲学传统的“我思”、“理性”与“意识主体”等概念的激进瓦解与批判,并且在身体—历史、身体—权力的谱系学框架中把身体问题隆重地推向了理论的前台与思考的中心。在福柯看来,理性、灵魂、先验意识等观念纯粹是某种知识与话语类型的产物,乃至是一种虚构。它们既不构成意义的真正来源,也不决定历史的运行机制。相反,只有活生生的、向来都不得不屈居于灵魂阴影中的身体才是历史的中枢与见证:历史既没有内在目的,也没有特定轨迹,而只有事件的弥散与闪现;这些历史事件无一例外地通过身体而被铭写与展示,而且这一身体可以被一再地、反复地铭写与展示。当然,这不仅是由于历史事件是复杂的、繁多的,而且在于身体本身是可变的、流动的。身体的可变性、流动性的基础与机制,一方面在于它的生物性,一方面更主要地在于这种身体或肉体“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这种对肉体的政治干预,按照一种复杂的交互关系,与对肉体的经济使用紧密相联;肉体基本上是作为一种生产力而受到权力和支配关系的干预;但是,另一方面,只有在它被某种征服体制所控制时,它才可能形成为一种劳动力(在这种体制中,需求也是一种被精心培养、计算和使用的政治工具);只有在肉体既具有生产能力又被驯服时,它才能变成一种有用的力量”[13—p27~28]。
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历史是身体的历史,而身体则是权力的身体。当灵魂、意识这些曾经光芒万丈的赫赫实体在福柯一系列的考古学、谱系学的研究中隐匿而去,隆重登场的身体或者说肉体也并非风光无限,领尽风骚,尽管它终究走出了角落与阴影,来到了近位与前台,但是却示人以无比屈从与臣服的面目与形象。“这是一种操练的肉体,而不是理论物理学的肉体,是一种被权威操纵的肉体,而不是洋溢着动物精神的肉体,是一种受到有益训练的肉体,而不是理性机器的肉体。”[13—p175] 这种崭新的身心格局听起来似乎不无讽刺意味,但在福柯看来,这恰恰正是身体的真实与真实的身体。
无独有偶,福柯权力谱系学的身体观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构成了德勒兹欲望—机器身体观的隐秘前提。同福柯一样,德勒兹也认为身体的存在才是根本性的,同时身体又是可变的、生成的,不稳定、无规则的,是“无政府主义的身体”或“无器官的身体”。但是,问题在于,这种景观中的身体之流动性与变化性并不是无所不在、到处弥散的外在权力作用的结果,而是身体本身就是一种永不停息的欲望之流,是四处冲撞与奔突的力本身,是一种块茎式的处于不断延伸、分解和重组状态中的身体过程。简单地说,身体就是一架欲望机器。这架欲望机器依其本性直接投入社会,并且生产出了一切现实。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欲望受到了与其紧密相关的另一架机器即资本主义的再编码。作为一种对欲望进行压制的外在力量,“资本主义通过其生产过程,制造了一种令人生畏的精神分裂的能量或负荷的聚积,为了反对这种聚积,它动用了巨大的压制性权力。尽管如此,这仍然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局限……它不断地试图避免滑向它的局限性,而同时又不可避免地趋向它的局限”[14—p177]。换句话说,身体在生产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资本主义的各种力量与制度的规训与控制,但是由于身体本身的激荡能量与冲撞欲望,它决不会沉默或姑息于对它的任何形式的摆布之链与压迫之网。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而言,精神分裂症就是资本主义的局限表征,而精神分裂者就是欲望身体的革命代理人。
德里达向来被认为是后现代理论在哲学领域最有建树甚至是唯一的代表,不过他也可以说是最具现象学背景的后现代哲学家。因为,无论对现象学究竟持何种态度,他的《〈几何学的起源〉导言》、《书写与差异》以及《声音与现象》等作品都表明,现象学的问题一直都没有脱离他的视野。当然,对于本文的直接主题即身体观问题,德里达似乎并没有给出明确而集中的论述。但是,从他对书写及差异等问题的特别关注与独到分析,或多或少也可隐约发现他在身体观方面的大致态度。
德里达通过对胡塞尔现象学的大量研究,认为胡塞尔已经揭示出了不在场、差异等问题的重要性,但是失之于仍然固执地要为世界奠定确实的基础,并且把个体自我的纯粹意向理解为思维的同一性和知识的真实性之来源。而事实上,“一种纯粹的差异要分裂自我在场。人们认为可以从自我影响中驱逐出去的一切可能性正是扎根于这种纯粹的差异之中:空间、外在、世界、形体等等”[15—p105]。自我在场的分裂与纯粹差异的凸现在书写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主体的整体不在场和一个被表述的对象——作家的死亡或(和)他能够描述的对象的消失——并不阻碍‘意谓’的行文。相反,这种可能性使得‘意谓’本身诞生”[15—p118]。这与德里达对书写的格外强调与独特理解十分有关。书写作为一种既保存又抹去符号的过程,总是在涂抹原初词语的基础上进行新的记录,但是原初词语的痕迹仍然保存在其中。这些原有符号的痕迹作为“在场的缺席”,必然会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作为“延异的运动”的书写。换句话说,书写总是要反映其他符号的痕迹,甚至本身就是由这种多重而持续的差异构成的。这样一来,书写或文字并不就是言语与思想的完整再现,阅读或理解也并不就是追寻作者与作品的原初意义。进而,我们也就可以判断,书写根本不是为了心灵或通过心灵而书写,而主要是为了一种痕迹、印迹而进行的符号活动,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一种身体书写。这种身体式的书写或写作注定是“危险的,是令人痛苦的”,“是作为衰退的深度时刻。是铭写(引力)的场域与强烈要求”[16—p50]。欲望的身体以一种迂回曲折的方式再次获得了张显。
综上所述,从柏拉图—奥古斯丁—笛卡尔路线的虚假的、邪恶的、无知的身体到现象学传统的功能性、形式化、基源性身体,再到后现代理论的物质性、生产性和欲望化的身体观念,身体问题的崛起与凸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从现象学传统的身体观到后现代视野下身体观的转变与过渡尤其值得关注。这不仅是因为它属于似乎与我们的关系更为密切的20世纪西方哲学进程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在于身体问题在这种具有某种根本性或标志性意义的转变与过渡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由隐而显、由虚而实,从形式到内容、从边缘到中心的推进过程。这一方面体现了哲学问题的连续性与理论思考的相关性,一方面也产生了大量的现实效应和社会后果。
第一,身体问题在当代尤其是在后现代理论视野中的崛起既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完全孤立的。从根本上讲,它从属于或隶属于20世纪西方哲学对于柏拉图以来尤其是笛卡尔式的主体形而上学或意识哲学的大力批判与结构的整体性努力之中。而身体问题既是这种整体性努力的一个角度,一种方式,一个侧面,又可以说是这种整体性努力的一个结果,一种产物,一项成就。与此同时,伴随着身体问题出现的还有他人问题、语言问题、交往问题等等。虽然在本文中鉴于篇幅及主题等方面的限制,并没有对于所有这些问题及其相关性进行专门论述,但是仍然可以隐约感受到它们之间的牵引与互动。譬如,身体问题最初就是胡塞尔、萨特在解决他人问题的过程中而特别提出来的;而语言无论是在福柯那里,还是就梅洛-庞蒂来说,身体与语言一定是密不可分的。“是身体在表现,是身体在说话”[12—p256],不存在无言语的哑巴身体。
第二,身体问题的推进与崛起并非是与传统哲学的身心观念完全断裂的。任何“崭新”的哲学问题都已经内在于它的传统之中。身体问题亦不例外。20世纪身体哲学的一个最大图谋就是克服传统的身心二元论,所以如果仅仅是简单地把二者的各自位置做一个颠倒或翻转就可万事大吉,这绝对是大错特错。事实上,从梅洛-庞蒂异常“含混”的“肉体”、福柯的作为社会意义表征的身体诸概念中,不难看出,20世纪的身体哲学家也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在诸多形形色色的身体概念中,也已经或多或少内在地包含着本属于灵魂、心灵、精神的一些特定因素,譬如激情、意愿、意志、经验等等。而这些问题在扬心抑身的传统身心格局中都曾以相反的形式获得过类似的处理。譬如,在柏拉图那里,身体与灵魂之间并非是完全隔膜而断裂的。一方面,身体的锻炼及其健康有助于精神的训练与调节,另一方面,由于灵魂不可避免地包含着理性、激情、欲望三个部分或者三个原则,而当灵魂中的欲望部分或原则发挥着主导作用,不良的身体习惯或身体行为便得以出现,从而最终影响灵魂向理念、真理的靠近或到达。在笛卡尔那里,我们也可以读到,身体的许多感觉“不过是思维的某些模糊方式,它们是来自并且取决于精神和肉体的联合,就像混合起来一样”[3—p85]。传统哲学家的这种处理方式不仅显示了彻底合理地解决身心问题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为后来者的思考提供了契机或者空隙。
第三,身体问题以及与其相伴随的语言问题、交往问题、他人问题逐渐进入哲学思考的中心,不仅使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意识哲学或主体形而上学的局限性与困难,而且也促使我们越来越自觉而清醒地把哲学的目光从专注于个体的心理、意识和精神的时代推向地把话语集中于差异主体的语言、行为、身体的另一个时代。在这一时代中,通过对身体及其行为等问题的更多研究,将促使我们不仅能够更为深刻、全面地了解权力体制、法律系统、生产体系、文化政治等实践方向与社会层面的诸多秘密及其问题,而且可以更加细致入微地准确把握那些诸如流浪乞丐、失业工人、监狱惯犯、孤寡老人等经常在同一的平面下被压制为“幽灵”或“沦为绝对的无”等的身体性权利及其要求。换句话说,身体问题的深入研究有利于我们对人自身的深入理解、对生活世界的全面把握以及对社会问题的细微洞察。但是,身体问题所显示或牵引出来的这种巨大而迷人的可能性意义空间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要把一切社会关系、一切理论问题都进行理所当然的身体化。若果然如此,不仅势必带来一种新的形而上学——身体形而上学——的局限性与困难,而且在一种自然与社会的“习惯性边界”被不断地侵蚀和分化、身体及其行为的面目也被不断地涂抹与改写的情形下,这种取向既不可能成功,也无绝对必要。至少目前仍然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