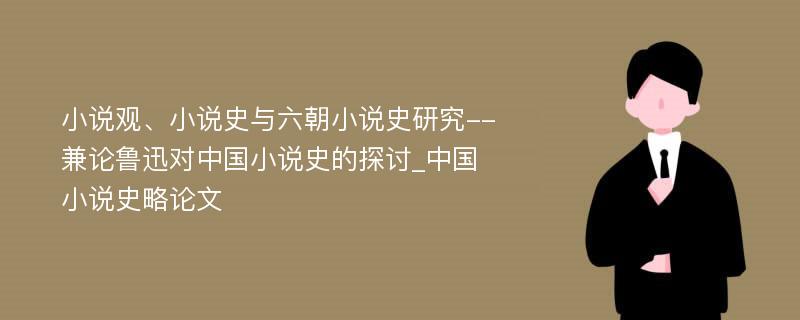
小说观、小说史观与六朝小说史研究——兼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有关论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说论文,鲁迅论文,史略论文,论述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4799(2008)06-0062-07
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建立,如从林传甲、黄人的《中国文学史》算起,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而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小说史的建立,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算起,至今也有八十多年历史。文学史的建立,离不开文学观和文学史观的指导,否则不仅不会清理出文学发展的历史线索,而且连观察和研究的对象也会模糊不清。同样的道理,小说史的建立,也离不开小说观和小说史观的指导,如果没有明确而清晰的小说观和小说史观,我们实在不知道哪些作品是小说,它们是如何发展壮大的,各个时期的小说之间有哪些历史的联系。以六朝小说为例,八十多年来,我们基本上是按照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确立的小说观和小说史观为指导,来确定其研究对象、范围和进行学术研究的,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有目共睹。以此作为个案加以探讨,或许能够对当下的中国小说史研究甚至整个中国文学史研究提供经验并促进人们的深入思考。
鲁迅在1923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的《序言》中说:“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作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1]这一说法是符合事实的。中国古代小说大体说来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被正统史家所承认的子部小说,它们虽然被正史《艺文志》或《经籍志》子部小说家类所收录,却始终被视为“君子弗为”的“小道”,自然不会有人清理它的历史线索,为其建立专门的历史。一类是正统史家所不屑一顾的通俗小说,它们连进入正史堂奥一个旮旯的机会也没有,遑论有人为其建史。所以“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近代以来,有识之士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以为小说可以改造社会与民生,可以“新民”,小说地位才逐步提高。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使人们对小说的认识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1920年,鲁迅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中国古代小说第一次走进大学讲堂,而他印发的讲义《中国小说史大略》也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在此基础上修订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便成为中国的第一部小说专史。
既然“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那么鲁迅是靠什么来构建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呢?这里牵涉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一是他把哪些作品当作小说,二是他是如何理解这些小说的历史联系的。前者是关于小说的观念即小说观,后者是关于小说的历史的观念即小说史观,二者是建构小说史的核心和灵魂。
先说小说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的第一篇《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中回顾了中国古代的小说观念的发生和演变,如《庄子》的小说观、桓谭的小说观、《汉志》的小说观、《隋志》的小说观、胡应麟的小说观、《四库》馆臣的小说观,等等,他虽然没有正面归纳自己的小说观,但从其所述“桓谭言‘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始若与后之小说近似”,以及《汉志》小说“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者也”等语来看,他是有自己的小说观念的。在1924年7月的西安暑期讲学中,他对自己的小说观作了明确阐释,他说:“《汉书·艺文志》上说:‘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这才近似现在的所谓小说了,但也不过古时稗官采集一般小民所谈的小话,借以考察国之民情、风俗而已,并无现在所谓小说之价值。”[1]269他进一步指出:“在文艺作品的发生的次序中,恐怕是诗歌在先,小说在后的。诗歌起源于劳动和宗教。其一,因劳动时,一面工作,一面唱歌,可以忘却劳苦,所以从单纯的呼叫发展开去,直到发挥自己的心意和感情,并偕有自然的韵调;其二,是因为原始民族对于神明,渐因畏惧而生敬仰,于是歌颂其威灵,赞叹其功烈,也就成了诗歌的起源。至于小说,我以为倒是起源于休息的。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咏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所以诗歌是韵文,从劳动时发生的;小说是散文,从休息时发生的。”[1]270鲁迅受西方文艺思想的影响,以为诗歌起源于劳动、小说起源于休息,这一结论是否符合中国实际我们暂且不去讨论,但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小说观念却是需要注意的。在鲁迅的心目中,小说就是讲故事,而且是虚构的故事,这与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叙述中国小说的历史从“神话与传说”开始是完全一致的。这种小说观念成为了鲁迅确定小说史叙述对象、评价古代小说作品的历史价值的核心思想和重要理论基石。
再说小说史观。确立了小说是虚构的故事这一小说观,各个时代小说之间的历史联系似乎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因为当时正盛行着历史进化论,大家认为文学也不例外,其历史也是进化的。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的序言中表达了自己对于小说历史的认识,他说:“我讲的是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许多历史学家说,人类的历史是进化的,那么,中国当然不会在例外。……文艺,文艺之一的小说,自然也如此。”[1]268毫无疑问,鲁迅的小说史观的核心是进化论思想,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正是按照进化论的理论建构的。鲁迅的小说史观来源于当时的社会思潮。19世纪末,赫胥黎的《天演论》经严复翻译介绍到中国,进化论迅速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主流社会思想,并影响着人们对文学的认识。1901年蔡元培在《文变序》中说:“先儒有言,‘文以载道’,道不变也;而见道之识,随世界之进化而屡变;则载道之言,与夫载道之言之法,皆不得不随之而变。”[2]1171904年东吴大学使用的黄人编撰的《中国文学史》这样写道:“盖百年来,劫持于一王之制,一师之说,而不能自振也,若固然矣。然而,言语思想之自由,根于天赋,而演进之公理,又举世所同,虽有雷霆万钧之力,只能阻其前进,而不能禁其横溢。”[3]1915年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说:“不进则退,中国之恒言也。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特以俗见拘牵,谓有二境,此法兰西当代大哲伯格森(H·Borgson)之创造进化论(L'erolntion Creatrice)所以风靡一时也。”[4]1916年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表明了自己对文学进化的看法,他说:“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5]笔者曾撰《论文学的进化与退化——20世纪的一种文学史观的检讨》一文[6],详细讨论了进化论对百年来中国文学史研究与编撰的影响,这里不再赘述。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和社会思潮下诞生的,其具有小说进化论的思想倾向是再自然不过的。根据进化论观点,小说也有由萌生、发展直至成熟的过程,小说在技巧上也是“由略到详,由粗枝大叶到琐屑细节的进步”[7]688。鲁迅以为,“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的文章,都很简单,而且当作记事实;及到唐时,则为有意识的作小说,这在小说史上可算是一大进步”[1]280;宋代文人于小说“无独创之可言矣,然在市井中,则别有艺文兴起,即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谓之‘平话’,即今所谓‘白话小说’者是也”[1]87。显然,他是把唐传奇、宋话本以及后来的章回小说作为了完整而成熟的小说作品,并以此为标准,“在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索来”[1]268,从而构建起他的中国小说史的体系。即是说,在鲁迅心目中,中国小说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进化的过程,越往古代,小说就越粗略,越往现代,小说就越成熟。根据小说进化的线索,鲁迅归纳出神话传说、汉人小说、六朝志怪志人、唐代传奇、宋元话本、明清章回小说等不同的小说类别,这些类别显示了小说在故事情节、叙述手法、描写艺术等从粗糙到精细完备的发展轨迹。神话传说是小说渊源,六朝志怪、志人小说承上启下,唐传奇直接受到志怪小说的影响,开始了有意识的小说创作,又为明清小说提供了艺术上的借鉴;明清章回小说则无疑是最成熟的小说形式。因此,有学者按照这一逻辑断言:“就中国真小说而言,直至元后始起。”[8]36
按照鲁迅的小说观和小说史观,六朝志怪和志人著作虽然不是成熟的小说,但它们却是小说进化史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志怪书的虚构性与故事性特征,不仅符合鲁迅的小说观念,而且作为唐传奇的直接来源,在古小说的进化发展中有着承上启下的独特的地位,不能不特别关注。而志人之书秉承传统史家传记笔法,在魏晋名士清谈的习俗中有所发展。魏晋清谈虽是汉末士流清议的延续,但它与崇尚虚无的玄学相结合,使得魏晋人“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呈现出与“汉之惟俊伟坚卓为重者”迥异的精神面貌[1]45。这种记录名士言谈举止的作品,在人物刻画、语言描写、情景设置等方面,为后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对于小说技术的进步也不可忽视。
志怪作品是六朝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文体形式之一。志怪虽说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如先秦的神话、寓言,两汉的方士小说,都或多或少有志怪成分,但志怪作为一种文体直至六朝才蔚成大观。据李剑国先生统计,六朝时期,志怪小说可考者达八九十种之多[9]218。仅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到的就有旧题曹丕《列异传》、张华《博物志》、干宝《搜神记》、陶潜《搜神后记》、荀氏《灵鬼志》、陆氏《异林》、戴祚《甄异传》、祖冲之《述异记》、祖台之《志怪》、刘敬叔《异苑》、刘义庆《幽明录》、《宣验记》、东阳无疑《齐谐记》、吴均《续齐谐记》、王琰《冥祥记》、王浮《神异记》、颜之推《集灵记》、侯白《旌异记》、王嘉《拾遗记》等,以《搜神记》为其代表作品。志怪小说如此繁盛,根本原因在于六朝时宗教思想的盛行。如鲁迅所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1]29《中国小说史略》全书28篇,鲁迅用了第五、第六两篇的篇幅来叙述“六朝之鬼神志怪书”,由此可见他对这一类作品的重视。
志人作品以记述人物的轶闻琐事、言谈举止为内容,也是具有六朝特色的文体形式之一。鲁迅以为:“其时释教广被,颇扬脱俗之风,而老庄之说亦大盛,其因佛而崇老为反动,而厌离于世间则一致,相拒而实相扇,终乃汗漫而为清谈。渡江以后,此风弥甚,有违言者,惟一二枭雄而已。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1]45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中有一篇专论志人作品,题为“世说新语与其前后”。其中提到的作品包括裴启《语林》、郭澄之《郭子》、刘义庆《世说》、沈约《俗说》、殷芸《小说》、邯郸淳《笑林》、杨松玢《解颐》、侯白《启颜录》等,以《世说》为其代表作品。
志怪、志人这两类作品与六朝人的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紧密联系,且作品数量多、一些作者地位颇高,在六朝时期影响广泛,并对后世的小说样式及其他文学体裁产生了深刻影响。鲁迅以这两类作品作为六朝小说的基本类型,是从这些作品的基本形态及其与小说进化的关联度来考虑的,符合他的小说观和小说史观,体现了他独特的学术眼光。如果说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还没有直接使用“志怪小说”、“志人小说”这样的称谓指称这些作品,也许是受到传统观念的制约而有所顾虑的话,那么,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的演讲中,他便直接使用“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来指称这些作品了。他说:“此外还有一种助六朝人志怪思想发达的,便是印度思想之输入。因为晋、宋、齐、梁四朝,佛教大行,当时所译的佛经很多,而同时鬼神奇异之谈也杂出,所以当时合中、印两国底鬼怪到小说里,使它更加发达起来,如阳羡鹅笼的故事……就此也可知六朝的志怪小说,和印度怎样相关的大概了。”[1]275~276而“六朝的志人的小说,也非常简单,同志怪的差不多”[1]276。鲁迅意识到无论是“志怪小说”还是“志人小说”,与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或说他的小说观)是有距离的,但它们在小说发展史或进化史中又是不可或缺、不容忽视的,因此需要特别加以关注。鲁迅之后,治中国小说史者普遍接受了鲁迅的小说观和小说史观,对于六朝小说,在他们的小说史著作中大都重复着鲁迅的意见,没有多少新的突破。如范烟桥的《中国小说史》(1927)、胡怀琛的《中国小说的起源及其演变》(1934)、谭正璧的《中国小说发达史》(1935)、郭箴一的《中国小说史》(1939)、孟瑶的《中国小说史》(1965)、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的《中国小说史稿》(1960)、北京大学中文系重编的《中国小说史》(1978)、南开大学中文系的《中国小说史》(1979)、谈凤梁的《中国古代小说简史》(1988)、杨子坚的《新编中国古代小说史》(1990)、齐裕焜、陈惠琴的《中国古代小说发展演变史》(1990)、侯忠义的《中国文言小说史稿(上)》(1990)、徐君惠的《中国小说史》(1991)、李悔吾的《中国小说史漫稿》(1992)、石昌渝的《中国小说源流论》(1994)等,包括专论六朝小说史的如侯忠义的《汉魏六朝小说史》、王枝忠的《汉魏六朝小说史》等,这众多小说史著作中的绝大部分基本沿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小说观和小说史观,六朝小说也以志怪小说与志人小说为固定称谓和主要叙述对象。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中国小说史领域,至今仍处在鲁迅时代”[10]85。除了小说史著作外,古代文学史著作在描述六朝时段的文学面貌时,几乎毫无例外也将志怪小说、志人小说作为这一时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并非六朝时期出现的小说概念,而是鲁迅的创造,这一创造是与他的小说观和小说史观契合一致的。然而,这样选择小说史叙述对象和概括小说作品形态,与这些作品在六朝的实际存在状态却有一定的隔膜。鲁迅不仅深知这一点,并且不厌其烦地在自己的著述和演讲中加以说明,留给后人许多想象和讨论的空间。
按照鲁迅的小说观,故事性和虚构性是小说的两大基本元素。然而,六朝的“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在故事性方面并非特别注重,其描写都很简单,多是粗陈梗概,并且没有自觉的艺术虚构,称之为小说也许名不副实。
鲁迅指出,六朝志怪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1]29。又引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谈》中的论述云:“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着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他的基本结论是:“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1]54应该承认,唐人的“始有意为小说”与六朝人的“非有意为小说”之区别,不仅涉及小说形态,更涉及小说观念。即是说,在六朝人心目中和作者们的实际创作中,并无虚构故事以成小说的观念。并且,在六朝人甚至在晚唐五代以前人的眼中,志怪书和记载社会生活的历史书其实并无截然的区别,唐初史家编撰晋史,便把鲁迅所谓志怪小说的代表作《搜神记》当作信史,大量采入《晋史》中。事实上,《搜神记》作者干宝本是东晋著名史学家,元帝时以著作佐郎领修国史,著《晋纪》23卷,时称良史。其所作《搜神记·自序》云:“今之所集,设有承于前载者,则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辈分其讥谤。”[11]2由于他坚守信实的原则编撰《搜神记》,故被时人誉为“鬼之董狐”,《搜神记》也因此成为“信史”被唐人采入《晋史》。鲁迅也说:“六朝人并非有意作小说,因为他们看鬼事和人事,是一样的,统当作事实;所以《旧唐书·艺文志》,把那种志怪的书,并不放在小说里,而归入历史的传记一类,一直到了欧阳修才把它归到小说里。”[1]278~279这样看来,六朝人并不以志怪书为小说,将六朝志怪书收入小说史应该说是与六朝人观念并不符合,与鲁迅所主张的小说观念也是有些隔膜的。
六朝志人书亦复如是。六朝志人首先强调的不是虚构而是真实,与小说的虚构性要求大相径庭。例如,东晋处士裴启撰集“汉魏以来迄于今时言语应对之可称者,谓之《语林》”,开始颇为流行,为人称道,后因记谢安语不实为谢安所诋,其书终于不传。此事被刘义庆记录于《世说新语·轻诋》中,作为著作者的鉴戒。他所撰著的《世说新语》也以真实为第一要务,不敢有所疏忽,自然谈不上艺术虚构。至于其“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1]47,并不是艺术虚构的结果,而是魏晋之风度使然。正如鲁迅所说:“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去,阮光禄之烧车,刘伶之放达,是觉得有些奇怪的,但在晋人却并不以为奇怪,因为那时所贵的是奇特的举动和玄妙的清谈。”[1]276-277作者如实记下这些“奇特的举动和玄妙的清谈”,就成了今天让我们惊异以至神往的佳作。当然,我们也不否认作者描写技巧的高妙,而史学家不同样也需要这种描写技巧吗?司马迁的《史记》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至于故事性,六朝志人书也不刻意追求。以《世说新语》为例,无论记言记行,只是粗陈梗概,写到为止,就像王徽之访戴安一样,“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世说新语·任诞》),并不追求故事情节的丰富和完整。既然如此,我们又凭什么称其为小说呢?
不过,话得说回来,鲁迅以六朝志怪、志人书为小说,除了有小说从萌生到成熟、从粗糙到精致的进化史的考量外,于中国传统文献学上也是有根据的。中国古代小说和小说观念一直在发展变化着,鲁迅按自己的小说观念来选择小说对象,亦是传统的延续。历朝历代的书目著作编撰者都是按自己的小说观念来选择小说对象的。《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首创小说家类,它给小说家的定义是:“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以为小说是“刍荛狂夫之议”。其著录的小说作品多为方士的虚诞依托之作。《隋书·经籍志》虽然承袭《汉志》旧说,著录《燕丹子》、《杂语》、《郭子》、《辨林》等为小说,但同时也著录了《琐语》、《笑林》、《笑苑》、《解颐》、《世说》、《小说》等作品,这些作品的故事性、娱乐性特征使小说有了新的内涵。此外,《古今艺术》、《鲁史欹器图》、《器准图》等艺术博物类书籍也被著录入小说,使小说显得更加羼杂。欧阳修等所编撰的书目《崇文总目》和《新唐志》等,根本性地改变了文献著录中六朝小说的面貌。他们将《隋志》、《旧唐志》史部杂传或杂史类著录的大量六朝志怪书转移进子部小说类,这在客观上反映了人们对小说的故事性和虚构性特征的认识和对历史著作的真实性的要求,其小说观念也逐渐趋于向近代发展[12]。以后的目录学分类,大体沿袭了《新唐志》的分类。既然自欧阳修以来,人们已经认可了《搜神记》之类的志怪书就是小说,鲁迅为什么不能称它们是志怪小说,我们又凭什么说它们不是小说呢?至于像《世说》之类志人书在中国图书分类上一直是列在小说类的,直到《四库全书总目》也仍然如此,称之为志人小说似乎更没有不妥。退一步讲,即使古人从来没有把志怪、志人书当作小说,今人难道就不可以把它们当作小说吗?例如,《山海经》在中国古代目录学分类上长期著录在史部地理类,《四库全书总目》将其列入子部小说类,以之为小说,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每一个时期的文化结构、思想观念都存在差异,当时人用自己的小说观来重新为作品分类,不仅是允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李时人先生所说:“至于有人不赞成用近世的小说观念去界定中国古代小说,理由也不一定很充分。……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观念认识,每个时代使用每个时代的学术概念,本来就是很自然的事。《四库》馆臣纪昀们以他们对‘小说’的认识决定对‘小说’的取舍,我们自然也应该以我们对小说的认识来界定小说。”[13]这一说法显然有很强的说服力。
然而,问题并没有因此解决。今人固然有按照今人的学科标准重新划分古代学科和重新对古代文献进行分类的权力,有按照今人的小说观和小说史观构建中国小说史的权力,但并没有要求古人遵守今人的学科分类标准和接受今人的小说观念的权力,也没有曲解古人的观念以合于今人的要求的权力。事实上,在今人对六朝小说的研究中,存在着这种滥用权力的现象,造成了一些使人困扰的误区。
这里不妨以欧阳修作为一个案例略加分析。欧阳修把《隋志》、《旧唐志》史部杂传类的一批作品如《搜神记》之流改录于子部小说家类,是因为他的历史观和小说观与五代以前的人们迥别。他认为,正史应记载“君臣善恶之迹”,“要其治乱兴废之本,可以考焉”(《崇文总目叙释·正史类》);而传记“或详一时之所得,或发史官之所讳,参求考质,可以备多闻焉”(《崇文总目叙释·传记类》)。即是说,历史著作应该记载朝政大事,以真实为生命,其基本事实是可以考证质实的。至于小说,欧阳修认为:“《书》曰:狂夫之议,圣人择焉。又曰:询于刍荛。是小说之不可废也。古者惧下情之雍于上闻,故每岁孟春以木铎徇于路,采其风谣而观之。至于俚言巷语,亦足取也,今特列而存之。”(《崇文总目叙释·小说类》)即是说,小说可以不受真实性限制,不需要去考证质实,只要下情能够上达就发挥了它的作用。《搜神记》之类志怪书不符合史书标准却符合小说标准,所以需要重新分类。欧阳修按照他的历史观和小说观在《崇文总目》和《新唐志》中重新对文献分类,其实存在巨大风险。其一,这一分类标准恐怕难以服古人之心(六朝人相对于欧阳修来说也是古人)。干宝曾在《搜神记自序》中说:“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又安敢谓无失实者哉?卫翔失国,二传互异所闻;吕望事周,子长存其两说,若此比类,往往有焉。从此观之,闻见之难,由来尚矣。夫书赴告之定辞,据国史之方策,犹尚如此;况仰述千载之前,记殊俗之表,缀片言于残阙,访行事于故老,将使事不二迹,言无异途,然后为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国家不废注记之官,学士不绝诵览之业,岂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11]2前面已经说过,六朝人以鬼神为实有,人鬼之间并无诚妄之别,所以真实或虚构不能准确描述他们的观念。何况正如干宝所说,史书记载也并非真实可靠,因为记载历史的史家不可能事事亲见亲闻。在历史上发生的同一件事情,可能有几种不同记载,到底哪一种记载真实可靠呢?即使是那些没有分歧的记载,就一定符合历史的真实吗?立场不同,视角不同,认识不同,方法不同,都可能影响对事件的记载,因而真实并无绝对的标准。其二,欧阳修的新分类反映的是宋人的历史观和小说观,自然无可厚非,但以这种分类去描述六朝小说历史,就遮蔽了六朝小说历史的原貌,使人们看不清六朝小说观念与小说形态的历史状况,影响了人们对六朝小说的正确认识。
鲁迅运用现代小说观念观察六朝文学,并按照自己对小说的理解来决定小说作品的分类和取舍,他和欧阳修一样,把《搜神记》等志怪书归入小说类,同样存在与欧阳修类似的风险。与欧阳修不同的是,他十分清楚地说明了六朝人对鬼神的认识以及他们的真实观,即是承认,他的分类采用的是他所处时代的学科分类标准,而并非古人的标准,对小说的内涵不同时期人们的认识不尽相同,今人应该实事求是地了解古人的认识。有了这样的交代,我们对中国古代小说的认识就不会过于简单,对小说发展规律的探讨就会更加务实而谨慎。这是鲁迅的高明处,也体现了鲁迅严谨的学风。
鲁迅既然知道六朝人并非有意识为小说,其真实和虚构的概念与后人也不一样,那他为什么要将志怪、志人书作为小说,并视作中国小说发展的重要阶段呢?这主要是建构小说史的需要。因为如果缺少这个环节,小说进化史的线索就不清晰,结构也就不完整了。这就牵涉到小说史观的讨论。
小说进化史观确实有它的很多好处。它运用统一的概念,采用统一的标准,对历史事实进行统一的剪裁,能够做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让人们很容易理清出小说发展的历史线索。然而,历史发展并不如我们所理解的这样单纯和简单,这样具有条理和统系,正如陈寅恪批评某些中国哲学史著作时所说:“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14]2中国小说史也是如此,其“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小说历史之真相愈远。就六朝志怪书而言,我们固然可以按照今人的小说观视其为小说,但并不能按照进化史观以为它只是小说进化史的一个环节,因为志怪书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六朝之后,这一文体也仍然保持着蓬勃发展的态势,如唐人唐临的《冥报记》、孔慎言的《神怪志》、赵自勤的《定命录》、温畲的《续定命录》、牛肃的《纪闻》、戴孚的《广异记》、张荐的《灵怪集》、旧题柳宗元的《龙城录》、陈劭的《通幽记》、牛僧孺的《玄怪录》、李复言的《续玄怪录》、韦绚的《戎幕闲谈》、谷神子的《博异志》、薛用弱的《集异记》、李玫的《纂异记》、李亢的《独异志》、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张读的《宣室志》、佚名的《闻奇录》等,以及南唐徐铉的《稽神录》,都是颇有特点的志怪作品,也大体保持了六朝志怪的风格。至于宋人的志怪书,李建国《宋代志怪传奇叙录》录宋人志怪和传奇205部(不计存目21部),其中多数为志怪作品,著名者如吴淑的《江淮异人录》和《秘阁闲谈》、张师正的《括异志》、章炳文的《搜神秘览》、秦再思的《洛中纪异》、张君房的《乘异记》、洪迈的《夷坚志》、张邦基的《墨庄漫录》、郭彖的《睽车志》、王明清的《投辖录》等,也多继承了六朝志怪书“搜奇记逸、粗陈梗概”的传统。直到清代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六朝志怪传统的深远影响。如果六朝志怪仅仅是中国小说进化的一个环节,那又如何解释这源远流长的志怪传统和大量志怪作品?其实,志怪作品有自己发展的历史,完全可以单独写一部志怪小说史。志人书也有类似情况。并且,“文学是一个与时代同时出现的秩序”[15]31,中国古代子部小说与通俗小说在传统文化中本来分属两个不同的子系统,一属主流文化(不管其地位有多低),一属非主流文化(不管今天评价有多高),它们各有其发生发展的特殊路径,其源头也各不相同[16],虽互有影响,却各自独立,这只要看看历代正史中从不著录一篇通俗小说即可明了。因此,按照进化论建构的中国小说史并未能客观地反映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状况,自觉不自觉地将许多古代小说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那些拟定的各种小说体式之间的联系也并非都真实可靠,中国古代小说自身的许多特点和影响中国小说发展的众多因素可能在进化论的干扰下被屏蔽掉。正如齐裕焜先生所说:“进化论的观点不能完全正确地阐释小说史的发展,在强调一条进化主线时,容易忽略主线之外的其他小说的演变,容易忽视其他因素对小说发展的影响。”[17]并且,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是否在进化,又如何进化,也是一个没有论证且无法证明的命题[6]。因此,中国小说史的建构从鲁迅开始,不必也不应该到鲁迅就结束,全体小说研究者都有责任和义务用新的观念、新的视角、新的方法来重构中国小说史,让中国小说史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以推动中国小说史研究的深入,发现和总结出中国小说的民族形式及其文化特色,为新时期的小说创作提供经验。
本文以六朝小说为例,分析了鲁迅以来中国小说史建构中小说观和小说史观对小说研究的影响,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却没有给出解决问题的明确答案,可能让读者失望。然而,如果承认这些问题的存在,也就知道了努力的方向,为解决问题提供了动力和参照,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小说史研究必将呈现出崭新的面貌。正所谓“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标签:中国小说史略论文; 小说论文; 鲁迅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文学论文; 六朝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志怪小说论文; 读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