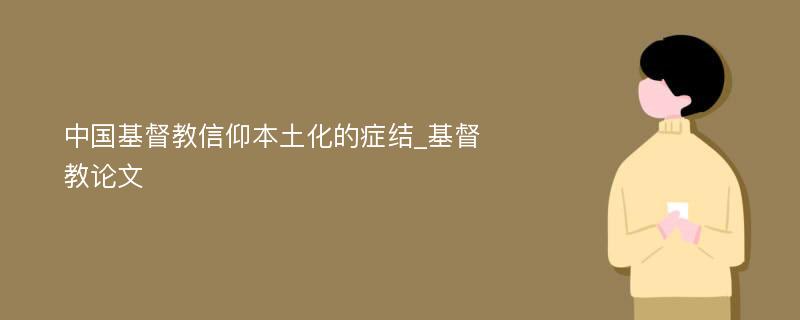
基督信仰中国本土化的症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论文,本土化论文,症结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基督信仰传华以来,有15个世纪的长远历史,自入华伊始,便致力于本土化,却迄今未见成功,未尝建树一种略类于中国佛教的中国基督教,根源究竟何在?
或谓近代基督教在华广传,乃以不平等条约为先导,颇有文化侵略之嫌。中华民族的自尊受到挫伤,故对基督信仰较之其他外来信仰,拒斥特甚。近百年来便有多次民众性的运动,皆与拒斥外来基督教相关,如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20年代的反基督教运动,50年代的三自爱国运动,皆是。在此历史形势下,基督教广传则广传矣,深入本土文化则缺乏和平交融的心理基础。
此论虽似有历史实据,然仔细思量,实不构成充足理由。一者,反基督教运动大抵局限于近几十年之内,而基督信仰入华有近15个世纪的历史,何以长久未能广传华化?假使在1900年以前早已本土化,尚会发生近代之反基督教运动乎?二者,以佛教为例,入华以来又何尝未曾受过多次的反佛运动?北魏太武、北周武帝、唐朝武宗以及后周世宗的灭佛运动,皆恃朝廷的权势,远较近世的反基督教运动为惨烈,而儒道二家历代多次的辟佛运动,也比“反基”的宣言批判有过之无不及。然而佛教终于融会中国社会及文化心理特质,形成独具中国风貌的三论、天台、华严、净土、禅宗,长久以来,儒道释三教终渐趋交融而成中国传统文化。而基督信仰,无论借着什么时势广传,也只处于这个文化传统的边缘。五四时代以来,国人曾对传统文化进行长期而系统的毁坏,社会体制亦长久处于震荡嬗替之中。不论在制度抑意识层面,固有的儒道释传统皆已成支离疏叟,却并未溘然长逝。扭曲凋蔽而又杂学旁收的传统意识,仍然支配着国人的一言一行。处于这支离文化中心的仍是儒道释,而基督信仰亦仍居边缘地位。何以如此?
既然舶来信仰大抵经过颇相类似的风雷之变,故用外部条件说明其归宿之殊途,恐难服人。印度佛教得以融会中国文化,说明两种文化在根本观念上必有相通之域。基督信仰未得融入中国文化,亦说明两种文化在世界观上有拒斥之域。皆以内在的条件为依归。外在条件只是提供一种机遇而已。
具体言之,基督信仰所代表之文化系统,特具一种目的论世界观,就本文宗旨而言,可自目的论历史观立论。犹太文化传统,自古以来强调独一上帝创造世界以及先知预言的弥赛亚救主等观念。这里蕴涵目的论的历史观。时空的推移,人类历史的进程,是一种神圣计划得以实现的过程。宇宙的秩序,历史的进展,皆不是自在的存在,而依存一自在永在、即外在于时空世界又以特殊启示临在于历史的神圣力量。故犹太文化的历史观是一种神圣的启示的目的论历史观。这便是基督信仰的世界观基础。西方希腊文化得以接纳基督信仰,根柢是二者皆秉具一种相通的历史观,即希腊目的论历史观。古希腊悲剧的构成因素便是人的命运在神,也就蕴涵历史的神圣性。努力在人,但人的努力终归为神的目的所挫败。德尔菲的神示永为模糊两可,不是人的理性所能猜透。克雷安提斯向宙斯的祈祷,是祈求按个人的努力行事。柏拉图的理念世界,是一个具有神圣秩序的本体界。《斐多篇》描述的地表以上的光明世界,被汤因比拟作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A.Toynbee, Civilization onTrial、The World and the West,Cleveland and New York,1963,)亚里士多德的宇宙亦是一个目的论的世界。希腊化时代的新柏拉图主义“伊涌”(或译作“伊昂”,Aeon,系柏拉图哲学和诺斯替哲学重要概念,意指自古而在的力量,神的溢出物,永恒之本质。——编辑谨识)救赎模式,已向犹太传统靠拢。加上斯多葛主义的目的论宇宙观,便是希腊文化接纳基督信仰的思想基础。在根本论域,两种文化不是异质相斥,而是有着广阔的在观念结构上同质的融会领域。
中国文化的宇宙图景则不同。在中国人的思维视野中,历来不具神圣秩序的本体界与现象界相分离的观念结构。历史的进程并不体现一种神圣目的之实现。上帝的创世与救赎计划之类的思维模式,根本在中国文化视野之外。上古的人格神祗,诸如《诗经》、《尚书》中的上帝、天帝,虽然受到敬畏,在人采取行动时或亦引用其意志,但神的意志既无启示诚命又不与人交通,十分模糊分散,并不构成秩序化的宇宙目的。人的行动终归以人的理由,即义与德,来说明。历史不具目的,为未知者,人的理性努力乃是最终的标准。《立政》:“吁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敬畏上帝是知慎,具体准则是九德之行。《皋陶谟》:“在知人,在安民。”不在知天。《汤誓》:“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但如问“其罪其如台?”则为“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一以人事为标准。“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皆自人意验之。《左传》里大量的“天夺之”“天赐也”“天救之”“天祸……”“天欲杀之”“天将兴之”其实皆属于为人的行动找寻理由,与《旧约》中上帝亲手的行动绝不相同。孔夫子发誓则曰:“天厌之,天厌之?”与现代人发誓并无不同。利玛窦氏所谓“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纯系比附,实则两种语义系统在同一相类的词语之下所述说的实为两个根本不同的世界图景。圣经中的上帝与人订约,有明确的启示诚命,与人的祈祷对话,介入历史有所行动,化成肉身,为人的罪受难,以此救赎人的罪,复活升天,以圣灵引领人,将再来审判活人死人,带来新天新地。总之圣经中的上帝蕴涵一个有目的之宇宙和实现创世主救赎计划的历史。这个历史结构便蕴涵人的原罪,即人本性中意志和理性的堕落和无力自救。而中国古代经书中处于模糊背景中的天帝则蕴涵一个未知的宇宙和以人的努力为转移的历史结构。这个历史结构便蕴涵人性的乐观和人的自足。《易大传》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或可代表此种历史观。“天行健”是一种猜测,类于泛神论的对不可知的天道之敬畏,是一种信仰情怀,却不足以构成热烈虔敬与神交通、受神引领的宗教生活,而关怀的重点则是“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古代经书记载观之,中国的历史观从来如此。
至春秋战国之际,儒家的天道,已脱离人格上帝的模式。“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所重:民食丧祭。”(《论语·尧曰》)孔子关于天命的言论甚少,大抵处于暗淡的背景地域。墨子主张有天之志,但知天意的方法如轮人操其规,以量度圆与不圆,也就是以人的规范为准。“观其行,顺天之意谓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谓之不善意行。观其言谈,顺天之意谓之善言谈,反天之意谓之不善言谈。观其刑政,顺天之意谓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谓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为法,立此以为仪,将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与不仁,譬之犹分黑白也。”(墨子·天志中》)天意只是一种判断仁与不仁的方法。天既无启示又无计划,而“天欲义而恶不义”早已设定,人与天并无交通。“何以知天之爱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念焉。何以知其兼而念焉?四海之内,粒食之民,莫不牛羊、豕犬,洁为粢盛酒醴,以祭祀于上帝鬼神。天有邑人,何用弗爱也。且吾言杀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杀不辜者谁也,则人也。予之不详者谁也,则天也。若以天为不爱天下之百姓,则何故以人与人相杀而天予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爱天下之百姓也。”(《天志上》)墨子知天意,全赖假设与推论,其设定的义之标准即是天意。老子则全然否定意志的天,而代之以自然的道。天法道,而道则是本然如尔。道是宇宙本原,万物之宗,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显然不具主宰的意志人格。道又是形而上的超越界,不可知,不可名,惟恍惟忽,玄之又玄,是神秘主义信仰的对象,如果理解为临在于万物的“万物之奥”,则稍类于泛神论。韩非子理解老子的道为“万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则不是物各以据的物理规律,仍是形而上的道。老子更言“太”“一”,《吕氏春秋》合之为“太一”,以及阴阳(“万物负阴而抱阳”),似为太极阴阳的宇宙观的先导。
大凡古老的伟大文化传统,皆在古代某一特殊机缘中有过一个黄金时代,其时巨人辈出,百葩怒放,神思煌跃,与日争辉。在中国,便是春秋末至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民族睿智成熟、性格塑型的时代。如同个人,一个民族亦有其性格的塑型时期。一旦形成民族的语言结构,以及蕴涵其中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态度等基本模式或潜在前设,这个文化的发展便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和选择性。文化不是永住不变的本体,自然处于变动不居的过程中。由于地球上人类共存的交流,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必交融,有时候一种文化甚至发展为原来形态的异质形态。然而一种文化越是有自身的完整观念体系,以及处理人与世界和人际关系的自信,则越难融会异质的文化。如果将文化狭义地理解为人的生存手段,则一个民族越是处于生存危机之际,越是可能迷失文化的自信,而接纳或服膺外来甚至入侵的文化。汉末南北朝,异族入主,兵火连年,公私涂炭,丧乱流离。当此之时,武帝独尊的儒术,既已倾压百家的活泼创造性思维,又已融合谶纬阴阳灾异之说,早已不复支持民族的自信。自孝武至于哀平,百余年间,儒生进用,功业志气纪于世者,不过三四。汉初原来重用黄老,以其顺阴阳之大,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无所不宜。至魏晋,崇尚个人自由蕴蓄精神解脱的老庄思想大行于世,在这一落一扬之间,便呈现印度佛教入华广传的机缘。而佛教信仰的对象,原非主宰万物介入历史的救主,故给人的自主留有相当余地。
中国文化的所谓特质,就其最普遍一般的价值取向而言,并非儒家或其他某一学派的学说,而是汉语结构中所蕴涵的一种世界观模式,大体而言,可姑称之为非神圣目的论的世界观模式。此种观念结构,与中国传统各家思想皆可相通,可以说是中国民族所共有的关于世界人生的基本观念或态度。假若不追究终极原因,“目的”可以不关涉意志,更与神圣性无关。论及宇宙整体的目的,实已超越人类理性及知识,故关涉神圣意志或目的之信仰。在中国人的信念中,对于宇宙及历史是否体现一种确定不移的神圣计划,与其说有一种确认的信仰,勿宁说持一种未知或不可知的敬畏之心。这也是对于超越界的一种信仰情怀,但独具中国民族的性格。其特点是并不确信或深究神圣意志的结构,并创造一个严整的象征、仪式、观念系统来表达人与神圣意志的交通,以此反复加强对神圣意志的确认和信仰。这正是中国文化心理对世界的根本态度:即信仰一个超越的世界本原(天、道、理、太极),又不以人可确证交通的方式深究其结构,而满足于敬拜(古代天帝崇拜及民间信仰)、冥思(道家)、敬而远之(先儒)、敬而用之(墨家及董仲舒派)、思而修身(理学及心学)。在这个根本态度中,蕴涵着非目的论的历史观,人的自足或自弃,以及对人性的乐观或悲观。既然信仰宇宙的神圣本原而又不可知其确切的目的计划,人的存在便是孤立无助的存在,除自强不息、冥思超脱或反求诸已而外,只有醉生梦死。彼岸的救度,本在中国文化视野之外。
此种非神圣目的论的世界观隐涵在各家中国思想以及中国人行为模式中,可谓中国的基本文化心理。上文已经探讨儒道墨各家学说中隐涵的此一根本观点。宋儒较之先儒更明确地排除神圣意志,而设定自为、无意志、无启示的理或太极。如周敦颐《通书·顺化》称:“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实即《易大传》的“神无方而易无体,阴阳不测之谓神。”以及荀子《天论》的“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谓之神”的复述。邵雍也说:“天之象数,则可得而推,如其神用,则不可得而测也。”(《观物外篇》)。程伊川则公开批判先儒经书中的天帝意志:“万物皆是一个天理,已何与焉?至如言‘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理自然当如此。”(《河南程氏遗书,二先生语二上》)朱熹所谓“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也是自然的理,需要人通过格致修养的方法去体验,理本身并无启示的历史目的及救赎计划。至若心学,则一切唯心,“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陆象山《与李宰书》)“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王阳明《答李明德》)“人心是天渊,心之体无所不该,原是一个天,只为私欲障碍,则天之本体失了。心之理无穷尽,原是一个渊,只为私欲窦塞,则渊之体失了。”(《传习录》)心学所关注者,是去私欲,求良知,更无所谓历史的神圣目的可言。心学的“心”定义模糊,致使立说支离。湛甘泉说“所谓心者,非偏指腔子里方寸内与事为对者也,无事而非心也。”(《语录》)这里牵涉所谓“内在超越”的问题。如果“超越”指超越于人类全部经验,则无所谓内在超越。如果“超越”指超越于人类理性知识,亦不可能作为先天观念而内在于人的“心性”。如果“超越”指内在于世界的形而上(超越范畴)的理,又如何能具于人的“心性”?总之如何向人的“心”达致“超越”必须给以清晰的定义方能知其所言为何物。
在传统中国思想中,表面上有神圣目的论色彩者,有片断言论,如《中庸》中的“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以及孟子所谓天如欲平治天下等语。此外便是邹衍的五德终始说, 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今以董说为例。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引用阴阳消长、五行生克的阴阳家言,设定一种宇宙结构,仿佛说明神圣目的在宇宙历史中的实现。然而他所描述的每一宇宙结构,皆实现为非神圣的目的,即所谓王道,或三纲五纪之类的尊卑秩序,所谓“起于天至于人而毕。”例如五行相生之序:“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而金受土,水受金也。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是故木已生而火养之,金已死而水藏之,火乐木而养以阳,水克金而丧以阴,土之事天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五行之义》)又如:“阳之出也,常县于前而任事;阴之出也,常县于后而守空处,而见天之亲阳而疏阴,任德而不任刑也。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天为君而复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基义篇》)董仲舒的宇宙结构是以人事为指归,而他的人性和社会结构,则是“副天数”和“配天”。总之,天的目的在人事,而人对天意的领悟在于猜测和比附。既然目的在人事,亦即没有神圣目的。神圣目的论的要旨,在于历史体现神圣的计划,最终使世界包括人复归于神圣(在基督信仰则是通过言成肉身的基督受难之救赎)。董仲舒的宇宙结构,如果说有目的,则是使世界实现王道和三纲五纪,而非复归于神圣,因此并无神圣目的论可言。
于此可知,中国文化心理的基本前设,与基督信仰的基本前设,并不相通;接受或持守其一,则必放弃另一。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理论上,如果一个中国人皈依基督信仰,必放弃非神圣目的论的世界观历史观。如果他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教养的知识者,必经历一番深刻的传统文化批判反省和调整的自我改造过程。这样的实例也确实不少。明末以来士人归信基督信仰之后的一些文章著作可以参证。走极端者,今人如章力生归信以后的大量著作,几乎是对中国文化的系统批判书。如果皈依者是一个未受高深教育的普通人,而又对教义有相当的理解和执著,则他必在固有的中国式生活态度上做出相当深入全面的改造和调整,包括对罪与人性,对善与恶,对生与死,对人际与家庭等的感性态度。然而事实上并不如此泾渭分明。那是因为人在心理上有安于矛盾的倾向之故。再者,人对教义的理解与执著亦有相当大程度上的差异。然而无论如何,有两种情况历来存在,则不容否认。其一是中国基督徒居民在社会上相对地疏离一般居民,而自成社区。在中国,信仰基督者不可能如信仰儒道释的居民那样舒畅地安于中国文化环境。其二是基督教历来采取融会中国文化的态度却始终不见成效,即而复离,离而复即,疏也依然。
佛教的情形则迥乎不同。其根本观念与中国文化心理并不形成结构上的非此即彼式的对立。佛是觉者,成佛是正觉,皆以人为立足点,而不是本体界的神圣计划在历史中的实现。佛教的彼岸救度,与中国的成圣成仙可以相通,而非目的论之使世界归于神圣。以中唐以后广为流传的弥陀信仰为例,阿弥陀佛本是国王法藏,于世自在王佛跟前听法,弃国向道,发二十四愿,成佛度人。愿国中无三恶道名,愿国人得无量寿,以及观世音救苦救难等关怀现世的理想,颇与中国圣贤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居天下之广居而得志与民由之、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的普救精神,在观念结构上有相通之处。弥勒信仰的兜率净土,在欲界四天,俨然乐园,与中国的神仙理想亦有相通之点。此种救度,对于中国人而言,亲切近人,与创世主的独生子通过受死而救赎人类的罪并审判活人死人的神圣目的极不相同。大乘佛教的许多观念,诸如观理得性、理事不二、法性融通、诸法为佛、一念三千、贪欲即道、即心即佛、明心见性之类,皆与中国观念相通。
佛教东来,从发轫之初便利用与中国文化的共界,以求因风易行。般若学流行的原因,道安说“以斯邦人老庄教行,与方等经兼忘相似,故因风易行也。”(《鼻奈耶经序》)。大凡可以利用中国传统观念来诠解佛学原理的地方,往往因势利导,以求易行。诸如早期译经的安世高所译小乘上座部,特重禅数,其禅法之一是“安般守意”,控制呼吸和意念,颇与道家的吐纳相近,适合中国观念。三国吴康僧会译《察微王经》(出自《六度集经》)谓四大“地水火风”为元气的四态,灵魂与元气相合,轮转无际,其元气纯是中国概念。疑经《提谓波利经》将五戒比附儒家的五常:“佛言人不持者为五无行,煞者为无仁,食酒为无礼,淫者为无义,盗者为无知,两舌者为无信,罪属三千。”并用阴阳五行诠释斋戒。又如南朝道生的顿悟新说,据“理不可分”提出“以不二之智,符不分之理,”与儒家的“理归一极”、“君子无所不用其极”相通,也属适应中国观念。佛教本土化的发展过程十分复杂,不在本文范围之内。这里仅举《大乘起信论》的本觉之说:“所言觉义者,谓心体离念。……依此法身说名本觉。……本觉义者,对始觉说。以始觉义者,即同本觉。始觉义者,依本觉故而有不觉,依不觉故说有始觉。又以觉心源故,名究竟觉。……以远离微细念故,得见心性,心即常住,名究竟觉。”印度佛教本主心性本寂,而中国化的佛教,从天台、华严到禅宗、皆主心性本觉,显系受中国传统心性观的影响。
自古以来,中国人便将心与诚、敬、德、道相联系,仿佛信仰的对象可以不在身外,而向心性求之,而向心性求之的前提,必是本觉。古经书中已有不少此类暗示,诸如《周书·立政》:“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长伯。”《酒诰》:“厥心藏。”《康诰》:“联心联德,惟乃知。”《公羊传·文公二年》:“以人心为皆有之。”《左传·喜公二十四年》:“心不则德义之经为顽,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嚣。”《闵公元年》:“且谚云‘心苟无瑕,何恤无家?’天若祚太子,其无晋乎?”《昭公二十年》:“其祝史荐信,无愧于心。”“心平,德和。”至若《礼记·大学》的那些“心诚求之”“心正而后身修”以及《孟子·告子》的“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尽心》:“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管子·内业》:“凡心之刑,自充自盈,自生自成。其所以失之,必以忧乐喜怒欲利。能去忧乐喜怒欲利,心乃反济。”《荀子·解蔽》:“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一而静。”“是之则受,非之则辞,故曰心容其择也。”仿佛心中皆有择善的本性。汉人如董仲舒,论心性虽驳杂,似也有“唯心”“诚敬在心”的倾向,诸如:“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诚。”(《深察名号》)“内视反听,故独明圣者知其本心,皆在此耳。”(同类相动》)徐干《中论·修本》:“人心莫不有理道,至乎用之则异矣。”晋傅玄《傅子》:“心者,神之主;万理之统。”佛教由本寂转向本觉,正是在这种文化思想环境中发生。一旦树立起禅家的明心见性,又影响宋儒的学说,凡此皆是中国文化心理在一定条件下合乎逻辑的发展。至王阴阳,乃集唯心之大成。阳明弥留之际但曰:“此心光明,何复可言?”如此自足自信,自与神圣目的论格格不能相入。非神圣目的论的世界观历史观不仅可从中国传统各家学说中抽绎出来,而且在《太史公自序》以及历代史家论述中亦有相当明确的表达。故可视为中国文化心理的最一般表现形式。心性本觉、心即理也云云,乃是此种文化心理在观念结构上的一种却并非唯一的合乎逻辑之演化。
如此说来,中国文化与基督信仰是否便永无融会的可能?世界并不如此简单化。历史也从未提供简单的必然律。上文曾论及,民族危机之际往往自信低落而易接纳外来的文化。然而历史经验也往往提供相反的例证。民族危亡既可以表现麻木冥顽,也可以如犹太民族那样,其命弥舛,其信弥坚。历史的机缘,难以预测。故中国文化与基督信仰的关系,亦不能论定。这里可以探讨另一种理论;来“辩护”中国文化与基督信仰融会的可能性。便是中国文化心理中隐涵的“作为方法的文化”论。
文化可以视为实体,甚至本体。后者又与语言本体论有关。现代西方哲学,从维特根斯坦到海德格,大抵与语言本体论相关。在语言结构之外并无意义的本原。此间有繁复的技术问题,本文不遑论及。总之可将文化视为不变的实体和意义的本原。其后承之一,便是异质文化不能相融和相容,甚至不能交流,而导致文化冲突论。然而中国文化心理既然不主神圣目的论,也就将文化和历史视作变化不已、流动不息的可塑性对象,而突显出人的主体性。事实上,任何文化,作为主体的人的产物,皆可视为方法,人的存在的形式。文化是过程而非实体,是方法而非本体。
过程的观念,与大易生生不息,以及“大道汜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的思想相通。与后儒气化学说、佛家的缘起之说,以及过程哲学,皆有相通之处。文化是人的精神产物,是与自然相对待的人之语言行为所构成的精神及物质结构。一旦形成,便成为意义的本原,有极大的相对稳定性格,故易被视为不变的实体。然而文化并非自在,不可能脱离人这个主体而存在。因此,只要人的存在生生不息,作为方法的文化亦必生生不息,恒常流动。
再者,过程流动的观念与时间的真实性相关。时间的历程不是简单的流逝,而每时每刻赋有新的内容和意义。故历时的文化即使呈相对的稳定态,也不是重复一种不变的实体,而是时时再创造一种模式。这种变易性、创造性,乃是作为方法的文化之基本存在形式。
作为方法的文化既然是过程,故亦意指内在的动力。这是文化自主性的根源,然而此种内在的动力不是维持不变的实体,而是推动生生不息的过程。文化结构的内在因素皆赋有自主的能动性。观念、话语、象征、仪式等皆具有交流、结合、发展的趋势。因此,作为方法的文化,就原初设定而言,便具有与他种文化相交流相融会的倾向。交流与对抗之不同,在于交流溯源于自主而非自足,对抗则取决于凝固不变的自足。在流变的世界中立足于不变的实体,必排他而终至对抗。反之,在流变的世界中立足于生生不息的过程,自然会审时度势,顺化而安。中国文化的基本态度,既然不视时间与历史为一神圣目的之实现,而视之为不可确知的自然过程,故中国世界观中蕴涵作为方法而非本体的文化。而作为方法的文化便蕴涵与他种文化的交流融会。因此,在中国文化的基本态度中亦涵有与基督信仰相融会的先在可能性。在原则上,在原初设定上,没有不可能融会的理由。迄今为止未能融会仅仅由于尚未找到融会的方法,而并非在原则上不可能融会。
作为方法的文化亦涵有人的主体性。文化之所以为方法,在于它是作为主体的人之存在的形式,而不是脱离人的自在。如果主体的人处于生生不息的过程中,时时寻求新的意义,那么作为方法的文化便是寻求新意义的形式。新的意义蕴涵新的关系,新的关系蕴涵交流与融会。在此意义上,中国文化的性格中涵有与他种文化包括基督信仰融会的可能性。生生不息、作新民、日月新、大道汜兮是探求新的存在意义的理据,却不是唯一可能的理据。基督信仰作为一种救赎的文化,其救赎的理念本身,新天新地的观念,亦是探求新意义的理据。因此,作为方法的中国文化与作为救赎的基督信仰之间,在原则上存在着交流融会的可能。
在简略探讨上述理论之后,再来审视基督信仰在中国本土化的问题,应该有新的视野。基督信仰若欲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生根立足,有几个契入点,值得探讨。
1.思想的契入点 本文曾用不少篇幅说明中国文化的基本态度是一种非神圣目的论的世界观历史观,即视时空与历史为一生生不息但却不可确知的自然过程,其中不涵有神圣的创世目的和计划,以及与此相关的启示。中国的神圣的理念,如天、道、太极、真如,无论外在于时空抑内在于心性,皆是一种不可确知的神圣性,而非明确的启示或救赎计划。人对历史,只知其实然而不知其必然。故人文的努力,备受尊崇,有时亦可弃之如敝履。格物致知,修齐治平,诚敬存之,无为寂灭,一切皆是人的努力,而非神的恩典。然而中国文化同时亦十分注重变易、创造、探求新的生存意义。当中国文化的自信处于相对低潮之际,印度佛教曾以“无”为契入点,融入中国文化,很快便超越“本无”而引入“性空”的信仰。基督信仰没有理由不可从神圣观念(而非由世俗观念如“孝”)为契入点寻求共同的语言。关键在于以同情的态度深入精研中国文化。如历代佛教大德那样博通内书外典而学养深湛的汉学者,在基督徒中间不可多得,而不抱 Patronizing 态度的霭然学者, 尤为难能可贵。
2.学术的契入点 基督徒学者的学养越精深,则理解和运用全部中国文化资源的可能性越大。大凡外来信仰,能否融会中国文化,与其能否以艰贞卓绝的成绩立足于中国学术有莫大关系。仅仅译介外国神学,只是一种学步,如果再加傲慢,恐连学步亦且未及。仅以译经为例,亦应直追六朝隋唐的庄严宏大。当时的翻译事业,固然常有朝廷的支持,然组织之缜密,备略之妥慎,用功之黾勉,辞义之庄雅,诚信之深笃,皆属个人努力之结果。于翻译原则的探究,亦不遗余力。竺法护的“言准天竺,事不加饰”,释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以及所谓“声声不别,印印皆同”的求真不舍精神,足令后之来者,有所敬畏。何况佛家的学术业绩绝不仅止经典的译介。
3.伦理的契入点 中国文化注重履践,对宗教生活的需求,以及对一种宗教的接纳,往往以传布者的人格表现为归依。听其言而观其行,讲道者所行之道,较其所讲之道,对于中国人而言更为真实。凡有善行救人的宗教,大抵易为国人所容纳。义和团时期内地会的戴德生,至今被人传诵。假如19世纪广传时期在华的传教士有成千上万个戴德生,也许不致发生义和团运动。明末利玛窦在士大夫阶层受到敬重,与其人格力量颇有关系。基督信仰在华成败的关键,颇大程度上在于有多少爱人如己笃行不倦的基督徒生活的中国人中间,活出基督。
4.美学的契入点 中国文化注重美感。中国人与宇宙自然以及超越的道之交流,常在美感领域。如果没有历代的佛教艺术,如石窟壁画、大佛石雕、庄严寺院、绘画诗歌、民间宝卷、戏曲传说,能否想象佛教在中国的流布?固然古代佛教建筑常有权势者的支助,如《洛阳伽蓝记》记述的佛寺四十所,皇帝敕建者四,后妃兴建者三,亲王建造者十二,阉寺所造者六。然而民间建筑尤赖信仰,艰苦卓绝。《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北凉石窟开凿情形:“……以国城寺塔终非云固,古来帝宫终逢煨烬,若依立之,效尤斯及,又用金宝终被毁盗。乃顾眄山宇,可以终天。于州南百里,连崖绵亘。……安设尊仪,或石或塑,千变万化。有礼敬者,惊眩心目。”又如《李君莫高窟佛龛碑》:“莫高窟者,厥前秦元二年有沙门乐樽,成行清虚,执心恬静,当杖锡林,行止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山臣,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尊师窟侧,更即营建。佛教在中国的成功并非偶然,确实付出最艰巨的劳作,发挥了信仰与人格的光芒。
以上所论契入点,意在提示,决非定论。总括言之,中国文化的天然性格,虽难调合所谓异质文化,但在原则上并不拒拆与任何文化的融会。法相唯识宗曾因坚持印度本寂思想而未能流行中国,然而本世纪以来又有复兴,学术界日益认识到唯识论严谨思维的价值。基督信仰,唯其具有异质文化的特色,方有激励催化中国本土文化的作用。中国文化以其非神圣目的论世界观曾疏离基督信仰,而中国世界观又隐涵作为方法的文化,趋向于各种文化的融会,并于现代显示出对异质文化的需求,而此时西方的基督信仰已一落千丈。
基督信仰在西方不仅早已由普世的社会体制降而为多元价值中的个人抉择,而且在上帝已死和科技至上的氛围中,亦早已退居少数地位。此时的中国社会却由于长期以来对传统的毁坏而呈现价值的空虚,甚至有人希冀在中国出现类如韦伯所理想化的那种以加尔文教事奉上帝的工作精神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实际上,韦氏所理想化的那个时代正是西方基督信仰世俗化的那个时代:如果事奉上帝成为一切行业的日常工作,亦即无异于取消普遍宗教意义的事奉上帝。此必以曾经基督化的社会历史为前提。故此种历史机缘不可能在中国重现。中国的历史从来便是以非神圣目的论世界观为基础的人文传统。目前的价值空虚,既以市场、法制、科技的现代社会为指归,故不可能指向传统的复兴,或皈依外国的历史,而只能指向本国传统的新生。在这新生途路中,对异质文化的需求,亦仅能通过个人的抉择,而非社会整体的抉择,在历史的演化中渗入中国的文化传统,如佛教的中国化过程所显示。在现代社会中,真正具有普世社会体制的资格者,唯有市场、法制与科技。一切宗教信仰,或超越法律的价值,皆属个人抉择。故基督信仰,或任何其他超越性的信仰,其在现代中国的少数地位,实已历史地预设。契入融会云云,亦是融为多元文化之一元。这便是基督信仰与中土文化遭遇千五百年后所处的一种奇异关系。
标签:基督教论文; 目的论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宇宙结构论文; 文化论文; 上帝已死论文; 读书论文; 国学论文; 心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