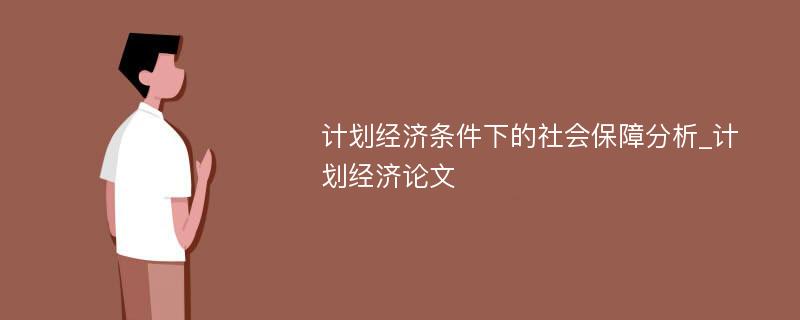
计划经济下的社会保护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计划经济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每当提到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国学者多半把注意力投向重构国有企业职工的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因此,也仅仅是从这个角度回顾现存制度的产生和运行弊病,且以发达国家相应的保障项目的营运为对照,以其它发展中国家保障计划的改革为榜样,来重新设计中国城市社会保障计划。不过,计划经济下保障制度的建立,除了保护生产和稳定社会的目标之外,还有更为广阔的经济理论、意识形态和发展战略选择等背景。忽略这些背景及与之相关的保障制度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就很可能在革除现存制度弊病的同时丢掉它包含的优越之处。进一步讲,在乡村人口依然占大多数的中国,更需要从发展的眼光和城乡社会整合的角度讨论社会保障问题。因此,探讨今日变革之路,有必要回顾以往的思想理论和制度实践轨迹。本文拟通过对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比较,论述后一类国家特别是中国社会保护体系的形成及历史作用,并对其在经济转型前的运作特点及存在的隐患加以说明。最后,还将对中国经济改革中的社会安全网的构建提出一些设想。
一、起点的区别
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可以简要概括为如下过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使国民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加,大规模的流浪人口混杂着工业社会的贫困与剧增的犯罪现象滚滚而来。被卷入工业化进程的人们尤其是雇佣工人对改善生活状况、保障经济安全的强烈要求,或通过同业组织的自助活动和工会出面的劳资谈判,或通过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活动表达出来。对此,统治阶级不得不做出反应。被视为现代工业社会保障制度经典之作的英国济贫法和德国社会保险法,便是这两个国家的政府在本国的工业化初始时期,面对生产方式变革的内在要求和民众的反抗而先后出台的对策。这一点,一位当代美国经济学家就曾一语道破:历史上,左派的部分先见总是被右派保守主义者拿来使用,并借此阻止左派上台。俾斯麦、丘吉尔和罗斯福实行社会福利政策是以保护中产阶级的方式来挽救而不是破坏资本主义(瑟罗,1996)。
如果说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是工业化的一个结果的话,苏联、东欧和中国、越南、朝鲜、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保障制度,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工业化的一个起点、前提或组成部分。工人阶级政党在这些国家取得政权,多半是在世界大战结束之际。人民向往和平、安定、富足,执政党需要巩固政权、稳定社会,建立社会保障无疑是争取民众支持、把握社会控制权的有效手段。进一步讲,这也是社会主义理想的一种实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和《哥达纲领批判》中曾设想,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在对个人消费品分配前必须做出一系列扣除,其中包括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以及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就制订了保险提纲,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便将这些设想迅速付诸实践(丁之锁,1994)。苏联的保障模式继而又为后起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仿效。因此,所有这些国家保障项目的设计、权利和义务的规定、管理原则和机构的确立等等,都更多地源于已有的理论设想,而不是取决于当时存在的生产方式。故而新的社会保障制度虽然在建立之初即发挥了保护生产和稳定社会的功能,但是从诞生之日起就留有重大隐患。那些隐患积蓄日久,最终使得整个保障制度在运行数十年后难以为继。这在建立社会主义政权之后才开始推进工业化的国家里都可以找到例证,中国即是如此。
二、权利和义务的安排
社会主义国家的保障制度最明显的隐患在于,国家与个人的责任关系不平衡。除了南斯拉夫、波兰、民主德国、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保障费用全部由国家(或国有企业)承担,个人虽无缴费的义务,却有享受保障的权利(Voirin,1994)。这看起来似乎对双方都有利:个人可以尽管享受“免费午餐”而不必挂虑衣食住行的任何风险,国家则能够一切按计划办事而无需为建立和维护社会契约配置资源。可是这种一切听凭国家安排的做法,既可能在免除个人义务的同时剥夺个人选择的自由,又可能造成个人对国家的过分依赖甚至依附。此外,这种制度安排隐含的一个前提就是国家计划无失误、经济无波动、财政无危机。然而只消引入人口增长过快、老龄化以及经济增长相对迟缓等变量,国家曾经承诺的一切可能就靠不住了,保障制度本身也许反而会成为国民生活中的一个不确定因素。
与上述责任关系相联系,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和管理,都由政府一手操作,实行现收现付制。它不仅与每一个具体的受保人无关,而且也缺少必要的社会监督。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几近于政府机构的延长部分,承担着相当数量的政府职能。加之企业无权自主经营,一切由国家计划控制,社会保险金一般按企业工资总额的一定比率而不是根据每一个就业者的工资额抽取。这种筹资方式固然简便易行,可是它没有提供单个受保人的信息,使得保障机构不可能建立相应的个人帐户,从而也不可能根据与特定个人相关的投保期限确认享权资格及待遇水平,其结果显然是在社会保险领域引入了一个“大锅饭”制度。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个人不关心也无从关心保险金的使用和管理,更难以预期自己究竟可以从中得到何种待遇,因为那取决于个人的就业年头和政府的决策而不是其它。如此看来,计划经济下那些称为保险项目的安全措施,例如工伤、养老和医疗保险,实质上少有保险的色彩而更多地属于国家保障的范畴。在这些领域里,保险的基本操作规则与商业保险机构一起被摒除了,留下的只是国家的垄断权利。
假设在同一领域里(例如养老项目)有商业保险存在,人们至少可以看到,单个受保人的供款义务、享权资格及待遇在投保之日即通过合同明晰规定,政府则对保险公司的运作实施监督,以确保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实现。如果在社会养老保险的财务安排中设有个人帐户,那么即使退休金的支付额不与供款额和投资利息挂钩,单个受保人的资格和待遇也不难确定,更何况与收入挂钩的补充养老金的积累和发放尤其需要个人账户作为依据。进一步讲,在不设个人账户的情形下,倘若将社会监督机制引入保险金管理,受保人的权利一般还不至于因为就业岗位转换、工作地点更动或社会经济环境变化而变得模糊不清。例如波兰,自1960年开始,在中央和地方分别设立了由工人、退休人员和政府三方代表组成的监委会,一方面监督资金管理,另一方面对保险诉讼事件负责。与社会保险有关的各方因此有可能相互制衡和监督,到经济转型之时,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并不难重新划分(Voirin,1994)。以此为对照来看中国的国有部门,情况就远非像在波兰那样具有透明性。企业一旦破产,工人的保险权利就成了一笔糊涂账。
三、保障项目的误用
计划经济时期社会保障制度的另一个隐患,是政府对保障项目的误用。社会保障的功能本是规避风险、防止贫困,那就意味着需要设计一些项目用以维持一般国民最低限度的生活需求,如社会保险和社会服务;还有些项目则作为干预贫困的手段,例如社会救济和社会服务。前者的保险对象未必贫困,后者的目标人群则必定是最需要援助的贫困人口。然而计划经济下的保障项目设计,则使项目功能远远超出了上述范围。政府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将收入分配混同于再分配,将实物收入分配混同于社会服务供给,以至于使保障项目成为推行收入均等化和控制个人消费的工具。
首先,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权建立之初都承诺保障就业而没有设计失业保险或救助项目。这样做的理论依据出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济学说。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考察和对资本积累的理论分析,指出了资本积累和失业现象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他认为,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引起资本技术构成提高,使得可变资本相对减少,其现象即为机器排挤工人,形成相对过剩人口或失业人口。这一产业后备军的存在形成对在业工人的压力,从而使后者或过度劳动或不得不接受低于劳动力价值的工资。因此,资本积累的必然产物就是失业和贫困。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消灭私有制(马克思,1867)。由此不难理解,当社会主义国家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建立起来的时候,其决策层会以为在剥夺私人资本的同时就必将消除失业和贫困。进一步讲,新政权的领导人多有革命斗争的经验而少有对现实经济运行过程的理解。他们所制订的社会经济政策,一方面基于自己信奉的理论,另一方面取决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在这一背景下,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就业保障在当时会成为一种顺理成章的制度选择。
其次,虽然这个承诺并未形成任何一个具体的保障项目,但是却在就业政策实施过程中表现出来:劳动者由政府安排工作,而且一旦进入国有部门,无论劳动态度好坏、能力强弱,只要不犯罪,就不会被解雇,并有权享有“从摇篮到坟墓”的一揽子保障,即工伤、疾病、孕产、养老、死亡等多种项目构成的“福利包”(参见表1)。 尽管某些工业化先于社会主义政权建立的国家早已设立了其中的某些项目,例如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这些国家几乎与首创社会保险制度的德国在同一期间颁布了工伤保险或疾病保险法。而由政府全面提供上述福利包,并将其与就业保障连续在一起,则是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以后的事。由此而埋下的隐患恰恰来自就业保障的缺失,这在90年代的现实经济中得到了完全的证明。无论是出于劳动力绝对过剩的缘故,还是由于国际竞争压力下不得不关闭低效企业以调整经济结构的原因,90年代大量公开失业人口的出现,使那些做出过就业保障承诺的政府措手不及、尴尬不已。即使是仓促设立失业保险或救助项目来应急,也难以在短期内消除失业和贫困酝酿着的社会危机,因为多数习惯于国家保护的失业者对所遭受的双重打击并无心理准备:他们既丢掉了工作岗位,又部分或全部失去了那些与就业相联系的其它保障。
表1. 中欧、东欧转型国家和中国主要社会保障项目的建立时期
(以首次颁布法令的年份为准)
国家
养老、残疾 健康、生育 工伤保险 失业保险 家庭津贴
和死亡保险 保险
阿尔巴尼亚 1947 1947 1947 1991 1992
白俄罗斯1956 1956 1964 1991 1992
保加利亚1924 1918 1924 1991 1942
捷克1906 1888 1887 1991 1945
爱沙尼亚1924 1924 1924 1991 1922
匈牙利 1928 1891 1907 1957 1938
拉脱维亚1922 1924 1927 1991 1990
立陶宛 1925 1925 1991 1919 1991
摩尔多瓦1956
—— 1992 1944
波兰1927 1920 1884 1924 1947
罗马尼亚1912 1912 1912 1991 1944
俄罗斯 1922 1912 1912 1921 1944
斯洛伐克1906 1888 1887 1991 1945
斯洛文尼亚 1922 1922 1922 1927 1949
乌克兰 1991
——
— 1949
中国1951 1951 1951 1986 1952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Association (1994),Restructuring Social Securit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pp.197-254,Geneva.
冯兰瑞等:《中国社会保障制度重构》,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7—58、69—71、125—127页。
再其次,政府不仅许诺对劳动者的生、老、病、死都提供保障,而且还把处于正常状态下的劳动者的一些生活必需品消费纳入保障项目,通过行政手段进行分配。这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住房。国有部门劳动者的住房皆由其就业所在企业和机构免费提供,个人只需支付含有大量补贴的房租,因为劳动者的工资被设定在仅足以支付除住房之外的购买其它基本生活消费品和享受基本服务所需的水平上。虽说是住房保障项目在非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也不鲜见,例如英国的房屋补贴、德国的“社会住房”(sozialer wohnungsbau)和香港的廉租公屋计划等等,但这些项目只是对市场的补充,只是对低收入人群的社会支持,与社会主义国家以公房分配排除市场的做法绝无共同之处。
其一,市场经济下的住房计划显然是收入转移或曰收入再分配的一种方式,由政府出面,通过向高收入人群征税,对低收入者实行住房补贴,以保障弱势人群的基本生存需要。计划经济下的住房分配实质上是收入分配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个人收入中本应用于住房消费的部分没有发放给劳动者,而是由政府或企业集中起来,以实物形式分配给他们。但分配原则既非政府所提倡的按劳分配,亦非理论上的共产主义按需分配,而是战时的供给制、新政权下的等级制以及各类当事人之间的谈判、游说、争夺等因素夹杂在一起的混合物。它并不完全向低收入人群倾斜,因为住房按级别或职位高低分配;它也不特别垂青劳动贡献大的人群,因为劳动贡献并不是分配住房的决定因素。它还要受到诸多其它条件的限制,如就业者所在单位的资源情况,分配过程中长官意志的干预等等。
其二,在前一种情形下,有住房市场价格参照,有收入调查前提下对享权人群资格的限定,低收入人群对附有补贴的住房需求,也会自动受个人收入水平和房价、房租水平的遏制(瑟罗,1998)。而在后一种情形,无偿分配创造了对住房的无限需求,其限制仅来自供给短缺以及短缺条件下的行政操作规则。结果,住房对于所有的人似乎永远都是短缺的。
其三,市场经济下的住房保障项目是由政府操办的一种公共援助,计划经济下的住房分配则成了企业的社会负担。前者与劳动力流动无关,后者则导致劳动者对企业的依附,形成劳动力流动的障碍。
在中国,除了住房以外,国有部门的从业人员还能够得到上下班交通费、书报费、洗理费、北方职工的冬季宿舍取暖费等30多种现金补贴(冯兰瑞等,1997)。这些项目显然应成为工资的构成因素,而无需以补贴的形式平均分配。值得一提的是,大中型国有企业还办有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和医院、疗养所等,为本企业职工及其亲属提供免费或附有价格补贴的服务。然而,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服务属于社会服务的范畴,例如保健、预防、康复、儿童福利和照料等等(ILO,1984)。 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除了根据法律规定为雇员交纳社会保险费外,也或多或少地为他们提供各种各样可以归纳为职业福利或机构福利的津贴或服务(周弘,1998),这种做法有着明确的企业目标,即培养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并吸引高质量的劳动者,以便加强企业的竞争力。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在计划经济下提供给员工的补贴和服务,却并非出于竞争的需要,而是部分地作为平均分配的附加货币工资,部分地作为实物或服务形式平均分配给员工的收益。
上述以收入再分配取代部分收入分配的制度显然既缺少社会公平,又有损于经济效率。但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和中国的政府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制度安排呢?流行的解释是用“低工资、高就业、高福利”之间的政策关系来对诸多原因加以概括:政府为了实现对就业保障的承诺,在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便采取一个人的工作分给几个人干的做法,实行低工资政策;由于低工资不能满足职工的基本生活需求,就设置各种补贴和集体福利来改善他们的生活(冯兰瑞等,1997)。可是这些解释引起更多的疑问:如果说在中国这样劳动力供给过剩的人口大国,“高就业”和“低工资”还有必然联系的话,苏联却曾一度因人力短缺而不得不采取奖励多子女母亲的措施来刺激生育,为什么也推行低工资政策呢?再者,既然明知工资加上补贴和集体福利才能满足职工的基本生活需求,为什么不干脆把它们加算在一起直接作为工资发放给个人呢?若想回答这些问题,显然需要简单地回顾一下那些工资和福利政策由以产生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
第一,“低工资—高福利”所隐含的政策意图,在于政府尽可能地把个人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压低到仅能维持生存的水平,以便增大可供统一支配的收入部分。其中,统一分配的福利待遇,即为政府直接分配的个人消费品和服务。这样做的思想理论背景,是社会主义政权创始人对商品生产和交易的排斥。依据马克思对未来社会资源配置的设想,列宁曾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尝试由国家直接调节生产与分配,从而以最迅速、最有计划、最节省的方式分配一切必需品。可是这种制度试验不出三年(1918—1921)就遭到失败,因此才转向新经济政策,在经济调节中引入商品、货币和市场的力量。然而新经济政策也只是作为权宜之计,以回应大工业尚未得到完全恢复和建立、千百万小农和私有经济依然存在现实(胡家勇,1997)。斯大林到1951年也只是承认把个人消费品纳入商品流通的必要性,但仍然强调,要一步一步地缩小商品流通而扩大产品交换的范围。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把产品交换与全民所有制相联系,将商品生产和流通视为与共产主义理想决不相容的东西。这可以从他有关农产品剩余的论述中得到注解:为了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必须将集体农庄的剩余产品从商品流通系统中排除出去,把它们纳入国家工业和集体农庄之间的产品交换系统(斯大林,1951)。
第二,“低工资—高福利”作为个人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工具,反映的是对收入均等化的意识形态诉求。在计划经济时代,工资是依据按劳分配原则分等级制订的。不同等级之间虽然差距不大,不足以对劳动者产生激励,但毕竟高低有别,那么从理论上讲,政府对所掌握的福利品平均分配即可促进收入的均等化。问题在于,这一部分产品和服务既有平均分配的部分,例如交通、洗理和书报补贴;也有按需求分配的部分,即具有社会保障功能的部分,例如困难补助和医疗服务;还有根据个人身分等级供给的部分,例如住房待遇。后者产生的巨大不平等恰恰在统计上难以反映出来,在国际比较中也常常被忽略,从而被工资和平均分配的福利部分所呈现出的均等化所掩盖。事实上这样的分配既缺平等也少效率,而且还与制度设计者的初衷相悖。
第三,实施“低工资—高福利”政策的直接经济原因,是政府力图加速积累和实现工业化的需要。为了维持较高的积累率,政府在经济转型前一直把个人消费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上。在农村,通过农产品低价收购的办法把剩余产品转移到政府手中,使生活水平低于城市的农业人口长期得不到提高收入的机会;在城市,则以低工资、高福利和生活必需品价格补贴制度维持个人收入低水平,从而尽可能增加企业上交财政的利润。这里,所谓高福利也只是相对于工人基本的工资和农民极低的收入而言。若从个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来看,这些福利待遇水平并不高,因为它主要还是用于生存领域。以中国的国有企业为例,1978年政府对职工的各项补贴相当于工资的82%。这其中,劳动保险和医疗费占22%,食品补贴高达34%,房租、取暖、探亲和交通补贴约占19.3%,余者为其它集体福利。如此看来,“低工资—高福利”政策不过是为政府集中配置资源和决定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提供了方便。事实上,以苏联和中国为典型的国家工业化,都是以25%—30%的积累率为支撑的,远远高出市场经济国家的一般水平(罗德明,1995)。
在经济欠发达国家迅速实现工业化,无疑需要抑制个人消费的过快增长。以计划经济的手段达到这一目标,在当时的国际政治和国内社会经济条件下不失为一种理性的选择。然而,一旦把计划经济固定为长期实行的制度,就难免导致政府权利排挤个人权利,以政府管制取代市场作用。这其中包含的危险便是对国家力量的迷信,具体来说,就是对政府决策科学性的盲目信赖。实际上,由于决策失误造成浪费和损失的情况普遍存在。工业化实现后,社会主义国家的个人消费依然受到极限积累的挤压,无效投资也日积月累不断增加,逐渐把国家财政及其所支持的社会保障项目一起拖到危机的边缘。
四、保障项目的覆盖
就国家提供的养老、医疗和伤残保障等项目而言,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皆为全民覆盖(Meierkord and Sailer,1994), 在中国和越南,则主要覆盖城市公有部门的从业人员和职业军人(Lu Aiguo ,1996;Jansen,1997)。 中国之所以在这一点上采取了不同于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首先是因为工业化程度低,农业人口规模巨大,国家财力薄弱,难以对农业劳动力提供与工业部门从业人员同等的保障待遇。即使以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状态与其它对照国仍处于经济低谷的状态作比较,中国在人均资源和收入水平方面的劣势也还是显而易见的(参见表2)。尤其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大约仅相当于俄罗斯的1/5,还不到捷克的1/6和匈牙利的1/7。对照国的总就业人口中,农业人口的份额大约都在11%—24%之间。这个比率在中国则达58%,经济转型前还要高一些,约为80%。
表2. 中国和一些中、东欧转型国家发展指标选录
国 家 人口(万人)面积人均国内生产
1995年* (万平方公里)总值(1994
年美元)*
中国
119 090960
530
俄罗斯 14 8301 707.5 2 650
波兰 3 850
31.3 2 410
捷克 1 0307.9 3 200
斯洛伐克
5304.9 2 250
罗马尼亚 2 270
23.8 1 270
保加利亚
840
11.1 1 250
匈牙利
1 0309.3 3 840
立陶宛 3706.5 1 350
乌克兰
5 190
60.4 1 910
爱沙尼亚
1504.5 2 820
国 家 平均预期寿命 农业就业人 社会保障支出
(岁)1994年* 数/总就业 /国民生产总值
人数(%) (%)1987年***
年美元)*
中国 6958.0* 2.8
俄罗斯64
14.0**10.8
波兰 72
15.0**10.3
捷克 73
11.0**20.9
斯洛伐克 72
12.0**20.9
罗马尼亚 70
24.0** 9.6
保加利亚 71
13.0**15.1
匈牙利70
15.0** 17.3**
立陶宛69
18.0** —
乌克兰68
20.0**17.8
爱沙尼亚 70
14.0**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1996 ):《从计划到市场(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90—191页。
** UNDP (1997)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pp.209,212,OxfordUniversity Press,New York,Oxford.
*** ILO(1996) The cost of social security,Fourteenthinternational inquiry,1987—1989,Comparative Tables,pp.73,75,Geneva.
表中有关俄罗斯社会保障支出的份额借用的是苏联1987年全国统计数字。
此外,多数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机械化程度较高,农业劳动者与工业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相去不远,因而也需要相近的防护措施以应对工作和生活中的风险,例如伤残和疾病的袭击。相形之下,计划经济下的中国农业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进展缓慢,乡村劳动者面临的风险,依然是传统农耕社会所具有的风险,故而在这一点上中国政府没有仿效苏联模式,而是做出了一系列与当时乡村实际情况相适应的制度安排。
第一,通过土地改革和随之而来的农业集体化,使农民先是个人拥有土地,继而实行对土地的集体所有。在这两种形式下其实都保持了耕者有其田的状态,从而将土地作为农民及其家庭的生存保障。这其中,集体化为将农业纳入计划经济体系奠定了制度基础。一方面,政府借助于统购统销政策低价收取绝大部分剩余农产品,只给农民留下大致足以裹腹的口粮和少量用于集体储备以及公共积累和公益事业的农产品剩余;另一方面,又采取粮食返销的方式,售予缺粮地区的农民和专事蔬菜和畜牧生产的集体组织低价粮。此外,还对灾民和特困户提供亟需的救济食品和衣物。这样的制度安排,只是维持着农民及其家庭低水平的食品保障,使他们获得生存水平上的经济安全。
第二,在人民公社时代,集体生产组织对既无劳动能力又无经济来源的老、弱、孤、残成员实行“五保”制度,即保吃、保穿、保住、保医和保葬(孤儿保教)。虽然保障水平也很低,但是不致于使这一弱势人群被排除于正常的社会生活之外。
第三,建立农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及合作医疗制度,使农村人口得以用较低的花费获得卫生防疫和流行病防治方面的服务。尽管合作医疗并未像苏联、捷克、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等国的医疗保障制度那样,使集体农庄成员获得免费医疗和工伤、病假、孕产假补贴(Savy,1972),但毕竟有效地减少了农村人口因小病不治而丧失健康和劳动能力的风险。在60年代和70年代,即合作医疗制度发展的高峰期,全国80%左右的村庄都在这一制度的覆盖之下(Hu Shanlian,1997)。
第四,农业人口中的老龄人群,皆有从生产队分得口粮的权利,但对老年人的照料则依赖其家庭。这可以称得上是一种集体生产组织和家庭相结合的养老形式。虽然它从未得到过任何正规的保障制度名称,但实际上起到了在生存水平上实行养老保障的作用。
如此看来,尽管计划经济下的中国社会安全网赋予工农业劳动者乃至城乡居民以程度大不相等、支付水平截然不同的社会保护,但是它毕竟由于政府的支持而使全国人民都获得了生存意义上的经济安全。这就使中国在社会保护方面的成就高于其它同等水平的低收入国家,因而被视为欠发达国家推行公共支持式社会发展战略的一个典范(Dreezeand Sen,1989)。
五、小结
社会保障项目的诞生,在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是由工人阶级的斗争助产的;在社会主义国家则直接出自执政党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正是由于这美好理想的导引,此类国家的决策层并未把社会保障项目仅仅作为保护生产、预防贫困和稳定社会的手段,而是赋予它更多的使命,即消除失业、实现收入均等化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故而在制度设计中将收入分配与再分配混杂在同一个过程之中,或者说明将目标截然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与收入分配制度交错安插在一起,如同拼装了一幅阴阳互补的太极图。且不论城乡差别以及官员与百姓的差别,仅就城市居民内部和乡村居民内部而言,收入和保障待遇的分配称得上是均匀的。这在东西方两大阵营直接对峙的时代曾是不争的事实,而且由此还或多或少地引发出双方的福利竞赛。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卷入收入再分配的范围逐渐扩大,使福利国家模式在60年代达到鼎盛时期。可以说,竞赛的积极作用在于世界范围内社会保障项目的推广和保障水平的提高。
社会保障项目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计划经济下推行工业化的一个前提,或工业化战略的组成部分。它与就业、工资和生活必需品补贴制度一起,成为政府压抑个人消费、实行极限积累和加速工业化的工具。出于这个原因,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曾经承担保障项目筹资和管理的全部责任,而免除受保人直接缴款或纳税的义务,同时也剥夺了后者进行个人选择的自由和监督保障项目运营的权利。这种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称以及相关的财务安排,显然也是由计划经济的制度框架所决定的。
当然,即使是在相似的制度框架下确立的同一名称的项目,其覆盖面和支付水平、筹资规则和管理方式等等,也无不受特定国家人文、地理、经济、政治、文化、伦理道德、法律和行政条件的制约,不同国家的项目设计因而也有可能大相径庭。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凭借优越的人均资源条件、较高的工业化水平和农业机械化程度,建立了以普及化为特征的国家保障体系。处于城乡二元经济状态的中国,则设计了具有二元特征的多种保障项目。尽管这些项目处处显露出城市偏好和国有经济偏向,以至于城乡人口相对照,前者保障过度而后者保障不足,但是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它毕竟为国民提供了生存意义上的经济安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乡村通过对生产和分配制度的干预将集体保障和家庭保障相结合,并辅之以对基层社会服务的实质性改善,使得中国在同等水平的低收入国家中走在了社会发展的前列。
然而,政府对权利和义务的垄断以及对保障项目的误用,使整个经济缺乏激励、缺少效率,当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和经济结构不得不进行调整的时候,保障项目的运行就由于缺少足够强大的经济基础支撑而难以为继。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折的过程中,苏联和东欧国家都程度不等地经历了经济急剧下滑、通货膨胀和失业压力迅速加大的困难局面,此时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陷于瘫痪,新创立的社会保险计划运转不灵。在改革中设立的保险项目以缴费或储蓄为前提,可是大量突然陷入低收入或贫困阶层的居民却无力缴费,不少经营困难的企业也无能供款。因此,被称之为“社会支持”的救济和补贴项目成为转型过程中应急的保障手段。在此期间,社会保护措施负有极其沉重的政治使命,即维持最低水平的经济安全和最低限度的社会公平从而保持社会的稳定。
中国虽然自改革以来一直保持着令人瞩目的高速经济增长,可是所承受的巨大的人口压力以及失业和就业不足的压力一点儿也不亚于其它发展中国家。更有甚者,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比别的国家还快一些,其它诸如通货膨胀之类的经济难题也不比苏联和东欧国家少。然而,中国社会保护体系既有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弱势,又包含其它转型国家曾经有过的弊病。因此,对应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社会安全网构建,存在着双重的难题,也面临着社会整合的机遇。这一背景下的制度选择必然需要从多种角度考虑:第一,在经济全球化的态势下中国的社会安全网必须保留灵活性,做到既能够保护社会,又能够适应国内外市场竞争的需要。为此,有必要在设计改革方案时,把政府的作用严格地限制在基本社会保险的领域里,同时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鼓励和调动企业、社区、村落、家庭、个人和其它社会机构的作用。第二,社会保障项目的设计应包含有利于劳动力流动和促进二元经济整合的机制。例如,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乡村人口,都可以依据就业身分划线(雇员、雇主和自雇者),以便确定其权利和义务。第三,社会保障行政权力的安排,必须有利于消除部门垄断,缩小地区差距。第四,转型中的社会保护只能以应急措施与制度建设并进的方式实现,即将扶贫项目、救济措施、再就业工程的实施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相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