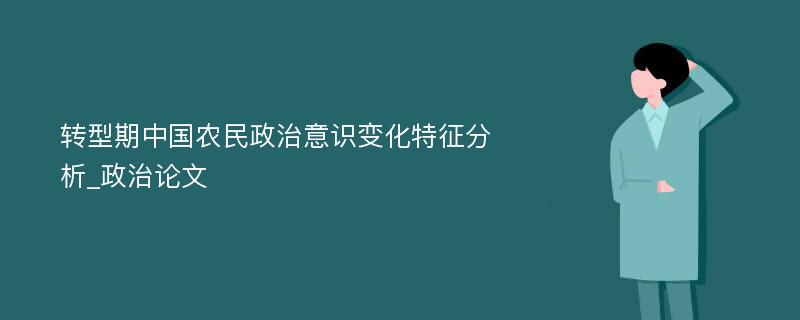
转型期我国农民政治意识变迁的特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特征论文,意识论文,农民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27(2010)02-0089-05
政治意识是思维主体把自己当作政治主体纳入到自己意识之中时所呈现出的一种意识状态,政治意识是“群体意识形态”①的核心内容,而群体意识形态则是指共同体内部的行动者所共享的知识的总称,它属于广义的意识形态。②在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农村的市场化改革引致了农村社会的诸多变革,从而也引致了农民政治意识的变迁。把握这些特点对于目前在农村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么,转型时期我国农民的政治意识所发生的变迁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通过多方面的研究和分析发现,至少体现出如下三大特点来:一是在主体的呈现上由依附性向自主性过渡;二是在自我的表达上由被动性向主动性过渡;三是在利益的追求上由单一性向多样性过渡。本文试图对此略抒管见。
一、由依附性主体向自主性主体过渡
几千年以来,传统中国的专制主义及由此所型构的各种地方性知识完全冰释了农民“个人同一性”③。在此背景下,农民的需要在农民的自我意识中成了无所谓的随意之笔,农民基本上变成为一种失去主体资格的、只能随着专制政治起舞的玩偶,于是,农民成为缺少“主体意识”的存在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在统治集团所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中,统治集团的精神生产总是为了统治集团的专制服务的,虽然有些精神生产者在需要利用人民的力量之时会发出“民贵君轻”的呼喊,但是这种呼喊与专制主义的“超声波”相比显然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它也不能从根本上产生制约专制帝王的专制行为的自觉。加之,各种地方性知识包括宗教文化的存在实质上也强化着专制主义的超强制。因此,专制环境决定了农民的“无我”状况。陈独秀曾对中国人“无我”的状况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以一物附属一物,或以一物附属一人而为其所有;其物为无意识者也。若有意识之人间,各有其意识。斯各有其独立自主之权。若以一人而附属一人,即丧其自由自尊之人格……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而吾国自古相传之道德政治胥反乎是。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已属人之奴隶道德也。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奴隶道德者即丧失此中心,一切操行悉非义由己起,附属他人以为功过者也。”④在笔者看来,陈独秀的看法的确深刻透辟,抓住了专制下人的“无我”性以及这种“无我”的人性所制造的“无我”社会。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专制制度从根本上被颠覆,中国农民阶级被确立为新社会的主人,而且,当农村实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以后,农民阶级的主人地位不仅在身份上、而且在事实上得到一定程度的确认。但是,由于专制文化的余毒没能在短时期内消除,而且这种文化所挟带的思想残余在农民阶级中还有相当的市场,因此,农民意识仍然属于被改造或者需要进一步“解放”的意识。这样,农民阶级的“主人”地位只是一种政治解放的确证,还不具有整体解放意义的内涵。农民的“主人”地位的确立还不是农民主体地位确立的标志,因为从“主人”到主体的建构必须遵循历史过程发生学逻辑,服从解放事件呈现基本原则:解放事件呈现由制度逻辑向意识逻辑的演绎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农民“主人”地位的确认只能被理解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实施或者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只能被理解为一种认识论在发生断裂后的重新创生,而不可能被理解为一种意识逻辑或者认识论逻辑建构的完成,由于制度逻辑的建构往往是在一种制度颠覆另一种制度或制度转换中实现,而意识逻辑的变换是在意识发生根本交替中实现,因此意识逻辑的变换并不与制度逻辑的转换同步。⑤新政权建立之后所呈现的有关农民的各种事象正好证明了这种演绎逻辑:农民把所获得的政治解放全都归功于领袖和执政党成为当时农村乃至全国的惯像。这种状况说明农民的主体性并没有从其“主人”地位的确立中一同确立,因此,农民还没有真正意识到自身的主体地位,农民仍然沉淀在对领袖和执政党的情感依附之中。农民对领袖和执政党的“感恩情结”就是这种情感依附状况的最好诠释。感恩,本是一种经验性的情感,但在一种特殊的政治氛围里,它却演变成一种人格不平等的机械关联。正是在这种人格不平等的机械关联中,“主人”因缺乏主体意识而失去立意的根基。农民不能代表自己,仍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最初二十多年的景象。正如马克思所说:农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⑥
从认识论逻辑的角度看,只有当农民阶级把自身当作主体而纳入到自身的意识之中并在自身的意识之中不断深化这种意识的时候,农民阶级才能真正实现了从“主人”到主体的建构。而实现这种建构是在以后的社会发展中进行的。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国家在农村推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体制的转型大大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获得土地经营权的农民对自有土地经营的关心便超越了他们对任何一种他者的操持。在此背景下,利益主义便大行其道。利益主义在农村的盛行从实质上颠覆了农村经济体制转型之前农民的感恩情结,也从根本上摧毁了专制主义时代所建立起来的各种与利益主义关联不大的地方性知识。正是在此背景下,农民的主体性开始在“自主意识”中出场:农民可以对自己的经营有一定的自主权;农民可以对自己的收获物有一定的处置权;农民可以对自己的劳动时间有一定的支配权;农民可以对自己的行动有一定的控制权……,总之,农民有了一定的自主思维空间。正是在这种思维空间里,农民开始真正把自己的行为作为一种自我的凭持来思索、来意识、来算计,而不再如传统社会中的农民总把“自我”放在他们的意识之外。而且,村民自治也激活了村庄里的政治幽灵,村庄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治争斗的实验场⑦。村民自治也在一定程度上催逼了农民自主性主体的出场。
在此背景下,农民正在由依附性主体向自主性主体过渡。
二、由被动性表达向主动性表达过渡
传统中国的专制主义不仅制造了农民自主性主体的缺失,还制造了农民的主动性表达自我的缺失。马克斯·韦伯认为,专制社会存在的前提是权威形态的建构并将权威神秘化,于是,韦伯将权威分为三种类型:神异性权威(charisma)、传统性权威(tradition)、官僚式权威(bureaucracy)。神异性权威是指神的力量成为人的一种规制;传统性权威是指某种制度性设置逐渐成为具有公信力的道德伦理约束;官僚式权威是指官僚等级被逐渐神秘化为一种制约现实人的异在。⑧由于种种权威对现实人的生活的规制容易在神秘化的语境里演化为一种奴役,因此民众也就会在这种奴役中把意识权利完全或大部分交付给专制、交付给神灵,于是在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普遍缺乏的语境下的专制主义就会变得更为神秘,同样语境下的神秘主义又会变得更为专制,专制的东西又会在神秘中被赋予权威性。这些正是专制统治者们所孜孜以求的。生活在这种语境里的民众也便会缺乏基本的判断力和辨别力。这样,他们的意识就不能成为一种有关他们与其周围世界的关联物,因为他们的意识与其外在世界之间的各种联系通道被堵塞或屏蔽。这样,他们就难以通过自己的意识来完成各种给定性所规定的任务。自我意识的缺乏必然导致精神的麻木。在精神普遍麻木的社会里,倘若只有专制主义的权杖是清醒的,而且它还履行着各种法力无边的功能,那么这种权杖就会把每一个显形的自我与深层的自我、现在的我与过去的我、自我与自我之外的世界集中在一种绝对的容器里,并将这些东西捣得粉碎,使生存在此间的生灵难以辨别它们的界限或探索它们的奥秘。连一个基本的“自我”都是模糊的,还能表达什么呢?因此,马丁认为,中国传统的民间仪式是一种神与人的交流模式。在这种交流模式里,人只有在获得了神灵“护佑”的时候,人对自身存在的感知才是踏实的。⑨这样一来,神灵就成为人的代言者。传统的中国农民一样生活在这种民间仪式里。仪式,虽然描述了一种事件,但是,它实际上是把过程当作事件来浓缩的。这样,民间仪式尽管不是经常性的生活,但它却是一种惯常性的折射。这种特殊语境决定了农民表达自我的方位:一般说来,农民是不能表达自我的,而是借着自身以外的力量来表达自我的。即使偶尔表达一下自我,也往往是残缺不全的。这样,农民的表达只能成为一种被动性的表达。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新生的政权对各种专制主义、神秘主义、神灵主义及其所代表的各种传统文化的解构,随着各种适应新时代的公共符号体系的建立,民众的个人心理认知体系也开始发生深刻的革命。在此语境里,农民的精神归属开始发生了根本性变迁。尤其是,在新政权下,农民的话语、农民的实践行为不再处于一种边缘化的地位,农民的身份具有一种“显学”意义。当然,由于中国农民阶级不是一种新生的阶级力量,它曾见证过几千年的专制主义、神秘主义、神灵主义及其所代表的各种传统文化,并深受其影响,因此,农民意识形态具有进步和落后的双重性。除此以外,传统农民还存在平均主义观念、保守主义思想等等,因此,改造农民意识形态就成为新生政权的重要任务之一。改造农民意识形态实际上是新生政权重新塑造农民和向农村输出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重新塑造农民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农民重新认识自我、表达自我的过程。新生政权通过向农村输送集体主义以改变传统农民的分散状态,从而从组织上和思想上保证了被改造后的农民意识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对接或者一致。应该承认,集体主义的确带给了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从根本上改造了农民阶级。然而,因为新生政权在向农村输出主流意识形态中采取了“超强制”方式,因此农民对自身的改造并没有实现预期。在此语境里,农民的个体自我与集体的边界是模糊不清的,个体化农民的利益与集体化的农民利益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画等号。在此背景下,农民虽然获得表达自我的机会和平台,但是因仍然找不到完整的自我而只能将这些机会白白浪费掉。
1978年以后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直接把利益主义送到农村。在此背景下,农民又回到了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自然经济”状态,自己对自己的安排,自己对市场的算计,使农村的一切潜规则都服从于利益最大化原则。在利益最大化原则的驱使下,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民不得不与国家、地方政府以及各种利益集团构成多种层次的利益博弈关系。出于生存本能和利益原则,农民不得不将“自我”从集体主义时期的模糊状态慢慢找回,或者重新认识“自我”与国家、集体或其他各种利益共同体之间的关联,划清“自我”与国家、集体或其他各种利益共同体之间的边界。当农民真正开始意识“自我”的时候,能够主动表达自我的农民也就要出场了。正如梅洛—庞蒂所言:“意识是宇宙的关联物,是拥有已绝对完成的所有认识的主体,而我们的实际认识则是已绝对完成的所有认识的初露。这是因为人们假定了仅在意向中为我们存在的东西已经在某处实现:一个绝对真实的、能协调所有现象的思想体系,一个能解释所有透视的几何图,一个所有主体都朝向的纯粹客体。为了摆脱狡猾的神灵的威胁,为了保证我们对真实的观念的拥有,应至少需要这个绝对的客体和这个神圣的主体。”⑩从二十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的村民自治为农民提供了展示自我、发现自我和表达自我的舞台。李连江和欧博文认为,“依政策抗争”是一些地方的“钉子户”、“刁民”在反对地方政府或利益集团实施“赢利型经济”时的一种自我保护措施,更是一种自我表达的有效形式。他们进一步认为,农民在被侵权的情况下,不断上访告状不再局限于经济利益,而且还涉及到农民自身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监督权和罢免权等方面的政治权利。(11)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开始由被动性表达向主动性表达过渡。
三、追求利益由单一性向多样性过渡
阿尔蒙德(G.Almond)曾经认为,传统中国的民众没有“自我取向”或“投入取向”(input orientation)及“参与取向”(participant orientation),主要原因在于传统中国的民众缺乏对自身利益的基本意识,这样,他们就不会以利益主体的身份去主动参与各种社会事务(12)。正如葛兰西所说的,在传统的东方,“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原始状态,尚未开化”(13)。而“市民社会”在黑格尔看来却“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14)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确认了人的实际需要和利己主义原则,由此,“市民社会”便构成了与国家的对立,从而就成为了解构普遍利益的虚假性的有力武器,“市民社会”通过确认特殊利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真正实现了人的“政治解放”。(15)在几千年传统中国的专制社会中,君权至上,皇帝就是专制国家的惟一代表,专制国家就属于皇帝所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这种说法的最好写照。在此背景下,广大民众不过是皇帝的子民而已,即使是为专制主义服务的士大夫们也只不过是专制皇帝的臣子。他们不可能建构出一个具有一定政治独立性的布尔乔亚集团(16)来制衡专制君主。因此,金耀基先生认为,“中国两千年来,即是一君主制,则政治的最高权力在君主,政治之主体亦在君主,亦即君主是主权之所寄。以此,中国的政治的权力是‘自上向下地’。”(17)马克斯·韦伯也把传统中国的政治格局形容为“家产官僚主义”(patrimonialism)(18)。在此背景下,传统中国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样一来,他们连自己都掌握不了,还有什么利益可言?
新中国成立后,新生政权打碎了一切旧的国家机器,把穷苦百姓从旧的“关系”下解放出来。农民阶级身份的变迁在我看来主要是一种政治解放的“所指”,因为,第一,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不再归属于专制君主;第二,新政权下的农民可以根据国家输出的相关制度规约组织集体并在集体中担当起领导责任,由此农民可以自己管理自己;第三,旧政权下越是处于社会底层、受剥削越重的人在新政权下越是受到尊重或器重,由此穷人可以扬眉吐气;第四,集体主义解构了传统中国的小农经济的桎梏,把原子化的农民组织起来,克服了原子化带给农村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农村惯像;第五,农村是集体利益的战场,代表普遍利益的国家对农村的输出主要是一种政治输出或者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输出。在国家“超强制”输出意识形态的背景下,代表国家的普遍利益与代表村庄的集体利益构成了“超级统一”;第六,新政权背景下,国家通过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向农村输出各种政治符号、政治事象,用“阶级斗争”来刺激每一个人的政治神经,甚至有时人为制造阶级对立和矛盾,并运用强大的专政机器对部分“分子”进行专政,这样,通过制造政治恐惧来根本改造村社并力图使村社出现泛政治化态势。在此情景下,农民个人被泛政治化了;第七,新政权为了更方便输出各种国家元素,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中国城乡之间建立起二元结构。在此结构下,全体公民被人为分割为两种不同种类,城市市民与农民便具有了截然不同的身份、规范、价值和角色,他们也便生活在截然不同的境遇中。由于“农民只拥有形式公民权利,而无实质公民权利,无法得到国家提供的福利与服务。农民集体福利制度安排的主要问题是缺乏相应经济基础,现代取向社会福利制度建基于传统农业生产基础上,农民集体福利的低水平、短期性、普遍性贫困和无法维持是可以预期的必然结果。”二元结构从根本上剥夺了“农民的公民权利与社会权利,其实质是制度性社会不平等和政策性不公平”(19)。在此语境里,由于农民阶级通过政治解放所获取的实际利益并没有经济基础作保障,因此,其实际解放并不没有达到规范性预期。这样,农民所获得的利益就只能是单一的或者稀疏的甚至是虚幻的。
由于改革开放所具有的发生学意义引致了农民的利益观的根本性变迁。在此背景下,农民的政治诉求不再是单一的、零碎的,而是多样的、复合的。这样,村庄逐渐成为政治利益争斗的舞台。在此背景下,村民对村社政治的认识由肤浅逐步走向深刻;村民对村社政治的参与由被动逐步走向主动;村民对村社政治的态度由消极逐步走向积极;村民对村社政治的认同由感性逐步走向理性。村社政治不仅深刻改变着普通村民,而且极大地改变着村庄里的一切。(20)在此基础上,村庄正在成为马克思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李江涛、郭正林等学者通过大量调查后得出结论说,市场经济大大刺激了发达地区的农民参与政治的热情,尤其在村级选举中,竞争更加激烈、拉票方式日益多样化。何包钢和郎友兴认为,发达地区的村落要比经济落后的村落村级选举激烈。欧博文认为,村民选举村干部不仅仅看村干部的经济能力,还看重村干部的品行。这就说明,村民不仅需要政治给他们带来的看得见的实惠,还需要通过一种正义带给他们的潜在利益。郭正林和白思鼎还注意到了这种现象,村民选举开始挑战农村党支部的传统权威。(21)李连江的研究还表明,村民通过选举村干部不仅希望他们能带动村民治富,还希望他们能帮助抵制各种“土政策”对村庄的侵害。由此,村民选举提高了村民的政治效能感,农民开始把政治参与理解为权利本身,并为捍卫这种权利而采取行动。(22)戴慕珍和罗丝高发现,农村私营企业主的参选兴趣很浓,村庄个体户的数量同竞选呈高度相关。在此背景下,倘若村级党支部对此视若无睹,那么它们就会很难从中获得好处。因此,农民的政治消费日益走向多样化。除此以外,农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能力也在村民自治中不断得到提高。他们不再被动地接受政府的安排和动员,而是在现有的组织和制度平台上,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民主热情和创造力,结合各自的具体实际,通过各种创新,主张和实现自己的民主权利。(23)农民还自发创造各种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并以此来丰富了村民自治的内容和满足农民自身日益增加的多样性利益需求(24)。
三个特点遵循着同一个发生学原则:国家主导农村变迁;履行着同一个历史学程式:折射共同的历史事实或现象;聚焦着同一种变迁意义:当利益主义和自身需要成为农民的基本原则的时候,村庄也就开始成为利益争斗的场所。利益主义的出场既催逼了农民自我意识的主体性出场,也制造了前所未有的“奥尔森困境”。在此语境下,如何顺利实现向村庄输出主流意识形态的战略与策略转型就成为国家不得不认真面对的问题。如果仍然沿用人民公社时期的“超强制”做法,那么很可能达不到理想预期,因为人民公社时期农民自我意识的主体性还没有出场。当农民自我意识的主体性出场之后,农民逐渐建构了属于自己的标准和尺度,从而也形成属于自身的判断力。这种判断力对于农民来说无疑会成为各种输入物的裁减尺度和评判标准。在此背景下,如果国家仅以经济利益诱导农民或者仅以某种政治宣示或精神鼓励激励农民,在我看来,效果恐怕都是有限的。只有明确经济利益、政治宣示和精神鼓励的合理边界并在此基础上把它们紧密结合在一起,并利用它们的合力来引致农民的实践行为,才有可能顺利实现各种输出的预期。
注释:
①[匈]捷尔吉·卢卡奇著、李鹏程编:《卢卡奇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61页。
②(20)牟成文:《中国农民意识形态的变迁》,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150-152页。
③[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
④《青年杂志》1916年正月号,第3页。
⑤牟成文:《关于目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我国农村建构的思考》,载于《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6期。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8页。
⑦何清莲:《农村基层社会地方恶势力的兴起》,收入刘青峰、关肖春编:《90年代中国农村状况:机会与困境》,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贺雪峰:《派性、选举与民主规则和民间化》,收入李连江等:《村委会选举观察》,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⑧Max Weber,1978,Economy and Society,California,pp.121-299; S.N.Eisenstadt,ed.,1968,Max Weber on Charisma and Institution building,Chicago,pp.i-Ivi.
⑨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72页。
⑩[法]莫里斯·梅洛—庞蒂著:《知觉现象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68页。
(11)欧博文、李连江:《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收入吴国光主编:《九七效应:香港、中国与太平洋》,香港太平洋世纪研究所出版社,1997年版。
(12)G.A.Almond & S.Verba,The Civic Culture.Boston:little,Brown & Co.1965,pp.11-26.
(13)安东尼奥·葛兰西著:《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4页。
(14)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09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5-195页。
(16)D.Bodde,"Authority and law in Ancient China." in Authority and law in the Ancient Orient,Supplement NO.17.1954,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pp.54.
(17)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
(18)R.Bendix.Max Weber:An Intellectual portrait.op,cit.,p.100.Passim.
(19)刘继同:《由集体福利到市场福利》,载于《中国农村观察》2002年第5期。
(21)郭正林:《国外学者视野中的村民选举与中国民主发展:研究综述》,载于《中国农村观察》2003年第5期。
(22)lilianjian 2001,"Elections and Popular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China Information,VOL.XV,No.2:1-19.
(23)徐增阳、杨翠萍:《村民自治的发展趋势》,载于《政治学研究》2006年第2期。
(24)徐勇:《村民自治的成长:行政放权与社会发育——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村民自治发展进程的反思》,载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