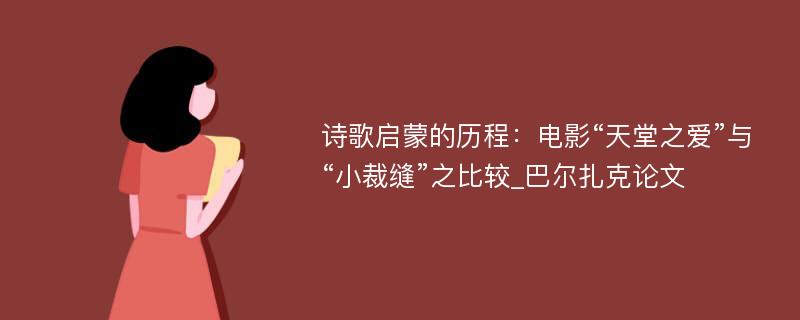
诗意启蒙的历程——电影《天上的恋人》和《小裁缝》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裁缝论文,诗意论文,历程论文,天上论文,恋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蒋钦民导演的《天上的恋人》和戴思杰导演的《小裁缝》(注:《天上的恋人》(荣获 第十五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导演:蒋钦民;主演:陶虹、董洁、刘烨 。《小裁缝》(香港第二十五届法国电影节开幕电影),导演:戴思杰;主演:周迅、陈 坤、刘烨。)这两部影片中都用唯美的风景画剪出了一个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他们用 各自的风格倡导诗意启蒙,去挖掘各个时期开启文化蒙昧的故事。两部影片中始终有一 批跳跃在过去、自然和青春之间的青年男女形象,在爱和诗意启蒙之中交织着年轻的冲 动和无畏的理想。本文从《天上的恋人》和《小裁缝》这两部电影所采用的表现手法、 布景道具、爱情故事和故事结局四个方面,分别以小标题逐日、乐土、醉泉和超度来论 述,两部电影都表现了主人公的诗意启蒙历程,导演通过电影的感染力,揭示了同是诗 意启蒙主题在不同年代的不同形式和风格,力求追寻其历史、文化和心理的渊源。
逐日
《天上的恋人》和《小裁缝》均是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前者发生在离我们并不久远 的年代,或许就是今天的普通乡村;后者发生在文革年代。无论二者的时代反差有多么 鲜明,但其中蒙昧与文化、乡村与城市、手工与机械的相互映衬,形成了纵横流动的诗 意启蒙的大背景。
在广西天峨县的壁立群峰中,《天上的恋人》散发着一股巨大的吸引力。从影片一开 始耀眼的红气球,我们便感染到它些许城市商业的气息。当家宽摸奖券中了一辆自行车 时,大家伙脸上羡慕和嫉妒的表情,足以让人领会他们对山外和城市的向往。可是这并 没有让漂亮的朱灵爱上他。相反,那位会医牛的兽医——张复宝,不仅有文雅的举止, 他还会吹小号呢。那让人迷恋的音乐,多么动听!家宽可不知道这些,他只知道学写两 个字儿——“朱灵”,然后把它放飞在红艳艳的热气球上。在这块蒙昧和文明并存的绿 洲上,音乐、文字和善良的人们开启了朱灵心中的一块净土。同样,对于《小裁缝》里 的小裁缝和她的乡亲们来说,一辈子生活在凤凰山里,没有杂念、没有冲突,那里有美 丽的只供女孩子洗澡的一线天温泉。姑娘们在闭塞的山区里长大,从来没有见过闹钟、 小提琴、水手服、美丽的爱情故事以及大堆的“禁书”。然而就在“我”和罗明下乡接 受教育的时候,这里的寂静被訇然打破了。
这些新奇的东西、美丽的事物和善良的心灵开启了朱灵、小裁缝,还有他们身边人的 心,小号、小提琴,原始的壁画,偷来的名著,善良的玉珍,伟大的巴尔扎克,这一切 都在启蒙她们年轻的心智:这便开始了诗意启蒙的历程。这里的诗意启蒙,是指“以活 生生的艺术形象体验去传达理性意图,即凭借艺术的审美体验而使得蒙昧的心灵获得解 放”,它“要求启蒙意图必须寓于艺术形象之中,并始终不离艺术形象体验”。[1](p5 1)借助于这些诗意的启蒙方式,两部影片的导演仿佛是把曾经凄凄然在他们心中划过温 柔的夕照余辉的那一轮暖融融、乐陶陶的太阳追回。他们是一对夸父,带着自己心中的 主人公,一手抓住弓箭,一手紧握缰绳,去追回那一轮落日。
文明与蒙昧的对立,远不在见识过和未见识过的区别上,更在于深埋于生活方式和道 德规范之下的思想潜流。《天上的恋人》里把旧习和新气象、美和丑分得很清楚。实际 上旧习只是影片的陪衬和辅助,其用意在于形成比较和对照,看看愚昧的“门第”婚姻 :因为家宽是个聋子,聋子是不配有好姻缘的,自然娶不到身体健全、漂亮年轻的朱灵 ,只能找到带着几个孩子的寡妇。与此不同的是,《小裁缝》并没有把文明和蒙昧、美 和丑割裂在两极板块中,而是把它们铸成合金,两种因素犬牙交错的咬在一起,胶成一 只杂彩的圆球。这样,二者就有了各自的手法:《天上的恋人》采用平行法,《小裁缝 》则采用透视法。前者将矛盾双方摊着加以对照,用事实教人们选择。后者则是纵向延 伸,像剥皮刨根一样,将蒙昧的浮土拨开,裸露出演化的泥层,而那闪闪发光的老根却 永远藏而不露。在深邃的凤凰山间,总有新绿依稀摇曳。影片的重点落在了“新”事物 的启蒙入侵上,如何引发“莫扎特永远想念毛主席”、闹钟风波、偷书事件等等观念的 蜕变和发展,重在“变”不在“比”。在工地上,旧的时间计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 “资产阶级狗仔”的闹钟,“资产阶级”的玩具——小提琴和“资产阶级狗崽子”讲的 电影和故事也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最大享受,一切都被搅乱似的。无论是平行还是透视 ,都达到了凸显诗意启蒙的效果,在新旧交手的回合中,由于作者的偏袒,占上风的是 后者。
在处理文明和蒙昧、美和丑的对比上,《天上的恋人》擅长的是渲染的手法。朱灵心 中的张复宝是什么样的呢?是那个能吹动人曲子的小号的主人;是那悠扬乐声一响起, 就让朱灵魂不守舍,像电击似的赶紧放开搂着家宽的那双手。一种青春少女情窦初开、 又羞又爱、又惊又喜的复杂心绪跃然于心。音乐的渲染,不仅交待了张复宝的特点,也 生动地突出了朱灵的心理世界的变化:空灵的音乐和有知识的张复宝开启了朱灵对幸福 的追求。另外,玉珍的善良和成人之美的美德,在她为家宽唱歌时发出的令人震撼的呼 唤时,达到了升华。这个声音的渲染和朱灵在玉珍房间里看到的新婚洞房的红颜色的渲 染一样,一个纯美的形象感染了朱灵,提升了朱灵的人格形象。
《小裁缝》的另一技巧是貌似荒诞的幽默,穿插着那个文化缺席而人性未泯的时代特 有的滑稽与黑色幽默,酿造了文革年代悲喜剧气氛,影片在某种意义上揭穿了当时生活 的荒谬性。大脑被“红色文件”所占,人被挤进了思想的死角,这是一种滑稽。于是导 演从悲剧的下乡事件中提炼出笑,用红给黑镶边,制造“黑色幽默”。为了保存小提琴 ,马剑铃不得不演奏一曲,可是曲子是莫扎特创作的,罗明灵机一动,报上一个响亮的 名字“莫扎特想念毛主席”,革命委员会生产队队长觉得还不够“革命”,又补充了一 下“莫扎特永远想念毛主席”。于是全村人直至文革结束以后的很久(三峡工程的开工) ,大家还忘情的把这首曲子叫做“莫扎特永远想念毛主席”,而这正是对文革蒙昧时代 的发难。也正是在这曲名荒诞的曲子之中,熏染了人们的审美情趣,滋润了每个人的心 。
值得注意的是,《小裁缝》的荒诞是一把双刃剑:当这些“革命积极分子”正在席卷 人们纯洁和美好思想的时候,却不知道自己也需要“碰了毛主席牙齿的阶级敌人的儿子 ”帮他补牙。正是这种双重性,添加着荒诞气氛,催化了诗意启蒙的喜剧性。当队长的 牙齿被“革命”的赤脚医生拔错了后,他不得不求救于罗明,因为罗明的父亲曾经帮蒋 介石、省长和市长拔过牙。于是,令人爆笑不已的漫画出现了:由于机械条件有限,所 以只能用缝纫机当牙钻头的动力,加上伙伴们杀猪似的架势,终于补好了牙。这样一场 滑稽的闹剧使得罗明成为了村里受人敬仰的牙医。科学的光辉把蒙昧人的心照亮,当我 们看到村里的人们排着队、手里拿着鸡蛋和食物作为医牙的报酬时,不禁哑然失笑。
乐土
对于生活在隐瞒和痛苦之中的朱灵来说,逃避人们的眼光,躲进自己的小屋子,对着 傻傻的聋子说话,就是她唯一可以排解的方式。而对于生活在没有思想自由之中的小裁 缝来说,现存的生活状态只会让她“一张嘴说话就太土了”。只有大自然才是一片乐土 :《天上的恋人》里云峨山壁立千仞的群峰,有袅袅的乐声,有拙朴的壁画,有善解人 意的姑娘;《小裁缝》里崎岖蜿蜒的凤凰山,有沁人肺腑的琴声,有引人入胜的“藏书 洞”,有睿智的小伙子。这些都成为诗意启蒙的象征。其象征意义具体表现有三:
其一,音乐激发的心灵升华
音乐是一门具有较高思维形态的艺术,具有心灵的表现性和想象性。它能够激发精神 的反思能力和顿悟能力,也能将情感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以极其抽象的方式表现出来。音 乐最大限度的发掘了艺术的象征和隐喻功能。它最大限度的将心灵的抽象呈现出一个具 象,这使得音乐赋予人以自由联想的模糊内容。两部电影不约而同地采用了音乐因素来 充当诗意启蒙的先锋:一个是小号,一个是小提琴,“借助音乐所幻化出来的充满诗意 的形象”[1](p50)去开启乡亲们蒙昧的心灵。
电影《天上的恋人》中的小号,只有朱灵才听得到,听得懂。第一次交待小号是在家 宽给张站长送水的当儿,张站长正在吹小号,可是家宽是听不见的。第二次出现小号, 是在朱灵牵牛到张站长家去治病,她悄悄地走进了张复宝的家,一本正经的坐在长椅上 ,看看四处无人,她忍不住站起身来,蹑手蹑脚地摸起小号来。第三次出现则是朱灵正 坐在家宽的单车上,紧紧的搂着家宽,怕会摔坏。这时悬崖上传来了一阵悠扬的小号声 ,朱灵的手立马从家宽的腰间缩了回来。朱灵忐忑不安地应对着家宽,耳朵里除了音乐 声,什么也听不见。美妙的音乐带给朱灵的不仅仅是张复宝发出的爱的讯号,更是一种 来自心灵深处的快乐和倾诉。这种力量是家宽的单车永远带来不了的,它是高雅的艺术 所带来的精神愉悦,像天峨山玉米地里的庄稼一样生机勃勃,像窗前茂密的竹林一样郁 郁葱葱,像桂花树上沁人心脾的花香一样令人心醉。从对新奇玩意儿的羡慕到对纯美艺 术的向往,这无限的遐思犹如生命的提升,用幻想的语言张扬了生命和爱情的美和永恒 。
《小裁缝》里的音乐是马剑铃带来的,第一次在山里头演奏就吸引了大家,人们陶醉 的陷入了这个“资产阶级的玩具”的声音中:“农民们的脸,刚才还是那般的坚毅,在 莫扎特清澈欢快的乐曲下变得一分钟更比一分钟温柔,仿佛久旱的禾苗逢上了及时的甘 霖,然后,在煤油灯那摇曳不定的光亮下,渐渐地失去了它们的轮廓。”音乐作品的异 域风韵,形象、夸张而生动,超越时空的绝对敏感让听众怀着超越历史超越文化的永恒 幻想,去对待生命。正是这琴声,在痛苦的人流手术中,小裁缝第一次体验到了如急骤 旋律般的人生的多变,爱情有美丽的表面,也有痛苦的经历。她终于明白了那句话的真 意:“文明人”除了有情感,还要有思想。如诗如画的音乐,以充满幻想的音乐语言勾 画出了生命的绚烂和诗意,两部电影通过音乐的初期启蒙给接下来的启蒙过程营造了浪 漫的氛围。
其二,美的艺术形象带来的审美体验。
在这方面,《天上的恋人》和《小裁缝》分别用神秘的壁画和巴尔扎克的小说带领人 们进入一个审美的世界。岩壁上神奇的舞蹈在视觉上产生的震撼力,展示了大自然和祖 先的豪壮与恢弘,提醒了人们的平庸与细微。一面是浩瀚的人类历史,一面是渺不足道 的人生。在张复宝抛弃朱灵之后,“朱灵和王家宽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世界,我们在 朱灵的世界里看到了欺骗和疼痛,而在王家宽的那个世界里却看到了纯洁和美好。”朱 灵从壁画中领悟到的不只是人类生命的繁衍,更是一种博大的胸怀和宽容的胸襟。最终 ,朱灵和家宽、玉珍终于携手在悬崖边跳起了壁画上原始的舞蹈。影片在这个时候运用 了叠化:其目的就在于将人世间的无奈猥琐与壁画背景的庄严华丽相结合,把人缩小到 极不重要的一点上,听其逐渐全部消失在自然神韵之中。
《小裁缝》里罗明说小裁缝很漂亮,可是“一张嘴就太土了”,于是他的愿望就是用 文学来改造她。所以小裁缝、罗明和马剑铃把从另一个知青“四眼”那儿偷来的那个装 满“禁书”的皮箱,藏在了“藏书洞”。小裁缝不识字,只能听从罗明嘴巴里念出来的 巴尔扎克笔下的女性形象,开启了小裁缝蒙昧的心灵,她开始变化:制作了凤凰山里从 来没有的胸罩,在危难之时,开始像包法利夫人一样思考问题,甚至懂得了女人必须精 神和美貌共存。就连为村民们做衣服的老裁缝也发生了变化,由于受到了这位法国作家 的影响,一些奇思怪想,神秘的和自发的念头,开始出现在了村民们新做的服装上,尤 其是种种有关航海水手的因素。假如大仲马看到我们的山民们穿着某种水手服式的短上 装,他本人可能第一个会感到惊奇,这些衣服双肩窄,领子大,肩后面方,脖子前尖, 风一吹来便扑啦扑啦地拍响。它们散发着地中海的异国气息。由大仲马描绘、而后又由 他的徒弟我们这位老裁缝剪裁的蓝色的水手裤,已经赢得了姑娘们的欢心,裤腿宽大, 迎风飘荡,从中似乎弥散开蓝色海岸的芬芳清香。他为我们描画出一个五爪的铁锚,它 成为了那几年中凤凰山上女人们最时髦的图案。终于有一天,小裁缝背上行囊离开了这 片乐土,只因为巴尔扎克让她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女人的美是一件无价之宝。
其三,纯粹的“美”和理性的光辉
画和书带来了根本性的启蒙效果,而生活在朱灵和小裁缝身边的人,则是在潜移默化 的影响她们。善良的玉珍始终是善良的化身,强健有力的家宽,这些纯美的形象唤醒了 朱灵的心灵。罗明和马剑铃就像理性的光辉照亮了小裁缝寻找新生活的方向,鼓足了她 的勇气。
所有乐土上的一切都成为诗意启蒙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醉泉
人在自然的乐土上汲取初级营养,大自然本身就是性的象征。两部电影几乎用同样的 方式,别开生面地将主人公的第一次性行为安排在大自然的怀抱之中。性与自然界熔铸 为严丝合缝的一体。朱灵和张复宝是在原始壁画的悬崖上浪漫地完成首次灵与肉的结合 。原始生殖的舞蹈壁画是绝妙意象:岩石凹凸的悬崖默许地注视着,树木旺盛的夏季, 天峨山灌注了万千生命。这让我们想起了家宽给朱灵唱的山歌:
高山无楼我盖楼,平地无沟我开沟,盖楼只为妹常住,开沟只为水常流。我俩变鸟共 一山,我俩变鱼共一滩,我变七星你变月,五更同路共一天。
小裁缝和罗明是在藏书洞前的潭水里怀上孩子的。潭水边枝蔓攀扯的水草,覆盖着绿 茵茵苔藓的岩石,潭边茂密的灌木丛,都在火辣辣的烘托一个野性的小小生命。此时电 影里传来了一首谜语歌谣:
什么鸟飞来节节高?什么鸟飞来像双刀?什么鸟飞到天池里?什么鸟飞来伏青草?鸽子飞 来节节高。燕子飞来像双刀。雁鹅飞到天池里。野鸡飞来伏青草。
这里,谜底明摆着:从爱情的萌发到冲动到亢奋,这全部的过程都托付在那深不见底 的潭水。当感情启蒙发生作用时,青年男女在山泉、在山崖,狂热地醉饮着生命之甘泉 。没有性宣泄,没有矫揉造作的语言,壁画岩、潭水,这大自然如诗如画的、给人以美 感的意境,犹如诗一般地唯美。当生活在都市里的人整天抱怨没有爱情的时候,想不到 却在遥远的地方演绎了这样一段纯美的爱情故事。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诗意的感情启蒙呢 ?
超度
两部影片为我们筑起了过去、自然和爱情三层围堤,通过音乐、文学、感情等等文化 启蒙,来完成导演心目中的诗意启蒙。在这个已经出演在我们眼前的诗意启蒙历程的结 尾,影片给我们展现了一种新的超度方式,不再像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神们看待我们 ,好比顽童看待苍蝇,他们杀害我们,为自己开心。新生和涅槃,不只有死亡这一种形式。佛教和道教用念经、做法事来超度鬼魂,使之脱离苦难,影片之中的超度则是采用了十分诗意的方式来超越现实的矛盾。两部影片采取了迥然不同的超度方式:一个(朱灵)是被气球带走,一个(小裁缝)是到大城市去寻找新生活。但同时两部片子又同时使用了开放式的结局,没有定局,不知道将来对于她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只留给观众无限的想象和补充。
作为最佳艺术贡献奖的《天上的恋人》,其唯美之处就在于“天上的恋人”,谁也不 知道朱灵会被红红的热气球带到什么地方去,只希望她能够找到更好的去处。或许是死 亡,或许会生出更好的结局来,这样没有固定格局的开放式结尾,即使是死亡,也是“ 亮色的死亡”,浪漫和唯美的结尾,没有忧虑和痛苦的离开,留下了对家宽和玉珍的美 好祝愿。
一切朱灵所得到的审美体验:从音乐中汲取的心灵升华,从原始艺术中体验到的自然 之美,从典型纯美形象玉珍身上看到的善良和成人之美,这一切的诗意启蒙促使她选择 了离开这块乐土,去寻找自己真正爱情的归宿。身边所有的、纯粹的美,让她选择了乘 着红艳艳的气球,随着风,诗意地成为天上的恋人。
谈到这种诗意,就不得不提影片的导演了。导演蒋钦民是一位“海归”导演,他1992 年去日本,先后在日本电影学校和日本大学艺术学部电影学科深造,于2000年3月获得 硕士学位。讲到“海归派”电影人才,蒋钦民说:“我和陈冲等人,现在被称为‘海归 派’导演,我们在海外学习电影艺术、或从事创作实践;吸收了一些新鲜文化,再加上 中国文化背景,结合中国的思想和情结,两者相结合,就是一种创新。”《天上的恋人 》正是这样的一个创新,其中新鲜的文化,我想恐怕就是他在日本所受到的熏染吧。该 影片唯美、空灵的结局似乎可以看到日本文学、日本影视的唯美之风。从紫式部《源氏 物语》里唯美的女性生活风格,到川端康成、村上春树的浪漫和唯美主义,都把空灵、 不可言语的美幻化在纯净的想象中,就如日本电影《情书》中一纸情书带来的爱情的浪 漫等待一般。而蒋钦民《天上的恋人》正沿袭了这一点,把东西的小说《没有语言的生 活》的悲剧改编成一部“此情只应天上有”的浪漫、唯美的一曲动人的爱情乐章。
《小裁缝》中罗明和马剑铃的启蒙是没有白费的:小裁缝最后剪成了齐耳短发,穿上 带有地中海气息的短衫,利落的裤子,脚上是一双洁白的球鞋。当面对着前来挽留的罗 明时,小裁缝的脸很坚决,执意要去大城市寻找新生活。
罗明问:是哪个改变了你?
她说:巴尔扎克。
罗明反问:巴尔扎克?
小裁缝回答:他说,一个女人的美是一件无价之宝。
是的,从巴尔扎克及其他作家的许多小说,如《贝姨》、《高老头》、《包法利夫人 》、《红与黑》、《死魂灵》、《罪与罚》等等,里面美丽又有胆量、叛逆的女性深深 的吸引了小裁缝,她不再是那个傻乎乎执著寻找闹钟里小公鸡的山村妹子了。她用自己 的行动实现了自己的二重身。这样一部由神秘的“禁书”皮箱和一位美丽的乡村裁缝女 ,由知识与美、青春与激情导演的情节剧上演了一位女性的诗意启蒙的成长历程。片中 始终激荡着女性从软弱——独立思考——追求独立和叛逆的女性的青春成长历程,和法 国文学,尤其是与巴尔扎克息息相关的。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他的小说里 表现得非常充分,尤其是小说里女性通过文学来达到对命运的抗争,和小裁缝的出走如 出一辙,本片的导演戴思杰改编了自己的小说《巴尔扎克和小裁缝》,将它拍成了电影 。戴思杰,生于1954年,1971至1974年作为知青在四川省插队落户,后考入南开大学学 习艺术。1984年去法国深造,成为一名电影导演。他本人的插队体验给了他题材的来源 ,而后来的出国深造的经历又使影片增添了异国色彩。可以说《小裁缝》里展现了艺术 形象的诗意启蒙。
作为不同时代背景、不同影视风格和不同人物类型,却又同是抒写爱情的电影——《 天上的恋人》和《小裁缝》的意图就在于想要展现一个诗意启蒙的过程,为女性追求新 生活写下坚定有力的一笔。直到今天,这种启蒙仍旧在承担着巨大的神圣使命,朱灵和 小裁缝的经历也在不断的督促着我们通过反省自我,认清自己的现在和未来,去正视自 身和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或许现今越来越多的女性通过自己不断的抗争和奋斗去谋取 更好的发展,就是女性争取诗意启蒙的一种最主动的方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