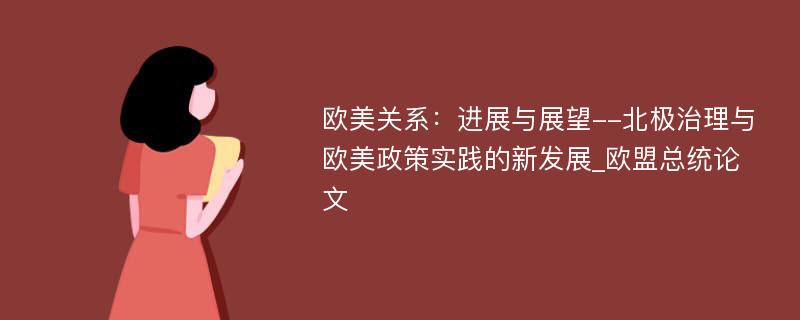
欧美关系:进展与前景——北极治理与欧美政策实践的新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美论文,北极论文,新发展论文,前景论文,进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全球气候变暖、北极海冰快速消融等因素的推动下,以海上航道的归属与利用、自然资源的勘探与开发、原住民社群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等为代表的各种北极治理议题,正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而作为北极治理的重要行为体,欧盟与美国的北极政策实践值得密切关注。
近年来,基于自身应对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的多重战略考量,欧盟对北极事务表现出日益浓厚的兴趣;以欧盟委员会、理事会及欧洲议会为代表的欧盟三大机构连续推出有关北极政策的官方文件,宣示欧盟在北极地区的利益关切,展示其作为北极治理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定位,并积极谋求北极理事会的常任观察员资格。2008年11月,欧盟委员会推出首份北极政策报告《欧盟与北极地区》,强调无论在历史、地理、经济和科学等方面,欧盟都与北极有着重要而密切的联系;同时,反对任何将欧盟或欧洲经济区成员国排除在外的政策安排,并主张将北极事务纳入更为广泛的欧盟议程中,以持续加强与北冰洋沿岸五国之间的对话。2009年12月欧盟部长理事会通过的关于北极事务的决议,以及2011年1月欧洲议会通过的《可持续的欧盟北方政策》决议,均是对上述委员会政策文件的进一步阐释与发展。①此外,《里斯本条约》的正式生效与实施,则使欧盟对内与对外政策得到整合,其中欧盟对外行动署在北极事务上的协调功能将得到极大的提高。2012年3月,在“欧债危机”持续发酵的背景下,欧盟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访问了芬兰、瑞典、挪威三个北欧国家,表示希望通过与有关北极国家的沟通和交流,推进欧盟在北极地区的战略和政策。2012年6月,欧盟委员会正式发表《发展中的欧盟北极政策:2008年以来的进展和未来的行动步骤》。这一最新战略文件,②强调要加大欧盟在知识领域对北极的投入,并以负责任和可持续的方式开发北极,同时要与北极国家及原住民社群开展定期对话与协商。
结合有关官方文件,欧盟的北极政策目标大致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北极环境及生态保护、北极资源的绿色开发和提升北极多边治理。在北极环境保护上,欧盟强调将尽最大努力防止和减轻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保护北极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在北极资源的绿色开发方面,欧盟认为北极航运、自然资源开发及其他企业行为须采取负责任、可持续和审慎的方式进行;在提升北极多边治理问题上,欧盟认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其他有关国际文件构成多边治理的坚实基础。但三大政策目标之间难免存在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的地方;最为明显的是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这两大政策领域之间的矛盾。首先,对欧盟而言,能源安全主要意味着能源供应安全,即能源的依赖性和稀缺性问题,它要求增加能源供应或能源替代。北极作为能源聚集地提供了新的能源供应的可能,但该地区主要蕴藏的是油气等化石燃料之类的传统能源,而它们正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这与欧盟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目标(即关注可替代的清洁能源及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确立领袖地位)相矛盾。其次,北极的资源开发是一项高能源密集型的产业活动,这与欧盟强调能源效率的政策目标相悖,并可能给当地环境造成损害,进一步加剧气候变化。因此,欧盟官方文件所描绘的三大目标之间的和谐状态,在其北极政策实践中实际上是很难实现的。
从欧盟2012年发布的北极战略文件可以看出,欧盟政治机构更为强调从“知识、责任与参与”三个层面进行政策阐释,更加注重政策目标和举措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即通过进一步加大在北极生物多样性保护、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防治、国际海运环境标准与海事安全标准的制定、可再生能源产业等知识领域的投资、促进地区和平与可持续发展,强调对商业的开发采取负责任的方法,并与北极国家及原住民进行建设性的接触与对话。欧盟将北极突出的环境保护、航行安全及基础设施问题内化为其“北极责任”,试图将自身界定为北极治理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身份,以便更加有效地介入北极事务。在2007-2013财政年度内,欧盟提供了11.4亿欧元的资金以支持欧盟北极区域及邻近区域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潜力的可持续发展。在科学研究方面,欧盟在最近十年已通过第七框架项目提供了约2亿欧元的资金支持北极国际研究活动;欧盟委员会还专门在“2020地平线”研究与创新项目下支持北极科学研究,并将通过发射新一代的观测卫星促进北极搜救能力的提高。此外,欧盟及其成员国自2007年以来通过各种渠道向包括原住民在内的当地居民提供了累计达19.8亿欧元的财政资助。欧盟委员会及对外行动署还将定期与北极原住民代表举行对话,取得其对欧盟北极政策立场的支持。
欧盟承认北极理事会是北极治理的首要机构;因此,对欧盟而言,获得北极理事会常任观察员资格意味着可以进一步强化与北极理事会的合作,并在理事会的框架内清晰地了解美加俄等北极伙伴国的具体关切,这对欧盟发展其对内政策也是至关重要的。③欧盟还利用其在全球及区域治理机制建设上的优势,对北极事务施加有效影响。欧盟支持国际海事组织制定强制性的《极地冰封水域航行规则》,从而为北极航道的自由航行奠定制度性基础。欧盟相关机构和人员还积极参与北极理事会下属专门工作组,如北极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组的工作。欧盟委员会在“欧洲海事安全署”的协助下,支持北极理事会采取海上应急和响应措施。欧盟还利用其主导的各种次区域组织架构开展与北极国家的合作与交流。欧盟通过巴伦支一欧洲北极理事会与俄罗斯、挪威、冰岛、芬兰、瑞典等国进行政策协调和领域合作,在航运、渔业、环境、能源等领域进行综合治理。利用冰岛、挪威作为欧洲经济区成员的身份,欧盟还试图将与冰岛和挪威的北极事务合作纳入其欧洲事务的范畴。
欧盟意识到保持北极地区良好的国际合作势头、促进地区稳定符合其根本利益,并试图通过其“软实力”影响北极治理的发展趋向。但在当前欧洲经济复苏乏力,部分成员国“离心”倾向日益凸显的背景下,如何协调欧盟内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之间对北极利益或北极政策的不同取向是其必须解决的问题,因此,欧盟北极政策未来的实施效果还有待观察。
作为一个北极国家,美国在北极地区拥有广泛的根本利益,④具体而言包括:确保国家安全的需要、保护环境、负责任地管理资源、对原住民社群负责、支持科学研究,以及在广泛事务上加强国际合作。2013年5月10日,奥巴马总统发布了其任内的第一份北极战略文件——《北极地区国家战略》。⑤该战略明确了美国在北极的三大战略优先事项(即增进美国的安全利益、致力于负责任的北极地区管理以及加强国际合作)和四项指导原则(即和平与稳定、科学决策、创新型安排以及原住民协商)。与美国政府先前发布的多个北极战略文件⑥相比较,2013年版的《北极地区国家战略》仍强调安全是美国在北极地区的核心利益,但其对安全的认知趋向多元化。当前美国在北极的安全利益,涵盖了从安全的商业和科学行为到国防行动在内的广泛意义上的各类活动。北极地区的能源因素构成美国能源安全战略的核心内容,因此负责任地开发北极油气资源符合美国“全方位”加强国家能源安全的战略。在北极地区管理方面,保护北极独特而脆弱的环境是美国政策的中心目标之一,强调依据可获取的最佳科学信息进行决策,并在资源开发过程中综合考量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文化价值等多重因素。在国际合作方面,则强调通过加强与俄加等北极国家的双边关系以及改进北极理事会等多边机构的工作,致力于增进北极国家的集体利益,提升地区整体安全。所谓创新性安排,则是指在财政紧缩期间,为更有效地开发资源和运筹各种能力,美国不仅强调与北极国家和其他伙伴国的合作,同时也培育与阿拉斯加州以及私营企业的伙伴关系,以增进美国的战略利益。因此在合作渠道上,该战略不仅涉及国际层面的合作,也包括了联邦与阿拉斯加州之间国内层面的协调与合作。
鉴于美国是唯一一个未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北极国家。该文件强调,加入《公约》有助于保护美国在整个北极地区的海洋和空间的权利和自由,捍卫其关于西北航道和北方海航道自由航行和自由飞越的立场;而且只有加入《公约》,才能最大限度地确保对美国在北极和其他地区延伸大陆架的主权权利,并主张美国对北极地区大陆架的申索将从阿拉斯加北部海岸延伸超过600海里。尽管美国目前还不是《公约》缔约方,但将继续支持和遵守《公约》所包含的习惯国际法规则。
在北极议题日趋“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美国维护自身北极战略利益的紧迫感日益增加。在5月15日北极理事会部长会议召开前夕出台国家级的综合性北极战略,表明美国试图引导北极治理的未来发展趋向。在北极治理机制的构建上,美国既重视北极理事会作为处理地区事务首要平台的作用,又意识到当前有关地区治理机制多样化、碎片化的局面,⑦有意借重其他多边机制和法律框架,包括加入《公约》以维护其根本利益,同时也不排除在适当情形下与其他北极国家协商制定“新的协调机制”,以赋予自己更多的灵活性和运作空间。该战略文件对内则有整合资源、加强协调,以便更为有效地管理北极事务的意图。长期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地方政府、私营企业、原住民团体在北极问题上的利益并不一致,各方沟通和利益协调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联邦政府在阿拉斯加油气资源开采问题上,就面临来自能源巨头和环保团体的双重压力。奥巴马政府试图通过出台国家战略进行整合,以回应和平衡国内各利益团体的关切。此外,北极战略文件将加入《公约》作为战略优先事项之一,也有进一步推动国会尽快批准《公约》的考虑。
虽然由于地缘因素和身份定位的不同,欧盟与美国的北极政策/战略大相径庭,但两者之间还是有相通之处:欧美均倡导负责任地开发北极资源,均强调北极航道的自由航行,均重视与原住民的对话与交流,均将国际合作作为增进自身北极利益的主渠道等。作为负责任的北极治理“利益攸关方”,中国今后如要更为积极有效地参与北极事务,就必需加强对欧美等主要行为体北极政策与实践的研判,把握主流,消除误解,从而实现“多赢”。
注释:
①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Conclusions on Arctic Issues",16826/08,Brussels,8 December 2009,European Parliament,"Resolution on a Sustainable EU Policy for the High North",2009/2214(IM),Strasbourg,20 January 2011.
②European Commission and the HR,"Developing a European Union Policy towards the Arctic Region:Progress since 2008 and Next Steps",JOIN(2012) 19 final,Brussels,26 June 2012.
③由于与加拿大、挪威存在海豹皮制品贸易及渔业问题上的矛盾,欧盟的观察员资格问题在2013年5月举行的北极理事会基律纳部长会议上仍然“悬而未决”,但会议还是决定欧盟今后仍可以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北极理事会各项工作。
④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May 2010.
⑤National Strategy for the Arctic Region,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docs/nat_arctic_strategy.pdf
⑥有关美国1983年、1994年及2009年发布的北极战略文件的解读与分析,参见白佳玉等:“美国北极政策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沈鹏:“美国的极地资源开发政策考察”,《国际政治研究》(季刊)2012年第1期。
⑦有关北极治理机制多样化、碎片化的论述,参见程保志:“北极治理论纲:中国学者的视角”,《太平洋学报》2012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