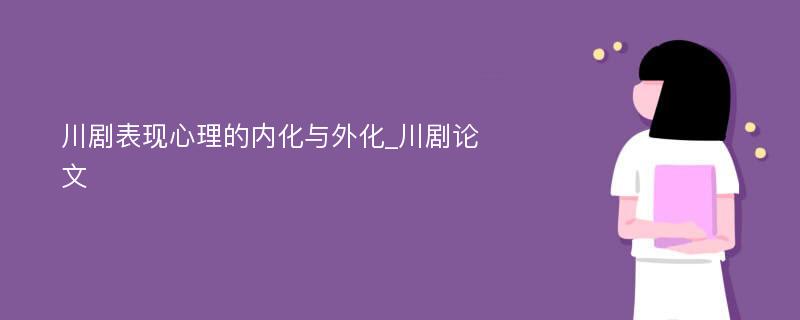
川剧表现心理的内化与外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川剧论文,化与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戏圣康子林曾提出:“心领神会形附”这样有着心理学意义的命题。川剧舞台的艺术实践,是心领后的自觉运动。要表现角色的性格,再现剧本的内容,得去对表现对象进行认知:这一角色的性格特征,舞台文本的内在旨意应有所了解;有了明晰的认识后,对角色的表现,内容的赋予,意向的点定,再具体化为心象,造就应该表现的具体形象外化于舞台。把对角色的理解,内容的透识内化于心中,然后外化出去。这样,对要表现的对象的舞台行为使之随心所欲不逾矩,形能附随于心。
康子林先生的“心领神会形附”包容着表现心理的内化与外化:认识对象,理解对象,将对象的行为形象于以心拟构形,这是表现心理的内化;对要表现的对象进行内的信息加工、编码,拟形外的投射,这是心理外化的历程。外化是内化后的客观性;外化的具象行为是对所要表现的对象认识、读解后内化于心的拟形显象。川剧艺术领域里的外化是“心领”后内化的外射;“附”于心的形则又是“神会”心化后的具象。
一、内化中的感悟与心化
内化中角色自我的内寻求:觅象,拟形。内的抽象,来自外的具象;直接经验、客观世界物质形象的摄入。“把感觉到的外部客体意象传达给表现的功能;另一方面,它是一种情感的因素,因为通过体感的变化,它把情感的特征赋予情感。”(引自瑞士·荣格《心理类型学》560页)感受的实在,内的造象拟形多些真实。心悟是内在的体认:寻求新感觉,扬弃旧的不适时宜。川剧艺术家们很在意感悟,因为感觉、自悟是有意识的知觉与内觉。
《曾荣华舞台艺术》一书,有这样一段话:“1953年我参加赴朝慰问团,在朝鲜每天都基本下大雪,我在雪地里走台步,雪里现出足印,走远了,线路就长了,用眼睛看去多遍就有实感了,同时我身上雪花用手扫去。后来在《评雪辨踪》演出中也使用了好多。”他在表现吕蒙正的“冒雪回窑,浑身上下似水浇”的寒侵冷袭的外现状态,让人感受到真实、可信。艺术外观的真实感觉,是曾荣华先生所经验的那个下雪天:纷飞的大雪,刺骨的寒风。这些有着实在感觉的物质具象信息进入心理界,被储存、被嵌入大脑屏幕的记忆库,是角色的需要,戏剧情境的需要,需要的形象在储存中开释转化为艺术的意象,内化发生了。曾先生先在感受冷飕飕的风雪,才有那“似水浇”的实在舞台意象,他把感受中的意念内拟定具象化的形态:搓着双手,嘘着口中的热气,以此化解寒冷;当其上场亮相时,迎面扑来阵阵寒风,风动雪飘,随之双手抱胸,以示抗御袭来的酷冷严寒。心象是这样的内化拟定,物质化的舞台具象行为又是依循内化心拟之形去造象。
曾荣华先生对那:“男踪女迹,来往相交”看得那么具体、实在,是他对那“雪地现出足印”物质化具象有着实实在在的感觉。感受的真,实在确切,内化于心的表象的真,外化出的象就有着真的反映。人们看到曾荣华先生所指的男踪女迹,舞台上并没有这样的物质真实:真实的冰天雪地,雪块、雪珠、雪花,腐草旁边男人与女人的脚印;这些虚拟的无,却给人的感知是有,从艺术欣赏视角看,是真实可信的。心外客观化的雪珠、雪花、腐草旁边的男踪女迹,那在感知上的真,是曾先生内化这些心象时注意了它们的客观真实,是有感于真实的物质形象去拟真构形造就了真实。
内的拟形造象的化,化出特定情境、特殊心性。化是实现一种目的,完善相应的需求。吕蒙正对那所见的男踪女迹,“来往相交,这寂寞荒村,又是谁来到?”引起了疑心,竟对妻子刘翠屏有着他恋不贞的特别思考。这里要对人物心绪进行拟形内化,得把吕蒙正的内在人格有个确切的把握,人物吃准了,所拟定内化的象才有个准确的构形。角色外现的形,是运载内在的心。心性与行为相背,显现的是表里不一的人。内化的是人,先要吃准心性:吕蒙正很注意人格尊严,他奉行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当感觉到妻子有失节不贞的疑点,便不能容忍:“忙回窑中”。回窑以后,发现刘翠屏仍熟睡窑中,才放下心来,发泄了一番感慨,内省自己的无能,不能给妻儿以丰足的衣食,以致困居寒窑,受饥受寒。吕蒙正感觉到自我是一个不能荫妻蓄子的男人,在那男人主宰一切的社会里,他不能不涌动着自卑。有了这样的心理情结,潜在的怕妻子鄙弃自己,怕她另外寻求倚恃,离他而去。这样的出走,影响着他这个男人的自尊。于是十分关注那能给她饱食的人儿来到,吕秀才便时刻警惕着这寂寞荒村非我的男人的行踪步迹对这一穷困王国的进入。这是吕蒙正的真实人格,对他的内化拟形,先要确切把握住那颗跳动着的心。造形先知心,心的不能透识,惟恍惟惚,那么外现的构形,将是恍兮惚兮,没个明晰的心象谱。这心的内化,首先得化好心。
《周企何舞台艺术·自悟篇》写道:“学、明、通、精、化、人、情、技、美、神”的自悟一得,是他的表现心理具体的、系统的内化过程。所要表现的对象,通过学习认识,以求心明了了,明心见性的通达后,进行心的内化拟象,所具象的这一个人,其性格系统,情感态度,在剧中应有的情绪行为,内向的无言隐衷,这些属于人(角色)的完形,有了明晰的心象谱,再赋予美丰姿,应有的情感态度,这样内化拟定,依此外现神情。周企何先生自悟中用心去琢磨所需求的表现,细省心象的完形,外化所选择的范式,其舞台活动的“美中见神”是自觉的运化。
内化中演员对自己所创造的角色,外化行为的手段的自省、评价,从中发现缺失,不尽人意之处,进行自我评估,细省后加以裁夺,最后予以再造重创。这样的内省补偿,仍是内化中求得。周企何先生介绍他:“一次,当我收听到当年与谢文新合作演唱《迎贤店》,在语势、声调、气息、情感等方面,顿时悟出若干不尽完美之处,再次扮演店婆时,我便注意作一些必要的修改,藉以强化剧中特定的语言环境和情感氛围,渲染人物的个性色彩。”内化中的自悟、自省,在人物塑造上、艺技表现上寻求新境界,完善再现中尚还有缺失的色块。
内化中的心象拟定,是川剧艺术创造角色,结构表演必要的心理过程。外现形的造就,是内化心理必然的拟形。“形动于衷,形遂于外”(张德成语)。心动则形随,心不动则形不随。动态中的形,形的大动,小动,不动,似动非动,动的优美,动的灵动;动的运载着人情思绪,这些是内心在运作,内心拟形;心拟后的物化是心化的外现,动于心,才形于外。《秋江》中的老艄翁,这位长年在秋江河荡舟的老人,他的着装,摇船搬桨的动,与女尼陈姑在小舟上的谐谑,是表演者先感实象,后拟心象,那感人的形动与声的波动,是真衷内动。这正如周企何先生所反观概括那样:“形,成于未演之前,神,流于演出之中。”
川剧艺术家们,他们对舞台的把握,角色的开掘,先求有感,然后深悟,悟出需求中的境界,内向心化,化出角色的形,内蕴人物的魂,这样层层递进,渐入佳境,正如荣格在《心理类型学》中所说:“纯粹的感觉印象向含义的内在深度发展。”
二、演员自我的内向投射
川剧舞台上的角色形象、自然物象、行为形象,这些象的构成形态是由演员主体的造就,他们把需求表现的对象和构置的意义价值转化为物的拟形向外投射。“正象投射概念所恰当地表达一样,它以此要求主体内容转换进入客体。因此,它也具有投射概念的过程。弗伦克兹现在把内向投射定义为投射的对立概念,即把客体摄入主体的兴趣范围之中去,而投射却意味着主观内容向客体的移置。”(《心理类型学》542页)这即是说内向投射把主观的意念外向移于对象。川剧艺术领域里的表现,十分注意内向投射。为着一种表现需求,演员们常常把要表现的内容:道德伦理的,内隐情感的意象转换为理念形态与心拟物象去造就角色应有的行为。演员的内向投射,作为一种特定的心理,它是演员自我对要表现角色的隐蔽灵魂的揭示,角色意志力的体现,自为的一种理念道德的构形去投射需要击中的目标;把那最能体现角色意志的物象赋予心象以实现表现目的。下面要谈的是川剧演员几种内向投射的具体形态:
演员心里要有一根响鞭抽打杨广
著名川剧演员晓艇在《问病逼宫》中谈道:他所饰演的杨广,行为残暴,逼母夺印,为皇权承袭,竟置母亲于死地。杨广还是一个伪君子,披一件“人品出众、风度俨然”的外衣,竟然当着父皇之面,调戏皇娘陈妃,无君无父,禽兽行为。为鞭辟入里地撕下杨广伪君子的画皮,暴露他阴险凶残的本性,在唱腔、念白和身段都作了贴近人物的处理。为从心灵深处揭示人物,并按川剧前辈的说法:“演员心里要有一根响鞭抽打杨广。”这里的“响鞭”是心象,不是具体的物质,是演员自我为深刻揭示角色的内隐灵魂内化心理的假定形象。假定的抽象,没有具体的长度和实质性的重量,是难以实施鞭打。川剧前辈提出心里要有一根响鞭抽打杨广,那假定的意象物是理念道德的运载体,它作为饰演杨广的演员对角色行为的内观照心象。杨广的凶残本质、禽兽行为通过心里的响鞭去抽打,去拷问那肮脏的灵魂,去揭示隐潜中的阴暗处。杨广的逼母夺印,皇宫乱伦,行为是受心理动机支配,是心作用其“灭伦欺天”的胡作非为。抽打杨广的响鞭,是道德观念内化的心象鞭子,把杨广内隐的丑恶灵魂驱赶外出,毫不留情,使之赤裸裸地外化于舞台。演员心里有这根理念道德的响鞭,其表现心理更理智于舞台的实践:内化中有着鞭打的心象,表现心理通过理念的导引,循着道德化的心声呼唤内情,时时刻刻不忘记对杨广丑恶本质的审视,还对掩饰着的虚伪要剥开予以抽打。这样的拟形鞭打挤压,就像气压水瓶一样:通过压力,瓶内之水,才得以向外投射。
用心去刺杀人
物质化的心不能杀人,非物质意念的心更不能杀人,心杀,只能是物质的杀人利器运载着心志去杀。这里提及的“用心去杀”仍然是演员自我的内向投射:
彭海清对我们说,他八九岁时向老师学艺,演一段豫让刺赵,排练完了,老师问道:“娃娃,你刚才是用什么刺杀赵王的?”他说:“用的刀”。老师摇头说:“不是的,你好好想想嘛。”后来老师又问他,他又答应道:“是用的棒棒。”(排练时用棒棒代用)。老师又摇头,并且说:“娃娃,如果你只这样想,那你将来就只能在棒棒上下功夫,娃娃,你是用你的心去刺杀赵王呵!”
——丁玲《看川剧打红台》见(《川剧艺术研究》·六)心是不能刺杀人的。血肉之体的心,非金属利器不能刺杀,伤害不了人。师辈教彭海清用心去杀,是意在对赵襄子的刺杀行为的内心化:刺杀的有形工具要内蕴着演员要必然杀着的意志。刺杀的舞台道具是竹刀(或木刀),并以此去进行刺杀行为,行为在必然要刺杀死赵襄子这样的意志支配下进行“心杀”。心杀人,不是心去直接杀人,是杀的动态行为,杀的工具运载着生命意志。刀是人的意志化,心内化于刀的这样刺杀,杀更能倾注于角色刺杀赵襄子的刚强意志。这样,那物的搏杀注入了活生命,杀是人杀人,便不是单纯的物的机械进入。这里,演员自我的内倾投射,是把主观需求用心去杀人的“心”转换“客体方式”以体现主体意志。
紧紧抓着扣住观众心弦的手
著名川剧旦角张光茹的《层次与艺术》一文,有这样一段说:“为了加强效果,渲染气氛,一出场就能引起观众的特别注意,就像一只有力的手紧紧扣住观众的心弦。”紧紧扣住观众的心弦,造就一种“张力”,形成欣赏的兴奋,专注于舞台。作为一个演员,造就一种有利于表现的情势,为能有着好的受纳。张光茹在《铁笼山》一剧中,意在造就一种逼人的氛围,形成情感张力扣住观众的心。杜后到铁笼山,她以居高临下之势,把那象征皇权的金马鞭置放得特别显眼,做出不可一世之慨。这样,她以为用手一挥,将令铁笼山这里的一草一木,以及最高统帅的铁木耳都将匍匐拜倒,任她鞭打,击碎违逆她意志的山川与人。杜后有着凌人盛气,铁木耳根本不把她一朝国母放在眼里,金马鞭在雄威抖擞的铁笼山三军宝帐中反而自惭形秽,畏畏怯怯不敢挥鞭。威严与卑怯两种有差距的情绪态的艺术呈现,“就像一只有力的手紧紧扣住观众的心弦。”这“手”是“力”的意象,非物质的,力场在演员自我的心灵世界里。虚无的心象要伸入观众血肉的胸腔去扣住心弦,在现实世界是不客观的。演员把观众心弦的扣住只能是主观的投射,靠意的通达,心与心对应,情以情相激:演员自我的真情内动,情感相系,去感动观众这个人。扣住观众心弦这只手,是演员的心化意象,是内化投射于一物,以此实现一种表现的主体调节。
邓运佳著的《中国川剧通史》,其中转引《川剧人物小识》有关康子林演《情探》的评说:“(子林饰演的王魁)眉宇之间,神色不定,观其屡次心口相商,能将王魁良知与私欲争战之种种神情,一一传出,体会极其深刻。”王魁与焦桂英情与情相激的碰撞,角色心灵闪射着火花,神情的“一一传出”,造就了好的受纳情势,注意舞台,关心演员所要表现的投出。这只意念的手能扣住观众,抓住人心,是演员自我心理表现的最佳寻求注意到了这一关键的“手”:“不动观众情,戏会失去魂”。情动:是为情感的动力所动;情感动力的产生,是情感的逆差引发着这动;杜后到铁笼山内在心理的自视甚高与客观背向,逆差中的尴尬难以承受,诱发情感失态;人在情中碰撞,观众便为情所系,情的逆差形成的情感动力紧紧扣住观众的心弦。紧扣观众心弦的“手”,它不具有自然物质属性,是演员自我内向投射的“客体方式”,外化中又作用于“对主体的调节”。
三、外化的心理意象
外化是内在心理的客观化。内心的表现意象,完善意的拟形外现为具体的物质形象。艺术家们要把所要表现的对象得从内的拟形外化。在这里所要介绍的是那些具有心理学意义的外化,所化的形象,给人直觉不是一般意义的形态,是心理外化的意象。这些意念形象,象是可视的,有的还可触摸,是实在的物质形象。但是,这种实在的存在,有的是心灵的幻象,有的是睡梦的视象,有的竟是意的造象,是心在感觉它。川剧《伐子都》中的颖考叔的幻象出现,是子都做贼心虚,“疑心生暗鬼”幻觉形象。子都在战场杀害了救过其性命的大恩人颖考叔,夺得军功。在凯旋而归的庆功宴上,当有人提到颖考叔,亏心的子都,那不安的心灵顿感到杯中、席宴上、座椅下,似乎都发觉了颖考叔的身影。颖考叔的出现似乎在拷问他的灵魂,在鞭打他的脊梁,甚至还要卡死他。颖考叔的形,是子都的幻觉。人物心灵的异常感觉到了颖考叔的存在,这不存在的存在是不安心灵的致幻;内心已有了惊恐惕怵,才感觉到颖考叔的凌逼与威胁。子都眼睛里幻象发生是心在作用,有血有肉的颖考叔并无真实的存在,他早已尸寒骨朽。现实舞台上所发生的诸种行为是“无意识内容对意识的不自觉的侵入。”(荣格语)
《石怀玉惊梦》一剧的胡莲娘,她的出现对石怀玉忘恩负义的指责,最后的活捉,是睡梦中的发生。《心理学大词典·梦》的定义:“在睡眠状态下所发生的想象活动。人醒时接触客观外界环境,获得了丰富的感性材料,经人脑加工成为经验和表象。在睡眠状态下,这些经验和表象中的一部分重新出来,就成了梦的内容。”石怀玉杀害仙狐胡莲娘后,在他的心理意识中有一种预感,她会来图施报复。这种意念一当进入潜意识层后,便在睡梦中不自觉地袭上心来,做出被扼杀、被活捉的恶梦来。“惊梦”中胡莲娘与石怀玉的捉与反捉,是心象化的具型。“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由心思成梦的梦里形象,是隐潜意识的物质化。
川剧艺术家们在表现角色,演义剧情时,当其心领剧内宏旨后,则是外化其人,其事。具体的外化中,拟化的物质形态,则更多地注视于内在心灵的表现。曾荣华先生介绍他饰演《哑妇与娇妻》中林雨农一角,有着这样一番心得:“林雨农是西装革履,打领带,梳光光头。此外,我还在他左胸部荷包里,插上一朵红绢花。这一方面使人物扮相华丽俊俏,插一朵花,预示他是一个寻花问柳之人。”这一点外化的显摆,是意在对内在人格质的揭示。曹俊成饰演《打红台》中的萧方,在耳边插上一朵红花,他亦意在外化爱女色的人的内在心理。
内在心理的外化形态,川剧舞台上有这样几种类型:1.欲求意向的幻觉外化;2.潜在心理致幻的外化;3.虚化意象型;4.心理物化型;5.视觉后象残留型:
1.欲求意向的幻觉外化
外化客观化的随意移置是内在意向欲求的回应,化的物质形态是意向需求的具象。川剧《射雕》中车夫的胡髭的时有时无,是随着意向需求而存在,而消失。车夫是长着胡髭的中年人,他的容貌与花荣有些相似,所不同的是年轻美俊的花荣嘴上无须。这个与花荣近似的车夫嘴上长了胡髭,便不是少女耶律含嫣所希望的。耶律含嫣切盼花荣:殷切希望这位可意男儿再现她的面前,这车夫有了胡髭便不是花荣,她心理意向的不希望有胡髭长在他的脸上。心理基于此种意向需求,车夫嘴上的胡髭一下没有了,俨然如花荣再现于她的面前。耶律含嫣十分惊喜她的意外得到,欢跳着去告诉庹氏嫂嫂:花荣已经为她们打来车儿。庹氏难以置信这一事实,走向车夫看去,印象完全相反:其人并不英俊勇武,是一个长着胡髭的中年人。耶律含嫣不信,再次前去审视,车夫嘴上无须。庹氏去看,车夫嘴上确实有着短髭。姑嫂二人同去观察这位车夫,他实实在在长着胡髭。这个车夫是花荣的相似者,是上了年纪的中年人,嘴上长着黑黑的短髭。耶律含嫣看他一下没有了胡髭,那不是真实的存在,是意向需求的虚幻。她深深爱恋着花荣,希望他走后回返。近似花荣的车夫来到面前,他有胡髭,她意向欲求胡髭的不存在,车夫无须的幻象发生了。这变的外化,是意的作用,如心理学家荣格所说:“却是一种意识的积极参与”,使那本来长着胡髭的车夫一下变得了没胡髭。庹氏的视觉里车夫的胡髭一下没变无,在于她的内在心理没有一种意向这车夫应是无胡髭的花荣突现眼前。无确定意向的指归,生活自然按照它本来的原貌再现。在耶律含嫣的视觉里,相似花荣的车夫,一下没了胡髭,活脱脱的花荣再现,又是耶律含嫣意向欲求的幻觉外化。这种幻象的外化,是她欲想再见花荣偏又看不到这可心男儿的心理补偿。
2.潜在心理致幻的外化
潜在意识是人在社会所接触的人和事,留下的心象的沉淀,这潜沉并不等于无,当相应的刺激发生便被激发形成对应。任庭芳演的《伍三拿虎》,伍三的视觉中的土地,陡地幻化成县太爷,这变是潜在意识被激惹后的变异。土地与一方消灾,受到人们的敬仰,逢年过节,土地庙会,民众们会自觉自愿送些刀头,烧些香蜡纸钱,以表达一番虔诚敬意。即使是无钱的人,因家中穷窘,手里不宽裕,不买纸钱刀头奉敬,土地爷毫不见怪,仍然乐呵呵地笑着。土地爷在伍三、乡民们的心底里是个和善老人的心象,见着他只有亲近,没有畏怯。
当伍三见着土地爷那象征权力的黑纱帽、红官衣时,潜在意识致幻外化,土地爷一下变成了县衙的太爷。这下伍三嬉笑的脸拉长了,恐惧、惊怕之情涌上面庞,支撑坚实步履的髂膝一下变软,县太爷还没有大发怒威,伍三竟自下跪了。舞台上所出现的序化动作:土地爷变成县太爷,祥和的气氛一下变得肃穆、死寂,是伍三潜在心理涌上了固有的沉淀于内的心理恐惧。潜在的恐惧是这位县太爷以往的冷酷无情,对属下的残酷,留下了诸多可憎可怕的印记,时间长河的日积月累随之潜降于心,在红官衣的触发下袭上心头,把一个土地爷幻化成县太爷,顿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惊恐不已。当伍三一冷静下来想想,感到比虎还凶猛的县太爷,却惧怕真正的老虎,特命伍三前来拿虎,是不会冒险来到有活老虑的山岗。理智地审视现实,县太爷一下又变化土地爷。这突现与瞬间的逝去,它是潜在意识恐惧的升腾与潜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指被压抑的、当时知觉不到的本能欲望和经验。伍三的怕,畏惧县太爷的畏葸态,是压抑后扭曲心灵的外射。
3.虚化意象型
川剧舞台的写意空间,那水,那山,花鸟虫鱼,长亭短榭的存在、运动是虚化的,由演员意识所假定,虚拟的呈姿,那不实在的意象而观众实感其有。这种意念性的舞台运动是川剧表现的主要形式。这里提及的虚化意象型是演员自我对所要表现的对象给予造就虚化的意象,意象的物象是虚无的。它有明晰可感的意象,却无实在的可触摸的具体物象。《佛堂佛天》中,申桂生所看的“一煞时大佛堂前变铁瓦,满堂神相变夜叉”。他触觉到判官、小鬼在抽打牛头,马面,夜叉的抓拿,把他拉向阴曹地府的扯扯拉拉有着质感;在推拉中,申桂生有乞求,有忏悔;而鬼役阴差们对投来的苦苦哀求,却有着毫不为之动容的姿态;推拉与反推拉的行为动态,是可感的。这能感觉到的东西,却没有具体的物象,也没有物质性的具型动作。这里的舞台行为,只有意象,没有物形。象是由实际存在的申桂生扮演者——演员虚拟着意念形象去具型体现。这种外化中的虚化意象型的特质:是有象而无物质的形;运动的动态感是演员虚拟的意象,是假定中的意义形象。
4.心理物化型
外化的心理物质化,它的结构特质是:剧中人物有真实的存在,存在的实存体是心理物化形象的存在,现实世界中又不复存在。这个不存在却在舞台空间的流动时间里:审视对象,外倾情绪。那愤怒、那憎恨、那斥责,又是活生命的交响。行为形象是存在的、可感的。现实世界的不存在,是因为没有血肉之躯。动的动态象,是另一实在主体的心理意象,是心化形象外现于舞台。川剧《东窗修本》的心理物化在于岳飞这个形象彼时作为有血有肉的人是不存在的,而是秦桧心怀鬼胎,心虚而生幻,自己心理编织着岳飞的再现。东窗下秦桧继续在捣鬼。岳飞死于“莫须有”罪名,韩世忠等忠义爱国之士不服,纷纷为其鸣冤,秦桧甚为震恐,在东窗之下修本,企图给韩世忠等人罗织罪名,拿来诛却!正在思谋干欺心事时,忽然背上受到重击,回头见是岳飞吓得魂不附体。现实世界岳飞的不存在,在秦桧心里感到死去的岳飞存在于现实:岳飞有愤怒,怒发冲冠的情绪令人望而生畏,步步进逼的步态、情姿定要置人于死地;死亡的凌逼激起求生的欲望,秦桧正视着现实,为弄个明白,细省现实中已不存在的岳飞,察其形,观其貌,似乎感到这不是真实的存在,早已将他送进无血肉的鬼域,壮着胆儿去逃命,这不存在的存在紧追不舍,秦桧被吓瘫了。
《东窗修本》中岳飞的舞台形象是物质化的,他由有血有肉的演员扮演,手拿的铜锤,对秦桧的打、愤怒的追击是物化行为,有着质的运动,这些物质化形态,“是被错误地知觉了”,(引自克雷奇《心理学纲要》502页)岳飞早已死于无罪的冤杀。那东窗下突然出现在秦桧面前的岳飞,物与物相撞击的动态、静态形象的呈现是秦桧心理内拟象的物化。
5.视觉后象残留型
视觉后象,人的视觉触知自然物象所滞留的觉后形象。心理学家杨清先生主编的《简明心理学辞典·视觉后象》条写道:“在视觉刺激物停止发生作用若干时间内,所延宕的视觉映象叫后象。”川剧舞台上运动中的角色,所涉猎的自然物象,精神现象,幻觉意象,感觉中的情境、物象在视觉中滞留、延宕,一种表现的需求,外化成可视可感的艺术形象。《火烧濮阳》一剧,曹操在濮阳与吕布交战,中了陈宫台的火攻之计,烧得曹营内外一片火海,曹操也被烧得焦头烂额。后来收拾残部,远离那燃烧的土地,在无火区安营扎寨。当曹操自嗟自叹着从那熊熊烈火中得以活命时,忽然从他座椅下又冒出一股火来,受了一番意外的惊骇。在这非燃烧区座椅下又冒出一股火来,火的燃烧是物质的,是传统中的粉火(用松香研细而成)。火的发生,是心灵的外化,是感觉中的后象的客观化。曹操在濮阳被烧,身上着火,须发燃烧。在他的视觉触及:那燃烧的火焰,汇聚成巨大的火海,吞没了曹营许许多多的辎重,烧死了数以万计的曹军。这燃烧的现实不管曹操愿意不愿意都会进入视觉,存留印象。燃烧已成过去,所触知的火海,燃烧的后象已经嵌入视觉里残留着。座椅下冒出的那股火,它不是真实的存在,而是曹操视觉后象的外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