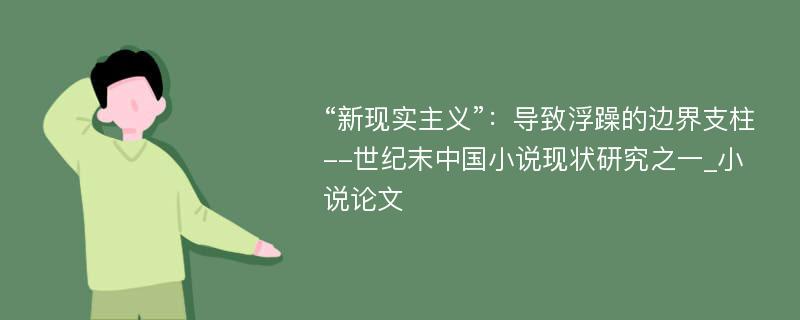
“新写实”:通向浮躁的界碑——世纪末中国小说现状研究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界碑论文,世纪末论文,中国论文,浮躁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回眸往昔:逐“新”情结何以难消解
人们不会忘记,20世纪的最后十年,在商品大潮的冲击和挤压下,中国的小说创作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和挣扎。寂寞的文场上,小说家们有着极为悲壮的超常表现:一个接一个的文学潮汐不断涌流,一个接一个的“炒红”作品风靡文坛,一个接一个的新人递领风骚,一个接一个的小说旗号此伏彼起,真是“似曾相识燕归来”,“乱花渐欲迷人眼”!在这林林总总的小说创作潮流中,一批标新立异的“新”字号思潮给人们带来了高远的期许和短暂的激动:新历史、新都市、新乡土、新市井、新女性、新军旅、新知青、新体验、新状态、新武侠、新法制、新闻、现实主义冲击波(当然是新现实主义的!)……“你方唱罢他登台”,甚至“你没唱完他上台。”走马灯式的小说更新,快节奏的自然淘汰,使小说园地喧嚣动荡,使作家读者目迷五采。在这喧哗与骚动之中,人们对小说的走势当然难以作出科学的扫描与梳理,当然难以作出准确的预测与评估。这真是中国小说的“春秋战国”!其实,对这种态势作出巅峰也罢、低迷也罢的结论,显然都失之简单与武断。在尘埃落定的世纪末霞光夕照中,当务之急倒是应该检视、反观一下,抑或是追溯、探寻一下这种小说创作的浮躁病源。病源清晰了,才能通过对个案的剖析举一反三,才能为这十年的小说潮流作准确定位,才能对浩如烟海的小说文本作恰切评判。
本着这样的初衷,我们将审视的眼光投向了肇始于80年代末的新写实小说,力图通过对新写实小说崛起的时代因缘、艺术品位、阅读效应、文学影响的探索,总结其成功与缺失,为小说创作的跨世纪腾飞提供殷鉴。
应该说,在那时的文坛上,再没有比新写实小说的处境更尴尬的了。接连不断的研讨、铺天盖地的宣传、读者颇高的期望,与天南海北难布战阵的艺术群落、千呼万唤终难面世的宏篇佳制,形成了那么强烈的反差——这些,铸成了新写实小说当年的现在时态势。作为新写实小说的那些主将,无疑也处在焦灼之中。他们如同一度为国人抱憾的运动员一样,虽然想重抖雄风,一鸣惊人,却总是难以超越昨日的辉煌。种种情势说明:新写实小说远非成熟的流派,过高的评估无助地于它的发展;它是亟待实现自我超越的、仍需不断调整完善的小说艺术。历史证明,恰恰是对它的浮夸,浓化了作家们的逐“新”情结。
历史契机:被拖下产床的“宁馨儿”
新时期以来,在奔涌澎湃的文学海洋中,新潮评论家们无疑是推波助澜者。他们以其特有的敏感洞幽烛微,捕捉着文坛的蛛丝马迹。呼唤着一次又一次的文学轰动。评论家们在新时期的文学发展中,确实功不可没,然而,渴望标新立异、追新逐奇的敏颖和急切,又常常使其有揠苗助长的举措。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一种文学倾向刚刚浮现,评论家们就争相论证和认同,似乎不这样不足以显现评论的睿智和品位。于是,新时期文坛上就涌现了“茫茫九派中国”的诸多文学现象或文学流派,使人目不暇接。这些,有的是对存在的天才发现,有的不过是虚光幻影、过眼云烟,有的则是刚刚萌芽的胚胎。对新写实小说的发现,当属于后一种。
1987年,历史为新写实小说的脱颖而出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当时,小说创作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形势,步入了必须转轨的临界点。一方面,肇始于1977年的伤痕、反思等现实主义小说逐渐开始落潮,不见了当年恢复现实主义、返归作家主体时的声势。它对现实生活那传统的把握方式,在审美创造中那刻板趋同的范式,使其失去了初始的轰动效应。小说创作的主体,那批归来的现实主义作家们,生活的库存和艺术的创造也都需要补充和调整。从接受美学角度来考查,整个社会已经处于接受饱和点,原有的共振度已经很难与读者新的审美需求相契合。另一方面,闯入文坛的小说新生代所奉献的探索成果,例如先锋小说、寻根小说等大受冷遇。他们在欧风美雨中得到的艺术启蒙和借鉴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那些波诡云谲的小说技法很少被大家认同,难以形成“召唤结构”。这样,小说的输出与接受出现了断层,作家的主体热情与读者的阅读效应呈示了落差。对此,作家忧虑,评论家更忧虑,迫切希望小说调整自己的视角,热烈呼唤迥异于前者的新体小说出台,以迅速打破雾重难进的寂寥和沉闷。
就在这时,武汉的两位女作家方方和池莉分别发表了《风景》和《烦恼人生》。敏锐的评论家一下子嗅出了嬗变的信息。那惊喜过望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些小说的非同凡俗以至戛戛独造之处就在于,它们把焦点对准了芸芸众生、平头百姓,赤裸裸地展示了他们的生存本相。这在当时是颇具冲击力和刺激性的。你看,现实主义小说多是在讲述过去的存在,咏唱那理想的歌吟;寻根小说在溯源那洪荒的往古,倾吐怀旧的情结;先锋小说常把读者引向黑暗的真空,探求精神的荒野,而《风景》、《烦恼人生》则描绘了人间烟火、平民百姓的人生风景线,叙说了凡夫俗子的辛苦遭逢。可谓“生正逢时”!兴奋不已的评论家们匆匆将尚没定名的“宁馨儿”拖下产床。艳羡至极的先锋作家们也纷纷加盟。一时间,似乎小说结束了“烦恼人生”,前方出现了绚烂的“风景”。
除此,读者期盼的社会心理,也是它早产的原因之一。首先,平民追求的务实心理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一段时间内,现实主义曾被曲解为急功近利式的图解政策和阐释理想,小说中的生活离读者越来越远,典型人物使读者越来越陌生,由此,读者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加之改革在中国引起的巨大震荡,广大读者再不象从前那样沉湎于理想的陶醉之中,务实心理得到了普遍强化,这就使平民的艺术追求急剧膨胀。因此,当展示了平民人生的作品问世,当平民们须臾难离的油盐酱醋、生老病死乃至物价、工资、住房、资金、子女、爱情、性等问题出现在作品中时,他们必然投以极大的关注。其次,自我价值的观照心理也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马克思说过,所谓审美,就是人“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对于小说的阅读,也是如此。不少读者就是通过阅读作品来直观自身的。在直观自身的过程中,他们对自己的人生命运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更透彻的感悟,从而确立新的人生目标,借以实现自我价值。以平民为描写对象的小说恰恰给了他们这方面的满足,这怎能不使新写实小说洛阳纸贵呢?
面对“新潮”与“传统”的疲软,面对作家的焦急与评论家的期盼,面对读者的希望视野,新写实小说终于早产了。
先天不足: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新写实小说很快就成了读者、评论家的宠儿。它的应运而生显示了一种必然性:在社会生活发生嬗变时,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也要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然而,由于早产,它必然带有先天的不足。因此,在全社会日益升值的阅读期望和审美标准面前,它显得那样迟钝和孱弱。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它没有如理论家们所预言的“代表着当代小说光明未来”,或“以一种全新的姿态,调整中国文学的步伐,使其走出低谷,导引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如果我们认真研究新时期文学纵横交叉的坐标系,以多种文学倾向作为参照,从中廓清新写实小说的流向,并窥视其全貌,便会发现,它在给文坛带来不少新的气息、新的冲击的同时,也存在许多先天不足,同时少了必要的后天滋补。具体说来就是:
第一,缺乏丰富的、大量的艺术实践,不具备形成自己艺术特质和独特追求的、动作整齐的实验群体。一种文学倾向,一个文学流派,都要经过较长阶段的艺术积淀,在作家和读者的双向选择中不断修正、磨炼,有了大量成功作品之后,才能为社会认同: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新写实小说则缺乏这个不应跨越的过程,而得益于评论家的施惠。在评论家们欢欣鼓舞时,针对的不过就是那么三几位作家,三几篇小说。直到几年后的今天,汗牛充栋般的评论文章中,所举的例证仍然是两位开山女将的发轫之作。这是多么耐人寻味的事啊!一位朋友想编一本新写实小说集,无论他怎样开放、发展、包容,也仍然只有那么二十几篇,引人瞩目的就是方方的《风景》、《落日》,刘震云的《塔铺》、《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及几位先锋作家很勉强归入新写实的作品。新写实,长不大的早产儿!无怪乎有些被认定是新写实的作家幽默地说:“新写实是评论家制造出来的,制造一种文学现象,使人们对文学重新感兴趣。新写实是评论家、读者的事。”(注:《新写实作家、评论家谈新写实》,《小说评论》1991年第3期。)虽然言之过苛, 但也从侧面反映了一定的问题,那就是:新写实小说的实践准备太匆忙了。
这种匆忙的实践,是新时期其他文学倾向所少有的。比如以伤痕、反思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小说,其酝酿之长,来势之猛,影响之大,震动之广,作者之多,那才称得起流派风格呢!就是有些人不以为然的朦胧诗派,艺术实绩也远大于新写实小说。很短期间内,它竟取代了现实主义诗派和新现实主义诗派的盟主地位,成为诗坛的主潮。新写实小说则不然。如前所述,在其“犹抱琵琶半遮面”,“未成曲调先有情”时,人们就为之催生,举行庆典,致使新写实小说在其荫庇下陶陶然举步维艰。文学实践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发展,都是创作与评论合力的结果。如果是一厢情愿,那么这种文学现象必然底气不足,难以持久,甚至造成错位。新写实小说几年来的蹒跚行进与评论界的巨大投入相比,不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吗?
第二,缺乏有力的理论准备与明确的创作指导,创作生产力一直处在人自为战的散漫自为状态。几年来,新写实的作家们始终没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没有联合作战的整体意识,一味跟着感觉走,不知道应向什么方向突破。方方就不讳言这点,她说:“我也说不清到底什么是新写实,只是觉得在叙述方式、语言语调等方面都和以前不同,在味道上也不是现实主义的。我写作以情感为主,凭直感”(注:《新现实主义,新现代主义》,《当代文坛报》1990年第2、3期)。池莉也说:“我写小说就是觉得作家有责任让越来越多的人读小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不只是这两位作家,其他作家也多是如此。他们并没有共同的文学观念,共同的创作指向,共同的艺术追求,一些作家甚至到现在也不承认自己是“新写实”。这就很难谈到理论的准备了。与此仿佛,倡导新写实的理论家也声音嘈杂、莫衷一是。有的甚至脱离文本,陷于理论玄学的迷乱之中,难以形成共识,这怎能有利于新写实的发展呢?比如,对新写实小说这毕竟存在的客观文学现象,始终在追根溯源,对其形成的原因争论不休,就没有多大意义了。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常盛不衰的争论热点。有的认为新写实是现实主义深化发展的必然,有的认为它是现代主义对现实主义的皈依、回归,有的认为它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杂交后的新生儿,有的则认为它是在创作盲区的新建树,等等,不一而足。此外,对新写实小说的性质、概念、表现特色等也歧见甚多。应该说,这些论争的出现都是必然的,是复杂的文学现象的正常反应。但是,如果这些论争不能针对现实,有的放矢,不能聚焦于色彩斑谰的文学现象,而是囿于一个大而无当、空洞模糊的概念之下,一切研究只是为了去证实一个尚不知为何物的东西,恐怕这种研究不会获得什么成果。本来,创作实践与理论探讨是并行不悖的,理论探讨应以创作实践为归宿,但那时的某些讨论一直在概念上纠缠不清,抛弃了许多实质性的工作,甚至是冷落了实践,这怎能不失去对创作的指导意义,“可怜无补费精神”呢!显然,它给先天不足的新写实小说又造成了后天匮乏。所以,对新写实应“不要问我从哪里来”,而应从其基本实践出发,观照它的新思维,发现它的新特质,促使它健康成长。
并非“零度”:而是一种“态度”
虽然,我们面对的新写实小说是一个孱弱的早产儿,然而,它毕竟领到了身份证,毕竟显示着一种倾向与潮流,毕竟陈述着一种价值取向和审美追求。这样,我们就有必要审视一下它张扬的文学主张及经过理论家们阐释的创作主体意旨。王干同志在分析新写实小说的表现特点时,说了一段最具代表性的话:“他们用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面对现实,诉说世界的原生态。具体地说,就是作家把自己创作的情感降低到零度,以避免作家的主体情感和主体意向的干扰,对生活进行纯粹的客观还原,以最大程度地接近生活的真实性”(注:《近期小说的后现实主义倾向》,《北京文学》1989年第6期。)。
这话确有道理,作家们也都有此初衷。然而在纷纭复杂、矛盾丛生的社会中,真有所谓的感情零度吗?真有未经过政治道德意义符号了的事实,未经过作家主观情绪过滤了的事实吗?这无论从什么立场上观照,都难以成立。作为作家,他是社会中某一层面上的具体人,他有自己的生活现状、文化背景、审美情趣、创作心态,有自己的爱爱憎憎、好好恶恶,这种客观存在,使他无论采用什么物理降温法,感情也难以到达零度的操作状态。他的思想感情、审美判断总会渗透、折射在字里行间。换言之,倘若作家真达到了六根清静、心如古井的境界,那他还有渲泄情感、诉诸文字的表现欲吗?因此,说到家,零度的冷漠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一种参与、一种介入,作家从秉笔为文那一刻起,感情就已经开始升腾了。那种不介入客体情感,不进行憎恶与赞美的宣扬,只不过是作家巧妙的表现方法而已。
其实,选材本身就是一种态度。方方为什么在大千世界中把目光投向那肮肮脏脏的河南棚子?是那里人们贫穷困窘、恶性循环的生态使她怦然心动,思之再三;池莉又为什么在茫茫人海中瞄准了印家厚?是这个活得艰难、疲累的普通中国人让她感喟至极,夜不能寐。同样,在《塔铺》和《新兵连》中,寄托了刘震云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娓娓情思和深沉的思考;取材于过去年代中的《妻妾成群》,当然不只是无端讲述封建家庭争风吃醋、勾心斗角的种种手段;《伏羲伏羲》也决不是为了告诉你一个侄婶通奸的天方夜潭。那弦外之音、音外之旨是很难掩饰得了的。
同时,作家冷静地还原生活或逼真地描写生活细节,这本身也是态度。我们都难以忘怀《风景》中那令人心弦为之震颤的生活现状和细节描写。作家象外科医生一样解剖人的思想灵魂,展现人物心底潜层的隐私奥秘,揭示生存的压抑和变态,这当中,自然隐藏着作者的美学评判。《妻妾成群》中叙述的封建家庭妻妾争宠、尔虞我诈的故事,表面上作者无好无恶,其实他是在尽情地倾吐着对那些受到非人待遇的女性的深切同情。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精采的细节俯拾即是,哪一个不是作家的独特感受,哪一个没活跃着作家感情的杠杆?对生活的惋叹,对命运的冥想,无可奈何的两难心境,字里行间都流溢着作家的万千情愫。这样看来,感情的零度只不过是作者一种更为高妙、更为隐蔽的参与而已。
理想失落:薄暮时分的灰色王国
有人说,读新写实小说有一种直感,仿佛是在听够了洪钟大吕的英雄交响乐,那大弦嘈嘈之后奏起的小弦切切之语。这自然有一定道理,但我们却刻薄地认为,这些才华横溢的作家们弹奏的不是悠扬的小夜曲,而是失落了理想、失落了人生的咏叹,它使我们走进了薄暮时分的灰色王国,结识了那些充满世纪末情感的诸位公民。
理想,是烛照人类前行的火炬。远大的理想,对于健康的人生比什么都重要。遗憾的是,新写实小说没有点燃理想的火光,使人体验不到文学作品应有的牵引、振奋力量。作为芸芸众生相之集大成,新写实小说所描写的人物,大都是卑微、猥琐的俗人。他们崇尚实利精神,为活着而活着,浑浑噩噩如行尸走肉。油盐酱醋茶,父母老婆孩,生老病死,吃喝拉撒,是他们全部的生活内容。他们的生活情状,构成了作家抒写不尽的生命母题,并向人们宣示着对生命本体意义的了悟:人生是个走不出去的怪圈、围城,是个解析不清的“歌德巴赫猜想”。比如,印家厚的人生标尺只不过是定在丰衣足食、小有娱悦上;《新兵连》的新兵们争相攀爬,只是指望小有升迁,以离开黄土地;王腊狗呢,则将杀人报仇当作人生崇高的理想——因此,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审视,这些作品不啻是理想、信仰失落的哀歌。“从这些作品中很难感受到时代的主旋律,很难触摸到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宏伟历史脉搏,很难见识决定这个时代方向的为美好未来充满信心而战斗的人们,很难看到读者心灵为之燃烧,为之升华,不愧为民族脊梁的崇高刚强的人物性格。”(注:《“新写实”小说座谈辑录》,《文学评论》1991 年第3期。)确实,那些消极、被动、软弱,在困境中难以自拔的灰色人物,真的不能带给我们民族、时代以任何推动力!
理想的失落,使心灵世界充满了阴暗。新写实小说自诞生那天起,就营构了心灵与生活的灰色王国。在那里,人生陷入困境,生活充满苦难:困窘压抑、神秘诡谲、暴力凶杀、尔虞我诈、性格变态、情欲横流……无论是方方还是池莉,无论是刘恒还是刘震云,都抹掉了生活和心灵视界中的亮点,冷漠地展览人生或心灵的阴暗角落,以此揭示所谓的生活本色、原色和人类的生存本相。那些对当代生活的切入,对当代人生状态的剖析,那些对烟锁尘封历史的穿透,对封建积垢的展示,无不映射着灰色的光泽,无不隐喻着人生之旅不过是无目的的生活自耗的主题。平心而论,除我们这些有自娱能力的职业读者外,那些企望能从书中获取人生教益的人,会从中得到什么呢?肩负着庄严使命的作家,你们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
理想的失落,往往导致审美价值取向的倾斜。审美与审丑有着同样的终极目的。我们主张,审丑要特别注意掌握好“度”,以能真正满足当代中国人审美兴趣的心理欲求。然而部分新写实小说却偏离了正确的审美导向,近于毫不顾忌地揭示丑与恶(此时,不加感情色彩的冷静描写无异于助纣为虐)。那些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细节展示几近某些通俗小说,显得格外扎眼,如同在餐桌上落着个苍蝇。这些本应毫不留情地淘汰。鲁迅先生在几十年前就说过:“现在有些作品,往往若非必要而偏在对话里写上许多骂语去,好象以为非此便不是无产者作品,骂声越多,就越是无产者作品似的。”(注:《鲁迅文摘》第87页。)说得多么中肯!假如新写实小说跨过了这个误区,匡正了这个失误,甩掉负累,在不断的自我规范和探索中实现对当代小说的超越,那它或许能攀升到一个新的层面。
本文余论:尽快告别浮躁
综上,我们以为,对新写实小说的揠苗助长、热情催生,以及不适当的“炒作”、推销,造成了对小说创作的误导,更导致了整个小说创作的集体浮躁。自新写实“走红”以后,一些作家不在深入生活、感受人物上下功夫,而偏偏在追新逐奇什么主义上费脑筋;一些作家不去观照风雷激荡的现实生活,而专门去烟锁尘封的历史中寻找要炒的冷饭。今天新这个、明天新那个,看上去蓬蓬勃勃、热热闹闹,但平心而论,这些“新××”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新的套路呢?其主题、其艺术、其品位都使我们似曾相识,都不过是对老箱底的拆旧翻新。难怪人们慨叹与独立精神和创新意识的久违了,难怪人们对小说艺术越来越冷落和疏离了。
今天,当我们告别充满沧桑刻痕的20世纪,怀着挥之难去的祈盼情绪,回视十年来走过的道路时,我们的作家、评论家,也包括读者,是否应从新写实小说的来去匆匆感悟点什么呢?
尽快告别浮躁——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